您的购物车目前是空的!
序言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 1 章 政治的必需
第 2 章 自然状态
第 3 章 表亲的专横
第 4 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第 5 章“利维坦”的降临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 6 章 中国的部落制
第 7 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第 8 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第 9 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第 10 章 印度的弯路
第 11 章 瓦尔纳和迦提
第 12 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第 13 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第 14 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第 15 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第 16 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第三部分 法 治
第 17 章 法治的起源
第 18 章 教会变为国家
第 19 章 国家变为教会
第 20 章 东方专制主义
第 21 章“坐寇”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 22 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第 23 章 寻租者
第 24 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第 25 章 易北河以东
第 26 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第 27 章 征税和代表权
第 28 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 29 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第 30 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序言
本书有两个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请我为他 1968 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①亨廷顿的著作代表了从宏观角度论述政治发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要求学生阅读的。它在比较政治学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见解,包括政治衰败的理论、威权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是有别于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象等。
我在写新序时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很有启发,但确实需要认真的更新。它的成书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战后的世界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但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却取得成功。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订亨廷顿思想时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详细解说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的起源,还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其时,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制度(institutions,参见本书第 29 章“制度[机构]”一节的编者按)均已存在。它所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对制度起源的关心又与第二份担忧紧密吻合,即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就政府濒临崩溃或不稳的国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国家和民族构建的难题。与此有关的更早努力,是我在 2004 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 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②美国和广大的国际捐赠社区,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我本人也跟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接洽,观察包括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巴布亚省、所罗门群岛在内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国家建设问题。它们在建造现代国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难。
譬如,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亚社会,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该社会以人类学家所谓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体,其中的亲戚人数少至几十,多至数千。这些群体在本地被称为一语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词语“一种话语”的洋泾浜变种,即操同一语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分裂颇不寻常,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超过九百种互不通用的语言,几乎占世界现存语种的六分之一。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仅 50 万,却有超过七十种的独特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多数居民,从没离开过出生地的小峡谷,他们生活在一语部落内,与邻近的其他一语部落互相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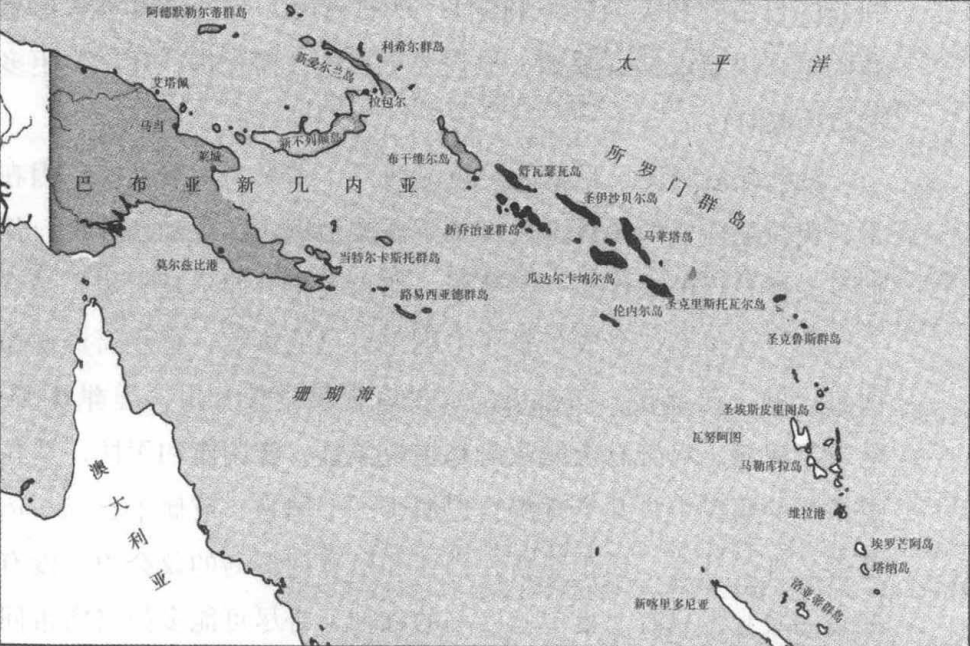
一语部落接受头人(Big Man)的指挥,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头人,也不能将之传给儿子。更确切地说,必须在每一代赢得该职。它不一定落在体力强壮者的头上,通常给赢得社区信任的人——以分配猪肉、贝壳货币和其他资源的能力为基础。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头人必须时时小心,因为权力觊觎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没有可供派分的资源,他就会失去其领袖地位。③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准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英国也承认所罗门群岛独立。它们都建立现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定期参加多党派的选举,以选出议会成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政治选择离不开中立偏左的工党和保守党(澳大利亚的自由党和英国的托利党)。总的来说,选民根据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决定取向(譬如,他们要更多的政府保护,还是要更多的市场取向)。
但这种政治制度被植入美拉尼西亚后,结果却一片混乱。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亚多数选民投票不看政治纲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支持自己的头人和一语部落。如果头人(偶尔是女头人)被选入议会,这位新议会成员将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将政府资源搬回自己的一语部落,向自己的拥护者提供学校费用、埋葬开支、建筑工程等。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象征,如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④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它阻止现代产权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 以上的土地属于所谓的惯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据惯例的规则,财产是私有的,由亲戚团体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说没有法律文件)一起拥有。他们对土地享有单独和集体的权利,地产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因为死去的亲戚都葬于一语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语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头人,都无权将土地卖与外人。⑤寻觅地产的开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必须与数百人谈判,有时甚至是数千人。此外,根据传统规则,土地产权不受时效法律的限制。⑥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亚政治家的行为看来像政治腐败。但从传统部落社会的角度看,头人只是在履行头人历来的职责,那就是向亲戚分发资源。只是现在,他们不但拥有猪肉和贝壳货币,而且享有开矿和伐木权利的收入。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起飞,几小时就可抵达澳大利亚的凯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航程跨越了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政治发展时,我开始考虑:社会如何从部落层次过渡到国家层次,现代产权如何从惯例产权中脱颖而出,倚靠第三方执法的正规法律制度如何问世。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远,认为现代社会已远远超越美拉尼西亚,依我看来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为头人——将资源派分给亲戚和拥护者的政治家——在当代世界依然到处可见,包括美国国会。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关答案,这段历史需要认真的梳理,以重温亨廷顿的主题。
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败的过程。这是两卷中的第 1 卷,涵盖从前人类时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发展。本书与过去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始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它的前四个部分讲述人类史前史、国家起源、法治、负责制政府。第 2 卷会一直讲到今天,特别关注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化时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然后再解说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
阅读本卷时需要预先掂量第 2 卷的内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讲得很清楚,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与 18 世纪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工业革命发轫后,人类社会退出了直到那时一直所身历的马尔萨斯式处境(Malthusian conditions),一种新动力被注入社会变化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
本书涵盖众多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也使用自己专长之外的资料,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等。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尽管我尝试让这些资料承受尽可能严密的专家过滤,但我仍可能犯了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对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专家来说,本书很多单独章节是不够格的。但我认为,以比较方式作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美德。若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 1 章 政治的必需
第三波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我们视各式制度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 年到 2010 年的 40 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1973 年,世界 151 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 45 个。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①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统”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们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约有 120 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 60%——成为民主制。②这一变化,即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 21 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③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的,是社会的一大转型。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达到顶峰。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④自由之家提及,2009 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其自 1973 年创办自由度测评以来的首次。⑤
政治焦虑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状。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⑥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乌克兰就是一个案例。2004 年,它给世人带来惊奇,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引发新一轮选举,导致改革家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当上总统。然而一旦当权,橙色联盟却一无是处,尤先科辜负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内部争吵不已,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在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2010 年初,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而 2004 年被指控操纵选票、企图窃取选举成果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与其说是不稳定的起因,倒不如说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觉得,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他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帮会、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会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 1947 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员的广袤,此成就尤为惊人。(如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 10—12 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责任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主的印度。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 1800 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⑦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 年是亚洲,1998—1999 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 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 2008—2009 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⑧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他国家的地位,如中国,则获得相对拔高。⑨
这些挑战,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挑战的艰巨。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偏向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 10% 或更少选票当选的国会议员席位,19 世纪末仍有将近 200 名,持续下降至 21 世纪初,仅剩 50 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⑩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
美国政治的未来,不仅依赖政治,而且依赖社会。国会的两极化反映了一大趋势,即美国的社区和地域正在日益同质化。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⑪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⑫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能力。工会、农产企业、制药公司、银行、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经常对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决权。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美国人抱怨美国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⑬不均本身,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美国强调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如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那么如此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在事实上,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作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他发达国家。⑭日积月累,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来避税,通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将优势传给下一代。该伎俩的大部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人们痛苦地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联。该行业动用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前十年想方设法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仍在继续抵抗新的管制。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指出,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类似团体,如俄罗斯或印尼。⑮
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应不良,即政治衰败的现象,会在本卷的后半部得到详细介绍。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较早接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做了。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制度的巨大惯性。
社会如不能通过制度上的认真改革,以应付重大的财政危机,像法兰西国王在 1557 年无力偿还“大借款”(Grand Parti,编按:此指 1555 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为支付战争开销,向里昂银行家大举借贷一事)后所做的,它就会倾向于采取短视的补救,最终却腐化自己的制度。这些补救屈服于各种既得利益者,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国家预算不平衡,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非法化,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危险的是,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直到某种强大力量彻底打破这当前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
无政府幻想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退回威权、印度腐败、发展中国家政府衰败、当代美国政治受制于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 21 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我认为,当前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思想对政治秩序极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础,它能够凝聚人心,并使民众愿意服从政府的权威。柏林墙的倒塌标志共产主义的破产,共产主义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为被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获得快速的蔓延。
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说,民主制仍是“预设”:“民主尚未获得普遍的实践,甚至未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⑯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石油民族主义、乌戈·查韦斯的“21 世纪社会主义”、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但它的威权主义模式,不易解释清楚,更少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来称颂民主制。
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很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预测广为人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 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学者,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⑰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党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力的国家机器,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动家。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集权政府。⑱这些活动家随后对无情的现实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来说,却不一定感到满意。⑲
右派中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认为,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20 世纪 90 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参照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利斯坦(Walter Wriston)的口吻,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主权的黄昏”。⑳新兴的信息技术在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使规则难以执行。互联网的上升,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约翰·巴洛(John Barlow)等活跃分子发布“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在我们中间,你们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㉑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取代民主制的主权。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限制贸易,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最后还是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㉒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就是对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甚至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样的基本机构。㉓
认为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因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风冷漠、政客腐败、政治中不讲原则,也绝对正确。但在发达国家,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致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还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当作理所当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结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的填补,无须担心在坑洼里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如没有填补,费尔法克斯县的居民会变得愤怒,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无能。没人(除了政府专家)停下来思忖哪个政府部门在尽此职责。它复杂,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没人停下来问,为何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却需要较长时间来填补坑洼,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不填补它们道路上的坑洼。
实际上,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 30%,部分欧洲国家占 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自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但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法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㉔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制度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来源。
达到丹麦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问题,常被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迈克尔·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㉕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丹麦”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度。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将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转化成“丹麦”。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尝试帮助落后国家来“达到丹麦”的水平。
这个想法,问题多多。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立起复杂制度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制度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此外,制度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谁也不清楚。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达到丹麦”的——甚至对于很多丹麦人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致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罹患了历史健忘症。
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一个很凶悍的部落,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率先定居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征服他们的罗马人、取代罗马人的日耳曼蛮族,起初都组成部落,像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存的那些部落一样。中国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有过同样经历。他们尽的主要义务,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宗族;他们解决争端,不通过法庭,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他们把死者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发展出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央集权,在固定领土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和平得到维持,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它们成为常备力量,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保护自己的社区。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而为个人所拥有,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产权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补偿损失。
日积月累,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这些正式规则,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换言之,制度替代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他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负责。传统的君主制,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征求非正式的咨询。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让自己的统治权臣服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坠地。
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刚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 2004 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制度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制度的出现,我们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制度很“黏糊”;这是指,它们长期延续,只有经受了重大的艰辛,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会继续向公民提供所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主义(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强大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久而久之,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设“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制度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个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国为中心。它可能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再到 1776 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会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群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制度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制度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都侧重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说,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作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制度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卷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备战和参战,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 2 卷中讨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 1 卷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天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本卷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种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既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楷模。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注重西方不难理解。1800 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卷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制度的进化。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 3 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探询其他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他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中南美洲。在此还需要作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卷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 4 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亲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在第 2 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 1 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 18 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底下无数龟
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㉖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㉗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 19 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 28—30 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第 2 章 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的哲学讨论;现代生命科学彰显人性和政治的生物学基础;黑猩猩和灵长目中的政治;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人类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学传统中对“自然状态”的讨论,一直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而正义和政治秩序,又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古典政治哲学把天性和惯例(或称法律)截然分开。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张,合理城邦必须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昙花一现和不断变化的人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给予这差别以进一步的拓展。他们撰写有关自然状态的论文,试图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石。讨论自然状态,其实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用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养的各级人性美德(a hierarchy of human goods)。
但在一个关键命题上,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卢梭泾渭分明。他主张,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赋使之在社会中兴旺发达。而这三位早期现代的哲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争辩说,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只是一种手段,使人类得以实现单凭个人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在罗列人类的自然激情后主张,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他由此演绎,大家享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这就是基本自然权。人性中有三项诱发争端的特征:竞争、畏葸(害怕)、荣誉;“第一项,诱发人类侵略以获好处;第二项,以获安全;第三项,以获荣誉”。因此,自然状态被描绘成“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为逃离这一危险处境,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国家,也就是利维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来保障他们天生拥有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政府,也就是利维坦,借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①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对自然状态的观念,比霍布斯的温和。他认为,人类所忙碌的,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以生产私人财产,而不是彼此打斗。洛克的基本自然法,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权,还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财产”。②依照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受节制的自由会引发战争;为保护自然的自由和财产,社会契约便成为必要。依照洛克,国家虽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为自然权利的褫夺者。所以他保留反抗不公正权威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追寻幸福之权,直追霍布斯的天赋人权,再辅以洛克有关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的暴力的自然状态,与卢梭较和平的版本,一直是鲜明的对照。在霍布斯那里,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好几处公开批评霍布斯:“最重要的,让我们与霍布斯一起总结: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对善念一无所知;他品行不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他拒绝为同类做事,因为他自信不亏欠他们;他因此而理直气壮,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并愚蠢地视自己为整个宇宙的主人。”③卢梭认为,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出自然人,《利维坦》讲述的暴虐人,其实只是数世纪承受社会污染的产物。对卢梭而言,自然人虽很孤独,但却是胆小恐惧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战。野蛮人的“欲望,从不超越其物质需求;除了食物、配偶、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他财产”;他害怕疼痛和饥饿,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会的产生,不代表拯救于“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反而因相互依赖,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奴役。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门见山:“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不可当作历史真相,只算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历史叙述,倒不如说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
很清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推测其思想、激情、行为的长期进化。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评判观察动物所获得的论据,尝试弄清天生人与社会人的差别。自认懂得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总是很危险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所以,将之对照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包括灵长动物学、人口遗传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实证资料,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所得的结果,既确认他的部分洞察力,又对他的其他观察提出疑问。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们可借此来理解人类制度后来的进化。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私人财产的发展。但卢梭、霍布斯和洛克,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这三位思想家,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根据霍布斯,原始人类的相处,主要表现为害怕、羡慕、冲突。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却不是;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如农业的技术发明,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出现,人与人相互妥协,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法律学家亨利·梅因,在 1861 年出版的《古代法》中,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
这两种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的),将英国的严肃政治家长期分裂成敌对的两派。其相似处,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其分歧处,则有前社会状态的特征,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我们熟悉的,只是社会。但他们一致认为,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④
我们可将之称为霍布斯式谬误: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进入社会,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社会合作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支持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也支持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该假设更支持了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人类是理性的,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但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今天,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制度,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他比这些早期现代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
现代生物学,与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完全相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技巧;促进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暴力是自发的。实施暴力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人类并不因为自觉且理性的决定,而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环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了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
事实上,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亲戚选择(kin 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关于第一,生物进化的竞争,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种情形一再出现,以致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将之定为包容适存性原则(inclusive fitness)或亲戚选择。该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⑤父母和小孩,亲兄弟姐妹,分享 50% 的基因。他们之间的利他,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因为后者仅分享 25% 的基因。这种行为可见证于各类物种。譬如,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庶姐妹。就人类而言,现实世界的裙带关系,不仅基于社会缘由,更基于生物学缘由。⑥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
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这是亲戚选择之外,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也可见证于众多物种。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游戏(prisoner’s dilemma)。⑦在那些游戏中,如大家合作,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则可获益更多。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 Axelrod)组织了解答“囚徒困境”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优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用合作态度;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则采用拒绝态度。⑧艾克塞洛德以此论证,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道德可自发产生,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类之外,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他众多物种。⑨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在群居地喂养和保护伙伴的后代。⑩另一些情况中,就像清洁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狗和人之间的交往,显示了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⑪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进化生物学,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从灵长目先驱进化而来提供了宏大框架。我们知道,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人类分支出来,约在五百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约有 99% 的重叠,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他的一对。⑫(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别,那 1% 的偏离与语言、宗教、抽象思维等有关,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这一共同祖先的行为,但灵长学家花费很长时间,在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观察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发现它们与人类拥有明显的连贯性。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去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入自己的族团。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所观察到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ö Indian)。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进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⑬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
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Steven LeBlanc)的研究,“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在那个社会层次,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行战略之一,另外还有缓冲区域、突袭、收纳女俘、刑辱敌人。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几乎是彻底平行的”。⑭其主要差异,只是人类的更加致命,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其他方面又有很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来抚养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然而,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并不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一样,必须借建立同盟来赢得。体力虽然要紧,但最终还得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灵长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荷兰阿恩海姆动物园观察驯养的黑猩猩群体。他叙述两只年轻黑猩猩,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篡夺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并最终将之杀害。⑮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通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一系列短促的咕噜声,再加上深鞠躬;向上级伸手,亲吻上级的脚。⑯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妈妈(Mama),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巅峰时,甚至包括成年雄性在内的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我多次看到,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告终于她的手臂。冲突升到顶点时,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反而大声尖叫,奔向妈妈。”⑰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不是直截了当的,需要有评判他人品质的能力。像人一样,黑猩猩擅长欺骗,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海姆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有的比其他的更可信赖。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或假装和解,等其他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动。由于这些行为,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远离她。⑱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一位名叫伊冯的研究生,与一只名叫可可(Choco)的年轻黑猩猩同住:
可可变得益加淘气,该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骂。这顿责骂似乎蛮有效果,伊冯便坐上沙发,开始读书。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嘴唇敞开)。⑲
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
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生活在狩猎采集或其他相对原始的社会中的,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成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从头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应是: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
唯独人类
将人类与类人猿祖先分开的 1% 染色体,还含有什么?我们的智力和认知力,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我们给人类的标签是智人(Homo sapiens),即人属(Homo)中“有智慧的”。人类自类人猿祖先分支出来,已有五百万年。其间,人类的脑容量翻了三倍,这在进化史上是异常神速的。不断增大的女人产婴通道,勉强跟上人类婴儿硕大头颅的需求。那么,这认知力又来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类似乎需要认知力来适应和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更高的智力,为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和适应苛刻气候等提供优势。但这一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很多其他物种,也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却没能获得类似人类认知的能力。
很多进化生物学家推测,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为了与人合作,是为了与人竞争。心理学家尼古拉·韩福瑞(Nicolas 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分别表明,人类实际上走进一场相互的军火竞赛;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⑳
前文提及的博弈论表明,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愿意与诚实可靠者合作,避开机会主义者。但要行之有效,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并揣测动机,以测将来。这颇不容易,因为潜在合作者的标记,只是诚实外表,而不是诚实本身。譬如,依照经验你似乎是诚实的,我愿意与你携手合作;但如果在过去,你只是在故意积累信任,将来,你就能从我这里骗得更大好处。所以,自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也鼓励了欺瞒、行骗和其他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黑猩猩能达到数十成员的社会族团层次,因为它们拥有所要求的认知技术来解答基本的“囚徒困境”游戏。如阿恩海姆动物园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历史,而遭遇其他黑猩猩的回避;“妈妈”取得领袖地位,因她调停纠纷时公正的声誉。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领袖与合作遂得到发展。
但黑猩猩无法迈进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和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的雄性资源。这两种战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认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㉑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语言、社交能力、掌控环境都在相互加强,为精益求精而施加进化压力。㉒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它恰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所独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是找不到的。㉓
语言的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词语可指具体物件,也可指物件的类别(狗群和树丛),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引力)。综合两者,便使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成为可能——那是指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因为太阳发光,所以变得温暖”;“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心智模型。这样的推论能力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尽管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无数一年级统计学的教授一再告诫,关联不表示因果,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以推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毒死你表亲的草根,你将免遭同样命运,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这就是宗教出现的基础。宗教——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很不幸,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的线索,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并有考古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也可能有宗教信仰。㉔
今天有人主张,宗教是暴力、冲突、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㉕但在历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的角色,它是凝聚社会的源泉。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简单、理性、自私的参与者。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广泛更安全。据我们所知,彼此一起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参与者,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但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显示,随着合作群体的逐渐扩展,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在庞大群体中,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乘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变得司空见惯。㉖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通过奖罚而大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我认为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如我相信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我会对他更加尊崇。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我的羞耻感可能更大。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我也不愿承担风险,万一这是真的呢?根据“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因为他可能存在。这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适用,虽然在早期怀疑者可能会更少。㉗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㉘“一报还一报”(tit-for-tat),即以牙还牙和报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这条黄金定律只是“一报还一报”的异体。它只是强调善,不讲恶罢了。(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人们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会,它也很少付诸实施。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把以怨报德当作其群体的道德准则。)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是人类天生偏爱宗教的原因。㉙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宗教不是唯一方式——今天,我们有民族主义,还有世俗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社会,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宗教,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㉚
从认知观点出发,可把任何宗教信仰称作现实世界的心智模型。它们把因果关系,归因于日常世界之外的无形力量,归因于形而上的王国。改造自然界的理论由此而生。例如,神的愤怒造成干旱,把婴儿血洒入大地的犁沟,便可使之平息。之后,它又导向礼仪,即有关超自然秩序的重复表演。人类社会希望借此来获得对环境的主导。
礼仪反过来又帮助区分群体,标记边界,使之有别于其他群体。它促进社会团结,最终会脱节于导致其产生的认知理论。譬如当代世俗欧洲人,仍继续庆祝圣诞节。礼仪本身和支撑它的信念,会被赋予极大的内在价值。它不再代表心智模型,不再是遇上更好选择时可随意抛弃的普通理论,而变成目的本身。
红脸野兽
促使人类合作和存活的心智模型和规范,产生时可能是理性的,恰似经济学家所说明的。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即便证明有错,也从来不是可弃之如敝屣的简单理论。它被视作无条件的真理,如指控其谬误,会受到社会和心理的沉重惩罚。现代自然科学带来的认知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实验模式,允许我们更好地改造环境(如使用灌溉系统,而不是人的血祭,来提高农业生产力)。这里有个疑问:人类为何忍受如此僵硬难改的理论构思?
基本正确的答案是: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人脑培养了情绪反应,犹如自动导航装置,以促进社会行为。喂奶的母亲看到婴儿,便会分泌乳汁。不是因为她清楚想到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而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她大脑产生荷尔蒙,诱发了乳腺分泌。对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对无缘无故的伤害表示愤怒,这不是精心考虑的反应,也不一定是学来的情感(尽管通过实践,这些感受会获得加强或受到抑制)。同样,当有人表示不敬,在朋友前蔑视我们,或评论我们母亲或姐妹的德行,我们不会核算评论的精确度,也不会考虑为未来交往而保护声誉,我们只是感到愤怒,只想痛揍这不尊重他人的家伙。这些行为——对亲戚的利他主义,捍卫自己的声誉——可用理性的自利来解释,但却是在情绪状态下作出的。一般情况下,情绪化的反应却是理性的正确答复。为什么?这是进化的安排。行动经常是情感的产品,而不是计算的产品。所以我们经常弄错,打了更强壮、更会报复的人。
这种情绪化反应,使人类中规中矩,遵循规范。规范的独特内容由文化决定(不吃猪肉、尊敬祖先、宴会上不点香烟),遵循规范的能力却是遗传的。同样,语言因文化而异,但都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例如,在违反规范和他人都遵守的规则时被人看到,大家都会觉得困窘。很明显,困窘不是学来的举止,因为小孩通常比父母更易觉得困窘,即使是小小过失。人类能将自己置于他人位置,并通过他人眼睛观察自己的行为。今天的小孩,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诊断为具有自闭症的病理征兆。
通过愤怒、可耻、有罪、骄傲的特殊情感,遵循规范的习惯得以嵌入人性。规范受到侵犯时,如陌生人费尽心思羞辱我们或团体分享的宗教礼仪受到嘲笑或忽视,我们会感到愤怒。无法跟上规范时,我们会感到耻辱。取得大家赞许的目标,从而获得群体的称赞,我们会感到骄傲。人类在遵循规范中,投入这么多情感,以致失去理性,危害自身的利益。帮派成员因受到侮辱(实际上的或想象的),而向另外帮派的成员施以报复,但心里很清楚,这将导致暴力的逐步升级。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metanorm),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如果后设规范得不到妥善的遵循,人类会发起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称的“说教型进攻”。㉛某命案的结局与自己利益毫不相关,但人们仍想看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解释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戏剧为什么特受欢迎,还解释了人们对巨大丑闻和罪行为什么着迷关注。
规范化行为植根于情感。它促进社会合作,明显提供生存优势,协助人类进化至今。经济学家主张,盲目遵守规则在经济上却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计算得失,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和适得其反。如必须跟伙伴不时谈判新规则,我们会陷入瘫痪,无法从事例行的集体行动。我们把某些规则当作目标本身,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大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宗教进一步加强这种稳定,并扩充潜在合作者的圈子。
这在政治上造成难题。很多案例中成效明显的规则,遇上短期的特殊情况,却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功能失调,因为导致其产生的情形有了大变。制度规则是很“黏糊”的,它抗拒改革,变成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
寻求承认的斗争
规范被赋予内在价值后,便成为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的目标。㉜寻求承认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经济行为中获得物质的欲望。承认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借此,个人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习俗、信念。我作为钢琴家或画家,可能很自信。如能获奖或售出画作,我会有更大的满足。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承认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寻求承认的斗争,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它是零和(zero sum),而不是正和(positive sum)。即某人获得承认,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地位只是相对的。在地位比赛中不存在贸易中的双赢情形。㉝
寻求承认的欲望有其生物学根源。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在各自的族团中,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凝聚成员,一致对外。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证繁衍成功。在包括人类的各种动物中,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serotonin),会获得大幅提高。㉞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其寻求的承认不同于灵长目。黑猩猩雄性老大只为自己寻求承认,而人类还为抽象概念寻求承认,如上帝、旗帜、圣地。当代政治的大部,以寻求承认为中心。对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者、土著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历史理由相信,自身价值从没得到重视。这些寻求可能有经济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并不是目标本身。㉟
我们今天把寻求承认称作“身份政治”。这类现象主要出现于流动且多元的社会,其成员可具多重身份。㊱甚至在现代世界出现之前,承认已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动机。人类奋斗,不仅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体,要求外人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上帝、传统。所采取的形式,有时是统治外人,更多时候是相反。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即避免隶属于不配的外人。犹太人三千多年前逃离埃及的奴役,以后每逢逾越节所庆祝的,就是此种自由。
承认现象的根本所在是裁决他人的内在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强迫的承认毫无意义,自由人的赞美远远胜过奴隶的卑从。群体钦佩某成员,因为他显示出彪悍、勇气、智慧、判决纠纷时的公平,政治领袖遂得以产生。政治可说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也是追随者的故事。大众甘做部属,愿意给予领袖更高地位。在凝聚且成功的群体中,部属地位是心甘情愿的,这基于领袖有权统治这一信念。
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认可自个人移至制度——转移到持续的规则或行为模式,像英国君主制或美国宪制。在这两个范例中,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以及合法统治所带来的权威。合法性意味着,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我们相信,当代社会的合法性,表现在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但在历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凝聚可源自自利,但光是自利不足以诱使追随者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生命。政治力量不仅是社会可掌控的公民人数和资源,也是对领袖和制度合法性的认可程度。
政治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构件来组建政治发展的理论。人类虽然自私,但却是理性的,如经济学家所称的为自利而学会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会性的既定途径,为人类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
- 包容适存性、亲戚选择、互惠利他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戚和互换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
-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关系,又偏爱在无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
-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理性。心智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常被赋予内在价值。
-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承认,或对自己的价值,或对自己的上帝、法律、习俗、生活方式。获得的承认成为合法的基础,合法本身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
这些自然特征是社会组织益加复杂的基础。包容适存性和互惠利他,不仅属于人类,也见于众多动物,为(主要是)亲戚小群体的合作作出了解释。人类初期的政治组织,很像在灵长目中看到的族团社会,如黑猩猩的。这可被认作社会组织的预设。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倾向,可通过新的规则和奖励加以克服。譬如,颁发规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种意义上,较高层次的制度则显得颇不自然,一旦崩溃,人类就会返回较早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我讲的家族制的基础。
人类以其抽象理论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环境和调节社会行为的新规则,远远超过黑猩猩中存在的规则。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他无形力量的观念,订下新规则和相应的奖励。不同种类的宗教大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并不断开发社会动员的新形式。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内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时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件。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是基本不变的。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人类社会分支蔓延,填补世界上多样的自然环境。他们在特定进化(specific evolution)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此外,各群体也在互动,在促进变化方面,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不相上下。
分隔甚远的社会,对政治秩序问题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多数社会随后发展了国家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方式。中国、中东、欧洲和印度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却发展出相似的制度,如中国、欧洲、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近年来,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只在实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会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
进化与迁移
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所谓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人(Homo 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往亚洲北部。三十至四十万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赫赫有名、散居多处的尼安德特人。㊲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开发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约在五万年前,这个其成员可能仅 150 人的群体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缺乏书面材料,但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 Y 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 DNA。Y 染色体归男性独有,余下的 DNA 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Y 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基本上完好无损。相比之下,线粒体 DNA 是陷入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数百万年前,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线粒体有它自己的 DNA,可与 Y 染色体媲美,由母亲单传给女儿,也基本上完好无损。Y 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的突变,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计算这些基因突变,弄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口遗传学家便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因为在中国、新几内亚、欧洲、南美洲,当地人口都可回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一个族团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进入现已不存的巽他大陆(Sunda,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和萨浩尔大陆(Sahul,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他们的迁移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冻成冰帽和冰川。与今日相比,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依据遗传定时法(genetic dating),我们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四万六千年。这表示,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仅花费不长时间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
其他族团离开阿拉伯半岛后,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前者经过近东和中亚,最终抵达欧洲。在那里,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约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已有人抵达智利南部。㊳ 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圣经故事称,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驱散到各地,令他们讲不同语言。在比喻意义上,这确是真相。人类迁移到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发明新的社会制度,开始退出自然状态。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起初的复杂社会组织,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其出现全靠宗教思想的协助。
第 3 章 表亲的专横
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家庭或族团层次的社会向部落的过渡;介绍血统、宗族和其他人类学基本概念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 年)发表之后,涌现出大量涉及人类早期制度起源的理论。首先在 19 世纪末,新兴人类学的首创者,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收集积累了尚存原始社会的实证资料。①摩尔根对日益减少的北美洲土著进行实地勘察,发明了解释其亲戚关系的详尽分类,并将此推及欧洲的史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阶段——野性、野蛮、文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须一一经历这三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读了摩尔根的书,运用该美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出私人财产和家庭的起源理论,之后变成共产世界的福音。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部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在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 1859 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在 20 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③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欧洲之外社会的发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滞不前。达尔文之后,进化理论在辩护当时的殖民秩序上确实取得成功。全球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北欧人,通过黄色和棕色皮肤的深浅不同,一直降至身处底部的黑色非洲人。④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 20 世纪 20 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部门。优秀的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他在一项著名研究中,以移民头颅大小的实证资料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因于种族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环境和文化的产物。博厄斯还认为,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认为,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⑤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把文化人类学科继续引向非评判性的、相对的、绝无进化的方向。
早期的进化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存有其他问题。它们的社会形式,往往是相对直线的,有严谨的等级,前阶段必须早于后阶段,某元素(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对尚存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借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亲戚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由文化的比较研究总结出真正的普遍规律。发现了违反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冷僻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感到兴奋。但这并不表示,不同社会中没有进化形式中的规则性和同类性。
史前阶段
以 19 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背景,博厄斯派的文化相对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比较人类学的领域里,留下了政治上求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持久遗产。严格的文化相对论,有悖于进化论,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厘清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并确定后一层次取代前一层次的原因。人类社会随时间而进化,这是显而易见的。生物进化的两个基本组件——变化和选择——也适合人类社会。即使我们细心避免后期文明“高于”前期文明的评判,但它们确实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强大。因应成功的文明,常常战胜因应不成功的,恰似个体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我们继续使用“发展中”或“开发”的名词(如“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佐证了下列共识:现存的富裕国家是上一阶段社会经济进化的结果,贫穷国家如有可能,也将参与这一进化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政治制度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与借基因的生物进化相比,则面对更多的悉心设计。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竞争,仍有很明显的类似。
这一新认可导致了进化理论在 20 世纪中期的复兴。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⑥、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⑦、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⑧、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⑨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⑩认为,各式社会在复杂、规模、能源使用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升级。⑪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人类群体都经历所谓的“特别进化”,以适应他们所占居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便是社会形式的多样化。对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不同社会往往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汇的“普遍进化”在生效。⑫
人类学家的难题是,没人能直接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早期模式发展到较复杂的部落或国家。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假设现存的狩猎采集或部落社会是早期模式的实例,再通过观察其行为来推测引发变化的力量,如部落何以演变为国家。可能是基于此,对早期社会进化的推理,已从人类学移至考古学。不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可通过不同文明在数十万年间留下的物质记录,追踪其社会活力的伸张。例如,考古学家调查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住宅和饮食的改变,得以了解战争和环境压力对社会组织的改造。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缺乏民族学研究的丰富细节。太依赖考古学记录,会导致对唯物主义解释的偏爱,因为史前文明的精神和认知世界,其大部已永远丢失。⑬
泰勒、摩尔根、恩格斯之后,对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的分类系统,也经历了自身的进化。放弃了具强烈道德色彩的词句,如“野性”和“野蛮”,而改用中性的描述,如点明主要技术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另一系统则点明主要的生产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工业社会。进化人类学家,以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来排列阶段。这是我在此所选用的,也是我的主题。埃尔曼·塞维斯发明了四个层次的分类,即族团、部落、酋邦、国家。族团和部落中⑭,社会组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对平等。相比之下,酋邦和国家等级分明,不以亲戚关系而以领土为基础来行使权力。
家庭和族团层次的组织
很多人相信,原始人类社会组织是部落的,这一见解可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如努马·丹尼斯·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和亨利·梅因,认为要在复杂的亲戚团体中去理解早期的社会生活。⑮但部落组织的兴起,要到九千年前定居社会和农业出现时。这之前,狩猎采集社会历时数万年,由类似灵长目族团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这样的社会,至今尚存于合适的边缘环境,如爱斯基摩人、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洲的土著。⑯(也有例外,如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属狩猎采集者,却生活于可支撑复杂社会的富饶区域。)
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农业的兴起,他在这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出现农业之前的族团层次社会,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私人财产。就像黑猩猩的族团,狩猎采集者居住于他们守卫的领土,偶尔为之争斗。但他们不像农人,犯不上在一块土地上设立标志,说“这是我的”。如有其他族团前来侵犯,或有危险猎食者渗入,由于人疏地广,族团层次的社会有移居他方的选择。他们较少拥有像已开垦的耕地、房子等投资。⑰
族团层次的内部,类似现代经济交易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阶段没有国家暴政,更确切地说,人类只体验到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所称的“表亲的专横”。⑱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亲戚,他们决定你做什么,跟谁结婚,怎样敬拜,还有其他一切。家庭或数户家庭合在一起打猎和采集。特别是打猎,与分享直接有关,因为那时没有储存肉类的技术,猎到的动物必须马上吃掉。进化心理学家纷纷推测,现代流行的进餐分享(圣诞节、感恩节、逾越节),都起源于长达数千年的猎物分享传统。⑲此类社会中,大多数的道德规则不是针对偷人财产者,而是针对不愿与人分享者。在永久匮乏的阴影下,拒绝分享往往影响到族团的生存。
族团层次的社会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别仅在年龄和性别上。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族团内,家庭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别,没有永久领袖,也没有等级制度。个人因突出的品质,如力大、智慧、可信,而被授予领袖地位。但该地位是流动的,很容易移至他人。除了父母和孩子,强制的机会非常有限。如弗莱德所说:
简易平等社会的民族学研究中,很难找到某人要求他人“做这做那”的案例,却充满了某人说“如能完成此事,那真太好了”之类的话语。之后他人可能照办,也可能不予理睬……因为领袖无法迫使他人。在我们的叙述中,领袖扮演的角色只牵涉权威,无关乎权力。⑳
此类社会中,领袖因群体的共识而浮现。但他们没有职权,不能传予子孙。没有集中的强制力量,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㉑
族团层次的社会围绕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类学家所称的异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女人嫁出自己的社会群体,搬到丈夫的居所。这种习惯鼓励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基因的多样化,创造群体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异族通婚也在减轻冲突中发挥作用。群体之间有关资源或领土的争议,可通过女人的交换而获得谅解,就像欧洲君主为政治目标而安排的战略性联姻。㉒群体的成员组成,与之后的部落社会相比,则更为流动:“任何地域的食物来源,不管是派尤特人(Pauite)的松果或野草籽的丰收,冬春猎场上海豹的数量,还是中部爱斯基摩人在内陆峡谷遇上驯鹿群的迁移,都是不可预测的,且分布太疏,以致任何一代的亲戚,即使想组成凝聚排外的群体,也屡屡遭挫。因为生态机遇时时在诱惑个人和家庭采取机会主义。”㉓
从族团到部落
农业的发展,使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变得可行。九千到一万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农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大洋洲、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冲积流域。野草和种子的驯化逐一发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繁密,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埃斯特·博塞鲁普(Ester Boserup)认为,这样讲是因果颠倒了。㉔无论如何,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0.1 到 1 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 40 到 60 人。㉕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次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分支”一词来解释由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成的社会,如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但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大批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产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支式社会中,每个“支系”都是自给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㉖各支系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支系。
部落社会里,支系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其最基本单位是宗族,成员们可追溯到好几代之前一名共同老祖宗。人类学家使用的术语中,后裔可以是单传(unilineal),也可是双传(cognatic)。单传系统中,后裔追随父亲,被标为父系;追随母亲,被标为母系。双传系统中,后裔可追随父母双方。稍作思考便可明白,分支式社会只能是单传。为了避免支系的重叠,每名小孩只可分给一个后裔群,或是父亲的,或是母亲的。
在中国、印度、中东、非洲、大洋洲、希腊、罗马曾经流行的宗族组织是父系家族。它是最普遍的,也存在于战胜欧洲的野蛮部落。罗马人称之为 agnatio(族亲),人类学家遂称之为 aganation。父系家族只追踪男性的血脉。女人结婚时,便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丈夫家族。中国和印度的男系家族制度中,女人几乎彻底切断与自己家族的联系。所以,婚姻之日变成妻子的父母悲伤时,只能在女儿的聘礼上获求补偿。女人在丈夫家里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其时,她彻底融入丈夫的宗族组织,在她丈夫的祖先坟前祷告祭祀,保障儿子将来的遗产。
父系家族虽是最普遍,但不是单传的唯一形式。在母系社会里,后裔和遗产追随母亲家族。母系社会(matrilineal)不同于女性掌权得以支配男性的女家长社会(matriarchal)。似乎没有证据显示,真正的女家长社会真有存在。母系社会仅表示,结婚时是男子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妻子的家族;权力和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男子手中;家庭中的权威人士通常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孩子的生父。㉗母系社会远比父系社会罕见,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亚、东南亚、美国西南部、非洲。埃尔曼·塞维斯指出,它们通常建立于特殊环境,如依靠女人劳作的雨林园艺区域。但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的霍皮人(Hopi),也是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㉘
宗族有个神奇的特点,只要追溯到更早祖先,便能进入更为庞大的宗族组织。例如,我是追溯到我爷爷的小宗族成员,邻人的爷爷便是外人。如作进一步的追溯,到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早,我们两个宗族又找到亲戚关系。如情况合适,大家就有可能携手合作。
此类社会的经典描述是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Nuer)的研究,他的著作《努尔人》为数代人类学的学生所必读。㉙努尔人是居住在苏丹南方养牛的游牧民族。20 世纪末,他们和传统对手的丁卡人(Dinka)联合起来,在约翰·加朗(John Garang)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向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展开长期斗争,以争取南方独立。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进行实地考察时,苏丹仍是英国殖民地,努尔人和丁卡人仍生活在传统中。
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部落是分支式的。我们把最大的支系,称之为主要部落。它再一步步分割成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部落……第三层次由数个村庄组成,其居民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和家庭的关系”。㉚
努尔人的宗族组织彼此经常打架,通常是为了在他们文化中占中心地位的牛。同一层次内,血统之间互相打斗。但他们又能联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作战。到了最高层,全体努尔人同仇敌忾,向以同样方法组织起来的丁卡人开战。埃文斯—普理查德解释说:
每个支系,本身也是可分的,其成员互相存有敌意。为反对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支系的成员会联合起来;为反对更高层次的支系,又会与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联合起来。努尔人以政治价值来解释这些联合原则,他们会说:如果娄(Lou)部落的郎(Leng)第三层次支系与努阿克瓦科(Nyarkwac)第三层次支系打仗——事实上,两支系之间战事频频——组成这两支系的各个村庄都会参战;如果努阿克瓦科第三层次支系与鲁莫乔科(Rumjok)第二层次支系发生争执——不久前,为了用水——郎和努阿克瓦科将团结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鲁莫乔科。鲁莫乔科也将组成其各支系的联盟。㉛
各支系能在较高的层次汇总。一旦联合的原因(如外部威胁)消失,它们又倾向于迅速瓦解。可在众多不同的部落社会中,看到多层次的支系。它体现在阿拉伯的谚语中:“我针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针对我表亲、我和我表亲针对陌生人。”
努尔人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没有制度化的领导等级。像族团层次的社会,努尔人社会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间有分工,宗族之内有分代的年龄级别。所谓的豹皮酋长,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帮助解决成员的冲突,但没有强迫他人的权力。“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说,努尔人酋长是神圣的人,但这神圣并没给他们带来特殊场合之外的权力。我从未看到,努尔人特别尊敬酋长,或在谈话中把他们当作重要人物。”㉜
努尔人是分支世系组织获得充分发展的范例,其宗族系谱的规则严格决定社会的结构和地位。其他的部落社会,则更为松散。共同老祖宗,与其说是严格的亲戚规定,倒不如说是建立社会义务的借口。甚至在努尔人中,仍有可能把陌生人带入宗族,视之为亲戚(人类学家称之为虚拟的亲戚关系)。很多时候,亲戚关系只是政治联盟的事后理由,并非构建社团的原动力。中国的宗族往往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整个村庄使用同样的姓,这显示中国亲戚关系的假想和包容。当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把自己称作“家庭”时,它的血誓仅是血亲的象征。现代的种族划分,把共同老祖宗推到很远,使宗族系谱的追溯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把肯尼亚的卡冷金(Kalenjin)或基库尤(Kikuyus)称作部落,该称呼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他们各自的人数,少至数十万,多至数百万。㉝
祖先和宗教
实际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自然的情形,或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弄不清,为什么你想与四圈之外的表亲合作,而不愿与非亲的熟人合作。难道,这只是因为你与表亲分享了六十四分之一的基因。动物不这样做,族团层次的人也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对死去祖先的崇拜开始于族团层次社会,每个族团内都会有巫师或宗教人,专司与死去祖先联络的工作。随着宗族的发展,宗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建制化,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制度,如领导权和产权。相信死去祖先对活人的作用,才是凝聚部落社会的动力,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本能。
19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提供了有关祖先崇拜的最著名描述之一。他的《古代城市》初版于 1864 年,给数代欧洲人带来启示。欧洲人习惯于把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与奥林匹克的众神挂起钩来。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则揭示更古老的宗教传统,其他印欧群体,包括移居印度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也在遵循这一古老传统。他认为,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死者的灵魂并不飞上天国,却住在葬地的底下。基于此,“他们总是陪葬他们认为死者需要的东西——服装、器皿、武器。他们在他坟上倒酒以解渴,放置食物以充饥。他们殉葬马匹和奴隶,认为这些生命将在坟里为死者继续服务,就像生前一样”。㉞死者的精灵——拉丁文是 manes——需要在世的亲戚不断的维持,定期供上食物和饮料,免得他们发怒。
在最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中,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知识领域远远超出欧洲史。他注意到,灵魂转世(死时灵魂进入另一肉体)和婆罗门宗教的兴起之前,印度教徒奉行类似希腊罗马的祖先崇拜。亨利·梅因也强调这一点,他认为,祖先崇拜“影响着自称为印度教徒的大多数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多数人的眼中,自己家神比整个印度万神庙更为重要”。㉟假如库朗日的知识领域涉及更远,他很有可能发现古代中国相似的葬礼。那里,崇高地位人士的墓穴填满了青铜和陶瓷的三足鼎、食物、马、奴隶、计划陪伴死者的妾。㊱像希腊和罗马人,印度—雅利安人也在家里供养圣火。圣火代表家庭,永远不得熄灭,除非家族本身不复存在。㊲所有这些文化中,圣火被当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这里家庭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部落社会中,宗教生活和亲戚关系紧密相连。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个社群都崇拜的神。你只对自己祖先有责任,对你邻居或酋长的祖先则没有责任。通常,祖先并不久远,不像所谓的罗马人祖先的罗慕路斯(Romulus)。祖先只是三或四代之前的人,家中老人可能还记得。㊳根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它丝毫不像基督教对圣徒的崇拜:“葬礼的礼仪只容最亲近的亲戚做虔诚表演……他们相信,祖先不会接受他人的奉献,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其死后照料他的灵魂。因此,结婚和育有男性后裔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形下,独身在早期希腊和罗马都是非法的。
这些信念的结果是,除了现存子女,每个人与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都有关联。裴达礼(Hugh Baker)这样解释中国的宗族关系,一条绳子代表血脉,“两端是无穷尽的,经过一把象征现在的剃刀。如果绳子遭到腰斩,两端就会自行掉离,绳子不复存在。如果一名男子死而无后,其祖先和后裔的连续体便跟着一起消亡……他的存在是必须的,因为他是整体的代表。除此之外,他又是无关紧要的”。㊴
部落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思想,对社会组织有极大影响。对先祖的信仰得以凝聚众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或族团层次。该“共同体”包括的,不仅是宗族、氏族、部落现有成员,而且是祖先和未来后裔的整条绳子。甚至最疏远的亲戚都会觉得,他们之间有牵连和职责。这种感受,借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礼仪,而获得加强。对如此的社会制度,成员不相信有选择的权力。说得确切些,他们的角色在出生之前已被社会预定。㊵
宗教和权力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 19 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可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人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无人目睹从族团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观念在后来历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观念。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族团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获得维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将在第 19 章看到,这就是基督教挺进野蛮欧洲后所发生的。随时间流逝,部落社会被更有弹性、更易扩张的社会所取代,但其缩了水的变种从未消失。
第 4 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第 4 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亲戚关系和产权发展;部落社会中正义的性质;部落社会作为军事组织;部落组织的优缺点
法国大革命以来,分隔左右两派的最大争议之一就是私人财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将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标为己产的首位男人。卡尔·马克思把废除私有财产定为政治目标,受他激励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所采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不单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国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论》第 10 篇中坚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护个人不均平的致富能力。①现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将私人产权视作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增长根本不会发生,除非现存经济组织是高效的”,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制度和产权”。②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发生了里根—撒切尔的革命。自那以后,市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其当务之急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虽然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
共产主义的经验,大大提升了现代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基于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剥削兴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意图恢复的理想国。摩尔根描述的惯例财产(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则强迫数百万无亲无故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化打破努力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摧毁对工作的奖励,在俄罗斯和中国造成大规模饥荒,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前苏联,仍在私人手中的 4% 土地,却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总产量。1978 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获得解散,农业产量仅在四年间就翻了一番。
私人财产重要性的争论,大都牵涉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传统英国村庄,其放牧地由村庄居民集体所拥有,共同使用。但其资源是可耗尽的,常因使用过度而荒芜。将共有财产转为私人财产是避免荒芜的对策。业主甘心投资于维护,在持续基础上开发资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著名文章认为,众多全球性的资源,如洁净空气和渔场等,都会遇上公地悲剧;如无私人产权或严格管理,将因过度消耗而变得一无用处。③
现代有关产权的非历史性讨论中,人们往往觉得,因为缺乏现代私人产权,人类一直面对公地悲剧。集体所有与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驰的。④现代产权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上的理性行为,人们讨价还价来分割共有财产,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从自然状态中脱颖而出。如此解释会遇上两个疑问。第一,现代产权出现之前,曾存在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虽未能像现代产权那样鼓励高效地使用,但也没导致类似的公地悲剧。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来证明,现代产权始于和平自发的讨价还价。共有财产让位于现代产权,其过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⑤
亲戚关系和私人财产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20 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逆转时光,进入想象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亲戚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把希腊和罗马人的家庭牵连到具体地产的有两样东西:屋内供圣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坟。渴望得到地产,不仅是为了它的生产潜力,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动的家灶。地产必须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国家才无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财产缺乏现代产权的重要特征,通常只是使用权(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⑥其主人不是单独的业主,而是现存和死去亲戚的整个社团。财产就像一种信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很多现代社会也有类似安排。20 世纪初,一名尼日利亚酋长说,“我想,地产属于一个大家庭,其成员中,很多已死,少数还活着,还有无数尚未出生的”。⑦地产和亲戚关系由此而紧密相连。它使你有能力照顾前世和后世的亲人,并通过与你休戚相关的祖先和后裔来照顾你本人。
沦为殖民地前的部分非洲,其亲戚团体受土地的束缚,因为他们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腊和罗马人。⑧西非的长期定居点则有不同形式的宗教运作。首批定居者的后裔,被指定为土地祭司来维持土地庙,并主持有关土地使用的各式礼仪。新移民不是通过买卖,而是通过加入当地礼仪社团,以取得土地使用权。社团把种植、狩猎、捕鱼权,当作社团会员的特权,但不是永久的。⑨
部落社会中,财产有时由部落集体拥有。历史人类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如此描绘凯尔特部落(Celtic),“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亲戚关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其地界往往与村庄边界不同,像蜘蛛网分布在不同定居点”。⑩集体拥有并不表示集体耕耘,像 20 世纪苏联或中国的集体农庄,个别家庭经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他情况下,个人可以拥有地产,但受严重限制,因为他有对亲戚的义务——活的、死的,还有未出生的。⑪你的土地挨着你表亲的,收获时互相合作,很难想象将你的土地卖给陌生人。如你死而无后,你的土地归还给亲戚团体,部落经常有权再分配地产。根据维诺格拉多夫,在印度的边界地区,战胜的部落在大块土地上定居下来,但没把土地划分给亲戚。有时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证明部落对土地的有效统治。⑫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戚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 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一语部落。⑬任何交易,部落中每个人都享有潜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效法律限制。因此,某亲戚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十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前被人偷走了。⑭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戚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将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⑮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丁叙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因议会圈地运动(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终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 和 19 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起初,敞田制与亲戚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⑯,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⑰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他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公地悲剧的纪录。⑱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畜牧而非农业,其规则略有不同。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护的坟墓,乃因追随牛群而要跋涉宽广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是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⑲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遭到过度开发。肯尼亚的图尔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⑳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认。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将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㉑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㉒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请酋长做代理人,不仅为了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统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亲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头人攫取权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㉓
法律和正义
部落社会只有软弱的中央权威——头人或酋长,因此,其强制他人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家。他们没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执法。维诺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会中的正义,有点像现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的主权决策者,有时互相谈判,有时全靠自助。㉔埃文斯—普理查德如此解说努尔人的正义:
血亲复仇是部落社会的规则,发生于违反法律之后,以获补偿。事实上,对血亲复仇的恐惧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惩罚,也是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主要保障……个人觉得受了损害,但投诉无门,无法得到赔偿。所以,他便向损害自己的人提出决斗,这一挑战必须获得接受。㉕
显而易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惩罚”都是泛指的,因为国家层次的法律与部落社会的正义很少存在关联。
然而,如何实施血亲复仇,又有一套规则。遇害努尔人的亲戚,可以追缉作案者和作案者的男性近亲,但不能碰作案者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母亲的姐妹,因为他们不是作案者的宗族成员。豹皮酋长会在中间调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寻求避难和遵循礼仪,以净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关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礼仪,以防冲突的扩大。例如,将伤害对方的矛送到受害者的村庄,以获魔法处理,从而避免伤口变得致命。豹皮酋长作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权威。他与被告村庄的其他长者一起,倾听对方的申述,但没权执行判决,就像无法执行现代国家之间判决的联合国仲裁人。仍以国际关系为例,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弱小的宗族很难从强大的宗族获得赔偿。㉖讨回公道的程度,则取决于争执双方出于自利的斟酌。大家都不愿看到,血亲复仇逐步升级,造成更多伤害。
实际上,所有部落社会都有寻求正义的相似规则:亲戚们有义务为受害者寻求报仇和赔偿;无约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帮助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各种犯罪相对称的赔偿表,北欧日耳曼部落将之称为赔偿金(wergeld)。《贝奥武夫》(Beowulf)传奇,就是一篇亲戚为遇害者寻求报仇或赔偿的英雄叙事长诗。不同的部落社会,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马斯河(Klamath)的印第安社会中,“尤罗克(Yurok)人如想提出诉求,就要雇用二、三或四名越界者(crosser)。他们是来自其他社团的非亲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这群人合在一起充当中间人,确定诉求和反驳,并收集证据。听过所有证据之后,越界者会作出赔偿裁决”。㉗像努尔人的豹皮酋长,越界者无权执行自己的判决,如当事人拒绝接受裁决,只能付诸排斥的威胁。部落男性同居于“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实,使之较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将来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伙伴的支持。因此,付出赔偿是得到鼓励的。㉘
同样,自 6 世纪克洛维一世(Clovis)时代以来,萨利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在日耳曼各部落中胜出,他们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也建立正义规则:“萨利族法兰克部落成员,如向邻居提出诉求,在传召对方时一定要遵循精确的程序。他必须前往对方居处,在其他目击者面前宣布自己的诉求,并定下对方出席司法聚会的日期。如被告不来,他必须数次重复如此的传召。”维诺格拉多夫总结说:“我们清楚看到部落社会司法的固有弱点:其法律裁决的执行,通常不靠最高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诉讼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说,这是部落社会在司法上批准和认可的自助。”㉙
第三方强制执行司法裁决,还必须等待国家的出现。但部落社会确实开发了愈益复杂的制度,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纠纷中提供妥当的裁决。部落法律通常不是书面的,但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赔偿额,仍需要监护人。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雷格曼一职(laghman),他是民选的法律专家,专门在审讯时发表有关法律规则的演讲。
民众聚会起源于部落纠纷的判决。《伊利亚特》(Iliad)有关阿喀琉斯护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节,就描述一场涉及被杀男子价格的争论,在市场的大庭广众面前发生,再由部落长者读出最后的裁决。讲个更具体的案例,执行萨利克法律的是条顿制度(Teutonic),称作百户法庭,由当地村民组成,即现代模拟法庭(moot court)的源头。百户法庭在露天开会,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户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选的,他主持实际上的仲裁法庭。亨利·梅因认为,“其主要功能是让热血有时间冷却,防止人们自行寻求赔偿,把争执接管过来,并协调赔偿的方法。如有不服从法庭的,最早的惩罚可能是逐入另册。不愿遵守其判决的人,将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被杀,其亲戚们迫于舆论压力,将不得参与本属职责和权利的复仇”。㉚梅因指出,英国国王也派代表出席类似的法庭,最初是为了分享罚款。随着国家的出现,英国国王逐渐坚持自己的裁决权和更重要的执法权(参看第 17 章)。百户法庭和主席一职,作为司法制度早已消失,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却得以保存。我们将看到,它最终成为现代民主代议制的一部分。
战争和军事组织
迄今为止,我还没从理论上解说,人类为什么自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社会。我只提及,它与历史上出现农业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有关。农业使人口的高度密集成为可能,并间接创造了对大型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需求。如我们所见,私人财产与复杂的亲戚组织,紧密纠结,盘根错节。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群体变成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供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族团层次,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他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支能组成各式联盟。恺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俟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㉛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㉜
类人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著名断言: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错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晚阶段才出现暴力。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生于社会群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还有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同类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伙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对很多人来说,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㉝基利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每五年中,70% 到 90% 的初期社会——族团、部落、酋邦的层次——参与战争。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环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邻人来犯。㉞狩猎采集者的残余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㉟
就黑猩猩和人类而言,狩猎似乎是战争的源泉。㊱黑猩猩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样技术追捕其他黑猩猩。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类的猎物更大、更危险,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会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将狩猎技术用于杀人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有历史记录。例如,蒙古人的骑术和马背上打猎,正好用来对付敌人。人类完善了追猎大动物的技术,以致考古学家往往把某处巨大动物群的绝迹,定在人类迁移至该地的时期。乳齿象、剑齿虎、巨型鸸鹋、大树懒——这些大动物,似乎都被组织良好的原始猎人斩尽杀绝了。
随着部落社会的出现,我们看到武士阶层的兴起,还看到人类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即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后续的历史中,这种组织实际上无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军阀和手下、民兵队、贩毒卡特尔、社区帮派。他们掌握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技术,开始行使以前族团层次中所没有的强制权力。
部落社会中,致富显然是发动战争的动机。讲到 10 世纪末战胜俄罗斯的维京人精英时,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Jerome Blum)说:
君主(维京人酋长)支持和保护他的侍从,以换取他们的服务。起初,他们与君主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员。其赡养费,则靠斩获的战利品和部落上缴的保护费……弗拉基米尔王的侍从埋怨,因为没有银勺,他们必须用木勺进食。君主旋即命令,赶快安排银勺,并说“金银难买侍从,有了侍从,就能获得金银”。㊲
20 世纪 90 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沦为军阀混战,因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积极招募侍从。这次,他们凭借武装侍从争夺的不是银勺,而是血钻石。
但战争的爆发,不单单依靠致富的冲动。武士可能贪婪金银,但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荣誉。㊳为一个目标而甘冒生命危险,为获得其他武士的认可,这就是荣誉。请看塔西佗(Tacitus)在 1 世纪编写的日耳曼部落历史,这是有关欧洲人祖先的罕见的同代人观察:
侍从中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是酋长手下第一副将;酋长中也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拥有最多、最犀利的侍从。身边有大量精选青年的簇拥,这意味着等级和实力……到达战场时,酋长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从的膂力跟不上酋长的,那是丢脸;比酋长活得更久,得以离开战场的,那是终身的臭名和耻辱;保卫酋长,以壮举颂扬酋长,那是侍从忠诚的精髓。酋长为胜利而战,侍从为酋长而战。㊴
即使从事农业或贸易的报酬更高,武士也不愿与农夫或商人交换地位,因为致富只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武士发现农夫生活可鄙,因为它不共担危险和团结:
如果出生地的社区长期享有和平和宁静,很多出身高贵的青年,宁可自愿寻求其时忙于战争的其他部落;休息于比赛无补,他们更容易在动乱中功成名就;再说,除了战争和暴力,你很难挽留优秀的侍从……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以伤疤为荣,比让他们犁地以待丰收更为容易;凭流血可获的,你偏要通过辛苦劳作,这似乎有点窝囊和闲散。㊵
塔西佗评论,战争之间的空闲期,年轻武士们懒散度日,因为从事任何民间工作只会降低他们的身份。这种武士道德被取代,一直要等到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 17 和 18 世纪。其时,以获利和经济计算为内涵的道德规范替代荣誉,成为杰出人士的标志。㊶
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其原因之一,就是无法预知领袖与侍从之间的道德信任。他们的共同利益以经济为主,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掠夺。但单靠经济是不能把追随者与领袖捆绑在一起的。1991 年和 2003 年,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作战时,它相信战场上失败将迅速导致其政府的倒台,因为他的重要部属会意识到,去掉侯赛因应是一件好事。但那些部属,由于家庭和私人的联系,加上害怕,结果却紧密团结,同舟共济。
长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诚,是凝聚力的非经济原因。部落社会向亲戚关系注入宗教意义和神灵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没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身上荷尔蒙高涨,偏爱冒险生活,对他们而言,经济资源不是掠夺的唯一对象。我们不应低估,性和俘获女人在造就政治组织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通常用女人作为交换中介的分支式社会。这些社会相对狭小,由于缺少非亲女子,其成员往往通过对外侵略来遵循异族通婚的规则。蒙古帝国的创始者成吉思汗,据称如此宣称:“最大的快乐是……击败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看他们的亲人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把他们的妻女拥入怀中。”㊷在实现最后一项抱负上,他是相当成功的。根据 DNA 的测试,亚洲很大一块地区,其现存的男性居民中约有 8% 是他的后裔,或属于他的血统。㊸
部落社会中的酋长和侍从,不同于国家层次中的将军和军队,因为两者的领导性质和权威是截然不同的。在努尔人中,豹皮酋长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没有指挥权,也不是世袭的。现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所罗门群岛,其头人处于同等地位。根据传统,他是亲戚们选出的,也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失去该职。塔西佗写道,日耳曼部落中,“他们国王的权力不是无限或任意的;他们的将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榜样及他人由衷的赞美,站在队伍的前列来控制人民”。㊹其他部落则组织得更为松懈。“19 世纪的科曼奇(Comanche)印第安人,甚至没有称作部落的政治组织,没有率领百姓的强悍酋长……科曼奇的人口,由大量组织松散的自治族团组成,没有应付战争的正式组织。战争头领只是战绩累累的杰出战士;如能说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动员一支战斗队伍;但其领导地位只在攻袭期间有效,还必须依赖他人的自愿。”㊺等到欧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军事压力,夏安人(Cheyenne)等的印第安部落才开始发展出持久和集中的指挥机构,如固定的部落会议。㊻
疏松且分散的组织,对部落社会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们联网的组织,有时可以发起强大的攻击。配备以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远方,征服广袤的领土。阿尔莫哈德王朝就是一个案例,其柏柏尔部落在 12 世纪突然崛起,征服了北非全地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没人可与蒙古帝国媲美,他们来自亚洲内陆的大本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设法攻克了中亚、中东大部、俄罗斯、部分东欧、印度北部、整个中国。但其永久领导的缺席、分支式联盟的松散、继位规则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会最终衰弱的命运。他们没有永久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无法治理征服的领土,只好依赖当地定居社会提供的例行管理。几乎所有征战的部落社会——至少是没能迅速演进为国家层次的——都会在一代或两代以内四分五裂,因为兄弟、表亲、孙子都要争夺创始领袖的遗产。
国家层次的社会,在继承部落层次的社会后,其中的部落制并不消失。在中国、印度、中东、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国家制度只是重叠在部落制度上,两者长期共存,处于勉强的平衡。早期现代化理论的错误,一是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必须相互匹配,二是认为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过渡是干净和不可逆转的。世界上只有欧洲,自觉自愿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取代部落制,基督教发挥决定性作用,打破了以亲戚关系为凝聚基础的传统。多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是欧洲人。他们假设,世界其他地区走上现代化,会经历与亲戚关系的类似告别,但他们错了。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在印度,亲戚关系与宗教互动,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会的最好特征。从美拉尼西亚的一语部落、阿拉伯部落、台湾人宗族,到玻利维亚的“艾柳”(ayllu)村社,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现代世界众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并塑造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互动。
从部落制到保护人—依附者和政治机器
我以亲戚关系来定位部落制(tribalism),但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支世系制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亲戚关系成员的部落。如果我们采用更广泛的定义,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亲戚,还包括因互惠和私人关系而绑在一起的保护人和依附者,那么,部落制便成了政治发展的常数。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亲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戚关系的追随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他们由自由民、佃户、家庭侍从所组成,到后来甚至包括愿意提供支持以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贫穷平民(plebeian)。从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的政治离不开强悍领袖动员各自依附者来攫取国家机构,像恺撒、苏拉(Sulla)、庞培。富有的保护人,把他们的依附者编成私人军队。在考察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治时,历史学家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抛开具体人物……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尔虞我诈、大公无私、高贵庄严,并不比一个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多多少。如果把罗马共和国看成是弗里多尼亚共和国(Freedonian Republic),将时间设在 19 世纪中期,将苏拉、庞培和恺撒想象成加西亚·洛佩兹、佩德罗·波德里拉和海梅·比列加斯,你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由依附者构成的派系、私人军队和对总统职位的武装争夺”。㊼
宽泛意义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实。例如,印度自 1947 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议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严格讲,这些关系有时仍属部落的,因为部落制仍存在于印度较穷、较落后的地区。其他时候,政治支持以种姓制度或宗派主义为基础。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与支持者的社会关系,与在亲戚团体中的一模一样。它仍建基于领袖和追随者的相互交换恩惠:领袖帮助促进团体利益,团体帮他获得竞选。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城市的赞助政治。其政治机器所依据的,仍是谁为谁搔了痒,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现代”动机。所以,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 21 世纪继续。
第 5 章 “利维坦”的降临
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分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重要差别:①
第一,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任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他权力,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地方行政官,凭借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策权。
第二,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支、部落、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邦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因为其成员资格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发展。
第五,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亲戚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如何自亲戚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亲戚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 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②缺乏悠久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 20 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前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么?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国家形成的理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弄清政府的合法性。但最先的国家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而建立集中权力,弄清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如此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换。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因缺乏集中的权力,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一天,部落群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支系的共识,因为如有不喜欢,每一支系仍可出走。
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中,又很自由自在。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等级分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象,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逼迫之下才出此下策。譬如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委托一名独裁者;或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 216 年坎尼会战后,汉尼拔(Hannibal)对罗马造成了切实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利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解释。他认为,大规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满足,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③
水利工程的假设要解答很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这种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该是原因。④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设,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说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主张,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作物、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族团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匮乏,如何取得重要公共资源,这一切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么造就了密集人口?密集人口与国家又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亚马孙印第安人开发了农业,尽管在技术上做得到,却不愿生产余粮。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并不保证这一切确实发生。⑤人类学家表明,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说,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因为面对他人分享盈余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念头。⑥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们不愿生产盈余,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们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压迫他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原因的产物。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把国家形成的来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象,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么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比较可信。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群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⑦
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契丹、匈奴、女真、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是,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起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部落社会自有平衡的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他原因。彪悍的部落群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他环境因素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认为,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中,才能解释等级制国家的出现。在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随时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都不存在逃跑的选择。⑧地理界限也能解释,由于没人搬走,生产力的增长只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也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可在广阔地区施展威力。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尚可提供额外的帮助,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邦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那样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⑨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⑩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要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以来,部落群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合农耕,所以没有遭遇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定居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余。
公元 570 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城镇的麦加,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 40 岁那年获得上帝的首次启示,随即开始向麦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随者由于受到迫害,在 622 年搬至麦地那。麦地那部落的争执需要他的调解,他便草拟所谓的麦地那宪法,为超越部落忠诚的信徒团体(umma)定位。穆罕默德创立的政体,尚无真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脱离了亲戚关系,不靠征服,而靠社会契约,这全凭他作为先知的魅力型权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治体经过数年征战,赢得信徒,占领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一举成为国家层次的社会。
在征战国家中,创始部落的领袖血统通常开创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只有女儿法蒂玛(Fatima),没有儿子。新兴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传给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属倭马亚氏族,也是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的支系。之后,倭马亚氏族确实开创了新王朝。倭马亚国家在奥斯曼(Uthman)和穆阿维叶(Mu‘awiya)的领导下,迅速战胜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在这些现存的国家层次社会中实施阿拉伯统治。⑪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国家兴起是最好的证明。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边缘角色。多亏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得统一,并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部落自己没有经济基础,但通过宗教思想和军队组织的互动,不但获得经济实力,还接管了产生盈余的农业社会。⑫这不是纯粹国家原生形成的案例,因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边如波斯和拜占庭等现成国家,先作为仿效榜样,后予以征服。不过,其部落制的力量非常强大,后来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建不成无部落影响的官僚机构(参看第 13 章)。这迫使后来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别措施,如军事奴隶制和招聘外国人充当行政官,以摆脱亲戚关系和部落的影响。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请看中国《诗经》中,献给商朝创始者的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降,入世生下我商王,居衍殷地广且强。古时帝命神武汤,整顿边界安四方。)
另一首颂诗《长发》称: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现朝代的祯祥。洪水滔滔,禹来治理大地四方。)⑬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须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⑭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 2 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人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织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们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的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国家为何不是普世共有?
我们现在明白,国家为何没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现,部落社会又为何持续存在于阿富汗、印度、东南亚高地。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总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⑮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 8% 的地区处于热带,50% 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 1975 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 1500 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尼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在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⑯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因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⑰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自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⑱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很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太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的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我将要在后续章节论证,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之前,后者可以是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商人、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长期锁定,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 20 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敌曾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 19 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关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 6 章 中国的部落制
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中国的部落社会组织;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特征;周朝的封建扩张和政治权威的性质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残留于中国南部和台湾。历史学家谈起中国“家庭”时,不是指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员达数百乃至数千的父系家族。中国早期历史有相当齐全的记载,提供了观察国家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的罕见良机。
人类长居中国。早在 80 万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类已现踪迹。智人离开非洲数千年后,也抵达中国。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获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区的首次出现,则在中国朝代之前的仰韶时期(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到龙山时期(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可见城郭和社会等级分化的明显遗迹。在这之前,宗教基于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由巫师主持。他不是专家,像在大多数其他族团层次社会,只是社区的普通一员。随着等级社会的逐渐成形,统治者开始垄断巫术,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①
开发农业后,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恐怕是马匹驯养,公元前四千年在乌克兰率先发生,又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传至中西亚。过渡到草原游牧业则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初,也是马背部落向中国挺进的开始。②这种挺进主宰了中国后续历史的大部分。
古代中国的分期有点让人困惑。③仰韶和龙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学的范畴,以中国北部黄河中下游的定居点而命名。中国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 770 年,周朝又发生分裂,从陕西的镐京迁都至现代河南的洛阳,前为西周,后为东周。东周本身又分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段。
| 年份(公元前) | 朝代 | 时期 | 政治体数量 |
| 5000 | 仰韶 | ||
| 3000 | 龙山 | ||
| 2000 | 夏 | 三代 | 3000 |
| 1500 | 商 | 1800 | |
| 1200 | 西周 | 170 | |
| 770 | 东周 | 春秋(前 770—前 476) | 23 |
| 战国(前 475-前 221) | 7 | ||
| 221 | 秦 | 1 |
从远古到统一中国的秦是古代中国所涵盖的历史。我们的有关知识来自浩淼的考古资料,包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通常是羊肩骨)、青铜器彝文、官员用来记录政务的竹简。④另一来源是问世于东周最后数世纪的伟大经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嗣后成为中国官员的教育之本。据称,这五部经典是孔子编纂和传播的,再加上卷帙浩繁的注释,构成了塑造千年中国文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经典的形成背景是东周时期,其时内战方兴未艾,政治分崩离析;《春秋》就是鲁国十二名国君的编年史,在孔子眼中,显示了这段时期的退化和堕落。这些经典和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的著作,虽然蕴含大量历史信息,但大体上仍属文学作品,其精确性尚不明确。
但有确凿证据显示,中国政治体数量经历了极大的收缩,从夏初的大约一万,到西周开国时的一千二百,到战国时只剩下七个。⑤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
部落的中国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本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⑥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会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⑦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别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⑧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⑨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制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⑩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的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⑪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秦国君主试图抑制亲戚裙带,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国,统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上台后,也尝试使用专政权力消灭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使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但这两项政治工程,都没获得发明者所期待的成功。中国家庭证明是颇有韧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跃于中国部分地区。⑫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 206—公元 9 年)。到了东汉末期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 20 世纪。它们在地方上发挥准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国家成为权力的来源。
关于中国亲戚关系,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料,大部分由人类学家所编撰。他们研究台湾和中国南部的现代社区,所使用的亲戚团体记载可追溯到 19 世纪。⑬个别亲戚团体所保存的详细记录,有助于研究更为早期的家庭关系。但在古代中国亲戚关系上,我们却只有很少信息。将现代趋势投射得那么久远,风险不小。有学者主张,当代宗族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政策的产物,与公元 1000 年之前的亲戚关系是迥然不同的。⑭尽管如此,在中国数世纪的历史中,亲戚团体的某些特征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中国社会的亲戚关系严格遵循父系社会或父系家族的规则。有人类学家将之定义为“使用统一礼仪、显示共同祖先的集团(corporate)”。⑮某些现代宗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二十五代以上,但历史上的宗族通常不超过五代。相比之下,氏族是容纳若干宗族的更高级组合,通常基于虚拟(fictive)的亲戚关系。这种氏族和相关的姓氏联盟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确定异族通婚。⑯
像其他父系家族社会一样,继承和遗产只通过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员,而是与其他重要家庭联姻的潜在资源。结婚后,她与生身家庭一刀两断,在很多中国历史时期,只可在规定时日回访娘家。妻子不再往生身的家庙祭拜,而是改去丈夫家的。香火传承全靠男子,因此,她在新家庭中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除非有了将来为父母灵魂祈祷的儿子,她的灵魂将不得安宁。讲得实在些,儿子又是她晚年的经济保障。
数世纪来,无数中国小说和戏剧记载了年轻妻子与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婆婆虐待未生儿子的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有了儿子,女子作为重要宗族继承人的生母,又可获很高的地位。中国王朝众多的宫廷权术,都涉及意欲提升儿子政治地位的擅权遗孀。西汉时期的皇太后,至少六次得以选择皇帝继承人。⑰
前现代(premodern)社会的可悲真相之一,就是很难把儿子抚养成人。现代医药发明之前,地位和财富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差别。世界君主政体的历史,充斥着王后或妃嫔没能生下儿子而引起的政治危机。日本皇太子徳仁亲王于 1993 年结婚,与妻子雅子一起尝试生个儿子(而未成功),引起众多现代日本人的急切关注。与一连串早期皇帝相比,这又算不了什么:仁孝天皇(1800—1846)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三个活到三岁;明治天皇(1852—1912)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五个活到成年。⑱
跟其他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的因应对策是纳妾。地位高级的人士可娶二房、三房甚至更多的妻子。为确定个中的继承权,中国发展了复杂的正式规章制度。妻子再年幼的儿子对妾的儿子,仍享有优先继承权,但也有违反此例的皇帝。虽然有具体规矩,继承权的不确定性仍是宫廷政治的主题。公元前 71 年,霍光妻霍显设法谋害了坐月子的许皇后,让女儿成君取而代之。公元 115 年,汉安帝多年不育的阎皇后鸩杀了刚生下儿子的皇妃李氏。⑲
像库朗日所描述的希腊和罗马,中国亲戚制度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关。周朝宣称,所有土地都是国家财产,但周天子太弱,难以付诸实现。土地日益私人化,买卖和改造也变得普遍。⑳作为整体,宗族拥有祖庙或祠堂。较富的宗族又投资于共同财产,如水坝、桥、井、灌溉系统。单独家庭拥有自己的耕田,但不得随意处置,因为有对宗族的礼仪义务。㉑
宗族增长始终给遗产的继承制造难题。周朝早期有长子继承权制度,之后又改为儿子们平分。这一规矩延续了中国历史的大部,直到 20 世纪。㉒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土地经常越分越小,以致无法维生。中国开发了大家庭概念,数代男子同堂。成年的儿子或在分到的祖地上安家,或试图购买邻地。对宗族的共同财产,他们仍然有份;对共同的祖先,他们仍有祭拜的责任。这一切阻止了他们的搬迁,或出售祖地。㉓
在财产和同堂方面,不同区域出现了巨大差异。中国北方,宗族力量逐渐变弱,宗族成员搬往分散的村庄,丧失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在南方,宗族和氏族成员继续并肩生活,以至整村人只有一个姓。为此出现很多解释,其中之一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世纪以来,南方一直是蛮荒地带,宗族即使增长却仍能抱成一团;而在北方,战争频仍,流离失所时有发生,从而拆散了数代同堂的宗族。
要记住,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形中纯属富人特权。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平分的庞大地产、共同财产、为传宗接代而娶的多房妻妾等。事实上,周朝首次编纂的宗法规则,只适用于精英家庭。贫困家庭只能负担很少的孩子,有时为弥补无子无孙,而让入赘女婿改用妻子的姓氏。这在日本很普通,在中国却遭否定。㉔
中国的“封建”时期
商灭于周。周的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当代陕西省),在商的西方。周的征服始于公元前 11 世纪初,历时数年。其时,商的军队还必须在山东应付马背游牧民族的袭击。周王杀死商的储君,谋害自己兄弟,夺取政权,建立新朝。㉕
这一征服开创了很多学者所谓的中国封建时期。其时,政治权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从西周到东周早期,亲戚关系仍是社会组织的原则。到了春秋和战国,这些亲戚团体之间战火纷飞,国家开始慢慢成形。我们可仔细追溯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所依靠的不再是考古学的重新组合,而是历史记载中的证据。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的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㉖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中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㉗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传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㉘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而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度的更新。㉙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又相对平等。”㉚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的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㉛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㉜,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给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分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㉝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是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手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次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制,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是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㉞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责备君主,并吐口水,却没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拒绝他对珍玩的索求;在他妻妾群中与他一起玩游戏;未获邀请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门邀他分享晚餐,却发现他在外射鸟。”㉟
周朝社会的氏族组织中,军队也是分支式的,没有中央统领。各个宗族动员自己的军队,再蜂聚到更大单位中(像努尔人的分支)。“有关战争的记述透露,战场上,征来的士兵只跟随自己的将领;重要的决定通常由将领们集体讨论决定;部队编制松散,以致将领只能指挥自己手下,而顾不上其余。”㊱很多案例显示,因为没有严格的统领制度,部将得以修改名义上君主的命令。根据第 5 章介绍的人类学分类,周朝早期政体是部落的,至多是酋邦的,而绝不是国家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非常相似,都发展了悬殊的阶级分化和贵族阶层,起因是关于荣誉、暴力、冒险的道德信念。开始时,早期部落社会相对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悬殊的各式调整机制。然后,某些人开始在狩猎中出类拔萃。狩猎与战争有关联,这可追溯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等级制度在狩猎和征战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些人或群体就是略胜一筹。优秀猎手往往又是优秀战士,狩猎所需要的合作技能进化成军事战术和战略。通过战绩,有些宗族获得更高的地位;宗族内,卓越的战士崛起而成为将领。
这也在中国发生。狩猎和战争的关联保存于一系列礼仪,使武士贵族的社会地位获得合法化。陆威仪(Mark Lewis)解释说,春秋时期,“君主之所以在群众中鹤立鸡群,全靠在圣坛前的‘壮举’,即礼仪化的暴力,如献祭、战争、狩猎”。㊲狩猎把动物送上祖先的祭台,战争把战俘送上祖先的祭台。血祭是商朝的习俗,到周朝仍然继续,一直到公元前 4 世纪。军事征战出发于庙堂,为确保战争的胜利,既有牺牲品又有祈祷。礼仪中,大家分享祭肉,战鼓因战俘的血液而变得神圣,特别可恨的敌人则被剁成肉酱,供宫廷或军队成员进食。㊳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战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发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种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㊴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
第 7 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国家源于军事竞争;商鞅的现代化改革;法家对儒家家庭主义的批判;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伴的政治发展
东周时期(公元前 770—前 256 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的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尤其秦国,全力投入不寻常的现代化工程,目标直指周朝早期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它绕过武士贵族,直接征募大量农民,使军队趋于民主化;从事大规模土地改革,将家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破坏世袭贵族的权力和威望,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些改革听起来像是“民主的”,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国强兵,打造冷酷的专政。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的优势,令秦国打败所有对手,进而一统天下。
战争与国家建设
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个著名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①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关联不是普世共有的。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就没有这一历史过程。②但毫无疑问,在中国的东周时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从公元前 770 年的东周初期到前 221 年的秦朝统一,中国经历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规模、耗资、人命的牺牲有增无已,从分散封建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过渡全凭武力征服。这时所建立的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发动战争息息相关。
与其他好战社会相比,中国在东周期间的血腥记录仍然突出。有学者计算,春秋时期的 294 年,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 1211 次战役,和平岁月仅有 38 年,超过 110 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 254 年战国时期,打了 468 次战役,仅有 89 年太平无事。兼并使国家数量大跌,战役总数因此减少,战国七雄灭了其余十六国。另一方面,战役的规模和历时却有显著的上升。春秋时,有些战役只打一个回合,一天就完。到战国末期,围攻可持续数月,战役可持续多年,参战将士高达 50 万。③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 8% 到 20%,而古罗马共和国的仅 1%,希腊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仅 5.2%,欧洲早期现代则更低。④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李维(Livy)报道,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Lake Trasimene)和坎尼会战(Cannae)中,总共损失约 5 万军人。而一名中国史官称,24 万战死于公元前 293 年的战役,45 万战死于公元前 260 年的战役。总而言之,从公元前 356 年到前 236 年,秦国据说一共杀死 150 多万他国士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夸大其词,无法证实。但它仍颇不寻常,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 10 倍。⑤
持续战争带来的制度改革
激烈战争造就强烈的奖励,导致了旧制度被摧毁和新制度取而代之。它们都与军事组织、征税、官僚机关、民间的技术革新以及思想有关。
军事组织
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激烈战争的最初影响是参战各国军事机构的演变。
如早先提到的,春秋早期的战事是驾战车贵族的互相厮杀。每辆战车配备一名御手和至少两名武士,还需多达七十人的后勤支持。驾车开打是高难度的技术,需要实质性的训练,的确是适合贵族的职业。⑥这时的步兵仅发挥辅助作用。
从战车到步兵加骑兵的转变逐渐发生于春秋末期。在南方湖泊和沼泽众多的吴越两国,战车用处非常有限,在多山地区更是相形见绌。很显然,与西方草原马背野蛮人打交道的经验,促使骑兵出现于战国初期。随着铁兵器、弩、盔甲的广泛使用,步兵变得更为有效。西部的秦是最早重整军队的国家之一,它淘汰战车,改换为步骑兵的混成。其主因,既是秦的地形,又是野蛮人的持续压力。楚是在他国征兵的第一国,击败陈之后,强迫当地农民提供军事服务。这些军队不再是亲戚团体的组合,而是等级分明的军事单位,统领着固定数量的部下。⑦公元前 6 世纪中期,第一支全步兵军队投入战斗,在未来两个世纪内,完全取代战车军队。到战国初期,将农民大批征入军队已成司空见惯。⑧
中国军队打击力量的核心从战车转到步兵;无独有偶,欧洲也从盔甲骑士转到弓箭和长矛的步兵军队。担任战车手和骑士的贵族,在这两个转向中,根本无法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这两个文明中,负担得起旧式装备和培训的只有贵族精英。这个转向似乎与技术改革有关;中国贵族数量持续下降,够格的战车手日渐稀少,可能是另外原因。
贵族阶层的人员损失,推动了军内的论功封赏。周朝早期,军事将领全凭亲戚关系和在氏族中的地位。斗转星移,越来越多的非贵族将领,单凭自己的骁勇善战而获晋级。国家也开始分配土地、爵位、家奴给将士以作奖励,无名小卒跃升为将军时有发生。⑨参战的野战军队中,骁勇善战不是文化规范,而是存活的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论功封赏的原则始于军队,辗转传入文官体系。
征税和人口注册
将农民大批征入军队,需要相应的物质资源来支付和装备他们。从公元前 594 年到前 590 年,鲁国开始征收田赋,不再作为亲戚团体的财产,而是以众多农家合成的“丘”为计量单位。邻国齐的入侵,迫使鲁国快速增征甲兵。从公元前 543 年到前 539 年,子产在郑国重划带渠的田地,把农民编成五户一组以征收新税。在公元前 548 年,楚国丈量土地,登记盐池、鱼塘、沼泽、森林、人口。这项调查是为日后的征税征兵预作准备。⑩
官僚机构的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官僚机构自周朝中国的混乱中崛起,全没计划,只为征收战争所需的税金。
周朝头几年的管理是家族式的,像其他早期国家一样,如埃及、苏美尔、波斯、希腊、罗马。行政官位配给君主的亲戚,被视作君主家庭的延伸。决策时,并不严格遵守等级分工,而是以咨询和忠诚为依据。所以,君主可能掌控不住大夫,如有分歧,也不能予以解雇。像一语部落中的头人,面对让贤的强大共识,周朝一名君主只好束手听命;除非他铤而走险,如公元前 669 年的晋献公,把合谋反己的所有亲戚统统杀光。宫廷权术不是个人操作的,而是宗族,满门抄斩才能绝其香火。⑪
官僚化始于军队,各项职能由贵族转让给庶民。军队需要征募、装备、训练大批新兵,记录和后勤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援军队的需要又增加了对文官体系的需求。他们帮助征税,确保大规模军事动员中的连贯性。军事机构成为文官的训练场所,并促进统领体系的形成。⑫同时,周朝贵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为大夫家庭提供了社会升迁良机。大夫虽在传统上也来自贵族阶层,但经常属于远离君主和其亲戚的外围。士族是低于贵族的另一阶层,包括军人和其他有功绩的庶民,也得以取代家族关系的大夫,承担重要职位。所以,随着贵族阶层的日渐式微,论功封赏而不是论出身封赏的原则开始慢慢获得认同。⑬
民间的技术革新
公元前 4 世纪到前 3 世纪,中国经历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靠的是技术革新,包括青铜工具转向铁工具、基于双向活塞鼓风的生铁冶铸、牲口耕犁的改进、土地和灌溉的改善。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业交流增加,人口密度也开始出现显著上升。粗放型增长靠的是人口增长,以及开发像四川那样的新边境。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增长源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这表示,它不是经济制度的内部逻辑所造成的,而是得益于意外的技术革新。军事上的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动力。战国时期的每个国家都面对增税的巨大压力,为此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仿效对方的技术革新以加强自己实力。⑭
思想
那么剧烈狂暴的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思潮,这很值得钦佩。战乱不断所造成的流离失所,促使了对政治和道德的深刻反思,并为天才的老师、学者、谋士提供了出人头地的良机。其时,众多老师四下游学,招揽学生。其中有孔子,他出身于贵族,但只是作为学者和老师而谋生。战国初所谓的百家争鸣时期,还有很多如此的学者,包括墨子、孟子、孙子、韩非子、荀子,身后都留下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著作。当时的政治不稳定,似乎造就了文人的无根无蒂,这反映在文人的周游列国,不管何等政权,只要感兴趣,他们都愿奉献自己的服务。⑮
这种智慧横溢有两层政治意义。首先,它创建了宛如意识形态的东西,即政府如何施政的思想,后代中国人可以此来评判自己政治领袖的表现。最为著名的就是儒家,而儒家学者又与其他学派展开激烈争辩,例如法家——这些争辩其实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学者和文人享有最高级荣誉,甚至高于武士和巫师。事实上,文人和官僚的作用合二为一,在其他文明中是找不到的。
其次,中国文人的流动性又孕育了愈来愈像全国文化的东西。其时创作的伟大经典著作,变成精英教育的基石和中国文化的基础。有关经典著作的知识,成为国民身份的坐标。它们享受如此高的威望,以至在中华帝国无远弗届,甚至传播到边界之外。边境线上的游牧王国,有时在武力上强于中国,但无法匹配中国的智慧传统。所以,他们倾向于以中国的制度和技术来治理中国。
商鞅的反家庭运动
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总顾问。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⑯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罚。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⑰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制,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井田制中,农田分成九方块,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户农家各耕一块,中间的是公田。每个贵族家庭拥有若干井田,耕耘的农家为此需要履行徭赋和其他义务,很像封建欧洲的农民。井田上布满路径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户农家组成贵族地主保护下的公社。⑱废除井田制使农民挣脱对地主的传统义务,并允许他们搬往他人新开发的土地,或干脆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国家避开贵族,向全体地主征收以实物支付的统一地赋。
此外,为了资助军事行动,商鞅还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国家颁布,家庭如有若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缴双倍的税。商鞅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大家庭,而赞许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对没有足够财产可分的穷苦家庭来说,该制度造成了莫大艰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个人奖励,也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这次改革还与新的家庭注册有关。传统中国由庞大的亲戚团体组成,商鞅则把家庭分为五户和十户的群体,让他们相互监督。其他国家也在实施类似改革,如鲁国的“丘”,不同之处是秦在执行中的暴虐。群体中的犯罪活动,如不予检举,惩罚是腰斩;举报人有赏,等同于在战斗中斩敌首级。该制度的翻版在明朝得以复活,称为保甲。
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中认为,所有国家都具备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试图掌控各自的社会,一开始就“昭告”天下。⑲它们清除自生自长的弯曲小街的旧区,代之以几何图形般秩序井然的新区,就是为此。19 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巴黎中世纪废墟上建造宽敞的林荫大道,不单是为了美观,还有控制人口的动机。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于商鞅治下的秦。除了废除井田制,他还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他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设四十一个县;县令不是地方推举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开始,这些县位于边境地区,表明其作为军事区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齐矩形,与东南西北的轴心相对称。现代地图学显示,曾是秦国的地域都有这种直线布局的地貌。⑳商鞅还颁布在秦国通用的统一度量衡,以此来替代封建制度下的杂乱标准。㉑
商鞅竭尽全力投入社会工程,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显而易见,他招惹了秦国家族贵族的极大反感。庇护人秦孝公一去世,继位人立即反目,商鞅只得逃亡。他最终遭人检举,所依据的恰恰就是自己颁布的严禁庇护罪犯的法律。据传,商鞅遭车裂之刑,即四车分尸,他的宗族成员全被诛杀。
东周的中国,每一项制度革新都与战争的需求直接相连:服役扩充至全体男子、先是军队后是文官的永久性官僚体系、家族官职减少、论功封赏、人口注册、土地改革、家族精英地产的重新洗牌、更好的通信和基建、非人格化的等级行政部门、统一的度量衡。这一切,都可在军事要求中找到根源。战争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唯一引擎,但肯定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涌现的主要动力。
儒家与法家
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政策得到后续学者的肯定,如韩非子,并被归纳成全套的法家意识形态。在法家和儒家的紧张关系中,可以读懂中国后来历史的大部,直到 1949 年共产党胜利,那份紧张都与政治中的家庭作用有关。㉒
儒家极力主张向后看,其合法性扎根于古代实践。孔子在春秋末期编辑他的经典作品,十分怀恋周朝的社会秩序。但它因战事不断,已在分崩离析中。家庭和亲戚关系是家族秩序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
所有部落社会都实行祖先崇拜,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儒家给中国版本涂上了特殊的道德色彩。儒家的道德原则规定,对父母的责任,尤其是对父亲的,要大于对妻子或子女的。对父母不敬,或在经济上没尽扶养责任,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儿子对妻子或子女的关心,如超过对他父母的,也要受到严厉惩罚。如发生冲突,例如父亲被控犯了罪,父亲的利益一定高于国家的。㉓
家庭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家庭责任高于政治责任的道德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迄今,中国家庭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竭力捍卫它的自治,不愿接受政治权力的干涉。家庭和国家的力量关系呈反比。19 世纪清朝式微,中国南方强大的宗族干脆接管地方事务的治理。㉔1978 年的中国,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农民家庭又变得生龙活虎,成为后来影响全国的经济奇迹的主要引擎。㉕
相比之下,法家向前看。它把儒家和对家庭的尊崇,看作巩固政治权力的绊脚石。儒家精致微妙的道德和责任,对他们丝毫没用。作为替代,他们追求直截了当的赏罚分明——特别是惩罚——使百姓臣服。如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所说的: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㉖
法家建议,不可把臣民当作可以教诲的道德人,只可当作仅对赏罚有兴趣的自私人——特别是惩罚。所以,法家的国家试图打破传统,废除家庭道德责任,以新形式将臣民与国家绑在一起。
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的社会工程与法家有明显关联。就像早先的商鞅,毛泽东也把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中国家庭看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的反孔运动意在铲除家庭道德的合法性,共产党、国家、公社变成帮助中国人团结起来的新式制度。一点不令人惊讶,商鞅和法家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复兴,在很多共产党学者的眼中成为现代中国的先例。
有学者说,“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㉗对皇帝的权力,儒家无法想象任何制度上的制衡。更确切地说,儒家试图教育君主,缓和他的激情,使他深感对人民的责任。让君主获得良好教育,以建良好政府,西方传统对此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在描绘合理城邦时所简述的,记载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皇帝到底深感多少对人民的责任,还是仅仅利用儒家道德来保护自身利益,那是后续章节的主题。法家直接剥去道德政府的外衣,公开宣称臣民是为君主而活的,不可颠倒过来。
我们不应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与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关联。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并获得教士等级制度的捍卫。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与当前统治者相比,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级、更合法,因此对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法治的含义就在:甚至国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缚的,不可随心所欲。
这种法治从没存在于中国,对法家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国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来,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它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㉘商鞅认为,惩罚一旦确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贵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与现代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点。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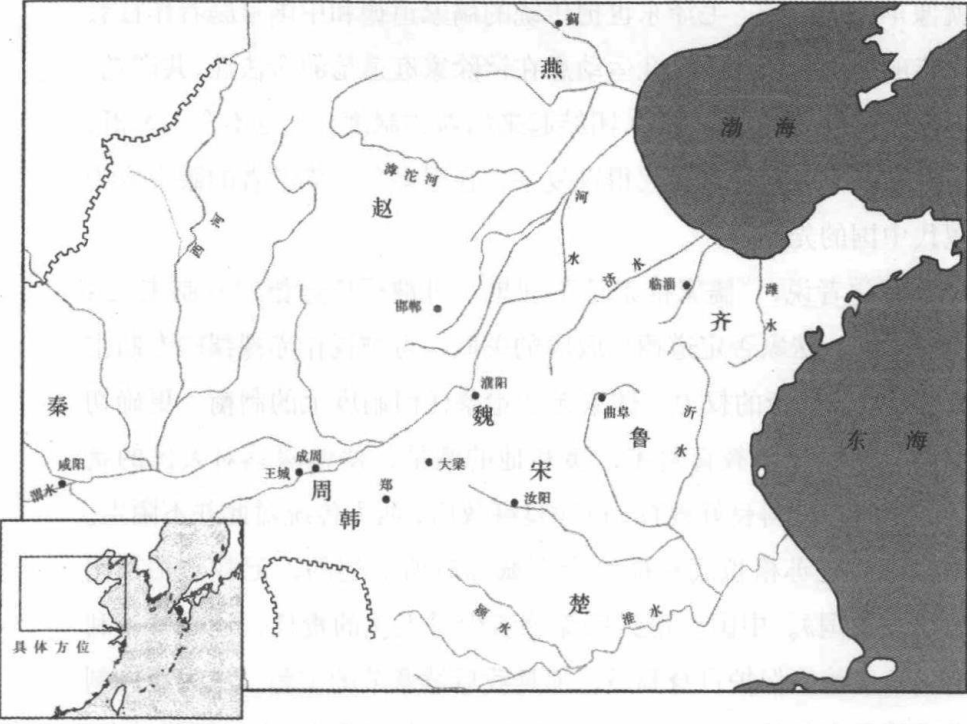
商鞅所创建的新式国家制度,使秦国在调动资源方面,比以前更加广泛,比邻国更加有效。但仍不是取胜的保票,因为敌对国家的强烈竞争导致了互相仿效。秦国崛起进而称霸全中国的故事,与其说是发展领域的,倒不如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
春秋末期为巩固国家而发起的争战中,秦国实际上是配角,只在更强大的对手中间发挥平衡作用。它处于争战国家中的最西面,在地理上受一定保护(参看地图)。从公元前 656 年到前 357 年,涉及大国的 160 场战役中,秦仅发动 11 场。秦孝公和商鞅开展国家改革后,这就有了大变。从公元前 356 年到前 221 年,秦发动了 96 场大战役中的 52 场,打胜 48 场。公元前 4 世纪最后十年,秦打败南方大国楚,又在前 293 年打败东面的邻国魏和韩。东方的齐国是仅存的主要敌人,也败于前 284 年。到了公元前 257 年,所有他国都丧失了大国地位。始于公元前 236 年的统一战争,最终导致中国在前 221 年出现大一统的秦朝。㉚
争战国家到底图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阶梯。这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儒家和法家为此而争论不休。这个争论发生于一国之内,也发生于各国之间;既是争战的原因,又是争战的结果。秦国把自己当作法家的旗手,它的动机与其说是信服,倒不如说是实用。㉛
这里利害攸关的主导思想,不同于上述争论,而是商周统一中国的古老理念。统一中国的实现,其传说的色彩大于现实。东周的分裂始终被看作旷日弥久的异数,需要承担天命的血统崛起,予以拨乱反正。寻求承认的斗争,就是看哪个宗族获得统治整个中国的荣誉。
中国发展路径为何异于欧洲
许田波(Victoria Hui)等学者提出这样的超历史大题目:公元前 3 世纪的中国由多极国家体系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却没有。欧洲国家体系实际上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 400 个主权政治体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25 个。尽管有不少尝试,包括哈布斯堡(Habsburg)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希特勒,但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
有下列可能的解释,第一条是地理。欧洲因河流、森林、海洋、山脉而分成众多区域,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喀尔巴阡山脉,等等。不列颠岛屿又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破坏霸权组合的平衡角色。相比之下,第一个中华帝国仅拥有今日中国的部分领土,由西向东,只是从渭河峡谷到山东半岛而已。战国时期已修筑很多道路和运河,当时的军队很容易在这个地区纵横驰骋。这个核心地区巩固成单一强国之后,才开始向南、北、西南方向拓展。
第二条与文化有关。商和周的部落之间有种族差异,但周朝时期涌现出的各国,则无种族和语言的明显区分,不像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匈人之间。中国北方有不同方言,但商鞅和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相互的思想交流,都证实了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
第三条是领导,或领导的缺乏。许田波指出,多极国家体系不是自我调整的机器,不能永远取得防止霸权崛起的平衡。国家有自己领袖,解读自身利益。秦国领袖运用机智的治国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击破敌国的联合。而敌人无视秦国的凶险,反而经常自相残杀。
最后一条与中国和欧洲政治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直接相关。欧洲从没见过像秦朝那样的强大专制国家,唯一例外是莫斯科大公国。但它发展较晚,一直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直到 18 世纪的下半叶。(俄罗斯进入欧洲国家体系后,很快占据欧洲的大部,先是在 1814 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后在 1945 年斯大林时代。)17 世纪晚期,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作“专制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在征税和动员方面,远远比不上公元前 3 世纪的秦朝。潜在的专制君主开始其国家建设大业时,就会遇上组织良好团体的阻挠。例如,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独立自治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国境内外灵活运作。
中国情形很不同,它依赖广泛的亲戚体系。中国的封建贵族,从没建立起与欧洲领主一样的地方权力。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权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作为对照,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此外,不像欧洲贵族,中国贵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权利、特权的保护。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近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队,轻易击败早期的贵族军团。周朝的中国从没发展出可与欧洲媲美的强大世袭地主贵族。君主、贵族、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它有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
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㉜迷惑韦伯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经济现代化的陪伴,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也没有社会现代化的陪伴,亲戚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人主义,反而与非人格化管理共存,一直到今日。像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样,韦伯相信发展中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紧密相连的。很可能是因为现代化的其他方面没在中国出现,所以韦伯认不出中国的现代政治秩序。欧洲的实际发展中,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也没有密切相连,有顺序上的先后,它的社会现代化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所以,欧洲的经验是独特的,不一定能在其他社会复制。
多种现代化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如要资本主义出现,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有一场认知革命,发明了科学方法、现代大学、以科学观察创造财富的技术革新、鼓励革新的产权体系。秦朝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学术传统是向后看,无法达到现代自然科学所需要的抽象。
此外,战国时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商人或工匠没有社会威望,崇高地位只属于地主。㉝虽有产权存在,但其形式无法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朝的独裁政府,剥夺大批家族地主的土地来削弱其权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税来支持军事扩张。国家不是创造奖励,让农人的耕耘更为有效,而是订出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还要加以处罚。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袭的地主庄园,开辟了土地买卖市场,但随之没有出现自耕农阶层,土地又被新贵阶层所吸纳。㉞没有法治来限制主权国家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㉟
亲戚关系体系崩溃,被更自愿、更个人形式的团体所取代,这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它在秦统一后没有发生,原因有二。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出现,促进新社会团体和新身份的广泛分工也无从说起。其次,破坏中国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相比之下,破坏西方亲戚关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论层次上,又通过教会对家事和遗产的影响力(参看第 16 章)来进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根发芽,比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足足早了数个世纪。 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经常不能达到目标。中国的父系宗族和以此为基础的家族政府,其相关制度虽遭受痛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将看到,昙花一现的秦朝之后,它们又卷土重来,并作为权力和感情寄托的来源,在后续世纪中一直与国家明争暗斗。
第 8 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秦始皇和他所创建的朝代为何迅速倒塌;汉朝恢复儒家制度,但仍保留法家原则;秦汉时期的中国治理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创始人嬴政(死后庙号是秦始皇帝,生于公元前 259 年,卒于公元前 210 年),精力充沛,且不可一世,全凭政治权力改变了中国社会。世界闻名的兵马俑是特地为他铸造的,在 1974 年出土于一个 2 平方英里的陵墓区。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声称,造秦始皇陵动用了 70 万劳工。即便是夸大其词,但很明显,他创建的国家掌控大量盈余,以惊人的规模调配资源。
秦始皇把秦的制度推广到全中国,其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将在后继者汉朝手里变成一种统一的中国精英文化。这不同于群众现象的现代民族主义。尽管如此,将中国社会精英链结起来这一新意识,坚韧不拔,在朝代兴亡和内乱之后,总能浴火重生。外邦人好几次打败中国,但无法改变中国制度,反被吸收消化,直到 19 世纪欧洲人抵达。邻居的朝鲜、日本、越南,虽独立于中国政体,但借鉴了大量中国思想。
秦始皇用来统一中国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他实施了商鞅所阐述的法家原则,其时,秦仍是个边陲国家。他攻击既存传统,推行庞大的社会工程,所作所为几近极权主义,从而激发了社会中几乎每个阶层的强烈反对。仅十四年后,秦朝轰然倒塌,改朝换了姓。
秦朝为后世君主留下一份复杂遗产。一方面,受秦始皇攻击的儒家和传统派,在之后的世纪中,诅咒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道德、最为暴虐的政权之一。儒家在汉朝重新得势,试图推翻秦的很多革新。另一方面,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制度,不但活过了汉初的贵族复辟,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尽管在后来中国王朝中,法家不再是钦准的意识形态,但在国家制度中仍可看到它留下的遗迹。
秦朝国家和崩溃
秦始皇的政策由丞相李斯执行。李斯是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同学,但设下阴谋让后者蒙辱自杀。一旦掌权,这名建国设计师的最初行动是将帝国行政分为两级,共设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由皇帝从首都咸阳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已孱弱的封建贵族是打击对象,历史记载说,为方便监督,全国十二万贵族被迫迁至首都近郊。①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很难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权的案例。这显示中国离开部落社会已有多远。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员抵抗国家集权,在公元前 213 年建议皇帝重新分封,试图在乡野为自己打下新的权力基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认为,这将破坏他们的国家建设大业: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②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烧经典,据称还下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这些行为招致了后世儒家对他经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国已有统一度量衡,现在推广至全中国。秦始皇还以史籀大篆统一全国文字,这也是秦国当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统一。③就是今天,中国各地仍有不同方言。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秦朝严格遵守法家方法,其统治如此暴虐,以致在全国激起一系列起义。它的轰然倒塌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的公元前 210 年。被押去军事营地的一队罪犯,因暴雨而受阻,遂揭竿而起。法律规定,无论什么原因,延迟到达者都是死罪。小队领袖决定,即使造反,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变得更糟。④叛乱迅速蔓延至帝国其他地区,很多幸存的前君主和前封建贵族,看到秦朝变得衰弱,便拥兵宣告独立。同时,丞相李斯与一名宦官共谋拥戴秦始皇次子胡亥登基,反而死于宦官之手。接下来,宦官又死于他想立为皇帝的子婴之手。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还有其庶民出身的部下刘邦,组织新军队,攻入秦首都,消灭秦朝。项羽分派土地给亲戚和拥护者,试图返回周朝的封建主义。刘邦(死后谥号是汉高祖)转过身来反对项羽,四年内战后成为胜利者。他在前 202 年建立汉朝,史称西汉。⑤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新皇帝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不像秦始皇,汉高祖没有既存国家的权力基础。他的合法性来自他的魅力,他是反暴政的造反军的成功领袖。为取得政权,他统领一个由杂乱军队组成的同盟,包括很多传统家族和前君主。此外,他还须提防北方游牧部落的匈奴。因此一开始,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远远低于其前任秦始皇。
高祖创建双轨制度,部分地区恢复了周朝的封建主义。他把内战中支持自己的前君主和将军们分封去小王国,又给自己家庭成员分派新的封地。剩下的地区则保留秦朝的非人格化郡县制,构成高祖自己的权力核心。⑥最初几年,朝廷对小王国的控制很弱。秦朝统一中国的工作本来就不彻底,汉朝早期仍需继续努力。高祖启动这一过程,逐渐取消地方封王中不是刘姓的权力。继承者汉文帝在公元前 157 年,废了长沙最后一个小王国。皇族成员管辖的封地持续较久,与搬到长安的中央政府日益疏远。公元前 154 年,它们中的七个为取得完全独立而反叛。成功的镇压导致汉景帝宣布,剩下的封地不再享有行政权力。政府提高征税,迫使封地在兄弟姐妹中分家。西汉开国一百年后,封建统治最后的残余变得无权无势,地方官几乎都是中央政府指派的。⑦
家族拥有地方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周朝封建主义,在中国后来历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乱时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稳脚跟,又夺回对这些政治体的控制。从来没有一次,封王强大到可逼迫帝王作出宪法上的妥协,如英国的大宪章。中国地方上的封王,不像封建欧洲的对应阶层,从未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我们将看到,以后的世袭贵族试图在中国掌权,不是打造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攫取中央政府。强大国家早期的中央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竟使自己变得永久化了。
在中国不同地区根除家族统治,代之以统一的国家政府,事实上是法家的胜利,也是秦建立集权强国传统的胜利。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儒家的传统主义得以东山再起。汉武帝(公元前 141—前 87 年在位)治下,儒家学者重返行政高位,兴办太学,设置儒学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各自的经典。读好经典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著名的科举制度的雏形也于此而起。⑧
思想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法家为君主着想的残酷统治,原是商鞅和韩非所倡导的,此时遭到贬谤,民为邦本的古代儒家见解重又获得尊敬。这离民主观念还很远,没有一名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或权威应有制度上的正式制衡,更不用说普选或个人权利。对皇帝权力的唯一制衡是道德;也就是说,给予皇帝正确的道德教育,敦促他仁民爱物,并时常劝诫他不可辜负这些理想。
早期的皇权也有限制,因为皇帝身处儒家官僚机构之中。官僚机构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制衡皇帝的正式权利。但像所有的官僚,凭借专长和帝国运作的知识,他们施加了可观的非正式影响。像任何等级组织的领袖,从军队、公司到现代国家,坐在汉朝政府顶端的皇帝,必须依赖众多顾问来制定政策、执行命令、判决呈入朝廷的案件。这些官员负责训练年轻太子,等他们长大登基后,再提供咨询服务。传统和文化上的威望,增加了高级官僚左右皇帝的影响。历史记载中,丞相和尚书批评皇帝的案例很多,有时还得以扭转有争议的决定。⑨
武装起义是对坏皇帝的最后制裁,根据儒家天命流转的原则,又是正当合法的。天命的首次提出是为了辩解公元前 10 世纪周对商的篡夺,之后又被用来辩解对不公或腐败皇帝的造反。没有精确规则来确定谁享有天命,其获得往往是在造反成功之后(第 20 章对此有更详尽的讨论)。显而易见,这种制衡是非常极端的,带有极大风险。
君以民为贵的儒家思想,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观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尔曼(Schurmann)认为,官僚机构所塑造的道德说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强烈反对法家君主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因为儒家就是这种权力的首批受害者。他们只想在汉朝复辟时期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官僚不是公众利益的监护人,而在代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又恰恰身处该制度的顶端。⑩尽管如此,对这一执政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多讲几句。它至少在原则上坚持君主应对人民负责,并执意保护抗衡集权的现存社会制度。
汉朝政府的性质
汉朝时期涌现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决家族统治的地方势力。在西汉末期王莽的土地改革之前,没有试图使用权力来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基本上,它不触及既存的社会人脉和产权。为营造公共工程,它也征用徭赋,但没有秦朝那样穷凶极恶。
汉朝时期,中国政府愈益建制化。在家族制中,无论是周朝的中国,还是当代的非洲或中亚国家,政府官员获得任命,靠的不是自己的资格,而是与统治者的亲戚或私人关系。权力不在职位,而在担任此职的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就是指家族统治被官僚机构所取代。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有明确专长、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级官职、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⑪
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⑫政府内确实有很多留用的家族官员,尤其是在高祖统治的早期,因为皇帝需要反秦和内战盟友,以帮助自己巩固新政权。但在中央政府,非人格化基础上选出的官员逐一取代家族官员。朝廷显贵和执行君主决策的永久官僚机构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差别。
始于公元前 165 年,皇帝昭告全国高级官员,推荐定额的优秀青年以任公职。汉武帝治下,官员被要求担保其推荐人选的孝悌和正直。在公元前 124 年,郡官推荐的学生赴都城长安的太学参加考试。考试成绩最好的,接受老师和学者的一年培训,以钦准的儒家经典为基础,然后再次参加考试,以担任政府要职。用人的来源也在进化,例如设立专职人员巡游帝国查找人才,或邀请公众就帝国现状撰文参加竞赛。这种非人格化用人,允许非汉族人才脱颖而出,例如出身匈奴的军事将领公孙昆邪。⑬
公元前 5 年,中国的编户人口是六千万,在首都和省级供职的就有大约十三万官员。政府设立专门培养公职人员的学校,训练十七岁或以上的青年,测试他们阅读不同文体、管账等能力。(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将变得更为成熟。)汉朝仍有很强的家族因素,高官可推荐儿子或兄弟担任要职,推荐制度肯定不能杜绝一切私人影响。就像后续的朝代,任人唯贤仍有教育条件的限制。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培育出满腹经纶的儿子,有资格获得推荐或参加考试。
尽管尚有家族制的残余⑭,根据韦伯的定义,汉朝的中央政府日愈官僚化。职位最高的官员是三公,从高到低分别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有时,丞相职位一分为二,分成左右丞相,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三公之下是九卿,各有自己的僚属和预算。最重要的卿中,有掌管宗庙祭祀的奉常(后改称太常)、负责皇帝禁卫的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负责皇宫和京城守军的卫尉、负责皇帝财政的少府、负责司法的廷尉、负责粮食和税收的大司农。在当时农业社会里,这最后一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手下有六十五个机构,派遣高级官员去各州帮助管理谷仓、农活、水利。⑮
理性的官僚机构不一定追求理性的目的。奉常手下的机构分管奏乐(太乐)、祝祷(太祝)、牺牲(太宰)、星象(太史)、占卜(太卜)。太史向皇帝提供举办大事和仪式的凶吉日期,还监督文官考试。太祝下设三十五名僚属,太乐掌管三百八十名乐人,政府的规模于此可见一斑。⑯
汉朝政府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中国截然不同于罗马,后者雄心勃勃的将军,如庞培(Pompey)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经常争夺政治权力。中国也不同于军事政变频繁的现代发展中国家。
这不是因为中国缺乏军人权威或魅力,其历史上充满了常胜将军和赫赫武功。即使在战国之后,中国仍继续打仗,主要与草原游牧民族,但也包括朝鲜、西藏以及南方部落。几乎所有朝代的创始皇帝,都凭借自己的军事能耐而登上龙位。如我们所知,刘邦原是农家子,全凭军事上的组织和战略能力才当上汉高祖,他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到了唐朝,像安禄山那样野心勃勃的将军也试图争夺王位。唐朝的最终崩溃,是因为防御北方野蛮部落的边境军队得以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一般来讲,征战成功的王朝创始人一旦登基,就会卸下戎装,实施文官统治。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摒除将军于政治之外,放逐野心军人至遥远边境,镇压妄图起兵造反者。不像罗马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s)或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皇帝的宫廷卫士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扮演过王者之王的角色。考虑到战争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中国文官统治为何如此强大?弄清此事非常重要。
原因之一是军事等级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太尉、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按理说,其地位都高于九卿,但这些职位经常是空挂的。它们多被认为是仪式性的,没有真正军事权力,通常由文官担任。此时,军队中尚无专业军官,皇帝手下的官员出将入相,被认作文武双全。一旦开国的内战结束,军事长官通常被派去边远的草原或要塞,远离文明。抱负不凡者所追求的,不会是这种职业。⑰
这些理由又带出新的疑问,中国制度中的武官为何获得如此低下的威望,答案很可能是规范化。春秋和战国的严峻考验中涌现出一种思想:真正的政治权威在于教育和教养,而不在于军队威力。觊觎王位的军人发现,必须披上儒家学问的外衣,方能获得他人的信服;必须让儿子接受大儒的调教,方能继承王位。光说笔杆子比剑更为强大,这似乎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文官政府得以成功控制军队,最终还得依赖有关合法权威的规范思想。如有需要,美国军队明天就可夺走总统权力,但它没有这样做。这意味着,大多数军官即使在梦中也不想去推翻美国宪法,如果真的想做,他们指挥的大多数士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汉朝在两种利益群体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创建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东周式的动乱和战争;另一方面,全国的地方精英又试图尽量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秦始皇打破制度上的平衡,过于偏向集权国家,所侵犯的不仅是家族精英的利益,而且是普通农民的利益。农民以前面对地方领主的暴政,现在则换成了国家暴政。汉朝重作平衡,既考虑曾是秦朝打击对象的封王和贵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渐减少他们的影响。它的儒家思想,虽糅入法家精神,但又矢口否认,使自己重归合法。西汉创建的国家是稳定的,因为大家达成妥协。但与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尽量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新平衡是成功的。除了篡位皇帝王莽(公元前 45—公元 23 年)短命的“新朝”,汉朝存活了四个多世纪,从公元前 202 年到公元 220 年。这是颇不寻常的政治成就,但很遗憾,最终还是不免寿终正寝。
第 9 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四百年汉朝为何倒塌;大庄园增长的意义和马尔萨斯式社会的不公;门阀士族攫取政府和国家变弱;中国意义的国家
不能假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就能自我持续。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初只是一篇名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的文章。他认为,与现代化理论的循序渐进相反,没有理由可以假设,政治发展比政治衰败更有可能。社会中各竞争力量取得平衡,政治秩序便会涌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和外部都会发生变化。当初建立平衡的参与者在进化,或干脆消失了,又出现新参与者;经济和社会条件也会发生变更,社会遭遇外部侵略,或面对新的贸易条件,或引进新的思想。因此,先前的平衡不再有效,引起政治衰败,直到现存参与者发明新的规则和制度来恢复秩序。
汉朝的崩溃原因多种多样,涉及早先政治平衡方方面面的变迁。公元 2 世纪,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干涉,汉朝皇族的团结和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破坏。除了中国,宦官还在很多帝王的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已被阉割,不再有性感觉和性能力,所以深得信任。他们没有家庭,在心理上完全依赖主人,也不会想方设法为子女(因为不存在)争夺利益。他们扮演重要角色,帮助中国皇帝避开强大自治的官僚机构,并慢慢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利益。
先是外戚梁太后一族的领袖挑选软弱的汉桓帝(公元 147—167 年在位)继承皇位,以便自己的宗族获得政府高位和特权。不久,大难临头。皇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发动了现代拉丁美洲人所谓的自我政变(auto-golpe),残杀梁氏外戚。宦官摇身一变,成了强大政治力量,获得皇帝褒奖的官职、免税等,从而威胁了官僚和儒家的地位。始于 165 年,官僚和儒家开始发起反宦官运动,最终取得彻底胜利。①
环境条件令形势雪上加霜。173、179、182 年发生瘟疫;176、177、182、183 年发生饥荒;175 年发大水。广大民众的悲惨导致道教的兴起,它在农民和其他庶民中吸引众多信徒。儒家是一种道德,不是超现实的宗教,一直是精英的行为准则。道教源于古老的民间信仰,现在变成非精英的抗议宗教。184 年爆发的黄巾(他们头戴黄色头巾)起义以它为精神支柱,更因过去十年中农民所忍受的艰辛,而迅速星火燎原。虽在二十年后遭到血腥镇压(据传死去五十万人),它摧毁了大量的国家设施和生产力。②这些灾难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骤减,从 157 年到 280 年,骇人听闻地减少了四千万,等于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③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家族精英攫取国家权力以削弱中央政府,是汉朝衰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秦朝消灭封建主义,创建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这一努力现在遭受极大挫折。在中国,亲戚关系再次成为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途径,一直延续到 9 世纪的晚唐时期。④
但这不是周朝封建主义的复辟。秦朝以来已有太多变动,包括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披上礼仪合法性的宫廷。西汉已逐步消除封地上的家族影响,当贵族家庭卷土重来时,他们没有重建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参与中央政府机构。周贵族和汉贵族之间的区别,有点类似 17 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之间的区别:英国领主仍住在自己庄园,行使地方上的权力;而法国贵族被迫迁去凡尔赛,以靠近宫廷和国王来谋取权力。在中国,宫廷中的权力就是通向地产的阳关大道,有权有势的官员可获得土地、侍从、农民、免税特权。
富人更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大庄园(latifundia)愈益扩张。它们受贵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长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这加剧了贫富悬殊,一小群贵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财富。他们逐步剥夺政府的税收,因为自己的富饶农地无需纳税,这些家庭就是今天所谓的追求租金精英的早期版本。他们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的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⑤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权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⑥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 1800 年之前,效率增长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⑦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人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⑧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定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 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 28 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 17 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从——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业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 7 年,有人建议大庄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 亩等于 0.165 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国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⑨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复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帝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的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个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的中央政府。⑩
日益增加的土地不均,加上 2 世纪 70 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黄巾起义终于爆发。秩序荡然无存,中央政府因派系斗争而分崩瓦解,这一切促使大户家庭躲在围墙后的庄园和地区,不再接受软弱国家的控制。汉朝的最后几十年,中央国家完全崩溃,权力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他们要么选择自己中意的皇帝,要么自己黄袍加身。⑪
国家分裂和家族制复辟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最长命的朝代汉朝,终于在公元 220 年彻底崩溃。除了很短的例外,中国在今后的三百年中不再有统一国家。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小说之一《三国演义》,讲的就是东汉到晋朝这段时期。晋朝始于 280 年,但持续很短时间。小说作者罗贯中,在明朝写成(也许在 14 世纪晚期,但没有确定日期)这部作品。其时,明朝已从蒙古人手中解放中国,在汉人自己统治下,再度统一中国。⑫小说的潜在主题是中国的不统一(内乱),造成混乱和外国侵略(外患),还阐述了恢复国家统一的条件。在塑造现代中国人历史意识方面,《三国演义》可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媲美。它被改编成电子游戏和无数电影版本。北京要求统一台湾,其背后对分裂的痛苦记忆,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看,值得关注的是亲戚关系和家族制,如何在汉和隋之间的空白时期(581 年中国再度统一)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的组织原则。中央国家的力量,正好与家族团体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现代国家获得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预设的政治组织。
汉朝终止之后的时期是非常复杂的,但从发展角度看,细节就不那么重要。中国最初分裂成所谓的三国:魏、蜀汉、吴。魏得以在西晋名下重新统一中国,但很快发生内战。西晋的都城洛阳在 311 年遭到匈奴部落的洗劫和占领,匈奴国王在中国北部创建众多外族朝代中的第一个。逃至南方的西晋幸存者,在长江边上的建康(现代的南京),也建立数个南方朝代中的第一个,即东晋。北方和南方一分为二,都经受了持续动乱。在北方,洗劫洛阳导致了所谓十六国的部落战争。有两次新的野蛮人入侵,第一次是原始西藏人的氐和羌部落,第二次是拓跋部落,即突厥鲜卑人的分支。拓跋部落建立了北魏(386—53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汉化。他们冠中国人的姓,与汉人家庭通婚联姻。拓跋部落中的紧张导致再一次的内战,到 6 世纪早期分成东魏和西魏。在南方,迁自北方的旧宫廷重组东晋朝代,大量贵族家庭和侍从跟踪而来。到 4 世纪中,东晋灭于军事政变,之后又有武将建立的数个孱弱朝代。⑬
汉朝军阀曹操和儿子曹丕在 220 年建立魏国,制定九品中正制,从而加速了始于东汉的家族制倾向。每个郡和州,都派有仲裁人,官名叫中正,依据品德和能力评议官职的候选人。不像早先的汉朝推荐制度,遴选仲裁人的不是中央,而是地方,显然要受更多地方精英的影响。新招聘制度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又与各层官位挂上钩。汉朝时,不做官的人仍可有高级地位。自从有了九品中正制,官位变成争取高级地位的唯一途径。加上对血统的愈益重视,子承父位便成家常便饭。⑭
在强大中央政府的手中,九品中正制可以是削弱豪门、加强国家的对策。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法国君主出售一套精细的爵位和等级给贵族阶层,从而削弱该阶层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每个贵族家庭太忙碌了,沾沾自喜,瞧不起底下人,以致不能互相合作来保护自己广泛的阶级利益。3 世纪的中国,九品中正制却似乎成了贵族攫取国家的手段。庶民人才不能再通过推荐或考试攀至高位,这些官位只保留给现任官员的孩子,好像他们是战胜部落的领袖。其时的皇帝往往不能保证自己的宠臣得到高位,因为宠臣缺乏合适的血统。这一切证明,真正的权力不在国家手中,而在贵族家庭手中。⑮
西晋垮台后,家族制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发展。在南方,东晋宫廷由本地大户和洛阳迁来的贵族流亡者所掌控。他们把九品中正制也带来,政府操纵在王、陆、张姓的大户手中,都是高级血统的近距离表亲。⑯
大庄园的继续扩张加剧了贵族控制。早在 3 世纪晚期,西晋颁布土地法,规定所有农民有权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以换取他们的徭赋负担。它也规定了贵族家庭拥有土地、免税租户和侍从的最高限额。但它和东晋时颁布的类似法律,从没得到执行。像王莽夭折的土地改革,这些失败证明了大庄园势力的日益壮大,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控制和资源。⑰
在北方,战胜的羌人和突厥人首先是部落组织,就把自己的主要宗族安插到重要官位。初期仍有持续的冲突和部落之间的争战,这些外族家庭便是整个地区的领导精英。汉朝时兴起的中国贵族家庭,要么南逃去投奔东晋宫廷,要么退回自己的庄园。他们仍拥有地方权力,但避开宫廷政治。5 世纪的后半叶,北魏朝代得以集中权力,5 世纪 90 年代迁都到历史名城洛阳,事情于是开始发生转变。魏孝文帝禁止在宫廷使用鲜卑语和鲜卑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邀请主要的汉贵族家庭赴宫廷供职。他得以创造统一的贵族阶层,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就像南方的九品中正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多数高级官员同属一个宗族,贵族等级又是晋升高级官位的必要条件。⑱大庄园兼并土地,贵族阶层权力日益增加,也都是北方的难题。485 年北魏颁布一条法令,限制大庄园,保证农民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⑲
强大的中国国家
6 世纪中期,北方的东魏和西魏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577 年,北周进攻并打败了北齐。时任北周将领的杨坚成为风云人物,他出身鲜卑族,妻子来自匈奴一个强大氏族。杨坚在内斗中击败对手,于 581 年建立隋朝。他的军队在 587 年打败南方的梁,在 589 年打败南方的陈。这是 220 年汉朝崩溃以来,中国在单一中央政府治理下的首次统一(实际领土与秦汉时不同)。谥号为文帝的新皇帝把京城搬回长安,以汉朝为榜样重新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他儿子兼继位人炀帝执迷于运河营造,还向朝鲜的高句丽王国发起草率的进攻最终失败。他死于 618 年,隋朝很快消失,这一段空白很短。名叫李渊的北方贵族在 617 年起兵,下一年攻取长安,宣布成立新朝代。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 10 世纪初。
隋唐重建中央集权,但没能终止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们在间隔的空白时期,攫取了众多小国的政府权力。我们将在第 20 章和第 21 章看到,反对家族制的斗争将持续随后的三个世纪,一直要到 11 世纪的宋朝,行政机构才返回汉朝时的“现代”基础。中国国家的重新集权,得以激活像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那样的制度。在先前的数世纪中,这些制度在门阀贵族面前一输再输。
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所提出的最有趣问题之一,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个命题绝对不是琐碎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尽管有查理大帝和其他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然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像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众多国家,相互竞争,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有了。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边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鲜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得以重新统一是因为秦汉两朝已创下先例,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谁有此权利呢?这是个复杂题目,要作出回答,先要认真弄清中国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朝代的间隔期尤其富有启示。这段时期无疑是一场自由竞赛,政治权力的门外汉——农家子、可疑种族背景的外族人、未受儒家教育的军人——都有机会攀爬到制度的尖顶。中国人愿意向他们和其后裔提供合法性和绝对权力,其原因有点扑朔迷离。在后面论以及其他的改朝换代时,我会重新回到这一问题。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后续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与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颇不寻常。
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程与印度截然不同。这两个社会作为“亚洲”或“东方”的文明,经常放在一起。它们在早期表现出相似特征,后来却各奔东西,南辕北辙了。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国家,缀以分裂和衰败;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国和公国,缀以短暂的政治统一。我们如果察看印度的历史长河,它是民主国家的事实就丝毫不足为奇。这不是说印度早期就有民主思想,从而创下先例;而是说很难在印度政治中,建立起专制统治。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其原因在宗教和思想的领域。
第 10 章 印度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发展因婆罗门教的兴起而不同于中国;瓦尔纳和迦提;印度早期的部落社会;印度亲戚关系的特征;印度在建国大道上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政治发展明显与中国形成分流。一开始,它们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会组织。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国家从印度北部的部落社会中脱颖而出,比中国晚不了太多。在这两个文明中,酋邦和国家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是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开始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权力。
就战争而言,它们的轨迹却截然不同。印度从没经历像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持续数世纪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确,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受地理局限较少;与其顺从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倒不如迁移他处。①无论如何,早期印度国家无须像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应对社会动员的极端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从政治观点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一分为二。中国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和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只是国家雇员,严格屈从于皇家权力。中国祭司从没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判然分开,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权威。虽然它没有组成像天主教一样的严密集团,但仍享有类似的道德权威,不受国家干涉。此外,婆罗门阶层被当作神圣法律的监护人,而这法律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且具更长历史。所以,国王必须遵从他人所编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国皇帝。跟欧洲类似,印度也有可称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权力。
第二项重要社会发展是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体,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②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也就是说,异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统,必须在迦提范围内谈婚论嫁,鞋匠女儿必须嫁给不同氏族的鞋匠儿子。成员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一点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会的分支式特征。但他们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广泛分工的一部分。与工业社会相比,这种分工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又远比单纯的部落社会复杂。依照涂尔干的标准,迦提显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双重特征——这是指,个人既是自我复制相同单位的成员,又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助。
在中国,出现于周朝的国家在社会顶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组织。宗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国家和亲戚团体之间出现了权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变弱。到最后,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在印度,瓦尔纳和迦提所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以瓦尔纳和迦提为定义的印度文明,获得广泛扩散,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东南亚,统一了语言和种族的众多群体。不像中国,这块辽阔领土从没受到独家政治权力的统治,也没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 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政治体中不少是外国入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印度部落社会
与中国相比,我们对印度部落社会以及其向国家的过渡,所知极其有限。虽然处于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印度社会的文化水平要低得多,绝对比不上记载商朝政治活动的大量甲骨文或东周的冗长编年史。印度最早的定居点是旁遮普(Punjab)和西部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它的哈拉帕(Harappan)文明仅留存于考古学资料。③我们所了解的印度早期社会组织,都是从“吠陀本集”(Vedic texts)中推断而来。该本集记载圣歌、祈祷、注释等,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或三千年,以前是口口相传,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中期才变成书面记录。④印度第一个本土帝国是孔雀王朝(Mauryas,公元前 321—前 185 年),在很多方面,它又是最伟大的本土帝国。但它的文字记载仅有流散到次大陆的数块法令岩石,再加上希腊、中国和其他外国著作的提及。这里可能有因果关系:缺乏流传广泛的书面文化,尤其是在印度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中,大大阻碍了强大集权国家的开发。
印度—雅利安部落自黑海和里海(Caspian)之间的俄罗斯南部迁移至印度,由此开创了印度政治发展。某些部落群体转向西方,成为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其他欧洲团体的祖先;另一群体朝南抵达波斯,第三群体向东到阿富汗东部,再穿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峡谷(Swat Valley),直达旁遮普和印度河—恒河(Indo-Gangetic)分水岭。现在通过 Y 染色体和线粒体,可以追踪印度—雅利安群体之间的血缘关联,但首次确定相互关系的却是语言学家,他们在印度梵语(Sanskrit)和西方语言之间找出相似,因为它们同属更大的印欧语系。
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群,以牛为食,并已驯养马匹。他们第一次迁入印度河—恒河平原时,碰上他们称作达萨(dasas)的其他定居者,后者可能属于不同种族,使用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或澳斯特罗—亚细亚语(Austro-Asiatic,又称南亚语)。⑤这段时期,这些部落的行为与他处部落非常相似。他们袭击达萨社区,偷他们的牛,与其他部落打仗。如果遇上强有力的军事抵抗,他们就退避三舍,该地当时仍属人烟稀少。吠陀本集中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Rg Veda),它提及部落之间的频繁冲突、拉贾(Raja)或部落领袖的涌现、确保战争成功的祭司。印度—雅利安人开始在恒河平原安顿下来,从单一游牧业转为游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种植由小麦改成稻米,农业技术因此获得改进,使更多盈余、更突出的送礼和礼仪奉献成为可能。大约同时,奶牛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从印度—雅利安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像努尔人一样),到受人崇拜的图腾动物。⑥
在这个发展阶段,与我们已经解说的其他分支式社会相比,印度—雅利安社会似乎没有任何的别具一格。例如,拉贾一词经常被译成国王,但实际上只是当时的部落领袖。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指出,拉贾的主要词根是“发光、带领”,但它的另一词根是“使人满意”。这显示,拉贾在部落中的权威有赖于众人的共识。⑦拉贾又是军事领袖,帮助保卫自己的社区,率领众人向邻近部落发起袭击以攫取战利品。他的权力受亲戚团体集会的制衡,如维达萨(vidatha)、萨巴(sabha)、萨米提(samiti)。其中的维达萨,专门负责在社区内分派战利品。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拉贾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奉献和盛宴中分配资源的能力。拉贾们彼此竞争,看谁可摆出最多的财富以及最终的浪费,很像夸扣特尔(Kwakiutl)和其他西北太平洋海岸印第安人的庆典。⑧
像其他部落社会,印度没有法律制度,以赔偿金解决争端(杀人赔偿金是一百头奶牛)。拉贾没有征税权力,也不在现代意义上拥有土地。所有权都在家庭手中,还有对亲戚团体的义务。像其他分支式社会,印度—雅利安部落可团结起来,组成像般庶王朝(Panchalas)那样的高层次分支,高层次分支之间可以再次联手,以达成更高层次的联盟。
印度家庭和亲戚关系
像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雅利安部落也组成父系家族的血统。19 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包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和亨利·梅因,在希腊、罗马、凯尔特、条顿、当代印度人中,找到甚多相似的亲戚结构。我曾提及,希腊、罗马、早期印度人都在家庭祭坛供养圣火(参看第 3 章)。从 1862 年到 1869 年,梅因是在印度度过的。作为总督会议的法律成员,他潜心攻读印度的原始文献。他确信曾有过统一的“雅利安”文明,包括罗马和印度。由于共同的历史起源,他们有关财产、遗产、继承的法律条款都非常相似。他相信,印度以某种方式保存了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古代形式,人们可从印度的现在看到欧洲的过去。⑨
后来的人类学家对梅因提出严格批评,认为他过于简化印度的亲戚关系,并在它之上强加了不妥当的进化结构。在显示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种族起源上,他似乎确有强烈兴趣,也许是为了提供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基础。但他仍是比较人类学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并以渊博知识展示,不同文明发展了相似方案,以解决社会组织问题。当代人类学家都意识到,各社会的亲戚结构中存有难以置信的微妙差异,但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不清同级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似程度。
像中国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当代印度亲戚组织,投射到早期的印度—雅利安人。亲戚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原则,从没在印度消失,这不像西方,倒与中国相近。所以,印度的社会组织自有其潜在的持续性,我们必须心领神会,方能解释其政治发展的此起彼伏。
印度的亲戚组织分属三大区,与次大陆的三大民族语言区相对应:第一,北部,其居民是讲梵语的印度—雅利安后裔;第二,南部,其居民讲达罗毗荼语;第三,东部,与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非常相似。⑩几乎所有的印度亲戚团体,都形成分支式的世系,绝大多数是父系社会。然而,在印度的南部和东部又有重要团体,分属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例如马拉巴地区(Malabar)的那雅人(Nayar)。⑪跟中国一样,后裔团体基于共同祖先,通过某种形式的共有财产而取得集团身份。
印度亲戚关系不同于中国,因为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参与其中。迦提确立异族通婚的界限。这意味着,任何人通常不得与自己瓦尔纳或迦提之外的人谈婚论嫁。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等级森严,较低地位女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男子,或较低地位男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女人(后者比较少见)(人类学家称之为向上通婚[hypergamy]和向下通婚[hypogamy]),它都设有精细规则来作规范。每个瓦尔纳和迦提的本身,在地位级别上又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所以,即使在自己分类中通婚,也会遇上甚多禁忌。例如,婆罗门中有些必须主持家庭仪式,而另一些则不必;有些主持葬礼,而另一些则不必。婆罗门最高级别的男子,绝不可能娶最低级别婆罗门的女儿(即主持葬礼的)。⑫
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它们在亲戚规则上的差别涉及表亲通婚,从而影响政治组织。在北方,儿子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不可与第一表亲通婚。在南方,儿子同样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但是,与父亲姐妹的女儿通婚,不但允许,而且获得鼓励。这种做法叫作交叉表亲(cross-cousin)的婚姻。而平行表亲(parallel cousin)的婚姻,即与父亲兄弟的女儿通婚,则不可,因为这违反了氏族的异姓通婚规矩。所以,男子可与姐姐的女儿和舅舅的女儿通婚。换言之,像很多阿拉伯部落一样,南方的印度部落倾向于把婚姻(以及相关的遗产)局限于狭窄的亲戚小圈子,相连的血统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在北方,家庭为了孩子能找到合适的配偶,被迫在更大范围内撒网。达罗毗荼的交叉表亲婚姻,加强了其社会关系狭小内向的特征,这存在于所有的部落社会。⑬可以假定,这样的婚姻实践降低奖励,使南方的国王不愿去寻求远方的婚姻同盟,如建立现代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Aragon)和卡斯提尔女王(Castile)的联姻。
这段简洁的概述,尚未触及印度复杂亲戚关系的皮毛。对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虽然可做出一个概述,但这两个地区在亲戚规则方面,因地理位置、种姓制度以及宗教的不同,而展示出巨大的内部差异。⑭
过渡到国家
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国案例。我们有两种关于国家形成的虚幻解说,与人类学家的暴力和社会契约理论遥相呼应。第一种解说,“吠陀本集”中较晚文本的《爱达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或译《他氏梵书》)解释:“众神与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敌人手中吃尽苦头,便聚会讨论,决定要一名拉贾来率领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罗(Indra)为他们的国王,战势很快获得逆转。”这个传奇显示,印度最早的国王应人们和军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职责是率领部下打仗。⑮第二种解说来自佛教资料:
当人们丧失原始的光荣,阶级差别(瓦尔纳)遂出现。他们签订协议,接受私人财产和家庭的制度,盗窃、谋杀、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们聚会讨论,决定要选出一名成员来维持秩序,报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获。他被称为“大选出王”(Mahasammata),头衔是拉贾,因为他取悦于其他成员。⑯
佛教始终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为仁慈,更为温和。它强调非暴力,以及轮回转生的更为可行。所以,佛教徒认为国家形成获得大家同意,也属意料之中。但上述两种解说都不是历史记载。
实际的过渡也许牵涉到其他社会在建立国家时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讲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达萨人,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尔纳,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会阶层,而是两大社会阶层,分别是雅利安阶层和达萨阶层。所以很明显,从平等部落社会到等级国家社会的过渡,开始于军事征服。最初,达萨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语言而与征服者有所区别,到后来,达萨一词变成了从属或奴隶的代名词。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时间在印度—雅利安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⑰剥削从属阶级创造庄稼收获的盈余,自己部落不必投入劳动,便可收取一笔地租。“拉贾”的意思,也从部落领袖变为“自土地或村庄享受收入的人”。⑱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早期,等级的日益分明又与永久定居、雏形城市、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⑲在土地上劳作的,不再是亲戚团体共同协作的家庭,而是与地主并不沾亲带故的农民。⑳为了使低级阶层永远处于被主宰的地位,为了防止他们逃逸,常备军和领土的政治控制变得不可或缺。
跟中国相似,促进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 800 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铁斧可用来清除密集的森林,铁犁可帮助耕地。国家没有控制铁的生产,但铁工具的使用带来威望,并增加国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总水平。㉑
像中国和其他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社会,独特和永久的祭司阶层婆罗门,赋予部落领袖愈益增长的合法性,使后者权力获得很大提升。拉贾行使政治权力,祭司通过仪式使之合法化;拉贾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资源来补偿这些服务。早期的拉贾凭借祭司而获得神性,从而将自己职位转为祖传财产,通过渐渐流行的长子继承权再传给儿子。显而易见,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长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会的萨巴失去了选择氏族领袖的能力,开始扮演咨询的角色。国王的授权仪式发展成持续一年的献祭仪式;其间,拉贾经历净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终结时,婆罗门再赋予他职位和神性。㉒
公元前 6 世纪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会已从部落过渡到雏形国家或酋邦,被称为伽那—僧伽(gana-sangha,编按:前者意为“众多”,后者意为“集合体”)。北方的国家,如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卢(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领土,治理城市中相对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权政治体。它们等级森严,王位世袭,其精英向农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会的特征:等级松弛,领导权模糊,不能像真正国家一样行使强制权力。㉓
弯路
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最初,社会组成父系氏族的联合体,信奉祖先崇拜;大约在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时,转向等级分明、世袭领袖、统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统治者比印度的统治者行使更多权力,但差别不很惊人。
首批真正国家出现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印度的政治演变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中国模式分道扬镳。印度国家没有经历五百年日益激烈的连续战争,就像中国早期国家在东周时所承受的。之后的数世纪内,印度国家也彼此打仗,也与伽那—僧伽交战,但从没达到中国所实施的相互灭绝的惨烈程序。如我们所知,中国独立政治体的总数,从东周初的数百持续下跌到东周末的一枝独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较少较不激烈的战争,以及较低程度的统一。较为原始的伽那—僧伽,没被强大的国家所兼并,一直生存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在发展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体不得不仿效邻国,而印度政治体显然没有此种压力。公元前 3 世纪末,孔雀王朝得以统一次大陆的大部,建成单一帝国,但仍有部分地区从没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统治也没得到彻底的巩固。孔雀王朝持续仅 136 年,这种幅员辽阔的政治体再也没有在本土政权下重现,直到 1947 年印度共和国出现。
差别的第二领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祭司主持对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没有自己的司法权。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时,或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统治者时,没有作为机构的祭司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合法性可由任何人赋予,从农民、军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则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国那样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吠陀本集”创作时,它发展成精细的形而上学系统,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新兴的婆罗门宗教,把重点从个人的祖先和后裔转到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为这超然世界把关的就是婆罗门阶层,其权威是很重要的。他们在未来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国王的血统,而且是最低级农民的福祉。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分别是雅利安人和达萨人的两大瓦尔纳,进化成四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处于顶端的是祭司阶层,他们创作了构成“吠陀本集”的仪式祈祷。随着宗教的发展,历代的婆罗门默记这些祈祷。这礼仪咒语的倒背如流成为他们的专业,与其他瓦尔纳争夺社会地位时,又变成其优势。法律就从这些仪式中脱颖而出,起初只是惯例,口口相传,最终写入法律书籍,像英国人所称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所以在印度传统中,法律并不来自政治权力,这不像中国;它的源泉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为崇高。事实上,《摩奴法典》讲得很清楚,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不可颠倒过来。㉔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 600 年走上一条大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㉕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他们相互依赖,以求生存。印度虽然没在当时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中国则没有。很明显,印度始终不能以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们将对此作更仔细的审视。
第 11 章 瓦尔纳和迦提
经济与宗教,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印度的社会生活因宗教而变得包罗万象;印度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启示
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经济利益与思想到底谁占鳌头?这是社会理论家最古老的争辩之一。从卡尔·马克思到持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物质利益享有优先权。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这个神话是精英编出的,为了辩护其对社会他人的掌控。很多现代经济学家不像马克思那么尖刻,但仍认为他们的功利最大化的理性架构(rational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足以解释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曾表示,不同意者只是研究得不够认真。①思想被认为是外在因素,也就是说,为了解释物质利益,它只是在事后建立的,并不是社会行为的独立原因。
站在该论点对面的是一批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包括韦伯和涂尔干。他们认为,宗教和宗教观念是主要因素,既是人类行动的动力,又是社会身份的来源。韦伯坚持,在现代经济学家所运作的架构中,个人是主要决策者,物质利益是主要动机;但最终,这架构本身又是新教改革的观念的产品。写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韦伯继续写出有关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著作。它们显示,要理解经济生活是如何组织的,宗教观念不可或缺。
如果要举马克思一方的例子,即宗教在为少数精英掌控他人作辩护,一定不会选普世平等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而要选公元前最后两个千年出现在印度的婆罗门教。根据《梨俱吠陀》:
众神奉献牺牲时,以普鲁沙(Man)为祭品……
他们分解普鲁沙时,将他分成多少块?
他的嘴和双臂叫什么?双腿和两足又叫什么?
婆罗门是他的嘴,他的双臂成为武士。
他的双腿成为吠舍,从两足生出首陀罗……
众神作完奉献,这是神圣法律之首。
这些大力神飞天,那里住有永久神灵。②
婆罗门不仅将自己安置在这四大社会阶层的顶端,而且授予自己对祈祷和圣歌的永久垄断。那些祈祷和圣歌在赋予合法性的各种仪式中不可或缺,从最高级的国王授权,到最低级的婚礼或葬礼。
以纯唯物主义来解释印度社会中的宗教功能,难以让人满意。首先,它无法解释神话中的实际内容。如我们所见,在过渡到国家的前夕,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上的相似。中国精英,像每个已知社会的精英,也利用赋予合法性的仪式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但中国人想象不出一个像印度那样的既深刻又复杂的形而上学系统。事实上,即使没有超然宗教的帮助,他们仍能有效夺取和保有权力。
此外,在印度占居首位的不是拥有强制和经济权力的精英,反而是仅有仪式权力的精英。即使有人相信物质原因是最重要的,他仍要回答这一疑问:为什么刹帝利和吠舍——武士和商人——甘愿臣服于婆罗门,不仅向后者提供土地和经济资源,而且让后者控制自己个人生活的隐私。
最终,就印度社会而言,不管是经济解释,还是唯物主义解释,都必须解释该制度为何经久不衰。公元前 600 年,婆罗门教适合精英小团体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不适合印度社会中其他阶层和团体的利益。为何没有反精英运动的兴起,宣扬新的宗教思想,以提倡普世平等?在某种意义上,佛教和耆那教就是抗议宗教。两者继承了很多婆罗门教的形而上学假设,但在次大陆却得不到广泛接纳。对婆罗门教霸权的最大挑战,却是外国入侵者凭借武力进口的——莫卧儿帝国带来了伊斯兰教,英国人带来了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必须把宗教和政治本身看作行为和变化的动力,不可视之为宏大经济力量的副产品。
印度宗教的合理性
就现代经济的需求而言,很难想象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制度,其兼容度低于婆罗门教迦提制度。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话。信息流通的灵活劳工市场,能够导致个人处境的最大改善和资源的优化分配。相比之下,根据迦提制度,个人天生只能从事有限行业。他们必须继承父业,必须与同一迦提团体的成员通婚。投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人永远都不能在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迦提制度中,社会升迁只适用社区总体,不适用个人。所以,迦提的团体可决定搬往新区,或开发新的商机,但不允许个人创业。该制度对社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对某些婆罗门来说,光是看见贱民就需要一个冗长的净化仪式。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这很不合理;对接受婆罗门教根本前提的人来说,这又完全合理。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中最细微的规则,作为宏观形而上学系统的逻辑结论,却是非常完美的。现代评论家经常试图以实用或经济功利来解释印度的社会规则,例如,禁食奶牛刚开始只是卫生措施,为了避开受污染的牛肉。除了不符合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像努尔人一样吃奶牛的事实,这种解释无法看透主观上体验到的社会凝聚,反而折射了评论家自己的世俗偏见。
韦伯认识到婆罗门教理后面的高度合理性——自然神学(theodicy),或上帝的理由,他称之为“天才的手笔”。③去印度修道院研读的西方皈依者,往往能体会到这一天才,其始于否认现实的现象世界。下面是皈依者自己的话语:
所有印度宗教系统,其终级目的是为了超越生命(moksha)。它们都假设,感知的存在是对现实(maya)的误解,仅是外表,躲在背后的才是终级存在的梵(brahman)。它无形无体,正因为无形无体,所以永恒。它是唯一的现实。我们所感觉的,我们因自己的物质存在而有所依恋的,都是稍纵即逝的(都会凋零和死亡),所以是虚无缥缈的(maya)。不像有些解说者所宣称的,存在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获得”对梵的认同,而是排除万难去体会,个人内心(atman)中真实永久的东西就是梵。④
凡人的生存涉及物质的生物生存,其对立面,就是超越此时此地的无形无体的真正存在。早期婆罗门认为,“与分娩有关的流血、与疾病和暴力有关的痛苦和变形、与人体排泄物有关的污浊恶臭、与死亡有关的衰败腐烂”,都会牵涉凡人生命,都需要得到超度。这就是为什么婆罗门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授予自己特权地位:“污染物质渗透了凡人的生存,在现世和漫长的上升轮回(samsara)中,需要婆罗门主持的仪式来予以控制和削减,这是获得解脱(moksha)的必要途径。”⑤
迦提制度源于业力(karma),即个人在现世所做的一切。职业的地位有高有低,取决于它们离污染源有多远——诸如血液、死亡、泥土、腐败的有机物。皮革匠、屠夫、理发匠、清扫夫、收生婆,以及处理动物尸体或死人的行业,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相比之下,婆罗门是最完美的,因为遇上血液、死亡、泥土时,他们可依赖他人的服务。这解释了婆罗门的素食主义,因为吃肉就好比吃尸体。⑥
社会升迁在现世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指望来世。业力只在代代相传时才有变更,因此,个人一生都陷于自己的业力。在迦提等级制度中,个人到底获得升级还是降级,则取决于自己是否履行了所属迦提的法(dharma),即良好行为的准则。未能遵守准则的,将在来世等级制度中降级,从而更加远离真正的存在。婆罗门教将神圣化赋予现有的社会秩序,履行现存迦提的法变成了宗教责任。
瓦尔纳秩序发展自同样的形而上学前提。前三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被认为是“两次投胎”,所以获得允许,进入仪式地位。包含大多数人口的首陀罗是“一次投胎”,只能希望在来世获得仪式地位。历史上不是很清楚,印度社会离开部落组织时,瓦尔纳和迦提的出现谁早谁晚。可能是宗族进化为迦提,它们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都有精细的亲戚关系规则。但也有可能是先进化为瓦尔纳,再为随后出现的迦提设置架构。⑦
宗教信仰所造成的迦提制度,创造了颇不寻常的组合,既有分支式的隔离,同时又有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每个迦提成为世袭地位,以调整现存的宗族系统。迦提设置了氏族的异姓通婚的外限,在众多分支式单位中,又倾向于成为自给自足的社区。另一方面,每种职业又是更大分工的一部分,所以需要相互依赖,从高级祭司到葬礼工。⑧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引用布兰特(编按:E. A. H. Blunt,1877—1941,英属印度殖民地官员)的资料:
理发匠联合抵制曾拒绝为他们婚礼跳舞的舞女。
在格拉克珀(Gorakhpur),一名地主试图中断皮革匠的生意。他相信他们在毒死自己的牛群(经常有如此的怀疑),便命令他的租户将无缘无故死去的牛的皮革故意割碎。皮革匠奋起反抗,命令他们的女人停止收生婆的服务。地主只好让步。
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又译阿默达巴德,位于古吉拉特邦),一名正在重盖屋顶的钱庄老板与糖果店主发生争执,糖果店主说服瓦片制造商,拒绝为钱庄老板提供瓦片。⑨
这不单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为每个执行自己功能的迦提,对其他迦提都具有仪式上的重要意义。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瓦尔纳制度对政治有巨大影响,它要求武士的刹帝利服从婆罗门。⑩根据哈罗德·古尔德(Harold Gould),“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有共生的相互依赖。王室权力需要连续获得祭司(即仪式)权力所赋予的神圣化,以维持神圣的合法性”。⑪每位统治者需要与宫廷祭司(purohita)建立私人关系,他作为世俗领袖所采取的每一次行动,都要得到宫廷祭司所赋予的神圣化。
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力在理论上的分离,何以在实践中对后者设限,初看上去不很清楚。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没有像天主教那样组成正式的中央权威机构。它有点像巨大的社会网络,单独的婆罗门互相交流和合作,但并不行使制度化的权威。单独婆罗门拥有土地,但作为制度的祭司阶层,不像欧洲教会,却没有自己的领地和资源。婆罗门肯定不能像中世纪的教皇,召集统领自己的军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 1076 年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革出教门,并迫使后者赤脚来卡诺莎(Canossa)请求赦免,这在印度历史中绝对找不出可媲美的案例。世俗统治者需要宫廷祭司来祝福自己的政治计划,在收买后者一事上,好像总能如愿以偿。印度宗教和社会的制度等级分明,各有分支,但它们如何使政治集权难以实现,我们还需寻找其他原委。
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限制了军事组织的发展,这个影响很明显。武士的刹帝利是瓦尔纳制度四大阶层之一,自动限制了印度社会军事动员的潜力。像匈奴、匈人、蒙古人的武装游牧民族,之所以如此强大,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动员几近 100% 的健壮男子。就必不可少的技能或组织而言,武装掠夺和游牧漂泊没有什么两样。仍是游牧民族时,印度—雅利安人曾经也很强大,但现已定居下来,建立了瓦尔纳社会。武士地位成为少数贵族精英的专业,如想加入,不但讲究训练和出身,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
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没有始终限制他人的加入。很多印度统治者出生于刹帝利阶层,但也有不少来自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新统治者夺取政治权力后,倾向于在事后获得刹帝利地位。以这种方式成为刹帝利,比成为婆罗门更为容易。⑫瓦尔纳四个阶层都参与战争,婆罗门中有级别很高的军事将领,首陀罗倾向于充当辅助部队。就从属关系而言,军队的等级制度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拷贝。⑬不像秦国和其他后期东周列国,印度政治体从未能动员大部分的农民。⑭考虑到仪式上对血液和尸体的厌恶,很难想象,受伤军人能从高贵战友手中获得很多救助。在采用新兴军事技术方面,如此保守的社会显然是迟疑不决的。他们在基督时代之后才放弃战车,比中国人晚了好多世纪;大象继续用于战争,尽管其效用早已被人怀疑。印度军队从没开发有效的射箭骑兵,以致惨败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人和 12 世纪的穆斯林。⑮
从社会上层一直到底层,印度社会以迦提为基础形成众多紧密结合的小集团,其组织动力正是由婆罗门教提供的。这是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二条途径。这些集团自我管理,不需要国家帮忙组织。事实上,它们抵抗国家的渗透和控制,政治学家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称之为软弱国家和强势社会。⑯这种情形维持至今,种姓制度和村民组织仍是印度社会的支柱。
19 世纪的西方评论家,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亨利·梅因,注意到印度社会自我组织的特征。马克思宣称国王拥有一切土地,但又指出,印度村庄在经济上偏向于自治,以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为基础(这种解释有点自相矛盾)。梅因指的是自我调整、一成不变的村庄社区,这种看法在维多利亚的英国非常流行。19 世纪早期,英国行政官员把印度村庄当作能幸存于帝国毁灭的“小小共和国”。⑰
20 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依据上述解释,想象出一幅本土村庄民主的田园画像,即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他们声称,这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源头,直到被英国殖民者破坏。现代印度宪法的第 40 条,详细解释了复原的潘查亚特机构,旨在促进地方民主,曾在 1989 年获得拉吉夫·甘地政府的特别关注。其时,政府正试图在印度联邦制中推动权力分散。但印度早期的地方统治,不像后来评论家和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实际上不是民主和世俗的,而是基于迦提或种姓制度的。每座村庄倾向于有个强势种姓,也就是说,其人数和拥有的土地都超过其他种姓,而潘查亚特制度仅仅是该强势种姓的传统领导组织。⑱
单独村庄自有地方的统治机构,不需要国家从外部提供服务。潘查亚特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司法,它依据惯例来裁决迦提成员之间的争论。村庄中的产权不是共有的,这有悖于马克思的想象。像其他分支世系社会,财产为复杂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单独家庭在处理土地时要面临很多责任和限制。这意味着,国王虽是名义上的主权君主,却没有真正“拥有”村庄土地。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征税和征地时,印度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往往非常有限。
商业活动也依据迦提,宛如不需外界支持的自控公司。从 9 世纪到 14 世纪,印度南部的贸易大多由像阿育尔(Ayyvole)那样的商人行会控制。它们派出的代表满布次大陆,与印度之外的阿拉伯人商人打交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长期控制印度洋、东非、阿拉伯半岛南部、东南亚的贸易。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组成全市大公司,吸引所有主要职业团体的成员。⑲在中国,贸易网络只靠宗族,不像印度同行那样组织良好。中国宗族的司法权,往往局限于家法、遗产和其他家庭琐事(尤其在强大政府时期)。印度的迦提除了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还发挥公开的政治功能。根据萨提希·萨贝瓦尔(Satish Saberwal),“迦提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各式场合:进攻性的,则争取掌控权和统治权……防御性的,则抵制国家和帝国入侵迦提领域……破坏性的,则任职于更大政治体,运用其权力和高位来谋取私人利益”。⑳迦提还为成员提供地理和社会上的升迁。例如,泰米尔(Tamil)纺织种姓的凯寇拉(Kaikolar),在朱罗王朝(Chola)时期改行,变成商人和军人;19 世纪后期,锡克人的木匠和铁匠离开家乡的旁遮普,迁往阿萨姆邦(印度的 Assam)和肯尼亚(非洲的 Kenya)。㉑这些决定由众多家庭集体作出,以便在新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印度北部,拉杰普特(Rajput)迦提在扩充地域方面尤为成功,得以控制大片土地。
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三条途径是婆罗门教社会制度对文化的控制,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使大批印度人陷于贫穷和绝望。现代印度处于某种吊诡状态。一方面有大量印度人接受良好教育,攀登众多领域的世界顶峰,从信息技术、医药、娱乐到经济。境外印度人始终享受较多的社会升迁机会,这一事实多年前便引起小说家奈保尔爵士(V.S. Naipaul)的注意。㉒经济改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出现,境内印度人也开始兴旺起来。另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居民仍是少数,国内文盲和贫穷的程度高得惊人。快速增长的城市,如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其郊外是广阔的乡村内地,那里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竟名列底层。㉓
这些差距的历史根源最终还归罪于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作为仪式监护人,婆罗门当然掌控学习和知识。一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他们坚决反对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诸文字。根据萨贝瓦尔,“为仪式上的使用而默记圣歌——既为自己,又为主顾——是婆罗门最独特的学习方式。仪式上和学习过程中的高效,并不要求弄懂所背诵的东西……很多婆罗门献身于浩瀚的默记、逻辑分析、辩论”。㉔为达到所需求的仪式效果,精确默记“吠陀本集”是必须的。据说,朗诵中的小错将导致灾难。
也许并非偶然,婆罗门坚持口头传诵“吠陀本集”,设置加入婆罗门的额外障碍,更加强自己的至高无上。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从他们宗教传统的一开始就是“圣书上的民族”,婆罗门却顽强抵抗文字和有关的书写技术。5 世纪和 7 世纪,中国取经人来印度寻求佛教传统的文献,竟找不到书面文本。中国人和欧洲人改用羊皮纸之后很久,印度人仍在使用棕榈树叶和树皮。讨厌耐用的羊皮纸有宗教起源,因为它来自动物的皮肤。11 世纪造纸技术来到时,婆罗门仍然迟迟不用。㉕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乡村,日常行政管理中的纸张使用一直要等到 17 世纪中期。一出现,它们就大大改善了记账和监管的效率。㉖
公元 1000 年之后,书写才变得普遍,自婆罗门扩散到印度社会其他群体。商人开始制作商业记录,迦提开始记载家庭谱系。在喀拉拉邦(Kerala),“王家和贵族血统”的那雅人开始学习书面梵语,该邦的统治阶级开始制作大量政治和商业的记录。(20 世纪晚期,当地共产党政府治理的喀拉拉邦成为印度治绩最佳的邦之一。有人怀疑,这样的治绩是否植根于数世纪前的文化传统。)
与中国相比,婆罗门垄断知识,抵制书写,严重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从商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使用文字传递命令、记录法律、保管账目、书写详尽的政治历史。在中国,对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识字、攻读漫长复杂的文学传统;对行政官员的训练,依现代标准看仍属有限,但仍涉及反复分析书本、以史为鉴。汉朝以来,科举制度获得采用,政府用人基于对文学技能的掌握,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虽然在实际情形中,普通老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机遇非常有限,但中国人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所以,宗族和地方社区在儿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科举制度。
如此情形在印度是不存在的。统治者自己是文盲,依靠同样无知的家族官员来维持治理。文化是婆罗门阶层的特权,他们维持对知识和仪式的垄断来保障自身利益。跟军队的情形一样,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阻止了大多数人获得教育和文化,从而减少了可为国家所用的称职人才。
在印度发展历史中,宗教影响政治权力的最后途径是建立了所谓法治的基础。法治的本质是一组反映社会正义感的规则,比国王的意愿更为崇高。这就是印度的情形,各种法典中的法律不是国王创建的,而是婆罗门依据仪式知识所制定的。这些法律讲得很清楚,瓦尔纳不是为国王服务的,更确切地说,国王只有变成瓦尔纳的保护人,方可获得合法性。㉗如果国王触犯了神圣法律,史诗《摩诃婆罗多》公开认可反抗,宣称此人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一条疯狗。在《摩奴法典》中,主权在法律,而不在国王:“在本质上,法律(danda)即是国王,享有权力,维持秩序,发挥领导作用。”(《摩奴法典》第 7 章第 17 节)㉘
不少古典文献叙述有关梵那(Vena)国王的警世故事,他禁止除了给自己的所有其他祭品,还推行种姓之间的通婚。结果,神圣的众神向他发起攻击,以奇迹般化成矛的青草叶,将他杀死。很多印度朝代,包括难陀王朝(Nanda)、孔雀王朝、巽伽王朝(Sunga),都因婆罗门的阴谋而变弱。㉙当然,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很难弄清婆罗门是在捍卫神圣法律,还是在保护自己利益。像欧洲而非中国,印度的权威是分裂的,对政治权力造成了颇具意义的制衡。 印度的社会制度源于宗教,大大限制了国家的集权能力。统治者不能动员大批人口以建立强大军队;不能渗透存在于每座村庄的自治且严密组织的迦提;自己和部下缺乏教育和文化;还要面对维护规范化秩序的严密的祭司阶层;自己在这一秩序中仅扮演从属角色。就上述的方方面面而言,印度统治者的处境非常不同于中国。
第 12 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孔雀王朝何以成为印度第一个且最成功的本土统治者;孔雀王朝治下的国家性质;阿育王的性格;式微、分裂、笈多王朝的复兴;印度为何被外国所征服
一开始,印度的社会发展就压倒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次大陆获得一种以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在尝试取得政治统一之前,就被标为与众不同的文明。统一过程中,社会力量足以抵制政治权力,阻止后者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发展了强大国家,其社会因此而处于孱弱地位,并自我延续。印度有个强大社会,先发制人,反而阻止了强大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的印度次大陆,成千上万的小国和酋邦,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其中三个王国——迦尸(Kashi)、拘萨罗(Kosala)、摩揭陀——和酋邦(或伽那—僧伽)的弗栗恃(Vrijji),成为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逐鹿者。摩揭陀(其核心地区在现代的比哈尔邦[Bihar])注定要扮演秦国角色,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公元前 6 世纪的下半世纪,频毗娑罗王(Bimbisara)登基,凭借一系列战略性的婚姻和征服,使摩揭陀成为印度东部的主要国家。摩揭陀开始征收土地税和收成税,以代替国家形成之前低级血统的自愿进贡,由此而招聘征税人员。税率据说是农业产品的六分之一,如果属实,这在早期农业社会是相当高的。①国王并不拥有国内所有土地,只享有荒地,其时人口稀少,应该是相当广袤的。
儿子阿阇世王(Ajatashatru)谋杀频毗娑罗,兼并西部的拘萨罗和迦尸,并与弗栗恃展开持久斗争。后来,他在伽那—僧伽领袖中挑拨离间,终获大胜。他死于公元前 461 年,其时,摩揭陀已迁都至华氏城(Pataliputra),控制了恒河三角洲和恒河下游的大部。统治权传给一系列国王,包括出身首陀罗的短命的难陀王朝(Nanda)。亚历山大大帝曾遭遇难陀军队,由于军队哗变,而不得不转向旁遮普。希腊的资料称,难陀军队有两万骑兵、二十万步兵、一千辆战车、三千头大象。这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以证明希腊人的退却是正确战略。②
继承难陀王朝的是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又称月护王)。他极力扩充领土,在公元前 321 年建立了印度次大陆第一个本土政治体——孔雀帝国。他是婆罗门学者兼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的门生,后者的《政事论》(Arthasastra)被视作是印度经世王道的经典论文。月护王率军攻击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征服西北部,并将旁遮普、阿富汗东部、俾路支地区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至此,他的帝国西到波斯,东到阿萨姆邦。
对印度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则留给了月护王的儿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和孙子阿育王(Ashoka)。宾头娑罗将帝国扩展到南方德干高原的卡纳塔克(Karnataka)。经过一场众所周知的持久的血腥征战,阿育王在公元前 260 年占领东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包含现代奥里萨邦[Orissa]和部分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其时,印度缺乏文学文化,阿育王的功绩从未见于史书,像中国的《尚书》和《春秋》。后代印度人一直要等到 1915 年,方才把他视作伟大的国王;其时,大批法令岩石的古文字获得译解,考古学家终于拼搭出他治下的帝国疆域。③
孔雀王朝历经三代而建起的帝国,占据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整个印度北方,西至波斯,东至阿萨姆,南至卡纳塔克。印度次大陆上,唯一没被统一的是南方边缘地带,分别是现代的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斯里兰卡。没有单独的印度本土政权再一次统治这么辽阔的领土。④莫卧儿帝国所征服的德里苏丹国要小得多,英国人在次大陆的帝国更大,但不得不问:说阿育王、阿克巴(Akhbar)、英国总督统治印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孔雀帝国:何等国家?
历史学家在古印度国家的性质上争论不休。⑤如果从比较眼光看,特别是对照阿育王的印度和秦始皇的中国,我们也许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个帝国几乎在同时形成(公元前 3 世纪的中到晚期),但它们政体的性质可说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个帝国都环绕一个核心而组成,分别为摩揭陀国和秦国。秦国是个真正的国家,具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现代国家政府的许多特征。管理国家的世族精英,大多已在数世纪的战争中战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凭借非人格化基础而获选的新人。秦国废除井田制,推翻传统的产权,以统一的郡县制取代世族封地。它最终打败对手,建立大一统帝国,便将这中央集权政府推向全中国。推广至被征服国家的,还有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我们已在第 8 章看到,秦朝君主的社会工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家族统治在西汉卷土重来。但汉朝统治者坚持中央集权,逐渐取消剩余的封地。它所建立的不算帝国,而是统一的中央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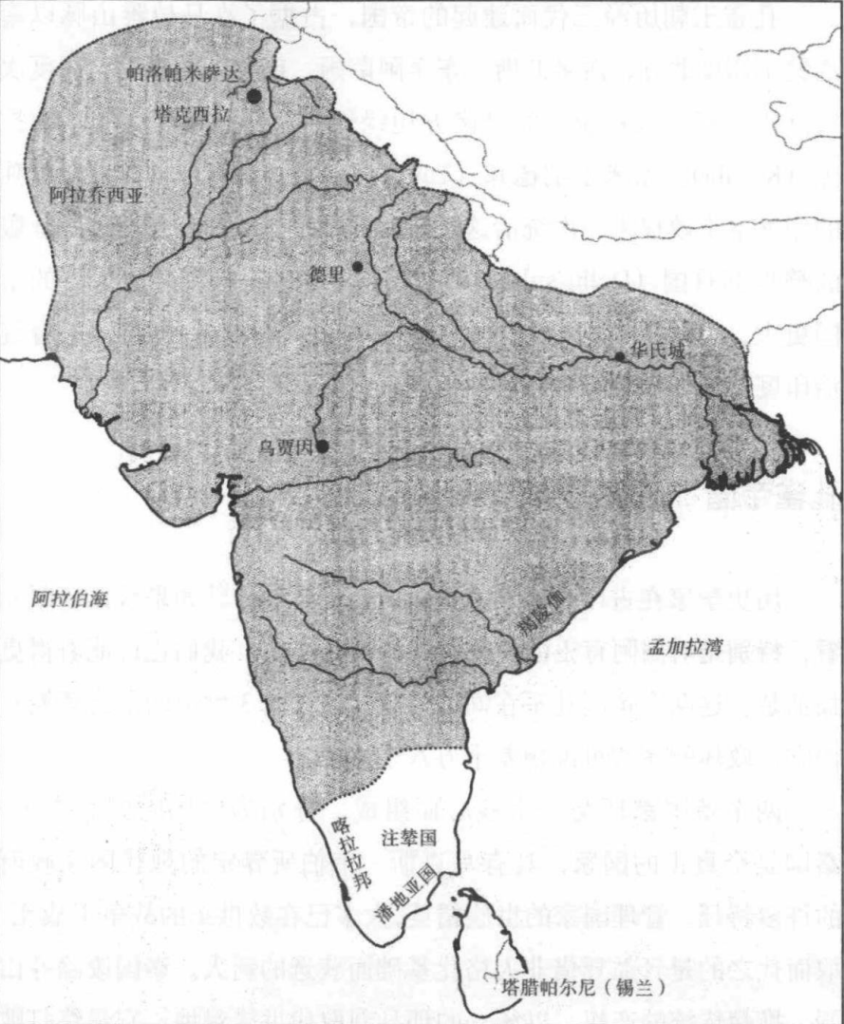
此类事项在孔雀帝国发生得很少,核心国的摩揭陀好像没有任何现代特征。与秦国相比,我们对其行政管理的性质了解得实在太少。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讲明,高级官位的主要资格应是高尚出身,其“父亲和爷爷”必须是大臣(amatya)或更高,他们几乎全是婆罗门。官僚的薪俸非常悬殊,最低与最高之间的比率是 1∶4,800。⑥没有证据显示,官府用人是选贤与能的,或前三级瓦尔纳之外的人也可申请公职。这些事实曾得到希腊旅行家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确认。⑦将摩揭陀推上战胜国地位的战争没有那么持久和残忍,不像秦国所经历的那样。旧精英得以留存,摩揭陀的处境从没恶化到非要动员男子总人口的地步。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事实上,迟至公元 16 世纪,印度国家仍在努力推行统一标准,其最终实行是在英国治下,距孔雀王朝已将近整整两千年。⑧
通过联姻和征服获得的地区,其与摩揭陀的关系也大大不同于中国。秦国灭绝他国,往往是消灭或放逐整个统治宗族,并鲸吞其领土。东周时期,中国精英宗族的数量大幅下降。孔雀帝国的建立则较为温和,涉及大量伤亡和焦土战术的唯一战役是对羯陵伽的攻占,给战胜者阿育王带来很大震撼。其他情形中,现有统治者吃了败仗后,便接受孔雀帝国在名义上的主权。《政事论》建议,孱弱的国王最好屈服,自愿向强大邻国进贡。没有出现中国或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即剥夺现有统治者,把领土赏赐给王室成员或侍从。印度历史学家有时谈到属臣国(vassal),但它没有欧洲属臣的契约意义。⑨说孔雀王朝重新分配权力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中央集权。孔雀王朝也没有设法将其国家制度,自核心国推向帝国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是家族的,没有试图建立永久且专业的行政制度。这意味着,每位新国王带来新的忠诚侍从,替换现有的行政官员。⑩
孔雀帝国在它管辖区域内,仅行使松弛的统治;它称霸的整段时期,部落联盟或酋邦(伽那—僧伽)始终存活,就是明证。与等级分明的王国相比,伽那—僧伽的政治决策涉及较多的参与和共识,但它仍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幸存的部落政体。印度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共和国”,这只是在为它涂上现代光彩。⑪
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详尽讨论了财政政策和征税,只是不清楚他的建议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践。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信徒相悖,国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他有自己地盘,另外宣称掌控荒地、森林等,但通常不向现存产权提出挑战。不过,国家坚持向各式地主征税的权利,缴税可依据个人、土地、收成、村庄、边界的小统治者,基本上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⑫似乎没有一名印度统治者尝试大型变革,像商鞅的废除井田制,或王莽雄心勃勃但一败涂地的土地改革。
阿育王死于公元前 232 年,他的帝国旋即衰落。西北部落到了大夏国(Bactrian Greek)手中,部落的伽那—僧伽在西部的旁遮普和拉贾斯坦(Rajasthan)重又兴起,南方的羯陵伽、卡纳塔克和其他领土纷纷脱离,返回独立王国的地位。孔雀王朝重又回到中央恒河平原的摩揭陀王国,其末代国王波罗诃德罗陀(Brihadratha)于公元前 185 年遇害。还要等五百多年,笈多王朝(Gupta)方才崛起,再次统一印度,其规模可与孔雀帝国媲美。次大陆的孔雀帝国仅维持一代,它的王朝持续一百三十五年。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于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帝国的统治如此短暂,至少从外表上看,它对下辖区域从没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事实上,这不是牵强附会。孔雀王朝从没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也从没自家族政府过渡到非人格化政府。它在整个帝国维持广泛的间谍网,但没有证据显示,它像中国一样建造道路或运河,以促进交通。很不寻常,除了首都华氏城,孔雀王朝没在任何地方留下有关它强盛国力的纪念物。后代没把阿育王当作帝国创建者,这也许是原因之一。⑬
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从没想到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没有尝试以一套新颖的共同规范和价值穿透整个社会。孔雀王朝没有真正的主权概念,即在全国范围实施非人格化统治的权利。次大陆没有统一的印度刑法,直到英国统治下诗人兼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cCaulay)第一次引入。⑭国王没有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反而保护现存的各式社会秩序。
印度从没开发出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思想,即政治目标就是赤裸裸地集权。《政事论》之类的论述,可向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君主提供建议,但只针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无关。此外,婆罗门教的精神孵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ahimsa)可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认为杀生对业力造成负面影响。它的有些文本批评吃肉和动物祭品,但另一些却予以批准。如我们所知,像佛教和耆那教的抗议宗教,非暴力更是中心思想。
孔雀王朝第一位国王旃陀罗笈多最后皈依耆那教,为了遂愿当一名苦行者,而自动让位给儿子宾头娑罗。他与一批僧侣搬到印度南方,据说,最后以耆那教的方式慢慢饿死。⑮他的孙子阿育王起初是正统的印度教徒,在生命后期皈依佛教。羯陵伽征战中的伤亡激起阿育王深深的悔恨,据传十五万羯陵伽人被杀或受逐。根据他的岩石赦令(Rock Edicts),“羯陵伽已被兼并,此后,陛下便开始了对宗教法律的热诚追求”。他还宣布,“曾遭杀戮和俘虏的羯陵伽人,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在今天遭受同样厄运,也会是陛下的遗憾。此外,如果有人冒犯他,只要还可以忍受,陛下也必须忍耐”。阿育王继续敦促仍在帝国边境的外人,“不用怕他,应信任他,应从他那里获得幸福,而不是悲伤”。他还呼吁他的儿子和孙子避免进一步征战。⑯帝国扩展由此戛然而止。不管阿育王后裔究竟是遵从他的意愿,还是本身就不中用,反正他们治下的帝国冰消瓦解。有人会问,如果印度开发了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权力原则,而不是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阿育王的帝国会变成怎样——如果真是这样,它就不是印度了。
社会战胜政治
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经历了政治衰败,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体在西部的拉贾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现。该地区又受到来自中亚部落的侵略者的骚扰,部分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太具优势。秦朝开始建设长城以御外人,迫使游牧的匈奴返回中亚,取代当地一系列部落。这一连锁反应又导致斯基台人(Scythians,即塞克人[Shakas])对印度北部的侵犯,紧跟在后的是月氏,它在现为阿富汗的地方建起贵霜帝国(Kushana)。印度北方的王国中,没有一个组织良好,可以考虑像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所以,部分印度北方平原为这些部落所占。⑰
在遥远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发展成王国,例如公元前 1 世纪统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但这个政治体持续不长,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机构,尚比不上孔雀王朝。为了控制德干北部,它与其他小王国发生冲突。此外,小王国之间也在争斗,如注辇国(Cholas)、潘地亚国(Pandyas)、萨提亚普特拉国(Satiyaputras)。这段历史相当复杂,难以融入政治发展的大叙述,也就缺乏启发功能,从中呈现出来的只是普遍的政治衰败。南方国家经常无法发挥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征税,因为其治下的社区既强大,又组织严密。⑱没有一国得以在永久基础上扩展疆域,实现霸权,也没开发更为复杂的行政机构,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统治。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状态还要持续一千多年。⑲
在印度第二次成功创建大型帝国的是笈多王朝(Guptas),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 Gupta I)。公元 320 年,他在摩揭陀国当政,其权力基础与孔雀王朝相同。他和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再次统一印度北方的大部。沙摩陀罗笈多在拉贾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区,兼并了众多伽那—僧伽,这种政治机构因此而寿终正寝。他还征服克什米尔,逼迫贵霜帝国和塞克国进贡。在他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的治下,文化生活变得繁荣,建了不少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庙宇。笈多王朝再持续两代,直到塞建陀笈多国王(Skanda Gupta)死于 5 世纪的下半叶。其时,西北部的酋邦变得衰弱,中亚新兴的游牧部落匈人(Huns 或 Huna)趁虚而入。笈多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尽自身,在 515 年将克什米尔、旁遮普、恒河平原的大部都输给匈人。⑳
姑且不论它的文化成就,笈多王朝没在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任何革新,也没有试图把征服的政治体整合成统一的行政机构。被打败的统治者,以典型的印度方式留下来继续执政,只是以后需要上缴贡品。笈多王朝的官僚,甚至比孔雀王朝的前任更为分散,能力更差。它征收农业收成税,拥有关键的生产资料,像盐场和矿山,但没有干预现存的社会安排。笈多帝国的疆土更小,因为没能统一印度南方。它持续了将近两百年,最后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众多小国,从而进入政治衰败的新时期。
外国人的国家建设
10 世纪后,印度的政治历史不再是本土发展史,而是一连串外国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国人。从今以后,政治发展成为外国人如何将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们仅取得部分成功。每个外国入侵者必须对付这同一的“小王国”社会,四分五裂,却又组织紧密;它们不团结,所以很容易征服;它们屈服后,又很难统治。外国入侵者留下了一层层新制度和新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风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没触碰内在社会秩序的一根毫毛。
10 世纪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伊斯兰教在 7 世纪涌现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先后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在很多方面开发了比印度本土政体更为精细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奴隶制和外国人充任行政官的制度(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允许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超越亲戚关系,实施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一批批穆斯林入侵者来自阿富汗,最为著名的是拉杰普特人部队(Rajputs)。印度国家的军队竭力抵抗,但实在太薄弱、太分散。13 世纪早期,马穆鲁克(Mamluk)朝代的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Qutb-ud-din Aybak)得以建立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维持三百二十年,长过任何一个本土印度帝国。虽然穆斯林建立持久的政治秩序,但其国家权力有限,仍不能改造印度社会。跟笈多王朝一样,它也没能向印度南方推进太多。用苏迪普塔·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的话说,“伊斯兰政治统治者,在社会习俗方面,含蓄地接受了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这与印度本土统治者非常相像……伊斯兰国家知道自己像其他印度国家,既有局限,又游离于社会之外”。㉑今天,穆斯林统治的遗产体现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还有印度一亿五千多万的穆斯林公民。就幸存的制度而言,穆斯林的政治遗产不是很大,除了像查明达利(zamindari)土地所有制之类的实践。
英国统治则不同,其影响既持久又深远。在很多方面,现代印度是外国人建国计划的产物。卡维拉吉认为,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相悖,“英国人没有征服一个既存的印度。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征服了一系列独立王国。在他们的统治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又聚合成政治层次的印度,也算是对英国统治的答复”。㉒这呼应了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的见解,与社会层次相对,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㉓将印度凝成政治体的重要制度,如行政机构、军队、共同的行政语言(英语)、实施统一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民主本身,既是印度人与英国殖民政府互动之后的成果,又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融入印度历史经验之后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社会层次的印度而言,英国的影响又很有限。英国人修改了他们发现的可恶社会习俗,例如自焚殉夫(Sati),引进了人人平等的西方观念,促使印度人反思种姓制度的哲学前提,鼓励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在 20 世纪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种姓制度本身、自给自足的村庄社区、高度地方化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完整无缺,远离殖民政府的权力。
中国和印度
21 世纪初,中国和印度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前景引起极大的讨论。㉔讨论的大部分围绕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质。作为威权国家,中国在推动大型基建工程方面比印度更为成功,像高速公路、机场、发电厂、大型水电项目。它的三峡大坝需要在漫水区迁走百万以上的居民。中国的人均储水量是印度的五倍,主要依靠大坝和灌溉工程。㉕中国政府一旦决定拆除街区,以建设工厂或公寓大厦,可以直接要求居民搬走。后者几乎没有途径保护自身权利或表述愿望。另一方面,印度是个多元的民主政体,各式社会团体都能组织起来,利用政治制度来达到自身的目标。印度的市或邦政府想建造新发电厂或新机场,很可能遭到反对,从环保非政府组织到传统的种姓协会。很多人认为,这会使决策程序瘫痪,经济增长的远景因此而变得暗淡。
这类比较都有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的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例如,很多人相信当代印度民主只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这历史发展又是相对近代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民主理论认为,印度自 1947 年独立以来一直维持成功的民主,这使很多人感到惊奇。印度丝毫不符合稳定民主“结构上”的前提:它过去非常贫困,从某种角度看,现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种族、语言、阶级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众暴力的狂乱中诞生,随着不同小团体的相互争斗,公众暴力又会定期重现。根据这个见解,在印度高度不平等的文化中,民主只是文化舶来品,由殖民政权输入,并不深植于国家传统。
这是对当代印度政治相当肤浅的见解。这倒不是说,现代制度所表现出的民主深深植根于古代印度实践,如阿马蒂亚·森等评论家所提示的。㉖而是说,印度政治发展的历程显示,它从来没有为暴政国家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以便其有效集中权力来渗透社会和改造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或俄罗斯出现的专制政府,即剥夺全社会(包括精英阶层)财产和私人权利的制度,从没存在于印度大地——不管是印度本土政府,还是蒙古人和英国人的外来政府。㉗因此而引发了如下的吊诡事态:印度有很多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不像欧洲和中国,大体上从不针对印度的执政当局。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针对婆罗门所控制的社会秩序,经常表现为异端的宗教运动,像耆那教或佛教,以否定现世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政治当局被认为离日常生活太遥远,也就太不相干了。
中国情形则不同。那里,拥有现代制度的强大国家早已产生,可刻意追求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广泛干预,并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和身份上取得成功。当新的社会组合出现并提出挑战时,国家的早期独尊给自己带来优势。今天,由于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全球化,有迹象显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渐渐成形,但中国的社会参与者始终比印度的更为薄弱,更加不能抵抗国家。公元前 3 世纪,秦始皇和阿育王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国,这一比照在当时很明显,在今天依然真实。
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 21 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从长远看,中国人是否因此而得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治的约束,也就无法遏制其统治者的异想天开。它可睹的成绩,都以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作为代价,而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过去和现在)来抵制国家的征召。
印度人也身历专横,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专横,而是我前文提出的“表亲的专横”。在印度,个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如亲戚关系、种姓制度、宗教义务、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印度的表亲专横允许他们对抗暴君的专横,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抑制了国家层次的强大机构。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同时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互相平衡,互相抵消,这样才会有较好形式的自由。这个主题,我以后还会回顾。但此时,我将考察浮现于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及其独特制度,它们允许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政体走出部落制。
第 13 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部落制是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军事奴隶制最早兴起于阿拔斯王朝;部落成员长于征服,却短于管理;柏拉图应付家族制的对策
16 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正处权力的巅峰,大约每隔四年就会看到一次非同寻常的征召。1453 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落到土耳其手中。1526 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莫哈奇(Mohács)战役中征服匈牙利;到 1529 年,才受挫于维也纳城门。在帝国的巴尔干半岛省份,官员分头寻找十二至二十岁的年轻男子,这便是德米舍梅征募制(devshirme)①,或基督徒壮丁征募制。这些官员像寻找足球明星的探子,在评判年轻人潜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经验丰富,要完成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规定的配额。官员访问村庄时,基督教士被要求提供所有获洗礼男童的名单,适龄的被带来供官员检验。多数富有潜力的男孩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编成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小组。他们的名字仔细登记在两本花名册中,一本是在家乡获选时,另一本是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互相对照,以防止父母把孩子赎回。如果儿子们长得特别强壮,父母身边可能一个也留不住。官员带着俘虏一起返回伊斯坦布尔,家人将永远见不到自己孩子。那段时期,这样带走的孩子估计为每年三千。②
他们不是注定在卑微和耻辱中度过一生。恰恰相反,最优秀的 10% 会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的宫殿中长大,受伊斯兰教世界中最好的培训,为充任帝国高级官员而作准备。其余的则被抚养成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加入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这是精英的步兵部队,陪伴苏丹左右,在欧洲和亚洲南征北战。
服务于宫殿的精英男孩,在宦官的监督下接受两至八年的训练。最为杰出的,再被派去托普卡帕宫(Topkapi),以获取进一步的调教,那是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居所。他们在那里攻读《古兰经》,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音乐、书法、数学,还参与严格的体育锻炼,以及学习马术、剑术和其他武器,甚至要涉猎绘画和书籍装订。那些进不了宫殿的,则在皇家骑士队(sipahis of the Porte)中担任高级职位。③如果年轻的奴隶军人证明是强壮能干的,可逐步升级为将军、维齐尔(vizier,大臣)、外省总督,甚至是苏丹治下最高级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即政府首相。在苏丹皇家军队服完役之后,很多军人会被安置在指定的庄园,靠居民的缴税而安享晚年。
另有一个平行的女奴制度,不属于军事奴隶制度。这些女孩是在奴隶市场从巴尔干半岛和南俄罗斯的掠夺者手中买来的。她们将担任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妻妾,像男孩一样,也被养在宫殿,高度制度化的规则督导她们的成长和教育。很多苏丹是奴隶母亲的儿子,像其他君主的母亲,她们也可通过儿子施展重要影响。④
但这些奴隶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禁忌。他们的职位和庄园不算私人财产,既不可出售,也不能传予子女。事实上,这些军人中的多数被迫终生保持单身。也有人与来自基督教省份的女奴组织家庭,但孩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地位或职位。不管如何有权有势,他们永远是苏丹的奴隶。苏丹稍有不满,就可对他们罚以降级或砍头。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度是非常奇特的。没有一名穆斯林可成为合法的奴隶,所以,也就没有帝国的穆斯林居民追求政府高位。像中国一样,文武官员都是量才录用,以固定的程序招聘和提拔最能干的军人和文官。但又不像中国,这个招聘和提拔只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各阶层。这些奴隶的军人和官僚在泡沫中长大,与主人和同僚建立亲密纽带,但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却格格不入。像在封闭阶层工作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发展了高度的内部团结,成为一个凝聚的团体。在帝国的晚期,他们变成了王者之王,擅自决定苏丹的废黜和任命。
不出意料,面临此种征召的基督教欧洲人,包括那些住得遥远只是听说此事的人,都心怀恐惧。等级分明的奴隶在治理一个强盛的帝国,这一图像在基督教西方的眼中,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到了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趋式微。不少评论家认为,土耳其禁卫军是怪诞且过时的制度,在阻挡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禁卫军在 1807 年罢免塞利姆三世(Selim Ⅲ),在下一年拥戴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登基。后者在后续年份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 1826 年放火焚烧禁卫军兵营,害死大约四千人。扫除了挡道的禁卫军,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现在可以推动改革,照现代欧洲的模式重建一支军队。⑤
显而易见,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使之成为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这种制度非常残酷,与现代民主价值格格不入,即使这些奴隶享有特权。穆斯林世界之外,没有看到可以媲美的相似制度,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等评论家认为,它的创建最终归于伊斯兰教深处的宗教原因。⑥
但进一步观察后发现,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并不从宗教原则进化而来,仅仅是强大部落社会中建国的对策。它发明于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其统治者发现,不能依赖部落组织的军队来维持帝国。阿拉伯部落的征召和扩军很快,以取得速胜。统一后,他们凭借伊斯兰教的激励,又成功占领中东的大部和地中海世界的南部。如我们所知,中国、印度、欧洲的部落层次制度,因不能完成持续的集体行动,而被国家层次的制度所取代。部落社会高度平等,以共识为基础,不轻易服从,倾向于发生内讧和分裂,很难长期守卫领土。
为了创建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军事奴隶制在世界最强大部落社会之一应运而生,成为一个精彩的适应。它作为集中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措施,极为成功,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它挽救了伊斯兰教,使之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⑦
创建穆斯林国家
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古莱什部落,其时,该地不属于任何国家。如第 5 章所提及的,他运用社会契约、实力、超凡魅力的组合,首先统一了争吵不休的麦地那部落,然后是麦加和周边城镇的部落,从而建成了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个意义上,先知的布道是故意反部落的。它宣称有个信徒团体,其忠诚只献给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而不是自己的部落。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在内争好斗的分支式社会中,为拓宽集体行动的范围和延伸信任的半径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维持政治统一始终是阿拉伯部落制背景下的艰辛斗争。穆罕默德死于公元 632 年,麻烦立即露出端倪。先知的超凡魅力足以凝聚他所创建的政治体,现在却面临四分五裂的威胁,其组成部分很有可能分道扬镳,如以麦加为基的古莱什部落、来自麦地那的“辅士”(Ansar)和其他部落的信徒。穆罕默德同伴之一的艾布·伯克尔(Abu Bakr),以他娴熟的政治运作,说服部落团体承认自己为第一任哈里发(caliph),即继承者。此外,他还是部落系谱的专家,借用他在部落政治上的渊博知识而赢得拥护自己的共识。⑧
在头三个哈里发的治下——艾布·伯克尔(632—634 年在位)、欧麦尔(Umar,634—644 年在位)、奥斯曼(644—656 年在位)——穆斯林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兼并整个阿拉伯半岛,以及今日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的主要地区。⑨最壮观的胜仗是卡迪西亚会战(Qadisiyyah),打败了波斯的萨珊帝国。20 世纪 80 年代两伊战争时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曾大肆庆祝这一历史战役。661 年,随着倭马亚王朝建立于大马士革,版图扩展仍在继续,进一步征服了北非、小亚细亚(Anatolia)、信德(Sind)和中亚。阿拉伯军队在 711 年占领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的北边继续挺进,直到 732 年在法国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受到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遏制。
阿拉伯部落虽有宗教动机,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奖励。他们所征服的定居农业社会,可提供大量土地、奴隶、女子、马匹、动产。最初的统治问题是所有掠夺游牧民族所面临的:如何分配战利品,以避免各部落之间的内讧。通常当场分配可搬走的战利品,五分之一给哈里发,运回麦地那。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变成哈里发治下的国家领土,不少干脆落到参与战役的各部落手中。⑩
过不多久,阿拉伯部落男子必须由征服者变为管理富饶农地和居民的统治者。哈里发不需要重新开发国家制度,因为四周都是成熟的国家或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萨珊帝国提供最及时的中央管理模式。曾属君士坦丁堡的领土现已被阿拉伯征服,居住于此的很多基督徒前来参加穆斯林政府的工作,从而带来拜占庭政府的治理方法。
真正的穆斯林国家何时出现?与文学描述相对的历史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缺乏,使精确判定变得异常困难。维持常备军队和警察、定期向居民征税、设立行政机构以收税、裁定司法以解决争端、主持像大清真寺那样的公共建设,从事上述这一切的政体,肯定存在于倭马亚王朝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685—705 年在位)时期。或许更早,甚至在倭马亚王朝第二任哈里发穆阿维叶(Mu‘awiya,661—680 年在位)时期。⑪很难说先知穆罕默德创建的不是部落联合体而是国家,因为上述的制度特征在他生前尚未出现。
波斯的理想绝对君主制中,其国王强大得能够维护和平和遏制贪婪的武装精英,后者是农业社会中冲突和混乱的主要来源。从现代民主角度看这样的社会,我们倾向于认为,农业社会的君主只是掠夺性精英团体的一员,也许由其他寡头选出来保护他们的租金和利益。⑫但实际上,这些社会中几乎总有三角斗争,分别是国王、精英的贵族或寡头、非精英的农民和市民。国王经常站在非精英一边来反对寡头,既可削弱潜在的政治挑战,又可争到份下的税收。于此,我们可看到国王代表大众利益的概念的雏形。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寡头精英的大庄园扩展,皇帝为此而受到威胁,遂运用国家权力来予以限制和破坏。同样道理,萨珊帝国的绝对君主政体被视作秩序的壁垒,以反对损害大众利益的精英的相互争执。所以有人强调,君主执行法律便是正义的标志。⑬
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早期阿拉伯统治者享有几点优势。绝对君主制的中央行政官僚模式,作为国家层次社会的规范,早已存在于周边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宗教意识形态。就某种意义而言,以巴士拉(Basra)和阿拉伯半岛为基地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从先知布道中得出了最符合逻辑的结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只要是穆斯林就够,不管他是不是阿拉伯人,也不管他来自哪个部落。如果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如此照办,他们可能会尝试创建一个包容不同种族的超级帝国,基于意识形态,不靠亲戚关系,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但对倭马亚王朝来说,光是维持帝国统一,且不谈建立横跨各地域的中央政府,已证明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顽强的部落忠诚胜过意识形态,穆斯林国家继续受困于亲戚关系的争吵和仇恨。
先知死去不久就爆发了一起最重要的冲突。穆罕默德属于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Hashemite)血统,但又与竞争的倭马亚血统共享曾祖父阿卜杜·玛纳夫(Abd Manaf)。倭马亚血统和哈希姆血统争吵得很厉害,不管是先知出生之前,还是先知在世时,前者甚至起兵,反对穆罕默德和他在麦地那的穆斯林信徒。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后,倭马亚血统改信伊斯兰教,但两个血统之间的仇恨仍在继续。穆罕默德没有儿子,只跟最心爱的妻子阿以莎(Aisha)生了女儿法蒂玛(Fatima),长大后嫁给先知的表亲阿里(Ali)。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属于倭马亚血统,把很多亲戚带入权力圈,最终死于行刺。继承他的是阿里,却被赶出阿拉伯半岛,在库法(Kufa,今日伊拉克)祈祷时,又被哈瓦利吉派系的人杀死。随之,哈希姆血统、哈瓦利吉派、倭马亚血统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内战(fitnas)。等到阿里儿子侯赛因(Husain)战死于伊拉克南部的卡尔巴拉(Karbala)战役,倭马亚血统才得以巩固政权,开拓新朝代。阿里的党羽被称为什叶派(Shiites),信奉正统主义,认为阿拉伯帝国只能属于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⑭倭马亚王朝穆阿维叶的追随者发展成为逊尼派(Sunnis),声称自己是正统理论与实践的奉行者。⑮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起源于阿拉伯部落竞争,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引发汽车爆炸、对清真寺的恐怖袭击等。
早期的哈里发尝试创建超越部落忠诚的国家组织,尤其是在军队里,其十人和百人单位都是跨越部落的。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新兴的穆斯林精英“知道部落身份在阿拉伯社会中植根太深,既不能以法令废除,也不能以超越部落排外性的措施将之驱走。他们能否将部落成员成功融入国家,既取决于为自身利益利用部落关系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超越部落关系的能力”。⑯占领伊拉克安巴(Anbar)省的美国人,在 2003 年入侵之后发现,倚靠部落领袖的传统权威,比创建无视社会现实的非人格化单位,更容易掌控部落军人。部落成员与指挥官发生争吵,可能会悄悄溜走,返回自己的亲人中。如指挥官又是自己部落的酋长,他就会三思而不行了。
但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国家本质上是孱弱和动荡的,部落领袖的暴躁闻名遐迩。他们缺乏纪律,经常因为争吵,或受到忽略,而与亲戚们逃之夭夭。早期哈里发对所招募的部落领袖满腹狐疑,通常不让他们担任重要的指挥职位。此外,新建国家经常受到独立游牧部落的威胁,穆斯林领袖对之只有轻蔑。据传,哈里发奥斯曼不愿理会一名重要部落领袖的见解,斥之为“低能贝都因人”的唠叨。⑰
军事奴隶制的起源
军事奴隶制发展于 9 世纪中期的阿拔斯王朝,用以克服之前穆斯林军队基于部落征召的重重弊端。⑱阿拔斯王朝属于哈希姆血统,在什叶派和波斯的呼罗珊(Khorasani)义军帮助下,于 750 年推翻倭马亚王朝,并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巴格达。⑲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在巩固其统治方面非常残忍,尽量灭绝倭马亚王朝的血统,并镇压曾经的盟友什叶派和呼罗珊义军。国家集权有增无减,大权独揽的是称为维齐尔的首相。宫廷的规模和奢华均有增加,定居城市的帝国与其发源的部落区域则更加分隔。⑳
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就暗示,基于亲戚关系的政治权力趋于浮躁善变,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军事奴隶制。哈里发马赫迪(al-Mahdi,775—785 年在位)宁可选择一批毛拉(mawali,释奴)作为自己的仆人或助手,也不愿挑选亲戚或呼罗珊盟军。他解释道:
我坐在观众席里,可以唤来毛拉,让他坐在身边,他的膝盖触碰我的膝盖。等到散席,我可命令他去侍候我的坐骑,他仍然高兴,不会生气。如果我要求其他人做同样的事,他会说:“我可是你的拥护者和亲密盟友的儿子”,或“我可是你(阿拔斯王朝)霸业的老兵”,或“我可是首先投入你霸业的人的儿子”。而且我不能改变他的(顽固)立场。㉑
到马蒙(al-Ma’mun,813—833 年在位)和穆尔台绥姆(al-Mu’tasim,833—842 年在位)的治下,阿拔斯王朝征服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大批突厥部落投靠帝国,外国人充当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方才成为惯例。当阿拉伯人遇上生活在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落时,其领土扩展受到阻止,后者优秀的打仗能力获得很多阿拉伯学者的承认。㉒哈里发不能招募整个突厥部落为自己打仗出力,因为它们同样有着部落组织的缺陷。所以,突厥人只是作为个别奴隶,在非部落军队中接受训练。马蒙创建了四千突厥奴隶的卫兵队,称作马穆鲁克,到穆尔台绥姆时期,壮大至将近七万人。㉓他们是凶悍的游牧人,新近皈依伊斯兰教,充满了对穆斯林事业的热情。他们成为阿拔斯军队的核心,“因为他们在威力、血气、勇敢、无畏方面,都比其他种族优越”。根据一名见证马蒙征战的观察员,
停战区道路两侧站着两行骑士……右首一侧是一百名突厥骑士,左首一侧是一百名“其他”骑士(即阿拉伯人)……大家都排成战斗行列,等待马蒙的莅临……时值正午,天气愈益炎热。马蒙到达时发现,除三四人外,突厥骑士依然危坐于马背,而“混杂的其他人”……早在地上东倒西歪。㉔
穆尔台绥姆把突厥人组成马穆鲁克团,因为本地居民与突厥士兵的暴力争端,而把首都从巴格达迁至萨迈拉(Samarra)。他让他们在自己学院中接受训练,购买突厥女奴配给他们成家,但不准与本地人混杂,由此创建了一个与周围社会分隔的军事种姓。㉕
忠于家庭,还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具有悠久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群年轻人的讨论,他们试图在“讲说中”创造一个“正义之城”。苏格拉底说服他们,正义之城需要特别激昂的保卫者阶层,为防御自己城邦而感到无比自豪;保卫者是武士,其首要原则是对朋友友善、对敌人凶狠;他们必须接受妥善的音乐和体操的训练,以培养公益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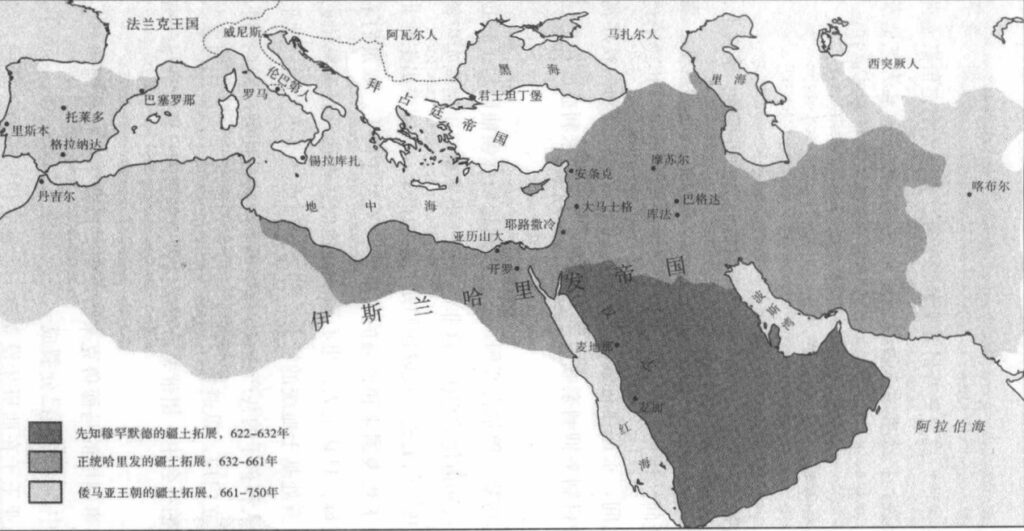
《理想国》第五卷有段著名论述,谈到保卫者应实行妻小共有制度。苏格拉底指出,性欲和生儿育女都是自然的,但保卫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两者会有竞争;为此,必须告诉孩子一个“高尚谎言”,他们没有生身父母,只是大地之子。他还主张,保卫者必须过集体生活,可有不同的性伙伴,但不可跟单独女子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必须过集体生活。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敌人:
那么,我们已讲过的和我们正在这里讲的这些规划,是不是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保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东西各各说成“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呢?㉖
不很清楚,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否相信此举的可行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讲说中”的正义之城能否成为现实,表示了巨大疑问。讨论的目的在于指明,亲戚关系和对公共政治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关系。它的启示是,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抑制亲戚关系,使保卫者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如果说马蒙、穆尔台绥姆或其他早期穆斯林领袖读到了柏拉图的著作,或知道他的想法,这非常可疑。但军事奴隶制确实应答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必需,没说他们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遥远,除了代表国家和公益的哈里发,不欠任何人。奴隶们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认主人,忠心耿耿。他们获得通常是突厥语的普通新名,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他们没有实行女人和孩子的共产主义,但隔离于阿拉伯社会,不准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门户,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都搬回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裙带关系和部落忠诚的难题,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作为军事制度的马穆鲁克来得太迟,以致不能保住阿拔斯王朝。9 世纪中期,帝国已分裂成一系列独立主权政治体。756 年,逃亡的倭马亚王子在西班牙设立第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帝国分裂自此开始。8 世纪末 9 世纪初,独立王朝建立于摩洛哥和突尼斯;9 世纪末 10 世纪初,独立王朝又在伊朗东部出现。到 10 世纪中期,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从版图上消失,阿拔斯国家只保留伊拉克的部分地区。阿拉伯政权,不管是王朝还是现代,再也没有统一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统一大业只好留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阿拔斯帝国灭亡了,但军事奴隶制得以幸存。事实上,它在后续世纪中,为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新的权力中心涌现出来,都基于军事奴隶制的行之有效。第一个是伽色尼(Ghaznavid)帝国,曾在前一章中提及。它以阿富汗的伽色尼为中心,统一了波斯东部和中亚,还渗入印度北部,为穆斯林统治次大陆铺平道路。第二个是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在阻止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军方面,扮演了生死攸关的角色,可能因此而挽救了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最后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它改善军事奴隶制,为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打下基础。所有三个案例中,军事奴隶制解决了部落社会中建立持久军事工具的难题。但在伽色尼和埃及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亲戚关系和家族制渗入马穆鲁克制度,使该制度衰落。此外,作为埃及社会最强大制度的马穆鲁克,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进而接管国家,预示了 20 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专政。只有奥斯曼帝国清楚看到,必须把家族制赶出国家机器,其照章办事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文官政府严格控制军队,但从 17 世纪晚期起,当家族制和世袭原则重新抬头时,它也开始走下坡路。
第 14 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马穆鲁克如何在埃及上台;中东阿拉伯的权力却在突厥奴隶之手;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于十字军和蒙古军;马穆鲁克实施军事奴隶制的缺陷导致政权的最终衰落
军事奴隶制帮助穆斯林政权在埃及和叙利亚掌权近三百年,从阿尤布(Ayyubid)王朝终结的 1250 年到 1517 年。其时,马穆鲁克苏丹国败在奥斯曼帝国的手中。今天,我们把伊斯兰教和全球的穆斯林社区(现今总人口约 15 亿)视作理所当然。但伊斯兰教的扩张,不仅取决于宗教思想的号召和吸引力,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权力。根据穆斯林的信念,穆斯林军队必须向身处战争土地(Dar-ul Harb)的非信徒发起圣战(jihad),再把他们带入伊斯兰土地(Dar al-Islam)。归功于穆斯林,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东不再是主要宗教。同样道理,如果十字军得以掌控中东,或蒙古军一路扫到北非,伊斯兰教也可能成为次要流派。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多哥、加纳等北部边界,就是当初穆斯林部队的远征终点线。要不是穆斯林部队的打仗威力,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派就不复存在。它的出现不仅靠宗教狂热,还靠国家建立有效制度来集中使用权力——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奴隶制。
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取决于军事奴隶制,这一见解与阿拉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不谋而合。他活在 14 世纪的北非,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同一时代。他在《历史绪论》(Muqadimmah)中说:
(阿拔斯)国家淹没于颓废和奢华,披上灾难和衰弱的外衣,被异教的鞑靼所推翻。鞑靼废了哈里发的宝座,毁掉该地的辉煌,使非信徒在信念之地得逞。这全是因为信徒们自我放纵,只顾享乐,追求奢侈,精力日衰,不愿在防卫中重振旗鼓,放弃了勇敢的脸面和男子汉的象征——然后,善良的上帝伸出救援之手,复苏气息奄奄的人,在埃及恢复穆斯林的团结,维持秩序,保卫伊斯兰教的城墙。上帝从突厥人和其众多部落给穆斯林送来保护他们的统治者和忠实助手。这些助手借助奴役的渠道,从战争土地来到伊斯兰土地,本身便藏有神的祝福。他们通过奴役学习荣誉和祝福,荣获上帝的恩惠;受了奴役的治疗,他们以真正信徒的决心走进穆斯林宗教,保持游牧人的美德,没受低级品行的玷污、享乐的腐蚀、文明生活的污染,他们的激情不受奢华的影响,仍完好无缺。①
马穆鲁克制度创立于库尔德人的阿尤布王朝末期,那是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阿尤布王朝短暂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其最著名的子孙是萨拉丁(Salah al-Din,在西方被称作 Saladin)。阿尤布王朝曾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反十字军战争中,投入了突厥奴隶军。它的最后一任苏丹萨里(al-Salih Ayyub),创建了伯海里(Bahri,编按:意即河洲)团,以总部所在地的尼罗河小岛的城堡命名。据传,库尔德士兵的不可靠使他转向突厥人。②该团含八百至一千的奴隶骑士,主要是钦察突厥人(Kipchak Turkish)。像钦察一样的众多突厥部落,开始在中东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其时,他们受到另一强大游牧民族的挤压,蒙古人正在把他们从中亚传统的部落地域赶走。
伯海里团很早就证明了自己的骁勇善战。法王路易九世 1249 年在埃及登陆,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翌年,他败在伯海里团手中。率领伯海里团的是一名钦察人,名叫拜伯尔斯(Baybars)。他曾是蒙古人的俘虏,作为奴隶卖到叙利亚,最后被招聘为新马穆鲁克的领袖。由此,十字军在埃及遭到驱逐,路易九世的赎金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1260 年,拜伯尔斯和伯海里团,在巴勒斯坦的阿音札鲁特(Ayn Jalut)战役中取得更为重大的胜利,他们打败了蒙古军。其时,蒙古军已经征服欧亚大陆的大部。成吉思汗于 1227 年去世,此前蒙古各部落已经在他手上完成统一。13 世纪 30 年代,他们摧毁了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打败了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同时又战胜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王国;侵犯和占领了俄罗斯的大部,1240 年洗劫基辅;在 13 世纪 40 年代挺进东欧和中欧。他们最终停止前进,不是由于基督教军队的威力,而是因为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的去世。蒙古指挥官奉召撤退,以讨论继承人选。1255 年,蒙哥命令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中东。他占领伊朗,建立伊儿汗国(Ilkhanid),再朝叙利亚挺进,旨在征服埃及。1258 年,陷落的巴格达遭到彻底蹂躏,阿拔斯王朝的末代哈里发也被处死。
马穆鲁克在阿音札鲁特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兵力优势,由于蒙哥的去世,旭烈兀不得不率领主力部队撤退。尽管如此,为了攻击马穆鲁克,他仍留下最好的指挥官之一和实质性的兵力。蒙古人是优秀的战术家和战略家,以迅速转移和简易给养,设法包抄敌人。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装备得更好,战马更为高大,携带更为坚实的盔甲、弓、矛、剑,并且纪律异常严明。③阿音札鲁特的胜利不只是侥幸,马穆鲁克曾与伊儿汗国发生一连串战役,以保卫叙利亚,直到 1281 年战争结束。它后来在 1299、1300、1303 年,又三次阻挡蒙古人的入侵。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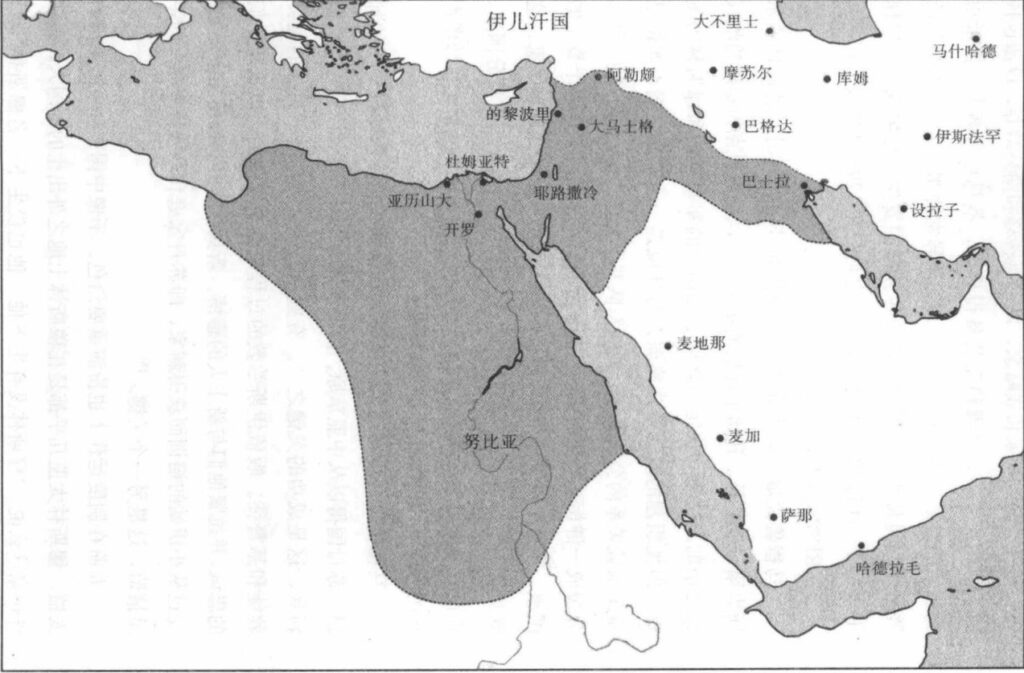
马穆鲁克取代阿尤布王朝,与伊儿汗国开战时,就以拜伯尔斯为第一任苏丹,开始了他们的统治。⑤以马穆鲁克为基础的政权比之前的王朝更为稳定。萨拉丁是伟大的军事领袖和穆斯林的英雄,但他组建的政体非常脆弱,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公国联邦。他的军队并不忠于王朝,在萨拉丁死后,分裂成一群相互竞争的民兵。相比之下,马穆鲁克治理一个真正的国家,设有中央官僚机构和专业军队——实际上军队就是国家,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⑥不像阿尤布王朝,马穆鲁克没有瓜分国家,也没有分发封地给亲戚或宠臣。不像萨拉丁死后,叙利亚在马穆鲁克的治理下,也没有马上脱离埃及。⑦
马穆鲁克制度在埃及马穆鲁克政权的统治下获得进一步的加强。苏丹国得以从中亚草原、西北和北方的拜占庭领土获得一波波新兵,这是成功的关键之一。有些新兵已是穆斯林,另外的是异教徒和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重建了他们的忠诚,并拉近了他们与新主人的感情。新兵与家庭和部落完全隔绝,经过从小伊始的培训而获得新家,即苏丹家庭和马穆鲁克相互的手足情谊,这是另一个关键。⑧
太监在制度运作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不像中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太监,穆斯林太监几乎都是在穆斯林土地之外出生的外国人。有位评论家这么说,“穆斯林没有生下他。他也没生下一名穆斯林”。⑨马穆鲁克几乎都是突厥人或欧洲人,太监则有可能是从努比亚(Nubia)或南方其他地区招募来的非洲黑人。跟马穆鲁克一样,他们也与自己家庭完全隔绝,因此对主人忠心耿耿。去势得以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年轻马穆鲁克的教师。后者的获选,除了体力和尚武,还取决于他们的健美。作为只有袍泽之谊而难近女色的军人集体,老牌马穆鲁克的同性恋索求,始终是一件头痛事,太监还可从中发挥缓冲的作用。⑩
作为政治制度的马穆鲁克之所以成功,除了教育特殊,还因为贵不过一代的原则。他们不能将马穆鲁克地位传给孩子,儿子会融入普通老百姓,孙子则完全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其中的道理简单明了:穆斯林不能是奴隶,而马穆鲁克的孩子生来就是穆斯林。此外,马穆鲁克的孩子生于城市,没经历过草原上流浪生涯的锻炼,在那里,孱弱就等于夭亡。假如马穆鲁克地位变成世袭,就会违反当年获选时严格的量才录用原则。⑪
马穆鲁克的衰退
马穆鲁克制度的设计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它本身变得日益软弱。第一,马穆鲁克军中没有制度化的统治机制。苏丹以下有等级分明的指挥链,但苏丹本身却没有明确的选任规则。有两条相互竞争的原则,第一条是王朝原则,当政的苏丹选择一个儿子来继位;第二条是非世袭原则,各派马穆鲁克一边争权夺利,一边试图达成人选的共识。⑫第二条比较占上风时,各资深埃米尔(emir,王公)所选出的苏丹,经常只是门面装饰。
马穆鲁克国家结构的第二个缺陷是缺乏最高的政治权威。马穆鲁克创建时,仅是阿尤布王朝的军事工具。到最后一任阿尤布苏丹去世,马穆鲁克却接管了国家,造成了逆向的代理。大多数政治等级制度中,主人拥有权力,委任代理人去执行自己的政策。很多政体发生功能的紊乱,因为代理人自有打算,与主人的目标大相径庭。制度的设计就是要鼓励代理人遵循主人的命令。⑬
相比之下,在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代理人自己又变成了主人。他们既是服务苏丹的军事等级机构,同时自己又在争夺苏丹职位。这意味着,他们既要做军官工作,又要图谋攫取权力并削弱对手。这自然给纪律和等级制度造成极坏的影响,就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府。这个问题在 1399 年变得异常尖锐,其时,蒙古的帖木儿国侵犯叙利亚,洗劫阿勒颇(Aleppo),而马穆鲁克忙于内斗,无暇组织防御,竟撤回开罗。此外,他们也让地方部落夺走对上埃及的控制。最终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帖木儿国需要应对另一新兴力量的威胁,即奥斯曼帝国。⑭如果马穆鲁克服从于文官政府,像奥斯曼帝国那样,文官政府就可采取措施予以解决。⑮
反世袭原则逐渐衰退,最终导致埃及马穆鲁克国家的崩溃。随着时间的推移,世袭不但用于苏丹,甚至蔓延至马穆鲁克,他们也试图建立自己的朝代。像中国的非人格化科举制度,贵不过一代的原则违背人们的生物性追求,马穆鲁克都试图保障家人和后裔的社会地位。富有的马穆鲁克发现,他们可以捐赠给伊斯兰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waqf)、伊斯兰学校(madrassa)、医院和其他信托机构,让自己的后裔担任主管,从而战胜贵不过一代的原则。⑯此外,有些马穆鲁克没有直系亲戚,却把种族关系当作团结基础。苏丹盖拉温(Qalawun)废弃钦察人,开始招募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和阿布哈兹人(Abkhaz)的奴隶,以组建新的布尔吉团(Burji)。最终,切尔克斯派从钦察派的手中夺走苏丹国。⑰
到 14 世纪中期,马穆鲁克制度的严重退化已经相当明显。事实上,其时的情形是一片和平繁荣,对马穆鲁克的纪律却有灾难性的影响。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多已消失,马穆鲁克在 1323 年与蒙古人签订和平条约。自己不是马穆鲁克的苏丹纳绥尔·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开始委派非马穆鲁克的效忠者担任高级军职,并清洗他心疑的能干军官。⑱
政府随着苏丹巴库克(Barquq)在 1390 年的上台而获得短暂活力。他的掌权全靠布尔吉,即切尔克斯人的马穆鲁克,他还恢复了招募外国奴隶的旧制度。后续的苏丹使用国家垄断所积累的资源,大大扩充了对年轻马穆鲁克的招募,从而造成代沟问题。老牌马穆鲁克开始演变成军事贵族,像现代美国大学的终身制教授,在等级制度中盘根错节,固守现状,以应对年轻一代的挑战。资深首领的平均年龄开始上升,人员流通显著减缓,古老贵族分为氏族。马穆鲁克开始提拔自己的家人,以财富的炫耀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女眷也在争取子孙利益上扮演更大角色。马穆鲁克制度,最初创建时是为了在军事招募中克服部落制,自己现在反而变成部落。⑲新的部落不一定基于亲戚关系,但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冲动:应付非人格化社会制度,以促进和保障后裔、朋友、依附者的利益。
久而久之,马穆鲁克制度从中央国家退化成军阀的寻租联合体。年轻的马穆鲁克不再忠于苏丹,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说的,反而变成
一个利益团体,它在战场上的可靠性是可疑的,它的造反倾向却是自然的。苏丹国的最后几十年,开罗的逐日编年史就是一个不断要求苏丹付款以换取国内稍稍稳定的故事。招募来的马穆鲁克以掠夺……欢迎甘素卧·胡里(al-Ghawri,一位晚期苏丹)的登基。受训新兵烧了五名高级长官的豪宅,以表达对自己低报酬的不满,作为对照,大首领通常聚敛巨额的财富。⑳
将马穆鲁克与早期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已被经济考虑所替代。高级马穆鲁克向低级军人购买忠诚,后者再向国家或平民百姓榨取租金,以期获得赞助人的奖励。苏丹只是伙伴中的老大,有些遭到了马穆鲁克派系的行刺或撤职,所有晚期的苏丹都不免会提心吊胆。
除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政府在 15 世纪晚期又遭遇财政危机。葡萄牙海军在印度洋取得首要地位,切断了香料贸易,苏丹的收入在 14 世纪末开始下跌,只好依靠税率的增加。这迫使经济主体——农民、商人、手艺人——想方设法隐瞒资产来逃税,征税官员愿意低报税率来换取自己荷包的回扣。结果,虽然税率增高,实际税收反而下降。政府只好诉诸没收所能找到的资产,包括马穆鲁克用来为后裔隐藏财富的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㉑
作为犯罪集团的国家
政治学家将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比作有组织犯罪。他们的意思是,国家统治者使用自己组织暴力的专长,向社会上其他人榨取资源,经济学家称之为租金。㉒有些学者使用“掠夺国家”的字眼来描绘一系列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像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下的扎伊尔(刚果),或查尔斯·泰勒治下的利比里亚。在掠夺国家里,掌权精英试图向社会提取最高程度的资源,以供自己的私人消费。这些精英之所以追求权力,就是因为权力可向他们提供经济租金。㉓
毫无疑问,有些国家是高度掠夺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在理解政治发展时要面对一个重要议题,即国家是否在掠夺最大化的租金,或出于其他考虑,仅在提取远远低于理论上最大化的租金。以租金最大化来描绘成熟的农业社会,如奥斯曼土耳其、明朝中国、“旧制度”下的法兰西王国,并不一定恰当。但对有些政治秩序来说,如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所设置的征服政权,这肯定是精确的,也愈来愈成为后期马穆鲁克政权的特征。马穆鲁克苏丹的征税,既是没收性的,又是任意的,使长期投资变得难以想象,主人只好将财产投入非优化的用途,像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有个有意思的推测:当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起飞时,在埃及却被扼杀在摇篮中。㉔
另一方面,高水平征税仅出现于埃及马穆鲁克三百年统治的末期。这表明,早期苏丹的征税远远低于最大化。换言之,最大化的租金提取并不是农业社会中前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特征。根据波斯的中东国家理论,君主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农民,以正义和稳定的名义来对抗贪婪的地主和其他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精英。这个理论为阿拉伯人所采用。所以,国家不单是占据领土的强盗,更是新兴公共利益的监护人。马穆鲁克国家最终走向完全的掠夺,归因于内外力量的交汇。
诸多原因导致马穆鲁克政权的政治衰败,它在 1517 年遭到奥斯曼帝国的摧毁。从 1388 年到 1514 年,埃及承受二十六年的瘟疫。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马穆鲁克越来越难以招募奴隶军,因为奥斯曼帝国直接挡在赴中亚的贸易途径上。最后,马穆鲁克制度证明太僵硬,不愿采用新军事技术,尤其是步兵军队的火器。面对欧洲敌人的奥斯曼帝国,早在 1425 年就开始使用火器,约在欧洲探索此项革新的一个世纪之后。㉕他们很快掌握这些新武器,其大炮在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要到甘素卧·胡里苏丹(1501—1516 年在位)时期,方才认真试验火器,离他们毁灭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远。马穆鲁克骑士发现使用火器有损自己尊严,而政府又受铜铁矿产匮乏的限制。经过一些夭折的测试(十五门火炮在试用时全部炸坏),苏丹国设法装备了有限数量的火炮,并组建了非马穆鲁克的火枪第五军团。㉖但这些革新姗姗来迟,无法保住这个资金短缺、堕落、传统的政权。
阿尤布苏丹创建伯海里团,所想解决的问题与早期中国建国者所面临的完全相同,即在高度部落化的社会中组建军队,不得忠于自己的部落,只能忠于以他为代表的国家。他的对策是购买年轻外国人,切断其对家庭的忠诚。他们进入马穆鲁克奴隶大家庭后,在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获得晋升;每年招募新人,前途全凭自己的才干。如此建起的军事机器令人印象深刻,顶住两代蒙古军的进攻,将十字军战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为保卫埃及而打退帖木儿国。如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马穆鲁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伊斯兰教,否则,后者可能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马穆鲁克的制度设计又包含了自己消亡的种子。马穆鲁克直接参政,不满足于担任国家的代理人。没人可以管教他们,每一名马穆鲁克都能追求苏丹一职,因此蓄谋弄权。王朝原则很早为最高层领袖所接受,很快传染给整个马穆鲁克上层,变成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精英。同时,这些精英没有安全产权,想方设法从苏丹手中保住自己的收入,以传给后裔。在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的治下,精英群体分化于年龄的差异,老牌马穆鲁克将年轻者招入自己的家族网络。曾将年轻马穆鲁克与国家绑在一起的训练不见了,只有为自己派别的赤裸裸的租金追求,他们使用强制力量,从平民百姓和其他马穆鲁克那里榨取资源。马穆鲁克精英为这些权力斗争煞费苦心,以致不得不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仅仅凭运气,15 世纪早期的帖木儿国侵略,没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外部威胁,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逐一崛起的世纪末。由于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外贸的丧失,马穆鲁克的财政日渐捉襟见肘。没有外部威胁,也就没有军事现代化的激励。奥斯曼帝国完善了军事奴隶制,并组建了更为强大的国家。所以,马穆鲁克 1517 年败于奥斯曼帝国,早成定局。
第 15 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奥斯曼帝国以欧洲君主做不到的方式集中权力;奥斯曼帝国完善军事奴隶制;不稳定的土耳其国家依赖持续的对外扩展;奥斯曼制度衰退的原因;军事奴隶制走进发展的死胡同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名的政论《君主论》写于 1513 年。其时,奥斯曼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将征服匈牙利,还将向哈布斯堡首都维也纳发起首次进攻。在该书第 4 章中,马基雅维利作出以下观察:
在我们的时代,两种各异的政府是土耳其和法国国王。土耳其整个君主政体由一人统治,其余的都是他的仆人。他将王国分割为众多桑贾克(sanjaks,编按:相当于中国的县或区),派去不同的行政官,可以随意调换。而法国国王身处自古就有的领主中间,后者在国内获得百姓的认可和爱戴,享有自己的特权,国王不可予以取消,否则会有危险。因此,无论谁在觊觎这两个国家,你将发现很难征服土耳其,但一旦征服,维持非常容易;作为对照,在某些方面,你会发现攫取法国比较容易,但很难维持。①
马基雅维利抓住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它在 16 世纪早期的治理,比法国更加集中、更加非人格化,因此更加现代化。16 世纪后期,法国国王攻击地主贵族的特权,试图创建同样集中统一的政权。他从巴黎派遣总督(intendents)——现代地方长官的前身——去直接管理王国,像治理各桑贾克的土耳其长官贝伊(bey,县长或区长),以取代地方的家族精英。奥斯曼帝国采用的制度与众不同,以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为基础,建成了高度强大且稳定的国家,可匹敌欧洲其时的任何政权,治理着比阿拉伯哈里发或苏丹所打造的任何一个都要大的帝国。奥斯曼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明朝有相似处,它们都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国家之外的社会参与者都相当薄弱,缺乏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奥斯曼政权仍受法律限制。)奥斯曼的国家制度是现代和家族制的奇怪混合体。家族制一旦以现代因素为代价来保护既得利益,国家制度就会衰败。奥斯曼帝国完善了马穆鲁克的军事奴隶制,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精英把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天性。
仅一代的贵族
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行政制度,即土耳其苏丹随意派遣和调换去外省的行政官,其根源在于,奥斯曼帝国尚是新兴的征战朝代,没有古老的制度可以继承,只能创建全新的制度。蒙古人 13 世纪的征服把一系列土库曼(Turcoman)部落,从中亚和中东赶到小亚细亚西部的边境地区,使之夹在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塞尔柱(Seijuk,自 1243 年起成为蒙古伊儿汗国的属国)苏丹国之间。这些部落组织起来,向拜占庭发动攻击(gaza)。领袖之一的奥斯曼(Osman)1302 年在巴菲翁(Baphaeon)打败拜占庭军队,因此而声名鹊起,鹤立鸡群,吸引其他边境领袖前来投靠。于是,宛如暴发户的边境国家奥斯曼得以站稳脚跟。它东西出击,以征服新领土,并向周边的成熟国家借用现成制度。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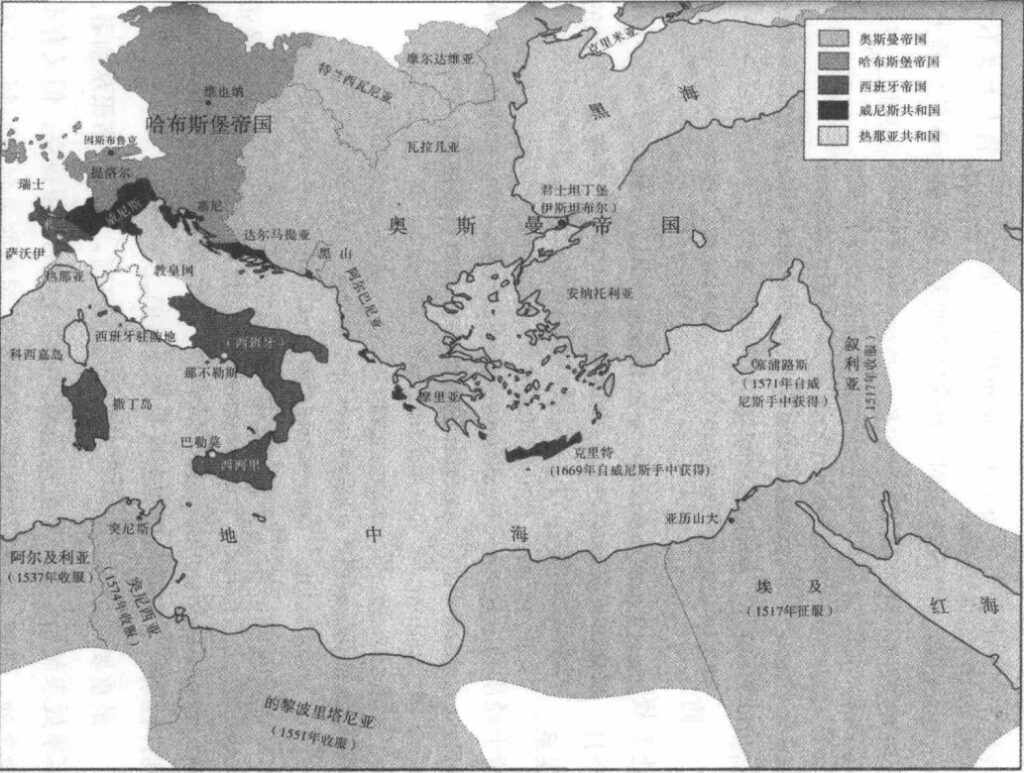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源于 15 世纪的西帕希骑士(sipahi)和其封地蒂玛(timar,养马的意思)。最小的封地只有一至数座村庄,其税收只能负担拥有马和其他装备的单名骑士。较大的封地叫扎美(zeamet),分配给称为扎伊姆(zaim)的中级官员,高级官员分到的封地叫哈斯(has)。骑士或扎伊姆住在自己的封地,向本地农民征收实物税,通常是每个农民每年上缴一车木材和饲料,再加上半车干草。该制度是拜占庭的,奥斯曼帝国只是信手拈来。像欧洲的领主,骑士也提供地方政府的功能,如安全和司法。他还要想方设法将实物转换成现金,以支付装备和奔赴前线的旅费。较大封地的主人被要求提供第二名骑士,包括侍从和装备。整个制度称作迪立克采邑制(dirlik),迪立克意即生计,这也是它的功能。其时的经济仅取得部分货币化,苏丹的军队由此获得维持,无须增税以付军饷。③
地方政府围绕桑贾克组成,包括数千平方英里和将近十万人口。奥斯曼帝国征服新领土,便组成新的桑贾克,并实施详尽的土地清查,列出每个村庄的人力和经济资源,目的就是为了纳税和分配封地。起初,用于各地的规则因地制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领土的快速增加,法律和规则趋于统一。④桑贾克长官贝伊不是从本地招聘的,而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指派。跟中国的地方官一样,他们任职三年后必须改任他职。⑤参战时,他们又是率领自己治下的骑士军队的将领。⑥比桑贾克级别更高的行政区是州(beylerbeyilik),他们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区域。
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迪立克制度与欧洲封建制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土耳其封地不能转换成遗传财产,不能传给骑士的后裔。由于新兴帝国的多数领土都是新近征服的,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约 87% 在 1528 年获得),封给骑士的期限只是他的一生。封地是为了换取军事服务,如果没有提供军事服务,苏丹就可收回封地。跟欧洲不同,大片封地的主人不可再作进一步的分封。骑士太老不能参与战役,或中途夭亡时,他的封地便要上缴,被分配给新骑士。骑士的地位不可遗传,军人的孩子必须回归平民。⑦在封地上耕种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不像他们的主人,其孩子可继承这种使用权。⑧所以,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仅一代的贵族,防止了享有资源基础和世袭特权的强大地主贵族涌现。⑨
防止领土贵族的出现还有其他实际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经常处于战争,因此要求骑士在夏季前来报到候战。所以每年有好几个月,封地主人外出,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骑士与封地的联系。有时,骑士必须在他处过冬,妻子和孩子要在家里独立谋生。骑士经常利用外出机会,挑上新的配偶。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贵族与封地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欧洲发展中是异常重要的。⑩
完善军事奴隶制
迪立克采邑制得靠军事奴隶制,不然就会管理失当。奥斯曼帝国以阿拔斯王朝、马穆鲁克和其他土耳其统治者的军事奴隶制为基础,但剔除了使马穆鲁克制度失灵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文官和军官之间有明确差别,后者严格服从前者。军事奴隶制始于苏丹家庭的延伸,像阿尤布的马穆鲁克。但又有不像之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一直保留对军事奴隶制的控制,直到帝国晚期。王朝原则仅适用于奥斯曼统治者的家庭。不管职位多高,才能多大,奴隶永远都不能成为苏丹,或在军事机构中创建自己的小朝廷。因此,文官政府可建立招收、训练、晋升的明确规则,侧重于建立高效的军事管理机构,不必担心其以军政府名义夺取政权。
为了防止军事机构中的小朝廷,遂定下有关孩子和遗产的严格规则。禁卫军的儿子不得加入禁卫军,在帝国早期,他们甚至不得结婚和组织家庭。皇家禁卫骑士(sipahis of the Porte)的儿子可加入骑士团队充任侍从,但孙子绝对不可。奥斯曼帝国似乎一开始就明白,军事奴隶制就是为了避免既得利益的世袭精英。军事奴隶制中的招收和晋升全靠能力和服务,他们的奖励是免税地位和庄园。⑪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派驻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宫廷的大使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提及,缺乏世袭贵族的事实允许苏丹挑选奴隶,全凭能力来提拔,“出身于牧羊人的杰出大维齐尔,欧洲评论家对他一直着迷不止”。⑫
奥斯曼帝国改善了马穆鲁克制度,将招募进执政机构的非穆斯林奴隶(askeri)与帝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百姓(reaya)严格分开。后者可有家庭和财产,可将财产和土地遗传给子孙。他们也可根据宗派附属关系,组织成半自治的社区米勒特(millets),但不能成为执政精英的一员,不能携带兵器,不能当兵或在奥斯曼政府中当官。非穆斯林奴隶的干部通常每年更新,因为年年都有新招募的基督徒。他们被切断与家庭的关联,只对奥斯曼国家效忠,没有行会、派别、自治协会,一切忠诚献给统治者。⑬
作为治理机构的奥斯曼国家
有证据显示,初期的奥斯曼帝国没有实施最大化征税。说得更确切些,他们视自己为监护人,除了较低水平的征税,还在保护农民对抗更像有组织犯罪的精英。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晚期发生财政困难,苏丹不得不大大提高征税水平。
继承于早期中东政权的自我约束已融入奥斯曼的国家理论。波斯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 年在位)曾说,“如有公正和适度,百姓将生产更多,税收将增加,国家将变得富强,公正是强国的基石”。⑭这里的“公正”意味着适度的征税。⑮我们可能发现,这无疑是里根执政时流行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中东版本:低税率给予个人较多奖励,个人因此生产较多,最后的总税收也水涨船高。这种想法获得早期土耳其学者的赞同⑯,并进入所谓的公平圆圈(circle of equity),由八条谚语组成:
1. 没有军队就没有皇家权力。
2. 没有财富就没有军队。
3. 百姓生产财富。
4. 苏丹以公正统治来留住百姓。
5. 公正需要世界的和谐。
6. 世界是花园,国家是花园的围墙。
7. 国家支柱是宗教法律。
8. 没有皇家权力,宗教法律就失去支持。
这些谚语通常环绕一个圆圈写下,到了第八条再轮回到第一条。这显示,对皇家权力(第一条)来说,宗教合法性(第八条)又是不可或缺的。⑰这是一份异常简洁的声明,阐述军事力量、经济资源、公正(包括税率)、宗教合法性的相互关系。这表明,土耳其统治者的目标不是经济租金最大化,而是平衡了权力、资源和合法性的综合国力最大化。⑱
与同期的欧洲君主政体相比,奥斯曼制度有个重大缺陷,因此而变得不稳定,那就是缺乏成熟的长子继承制或其他继承规则。按照中东的古老传统,统治者的继承权在上帝手中,建立继承规则有悖上帝的愿望。⑲在继承权未定时,不同候选人急需禁卫军、宫廷官员、乌里玛(ulama,教权阶层)、行政机器的支持。苏丹青春期的儿子跟导师一起去不同省城,以获取总督的工作经验,最靠近首都的儿子在影响禁卫军和宫廷方面就占了便宜。苏丹死后,儿子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偶尔,苏丹尚未死去就有人抢班夺权。在这些情况下,兄弟之间的残杀在所难免。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1595—1603 年在位)夺权时,在宫殿里处决了十九个兄弟。他终止将儿子送去外省的安排,让他们住在宫殿内特别居所,其生活宛如囚犯。⑳有人会说,这种制度确保新苏丹将是最严厉最残忍的儿子。但没有制度化的继承规则,往往造成致命弱点,在继承期间容易受到外国威胁,并让制度中的参与者获得过度的影响力,如仅是苏丹代理人的禁卫军。
奥斯曼帝国混乱的继承机制,让人们怀疑其制度在总体上的建制化。像处理中国情形一样,马克斯·韦伯也把奥斯曼制度归为家族制,而不属于现代。如果把“家族制”定位为整个政府听从统治者家庭,一切取决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奥斯曼制度确实如此。几乎国家的所有雇员,其正式地位都是奴隶,这表明苏丹对整个官僚机构享有绝对控制权。跟中国皇帝一样,他可以命令处决上至大维齐尔(首相)的任何官员。苏丹还有权更改制度上的任何规则,如苏莱曼一世决定放松禁卫军不得组织家庭的禁令。
另一方面,不管苏丹在理论上的权力,他治下的政府照章办事,所作的决定可以预测。首先,奥斯曼苏丹受穆斯林宗教法律——伊斯兰教法(sharia)——的束缚,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像中世纪的基督教君主,苏丹正式承认上帝的主权和法律,他自己的权力只是来自上帝的委托。法律的监护人是庞大庄严的宗教机构,乌里玛(神职学者)解说法律,主持宗教法庭,裁决家庭、婚姻、遗产和其他私人事务。对日常层次的执法,苏丹不予干涉。私人产权和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受到类似保护(参看第 19 章)。甚至混乱的继承权争斗,在一定意义上也以伊斯兰法律为依据,其原则就是禁止长子继承权。
奥斯曼政府照章办事,还出于代理制的需要。绝对统治者必须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委托给代理人,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由于专长和能力,代理人开始营建自己的权力。这在统治像奥斯曼帝国这样辽阔、多样、复杂的地域时,尤其如此。
很奇怪,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却是奥斯曼帝国最现代的特征之一。在功能上,它的目标与中国科举完全相同:都是国家非人格化招聘的来源,确保源源不断的候选人面对激烈的选择,只效忠于国家,与家庭和亲戚没有牵连,以攀高位。与中国相比,它比较不合理,因为它只允许外国人参与。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家族化,可以撇开与家庭或地方藕断丝连的本地精英。㉑
衡量国家制度现代性的另一尺度是法律和程序在帝国的统一。理所当然,中国人设下了最佳标准,很早就创造了不同寻常的统一行政制度,很少例外。奥斯曼制度则允许较多的差异,帝国的中央地区、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开始实施相当统一的规则,如土地租佃、征税、司法等。奥斯曼帝国强迫奴隶军改信伊斯兰教,但没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外省的行政机构。希腊人、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人,虽然享受不到穆斯林的法律权利,但仍能组织半自治社区。这些社区的宗教领袖负责财政、教育、执法和其他有关家庭法律和人身地位的事务。㉒离帝国的中心越远,地方上的制度就越偏离核心规则。在 1517 年打败马穆鲁克之后,中东的重要地区,包括埃及、叙利亚、汉志(Hejaz,现代沙特阿拉伯沿红海的西部地区),并入帝国的版图。马穆鲁克获准保留自己的军事奴隶制,但必须承认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汉志则实施自己的特殊规则,因为拥有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帝国现是穆斯林的监护人。
家族制的复辟和衰败
奥斯曼制度的衰退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帝国的地理极限,以及人口和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些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土耳其,而且影响了所有的农业大国。内部因素包括军事奴隶制的崩溃、禁卫军由国家权力的工具蜕变成既得利益团体。
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制度一开始就是一个征服王朝,依赖领土的持续扩张来增加税收和封地。到 16 世纪 30 年代末,奥斯曼帝国面对两条战线,相隔几乎两千英里:在东欧与奥地利人对峙,在波斯与新近崛起的萨非王朝(Safavid)争锋。奥斯曼帝国虽能动员其人力的大部,但军队不能整年驻扎在外。以当时的技术,他们开发了先进的物流制度,但军队仍需在春天聚合,行军数百英里,奔赴前线。第一次征服维也纳败北,因为军队抵达维也纳郊外已是 1529 年 9 月 27 日,围攻不到三个星期,就不得不放弃,因为军队要在冬天之前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类似的局限也存在于波斯前线。㉓
奥斯曼帝国为此决定全年防守匈牙利,并改善海军,以开展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他们继续赢得战利品(如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直到 17 世纪中期。但是,轻易的领土征服到 16 世纪中已近尾声,武装的外部掠夺不再是经济租金的良好来源。这给内部统治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更高水平的资源榨取必须来自帝国核心地区,而不是边境地区。没有新的基督教领土,也就减少了征募制人选的供应。
另一个外部发展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互为表里。从 1489 年到 1616 年,小亚细亚谷物的恒定银价上升了 400%。很多学者将价格上升归罪于来自西班牙新大陆的金银增长,但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认为,有理由说奥斯曼帝国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事件,因为没有找到新金银进入奥斯曼土地的证据。实际上,政府因为白银短缺而一再降低铸币的含银量。更确切地说,通货膨胀是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从 1520 年到 1580 年,小亚细亚的人口增长了 50% 到 70%。从 1520 年到 1600 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十万增至七十万。这种人口增长同时也在欧洲和中国发生,原因不明,但一定与 15 世纪摧毁欧亚大陆人口的瘟疫的退潮有关。戈德斯通认为这可能与气候有关,再加上人类由此而增强的免疫力。㉔
这些变化大大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制度,通货膨胀使采邑制度愈来愈靠不住。采邑的骑士靠土地生活,但另有土地和军事装备的货币开支,现在变得不堪忍受。很多人拒绝参与战役,另外的干脆放弃封地,开始组成掠夺农民和地主的强盗帮派。驻扎在城市的禁卫军,为应付开支,获准从事手艺人或商人的民间职业,这模糊了奴隶和百姓之间的明显界限。有些禁卫军当上财政官员,操纵采邑登记以谋私利,或授予自己土地,或分配土地给百姓以换取贿赂。㉕
16 世纪晚期,中央国家也面对财政危机。火器的引进使曾是 15 世纪奥斯曼部队支柱的骑士变成老皇历,国家必须以骑士为代价迅速扩充步兵。从 1527 年到 1609 年,禁卫军的人数从五千增至三万八千,再增至 1669 年的六万七千五百。此外,政府开始招募无地农民(sekbans)充任临时火枪手。㉖不像自我负担的旧骑士,这些新式步兵需配备现代武器,领取现金薪水。所以,政府急需将征税得来的实物,转换成已是经济交易基础的现金。骑士人数的跌幅相当于步兵人数的涨幅,放弃的采邑现在租给私人经营者,出身于非奴隶的税务承包商向他们征收现金。先前,政府约束对农民的剥削,现在为应付财政收入的燃眉之急,也就顾不上了。㉗
考虑到财政困境,军事奴隶制的规则受到腐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马穆鲁克的经验,阻止奴隶军人将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规则很难执行,因为这有悖人性。奥斯曼帝国的原始制度非常严格,规定禁卫军坚持独身,不得组织家庭。但在制度内部,一直有放松规则的压力。当遇上与日俱增的财政压力时,政府只得作出让步。这一过程始于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1512—1520 年在位)和苏莱曼一世(1520—1566 年在位),先允许禁卫军结婚和组织家庭。随之,这些禁卫军又向宫廷施加压力,允许他们的儿子加入军队。这发生于塞利姆二世(Selim Ⅱ,1566—1574 年在位)时期,设立了专收禁卫军儿子的定额。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在 1638 年正式废除征募制,这等于确认了禁卫军子承父业的纳新制度,甚至百姓也被允许加入军人阶层。㉘晋升不再依据规则,愈来愈靠国家制度中的私人关系。以前局限于宫廷政治的家族制,现在扩散到整个体系。㉙
跟布尔吉马穆鲁克一样,将禁卫军与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也受到蛀蚀,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福利和家庭,变成一个为己谋利的利益团体。纪律趋于崩溃,禁卫军开始定期在首都发动骚乱,以抗议薪酬的拖欠或铸币的贬值。跟马穆鲁克相似,他们与民用经济挂钩,收购商业,或提取被人遗弃的采邑的租金。㉚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奥斯曼帝国从 17 世纪初开始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它还维持了三百多年,直到 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奥斯曼帝国仍能展示令人惊讶的精力,例如 17 世纪的下半世纪,科普鲁律(Köprülüs)大维齐尔得以在帝国的中央省恢复秩序,在地中海继续扩张,征服克里特岛,并于 1683 年再一次向维也纳发起进攻。㉛但这次中兴又遭逆转。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在波斯崛起,导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长期战争。奥斯曼帝国鼓励在全国贯彻逊尼派的正统观念,并杜绝外部新思想。它发现自己愈来愈无法赶上邻近欧洲帝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从而不得不割让领土,每隔十年再来一次。虽然如此,土耳其仍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打败英国人,进入 20 世纪时,继续是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
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世界中迄今最成功的政权。他们凭借自己创造的制度基础,集中权力,其规模在那个地区是空前的。他们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然后发展了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国家制度。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和军队,以非人格化的择优标准,挑选和晋升有限的外国招聘对象。这一制度得以克服中东社会的部落机构的局限。
此外,奥斯曼帝国创造了可从中央遥控的省级行政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他们实施相对统一的规则,确定经济的日常运作,维护辽阔帝国的治安。不像欧洲的封建主义,奥斯曼帝国从没允许制造政治分裂的地方贵族涌现。所以,不像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苏丹也无需向贵族讨回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制度,比 15 世纪同期的欧洲政治组织更为成熟和先进。
就集权和支配社会的能力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比较不像同期的欧洲国家和印度次大陆上建立的本土国家,而更接近于中华帝国。跟中国类似,它只有很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良好的社会团体。如马基雅维利所注意到的,没有古老的贵族血统,没有获得宪章的独立商业城市,没有民兵组织和法律制度。跟印度不同,村庄没有依照古老的宗教社会规则组织起来。
奥斯曼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先驱者,其不同于中国之处是存在立法的宗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国家。它能否限制国家的集权,说到底,取决于宗教权威本身的制度化程度。(我在第 21 章讨论法治起源时,将回到这一题目。)
就全球的政治发展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核心力量的军事奴隶制只是一条死胡同。它的产生基于一种担忧,同样的担忧促使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今天,中国科举制度的实用等同物都在应用之中,不管是现代欧洲和亚洲的官僚招聘,还是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e)。相比之下,军事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从世界政治舞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从未认为它是合法的。问题不在奴隶,众所周知,直到 19 世纪西方都视奴隶制为合法制度。欧洲人或美国人所无法想象的,是奴隶后来又变成政府高官。
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军事奴隶制充任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的基石。但它面对各种内部矛盾,不能幸免于 16 世纪晚期帝国面临的外部变化。奥斯曼帝国从没发展出本土的资本主义,不能长期取得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所以只能依赖粗放式增长来增加财政资源。经济和外交的政策失败,彼此雪上加霜,使本土制度无法承受。它继续生存于 20 世纪,多亏了创新的苏丹和最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改用西方制度。但这一切不足以保住政权,继承它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依据截然不同的制度原则。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