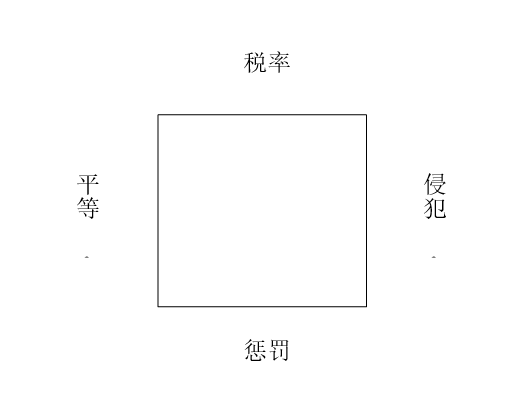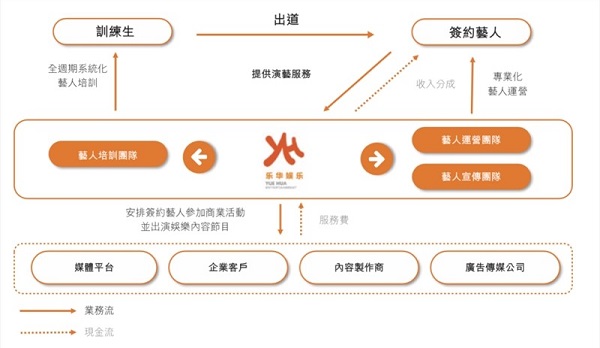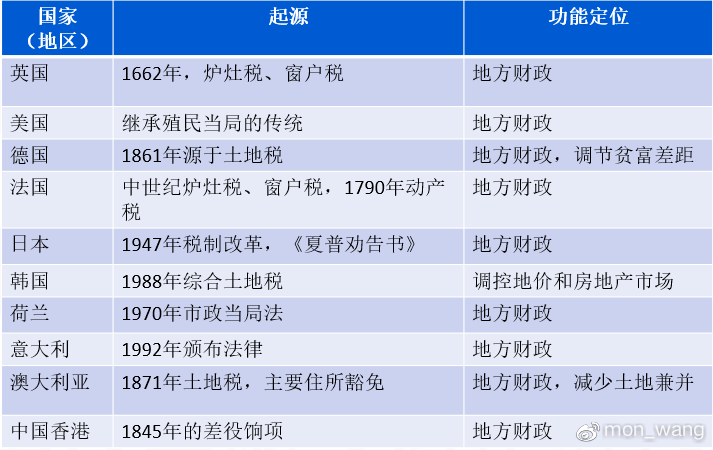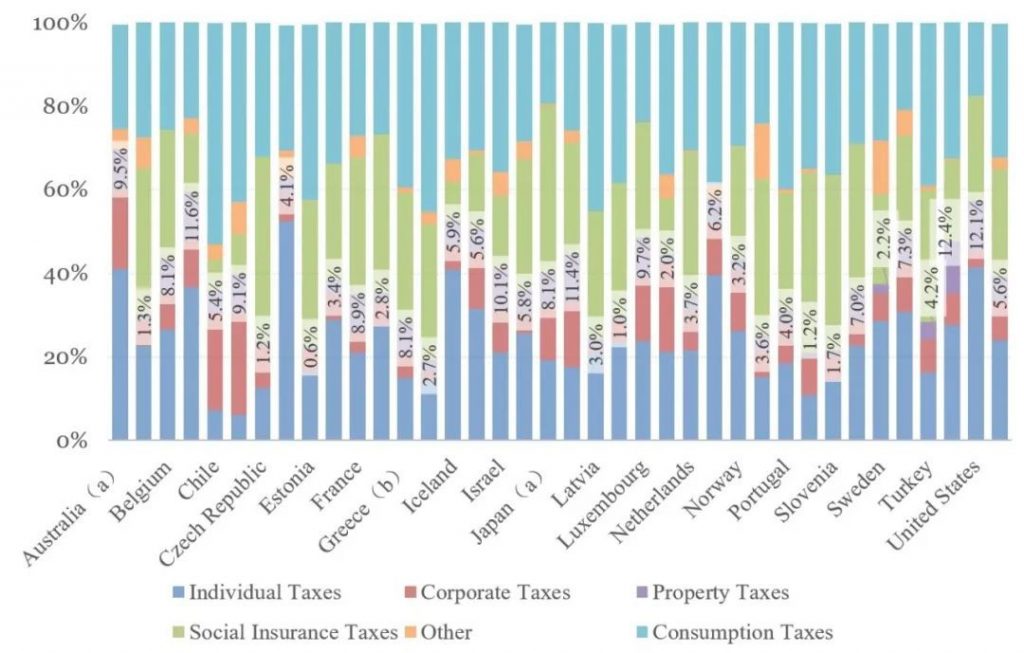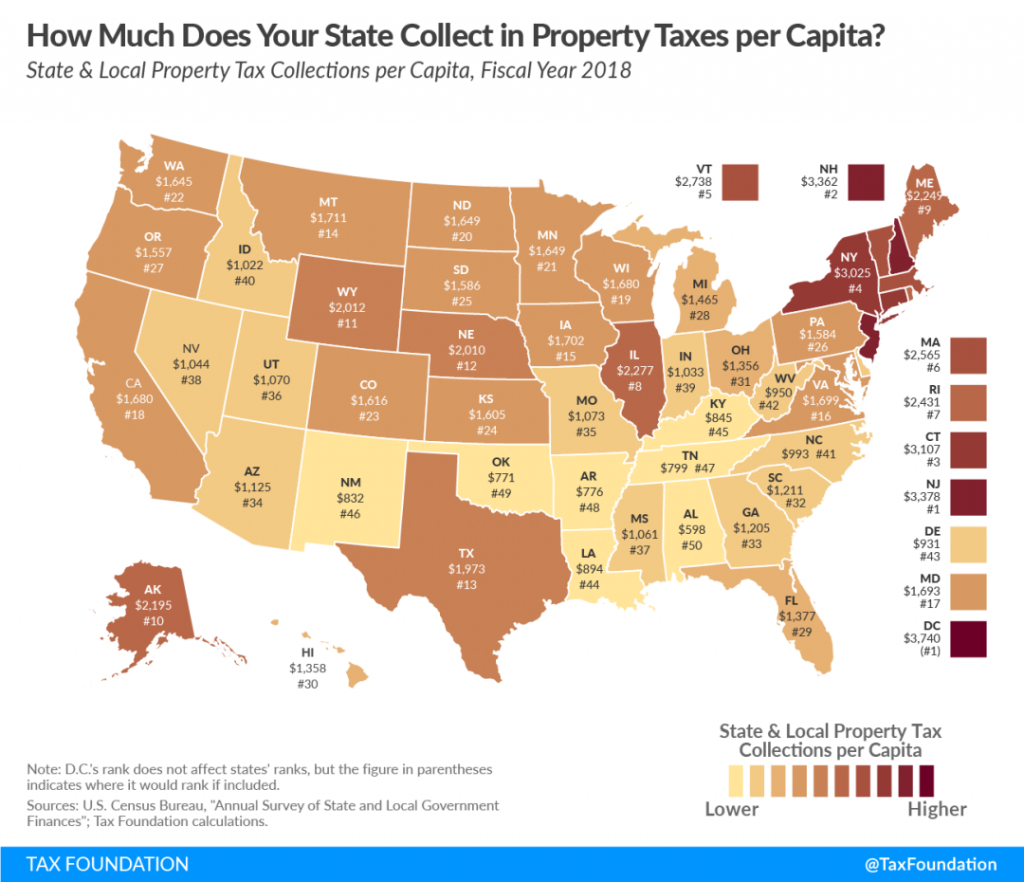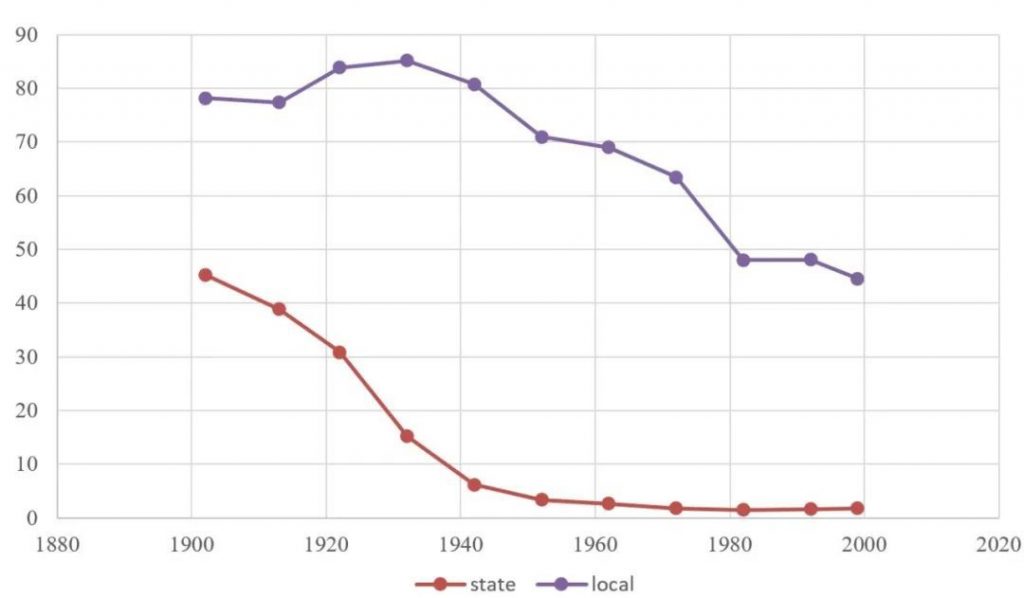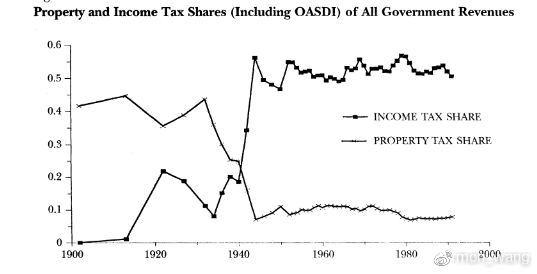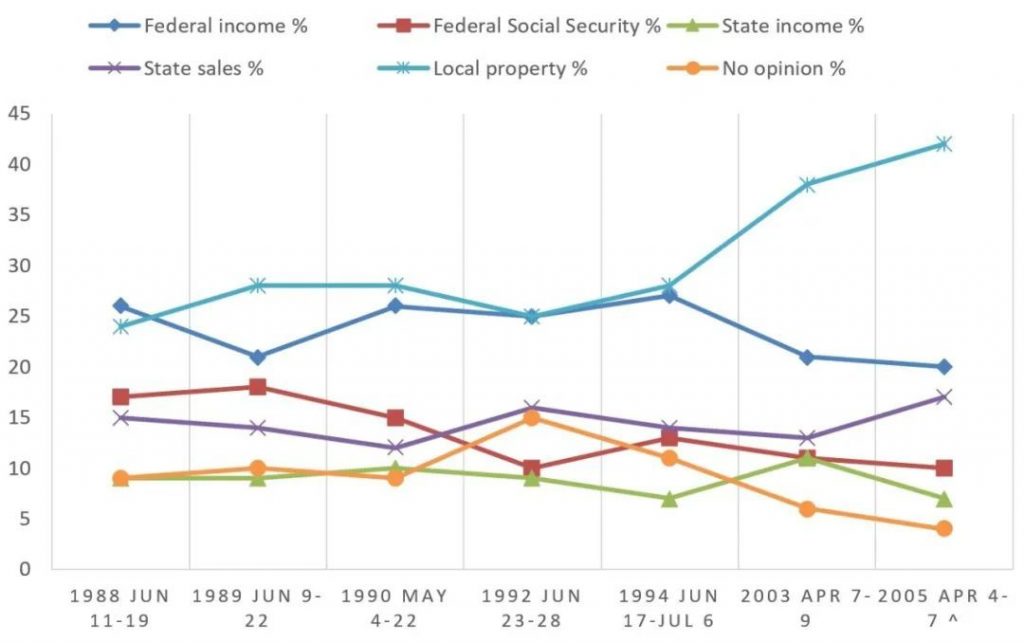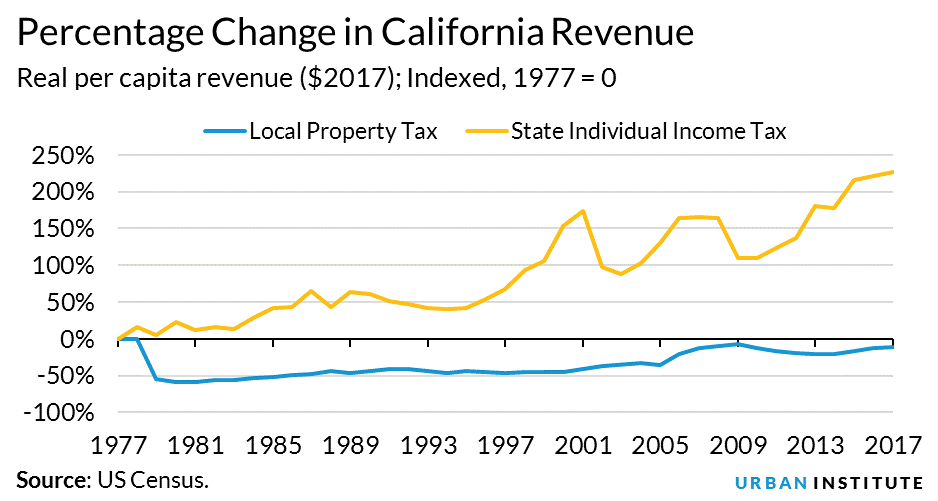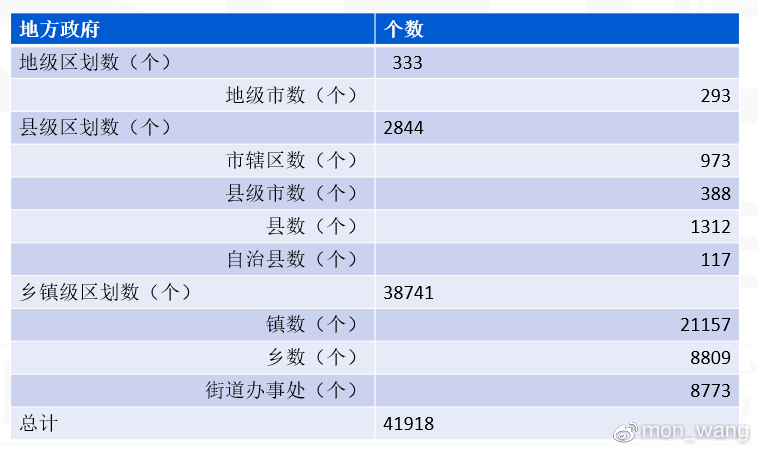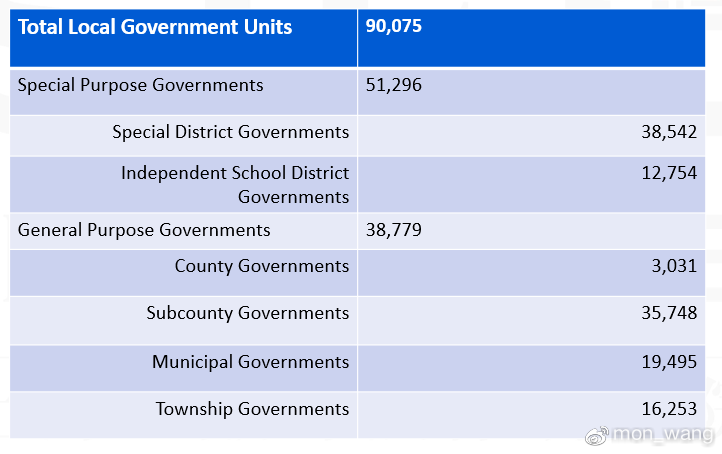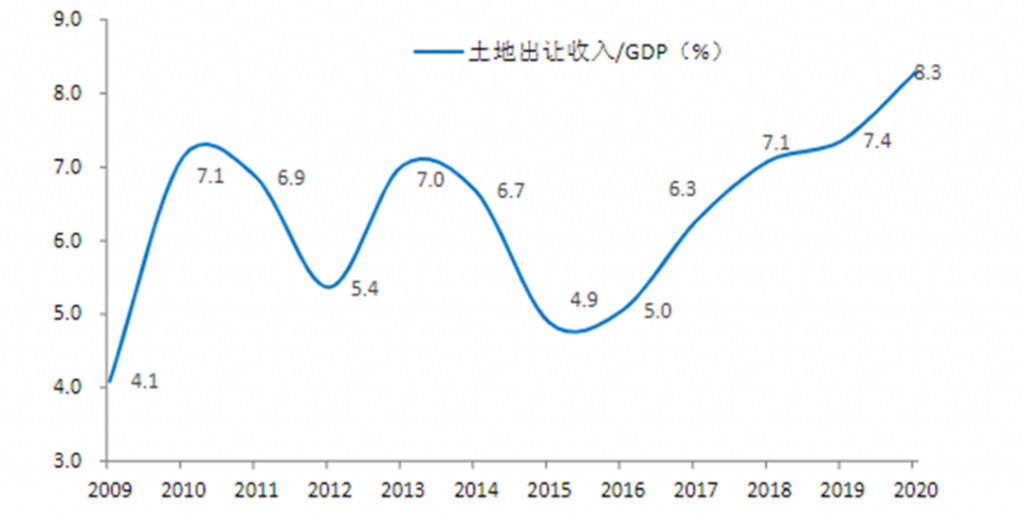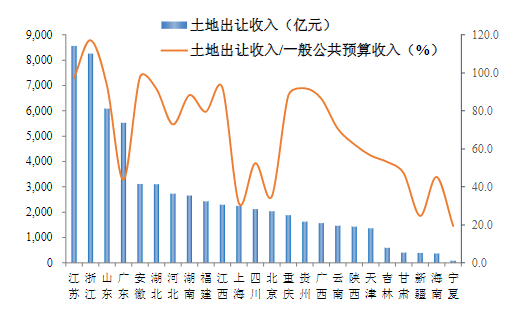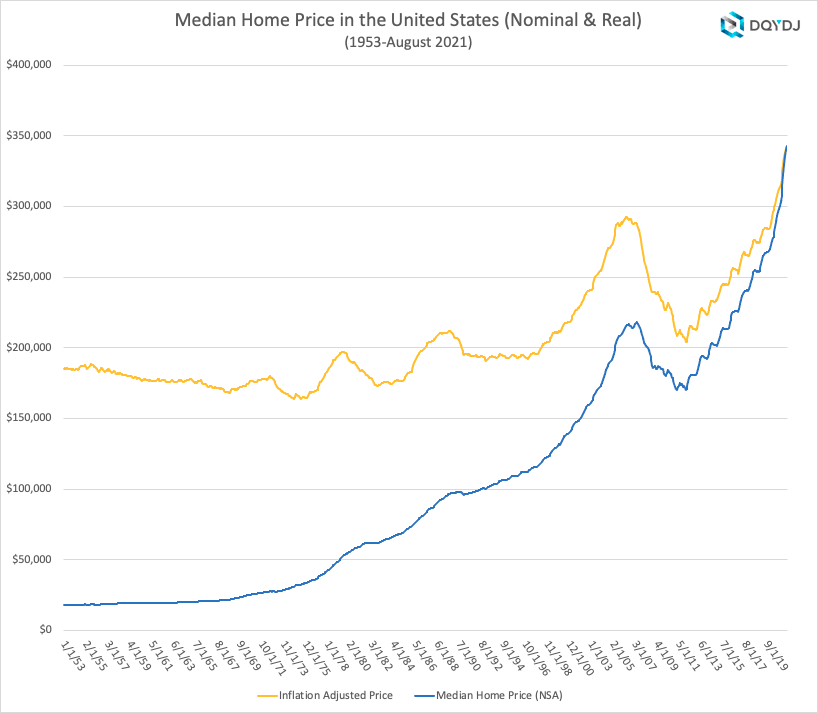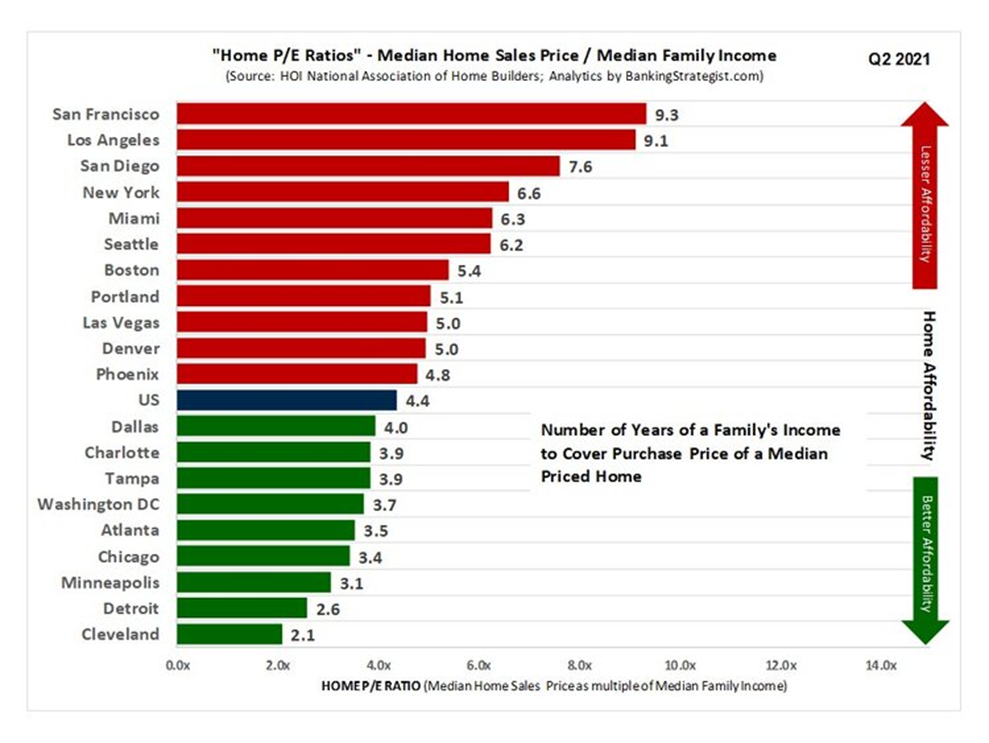第一章
体态丰满而有风度的勃克·穆利根[1]从楼梯口出现。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2]。他把那只钵高高举起,吟诵道:
我要走向上主的祭台。
他停下脚步,朝那昏暗的螺旋状楼梯下边瞥了一眼,粗声粗气地嚷道:
“上来,金赤[3]。上来,你这敬畏天主的耶稣会士[4]。”
他庄严地向前走去,登上圆形的炮座。他朝四下里望望,肃穆地对这座塔[5]和周围的田野以及逐渐苏醒着的群山祝福了三遍。然后,他一瞧见斯蒂芬·迪达勒斯就朝他弯下身去,望空中迅速地画了好几个十字,喉咙里还发出咯咯声,摇看头。斯蒂芬·迪达勒斯气恼而昏昏欲睡,双臂倚在楼梯栏杆上,冷冰冰地瞅着一边摇头一边发出咯咯声向他祝福的那张马脸,以及那顶上并未剃光[6]、色泽和纹理都像是浅色橡木的淡黄头发。
勃克·穆利根朝镜下瞅了一眼,赶快阖上钵。
“回到营房去,”他厉声说。
接着又用布道人的腔调说:
“啊,亲爱的人们,这是真正的克里斯廷[7]:肉体和灵魂,血和伤痕。请把音乐放慢一点儿。闭上眼睛,先生们。等一下。这些白血球有点儿不消停。请大家肃静。”
他朝上方斜睨,悠长地低声吹了下呼唤的口哨,随后停下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那口洁白齐整的牙齿有些地方闪射着金光。克里索斯托[8]。两声尖锐有力的口哨划破寂静回应了他。
“谢谢啦,老伙计,”他精神抖擞地大声说。“蛮好。请你关上电门,好吗?”
他从炮座上跳下来,神色庄重地望着那个观看他的人,并将浴衣那宽松的下摆拢在小腿上。他那郁郁寡欢的胖脸和阴沉的椭圆形下颚令人联想到中世纪作为艺术保护者的高僧。他的唇边徐徐地绽出了榆快的笑意。
“多可笑。”他快活地说。“你这姓名太荒唐了,一个古希腊人[9]。”
他友善而打趣地指了一下,一面暗自笑着,走到胸墙那儿。斯蒂芬·迪达勒斯爬上塔顶,无精打采地跟着他走到半途,就在炮座边上坐下来,静静地望着他怎样把镜子靠在胸墙上,将刷子在钵里浸了浸,往面颊和脖颈上涂起皂沫。
勃克·穆利根用愉快的声调继续讲下去。
“我的姓名也荒唐,玛拉基·穆利根,两个扬抑抑格。可它带些古希腊味道,对不?轻盈快活得正像只公鹿[10]。咱们总得去趟雅典。我要是能从姑妈身上挤出二十镑,你肯一道去吗?”
他把刷子撂在一边,开心地大声笑着说:
“他去吗,那位枯燥乏味的耶稣会士?”
他闭上嘴,仔细地刮起脸来。
“告诉我,穆利根,”斯蒂芬轻声说。
“嗯?乖乖。”
“海恩斯还要在这座塔里住上多久?”
勃克·穆利根从右肩侧过他那半边刮好的脸。
“老天啊,那小子多么讨人嫌!”他坦率地说。“这种笨头笨脑的撒克逊人,他就没把你看作一位有身份的人。天哪,那帮混账的英国人。腰缠万贯,脑满肠肥。因为他是牛津出身呗。喏,迪达勒斯,你才真正有牛津派头呢。他捉摸不透你。哦,我给你起的名字再好不过啦:利刃金赤。”
他小心翼翼地刮着下巴。
“他整宵都在说着关于一只什么黑豹的梦话,”斯蒂芬说,“他的猎枪套在哪儿?”
“一个可悯可悲的疯子!”穆利根说。“你害怕了吧?”
“是啊,”斯蒂芬越来越感到恐怖,热切地说,“黑咕隆咚地在郊外,跟一个满口胡话、哼哼卿卿要射杀一只黑豹的陌生人呆在一块儿。你曾救过快要淹死的人。可我不是英雄。要是他继续呆在这儿,那我就走。”
勃克·穆利根朝着剃胡刀上的肥皂沫皱了皱眉,从坐着的地方跳了下来,慌忙地在裤兜里摸索。
“糟啦,”他瓮声瓮气地嚷道。
他来到炮座跟前,把手伸进斯蒂芬的胸兜,说:
“把你那块鼻涕布借咱使一下。擦擦剃胡刀。”
斯蒂芬听任他拽出那条皱巴巴的脏手绢,捏着一角,把它抖落开来。勃克·穆利根干净利索地揩完剃胡刀,望着手绢说:
“‘大诗人’[11]的鼻涕布。属于咱们爱尔兰诗人的一种新的艺术色彩,鼻涕绿。简直可以尝得出它的滋味,对吗?”
他又跨上胸墙,眺望着都柏林湾。他那浅橡木色的黄头发微微飘动着。
“喏!”他安详地说。“这海不就是阿尔杰所说的吗:一位伟大可爱的母亲[12]?鼻涕绿的海。使人的睾丸紧缩的海。到葡萄紫的大海上去[13]。喂,迪达勒斯,那些希腊人啊。我得教给你。你非用原文来读不可。海!海[14]!她是我们的伟大可爱的母亲。过来瞧瞧。”
斯蒂芬站起来,走到胸墙跟前。他倚着胸墙,俯瞰水面和正在驶出国王镇[15]港口的邮轮。
“我们的强有力的母亲[16],”勃克·穆利根说。
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灰色眼睛猛地从海洋移到斯蒂芬的脸上。
“姑妈认为你母亲死在你手里,”他说。“所以她不计我跟你有任何往来。”
“是有人害的她,”斯蒂芬神色阴郁地说。
“该死,金赤,当你那位奄奄一息的母亲央求你跪下来的时候,你总应该照办呀,”勃克·穆利根说。“我跟你一样是个冷心肠人。可你想想看,你那位快咽气的母亲恳求你跪下来为她祷告。而你拒绝了。你身上有股邪气……”
他忽然打住,又往另一边面颊上轻轻涂起肥皂沫来。一味宽厚的笑容使他撇起了嘴唇。
“然而是个可爱的哑剧演员,”他自言自语着。“金赤,所有的哑剧演员当中最可爱的一个。”
他仔细地把脸刮得挺匀净,默默地,专心致专地。
斯蒂芬一只肘支在坑洼不平的花岗石上,手心扶额头,凝视着自己发亮的黑上衣袖子那磨破了的袖口。痛苦——还说不上是爱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她去世之后,曾在梦中悄悄地来找过他,她那枯槁的身躯裹在宽松的褐色衣衾里,散发出蜡和黄檀的气味;当她带着微嗔一声不响地朝他俯下身来时,依稀闻到一股淡淡的湿灰气味。隔着槛褛的袖口,他瞥见被身旁那个吃得很好的人的嗓门称作伟大可爱的母亲的海洋。海湾与天际构成环形,盛着大量的暗绿色液体。母亲弥留之际,床畔曾放着一只白瓷钵,里边盛着粘糊糊的绿色胆汁,那是伴着她一阵阵的高声呻吟,撕裂她那腐烂了的肝脏吐出来的。
勃克·穆利根又揩了揩剃刀刃。
“啊,可怜的小狗[17]!”他柔声说,“我得给你件衬衫,几块鼻涕布。那条二手货的裤子怎么样?”
“挺合身,”斯蒂芬回答说。
勃克·穆利根开始刮下唇底下凹陷的部位。
“不是什么正经玩艺儿,”他沾沾自喜地说,“应该叫作二腿货。天晓得是哪个患了梅毒的酒疯子丢下的。我有一条好看的细条纹裤子,灰色的。你穿上一定蛮帅。金赤,我不是在开玩笑。你打扮起来,真他妈的帅。”
“谢谢,”斯蒂芬说,“要是灰色的,我可不能穿。”
“他不能穿,”勃克·穆利根对着镜中自己的脸说,“礼数终归是礼数。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可是不能穿灰裤子。”
他利利索索地折上剃胡刀,用手指的触须抚摩着光滑的皮肤。
斯蒂芬将视线从海面移向那张有着一双灵活的烟蓝色眼睛的胖脸。
“昨儿晚上跟我一道在‘船记’[18]的那个人,”勃克·穆利根说,“说是你患了痴麻症。他是康内利·诺曼的同事,在痴呆镇工作[19]。痴呆性全身麻痹症。”
他用镜子在空中划了半个圈子,以便把这消息散发到正灿烂地照耀着海面的阳光中去。他撇着剃得干干净净的嘴唇笑了,露出发着白光的齿尖。笑声攫住了他那整个结实强壮的身子。
“瞧瞧你自己,”他说,“你这丑陋的‘大诗人’。”
斯蒂芬弯下身去照了照举在跟前的镜子。镜面上有一道弯曲的裂纹,映在镜中的脸被劈成两半,头发倒竖着。他和旁人眼里的我就是这样的。是谁为我挑选了这么一张脸?这只要把寄生虫除掉的小狗。它也在这么问我。
“是我从老妈子屋里抄来的,”勃克·穆利根说。“对她就该当如此。姑妈总是派没啥姿色的仆人去伺候玛拉基。不叫他受到诱惑[20]。而她的名字叫乌水苏拉[21]。”
他又笑着,把斯蒂芬直勾勾地望着的镜子挪开了。
“凯列班在镜中照不见自己的脸时所感到的愤怒,”[22]他说。“要是王尔德还在世,瞧见你这副尊容,该有多妙。”
斯蒂芬后退了几步,指着镜子沉痛地说:
“这就是爱尔兰艺术的象征。仆人的一面有裂纹的镜子[23]。”
勃克·穆利根突然挽住斯蒂芬的一只胳膊,同他一道在塔顶上转悠。揣在兜里的剃胡刀和镜子发出相互碰撞的丁当声。
“像这样拿你取笑是不公道的,金赤,对吗?”他亲切地说。“老天晓得,你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有骨气。”
又把话题岔开了。他惧怕我的艺术尖刀,正如我害怕他的冷酷无情的钢笔。
“仆人用的有裂纹的镜子。把这话讲给楼下那个牛津家伙[24]听,向他挤出一基尼[25]。他浑身发散着铜臭气,没把你看成有身份的人。他老子要么是把药喇叭[26]根做成的泻药卖给了祖鲁人[27],要么就是靠干下了什么鬼骗局发的家。喂,金赤,要是咱俩通力合作,兴许倒能为本岛干出点名堂来。把它希腊化了[28]。”
克兰利的胳膊[29]。他的胳膊。
“想想看,你竟然得向那些猪猡告帮!我是唯一赏识你的人。你为什么不更多地信任我呢?你凭什么对我鼻子朝天呢?是海恩斯吗?要是他在这儿稍微一闹腾,我就把西摩[30]带来,我们会狠狠地收拾他一顿,比他们收拾克莱夫·肯普索普的那次还要厉害。”
从克莱夫·肯普索普的房间里传出阔少们的喊叫声。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他们抱在一起,捧腹大笑。唉呀。我快断气啦!要委婉地向她透露这消息,奥布里 [31]!我这就要死啦!他围着桌子一瘸一拐地跑,衬衫被撕成一条条的,像缎带一般在空中呼扇着,裤子脱落到脚后跟上[32],被麦达伦学院那个手里拿着裁缝大剪刀的埃德斯追赶着。糊满了桔子酱的脸惊惶得像头小牛犊。别扒下我的裤子!你们别拿我当呆牛耍着玩!
从敞开着的窗户传出的喧嚷声,惊动了方院的暮色。耳聋的花匠系着围裙,有着一张像煞马修·阿诺德[33]的脸,沿着幽幽的草坪推着割草机,仔细地盯着草茎屑末的飞舞。
我们自己……新异教教义……中心[34]。
“让他呆下去吧,”斯蒂芬说。“他只不过是夜间不对头罢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勃克·穆利根不耐烦地问道。“干脆说吧。我对你是直言不讳的。现在你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呢?”
他们停下脚步,眺望着布莱岬角[35]那钝角形的海岬——它就像一条酣睡中的鲸的鼻尖,浮在水面上。斯蒂芬轻轻地抽出胳膊。
“你要我告诉你吗?”他问。
“嗯,是怎么回事?”勃克·穆利根回答说。“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啦。”
他边说边端详斯蒂芬的脸。微风掠过他的额头,轻拂着他那未经梳理的淡黄头发,使焦灼不安的银光在他的眼睛里晃动。
斯蒂芬边说边被自己的声音弄得很沮丧:
“你记得我母亲去世后,我头一次去你家那天的事吗?”
勃克·穆利根马上皱起眉头,说:
“什么?哪儿?我什么也记不住。我只记得住观念和感觉[36]。你为什么问这个?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沏茶,”斯蒂芬说,“我穿过楼梯平台去添开水。你母亲和一位客人从客厅里走出来。她问你,谁在你的房间里。”
“咦?”勃克·穆利根说。“我说什么来看?我可忘啦。”
“你是这么说的,”斯蒂芬回答道,“哦,只不过是迪达勒斯呗,他母亲死得像头畜生。”
勃克·穆利根的两颊骤然泛红了,使他显得更年轻而有魅力。
“我是这么说的吗?”他问道。“啊?那又碍什么事?”
他神经质地晃了晃身子,摆脱了自己的狼狈心情。
“死亡又是什么呢?”他问道,“你母亲也罢,你也罢,我自己也罢。你只瞧见了你母亲的死。我在圣母和里奇蒙[37]那里,每天都看见他们突然咽气,在解剖室里被开膛破肚。这是畜生也会有的那种事情,仅此而已。你母亲弥留之际,要你跪下来为她祷告,你却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可诅咒的耶稣会士的气质,只不过到了你身上就拧啦。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个嘲讽,畜生也会有的事儿。她的脑叶失灵了。她管大夫叫彼得·蒂亚泽爵士[38],还把被子上的毛莨饰花拽下来。哄着她,直到她咽气为止呗。你拒绝满足她生前最后的一个愿望,却又跟我怄气,因为我不肯像拉鲁哀特殡仪馆花钱雇来的送葬人那样号丧。荒唐!我想必曾这么说过吧。可我无意损害你母亲死后的名声。”
他越说越理直气壮了。斯蒂芬遮掩着这些话语在他心坎上留下的创伤,极其冷漠地说:
“我想的不是你对我母亲的损害。”
“那么你想的是什么呢?”勃克·穆利根问。
“是对我的损害,”斯蒂芬回答说。
勃克·穆利根用脚后跟转了个圈儿。
“哎呀,你这家伙可真难缠!”他嚷道。
他沿着胸墙疾步走开。斯蒂芬依然站在原地,目光越过风平浪静的海洋,朝那岬角望去。此刻,海面和岬角朦朦胧胧地混为一片了。他两眼的脉搏在跳动,视线模糊了,感到双颊在发热。
从塔里传来朗声喊叫:
“穆利根,你在上边吗?”
“我这就来,”勃克·穆利根回答说。
他朝斯蒂芬转过身来,并说:
“瞧瞧这片大海。它哪里在乎什么损害?跟罗耀拉[39]断绝关系,金赤,下来吧。那个撒克逊征服者[40]早餐要吃煎火腿片。”
他的脑袋在最高一级梯磴那儿又停了一下,这样就刚好同塔顶一般齐了。
“不要成天为这档子事闷闷不乐。我这个人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别再那么苦思冥想啦。”
他的头消失了,然而楼梯口传来他往下走时的低吟声:
莫再扭过脸儿去忧虑,
沉浸在爱情那苦涩的奥秘里,
因黄铜车由弗格斯驾驭[41]。
树林的阴影穿过清晨的寂静,从楼梯口悄然无声地飘向他正在眺望着的大海。岸边和海面上,明镜般的海水正泛起一片白色,好像是被登着轻盈的鞋疾跑着的脚踹起来的一般。朦胧的海洋那雪白的胸脯。重音节成双地交融在一起。一只手拨弄着竖琴,琴弦交错,发出谐音。一对对的浪白色歌词闪烁在幽暗的潮水上。
一片云彩开始徐徐地把太阳整个儿遮住,海湾在阴影下变得越发浓绿了。这钵苦水就躺在他脚下。弗格斯之歌,我独自在家里吟唱,抑制着那悠长、阴郁的和音。她的门敞开着,她巴望听到我的歌声。怀着畏惧与怜悯,我悄悄地走近她床头。她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哭泣着。为了这一句,斯蒂芬,爱情那苦涩的奥秘。
而今在何处?
她的秘藏:她那上了锁的抽屉里有几把陈旧的羽毛扇、麝香熏过的带穗子的舞会请帖和一串廉价的琥珀珠子。少女时代,她家那浴满阳光的窗户上挂着一只鸟笼。她曾听过老罗伊斯在童话剧《可怕的土耳克》[42]中演唱,而当他这么唱的时候,她就跟旁人一起笑了:
我就是那男孩
能够领略随心所欲地
隐身的愉快。
幻影般的欢乐被贮存起来了,用麝香熏过的。
莫再扭过脸儿去忧虑……
随着她那些小玩艺儿,被贮存在大自然的记忆中了[43]。往事如烟,袭上他那郁闷的心头。当她将领圣体[44]时,她那一玻璃杯从厨房的水管里接来的凉水。在昏暗的秋日傍晚,炉架上为她焙着的一个去了核、填满红糖的苹果。由于替孩子们掐衬衫上的虱子,她那秀丽的指甲被血染红了。
在一个梦中,她悄悄地来到他身旁。她那枯稿的身躯裹在宽松的衣衾里,散发出蜡和黄檀的气味。她朝他俯下身去,向他诉说着无声的密语,她的呼吸有着一股淡淡的湿灰气味。
为了震撼并制伏我的灵魂,她那双呆滞无神的眼睛,从死亡中直勾勾地盯着我。只盯着我一人。那只避邪蜡烛照着她弥留之际的痛苦。幽灵般的光投射在她那备受折磨的脸上。当大家跪下来祷告时,她那嗄哑响亮的呼吸发出恐怖的呼噜呼噜声。她两眼盯着我,想迫使我下跪。饰以百合的光明的司铎群来伴尔,极乐圣童贞之群高唱赞歌来迎尔[45]。
食尸鬼[46]!啖尸肉者!
不,妈妈!由着我,让我活下去吧。
“喂,金赤!”
圆塔里响起勃克·穆利根的嗓音。它沿着楼梯上来,靠近了,又喊了一声。斯蒂芬依然由于灵魂的呼唤而浑身发颤,听到了倾泻而下的温煦阳光以及背后的空气中那友善的话语。
“迪达勒斯,下来吧,乖乖地快点儿挪窝吧。早点做好了。海恩斯为夜里把咱们吵醒的事宜表示歉意。一切都好啦。”
“我这就来,”斯蒂芬转过身来说。
“看在耶稣的面上,来吧,”勃克·穆利根说。“为了我,也为了咱们大家。”
他的头消失了,接着又露了出来。
“我同他谈起你那爱尔兰艺术的象征。他说,非常聪明。向他讨一镑好不好?我是说,一个基尼。”
“今儿早晨我就领薪水了,”斯蒂芬说。
“学校那份儿吗?”勃克·穆利根说。“多少呀?四镑?借给咱一镑。”
“如果你要的话,”斯蒂芬说。
“四枚闪闪发光的金镑,”勃克·穆利根兴高采烈地嚷道。“咱们要豪饮一通,把那些正宗的德鲁伊特[47]吓一跳。四枚万能的金镑。”
他抡起双臂,咚咚地走下石梯,用东伦敦口音荒腔走调地喝道:
啊,咱们快乐一番好吗?
喝威士忌、啤酒和葡萄酒,
为了加冕,
加冕日。
啊,咱们快乐一番好吗?
为了加冕日[48]。
暖洋洋的日光在海面上嬉戏着。镍质肥皂钵在胸墙上发着亮光,被遗忘了。我何必非把它带去不可呢?要么就把它撂在那儿一整天吧,被遗忘的友谊?
他走过去,将它托在手里一会儿,触摸着那股凉劲儿,闻着里面戳着刷子的肥皂沫那粘液的气味。当年在克朗戈伍斯[49]我曾提过香炉[50]。如今我换了个人,可又是同一个人。依然是个奴仆。一个奴仆的奴仆[51]。
在塔内那间有着拱顶的幽暗起居室里,穿着浴衣的勃克·穆利根的身姿,在炉边敏捷地镀来镀去,淡黄色的火焰随之忽隐忽现。穿过高高的堞口,两束柔和的阳光落到石板地上。光线汇合处,一簇煤烟以及煎油脂的气味飘浮着,打着旋涡。
“咱们都快闷死啦,”勃克·穆利根说。“海恩斯,打开那扇门,好吗?”
斯蒂芬将那只刮胡子用的钵撂在橱柜上。坐在吊床上的高个子站起来,走向门道,拉开内侧的两扇门。
“你有钥匙吗?”一个声音问道。
“在迪达勒斯手里,”勃克·穆利根说。“老爷爷,我都给呛死啦。”
他两眼依热望着炉火,咆哮道:
“金赤!”
“它就在锁眼里哪,”斯蒂芬走过来说。
钥匙刺耳地转了两下,而当沉重的大门半开半掩时,怡人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就进来了。海恩斯站在门口朝外面眺望。斯蒂芬把他那倒放着的旅行手提箱拽到桌前,坐下来等着。勃克·穆利根将煎蛋轻轻地甩到身旁的盘子里,然后端过盘子和一把大茶壶,使劲往桌上一放,舒了一口气。
“我都快融化了,”他说,“就像一枝蜡烛在……的时候所说过的。但是别声张。再也不提那事儿啦。金赤,振作起来。面包,黄油,蜂蜜。海恩斯,进来吧。开饭啦。‘天主降福我等,暨所将受于主,普施之惠。’[52]白糖呢?哦,老天,没有牛奶。”
斯蒂芬从橱柜里取出面包、一罐蜂蜜和盛在防融器中的黄油。勃克·穆利根突然气恼起来,一屁股坐下。
“这算是哪门子事呀?”他说。“我叫她八点以后来的。”
“咱们不兑牛奶也能喝嘛,”斯蒂芬说。“橱柜里有只柠檬。”
“呸,你和你那巴黎时尚统统见鬼去吧,”勃克·穆利根说。“我要沙湾牛奶。”
海恩斯从门道里镀了进来,安详地说:
“那个女人带着牛奶上来啦。”
“谢天谢地,”勃克·穆利根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坐下。茶在这儿,倒吧。糖在口袋里。诺,我应付不了这见鬼的鸡蛋。”
他在盘子里把煎蛋胡乱分开,然后甩在三个碟子里,口中念诵着: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53]。
海恩斯坐下来倒茶。
“我给你们每人两块方糖,”他说。“可是,穆利根,你沏的茶可真酽,呃?”
勃克·穆利根边厚厚地切下好儿片面包,边用老妪哄娃娃的腔调说:
“葛罗甘老婆婆[54]说得好,我沏茶的时候就沏茶,撒尿的时候就撒尿。”
“天哪,这可是茶。”海恩斯说。
勃克·穆利根边沏边用哄娃娃的腔调说:
“我就是这样做的,卡希尔大娘,她说。可不是嘛,老太太,卡希尔大娘说,老天保佑,你别把两种都沏在一个壶里。”
他用刀尖戳起厚厚的面包片,分别递到共餐者面前。
“海恩斯,”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倒可以把这些老乡写进你那本书里。关于登德鲁姆[55]的老乡和人鱼神[56],五行正文和十页注释。在大风年由命运女神姐妹[57]印刷。”
他转向斯蒂芬,扬起眉毛,用迷惑不解的口吻柔声问道:
“你想得起来吗,兄弟,这个关于葛罗甘老婆婆的茶尿两用壶的故事是在《马比诺吉昂》[58]里,还是在《奥义书》[59]里?”
“恐怕都不在,”斯蒂芬严肃地说。
“你现在这么认为吗?”勃克·穆利根用同样的腔调说。“请问,理由何在?”
“我想,”斯蒂芬边吃边说,“《马比诺吉昂》里外都没有这个故事。可以设想,葛罗甘老婆婆跟玛丽·安[60]有血缘关系。”
勃克·穆利根的脸上泛起欣喜的微笑。
“说得有趣!”他嗲声嗲气地说,露出洁白的牙齿,愉快地眨着眼,“你认为她是这样的吗?太有趣啦。”
接着又骤然满脸戚容,一边重新使劲切面包,一边用嘶哑刺耳的声音吼着:
因为玛丽·安老妪,
她一点也不在乎。
可撩起她的衬裙……
他塞了一嘴煎蛋,一边大嚼一边用单调低沉的嗓音唱着。
一个身影闪进来,遮暗了门道。
“牛奶,先生。”
“请进,老太太,”穆利根说,“金赤,拿罐儿来。”
老妪走过来,在斯蒂芬身边停下脚步。“多么好的早晨啊,先生,”她说。“荣耀归于天主。”
“归于谁?”穆利根说着,瞅了她一眼。“哦,当然喽!”
斯蒂芬向后伸手,从橱柜里取出奶罐。
“这岛上的人们,”穆利根漫不经心地对海恩斯说,“经常提起包皮的搜集者[61]。”
“要多少,先生?”老妪问。
“一夸脱[62],”斯蒂芬说。
他望着她先把并不是她的浓浓的白奶倾进量器,随后又倒入罐里。衰老干瘪的乳房。她又添了一量器的奶,还加了点饶头。她老迈而神秘,从清晨的世界踱了进来,兴许是位使者。她边往外倒,边夸耀牛奶好。拂晓时分,在绿油油的牧场里,她蹲在耐心的母牛旁边,一个坐在毒菌上的巫婆,她的皱巴巴的指头敏捷地挤那喷出奶汁的乳头。这些身上被露水打湿、毛皮像丝绸般的牛,跟她熟得很,它们围着她哞哞地叫。最漂亮的牛,贫穷的老妪[63],这是往昔对她的称呼。一个到处流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女神假借这个卑贱者的形象,伺候着她的征服者与她那快乐的叛徒[64]。她是受他们二者玩弄的母王八[65]。来自神秘的早晨的使者。他不晓得她究竟是来伺候的呢,还是来谴责的[66]。然而他不屑于向她讨好。
“的确好得很,老太太,”勃克·穆利根边往大家的杯子里斟牛奶边说。
“尝尝看,先生,”她说。
他按照她的话喝了。
“要是咱们能够靠这样的优质食品过活,”他略微提高嗓门对她说,“就不至于全国到处都是烂牙齿和烂肠子的了。咱们住在潮湿的沼泽地里,吃的是廉价食品,街上满是灰尘、马粪和肺病患者吐的痰。”
“先生,您是医科学生吗?”老妪问。
“我是,老太太,”勃克·穆利根回答说[67]。
斯蒂芬一声不吭地听着,满心的鄙夷。她朝那个对她大声说话的嗓门低下老迈低头,他是她的接骨师和药师; 她却不曾把我看在眼里。也朝那个听她忏悔,赦免她的罪愆,并且除了妇女那不洁净的腰部外,为她浑身涂油以便送她进坟墓的嗓门[68]低头,而妇女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69],却不是照神的形象造的[70],她成了蛇的牺牲品[71]。她还朝那个现在使她眼中露着惊奇、茫然神色保持缄默的大嗓门低头。
“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斯蒂芬问她。
“先生,您讲的是法国语吗?”老妪对海恩斯说。
海恩斯又对她说了一段更长的话,把握十足地。
“爱尔兰语,”勃克·穆利根说。“你有盖尔族[72]的气质吗?”
“我猜那一定是爱尔兰语,”她说,“就是那个腔调。您是从西边儿[73]来的吗,先生?”
“我是个英国人,”海恩斯回答说。
“他是一位英国人,”勃克,穆利根说,“他认为在爱尔兰,我们应该讲爱尔兰语。”
“当然喽,”老枢说,“我自己就不会讲,好惭愧啊。会这个语言的人告诉我说,那可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哩。”
“岂止了不起,”勃克·穆利根说。“而且神奇无比。再给咱倒点茶,金赤。老太太,你也来一杯好吗?”
“不,谢谢您啦,先生,”老妪边说边把牛奶罐上的提环儿套在手腕上,准备离去。
海恩斯对她说:
“你把帐单带来了吗?穆利根,咱们最好给她吧,你看怎么样?”
斯蒂芬又把三只杯子斟满。
“帐单吗,先生?”她停下脚步说。“喏,一品脱[74]是两便士喽七个早晨二七就合一先令[75]二便士喽还有这三个早晨每夸脱合四个便士三夸脱就是一个先令喽一个先令加一先令二就是二先令二,先生。”
勃克·穆利根叹了口气,并把两面都厚厚地涂满黄油的一块面包皮塞进嘴里,两条腿往前一伸,开始掏起裤兜来。
“清了账,心舒畅,”海恩斯笑吟吟地对他说。
斯蒂芬倒了第三杯。一满匙茶把浓浓的牛奶微微添上点儿颜色。勃克·穆利根掏出一枚佛罗林[76],用手指旋转着,大声嚷道:
“奇迹呀!”
他把它放在桌子面上,朝老妪推送过去,说着:
别再讨了,我亲爱的,
我能给的,全给你啦。[77]
斯蒂芬将银币放到老姻那不那么急切的手里。
“我们还欠你两便士,”他说。
“不着急,先生,”她边接银币边说。“不着急。早安,先生。”
她行了个屈膝礼,踱了出去。勃克·穆利根那温柔的歌声跟在后面:
心肝儿,倘若有多的,
统统献在你的脚前。
他转向斯蒂芬,说:
“说实在的,迪达勒斯,我已经一文不名啦。赶快到你们那家学校去,给咱们取点钱来。今天‘大诗人们’要设宴畅饮。爱尔兰期待每个人今天各尽自己的职责[78]。”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海恩斯边说边站起身来,“今天我得到你们的国立图书馆去一趟。”
“咱们先去游泳吧,”勃克·穆利根说。
他朝斯蒂芬转过身来,和蔼地问:
“这是你每月一次洗澡的日子吗,金赤?”
接着,他对海恩斯说:
“这位肮脏的‘大诗人’拿定主意每个月洗一次澡。”
“整个爱尔兰都在被湾流[79]冲洗着,”斯蒂芬边说边听任蜂蜜淌到一片面包上。
海恩斯在角落里正松垮垮地往他的网球衫那宽松领口上系领巾,他说:
“要是你容许的话,我倒想把你这些说词儿收集起来哩。”
他在说我哪。他们泡在澡缸里又洗又擦。内心的苛责。良心。可是这儿还有一点污迹[80]。
“关于仆人的一面有裂纹的镜子就是爱尔兰艺术的象征那番话,真是太妙啦。”
勃克·穆利根在桌子底下踢了斯蒂芬一脚,用热切的语气说:
“海恩斯,你等着听他议论哈姆莱特吧。”
“喏,我是有这个打算,”海恩斯继续对斯蒂芬说着。“我正在想这事儿的时候,那个可怜的老家伙进来啦。”
“我能从中赚点儿钱吗?”斯蒂芬问道。
海恩斯笑了笑。他一面从吊床的钩子上摘下自己那顶灰色呢帽,一面说道:
“这就很难说啦。”
他漫步朝门道踱了出去。勃克·穆利根向斯蒂芬弯过身去,粗声粗气地说:
“你这话说得太蠢了,为什么要这么说?”
“啊?”斯蒂芬说。“问题是要弄到钱。从谁身上弄?从送牛奶的老太婆或是从他那里。我看他们两个,碰上谁算谁。”
“我对他把你大吹了一通,”勃克·穆利根说,“可你却令人不快地斜眼瞟着,搬弄你那套耶稣会士的阴郁的嘲讽。”
“我看不出有什么指望,”斯蒂芬说,“老太婆也罢,那家伙也罢。”
勃克·穆利根凄惨地叹了口气,把手搭在斯蒂芬的胳膊上。
“我也罢,金赤,”他说。
他猛地改变了语调,加上一句:
“千真万确,我认为你说得对。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称。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作弄他们呢?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咱们从这窝里出去吧。”
他站起来,肃穆地解下腰带,脱掉浴衣,认头地说:
“穆利根被强剩下衣服[81]。”
他把兜儿都掏空了,东西放在桌上。
“你的鼻涕布就在这儿,”他说。
他一边安上硬领,系好那不听话的领带,一边对它们以及那东摇西晃的表链说着话,责骂它们。他把双手伸到箱子里去乱翻一气,并且嚷着要一块干净手绢。内心的苛责。天哪,咱们就得打扮得有点特色。我要戴深褐色的手套,穿绿色长统靴。矛盾。我自相矛盾吗?很好,那么我就是要自相矛盾[82]。能言善辩的 [83]玛拉基。正说着的当儿,一个黑色软东西从他手里嗖地飞了出来。
“这是你的拉丁区[84]帽子,”他说。
斯蒂芬把它拾起来戴上了。海恩斯从门道那儿喊他们:
“你们来吗,伙计们?”
“我准备好了,”勃克·穆利根边回答边朝门口走去。“出来吧,金赤,你大概把我们剩的都吃光了吧。”
他认头了,一面迈着庄重的脚步踱了出去,一面几乎是怀着悲痛,严肃地说:
“于是他走出去,遇见了巴特里[85]。”
斯蒂芬把木手杖从它搭着的地方取了来,跟在他们后面走出去。当他们走下梯子时,他就拉上笨重的铁门,上了锁。他将很大的钥匙放在内兜里。
在梯子脚下,勃克·穆利根问道:
“你带上钥匙了吗?”
“我带着哪,”斯蒂芬边说边在他们头里走着。
他继续走着。他听见勃克·穆利根在背后用沉甸甸的浴巾抽打那长得最高的羊齿或草叶。
“趴下,老兄。放老实点儿,老兄。”
海恩斯问道,
“这座塔,你们交房租吗?”
“十二镑,”勃克,穆利根说。
“交给陆军大臣,”斯蒂芬回过头来补充一句。
他们停下步来,海恩斯朝那座塔望了望,最后说:
“啊,冬季可阴冷得够呛。你们管它叫作圆形炮塔吧?”
“这些是比利·皮特[86]叫人盖的,”勃克·穆利根说,“当时法国人在海上[87]。然而我们那座是中心。”
“你对哈姆莱特有何高见?”海恩斯向斯蒂芬问道。
“不,不,”勃克·穆利根烦闷地嚷了起来,“托巴斯·阿奎那[88]也罢,他用来支撑自己那一套的五十五个论点也罢,我都甘拜下风。等我先喝上几杯再说。”
他一边把淡黄色背心的两端拽拽整齐,一边转向斯蒂芬,说:
“金赤,起码得喝上三杯,不然你就应付不了,对吧?”
“既然都等这么久了,”斯蒂芬无精打采地说,“不妨再等一阵子。”
“你挑起了我的好奇心,”海恩斯和蔼可亲地说,“是什么似非而是的怪论吗?”
“瞎扯!”勃克·穆利根说。“我们早就摆脱了王尔德和他那些似非而是的怪论了。这十分简单。他用代数运算出,哈姆莱特的孙子是莎士比亚的祖父,而他本人是他亲爹的亡灵。”
“什么?”海恩斯说着,把指头伸向斯蒂芬。“他本人?”
勃克·穆利根将他的浴巾像祭带[89]般绕在脖子上,纵声笑得前仰后合,跟斯蒂芬咬起耳朵说:“噢,老金赤[90]的阴魂!雅弗在寻找一位父亲哪![91]”
“每天早晨我们总是疲倦的,”斯蒂芬对海恩斯说,“更何况说也说不完呢。”
勃克·穆利根又朝前走了,并举起双手。
“只有神圣的杯中物才能使迪达勒斯打开话匣子,”他说。
“我想要说的是,”当他们跟在后面走的时候,海恩斯向斯蒂芬解释道,“此地的这座塔和这些悬崖不知怎地令我想到艾尔西诺。濒临大海的峻峭的悬崖之巅[92]——对吧?”
勃克·穆利根抽冷子回头瞅了斯蒂芬一眼,然而并没吱声。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沉默的一刹那间,斯蒂芬看到自己身穿廉价丧服,满是尘埃,夹在服装华丽的二人之间的这个形象。
“那是个精采的故事,”海恩斯这么一说,又使他们停下脚步。
他的眼睛淡蓝得像是被风净化了的海水,比海水还要淡蓝,坚毅而谨慎。他这个大海的统治者[93],隔着海湾朝南方凝望,一片空旷,闪闪发光的天边,一艘邮船依稀冒着羽毛形的烟,还有一叶孤帆正在穆格林沙洲那儿抢风掉向航行。
“我在什么地方读过从神学上对这方面的诠释,”他若有所思地说,“圣父与圣子的概念。圣子竭力与圣父合为一体。”
勃克·穆利根的脸上立刻绽满欢快的笑容。他望着他们,高兴地张开那生得很俊的嘴唇,两眼那股精明洞察的神色顿然收敛,带着狂热欢快地眨巴着。他来回晃动着一个玩偶脑袋,巴拿马帽檐颤动着,用安详、欣悦而憨朴的嗓门吟咏起来:
我这小伙子,无比地古怪,
妈是犹太人,爹是只鸟儿[94]。
跟木匠约瑟,我可合不来,
为门徒[95]和各各他[96]干一杯。
他伸出食指表示警告:
倘有人认为,我不是神明,
我造出的酒,他休想白饮。
只好去喝水,但愿是淡的,
可别等那酒重新变成水[97]。
为了表示告别,他敏捷地拽了一下斯蒂芬的木手杖,跑到悬崖边沿,双手在两侧拍动着,像鱼鳍,又像是即将腾空飞去者的两翼,并吟咏道:
再会吧,再会,写下我说的一切,
告诉托姆、狄克和哈利,我已从死里复活[98]。
与生俱来的本事,准能使我腾飞,
橄榄山[99]和风吹——再会吧,再会!
他朝着前方的四十步潭[100]一溜烟儿地蹿下去,呼扇着翅膀般的双手,敏捷地跳跳蹦蹦。墨丘利[101]的帽子迎着清风摆动着,把他那鸟语般婉转而短促的叫声,吹回到他们的耳际。
海恩斯一直谨慎地笑着,他和斯蒂芬并肩而行,说:
“我认为咱们不该笑。他真够亵渎神明的。我本人并不是个信徒,可以这么说。然而他那欢快的腔调多少消除了话里的恶意,你看呢?他管这叫什么来看?《木匠约瑟》?”
“那是《滑稽的耶稣》[102]小调,”斯蒂芬回答说。
“哦,”海恩斯说,“你以前听过吗?”
“每天三遍,饭后,”斯蒂芬干巴巴地说。
“你不是信徒吧?”海恩斯问,“我指的是狭义上的信徒,相信从虚无中创造万物啦,神迹和人格神[103]啦。”
“依我看,信仰一词只有一种解释,”斯蒂芬说。
海恩斯停下脚步,掏出一只光滑的银质烟盒,上面闪烁着一颗绿宝石。他用拇指把它按开,递了过去。
“谢谢,”斯蒂芬说着,拿了一支香烟。
海恩斯自己也取了一文,啪的一声又把盒子关上,放回侧兜里,并从背心兜里掏出一只镍制打火匣,也把它按开,自己先点着了烟,随即双手像两扇贝壳似的拢着燃起的火绒,伸向斯蒂芬。
“是啊,当然喽,”他们重新向前走着,他说。“要么信,要么不信,你说对不?就我个人来说,我就容忍不了人格神这种概念。你也不赞成,对吧?”
“你在我身上看到的,”斯蒂芬闷闷不乐地说,“是一个可怕的自由思想的典型。”
他继续走着,等待对方开口,身边拖着那棍棒木手杖。手杖上的金属包头沿着小径轻快地跟随着他,在他的脚后跟吱吱作响。我的好搭档跟着我,叫着斯蒂依依依依依芬。一条波状道道,沿着小径。今晚他们摸着黑儿来到这里,就会踏看它了。他想要这把钥匙。那是我的。房租是我交的。而今我吃着他那苦涩的面包 [104]。把钥匙也给他拉倒。一古脑儿。他会向我讨的。从他的眼神里也看得出来。
“总之,”海恩斯开口说……
斯蒂芬回过头去,只见那冷冷地打量着他的眼色并非完全缺乏善意。
“总之,我认为你是能够在思想上挣脱羁绊的。依我看,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我是两个主人的奴仆,”斯蒂芬说,“一个英国人,一个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海恩斯说。
一个疯狂的女王[l05],年迈而且爱妒忌:给朕下跪。
“还有第三个[106],”斯蒂芬说,“他要我给他打杂。”
“意大利人?”海恩斯又说,“你是什么意思?”
“大英帝国,”斯蒂芬回答说,他的脸涨红了,“还有神圣罗马使徒公教会[107]。”
海恩斯把沾在下唇上的一些烟叶屑抹掉后才说话。
“我很能理解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认为一个爱尔兰人一定会这么想的。我们英国人觉得我们对待你们不怎么公平。看来这要怪历史[108]。”
堂堂皇皇而威风凛凛的称号勾起了斯蒂芬对其铜钟那胜利的铿锵声的记忆,信奉独一至圣使徒公教会,礼拜仪式与教义像他本人那稀有着的思想一般缓慢地发展并起着变化,命星的神秘变化。《马尔塞鲁斯教皇[109]弥撒曲》[110]中的使徒象征[111],大家的歌声汇在一起,嘹亮地唱着坚信之歌;在他们的颂歌后面,富于战斗性的教会那位时刻警惕着的使者[112]缴了异教祖师的械,并加以威胁。异教徒们成群结队地逃窜,主教冠歪歪斜斜;他们是佛提乌 [112]以及包括穆利根在内的一群嘲弄者;还有为了证实圣子与圣父并非一体而毕生展开漫长斗争的阿里乌[114],以及否认基督具有凡人肉身的瓦伦廷 [115];再有就是深奥莫测的非洲异教始祖撒伯里乌[116],他主张圣父本人就是他自己的圣子。刚才穆利根就曾用此活来嘲弄这位陌生人[117]。无谓的嘲弄。一切织风者最终必落得一场空[118]。他们受到威胁,被缴械,被击败;在冲突中,来自教会的那些摆好阵势的使者们,米迦勒的万军,用长矛和盾牌永远保卫教会。
听哪,听哪。经久不息的喝采。该死!以天主的名义![119]
“当然喽,我是个英国人,”海恩斯的嗓音说,“因此我在感觉上是个英国人。我也不愿意看到自已的国家落入德国犹太人的手里[120]。我认为当前,这恐怕是我们民族的问题。”
有两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眺望着,一个是商人,另一个是船老大。
“她正向阉牛港[121]开呢。”
船老大略带轻蔑神情朝海湾北部点了点头。
“那一带有五[]深,”他说,“一点钟左右涨潮,它就会朝那边浮去了。今儿个已经是第九天[122]啦。”
淹死的人。一只帆船在空荡荡的海湾里顺风改变着航向,等待一团泡肿的玩艺儿突然浮上来,一张肿胀的脸,盐白色的,翻转向太阳。我在这儿哪。
他们沿着弯曲的小道下到了湾汊。勃克·穆利根站在石头上,他穿了件衬衫,没有别夹子的领带在肩上飘动。一个年轻人抓住他附近一块岩石的尖角,在颜色深得像果冻般的水里,宛若青蛙似地缓缓踹动着两条绿腿。
“弟弟跟你在一起吗,玛拉基?”
“他在韦斯特米思。跟班农[123]一家人在一起。”
“还在那儿吗?班农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在那儿遇见了一个可爱的小姐儿。他管她叫照相姑娘[124]。”
“是快照吧,呃?一拍就成。”
勃克·穆利根坐下来解他那高腰靴子的带子。离岩角不远处,抽冷子冒出一张上岁数的人那涨得通红的脸,喷着水。他攀住石头爬上来。水在他的脑袋以及花环般的一圈灰发[125]上闪烁着,沿着他的胸脯和肚子流淌下来,从他那松垂着的黑色缠腰市里往外冒。
勃克·穆利根闪过身子,让他爬过去,瞥了海恩斯和斯蒂芬一眼,用大拇指甲虔诚地在额头、嘴唇和胸骨上面了十字[126]。
“西摩回城里来啦,”年轻人重新抓住岩角说,“他想弃医从军呢。”
“啊,随他去吧!”勃克·穆利根说。
“下周就该受熬煎了。你认识卡莱尔家那个红毛丫头莉莉吗?”
“认得。”
“昨天晚上跟他在码头上调情来看。她爸爸阔得流油。”
“她够劲儿吗?”
“这,你最好去问西摩。”
“西摩,一个嗜血的军官,”勃克·穆利根说。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脱下长裤站起来,说了句老生常谈:
“红毛女人浪起来赛过山羊。”
他惊愕地住了口,并摸了摸随风呼扇着的衬衫里面的肋部。
“我的第十二根肋骨没有啦,”他大声说。“我是超人[127]。没有牙齿的金赤和我都是超人。”
他扭着身子脱下衬衫,把它甩在背后他堆衣服的地方。
“玛拉基,你在这儿下来吗?”
“嗯。在床上让开点儿地方吧。”
年轻人在水里猛地向后退去,伸长胳膊利利索索地划了两下,就游到湾汊中部。海恩斯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着烟。
“你不下水吗?”勃克·穆利根问道。
“呆会儿再说,”海恩斯说,“刚吃完早饭可不行。”
斯蒂芬掉过身去。
“穆利根,我要走啦,”他说。
“金赤,给咱那把钥匙,”勃克·穆利根说,“好把我的内衣压压平。”
斯蒂芬递给了他钥匙。勃克·穆利根将它撂在自己那堆衣服上。
“还要两便士,”他说,“好喝上一品脱。就丢在那儿吧。”
斯蒂芬又在那软塌塌的堆儿上丢下两个便士。不是穿,就是脱。勃克·穆利根直直地站着,将双手在胸前握在一起,庄严地说:
“琐罗亚斯德如是说[128]:‘偷自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129]”
他那肥胖的身躯跳进水去。
“回头见,”海恩斯回头望着攀登小径的斯蒂芬说,爱尔兰人的粗扩使他露出笑容。
公牛的角,马的蹄子,撒克逊人的微笑[130]。
“在‘船记’酒馆,”勃克·穆利根嚷道。“十二点半。”
“好吧,”斯蒂芬说。
他沿着那婉蜒的坡道走去。
饰以百合的光明的
司铎群来伴尔,
极乐圣童贞之群……[131]
壁龛里是神父的一圈灰色光晕,他正在那儿细心地穿上衣服[132]。今晚我不在这儿过夜。家也归不得。
拖得长长的、甜甜的声音从海上呼唤着他。拐弯的时候,他摆了摆手,又呼唤了。一个柔滑、褐色的头,海豹的,远远地在水面上,滚圆的。
篡夺者[133]。
第一章 注释
[l]据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穆利根的原型系爱尔兰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参加者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1878一1957)。
[2]这里,穆利根在模仿天主教神父举行弥撤时的动作。他手里托着的那钵肥皂沫,就权当圣餐杯。镜子和剃胡刀交叉放着,呈十字架形。淡黄色浴衣令人联想到神父做弥撒时罩在外面的金色祭披。下文中的“我要……台“,原文是拉丁文。
[3]金赤是穆利根给斯蒂芬?迪达勒斯起的外号。他把斯蒂芬比作利刃,用金赤来模仿其切割声。
[4]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一五三四年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所创。会规严格,要求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会长。
[5]指坐落在都柏林郊外的港口区沙湾(音译为桑迪科沃)的圆形炮塔。这是一八0三至一八0六年间为了防备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入侵,而在爱尔兰沿岸修筑的碉堡的一座。其造型仿效法属科西嘉岛的马铁洛岬角上的海防炮塔,故名马铁洛塔。
[6]某些修会的天主教神父将头顶剃光,周围只留一圈头发。参看本章注[125]。穆利根只是装出一副神父的样子,故未剃发。
[7]这里原应作“圣餐”(Eucharist),作者却写成了女子名克里斯廷(Christine)。二词中均含有基督(Christ)一名。其用意是便它同第十五章末尾玛拉基?奥弗林神父在卧于圣女芭巴拉的祭台上的那个女人身上做黑弥撒的场面相呼应。参看该章注[956]及有关正文。耶稣和门徒(据《新约?马太福音》第l0章第l节,耶稣收了彼得、约翰等十二个门徒)吃筵席时,曾把饼和酒祝福后递给他们,说那是自己的身体和血(见《新约?路加福音》第22章第19-20节)。后世举行弥撒时,神父饮的葡萄酒即代表耶稣的血,教徒领的圣体(面饼)则代表耶稣的躯体。“血和伤痕”是中世纪的一句诅咒“天主的血和伤痕”的简称。
[8]克里索斯托[约347一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名叫约翰。三九八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后,锐意进行改革。但操之过急,开罪于豪富权门,曾被禁闭。死后得以昭雪,被封为圣约翰。他善于传教讲经,长于词令,因而通称“金口约翰”。
[9]据《新约?使徒行传》第6、7章,最早的殉教者斯蒂芬(?一约35)是个受过希腊文教育的犹太人。迪达勒斯(Dedalus)一姓来自神话传说中的希腊建筑师和雕刻家Daedalus。有史时期的希腊人把无法溯源的建筑和雕像都算作是出自迪达勒斯之手。
[10]指他的教名Buck,意译为公鹿。勃克?玛拉基?穆利根是全名。勃克是教名(即洗礼名或第一个名字)。玛拉基是纪念其父亲或家属中其他人的名字。穆利根是姓。通常只称作勃克?穆利根,中间的名字就省略了。
[11]原文作bad,原意吟游诗人。因含有挖苦口吻,故译为大诗人,并加上引号,以示区别。下同。
[l2]阿尔杰是阿尔杰农的爱称。这里指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查理?阿尔杰农?斯温伯恩(1837-1909)。“伟大可爱的母亲”一语出自他的长诗《时间的胜利》1866)。“伟大”是根据海德版翻译的,诸本均作“灰色”。
[l3]原文为希腊文。荷马的《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饭苇23页)有“强劲的西风歌啸着,吹过葡萄素的大海”一语。
[14]原文为希腊文。语出自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公元前431一前35O以前)的《远征记》。写作者跟随与胞兄波斯王争夺王位的小居鲁士远征。失败后,他率领万名希腊雇佣军且战且退,公元前四00年回到黑海之滨的希腊城市特拉佩祖斯。这是他们见到海时发出的吹呼。
[15]国王镇(丹莱里的旧称)是都柏林的一个海港区。有东西两个大码头伸入海中,构成一道人造港湾。
[16]语出自拉塞尔(参看第三章注[109]的《宗教与爱情》)。他在这篇散文中阐明“强有力的母亲”指的是“大自然的精神面貌”。穆利根紧接着所说的“姑妈……你手里”一语,当天上午在海边(见第三章注[943]以及当夜(见第十五章注[688])重新浮现在斯蒂芬的脑际。
[17]原文作“dog’sbody”。在凯尔特族(参看第二章注[48])的神话中,狗含有“严加保密”意,所以穆利根用此词来称呼..性格内向的斯蒂芬。
[18]“船记”是斯蒂芬等人经常去的酒馆的店名。
[19]康内利?诺曼(1858-1908),爱尔兰精神病学家。痴呆镇指里奇蒙精神病院,自一八八六年起诺曼在那里任院长。
[20]此处套用《天主经》中“不叫我们受到诱惑”一语,但将“我们”改成了“他”。见《路加福音》第11章第4节。
[21]女仆与四世纪的圣女乌尔苏拉同名。据传匈奴人入侵东南欧洲时,科隆(今穗国境内)有一万一千名童贞女殉教。乌水苏拉是她们的领袖。
[22]凯列班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1611)中一个丑陋而野性的奴隶。语出自爱尔兰诗人、小说家奥斯卡?王水德(1854一1900)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1891)的序言。在该文中,王尔德表达了自己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原话是:“十九世纪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是凯列班在镜中照得见自己的脸时所感到的愤怒。十九世纪人们对浪漫主义的厌恶,是凯列班在镜中照不见自己的脸时所感到的愤怒。”这里,穆利根把斯蒂芬比作凯列班。
[23]语出自王尔德的论文集《意图》中的《谎言的衰退》(1889)。全句是:“我完全明白你反对把艺术当作一面镜子。你认为,这样一来就把天才降低到有裂纹的镜子的境地了。然而,你无意说,人生是艺术的模仿。人生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艺术才是真实的,对吧?”
[24]牛津家伙指正在搜集爱尔兰格言的海恩斯。
[25]基尼是旧时英国金币,一基尼合二十一先令。
[26]药喇叭,又名球根牵牛;根部可以用来制做泻药。
[27]祖鲁人是非洲东南部班图族的一支土著。
[28]这里的希腊化指的是使爱尔兰开化。都柏林市不同于近代化的大都会,有着当年希腊城邦的性质。正如奥德修由于离乡多年,初回伊大嘉时未认出那是什么地方一样,斯蒂芬回到故里后也觉得格格不入。因此他听了穆利根所说的使爱尔兰“希腊化”的话,并不曾引起共鸣。
[29]在乔伊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5章里,克兰利(参看第九章注[13])曾和斯蒂芬挽臂而行。克兰利参加了爱尔兰独立运动。斯蒂芬则说:“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艺术形式中……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见黄雨石译本第297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0]西摩是英国牛津大学麦达伦学院的学生。
[3l]“要委婉……息”出自美国人查理?哈里斯所作通俗歌曲《向母亲透露这消息》(1897)。写一个战士临终前嘱咐道,向母亲透露自己阵亡的消息时,要说得委婉一些。奥布里是斯蒂芬迁居到都柏林之前,住在布莱克罗克镇时的一个游伴,见《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2章。
[32]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学生们当中时兴的一种捉弄同学的办法:把对方的裤子剥下来,用剪子将衬衫铰成一条条的。
[33]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
[34]“我们自己”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展的复兴爱尔兰语言文化的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意思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中心”,原文为希腊文。马修?阿诺德提出的文化理想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古稀腊人文主义与建立在社会伦理上的希伯来主义的统一。斯蒂芬从阿诺德的这一理想联想到要求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自救口号。他又进一步想到把异教与基督教相调和而成的新异教教义。最后才联想到omphalos一词。此词的意思是中心,指位于雅典西北一百英里处的帕耳那索斯山麓峡谷里的一块圣石,转义为人体的中心部位:肚脐。这里隐啥斯蒂芬等人所住的这座圆塔,乃是爱尔兰艺术的发祥地。
[35]布莱岬角位于沙湾以南七英里处。
[36]这里,穆利根借用了英国哲学家戴维?哈特利(1705一1757)的观点。哈特利的主要著作有《对人及其结构、职责和期望的观察》(两卷本,1749)等。他认为,真正存在于记忆中的只有观念和感觉。
[37]圣母是仁慈圣母玛利亚医院的简称。这是由天主教仁慈会修女所开办的都柏林市最大的一家医院。里奇蒙是里奇蒙精神病院的简称。
[38]彼得?蒂亚泽爵士是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戏剧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1751-1816)所作喜剧《造谣学校》(1777)中的一个人物。这位爵士晚年与一个年轻活泼的农村姑娘结了婚。
[39]指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
[40]撒克逊征服者,原文为爱尔兰语。
[41]这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一1939)所作《谁与弗格斯同去》一诗的第7至9行。弗格斯是据传于五世纪从爱尔兰移去的第一位苏格兰国王。下文中的“树林的阴影”和“朦胧的海洋那雪白的胸脯”,出自该诗的第10、l1行。
[42]老罗伊斯指英国喜剧演员爱德华?威廉?罗伊斯(1841一?)。《可怕的土耳克》(1873)是爱尔兰作家埃德温?汉密尔顿(1849一1919)根据英国童话剧《神奇的玫瑰》(1868)改编的。土耳克王由老罗伊斯扮演。当他发现神奇的玫瑰能教会他隐身术时,便高兴地唱起下面这首歌。
[43]英国通神论者艾尔弗雷德?珀西?辛尼特(1840-1921)在《灵魂的成长》(1896)一书中提出,一切事件和思根都贮存在宇宙的记忆中。参看第七章注[224]。
[44]天主教徒领圣体前,自午夜起禁止饮食。
[45]原文为拉丁文。这是信徒弥留之际助善终者在一旁为他(她)念的临终祷文中的两句。斯蒂芬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她死前,斯蒂芬却不曾满足她的愿望,拒绝为她祷告。
[46]这是斯蒂芬责备自己的话。他意识到在母亲生前,他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怀疑和不满曾使母亲深深苦恼,故以东方神话中的食尸鬼自喻。
[47]这是英国旧时的一种金币,每枚值一英镑。因上面镌有国王(或女王)像,所以俗称“君主”。
[48]德鲁伊特是古代凯尔特人中有学识者,通常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德鲁伊特的家庭里,竟连圣诞节的蛋糕都禁止吃。
[49]出自庆祝爱德华七世加冕(1901年1月22日)的歌曲《加冕日》。“加冕日”又指发薪日,因为工资可折合成克朗。(意即王冠)是旧时的一种镌有王冠图案的硬币,每枚值五先令。
[50]即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书中,斯蒂芬曾就读于这家小学。下文中的“提过香炉”指神父做弥撒时,斯蒂芬曾担任助祭。
[51]据《旧约?创世记》第7至9章,挪亚一家人乘方舟逃避水灾后,一天挪亚喝醉了酒睡在帐棚里。二儿子含看见父亲赤身露体,便出去告诉了哥哥闪和弟弟雅弗。闪和雅弗替父亲盖上长袍。挪亚洒醒后说:“迦南[含的儿子]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52]这是《饭前祝文》,引自《圣教日课》。
[53]原文为拉丁文。这是《圣号经》的下半段,引自《圣教日课》。
[54]葛罗甘老婆婆是爱尔兰歌曲《内德?葛罗甘》中的人物。
[55]登德鲁姆有两个。(一)位于都柏林市以北六十五英里的港口。(二)都柏林近郊的村。
[56]人鱼神是古代腓力斯人和腓尼基人所信奉的半人半鱼的神。
[57]命运女神姐妹原指《麦克白》中的三女巫,这里则影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姐妹伊丽莎白和莉莉。一九0三年,伊丽莎白在登德鲁姆村创立了邓恩?埃默出版社,并为叶芝出版《在七座树林中》一书。该书的版权页上写着,完成于“大风年七月十六日,一九0 三”。按一八三九年爱尔兰曾遭受一场空前的大风灾。从此,“大风年”一词便流行开来。
[58]《马比诺吉昂》是中世纪十一则威尔士故事的总称,以神话、民间故事和英雄传说为基础,记载十二世纪下半叶至十三世纪末的口传故事。
[59]《奥义书》是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用散文或韵文写成。自公元前六百年起次第成书,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所依据。
[60]玛丽?安是一八四三年左右为了吓唬苛吏而在爱尔兰民间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成员以妇女为主,也有乔装成妇女的男子。因此,后来又用此词来影射同性恋者。关于玛丽?安,流传着一些歌曲,而梅布尔?沃辛顿找到的那个版本的末句是:“像男人那样撒尿。”与下文中穆利根所唱的三句歌词刚好凑成一段。
[61]包皮的搜集者,指耶和华。犹太教徒有行割礼(割除阴茎包皮)的传统。参看《创世记》第17章第10至14节。
[62]夸脱是液量单位,一夸脱为一?一四升。
[63]毛皮像绢丝般的牛、最漂亮的牛和贫穷的老妪均为爱尔兰古称。
[64]征服者指英国人,这里,以海恩斯为代表。快乐的叛徒指满足于现状的爱尔兰人,这里,以勃克?穆利根为代表。
[65]母王八,原文为cuckquean,指其丈夫姘上了其他女人。
[66]在《奥德修纪》卷一中,女神雅典娜替奥德修说情,于是,主神宙斯表示同意让奥德修回国。女神便扮成外乡人的模样,到伊大嘉岛来鼓励奥德修的儿子帖雷马科。这里斯蒂芬把送牛奶的老妪比作雅典娜女神,他怀疑她是为了谴责自己不曾满足母亲最后的愿望而来的。
[67]下文中,海德版多一行,[“瞧,真是的,”她说。]其他诸本部没有。
[68]那个嗓门指神父。天主教徒临终前,神父在他(她)身上涂清香油,以便减轻肉体上的痛苦,并给心灵以慰藉。这叫作终傅礼。但据《旧约?利未记》第12章,天主曾通过摩西说,妇女分娩后以及月经期间不洁,因此不在阴部周围涂油。
[69]见《创世记》第2章第22至23节:“耶和华神就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那人说:‘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
[70]同上,第1章第27节有“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一语。
[71]同上,第3章: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禁果,并给她丈夫亚当吃。作为惩罚,耶和华将二人逐出伊甸园。
[72]盖尔语是苏格兰高地人和古代爱尔兰盖尔族的语言。“你有盖尔族的气质吗?”是爱尔兰西部农民的口头用语,意思是:“你会讲爱尔兰话吗?”十九世纪初叶,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人们重新对爱尔兰的语言、文学、历史和民间传说发生兴趣。当时,除了在偏僻的农付,盖尔语作为一种口语已经衰亡,英语成为爱尔兰的官方和民间通用语言。后来语言学家找到了翻译古代盖尔语手稿的方法,人们这才得以阅读爱尔兰的古籍。
[73]西边儿指爱尔兰西部的偏僻农村。那里的人们依然说爱尔兰语。
[74]品脱是液量名,一品脱合0?五七升弱。
[75]先令是英国当时通用的货币单位。二十先令为一英镑,一先令为十二便士。英币改为十进制后,合十便士。
[76]佛罗林是十三世纪时意大利开始铸造的一种银币。一八四九年以来在英国通用,一佛罗林合两先令。
[77]这是斯温伯恩的长诗《日出前的歌》(1871)“贡献”一节中的第1、2行。下文中的“心肝儿……你的脚前”见同一节的第3、4行。
[78]这里套用一八0五年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1758一1805)在特拉法尔加角与法、西军舰进行殊死战时对英国海军的训话。 只是把原话“英国期待每人今天各尽自己的职责”中的“英国”改成了“爱尔兰”。
[79]即墨西哥清流。它流向东北,在加拿大纽芬兰岸外与北大西洋漂流汇合,继续朝东北流向不列颠群岛以及北海和挪威海。
[80]语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5章第1场。麦克白夫人怂恿丈夫把苏格兰国王邓肯杀死后,在梦游中不断地擦手,并且说:“可是这儿还有一点污迹。”
[81]天主教为了纪念耶稣受难,在教堂里设十四座十字架,教徒沿着一座座十字架,边念经边朝拜。“被恶人强剥下衣服”是在第十座十字架前念的经文中的一句。这里,不信教的穆利根戏谑地以耶稣自况。
[82]“我自……矛盾”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的长诗《自己之歌》(1855)第51首第6、7行诗句。
[83]“能言善辩的”,也可以译为“墨丘利般的”,参看本章注[101]。
[84]拉丁区是巴黎塞纳河南岸的地区。有不少大学及文化设施,历来是学生和艺术家麇集之地。
[85]按当时都柏林郊区有两个叫作莫里斯?巴特里的农民。《路加福音》第22章第26节作:“于是彼得出去痛哭。”这是文字游戏,“metButterly”(遇见了巴特里)与“weptbitterly”(痛哭)谐音。
[86]比利是威廉的昵称。威廉?皮特(1759一1806),英国首相。
[87]“法国人在海上”一语出自《贫穷的老妪》。这首十八世纪末叶的爱尔兰歌谣表达了“贫穷的老妪”(爱尔兰古称)对越海而来的法国支援者的期待心情。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法国人曾两次派出远征军支援爱尔兰革命,均未能到达。一七九八年法国人虽登了陆,却被迫投降。下文中的“中心”,原文为希腊文。
[88]托马斯?阿奎那(1225一1274),意大利神学家、诗人。他区分了自然领域与超自然领域之后,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教父的思想加以综合,发展成为一套复杂而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
[89]祭带是神父做弥撒时所挂的细长带子,从脖颈垂到胸前。
[90]老金赤指斯蒂芬的父亲。
[91]指英国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1792一1848)所写的一部以寻父为主题的小说(1836)。弃儿雅弗千方百计找到的生父,却原来是东印度群岛上的一名脾气暴躁的军官。据《创世记》,挪亚喝醉后,他的儿子闪和雅弗曾去找他,见本章注[51]。斯蒂芬的父亲也是个酒鬼。这里,穆利根把斯蒂芬比作雅弗。
[92]艾尔西诺是丹麦的谢兰岛上一军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即以此港为背景。“濒临……之颠”一语引自《哈姆莱特》第1幕第4场中霍拉旭对哈姆莱特所说的话。
[93]“大海的统治者”指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国海军和商船在海上称霸。
[94]据(路加福音)第1章,犹太童贞女玛利亚已许配给木匠约瑟,但未成婚前,因圣灵降临到她身上而怀孕,遂生下耶稣。圣灵通常以鸽子的形象出现,故有“鸟儿”一说。《马可福音》第1章第l0节有云:“圣灵仿佛鸽子,降在她身上。”
[95]指耶稣的十二门徒。
[96]各各他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97]据《约翰福音》第2 章,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迦拿应邀赴婚筵时,酒用尽了。那儿摆着六口缸。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漫到缸口。舀出来一尝,水已变成了酒。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首打油诗的最后一句指喝下去的酒变成了尿。
[98]语出《路加福音》第24章第46节:“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99]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以东,耶稣经常偕同门徒到此。
[100]四十步潭是沙湾的一座专供男子洗澡的天然浴场。
[lO1]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信使,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穆利根与《旧约全书》末卷《玛拉基书》里的先知玛拉基(活动时期公元前约460)同名。该名是希伯来语“我的使者”的音译,所以这里把他与墨丘利相比。
[102]勃克?穆利根所唱的《滑稽的耶稣》是根据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所作的讽刺诗《快活的耶稣之歌》改编的。
[lO3]人格神是指神也具有人格,而神子耶稣基督乃是人格的楷模。
[104]典出自《神曲?天堂》第17篇。但丁的高祖卡却基达对他说:“你将懂得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苦涩,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难以攀上攀下。”
[lO5]指维多利亚女王(1819一1901),她统治英国达六十四年之久(1837一1901)。
[106]第三个,指穆利根。
[107]指罗马天主教会。
[108]后文中,斯蒂芬借用了海恩斯这句话(见第十五章注[860]及有关正文)。下段中的“独一至圣使徒公教会”,原文为拉丁文。
[109]即马尔塞鲁斯二世(1501一1555),意大利籍教皇,原名塞维尼。即位后仅二十二天即逝世。
[l10]《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系意大利作曲家乔瓦尼?皮耶路易吉?帕莱斯特里纳(1525一1594)所作。这支弥撒曲曾于一八九八年在都柏林的圣女德肋撒教堂被人重新演奏。
[111]指《使徒信经》。传统上,《信经》中的十二个信条分别由十二名使徒来象征,故名。如“我信全能者,天主父,化成天地。”(彼得) “我信其唯一子,耶稣基利斯督我等主。”(约翰)
[112]“教会的使者。指天使长米迦勒。
[113]佛提乌(816一891),原系在俗学者,由拜占廷皇帝米恰尔三世任命为拜占廷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受到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的反对。在君士坦丁堡会议(867年)上,佛提乌谴责尼古拉,从而形成对立,史称佛提乌分裂局面。
[114]阿里乌(约250-336),利比亚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司铎。尼西亚公会议(325年)公布《尼西亚信经》,指明基督(圣子)与天主(圣父)同样具有神性。阿里乌拒绝签名。他倡导阿里乌主义,认为基督是被造的(made, 指系天主所造,因而不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不是受生的(begotten,指由天主所生,因而具有完全的神性)。这种理论被早期教会宣布为异端。
[115]瓦伦廷是公元二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出生于埃及, 为诺斯替教罗马派和广大利派的创始人。公元一四0年前后曾谋求罗马主教之职位而失败, 遂脱离基督教。瓦伦廷的早期理论与保罗的神秘神学相似,强调基督死后复活,信徒因而得救。
[116]撒伯里乌(?一270),可能曾任罗马教会长老。他反对天主教会关于三位一体(谓天主本体为一,但又是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的教义,而主张天主是单一的,而有三种功能,圣父创造天地,圣子救赎罪人,圣灵使人成圣。因此,被斥为异端邪说。
[117]陌生人是爱尔兰人对英国人(侵略者与霸主)的称呼。
[118]这里套用英国诗人约翰?韦伯斯特(约1580一约1625)的《魔鬼的诉讼》(1623)的词句:“国王野心一场空……织网只为了捕风。”
[119]原文为法语。这是斯蒂芬从冥想中醒过来后暗自说的话。
[120]指德裔犹太富豪罗斯蔡尔德家族。当时他们控制着英国经济。
[121]她指船。阉牛港位于都柏林湾东南方的岬角。下文中的噚是测量水深用的长度单位,一噚合一·八九八米。
[122]它指溺尸。民间迷信:失去踪影的沉尸会在第九天浮上来。
[128]韦斯特米思位于都柏林市以西四十英里处,是爱尔兰伦斯特省一郡。亚历克·班农是个学生,参看第四章中米莉来信和第十四章注[146]及有关正文。
[124]指本书另一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的女儿米莉。她在韦斯特米思郡穆林加尔市的照相馆工作。该市距都柏林五十英里。
[125]这个泅水者的头顶剃光了,只留下一圏灰发,说明他是个天主教神父。直到一九七二年,这一习俗才由教皇保罗六世下令废除。
[126]这是基督教会自古流行的一种对天主三位一体(圣父=额头,圣子=嘴唇,圣神=胸部)表示尊崇的手势。天主教神父举行弥撒时,在诵读经文前以及仪式结束后,照例要划十字。
[127]原文为德语。《创世记》第2章第21节有天主抽掉亚当一根肋骨的记载。这里,穆利根以亚当自况,说他的“第十二根肋骨没有了”,这样,他就成了“超人”。
[128]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628一约前551),穆斯林先知、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古波斯语作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斯德如是说》(1883-1885)是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一1900)的一部谶语式的格言著作。他在其中借琐罗亚斯德来鼓吹自己的“超人”哲学(即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有权奴役群众,而普通人只是“超人”实现自己权力意志的工具)。
[l29]这里,勃克·穆利根故意篡改了《箴言》第19章第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一语,借以挖苦说,尼采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以别人为踏脚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本世纪初,西欧曾流行过这种论点。
[130]意思是说,这三者都是危险的,不能掉以轻心。
[l31]原文是拉丁文。
[132]本章以勃克·穆利根假装举行弥撒为开端[见本章注[2]],结尾处又把一位真正的神父出浴后在湾汊的岩洞中穿衣服比作弥撒结束后神父在更衣,并将神父那圈灰发描述成圣徒头后的光晕。壁龛指岩洞。
[133]篡夺者指从斯蒂芬手里讨走钥匙的勃克·穆利根。在《奥德修纪》卷1、2中,帕雷马科也曾指责那些求婚子弟们掠夺他的家财;哈姆莱特王子则对霍拉旭说,叔叔克劳狄斯“篡夺了我嗣位的权利”,参看《哈姆莱特》第5幕第2场。
第二章
“你说说,科克伦,是哪个城市请他[1]的?”
“塔兰图姆[2],老师。”
“好极了。后来呢?”
“打了一仗,老师。”
“好极了。在哪儿?”
孩子那张茫然的脸向那扇茫然的窗户去讨教。
记忆的女儿们[3]所编的寓言。然而,即便同记忆所编的寓言有出入,总有些相仿佛吧。那么,就是一句出自焦躁心情的话,是布莱克那过分之翅膀的扑扇 [4]。我听到整个空间的毁灭,玻璃碎成碴儿,砖石建筑坍塌下来,时光化为终极的一缕死灰色火焰[5]。那样,还留给我们什么呢?
“地点我忘记啦,老师。公元前三七九年。”
“阿斯库拉姆[6],”斯蒂芬朝着沾满血迹的书上那地名和年代望了一眼,说。
“是的,老师。他又说,再打赢这么一场仗,我们就完啦[7]。”
世人记住了此语。心情处于麻木而松驰的状态。尸骸累累的平原,一位将军站在小山岗上,拄着矛枪,正对他的部下训话。任何将军对任何部下。他们洗耳恭听。
“你,阿姆斯特朗,”斯蒂芬说。“皮勒斯的结尾怎么样?”
“皮勒斯的结尾吗,老师?”
“我晓得,老师。问我吧,老师,”科敏说。
“等一等。阿姆斯特朗,你说说,关于皮勒斯,你知道点什么吗?”
阿姆斯特朗的书包里悄悄地摆着一袋无花果夹心面包卷。他不时她用双掌把它搓成小卷儿,轻轻地咽下去。面包渣子还沾在他的嘴唇上呢。少年的呼吸发出一股甜味儿。这些阔人以长子进了海军而自豪。多基[8]的韦克街。
“皮勒斯吗,老师?皮勒斯是栈桥[9]。”
大家都笑了。并不快活的尖声嗤笑。阿姆斯特朗四下里打量着同学们,露出傻笑的侧影。过一会儿,他们将发觉我管教无方,也想到他们的爸爸所缴的学费,会越发放开嗓门大笑起来。
“现在告诉我,”斯蒂芬用书戳戳少年的肩头,“栈桥是什么?”
“栈桥,老师,”阿姆斯特朗说,“就是伸到海里的东西。一种桥梁。国王镇[10]桥,老师。”
有些人又笑了,不畅快,却别有用意。坐在后排凳子上的两个在小声讲着什么。是的。他们晓得,从未学习过,可一向也不是无知的。全都是这样。他怀着妒意注视着一张张的脸。伊迪丝、艾塞尔、格蒂、莉莉[11]。跟他们类似的人,她们的呼吸也给红茶、果酱弄得甜丝丝的,扭动时,她们腕上的镯子在窃笑着。
“国王镇码头,”斯蒂芬说,“是啊,一座失望之桥[12]。”
这句话使他们凝视着的眼神露出一片迷茫。
“老师,怎么会呢?”科敏问。“桥是架在河上的啊。”
可以收入海恩斯的小册子[13]。这里却没有一个人听。今晚在豪饮和畅叙中,如簧的巧舌将刺穿罩在他思想外面的那副锃亮的铠甲。然后呢?左不过是主人宫廷里的一名弄臣,既被纵容又受到轻视,博得宽厚的主人一声赞许而已。他们为什么都选择了这一角色呢?图的并不完全是温存的爱抚。对他们来说,历史也像其他任何一个听腻了的故事,他们的国土是一爿当铺[14]。
倘若皮勒斯并未在阿尔戈斯丧命于一个老太婆手下[15],或是尤利乌斯·恺撒不曾被短剑刺死[16]呢?这些事不是想抹煞就能抹煞的。岁月已给它们打上了烙印,把它们束缚住,关在被它们排挤出去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里[17]。但是,那些可能性既然从未实现,难道还说得上什么可能吗?抑或惟有发生了的才是可能的呢?织吧,织风者[18]。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老师。”
“请讲吧,老师。讲个鬼故事。”
“这从哪儿开始?”期蒂芬打开另一本书,问道。
“莫再哭泣,”科敏说。
“那么,接着背下去,塔尔博特。”
“故事呢,老师?”
“呆会儿,”斯蒂芬说。“背下去,塔尔博特。”
一个面色黧黑的少年打开书本,麻利地将它支在书包这座胸墙底下。他不时地瞥着课文,结结巴巴地背诵着诗句:
莫再哭泣,悲痛的牧羊人,莫再哭泣,
你们哀悼的利西达斯不曾死去,
虽然他已沉入水面下……[19]
说来那肯定是一种运动了,可能性由于有可能而变为现实[20]。在急促而咬字不清的朗诵声中,亚理斯多德的名言自行出现了,飘进圣热内维艾芙图书馆那勤学幽静的气氛中;他曾一夜一夜地隐退在此研读[21],从而躲开了巴黎的罪恶。邻座上,一位纤弱的暹罗人正在那里展卷精读一部兵法手册。我周围的那些头脑已经塞满了,还在继续填塞着。头顶上是小铁栅围起的一盏盏白炽灯,有着微微颤动的触须。在我头脑的幽暗处,却是阴间的一个懒货,畏首畏尾,惧怕光明,蠕动着那像龙鳞般的裙皱[22]。思维乃是有关思维的思维[23]。静穆的光明。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灵魂是全部存在,灵魂乃是形态的形态[24]。突兀、浩翰、炽烈的静穆:形态的形态。
塔尔博特反复背诵着同一诗句:
借着在海浪上行走的主那亲切法力[25],
借着在海浪上……
“翻过去吧。”斯蒂芬沉静地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您说什么,老师?”塔尔博特向前探探身子,天真地问道。
他用手翻了一页。他这才想起来,于是,挺直了身子背诵下去。关于在海浪上行走的主。他的影子也投射在这些怯懦的心灵上,在嘲笑者的心坎和嘴唇上,也在我的心坎和嘴唇上。还投射在拿一枚上税的银币给他看的那些人殷切的面容上。属于恺撒的归给恺撒,属于天主的归给天主[26]。深色的眼睛长久地凝视着,一个谜语般的句子,在教会的织布机上不停地织了下去。就是这样。
让我猜,让我猜,嗨哟嗬。
我爸爸给种籽叫我播。[27]
塔尔博特把他那本阖上的书,轻轻地放进书包。
“都背完了吗?”斯蒂芬问。
“老师,背完了。十点钟打曲棍球,老师。”
“半天儿,老师。星期四嘛。”
“谁会破谜语?”斯蒂芬问。
他们把铅笔弄得咯吱咯吱响,纸页窸窸窣窣,将书胡乱塞进书包。他们挤作一团,勒上书包的皮带,扣紧了,全都快活地吵嚷起来:
“破谜语,老师。让我破吧,老师。”
“噢,让我破吧,老师。”
“出个难的,老师。”
“是这么个谜儿,”斯蒂芬说:
公鸡打了鸣,
天色一片蓝。
天堂那些钟,
敲了十一点。
可怜的灵魂,
该升天堂啦。[28]
“那是什么?”
“什么,老师?”
“再说一遍,老师,我们没听见。”
重复这些词句时,他们的眼睛越睁越大了。沉默半晌后,科克伦说:
“是什么呀,老师?我们不猜了。”
斯蒂芬回答说,嗓子直发痒:
“是狐狸在冬青树下埋葬它的奶奶[29]。”
他站起来,神经质地大笑了一声,他们的喊叫声反应着沮丧情绪。
一根棍子敲了敲门,又有个嗓门在走廊里吆唤着:
“曲棍球!”
他们忽然散开来,有的侧身从凳子前挤出去,有的从上面一跃而过。他们很快就消失了踪影,接着,从堆房传来棍子的碰击声、嘈杂的皮靴声和饶舌声。
萨金特独自留了下来。他慢慢腾腾地走过来,出示一本摊开的练习本。他那其乱如麻的头发和瘦削的脖颈都表明他的笨拙。透过模糊不清的镜片,他翻起一双弱视的眼睛,央求着。他那灰暗而毫无血色的脸蛋儿上,沾了块淡淡的枣子形墨水渍,刚刚抹上去,还湿润得像蜗牛窝似的。
他递过练习本来。头一行标着算术字样。下面是歪歪拧拧的数字,末尾是弯弯曲曲的签名,带圈儿的笔划填得满满当当,另外还有一团墨水渍。西里尔·萨金特:他的姓名和印记。
“迪希先生叫我整个儿重写一遍,”他说,“还要拿给您看,老师。”
斯蒂芬摸了一下本子的边儿。徒劳无益。
“你现在会做这些了吗?”他问。
“十一题到十五题,”萨金特回答说。“老师,迪希先生要我从黑板上抄下来的。”
“你自己会做这些了吗?”斯蒂芬问。
“不会,老师。”
长得丑,而且没出息,细细的脖颈,其乱如麻的头发,一抹墨水渍,蜗牛窝。但还是有人爱过他,搂在怀里,疼在心上。倘非有她,在这谁也不让谁的世间,他早就被脚踩得烂成一摊无骨的蜗牛浆了。她爱的是从她自己身上流进去的他那虚弱稀薄的血液。那么,那是真实的喽?是人生唯一靠得住的东西喽[30]?暴躁的高隆班[31]凭着一股神圣的激情,曾迈过他母亲那横卧的身躯。她已经不在了,一根在火中燃烧过的小树枝那颤巍巍的残骸,一股黄檀和温灰气味。她拯救了他,使他免于被践踏在脚下,而她自己却没怎么活就走了。一副可怜的灵魂升了天堂:星光闪烁下,在石楠丛生的荒野上,一只皮毛上还沾着劫掠者那血红腥臭的狐狸,有着一双凶残明亮的跟睛,用爪子刨地,听了听,刨起土来又听,刨啊,刨啊。
斯蒂芬挨着他坐着解题。他用代数运算出莎士比亚的亡灵是哈姆莱特的祖父[32]。萨金特透过歪戴着的眼镜斜睨着他。堆房里有球棍的碰撞声,操场上传未了钝重的击球声和喊叫声。
这些符号戴着平方形、立方形的奇妙帽子在纸页上表演着字母的哑剧,来回跳着庄重的摩利斯舞[33]。手牵手,互换位置,向舞伴鞠躬。就是这样,摩尔人幻想出来的一个个小鬼。阿威罗伊和摩西·迈蒙尼德[34]也都离开了人世,这些在音容和举止上都诡秘莫测的人,用他们那嘲讽的镜子[35]照着朦朦胧胧的世界之灵[36]。黑暗在光中照耀,而光却不能理解它[37]。
“这会子你明白了吧?第二道自己会做了吗?”
“会做啦,老师。”
萨金特用长长的、颤悠悠的笔划抄写着数字。他一边不断地期待着得到指点,一边忠实地描摹着那些不规则的符号。在他那灰暗的皮肤下面,是一抹淡淡的羞愧之色,忽隐忽现。母亲之爱[38]:主生格与宾生格。她用自己那虚弱的血液和稀溜发酸的奶汁喂养他,藏起他的尿布,不让人看到。
以前我就像他:肩膀也这么瘦削,也这么不起眼。我的童年在我旁边弯着腰。遥远得我甚至无从用手去摸一下,即便是轻轻地。我的太遥远了,而他的呢,就像我们的眼睛那样深邃。我们两人心灵的黑暗宫殿里,都一动不动地盘踞着沉默不语的一桩桩秘密:这些秘密对自己的专横已感到厌倦,是情愿被废黜的暴君。
题已经算出来了。
“这简单得很,”斯蒂芬边说边站起来。
“是的,老师。谢谢您啦,”萨金特回答说。
他用一张薄吸墨纸把那一页吸干,将练习本捧回到自己的课桌上。
“还不如拿上你的球棍,到外面找同学去呢,”斯蒂芬边说边跟着少年粗俗的背影走向门口。
“是的,老师。”
在走廊里就听见操场上喊着他名字的声音:
“萨金特!”
“快跑,”斯蒂芬说,“迪希先生在叫你哪。”
他站在门廊里,望着这个落伍者匆匆忙忙地奔向角逐场,那里是一片尖锐的争吵声。他们分好了队,迪希先生迈着戴鞋罩的脚,路过一簇簇的草丛踱来。他刚一定到校舍前,又有一片争辩声喊起他来了。他把怒气冲冲的白色口髭转过去。
“这回,怎么啦?”他一遍接一遍地嚷着,并不去听大家说的话。
“科克伦和哈利戴分到同一队里去啦,先生,”斯蒂芬大声说。
“请你在我的办公室等一会儿,”迪希先生说,“我把这里的秩序整顿好就来。”
他煞有介事地折回操场,扯着苍老的嗓子严厉地嚷着:
“什么事呀?这回又怎么啦?”
他们的尖嗓门从四面八方朝他喊叫,众多身姿把把团团包围住,刺目的阳光将他那没有染好的蜂蜜色头发晒得发白了。
工作室里空气浑浊,烟雾弥漫,同几把椅子那磨损咸淡褐色的皮革气味混在一起。跟第一天他和我在这里讨价还价时一个样儿。厥初如何,今兹亦然 [39]。靠墙的餐具柜上摆着一盘斯图亚特[40]硬币,从泥塘里挖出来的劣等收藏品:以迨永远[41]。在褪了色的紫红丝绒羹匙匣里,舒适地躺着十二使徒[42],他们曾向一切外邦人宣过教[43],及世之世[44]。
沿着门廊的石板地和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迪希先生吹着他那稀疏的口髭,在桌前站住了。
“头一桩,把咱们那一小笔帐结了吧,”他说。
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用皮条扎起来的皮夹子。它啪的一声开了,他就从里面取出两张钞票,其中一张还是由两个半截儿拼接起来的,并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摊在桌子上。
“两镑,”他说着,把皮夹子扎上,收了起来。
现在该开保险库取金币了。斯蒂芬那双尴尬的手抚摩着堆在冰冷的石钵里的贝壳,蛾螺、子安贝、豹贝,这个有螺纹的像是酋长的头巾,还有这个圣詹姆斯的扇贝[45]。一个老朝圣者的收藏品,死去了的珍宝,空洞的贝壳。
一枚金镑,锃亮而崭新,落在厚实柔软的桌布上。
“三镑,”迪希先生把他那只小小的攒钱盒在手里转来转去,说。“有这么个玩艺儿可便当啦。瞧,这是放金镑的。这是放先令的,放六便士的,放半克朗的。这儿放克朗。瞧啊。”
他从里面倒出两枚克朗和两枚先令。
“三镑十二先令,”他说。“我想你会发现没错儿。”
“谢谢您啦,先生,”斯蒂芬说,他难为情地连忙把钱拢在一起,统统塞进裤兜里。
“完全不用客气,”迪希先生说。“这是你挣的嘛。”
斯蒂芬的手又空下来了,就回到空洞的贝壳上去。这也是美与权力的象征。我兜里有一小簇。被贪婪和贫困所砧污了的象征。
“不要那样随身带着钱,”迪希先生说。“不定在哪儿就会掏丢了。买上这样一个机器,你会觉得方便极啦。”
回答点儿什么吧。
“我要是有上一个,经常也只能是空着,”斯蒂芬说。
同一间房,同一时刻,同样的才智,我也是同一个我。这是第三次[46]了。我的脖子上套着二道绞索。唔。只要我愿意,马上就可以把它们挣断。
“因为你不攒钱,”迪希先生用手指着说。“你还不懂得金钱意味着什么。金钱是权,当你活到我这把岁数的时候嘛。我懂得,我懂得。倘若年轻人有经验……然而莎士比亚是怎么说的来看?只要把银钱放在你的钱袋里[47]。
“伊阿古,斯蒂芬喃喃地说。
他把视线从纹丝不动的贝壳移向老人那凝视着他的目光。
“他懂得金钱是什么,”迪希先生说。“他赚下了钱。是个诗人,可也是个英国人。你知道英国人以什么为自豪吗?你知道能从英国人嘴里听到的他最得意的话是什么吗?”
海洋的统治者。他那双像海水一样冰冷的眼睛眺望着空荡荡的海湾:看来这要怪历史,对我和我所说的话也投以那样的目光,倒没有厌恶的意思。
“说什么在他的帝国中,”斯蒂芬说,“太阳是永远不落的。”
“不对!”迪希先生入声说。“那不是英国人说的。是一个法国的凯尔特族[48]人说的。”
他用攒钱盒轻轻敲着大拇指的指甲。
“我告诉你,”他一本正经地说,“他最爱自夸的话是什么吧。我没欠过债。”
好人哪,好人。
“我没欠过债。我一辈子没该过谁一先令。你能有这种感觉吗?我什么也不欠。你能吗?”
穆利根,九镑,三双袜子,一双粗革厚底皮鞋,几条领带。柯伦,十基尼。麦卡恩,一基尼。弗雷德·瑞安,两先令。坦普尔,两顿午饭。拉塞尔,一基尼,卡曾斯,十先令,鲍勃·雷诺兹,半基尼,凯勒,三基尼,麦克南太太[49],五个星期的饭费。我这一小把钱可不顶用。
“现在还不能,”斯蒂芬回答说。
迪希先生十分畅快地笑了,把攒钱盒收了回去。
“我晓得你不能,”他开心地说。“然而有朝一日你一定体会得到。我们是个慷慨的民族,但我们也必须做到公正。”
“我怕这种冠冕堂皇的字眼儿,”斯蒂芬说,“这使我们遭到如此之不幸。”
迪希先生神情肃然地朝着壁炉上端的肖像凝视了好半晌。那是一位穿着苏格兰花格呢短裙、身材匀称魁梧的男子,威尔士亲王艾伯特·爱德华[50]。
“你认为我是个老古板,老保守党,”他那若有所思的嗓音说。
“从打奥康内尔[51]时期以来,我看到了三代人。我记得那次的大饥荒[52]。你晓得吗,橙带党[53]分支鼓动废除联合议会要比奥康内尔这样做,以及你们教派的主教、教长们把他斥为煽动者,还早二十年呢!你们这些芬尼社社员[54]有时候是健忘的。”
光荣、虔诚、不朽的纪念[55]。在光辉的阿马的钻石会堂里,悬挂着天主教徒的一具具尸首[56]。沙哑着嗓子,戴面罩,手执武器,殖民者的宣誓[57]。被荒废的北部,确实正统的《圣经》。平头派倒下去[58]。
斯蒂芬像画草图似的打了个简短的手势。
“我身上也有造反者的血液,”迪希先生说。“母方的。然而我是投联合议会赞成票的约翰·布莱克伍德爵士的后裔。我们都是爱尔兰人,都是国王的子嗣[59]。”
“哎呀,”斯蒂芬说。
“走正路[60],”迪希先生坚定地说,“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他投了赞成票,是穿上高统马靴,从当郡的阿兹[61]骑马到都柏林去投的。”
吁——萧萧,吁——得得,
一路坎坷,赴都柏林。[62]
一个粗暴的绅士,足登锃亮的高统马靴,跨在马背上。雨天儿,约翰爵士。雨天儿,阁下……天儿……天儿…一双高统马靴荡悠着,一路荡到都柏林。吁——萧萧,吁——得得。吁——萧萧,吁——得得。
“这下子我想起来啦,”迪希先生说。“你可以帮我点儿忙,迪达勒斯先生,麻烦你去找几位文友。我这里有一封信想投给报纸。请稍坐一会儿。我只要把末尾誊清一下就行了。”
他走到窗旁的写字台那儿,把椅子往前拖了两下,读了读卷在打字机滚筒上那张纸上的几个字。
“坐下吧。对不起,”他转过脸来说,“按照常识行事。一会儿就好。”
他扬起浓眉,盯看看肘边的手稿,一面咕哝着,一面慢腾腾地去戳键盘上那僵硬的键。时而边吹气,边转动滚筒,擦掉错字。
斯蒂芬一声不响地在亲王那幅仪表堂堂的肖像前面坐下来,周围墙上的那些镜框里,毕恭毕敬地站着而今已消逝了的一匹匹马的形象,它们那温顺的头在空中昂着:黑斯廷斯勋爵的“挫败”,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跨越”,波弗特公爵的“锡兰”,一八六六年获巴黎奖[63]。小精灵般的骑手跨在马上,机警地等待着信号。他看到了这些佩带着英王徽记的马的速度,并随着早已消逝了的观众的欢呼而欢呼。
“句号,”迪希先生向打字机键盘发号施令。“但是,立即公开讨论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为了及早发上一笔财,克兰利曾把我领到这里来;我们在溅满泥点子的大型四轮游览马车之间,在各据一方的赛马赌博经纪人那大声吆唤和饮食摊的强烈气味中,在色彩斑驳的烂泥上穿来穿去,寻找可能获胜的马匹。“美反叛”[64](!“美反叛”!大热门][65]以一博一;冷门马以十博一。我们跟在马蹄以及戴竞赛帽穿运动衫的骑手后边,从掷骰摊和玩杯艺[66]摊跟前匆匆走边,还遇上一个大胖脸的女人——肉铺的老板娘。她正饥渴地连皮啃着一掰两半的桔子,连鼻孔都扎进去了。
操场上传来少年们一片尖叫声和打嘟噜的哨子声。
又进了一球。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夹在那些你争我夺、混战着的身躯当中,一场生活的拼搏。你指的是那个妈妈的宠儿“外罗圈腿”吧?他好像宿酒未醒似的。拼搏啊。时间被冲撞得弹了回来,冲撞又冲撞。战场上的拼搏、泥泞和喊声,阵亡者弥留之际的呕吐物结成了冰,长矛挑起鲜血淋漓的内脏时那尖叫声。
“行啦,”迪希先生站起来说。
他踱到桌前,把打好了的信别在一起。斯蒂芬站了起来。
“我把这档子事与得简单明了,”迪希先生说。“是关于口蹄疫问题。你看一下吧。大家一定都会同意的。”
可否借用贵报一点宝贵的篇幅。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我国的牲畜贸易。我国各项旧有工业的方针。巧妙地操纵了戈尔韦建港计划 [67]的利物浦集团。欧洲战火。通过海峡那狭窄水路的[68]粮食供应。农业部完完全全无动于衷。恕我借用一个典故。卡桑德拉。由于一个不怎么样的女人的关系[69]。现在言归正题。
“我够单刀直入了吧?”斯蒂芬往下读时,迪希先生问道。
口蹄疫。通称科克配方[70]。血清与病毒。免疫马的百分比。牛瘟。下奥地利慕尔斯泰格的御用马群。兽医外科。亨利·布莱克伍德·普赖斯[71]先生,献上处方,恭请一试。只能按照常识行事。无比重要的问题。名副其实地抓住公牛角[72]。感谢贵报慷慨地提供的篇幅。
“我要把这封信登在报上,让大家都读到,”迪希先生说。“你看吧,下次再突然闹瘟疫,他们就会对爱尔兰牛下禁运令了。可是这病是能治好的。已经有治好的了。我的表弟布莱克伍德·普赖斯给我来信说,在奥地利,那里的兽医挂牌医治牛瘟,并且都治好了。他们表示愿意到这里来。我正在想办法对部里的人施加点影响。现在我先从宣传方面着手。我面临的是重重困难,是……各种阴谋诡计,是……幕后操纵,是……”
他举起食指,老谋深算地在空中摆了几下才说下去。
“记住我的话,迪达勒斯先生,”他说。“英国已经掌握在犹太人手里了。占去了所有高层的位置,金融界、报界。而且他们是一个国家衰败的兆头。不论他们凑到哪儿,他们就把国家的元气吞掉。近年来,我一直看看事态的这种发展。犹太商人们已经干起破坏勾当了,这就跟咱们站在这里一样地确凿。古老的英国快要灭亡啦。”
他疾步向一旁走去,当他们跨过一束宽宽的日光时,他的两眼又恢复了生气勃勃的蓝色。他四下里打量了一番,又走了回来。
“快要灭亡了,”他又说,“如果不是已经灭亡了的话。”
妓女走街串巷到处高呼,为老英格兰织起裹尸布。[73]
他在那束光里停下脚步,恍惚间见到了什么似的睁大了眼睛,严峻地逼视着。
“商人嘛,”斯蒂芬说,“左不过是贱买贵卖。犹太人也罢,非犹太人也罢,都一个样儿,不是吗?”
“他们对光[74]已下了罪,”迪希先生严肃地说。“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黑暗。正因为如此,他们至今还在地球上流离失所。”
在巴黎证卷交易所的台阶上,金色皮肤的人们正伸出戴满宝石的手指,报着行情。嘎嘎乱叫的鹅群。他们成群结队地围着神殿[75]转,高声喧噪,粗鲁俗气,戴着不三不四的大礼帽,脑袋里装满了阴谋诡计。不是他们的,这些衣服,这种谈吐,这些手势。他们那睁得圆圆的滞钝的眼睛,与这些言谈,这些殷切、不冲撞人的举止相左,然而他们晓得自己周围积怨甚深,明白一腔热忱是徒然的。耐心地积累和贮藏也是白搭。时光必然使一切都一散而光。堆积在路旁的财宝:一旦遭到掠夺,就落入人家手里。他们的眼睛熟悉流浪的岁月,忍耐着,了解自已的肉体所遭受的凌辱。
“谁不是这样的呢?”斯蒂芬说。
“你指的是什么?”迪希先生问道。
他向前边了一步,站在桌旁。他的下巴颏歪向一边,犹豫不定地咧着嘴。这就是老人的智慧吗?他等着听我的呢。
“历史,”斯蒂芬说,“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恶梦L76]。”
从操场上传来孩子们的一片喊叫声。一阵打嘟噜的哨子声,进球了。倘若那场恶梦像母马[77]似的尥蹶子,踢你一脚呢?
“造物主的做法跟咱们不一样,”迪希先生说。“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朝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神的体现。”
斯蒂芬冲着窗口翘了一下大拇指,说:
“那就是神。”
好哇!哎呀!呜噜噜噜!
“什么?”迪希先生问。
“街上的喊叫[78],”斯蒂芬耸了耸肩头回答说。
迪希先生朝下面望去,用手指捏了一会儿鼻翅。他重新抬起头来,并撒开了手。
“我比你幸福,”他说。“我们曾犯过许多错误,有过种种罪孽。一个女人[79]把罪恶带到了人世间。为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女人,海伦,就是墨涅拉俄斯那个跟人跑了的妻子,希腊人同特洛伊打了十年仗。一个不贞的老婆首先把陌生人带到咱们这海岸上来了,就是麦克默罗的老婆和她的姘夫布雷夫尼大公奥鲁尔克 [80]。巴涅尔[81]也是由于一个女人的缘故才栽的跟斗。很多错误,很多失败,然而惟独没有犯那种罪过。如今我已经进入暮年,却还从事着斗争。我要为正义而战斗到最后。”
因为阿尔斯特要战斗,阿尔斯特在正义这一头。[82]
斯蒂芬举起手里那几页信。
“喏,先生,”他开口说。
“我估计,”迪希先生说,“你在这里干不长。我认为你生来就不是当老师的材料。兴许我错了。”
“不如说是来当学生的,”斯蒂芬说。
那么,你在这儿还能学到什么呢?
迪希先生摇了摇头。
“谁知道呢?”他说。“要学习嘛,就得虚心。然而人生就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斯蒂芬又沙沙地抖动着那几页信。
“至于这封信,”他开口说。
“对,”迪希先生说。“你这儿是一式两份。你要是能马上把它们登出来就好了。”
《电讯报》,《爱尔兰家园报》[83]。
“我去试试看,”斯蒂芬说,“明天给您回话。我跟两位编辑有泛泛之交。”
“那就好,”迪希先生生气勃勃地说。“昨天晚上我给议会议员菲尔德先生写了封信。牲畜商协会今天在市徽饭店开会[84]。我托他把我的信交到会上。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发表在你那两家报纸上。是什么报来着?”
“《电讯晚报》……”
“那就好,”迪希先生说。“一会儿也不能耽误。现在我得回我 表弟那封信了。”
“再会,先生,”斯蒂芬边说边把那几页信放进兜里。“谢谢您。”
“不客气,”迪希先生翻找着写字台上的文件,说。“我尽管上了岁数,却还爱跟你争论一番哩。”
“再会,先生,”斯蒂芬又说一遍,并朝他的驼背鞠个躬。
踱出敞开着的门廊,他沿着砂砾铺成的林荫小径走去,听着操场上的喊叫声和球棍的击打声。他迈出大门的时候,一对狮子蹲在门柱上端;没了牙齿却还在那里耍威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斗争中帮他一把。穆利根会给我起个新外号:阉牛之友派“大诗人”[85]。
“迪达勒斯先生!”
从我背后追来了。但愿不至于又有什么信。
“等一会儿。”
“好的,先生,”斯蒂芬在大门口回过身来说。
迪希先生停下脚步,他喘得很厉害,倒吸着气。
“我只是要告诉你,”他说。“人家说,爱尔兰很光荣,是唯一从未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你晓得吗?不晓得。那么,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朝着明亮的空气,神色严峻地皱起眉头。
“为什么呢,先生?”斯蒂芬问道,脸上开始漾出笑容。
“因为她从来没让他们入过境[86],”迪希先生郑重地说。
他的笑声中含着一团咳嗽,抱着一长串咕噜咕噜响的粘痰从他喉咙里喷出来。他赶快转过身去,咳啊,笑啊,望空挥着双臂。
“它从来没让他们入过境,”他一边笑着一边又叫喊,同时两只鞋上戴罩的脚踏着砂砾小径。“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太阳透过树叶的棋盘格子,往他那睿智的肩头上抛下一片片闪光小圆装饰,跳动着的金币。
第二章 注释
[l]指皮勒斯(公元前3l9-公元前272),希腊西北部伊庇鲁斯的国王。
[2]塔兰图姆乃今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的旧称。公元前人世纪沦为希腊殖民地。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军队进逼时,塔兰图姆向伊庇鲁斯求救兵。
[3]“记忆的女儿们”指希腊神话里主神宙斯与摩涅莫绪涅(记忆女神)之间所生的九位缪斯(司文艺、音乐、天文等的女神)。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的名句:“寓言或讽喻系记忆的女儿们所编。想像被灵感的女儿们所包围……”。见《最后审判的景象》(1810)。
[4]这是把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约1790)中的两句箴言合并而成:“过分之路导向智慧之宫”和“只要凭自已的翼,不愁鸟儿飞不高”。
[5]在第三章中,描述炸监狱的场面时,也用了“玻璃碎成碴儿,砖石建筑坍塌下来”之句。见该章注[130]及有关正文。“终极的一缕死灰色火焰”出自《天堂与地狱的婚姻》。
[6]阿斯库拉姆是阿斯科利?萨特里亚诺的古称,在今意大利南部。公元前二七八年,皮勒斯在此击败罗马军队。
[7]皮勒斯是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于阿斯科利?萨特里亚诺之役中取得胜利的。
[8]多基是斯蒂芬执教的学校所在地,位于都柏林郡海滨区,属旅游胜地,到处是富人的住宅及别墅。
[9]皮勒斯(Pyrrhus)与栈桥(pier)二字发音近似。这里,阿姆斯特朗搞错了。
[lO]国王镇(见第一章注[15])与学校所在地多基相距不近。东码头长达一英里,夏季常有乐队在此举行露天音乐会。
[11]斯蒂芬教的是男校,他从班上男生的脸联想到可能与他们相好的四个女孩子的名字。
[12]皮勒斯那场以惨重伤亡换得的胜利,使斯蒂芬联想到栈桥。栈桥不能通到彼岸,所以是一座失望之桥。
[13]当天早晨即将离开圆塔时,海恩斯曾对斯蒂芬说,他想把斯蒂芬的说词儿搜集起来。见第一章。
[14]此语令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约翰王》第3幕第4场中康斯丹丝的一句台词:“人生犹如一段重复叙述的故事那洋可厌,扰乱一个倦怠者的懒洋洋的耳朵……”
[15]公元前二七二年,在阿尔戈斯巷战中,皮勒斯正要杀一个敌人时,其老母从屋顶上对推骑着马的他抛下一片瓦,致使他坠马丧命。
[16]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l00一前44)集执政官、保民官、独裁官等大权于一身,被以布鲁图和卡西乌为首的共和派贵族阴谋刺死。
[17]古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事情发生之前,有多种可能性;一旦其中一种成为事实之后,其他可能性便统统被排除掉了。
[18]织风者,参看第一章注[118]。
[19]出自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一1674)为悼念一六三七年八月十日溺死于爱尔兰海的友人爱德华?金而作的《利西达斯》(1638)一诗。
[20]亚理斯多德在《物理学》中指出,潜在的可能住变为现实的过程即是运动。
[21]圣热内维艾芙(约422一约500)是巴黎的女主保圣人。这座图书馆即以她的名字命名。乔伊斯本人在巴黎时常来此阅读。下文中的暹罗是泰国旧称。
[22]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写道:“我在地狱的一家印刷厂里看见知识怎样一代伏地传播。第一车间有个龙人在清除洞口的垃圾;里面,一批龙在挖洞。”
[23]亚理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了“主导力是有关思维本身的思维”的论断。
[24]参看亚理斯多德的《论灵魂》:“正如手是工具的工具,头脑乃是形态的形态。”头脑即指灵魂。意思是,一切事物都须通过头脑的活动来认识。
[25]见《马太福音》第14章第25节:“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26]据《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至21 节,法利赛人想用耶稣的话陷害耶稣,便问他可否纳税给恺撒。耶稣问:上税的钱币上的像和号是谁的?人们答以是恺撒的。耶稣便说了这句话。
[27]这是一个谜语的前半段,后半段是:“黑黑的籽儿,白白的地儿。/这谜语,你能破,我献给你喝。”(谜底:写信。)
[28]、[29]这个谜语见P?W?乔伊斯著《我们今日在爱尔兰所说的英语》一书。斯蒂芬把词句改得简练了,而且因对其亡母有着负疚感,故把原谜底中的“母亲”改为“奶奶”。原来的谜语和谜底是:“我猜谜,猜个准儿:/ 昨晚我看见了啥?/风儿刮,/公鸡打了鸣。/天堂那些钟,/敲了十一点。/我可怜的灵魂,/该升天堂啦。”(谜底,狐狸在冬青树下埋葬它的母亲。)
[30]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书第5章的末尾,克兰利曾对斯蒂芬说:“在这个臭狗屎堆的世界上,你可以说任何东西都靠不住,但母亲的爱可是个例外。……她的感觉至少是真实的。”
[31]高隆班(约543一615),爱尔兰人,凯尔特族基督教传教士。他不畏迫害,辗转在欧洲各地传教。他生性暴躁,在瑞士传教时曾放火焚烧过异教的教堂。死后被教皇封为圣徒。为了阻止他外出传教,他母亲曾横卧在家门口。
[32]在第一章中,勃克?穆利根曾对海恩斯说,斯蒂芬用代数运算出了莎士比亚与哈姆莱特及其父王亡灵的关系。现在斯蒂芬想起了穆利根这番话,然而这里的问句与前文略有出入。
[33]摩里斯一词源于摩里斯科,意力“摩尔人的”。摩尔人是在非洲西北部定居下来的西班牙、阿拉伯及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
[34]中世纪西欧人将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一1198)的名字拉丁化了,称他为阿威罗伊。他属于摩尔族,是出生在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哲学家。他提出“双重真理”一说,对西欧中世纪和十六至十七世纪哲学和科学摆脱宗教束缚而获得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摩西?迈蒙尼德(1135一1204),出生于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犹太族哲学家。他企图调和亚理斯多德哲学和犹太主义。主要著作有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迷途指津》。十三世纪传入西欧译为拉丁文后,对经院哲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等影响甚大。
[35]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被控用“巫镜”(水晶球或盛满了水、表面发光的容器)进行占卜。
[36]“世纪之灵”是意大利哲学家、数学家家乔达诺?布鲁诺(1548-]600)在《关于原因、原则和一》中使用过的词。他将亚理斯多德的二元论演绎成一元论。
[37]参看《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光在黑暗中照耀,而黑暗却不能理解它。”光指耶稣(见《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黑暗指世人。这里,作者把原话颠倒过来了。
[38]原文为拉丁文。按主生格讲是“母爱”,按宾主格讲是“爱母”。
[39]、[41]、[44]这里,作者把天主教《圣三光荣颂》的下半段拆开来引用了。全文是:“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我愿其获光荣。厥初如何,今兹亦然,以迨永远,及世之世。啊们。”
[40]斯图亚特家族自一三七一年起为苏格兰王室,一六0三年起为英格兰王室。一六八五年詹姆斯二世继位,一六八八年黜础,逃到爱尔兰,次年用贱金属铸币,后成为罕见的收藏品。
[42]指刻在羹匙柄上的十二使徒的像。
[43]据《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第7节:“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要我把福音的信息传给外邦人,好使他们听见而相信。’”从此,使徒们不但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即非犹太人)传教。
[45]圣詹姆斯(或圣雅各)的圣祠坐落在西班牙的康波斯帖拉。中世纪的香客到此朝圣回去时,在附近拾一枚扇贝佩带在帽子上作纪念。贝壳又是金钱的象征。
[46]故事发生在这一天是六月十六日。这所私立学校每半个月发一次薪。这是斯蒂芬第三次领薪水,说明他是从五月初开始执教的。
[47]“倘若年轻人有经验”是意大利一句谚语的前一半。被省略的后一半是:“而老人有精力,则世上无难事。”“只要把钱放在你的钱袋里”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中的坏蛋伊阿古挑唆威尼斯绅士罗德利哥为非作歹时所说的话,见第1幕第3场。迪希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此语。
[48]凯尔特族是公无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欧洲莱茵、塞纳等河流域的一个部落。其后裔今散布在法国北部、爱尔兰岛、苏格兰高原、威尔士等地。凯尔特族分布的地区虽广,但从未形成一个帝国,所以也不会这样夸口。“太阳是永远不落的”一语,最早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一前430/前420)说的,他指的是波斯帝国。到了近代,英帝国也曾这样自诩过。参看第十二章注[138]。下文“他用……指甲”诸本均接排。这里系按海德一九八九年版分段。
[49]康斯坦丁?P?柯伦和詹姆斯?H、卡曾斯分别为乔伊斯在都柏林的朋友和熟人(均见艾尔曼所著《詹姆斯?乔伊斯》第151页)。 麦卡恩和坦普尔均为《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5章中的人物。弗雷德?瑞安,参看第九章注[179]。T?G?凯勒是乔伊斯在都柏林的一个文友(同上书第164页、200页)。乔伊斯曾于一九O 四年做过麦克南太太的房客(同上书第151页)。
[50]艾伯特?爱德华(1841-1910),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出生一个月即被其母封为威尔士亲王。女王于一九0一年去世后,他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即爱德华七世。
[5l]丹尼尔?奥康内尔( 1775一1847 ),十九世纪英国下院中第一位爱尔兰民族独立领袖,毕生为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的自由和废除英、爱联合议会,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而奋斗。他曾成功地在爱尔兰境内各地组织一系列群众集会,因而于一八四四年以阴谋煽动叛乱罪被捕,监禁三个月。这里,迪希却将英政府当局把他斥为“煽动者”一事说成是天主教的主教、教长们所为。
[52]自一八四五年起,爱尔兰人民的主食土豆便歉收,一八四六、一八四七年间很多人死于大饥荒。
[53]橙带党(原名奥伦治党)是爱尔兰新教徒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旨在维护新教及其王位继承权。一七九五年,该党在爱尔兰和英国各地秘密组成分支,加强抵制爱尔兰自治法案,坚决反对地方自治。橙带党初成立时,曾反对将爱尔兰议会并入英国议会。然而那时的爱尔兰议会反正是操纵在信仰新教的英国殖民者手里的,所以他们反对联合议会,与爱尔兰人民开展的主张废除联合议会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意义迥然不同。
[54]芬尼是爱尔兰古部落名。芬尼社是由爱尔兰革命家詹姆斯?斯蒂芬斯(1825-1901 )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主张推翻英国统治,废除大地主所有制,建立共和国。该组织是一八五七年在美国成立的,不久即在爱尔兰本土展开反英活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斯蒂芬斯因内奸告密被捕,关在都柏林的里奇蒙监狱里。不出几天,芬尼社成员就在看守女儿的协助下,把他救了出来。次年二月,偷渡到美国,被选为在美国的芬尼社领袖。美国的芬尼社社员于一八六六、一八七0 年和一八七一年三次越境至加拿大举行起义,均告流产。爱尔兰的芬尼社亦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这里,迪希是把芬尼社社员一词作为激进的共和党人的俗称采用的。
[55]此语出自橙带党纪念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50-1702 )的祝酒辞:“纪念伟大的好国王威廉三世,他光荣、虔诚、不朽,拯救了我们……”威廉生在海牙,原为奥伦冶亲王。一六八九年英国议会宣布信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退位,威廉加冕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并于一六九一年征服了爱尔兰。
[56]一七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几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在北爱尔兰阿马郡首府阿马镇的钻石会堂聚会,以抗拒英国殖民者把全体爱尔兰天主教徒从该郡驱逐出去的勒令。他们追到残酷屠杀,无一幸存。
[57]自十七世纪初起,英政府便没收了爱尔兰北部大批土地,凡是迁移到那里的英国殖民者,只要宣誓效忠于英王,并承认信新教的英王为宗教领袖,就能领到土地。从此,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当地农民便沦为佃农。后文中“被荒废的”,原文作“black”,也可译为“黑色的”,“险恶的”。
[58]“平头派倒下去”一语出自橙带党反对爱尔兰独立运动的一首歌。“平头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七九八年,那些主张在爱尔兰实行共和制者,曾效仿法兰西革命者,也推成平头,故名。
[59]约翰?布莱克伍德(1722-1799)是爱尔兰议员。英国曾以晋升爵位为钓饵,要他投联合议会的赞成票, 但他坚决抵制。后却在前往都柏林去投反对票的途中,遽然去世。其子约翰?G? 布莱克伍德倒确实投了联合议会的赞成票,从而被封为达弗林爵士。这里,迪希把儿子的事写在父亲身上了。“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是国王的子嗣”是一句成语。
[60]原文是拉丁文,出自《旧约?诗篇》第25篇第8 节。全句为:“耶和华是善良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61]当郡是北爱尔兰东部一郡。十七世纪有大量移民涌入。阿兹是北爱尔兰的一个区,当时即属当郡。
[62]《一路坎坷,赴都柏林》是一首爱尔兰歌谣,写一个穷苦的农村少年行路时受尽侮辱、遭到抢劫的经历。
[63]“挫败”,马名,在英国新集市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中获一千基尼奖金(1866)。小母马“跨越”在新集市的赛马中获二千基尼奖金(1822)。“锡兰”在法国最著名的巴黎赛马中获大奖(1866)。
[64]“美反叛”是一匹名马,曾在位于都柏林西南的豹镇一年一度的赛马中获胜。
[65]参看第十五章注[753)。[]内的词句系据海德一九八九年版补译。
[66]杯艺是一种赌博,有三个扣着的顶针状小杯,叫观众猜测哪一只底下藏着豆子。
[67]戈尔韦是爱尔兰戈尔韦郡港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度计划把它开辟为国际航运中心,后未能实现。但这里所说此事是被利物浦集团巧妙地操纵,与史实相悖。前文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原文为法语。
[68]按日俄战争已于这一年(1904年)的二月八日爆发。这里指万一战争蔓延到欧洲,横渡大西洋的船只就只好不取道爱尔兰与威尔士之间的圣乔治海峡或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而径直驶入戈尔韦湾了。
[69]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最后一个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为阿波罗神所爱,被赐予卜吉凶的本领。但因不肯委身于阿波罗,受其诅咒,致使她的预言没人相信,因而无法避免灾祸。“不地道的女人”指的是海伦。她已嫁给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却和普里阿摩斯王的儿子帕里斯一道私奔到特洛伊,从而引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70]这是德国医生、细菌学家罗勃特?科克(1843一1910)研究出来的预防炭疽病(不是口蹄疫)的配方。
[71]亨利?布莱克伍德?普赖斯是乔伊斯的朋友。关于医治在爱尔兰流行的口蹄疫问题,他曾于一九一二年和乔伊斯通过信。参看理查德?艾尔曼所著《詹姆斯
?乔伊斯》(第325页)。
[7Z]“抓住公牛角”是英国谚语,意思是敢于处理棘手之事。
[78]出自布莱克的《清白的征兆》。原诗抨击了当时英国准许娼赌的政策。
[74]这里的光即指耶稣。参看本章注[37]。
[75]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建筑,是十九世纪初叶仿造罗马的韦斯巴芗神殿盖越来的。斯蒂芬所回忆的这个场面,使人联想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耶稣进了神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76]这里套用法国印象派诗人朱尔斯?拉弗格(1860-1887)的遗作《杂记》(1903)中的书信里的句子:“历史是一场古老而变化多端的恶梦……”
[77]英语中,恶梦(nightmare)由夜晚(night)和母马(mare)二词组成。当天晚上斯蒂芬借用了迪希在下面所说的“朝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一语。见第十五章注[705]。
[78]这里套用《箴言》第1章第20节的“听吧,智慧在街市上呼唤,…… 在热闹的街头减叫”。
[79]一个女人指夏娃。
[80]这里,迪希把事件中的人物关系颠倒了。史实是,一一五二年,爱尔兰的小国伦斯特的麦克默罗王把另一小国布雷夫尼的大公奥鲁尔克之妻拐走( 另有一种说法是二人一道私奔的) ,从而引起战争。麦克默罗向英国的亨利二世求援。这便是英国入侵爱尔兰的开始。
[81]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1846-1891),十九世纪末爱尔兰自治运动和民族主义领袖。一八七九年任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土地同盟主席。土地同盟遭到镇压后,各地不断发生恐怖事件。巴涅尔很快就便民族主义运动受到严格纪律的约束。一八八二年五月,英国政治家、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和次官伯克在都柏林西郊的凤凰公园散步时,被民族主义秘密团体“常胜军”成员刺杀。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泰晤士报》发表“巴涅尔信件”的影印图片,指控巴涅尔包庇凤凰公园暗杀案的凶手。巴涅尔立即指出这是纯属捏造的。约两年后,伪造信件者畏罪自杀,巴涅尔在英国自由党人的眼中成为英雄。这时期是他一生的顶峰。一八八九年他因与有夫之妇姘居,被其丈夫奥谢上尉控告。天主教的主教们指责他道德败坏,不宜担任领导职务。次年与奥谢夫人结婚,舆论哗然,他的事业遂前功尽弃。
[82]阿尔斯特是爱尔兰古代省份之一。一五九四至一六0一年,这里曾发生反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叛乱。一六0七年以后有数千名苏格兰人移居此地。这两句话是英国政治家伦道夫?斯潘塞?丘吉尔(1849-1895)在竞选时为了煽动本地人反对爱尔兰自治而说的。后即成为爱尔兰北部反对爱尔兰自治、反对天主教的口号。
[83]《电讯报》,即都柏林的《电讯晚报》,创刊于一七六三年。《爱尔兰家园报》是都柏林的一份周报。
[84]牲畜商协会每星期四在市徽饭店开一次会。
[85]阉牛之友派“大诗人”暗指荷马,因为在他笔下,《奥德修纪》卷12中,凡是宰食了太阳神的牛者,全都送了命。
[86]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其实早在十三世纪爱尔生就驱逐过犹太人,十八、十九世纪还通过立法,迫使犹太人归化。
第三章
可视事物无可避免的形式[1]:至少是对可视事物,通过我的眼睛认知。我在这里辨认的是各种事物的标记[2],鱼的受精卵和海藻,越来越涌近的潮水,那只铁锈色的长统靴。鼻涕绿,蓝银,铁锈:带色的记号[3]。透明的限度。然而他补充说,在形体中。那么,他察觉事物的形体早于察觉其带色了。怎样察觉的?用他的头脑撞过,准是的。悠着点儿。他歇了顶,又是一位百万富翁。有学识者的导师[4]。其中透明的限度。为什么说其中?透明,不透明。倘若你能把五指伸过去,那就是户,伸不过去就是门。闭上你的眼睛去看吧。
斯蒂芬闭上两眼,倾听着自己的靴子踩在海藻和贝壳上的声音。你好歹从中穿行着。是啊,每一次都跨一大步。在极短暂的时间内,穿过极小的一段空间。五,六:持续地[5]。正是这样。这就是可听事物无可避免的形态。睁开你的眼睛。别,唉!倘苦我从濒临大海那峻峭的悬崖之颠[6]栽下去,就会无可避免地在空间并列着[7]往下栽!我在黑暗中呆得蛮惬意。那把梣木刀佩在腰间。用它点着地走: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的两只脚穿着他的靴子,并列着[8]与他的小腿相接。听上去蛮实,一定是巨匠[9]造物主[10]那把木槌的响声。莫非我正沿着沙丘[11]走向永恒不成?喀嚓吱吱,吱吱,吱吱。大海的野生货币。迪希先生全都认得。
来不来沙丘,
母马玛达琳[12]?
瞧,旋律开始了。我听见啦。节奏完全按四音步句的抑扬格在行进。不。在飞奔。母马达琳。
现在睁开眼睛吧。我睁。等一会儿。打那以后,一切都消失了吗?倘若我睁开眼睛,我就将永远呆在漆黑一团的不透明体中了。够啦[13]!看得见的话,我倒是要瞧瞧。
瞧吧,没有你,也照样一直存在着,以迨永远,及世之世[14]。
她们从莱希的阳台上沿着台阶小心翼翼地走下来了——婆娘们[15]。八字脚陷进沉积的泥沙,软塌塌地走下倾斜的海滨。像找,像阿尔杰一样,来到我们伟大的母亲跟前。头一个沉甸甸地甩着她那只产婆用的手提包,另一个的大笨雨伞戳进了沙滩。她们是从自由区[16]来的,出来散散心。布赖德街那位受到深切哀悼的已故帕特里克·麦凯布的遗孀,弗萝伦丝·麦凯布太太。是她的一位同行,替呱呱啼哭着的我接的生。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她那只手提包里装着什么?一个拖着脐带的早产死婴,悄悄她用红糊糊的泥绒裹起。所有脐带都是祖祖辈辈相连接的,芸芸众生拧成一股肉缆,所以那些秘教僧侣们都是。你们想变得像神明那样吗?那就仔细看自己的肚脐[17]吧。喂,喂。我是金赤。请接伊甸城。阿列夫,阿尔法[18],零,零,一。
始祖亚当的配偶兼伴侣,赫娃[19],赤身露体的夏娃。她没有肚脐。仔细瞧瞧。鼓得很大、一颗痣也没有的肚皮,恰似紧绷着小牛皮面的圆楯。不像,是一堆白色的小麦[20],光辉灿烂而不朽,从亘古到永远[21]。罪孽的子宫。
我也是在罪恶的黑暗中孕育出的,是被造的,不是受生的[22]。是那两个人干的,男的有着我的嗓门和我的眼睛,那女幽灵的呼吸带有湿灰的气息。他们紧紧地搂抱,又分开,按照撮合者的意愿行事。盘古首初,天主就有着要我存在的意愿,而今不会让我消失,永远也不会。永远的法则[23]与天主共存。那么,这就是圣父与圣子同体的那个神圣的实体吗?试图一显身手[24]的那位可怜的阿里马老兄,而今安在?他反对“共在变体赞美攻击犹太论”[25],毕生为之战斗。注定要倒楣的异端邪说祖师。在一座希腊厕所里,他咽了最后一口气,安乐死[26]。戴着镶有珠子的主教冠,手执牧杖[27],纹丝不动地跨在他的宝座上;他成了鳏夫,主教的职位也守了寡[28]。主教饰带[29]硬挺挺地翘起来,臀部净是凝成的块块儿。
微风围着他嫡戏,砭人肌肤的凛例的风[30],波浪涌上来了。有如白鬃的海马,磨着牙齿,被明亮的风套上笼头,马南南[31]的骏马们。
我可别忘了他那封写给报社的信。然后呢?十二点半钟去。船记”。至于那笔款呢,省着点儿花,乖乖地像个小傻瓜那样。对,非这么着不可。
他的脚步放慢了。到了。我去不去萨拉舅妈那儿呢?我那同体的父亲的声音。最近你见那位艺术家哥哥斯蒂芬一眼了吗?没见到?他该不是到斯特拉斯堡高台街找他舅妈萨利[32]去了吧?难道他不能飞得更高一点儿吗,呢?还有,还有,还有,斯蒂芬,告诉我们西[33]姑父好吗?啊呀,哭泣的天主,我都跟些什么人结上了亲家呀。男娃子们在干草棚里。酗酒的小成本会计师和他那吹短号的兄弟。可敬的平底船船夫[34]!还有那个斗鸡眼沃尔特,竟然对自己的父亲以 “先生”相称。先生。是的,先生。不,先生。耶稣哭了[35]:这也难怪,基督啊。
我拉了拉他们那座关上百叶窗的茅屋上气不接下气的门铃,等着。他们以为讨债的来了,就从安全的地方[36]朝外窥伺。
“是斯蒂芬,先生。”
“让他进来。让斯蒂芬进来。”
门栓拉开了,沃尔特把我让进去。
“我们还只当是旁人呢。”
一张大床,里奇舅舅倚着枕头,裹在毛毯里,隔着小山般的膝盖,将壮实的手臂伸过来。胸脯干干净净。他洗过上半身。
“外甥,早晨好[37]。”
他把膝板放到一旁。他正在板上起草着拿给助理法官戈夫和助理法官沙普兰·坦迪看的讼费清单,填写着许可证、调查书以及携带物证出庭的通知书。在他那歇了顶的头上端,悬挂着用黑樫木化石做的镜框。王水德的《安魂曲》[38]。他吹着那令人困惑的口哨,单调而低沉,把沃尔特唤了回来。
“什么事,先生?”
“告诉母亲,给里奇和斯蒂芬端麦牙酒来。她在哪儿?”
“给克莉西洗澡呢,先生。”
跟爸爸一道睡的小伴儿,宝贝疙瘩。
“不要,里奇舅舅……”
“就叫我里奇吧。该死的锂盐矿泉水。叫人虚弱。喔[威]士忌!”
“里奇舅舅,真地……”
“坐下吧,不然的话,我就凭着魔鬼的名义把你揍趴下。”
沃尔特斜睨着眼找椅子,但是没找到。
“他没地方坐,先生。”
“他没地方放屁股吗,你这傻瓜。把咱们的奇彭代尔[39]式椅子端过来。想吃点儿什么吗?在这里,你用不着摆臭架子。来点儿厚厚的油煎鲱鱼火腿片怎样?真的吗?那就更好啦。我们家除了背痛丸,啥都没有。”
当心哪!
他用低沉单调的声音哼了几小节费朗多的“出场歌”[40]。斯蒂芬,这是整出歌剧中最雄伟的一曲。你听。
他又吹起那和谐的口哨来了,音调缓和而优雅,中气很足,还抡起双拳,把裹在毛毯中的膝盖当大鼓来敲打。
这风更柔和一些。
没落之家[41],我的,他的,大家的。你曾告诉克朗戈伍斯那些少爷,你有个舅舅是法官,还有个舅舅是将军。斯蒂芬,别再来这一套啦。美并不在那里。也不在马什图书馆[42]那空气污浊的小单间里。你在那儿读过约阿基姆院长[43]那褪了色的预言书。是为谁写的?为大教堂院内那长了一百个头的乌合之众。一个憎恶同类者[44]离开他们,遁入疯狂的森林,鬃毛在月下起着泡沫,眼珠子像是星宿。长着马一般鼻孔的胡乙姆[45]。一张张椭圆形马脸的坦普尔、勃克·穆利根、狐狸坎贝尔、长下巴颏儿[46]。隐修院院长神父,暴跳如雷的副主教[47],是什么惹得他们在头脑里燃起怒火?呸!下来吧,秃子,不然就剥掉你的头皮[48]。他那有受神惩之虞的头上,围着一圈儿花环般的灰发,我看见他往下爬,爬到祭台脚下(下来吧[49]!),手执圣体发光 [50],眼睛像是蛇怪[51]。下来吧,秃瓢儿!这些削了发、除了圣油、被阉割、靠上好的麦子[52]吃胖了的、靠神糊口的神父们,笨重地挪动着那穿白麻布长袍的魁梧身躯,从鼻息里喷出拉丁文。在祭台四角协助的唱诗班用威胁般的回声来响应。
同一瞬间,拐角处一个神父也许正举扬着圣体。叮玲玲[53]!相隔两条街,另一位把它放回圣体柜,上了锁。叮玲玲!圣母小教堂里,又一个神父正在独吞所有的圣体。玎玲玲!跪下,起立,向前,退后。卓绝的博士丹·奥卡姆[54]曾想到过这一点。英国一个下雾的早晨,基督人格问题这一小精灵搔挠着他的头脑。他撂下圣体,跪下来。在他听见自己摇的第二遍铃声与十字形耳堂里的头一遍铃声(他在举扬圣体)而站起来时,又听见(而今我在举扬圣体了)这两个铃的响声(他跪下了)重叠成双元音。
表弟斯蒂芬,你永远也当不成圣人。这是圣者的岛屿[55]。你从前虔诚得很,对吗?你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祈求她不要叫你的鼻子变红。你曾在蛇根木林荫路[56]上向魔鬼祈求,让前面那个矮胖寡妇走边水洼子时把下摆撩得更高一些。啊,可不是嘛[57]!为了那些用别针别在婆娘腰身上的染了色的节片,出卖你的灵魂吧。务必这么做。再告诉我一些,再说说!当你坐在驰往霍斯[58]的电车的顶层座位上时,曾独自对着雨水喊叫道:一丝不挂的女人!一丝不挂的女人!那是怎么回事,呃?
那又怎么啦?难道女人不就是为了这个而被创造的吗?
每天晚上从七本书里各读上两页,呃?我那时还年轻。你对着镜子朝自己鞠躬,脸上神采奕奕,一本正经地走上前去,好像要接受喝彩似的。十足的大傻瓜,万岁!万岁!谁都不曾看见,什么人也别告诉。你打算以字母为标题写一批书来着。你读过他的F吗?哦,读过,可是我更喜欢Q。对,不过W可精彩啦。啊,对, W。还记得你在椭圆形绿页上所写的深奥的显形录[59]吗?深刻而又深刻。倘若你死了,抄本将被送到世界上所有的大图书馆去,包括亚历山大在内。几千年后,亿万年后,仍将会有人捧读,就橡皮克·德拉·米兰多拉[60]似的。对,很像条鲸[61]。当一个人读到早已作古者那些奇妙的篇章时,就会感到自己与之融为一体了,那个人曾经……
粗沙子已经从他脚下消失了。他的靴子重新踩在咯吱一声就裂开来的湿桅杆上,还踩着了竹蛏,发出轧轹声的卵石,被浪潮冲撞着的无数石子[62],以及被船蛆蛀得满是窟窿的木料,溃败了的无敌舰队[63]。一滩滩肮里肮脏的泥沙等着吸吮他那踏过来的靴底,污水的腐臭气味一股股地冒上来。[一簇海藻在死人的骨灰堆底下闷燃着海火[64]。]他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一只竖立着的黑啤酒瓶半埋在瓷实得恰似揉就的生面团的沙子里。奇渴岛上的岗哨。岸上是破碎的箍圈;陆地上,狡猾的黑网布起一片迷阵;再过去就是几扇用粉笔胡乱涂写过的后门,海岸高处,有人拉起一道衣绳,上面晾着两件活像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衬衫。林森德[65]那些晒得黧黑的舵手和水手长的棚屋。人的甲壳。
他停下脚步。我已经走边了通往萨拉姑妈家的路口。我不去那儿吗?好像不去。四下里不见人影儿。他拐向东北,从硬一些的沙地穿过,朝鸽房[66]走去。
“谁使你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是由于鸽子,约瑟。”[67]
回家度假的帕特里克在麦克马洪酒吧跟我一道暖热牛奶。巴黎的“野鹅”[68]凯文·伊根[69]的儿子。我的老子是鸟儿[70]。他用粉红色的娇嫩舌头舔着甜甜的热奶[71],胖胖的兔子脸。舔吧,兔子[72]。他巴望中头彩[73]。关于女子的本性,他说是读了米什莱[74]的作品。然而他非要把利奥·塔克西尔先生的《耶稣传》[75]寄给我不可。借给他的一个朋友了。
“你要知道,真逗。我呢,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相信天主的存在。可不要告诉我父亲。”
“他信吗?”
“父亲吗,他信[76]。”
够啦[77]。他在舔哪。
我那顶拉丁区的帽子。天哪,咱们就得打扮得像个人物。我需要一副深褐色的手套。你曾经是个学生,对吧?究竟念的是什么系来着?皮西恩。P·· [78],你知道:物理、化学和生物[79]。哎。跟那些打抱嗝的出租马车车夫们挤挤碰碰在一块儿吃那廉价的炖牛肺[80],埃及肉锅[81]。用最自然的腔调说:当我住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82]时,我经常。对,身上经常揣着剪过的票。倘若你在什么地方被当作凶杀嫌疑犯给抓起来,好用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司法神圣。一九0四年二月十七日晚上,有两个证人目击到被告。是旁人干的,另一个我。帽子,领带,大衣,鼻子。我就是他[83]。你好像自得其乐哩。
昂首阔步。你试图学谁的模样走路哪?忘掉吧,穷光蛋。揣着母亲那八先令的汇款单,邮局的司阍朝你咣当一声摔上了门。饿得牙痛起来。还差两分钟哪 [84]。瞧瞧钟呀。非取不可。关门啦[85]。雇佣的走狗!用散弹枪砰砰地给他几梭子,把他打个血肉横飞,人肉碎片溅脏了墙壁统统是黄铜钮扣。满墙碎片哔哔剥剥又嵌回原处。没受伤吗?喏,那很好。握握手。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了吗?哦,那很好。握一握。哦,一切都很好。
你曾有过做出惊人之举的打算,对吗?继烈性子的高隆班[86]之后,去欧洲传教。菲亚克[87]和斯科特斯[88]坐在天堂那针毡般的三脚凳 [89]上,酒从能装一品脱的大缸子里洒了出来,朗朗发出夹着拉下文的笑声。妙啊!妙啊!你假装把英语讲得很蹩脚,沿着纽黑文[90]那泥泞的码头,抱着自己的旅行箱走去,省得花三便士雇脚夫。怎么[91]?你带回了丰富的战利品;《芭蕾短裙》[92],五期破破烂烂的《白长裤与红短裤》[93],一封蓝色的法国电报,足以炫耀一番的珍品:
母病危速回父
姑妈认为你母亲死在你手里,所以她不让……[94]
为穆利根的姑妈,干杯!
容我说说缘由。
多亏了她,汉尼根家,
样样循规蹈矩。[95]
他忽然用脚得意地打起拍子,跨过沙垄,沿着那卵石垒成的南边的防波堤走去。他洋洋自得地凝视着那猛犸象的头盖骨般的垒起来的石头。金光洒在海洋上,沙子上,卵石上。太阳就在那儿,细溜儿的树木,柠檬色的房舍。
巴黎刚刚苏醒过来了,赤裸裸的阳光投射到她那柠檬色的街道上。燕麦粉面包那湿润的芯,蛙青色的苦艾酒,她那清晨的馨香向空气献着殷勤。漂亮男人 [96]从他妻子之姘夫的老婆那张床上爬了起来,包着头巾的主妇手持一碟醋酸,忙来忙去。罗德的店铺里,伊凡妮和玛德琳用金牙嚼着油酥饼[97],嘴边被布列塔尼蛋糕[98]的浓汁[99]沾黄了,脂粉一塌糊涂,正在重新打扮。一张张巴黎男人的脸走了过去,感到十分便意的讨她们欢心者,鬈发的征服者 [100]。
晌午打盹儿。凯文·伊根用被油墨弄得污迹斑斑的手指卷着黑色火药烟丝,呷着他那绿妖精,帕特里斯喝的则是白色的[101]。在我们周围,老饕们把五香豆一叉子一叉子地送下食道。来一小杯咖啡[102]!咖啡的蒸气从打磨得锃亮的大壶里喷出来。他一招呼,她就来侍候我。他是爱尔兰的。荷兰的?不是奶酪。两个爱尔兰人,我们,爱尔兰,你明白了吗?啊,对啦[103]!她还以为你要叫一客荷兰[104]奶酪呢。就是你那饭后的[105]。你晓得这个词儿吗?饭后的。以前在巴塞罗那,我认识一个古怪的家伙,他常把这叫作饭后的。好的,干怀[106]!一张张嵌着石板面的桌子周围,酒气和咽喉的呼噜声混在一起。他的呼吸弥漫在我们那沾着辣酱油的盘子上空。绿妖精的尖牙从他的嘴唇里龇出来。谈到爱尔兰,达尔卡相斯一家[107],谈到希望、阴谋和现在的阿瑟· 格里菲思[108][以及A·E·[109],派曼德尔,人类的好牧人[110])。要把我也套进去,充当他的轭友,大谈什么我们的罪孽啦,我们的共同事业啦。你不愧为你父亲的儿子。一听声音我就知道。他身上穿的是件印有血红色大花的粗斜纹布衬衫,每当他吐露秘密时,西班牙式的流苏就颤悠。德鲁蒙 [111]先生,著名的新闻记者德鲁蒙,你知道他怎么称呼维多利亚女王吗?满嘴黄板牙的丑婆子。长着黄牙齿[112]的母夜叉[113]。莫德·冈内 [114],漂亮的女人;《祖国》[115],米利沃伊[116]先生;费利克斯·福尔[117],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一帮好色之徒。在乌普萨拉 [118]的澡堂。一个未婚女子[119],打杂女侍[120]替赤条条的男人按摩。她说,对所有的先生我都这么做[121]。我说,这位先生[122] 免了吧。这是再淫荡不过的习俗。洗澡是最不能让人看到的。连我弟兄,甚至亲弟兄,都不能让他看到。太猥亵了。绿眼睛[123],我看见了你。尖牙 [124],我感觉到了。一帮好色之徒。
蓝色的引线在两手之间炽热地燃着,火苗透亮透亮的。卷得松松的烟丝点燃了:火焰和呛人的烟把我们这个角落照亮了。晓党[125]式的帽子底下,露出脸上那粗犷的颧骨。核心领导[126]是怎么逃之夭夭的呢?有个可靠的说法。化装成年轻的新娘,你呀,纱啊,桔花啊,驱车沿着通向乌拉海德[127]的路疾驰而去。确实是这样的。败退了的首领[128]们啦,被出卖者啦,不顾一切的逃遁啦。伪装,急不暇择,逃走了,不在这里啦。
遭到冷落的情人,不满你说,当年我曾是个魁梧结实的年轻小伙子哩,等哪一天我把相片拿给你看。确实是这样。他作为一个情人,由于热恋她,就跟族长的后继者[129]理查德·伯克上校一道溜着克拉肯韦尔[130]的大墙下走。正蜷缩在那里的当儿,只见复仇的火焰把那墙壁炸得飞到雾中。玻璃碎成碴儿,砖石建筑坍塌下来。他隐遁在灯红酒绿的巴黎。巴黎的伊根,除了我,谁也不来找他。他每天的栖身之所是,肮脏的活字箱,经常光顾的三家酒馆,还有睡上一会儿觉的蒙特马特的窝,那是在金酒街[131]上,用脸上巴着苍蝇屎的死者肖像装饰起来。没有爱情,没有国土,没有老婆。她呢,被驱逐出境的男人不在身边,却也过得十分舒适自在。圣心忆街[132]上的房东太太养着一只金丝雀,还有两个男房客,桃色腮帮子,条纹裙子,欢蹦乱跳得像个年轻姑娘。尽管被赶了出来,他并不绝望。告诉帕特[133]你看见了我,好吗?我曾经想给可怜的帕特找工作来着。我的儿子[134],让他当法国兵。我教会了他唱《基尔肯尼的小伙子,个个是健壮的荡子》。会唱这首古老的民谣吗?我教过帕特里斯。古老的基尔肯尼,圣卡尼克教堂,那是诺尔河衅的强弓[135]的城堡。这么唱。噢,噢。纳珀 ·坦迪[136]握住了我的手。
噢,噢,基尔肯尼的
小伙子……
一只瘦削、赢弱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他们忘掉了凯文·伊根,他却不曾忘记他们。想起了你。噢,锡安[137]。
他走近海滨,靴子踩在湿沙子上吱吱作响。新鲜空气拨弄着粗犷神经的弦来迎迓他。野性的风所撒下的光明的种子。喏,我该不是正走向基什[138]的灯台船吧?他摹地站住了,两只脚徐徐陷进松软的泥沙。折回去吧。
他过往回走,边打量着南岸,双脚又缓缓地踩进新坑里。塔里的那间冰冷、拱顶的屋子在等待着他。从堞口射进来的两束阳光不断地移动着,缓慢得就像我那不断地往下陷的双脚,沿着日晷般的石板地爬向黄昏。夜幕降临了,蓝色的薄暮,湛蓝的夜晚,他们在黑暗的穹隆下等待着,杯盘狼藉的餐桌周围,是他们那推到后面的椅子和我那只方尖碑形手提箱。谁去拾掇?钥匙在他手里。今天入夜后,我不在那儿睡。沉默之塔的一扇紧闭的大门,把他们那盲目的肉体埋葬在里面。黑豹老爷和他的猎犬[139]。呼唤嘛,没有回应。他从沙坑里拨出脚,沿着卵石垒成的防波堤[140]踱回去。全拿去,你们统统留下好了。我的灵魂和我一道走,形态的形态。这样,在月光厮守着的夜晚,我身穿沫浴着银光的黑貂服,沿着巉岩上的小径走去,并倾听艾尔西诺那诱人的潮水声[141]。
涨上来的潮水尾随着我。我从这里可以看见它流过去了。那么,顺着普尔贝各路折回到那边的岸滩去吧。他踏过蓑衣草与鳝鱼般黏滑的海藻,坐在凳子形的岩石上,并将自己那梣木手杖搭在岩隙里。
一具胀得鼓鼓的狗尸耷拉着四肢趴在狸藻上。前面是船舷的上椽,船身已埋在沙里。路易·维伊奥称戈蒂埃的散文为埋在沙子里的公共马车[142]。这沉重的沙子乃是潮与风在此积累而成的一种语言。那是已故建筑师垒起的石壁,成了鼬鼠的隐身处。在那儿埋金子吧。不妨试试看。你不是有一些吗。沙子和石头。被岁月坠得沉甸甸的。巨人劳特[143]爵士的玩具。小心不要挨个耳刮子。俺是血腥的棒巨人,把那些血腥的棒巨石统维推滚过来,铺成俺的踏脚石。吭,吭。俺闻见了爱尔兰人的血腥味。
一个小点点,一只活生生的狗映入眼帘,越变越大,从沙滩那头跑过来了。唉呀!难道它要朝我袭击吗?尊重它的自由。你不会成为旁人的主人或奴隶。我有这根手杖。坐着别动。从遥远的彼方,两个人影正背着冒白沫的潮水走向岸滩。两个女土著[144]。她们把它妥藏在宽叶香蒲从中了。玩捉迷藏。我看了你们啦。不,是狗。它正朝着她们跑回去。是谁呀?
一艘艘湖上人的大帆船曾驶到这岸边,来寻觅掠夺品[145]。它们那血红的喙形船首,低低地停泊在融化了的锡镴般的碎浪里。玛拉基系着金脖套的年月里[146]。丹麦海盗胸前总闪烁着战斧形的金丝项圈。炎热的晌午,一群表皮光滑的鲸困在浅滩上喷水,满地翻滚。于是,穿着紧身皮坎肩的矮个子们,我的同族就成群结队地从饥饿的牢笼般的城里冲出来。他们手执剥皮用的小刀,奔跑、攀登、劈砍那满是肥厚的绿色脂肪的鲸肉。饥荒、瘟疫和大屠杀。他们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血管里,他们的情欲在我身上骚动。在冰封的利菲河上,我在他们当中活动[147]。我,一个习性无常的人,被松脂噼啪作响的火把映照着。我跟谁都不曾搭话,也没有人跟我攀谈。狗吠着向他奔来,停住,又跑了回去。我的仇人的狗。我脸色苍白,只是站在那儿,一声不响,随它吠去。你的作为何等可畏 [148]。身穿淡黄色心的命运之奴仆[149],看到我的恐惧,泛出微笑。你渴望的就是他们那狗吠般的喝彩吗?篡位者们,随他们怎么去生活吧。布鲁斯的弟弟[150];绢骑士托马斯·菲茨杰拉德[151];约克家的伪继承人珀金·沃贝克[152],穿着白玫瑰纹象牙色绸马裤,昙花一现;还有兰伯特·西姆内尔[153]加了冕的厨房下手,他的扈从是一群女仆和随军酒食小贩。统统都是国王的子嗣。自古至今,此地是僭君的乐园。他[154]搭救了快要溺死的人们,你呢,听到一条野狗叫唤也瑟瑟发抖。然而曾嘲笑来自圣迈克尔大教堂的圭多的那些朝臣们,是在自己的老家里。……的老家[155]。我们完全不希罕你们那中世纪装模作样的考证癖。他干过的,你干得了吗?假定附近就有只船。当然[156],那儿还会为你摆个救生圈。你干不干?九天前有个男子在少女岩的海面上淹死了。他们正等着尸体浮上来。说实话吧,我想干。我想试一试。我不擅长凫水。水冰凉而柔和。当我在克朗戈伍斯把脸孔进一脸盆水星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谁在我背后哪?快点上来,快点上来!你没看见潮水从四面八方迅疾地往上涨吗?刹那间就把浅滩变成一片汪洋,颜色像椰子壳。只要我的脚能着地,我就想救他一命,但也要保住我自己的命。一个即将淹死的人。他的眼睛从死亡的恐怖中向我惊呼。我……跟他一道沉下去……我没能救她[157]。水,痛苦的死亡; 消逝了。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我瞧见她的裙子了。准是用饰针别着的。
他们的狗在被潮水漫得越来越窄的沙洲上到处游荡,小跑着,一路嗅着。它在寻觅着前世所失去的什么东西。它猛地像跳跃着的野兔一般蹿过去,耳朵向后掀着,追逐那低低掠过的海鸥的影子。男人尖细的口哨声传到它那柔软的耳朵里。它转身往回蹦,凑近了些,一闪一闪地迈着小腿,小跑着挨过来。一片黄褐色旷野上的一只公鹿,没有长角,优雅,脚步轻盈地蹿来蹿去。它在花边般的水滨停下来,前肢僵直,耳朵朝着大海竖起。它翘起鼻尖儿,朝着那宛如一群群海象般的浪涛声吠叫。波浪翻滚着冲着它的脚涌来,绽出许许多多浪峰,每逢第九个,浪头就碎裂开来,四下里迸溅着。从远处,从更远的地方,后浪推着前浪。
拾海扇壳的。他们涉了一会儿水,弯腰把他们的口袋浸在水里,又提起来,蹚着水上了岸。狗边吠着边向他们奔去,用后肢站着,伸出前爪挠他们。又趴下来,再用后肢站直,像熊似的默默地跟他们撒欢。当他们走向干燥些的沙洲时,尽管没去理睬那狗,它还是一直缠着他们,两颚之间气喘吁吁地址着狼一般的红舌头。它那斑驳的身躯在他们前头款款而行,随后又像头小牛犊那样一溜烟儿跑开了。那具尸骸挡住了它的去路。它停下步子,嗅了一阵,然后轻轻地绕着走了一圈; 是弟兄哩,把鼻子挨近一些,又兜了一圈,以狗特有的敏捷嗅遍了死狗那污泥狼藉的毛皮。狗脑壳。狗的嗅觉,它那俯阚着地面的眼睛,向一个巨大目标移动。唉,可怜的狗儿!可怜的狗儿的尸体就横在这里。
“下三烂!放开它,你这杂种!”
这么一嚷,狗就怯懦地回到主人跟前,它被没穿靴子的脚猛踢了一下,虽没伤着,却倦缩着逃到沙滩另一头。它又绕道踅回来。这狗并不朝我望,径自沿着防波堤的边沿跳跳蹦蹦,磨磨蹭蹭,一路嗅嗅岩石,时而抬起一条后腿,朝那块岩石撒上一泡尿。它又往前小跑,再一次抬起后腿,朝一块未嗅过的岩石迅疾地滋上几滴尿。真是卑贱者的单纯娱乐。接着,它又用后爪扒散了沙子,然后用前爪刨坑,泥沙四溅。它在那儿埋过什么哪,它的奶奶。它把鼻尖扎进沙子里,刨啊,溅啊,并停下来望天空倾听着,随即又拼命地用爪子刨起沙子。不一会儿它停住了,一头豹,一头黑豹,野杂种,在劫掠死尸。
昨天夜里他把我吵醒后,做的还是同一个梦吗?等一等。门厅是敞着的。娼妓街[158]。回忆一下。哈伦·拉希德[159]。大致想起来了。那个人替我引路,对我说话。我并不曾害怕。他把手里的甜瓜递到我面前。漾出微笑:淡黄色果肉的香气。他说,这是规矩。进来吧,来呀。铺着红地毯哩。随你挑。
红脸膛的埃及人[160]扛着口袋,踉踉跄跄踱着。男的挽起裤腿,一双发青的脚噼喳叭喳踩在冰冷黏糊糊的沙滩上,他那胡子拉碴的脖颈上是灰暗的砖色围巾。她迈着女性的步子跟在后边,恶棍和共闯江湖的姘头。她把捞到的东西搭在背上。她那赤脚上巴着一层松散的沙粒和贝壳碎片。脸被风刮皴了,披散着头发。跟随老公当配偶,朝着罗马维尔[161]走。当夜幕遮住她肉体的缺陷时,她就披着褐色肩巾,走边被狗屎弄脏了的拱道,一路吆唤着。替她拉皮条的正在黑坑的奥劳夫林小酒店里款待着两个都柏林近卫军士兵。吻她并讲江湖话,把她搂抱在怀里。哦,我多情的俏妞儿!她那件酸臭破烂的衣衫下面,是魔女般的白皙肌肤。那天晚上,在凡巴利小巷里,有一股由制革厂吹来的气味。
双手白净红嘴唇,
你的身子真娇嫩。
跟我一道睡个觉,
黑夜拥抱并亲吻。[162]
啤酒桶肚皮的阿奎那管这叫作阴沉的乐趣[163]。箭猪修士[164]。失足前的亚当曾跨在上面,却没有动情。随他说去吧:你的身子真娇嫩。这话丝毫也不比他的逊色。僧侣话,诵《玫瑰经》的念珠在他们的腰带上嘁嘁喳喳;江湖话,硬梆梆的金币在他们的兜里当榔当啷。
此刻正走过去。
他们朝我这顶哈姆莱特帽斜瞟了一眼。倘若我坐在这儿,突然间脱得赤条条的呢?我并没有。跨过世界上所有的沙地,太阳那把火焰剑尾随于后,向西边,向黄昏的土地移动[165]。她吃力地跋涉,schlepps、trains、drags、trases[166]重荷。潮汐被月亮拖曳着,跟
在她后面向西退去。在她身体内部淌着藏有千万座岛屿的潮汐。这血液不是我的,葡萄紫的大海[167],莆萄紫的暗色的海。瞧瞧月亮的侍女。在睡梦中,月潮向她报时,嘱她该起床了。新娘的床,分娩的床,点燃着避邪烛的死亡之床。凡有血气者,均来归顺[168]。他来了,苍白的吸血鬼。他的眼睛穿过暴风雨,他那蝙蝠般的帆,血染了海水,跟她嘴对嘴地亲吻[169]。
喏,把它记下来,好吗?我的记事簿[170]。跟她嘴对嘴地亲吻。不。必须是两人的嘴。把双方的牢牢粘在一起。跟她嘴对嘴地亲吻。
他那翕动的嘴唇吮吻着没有血肉的空气嘴唇:嘴对着她的子宫口。子宫,孕育群生的坟墓[171]。他那突出来的嘴唇吐出气来,却默默无语。哦嗬嗬,瀑布般的行星群的怒吼。作球状,喷着火焰,边吼边移向远方远方远方远方远方。纸。是纸币,见鬼去吧。老迪希的信。在这儿哪。感谢你的隆情厚谊,把空白的这头撕掉吧。他背对着太阳,屈下身去在一块岩石的桌子上胡乱写着。我已经是第二次忘记从图书馆的柜台上拿些便条纸了。
他弯下腰去,遮住岩石的身影就剩下一小截了。为什么不漫无止境地延伸到最远的星宿那儿去呢?星群黑魆魆地隐在这道光的后面,黑暗在光中照耀 [172],三角形的仙后座[173],穹苍。我坐在那儿,手执占卜师的梣木杖,脚登借来的便鞋。白天我呆在铅色的海洋之滨,没有人看得见我;到了紫罗兰色的夜晚,就徜徉在粗犷星宿的统驭下。我投射出这有限的身影,逃脱不了的人形影子,又把它召唤回来。倘若它漫无止境地延伸,那还会是我的身影,我的形态的形态吗?谁在这儿守望着我呢?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读到我写下的这些话?白地上的记号。在某处,对某人,音色宛若用长笛吹奏出来的。克洛因的主教[174] 大人从他那顶宽边铲形帽里掏出圣堂的幔帐:空间的幔帐,上面有着彩色的纹章图案。使劲拽住。在平面上着了色,是的,就是这样。我看看平面,然后设想它的距离,是远还是近。我看看平面,东方,后面。啊,现在看吧!幕突然落下来了,幻象冻结在实体镜上。戏法咔嗒一声就要完了。你觉得我的话隐晦。你不认为我们的灵魂里有着含糊不清的东西吗?像长笛吹出的优美音色。我们的灵魂被我们的罪孽所玷污,越发依附我们,正如女人拥抱情人一般,越抱越紧。
她信任我,她的手绵软柔和,眼睛有着长长的睫毛。而今我真不像话,究竟要把她带到幕幔那边的什么地方去呢?进入无可避免的视觉认知那无可避免的形态里。她,她,她。怎样的她?就是那个黄花姑娘,星期一她在霍奇斯·菲吉斯书店的橱窗里寻找你将要写的一本以字母为标题的书。你用敏锐的目光朝她瞥了一眼。她的手腕套在阳伞上那编织成的饰环里。她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姑娘,住在利逊公园,心情忧郁,是个有些轻浮的姐儿。跟旁人谈这去吧,斯蒂维,找个野鸡什么的 [175]。但是她准穿着那讨厌的缀有吊袜带的紧身褡和用粗糙的羊毛线织成的浅黄长袜。跟她谈谈苹果布丁的事例更好一些[176]。你的才智到哪儿去啦?
抚摩我,温柔的眼睛。温柔的、温柔的、温柔的手。我在这儿很寂寞。啊。抚摩我,现在马上就摸。大家都晓得的那个字眼儿是什么来看[177]?我在这儿完全是孤零零的,而且悲哀。抚摩我,抚摩我吧。
他直着身子仰卧在巉岩上,把匆忙中写的便条和铅笔塞进兜里,将帽子拉歪,遮上眼睛。伊然是凯文·伊根打磕睡时的动作,安息日的睡眠。天主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非常好[178]。喂!日安[179]!欢迎你如五月花[180]。从帽檐底下,他隔着孔雀毛一般颤悠的睫毛眺望那向南移动的太阳。我被这炽热的景物迷住了。潘[181]的时刻,牧神的午后[182]。在饱含树脂的蔓草和滴着乳汁的果实间,在宽宽地浮着黄褐色叶子的水面上。痛苦离得很远。
不要再扭过脸儿去忧虑。
他的视线落在宽头长统靴上,一个花花公子[183]丢弃的旧物,并列着[184]。他数着皮面上的皱纹,这曾经是另一个人暖脚的窝。那脚曾在地上路着拍子跳过庄严的祭神舞[185],我讨厌那双脚。然而,当埃丝特·奥斯瓦特的鞋刚好合你的脚时,你可高兴啦。她是我在巴黎结识的一位姑娘。哎呀,多么小的一双脚[186]!忠实可靠的朋友,贴心的知己,王尔德那不敢讲明的爱[187]。他的胳膊,克兰利的胳膊。而今他要离我而去。该归咎于谁?我行我素。我行我素。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188]。
像是倒一根长套索似的,水从满满当当的科克湖[189]里溢了出来,将发绿的金色沙滩淹没,越涨越高,滔滔滚滚流去。我这根梣木手杖也会给冲走的。且等一等吧。不要紧的,潮水会淌过去的,冲刷着低矮的岩石;淌过去,打着漩涡,淌过去。最好赶紧把这档子事干完。听吧,四个宇组成的浪语,嘶——嗬——嘘 ——噢。波涛在海蛇、腾立的马群和岩石之间剧列地喘着气。它在岩石凹陷处迸溅着:唏哩哗啦,就像是桶里翻腾的酒。随后精力耗尽,不再喧嚣。它潺潺涓涓,荡荡漾漾,波纹展向四周,冒着泡沫,有如花蕾绽瓣。
在惊涛骇浪的海潮底下,他看到扭滚着的海藻正懒洋洋地伸直开来,勉强地摇摆着胳膊,裙裾撩得高又高[190],在窃窃私语的水里摇曳并翻转着羞怯的银叶。它就这样日日夜夜地被举起来,浮在海潮上,接着又沉下去。天哪,她们疲倦了。低声跟她们搭话,她们便叹息。圣安布罗斯[191]听见了叶子与波浪的叹息,就伫候着,等待时机成熟。它忍受着伤害,日夜痛苦呻吟[192]。漫无目的地凑在一起;然后又徒然地散开,淌出去,又流回来。月亮朦朦胧胧地升起,裸妇在自己的宫殿里发出光辉,情侣和好色的男人她都看腻了,就拽起海潮的网。
那一带有五噚深。你的父亲躺在五噚深处。他说是一点钟[193]。待发现时已成为一具溺尸。都柏林沙洲涨了潮。尸体向前推着轻飘飘的碎石,作扇状的鱼群和愚蠢的贝壳。自得像盐一样的尸体从退浪底下浮上来,又一拱一拱的,像海豚似地漂向岸去。就在那儿。快点儿把它勾住。往上拽。虽然它已沉下水去,还是捞着了。现在省手啦。
尸体泡在污浊的咸水里,成了瓦斯袋。这般松软的美味可喂肥了大群鲦鱼。它们嗖嗖地穿梭于尸首中那扣好钮扣的裤档隙缝间。天主变成人,人变成鱼,鱼变成黑雁,黑雁又变成堆积如山的羽绒褥垫[194]。活人吸着死者呼出来的气,踏着死者的遗骸,贪婪地吃着一切死者那尿骚味的内脏。隔着船帮硬被拽上来的尸首,散发出绿色坟墓似的恶臭。他那患麻风病般的鼻孔朝太阳喷着气。
这是海水的变幻[195],褐色眼睛呈盐灰色。溺死在海里,这是亘古以来最安详的死。啊,海洋老爹。巴黎奖[196]。谨防假冒。你不妨试试看。灵验得很哪。
喏,我口渴[197]。云层密布[198]。哪儿也没有乌云,有吗?雷雨。我说,永不沉落的晓星[199]。傲慢的智慧之闪电,被火焰包围着坠落 [200]。没有。我那顶用海扇壳装饰的帽子、手杖和既是他的也是我的草鞋[201]。踱向何方?踱向黄昏的国土。黄昏即将降临。
他攥住梣木手杖的柄,轻轻地戳着,继续磨磨蹭蹭。是啊,黄昏即将降临到我内心和外部世界。每一天都必有个终结。说起来,下星期二是白昼最长的一天 [202]。在快活的新年中,妈妈[203],啷,嘡,啼嘚嘀,嘡。草地·丁尼生[204],绅士派头的诗人。有着黄板牙的丑婆子[205]。可不是嘛 [206]。还有德鲁蒙[207]先生,绅士派头的记者。可不是嘛[208]。我的牙糟透了。我纳闷,怎么回事呢?摸了摸。这一颗也快脱落了。只剩了空壳。我不晓得要不要用那笔钱去看牙医?那一颗,还有这一颗。没有牙齿的金赤是个超人[209]。为什么这么说呢?或许有所指吧?
我记得,他把我那块手绢丢下了。我捡起它来了没有?
他徒然地在兜里掏了一番。不,我没有捡。不如再去买一块。
他把从鼻孔里抠出来的干鼻屎小心翼翼地放在岩角上。变成功了请喝彩[210]。
后面,兴许有人哩。
他回过头去,隔着肩膀朝后望:一艘三桅船[211]上那高高的桅杆正在半空中移动着。这艘静寂的船,将帆收拢在桅顶横桁上,静静地道潮驶回港口。
第三章 注释
[1]亚理斯多德认为,每一物体,每一个单一的实物,都是两种本原(物质和形态)所构成,例如铜像是由赋有一定形态的铜做成的。
[2]“各种事物的标记”是德国神秘主义者雅各布?伯梅(1575一1624)的话。
[3]爱尔兰哲学家、物理学家和主教乔治?伯克利(1685一1753)在《视觉新论》(1709)中提出,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带色的记号”,却把它们当成了物体本身。
[4]“有学识者的导师”原文为意大利语,指亚理斯多德,见但丁《神曲?地狱》第4篇。
[5]、[7]、[8]原文为德语,均套用德国戏剧家、评论家戈特尔德?埃弗赖姆?莱辛(1725一1871)的话。他认为画所处理的是物体(在空间中的)并列(静态),而动作(即在时间中持续的事物)是诗所特有的题材。见《拉奥孔》第15、16章,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6]“濒临……巅”一语,引自《哈姆莱特》第1幕第4场。
[9]巨匠(Los)是布莱克所著《巨匠之书》(1795)中的天神。
[l0]原文为希腊文,是柏拉图《蒂迈欧》篇中所载的世界创造者。
[11]沙丘是都柏林市东南的海滨。
[12]原文作Madelihemare,与当时还健在的法国水彩画家MadeleineLemaire(1845一1928)的姓名发音相近。只是把原名中的Le改成了the。下面引用时又抽掉了Ma二字,译出来就是“达琳”。
[13]原文为意大利语。
[14]“以迨永远,及世之世””是《圣三光荣颂》的最后两句。
[15]原文为德语。
[16]自由区原指封建时代教会领地附近的地区,不属于总督管辖,故名。后来范围逐渐缩小,及至一九0 四年只剩下位于利菲河南岸都柏林中心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周围的贫民窟。
[17]原文为希腊文。参看第一章注[84]。
[18]伊甸城是斯蒂芬给伊甸园取的名字。阿列夫和阿尔法分别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字母表首字音的音译,相当于英文的a。
[19]原文作Heva,希伯来文,意思是生命,系夏娃最早的称法。
[2O]《旧约全书?雅歌》第7章第2节:“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
[21]“从亘古到永远”一语,见《诗篇》卷4第90篇第2节。
[22]这里把《尼西亚信经》中的话颠倒,原话指耶稣:“是受生的,不是被造的。”
[23]原文为拉丁文,出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作于1265-1273)。
[24]“试图一显身手”,出自哈姆莱特王子在母后的寝宫里对她说的话。原指寓言中的猴子试图一显身手,到屋顶上去开了笼门。见《哈姆莱特》第3幕第4场。
[25]这是作者自造的复合词,由三十六个字母组成。将主张三位一体的“圣体共在论”一词中的“圣体”二字抽掉,又在“共在”和“论”之间插入“变体”“赞美”(指圣母赞美歌)“攻击”“犹太”等词。旨在暗示早期基督教对教义的不同解释引起的种种混乱。
[26]原文是拉丁文。阿里乌在就和解问题与教会商谈期间,猝死于君士坦丁堡街头厕所里。
[27]牧杖是主教职称。阿里乌是基督教司铎,曾任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长老。他非但未能升为主教,还被宣布为异端分子,于三二一年被撤职。
[28]这里把阿里乌比作丈夫,把主教的职位比作妻子。
[29]原文为拉丁文。这是主教佩带的白绸绣花饰带,从脖间搭到左肩上,下端垂及膝盖。
[30]“砭人肌肤的凛冽的风”出自霍拉旭在露台上对哈姆莱特说的话。参看《哈姆莱特》第1幕第4场。
[31]即爱尔兰神话中能够任意改变形状的海神马南南?麦克李尔。据说马恩岛(又译为曼岛,见第六章注[50])即得名于此神。马南南管理岛上乐园,庇佑海员,保障丰收。
[32]萨莉是萨拉的爱称。据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 第19页 ),萨利及其丈夫里奇?古尔丁,是以乔伊斯的大舅妈约瑟芬?吉尔特拉普?穆雷及其丈夫威廉?穆雷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威廉在科利斯-沃德律师事务所当会计师。他和内兄西蒙已绝交。他的弟弟是吹短号的,名叫约翰。见第十章注[124]。
[33]西是西蒙的爱称。这是里奇家的人所作的寒喧,而“我都跟些什么人结上了亲家呀!……”则是西蒙在背后议论里奇一家人的话。
[34]“可敬……船夫”一语出自英国喜剧作家威廉?施文克?吉尔伯特(1836-1911)与作曲家阿瑟?沙利文(1842-1900)合编的轻歌剧《平底船船夫》(1889)。西蒙把这用作对两位内弟的贬语。
[35]见《约翰福音》第l1章第35节。
[36]“安全的地方”出自班柯对苏格兰国王邓肯说的话。见《麦克白》第1幕第6场。
[37]在本书海德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32页倒l行)中,“早晨好” 下面还有“坐下来散散步”(爱尔兰习惯用语,指散散心)之句。但巴黎莎士比亚书屋一九二二年版,奥德赛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海德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饭,纽约加兰出版社《企鹅丛书》一九八四年饭和英国《企鹅二十世纪名著丛书》一九九二年版,均无此句。
[38]《安魂曲》和前文中的“携带物证出庭的传票”,原文均为拉丁文。《安魂曲》系王尔德于一八八一年为了悼念亡姊而写的诗。
[39]奇彭代尔是十八世纪英国家具大师,他的名字已成为英国洛可可式家具的同义语。最有名的奇彭代尔式样是宽座彩带式靠背椅。这里,里奇显然是在吹牛。
[40]原文为意大利语,这里指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吉乌塞佩?威尔第(1813-1901)之名作《游吟诗人》(1853)的男主人公费朗多出场后演唱的第一首咏叹调《离别歌》。首句为:“当心哪!”
[41]指费朗多所出身的家庭。他是这个“没落之家”的忠实维护者。
[42]马什图书馆在都柏林市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院内。
[43]约阿基姆?阿巴斯(约1130一约1202),即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意大利神秘主义者、神学家。曾任科拉卓隐修院院长。十三世纪中期方济各会属灵派以及十六世纪以前的许多修会都承认他所作的关于十三世纪的预言。
[44]指英国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西方文学评论界曾普遍认为斯威夫特憎恨人类,最后导致神经失常。其实他真正恨的是上层社会的腐败和罪恶。他早年就患有梅尼埃尔氏病,再加上晚年耳聋,一七四二年大病后又瘫痪了。
[45]胡乙姆是斯威夫特的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1726)中的智马。具有高度理性的智马们生活在宗法式的公社中,一切社员享有平等的权利。
[46]狐狸坎贝尔和长下巴颏儿是孩子们为一个耶稣会神父起的两个绰号。见《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4章。
[47]暴跳如雷的副主教指斯威夫特。一七一三年安妮女王任命他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副主教。他死后葬于该教堂墓地。
[48]这是约阿基姆预言中的话,原文为拉丁文。《旧约?列王纪下》第2章第23节有年轻人讥笑先知以利沙为秃子的描述。
[49]原文为拉丁文。
[50]圣体发光是供教徒瞻仰祝圣过的圣体用的金色容器,将圣体镶嵌在中央,作阳光四射状。
[51]蛇怪是希惜神话中出没于非洲沙漠的动物,其目光或呼气均足以使人丧命。
[52]见《旧约?申命记》第32章第14节:“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53]司铎举扬圣体时,助祭摇铃。
[54]丹?奥卡姆,丹(dan)是先生的古称,指威廉?奥卡姆(约1285-1349),英国经院派神学家。他是唯名论最著名的代表,主张神的存在和其他宗教信条不能靠理性来证明,它们纯粹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并认为圣体之所以代表耶稣的躯体是凭着信仰,而不是靠理性。(参看第一?章注[7] )本段中,斯蒂芬想到奥卡姆的这一论点,基督的躯体毕竟只有一个,怎么可能代表各个教堂内同时举扬的圣体。
[55]圣者的岛屿是中世纪时对爱尔兰的称呼。
[56]蛇根木林荫路在沙丘,位于都柏林东南郊。
[57]原文为意大利语。
[58]霍斯是爱尔兰都柏林郡内的一个半岛,海峡由古老的石英岩和页岩构成,与陆地之间有一条隆起的海滩连接。那里既是渔港,又是避暑胜地。下文中的“顶层座位”指双层公共车辆的上层座位。
[59]乔伊斯在他的早期作品《斯蒂芬英雄》(作者死后于1944年出版)中写道:显形系指潜在的灵感突然以具体形象显现出来。
[60]皮克?德拉?米兰多拉(1463一1494),意大利学者,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他以神秘哲学的理论维护基督教神学,曾从希腊、希伯来、阿拉伯和拉丁等文字的著作中搜集九百篇论文,其中十三篇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他的一篇讨论占星术的缺点的论文影响了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开普勒。
[61]这是《哈姆莱特》第3幕第2场中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回答哈姆莱特王子的话。王子说云彩像鲸,大臣也跟着说像。此语在这里的意思是:“唉,可不是嘛。”
[62]“冲撞着无数的石子”,套用爱德伽站在悬崖上所说的话,见《李尔王》第4幕第6场。
[63]指英国海军史上一大战绩。一五八八年,西班牙派遣由一百三十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驶到多佛海峡,准备入侵英国。然而在英国人的抗击下遭到重创,向北绕道苏格兰,逃经受尔兰,最后只有七十六艘船返回西班牙。这里,斯蒂芬从脚下的烂木料联想到当年毁在爱尔兰沿岸的那些船的残骸。
[64]海火指含磷的鬼火。[]内的句子系根据本书海德一九八九年版(第34页第27页至28行)补译的。
[65]林森德是都柏林市东岸的小渔村,位于注入都柏林湾的利菲河口。
[66]鸽房原是一座六角形要塞,后改为都柏林水电站。
[67]这两句对话,原文为法语。发问的是约瑟,回答的是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据《路加福音》第1章,玛利亚婚前,因天主圣灵降临到她身上而怀孕。鸽子是天主圣灵的象征。
[68]一六八九牛二月,英国议会宣布国王詹姆斯二世退位。二月,詹姆斯到达爱尔兰,在都柏林召开的议会承认他为国王。然而后来他被击败,保王派遂逃往欧洲大陆。他们被叫作“野鹅”。以后此词成了流落到欧洲大陆的爱尔兰亡命者的泛称。
[69]据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24页,凯文?伊根的原型是约翰?凯利。他曾以约翰?凯西一名,出现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书中。按凯西曾参加芬尼社(参看第二章注[54]),后流亡到巴黎。一九0 三年乔伊斯在巴黎经常与他见面。凯西之子帕特里斯正在法国军队中服役,有时参加乔伊斯与凯西的晤谈。
[70]当天早晨,勃克?穆利根唱的歌里有“爹是只鸟儿”之句。鸟儿指天主圣灵的象征――鸽子。
[71]、[72]、[73]原文为法语。
[74]朱尔斯?米什莱(1798-1874),法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爱情》(1858)和《妇女》(1860)二书是色情和说教的大杂烩。他还在作品中描述过参加法国革命运动的女斗士。
[75]《耶稣传》(1884)的作者是出生在法国的耶稣会士加布里埃尔?乔甘德-佩奇(1854一1907),他化名为利奥?塔克西尔,写过抨击教会的小册子。
[76]以上三句对话的原文均为法语。
[77]原文为德语。
[78]P??分别为法语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首字。
[79]、[80]原文为法语。
[8l]“埃及肉锅”代表美味的食品,《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第3节有“在埃及,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肉”一语。
[82]原文为法语。
[83]原文为法语,系模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的“朕即国家”语气,含有嘲讽意。
[84]、[85]原文为法语。
[86]高隆班,见第二章注[31]。
[87]圣菲亚克是守护园艺的圣徒,生于爱尔兰,六七0年左右死于法国。
[88]约翰?邓思?斯科特斯(约1266-1308),生于苏格兰的经院派神学家,是丹奥卡姆(见本章注[54])之师,主张尽可能把信仰和理性结合起来。
[89]“针毯般的三脚凳”,原文作creepystools,苏格兰教会里信徒忏悔时坐的三脚凳。
[90]纽黑文是英格兰东部位于乌斯河口一城镇,面临英吉利海峡,是斯蒂芬往返法国时必经的口岸。
[91]原文为法语。
[92]这是当时流行于巴黎的一种内容轻松的周刊。
[98]当时巴黎流行一种内容轻松的杂志《红短裤的生活》。法语“红短裤”(Culotte Rouge)又为“营妓”的俗称。
[94]这里,斯蒂芬回忆起当天早晨勃克?穆利根对他说的话。下半句是“我跟你有任何往来”,见第一章注[16]及有关正文。
[95]摘自爱尔兰流行歌曲作家珀西?弗伦奇(1854一1920)所作的《马修?汉尼根的姑妈》一歌。原歌中“穆利根”作“汉尼根”。
[96]原文为意大利语。
[97]-[100]原文为法语。布列塔尼是法国西北部同名半岛上的规划区。
[101]绿妖精是苦艾酒的俗称,白色的指牛奶。
[102]原文为巴黎俚语。照字面上翻译则是“来半赛蒂耶”。赛蒂耶是古代法升。一赛蒂耶约合两加仑。
[103]、[104]原文为法语。
[105]原文为拉丁文,指饭后的甜食。
[106]原文为爱尔兰语。
[107]达尔卡相斯一家是中世纪爱尔兰芒斯特的王族。
[108]阿瑟?格里菲思(1872一1922),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自由邦第一任总统(1922)。原在都柏林当排字工人。一八九九年创办以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为主旨的周刊《爱尔兰人联合报》。一九0五年他组织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次年将报纸也易名《新芬》;新芬是爱尔兰语SinnFein的音译,意即“我们自己”,也就是要建立“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见第一章注[34]。
[lO9][]内的句子系根据本书海德一九八九年版(第36页第15至16行)补译。A?E?即爱尔兰诗人、评论家、画家乔治?威廉?拉塞尔(1867-1935),他是当时健在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者之一。曾与叶芝、约翰?埃格林顿等人一道出版《爱尔兰通神论者》杂志,使用AEON(伊涌,参看第九章注[49])这一笔名。有一次,被误排为A.E.,他将错就错,就把它作为自己的另一笔名。派曼德尔是传授秘义的神,见第十五章注[458]。
[110]好牧人原是耶稣自况(见《约翰福音》第10章第l1节:“我是好牧人”),这里则是对格里菲思和拉塞尔等人的称赞,有“好带头人”的意思。拉塞尔也是爱尔兰的志士,组织过爱尔兰农业合作运动,积极参加独立运动。
[111]爱德华?阿道夫?德鲁蒙(1844-1917),法国新闻记者,他所编的《言论自由》报主张排斥犹太人。
[112]、[113]原文为法语。
[114]莫德?冈内(1865-1953),爱尔兰爱国志士,女演员,新芬党创始人之一。
[115]原文为法语,是一八四一年创刊的一份政治杂志。
[116]卢西恩?米利沃伊(1850-1918),法国政治家,一八九四年起任《祖国》杂志主编。
[117]费利克斯?福尔(1841-189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六任总统。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六日淬死于情妇的床上。
[118]乌普萨拉是瑞典中东部的乌普萨拉省省会,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面。
[119]原文为瑞典语。
[120]-[122]原文为法语。
[123]绿眼睛妖魔之略,指嫉妒,出自伊阿古对奥瑟罗说的话,见《奥瑟罗》第3幕第3场。
[124]尖牙是绿妖精尖牙之略,该酒因性烈遂有此称,一九一五年起在巴黎禁售。参看本章注[101]。
[125]晓党是十八世纪末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新教徒所组织的党派。 他们企图把信天主教的农民赶出阿尔斯特,时常在拂晓时分袭击其农舍,因而得名。橙带党(见第二章注[53])继承了他们的衣钵。
[126]核心领导指詹姆斯?斯蒂芬斯,参看第二章注[54]。
[127]乌拉海德是位于都柏林市以北九英里的村镇。
[128]这里套用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的《败退了的首领》(1845),只是把原诗中的单数改成了复数。
[129]凯尔特族的族长生前由年长或最有能力的人中选出后继者。
[130]克拉肯韦尔是英国人伦敦伊斯林顿自治市的毗邻地区。一八六七年三月五、六日,芬尼社成员举行起义。因缺乏武器,组织也不严密而失败。当年九月,理查德?奥沙利文?伯克上校因受芬尼社之托购买武器而被捕入狱。公审前,芬尼社的成员为了使他和关在同一座牢中的伊根(参看本章注[69])能够越狱,炸了监狱(事先曾关照他们躲在墙角,以免被炸伤)。那一次死伤多人,但监狱当局接到密告,临时改变了放风时间,越狱计划遂告失败。
[131]、[132]、[134]原文为法语。
[133]帕特是柏特里斯的昵称。
[135]基尔肯尼是爱尔兰基尔肯尼郡的首府。在都柏林以南六十三英里处, 有十二世纪建造的圣卡尼克大教堂。圣卡尼克(又名圣肯尼,约卒于599) 曾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传教。基尔肯尼一名得自纪念他的教堂。在爱尔兰语中,基尔是教堂。强弓是第二代彭布罗克伯爵理查?德克莱尔(约1130-1176)的绰号。他原是南威尔士贵族,经英王亨利二世批准,占领了整个爱尔兰。
[136]纳珀?坦迪(1740-1803),爱尔兰政治家、革命者、爱国志士。 一七九一年在都柏林参加创立爱尔兰人联合会支部。后流亡法国。一七九八年,法国政府派他回爱尔兰招募一支反抗英国人的军队。登陆后又折回,途径汉堡时被捕,并引渡给英国。在拿破仑的要求下获释。“噢、噢。纳珀?坦迪握住了我的手”是一七九0年开始流行的爱尔兰歌谣《穿绿衣》中的一句。原作者不详, 后经爱尔兰裔美国作曲家、剧作家戴恩?布奇考尔特(1822-1890)整理而成。
[137]锡安是耶路撒冷城内两山中的东边那座。《圣经》中多以锡安代表耶路撒冷城,后用以指犹太人的故土。这里,用锡安影射被占领的爱尔兰。《诗篇》第137篇第1节有云:“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锡安就禁不住哭了!”
[138]基什是位于都柏林湾南口的一道沙洲。
[139]黑豹老爷指海恩斯。由于勃克?穆利根成天跟在海恩斯后面,这里把他比作猎犬。参看第一章开头部分。
[140]这道防波堤的尽头筑有一座称作普尔贝格的灯塔。
[141]这里,斯蒂芬以哈姆莱特自况。在《哈姆莱特》第1幕第4场,霍拉旭曾劝哈姆莱特不要跟着鬼魂走,以免被诱到潮水里去。
[142]路易?维伊奥(1813一1883),法国作家,教皇至上主义者的领袖。西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新闻记者。“埋……车”,原文为法语。维伊奥在《真正的巴黎诗人》一文中说,戈蒂埃“文字拙劣……所有那些夸张的表现使他的句子看上去像是埋在沙子里的公共马车”。
[143]弗兰克?布捷恩在《詹姆斯?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的写作》(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饭)一书中指出,巨人劳特爵士是乔伊斯自已编造的传说。他还告诉布捷恩:“我的巨人劳特爵士长着满嘴石头,以代替牙齿,所以口齿不清。”(见该书第52-53页)
[144]原文作“thetwomaries”。在澳洲,mary作女士解。如果首字是大写,即为玛丽。“藏在香蒲从中”,暗指她们所藏的是孩子,《出埃及记》第2章第3节:“她……把孩子放在篮子里面,然后把篮子藏在河边芦苇丛里。”(参看第七章注[211])
[145]湖上人是爱尔兰人对自公元七八七年起入侵爱尔兰的挪威人的称呼。
[146]“玛拉基系着金脖套的年月里”,出自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1779-1852)的《让爱琳记住古老的岁月》一诗。玛拉基(948-1022)是个爱尔兰王,曾奋力抗击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并从他所打败的一个丹麦酋长的脖子上夺下作盔甲用的“托马尔脖套”。爱琳是爱尔兰古称,参看第七章注[46]。
[147]一三三一年,都柏林正闹着大饥荒的时候, 大批鲸被冲上离利菲河口不远的多得尔的岸上。人们宰食了约摸二百条。一三三八年,利菲河上结了极厚的冰,可以在上面踢足球,燃篝火。一七三九年也结过厚到足供人们在上面玩耍的冰层。
[148]原文为拉丁文。见《诗篇》第66篇第3节。
[l49]命运的奴仆指身穿黄色背心的勃克?穆利根;这里套用克莉奥佩特拉关于安东尼的评语:“他既然不是命运,他就不过是命运的奴仆……”见《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5幕第2场。
[l50]布鲁斯是苏格兰的古老家族。布鲁斯的弟弟指一三0六年成为苏格兰国王的罗伯特?德?布鲁斯(1274-1329)的胞弟爱德华。他代替乃兄攻入爱尔兰,一二一五年自封为爱尔兰王,一三一八年被英王爱德华二世击败战死。
[151]托马斯?菲茨杰拉德(1513-1537 ),爱尔兰第十代基尔代尔伯爵,因命侍从一律在帽子上加绢饰,故名。一五三四年他起兵反对亨利八世,占领了都柏林。抗英战争失败后,被处绞刑。
[152]珀金?沃贝克(约1474-1499),政治骗子,生于佛兰德。一四九一年去爱尔兰,诡称是约克公爵理查德,觊觎英格兰都铎王朝亨利七世的王位。后被俘,处绞刑。
[153]兰伯特?西姆内尔(1475?-1535?),英格兰王位觊觎者。原为牛津一个细木工之子,后在都柏林冒充王子登上王位,自称爱德华六世。被俘后,亨利七世认为他只不过是骗子而已,就让他在御厨房里打下手。
[154]他指穆利根。
[155]据卜伽丘的《十日谈》第六天故事第九,意大利诗人圭多?卡瓦尔坎蒂(约1255-1300)曾从佛罗伦萨的圣迈克尔大教堂前往圣约翰礼拜堂, 在坟地的云斑石柱间徘徊。一批绅士跑来嘲笑他。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在自己的老家里,爱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旨在挖苦他们不学无术,比死人还不如。“……的老家”, 应作“死亡的老家”。这里套用时,把嘲笑者的身份改为朝臣。
[156]原文为德语。
[157]她指斯蒂芬的母亲。
[158]据理查德?艾尔曼所著《詹姆斯?乔伊斯》(第49页),乔伊斯十四岁时曾初次嫖妓。
[159]哈伦?拉希德(763-809),伊斯兰国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教首脑)。他喜在首都巴格达微服出访,体察民情。《一千零一夜》中有不少关于他和他的儿子麦蒙当政时的故事。麦蒙统治时期(813-833)堪称阿拉伯文明的黄金时代。
[160]这里,埃及人指吉卜赛人。
[161]罗马维尔指伦敦,是十七世纪的隐语,原文作Romeville。罗马(rome,或rum)的意思是最好的;维尔(ville)是法语“城市”的音译。
[162]这是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理查德?黑德的《恶棍喜赞共闯江湖的姘头》(1673)一诗的第二段。前文中“恶棍和共闯江湖的姘头”、“跟随老公当配偶,朝着罗马维尔走”、“吻她并讲江湖话,把她搂抱在怀里。哦,我多情的俏姐儿!”等句,也均出自该诗。
[l63]阴沉的乐趣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用过的词,指动邪念之罪。
[164]原文为意大利语。箭猪也叫豪猪,因阿奎那立论尖刻,不易被驳倒而得名。
[165]剑,指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后, 天主为了防止人们靠近那棵生命树而安置在伊甸园东边的“发出火焰、四面转动的剑”。见《创世记》第3章第24节。黄昏的士地,见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的抒情诗剧(希腊)(1821、1822)。
[166]这四个字分别为德、法、英、意语,意思均为“拖着”,语尾变化则是按照英文写法。这里暗喻夏娃因先吃禁果而受的惩罚:“我要大大增加你怀孕的痛苦,生产的阵痛。”见《创世记》第3章第16节。
[167]原文为希腊文。
[168]原文为拉下文。见《诗篇》第65篇第2节。
[169]“他来了……亲吻”,这四句系将爱尔兰作家、学者、第一任总统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根据爱尔兰文译成英文的《我的忧愁在海上》(收入1895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康诺特的情歌》里)一诗的末段润色加工而成。
[170]这两句话与《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我的记事簿呢?我必须把它记下来”一语相呼应。
[171]这句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第2幕第2场“大地是生化万类的慈母,她又是掩藏群生的坟墓”一语相呼应。
[172]黑暗在光中照耀,参看第二章注[37]。
[173]仙后座是拱极星座之一,和大熊座遥遥相对。座内五颗亮星,加以线联接,形似拉丁字母W。
[174]乔治?伯克利(参看本章注[3])是克洛因(科克郡的一个小镇)的主教。他在《视觉新论》中提出,距离不是“看到”的,而是“设想出来”的。斯蒂芬在后文中说出了他此刻转的一些念头(见第十五章注[691]及有关正文)。
[175]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书第5章开头部分, 斯蒂芬的朋友达文句他述说路遇“野鸡”的经历。除了家人, 达文是唯一对斯蒂芬使用斯蒂维这个昵称的。
[176]原文为意大利语。
[177]当天中午在图书馆,斯蒂芬做了这样的解释:“爱――是的。大家都晓得的字眼。”见第九章注[231]及有关正文。
[178]原文为拉下文,见《创世记》第1章第31节。
[179]原文为法语。
[180]《欢迎你如五月花》是丹·J·沙利文作词并配曲的一首歌。歌中两次重复这个句子。
[181]潘是希腊神话中外形有点像野兽的丰产神,常到山上放牧,并擅长吹奏排萧。
[182]《牧神的午后》(1876-1877)是法国象征派诗人斯蒂芬?马拉美(1842-1898)的诗剧。法国作曲家克劳德?艾基利?德彪西(1862-1918)在其影响下,作了同名的管弦乐(1894)。
[183]指勃克?穆利根。Buck(勃克)的字义之一是花花公子。
[184]原文为德语。
[185]庄严的祭神舞,原文为拉丁文。
[186]原文为法语。
[187]王尔德因被控与青年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恋而被判入狱两年。“不敢讲明的爱”,指同性恋,出自道格拉斯写的《两档子爱》一诗。
[188]这里套用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的诗剧《布兰德》(1866)第2幕第2场中布兰德的话:“我的要求是:‘要么一无所有,要么得到一切。’”
[189]科克湖位于都柏林港南边。
[190]这里套用关于玛丽?安的歌曲第3句,参看第一章注[60]及有关正文。
[191]圣安布罗斯(约339-397),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他擅长通过音乐抒发信仰,并厉行禁欲,谴责社会弊端,经常为被判罪的人请求宽赦。
[192]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圣安市罗斯的《罗马书评注》。这是对保罗《罗马书》第8章第22节(“直到现在,一切被造的都在痛苦呻吟,好像经历生产的阵痛”)所作的说明。“它”,指被造的。(193]“你的……深处。”引自精灵爱丽儿所唱的歌,见《暴风雨》第1幕第2场。“他说是一点钟”,参看第一章注[122]及有关正文。
[194]天主变成人(参看《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节:“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人变成鱼(早期基督教会把鱼看作基督的象征),鱼变成黑雁( 中世纪的人们迷信黑雁是水生物变的),黑雁又变成堆积如山的羽绒褥垫( 雁羽可用来制作羽绒褥垫,而都柏林以南的都柏林群上中又有一座羽毛山)。
[195]精灵爱丽儿所唱的歌里有“海水神奇的变幻”之语,见《暴风雨》第1幕第2场。
[196]原文为法语。这是双关语。巴黎奖原指巴黎赛马会上的大奖。Paris(巴黎)与特洛伊王子帕利斯的名字拼法相同,故PrixdeParis又可解释为“帕利斯之奖”――即帕利斯由于将金苹果给了女神阿芙洛狄蒂,作为奖赏获得了美女海伦。此事最终导致奥德修(即尤利西斯)在回国途中多次几乎溺死在大海中。
[197]“我口渴”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即将咽气时所说的话。见《约翰福音》第19章第28节。
[198]据《马太福音》第27章,耶稣弥留之际黑暗曾笼罩大地。
[199]原文为拉丁文。晓星是耶稣自况。参看《启示录》第22章第16节:“我(耶稣)就是明亮的晓星。”
[200]指撒但。参看《路加福音》第10章第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2O1]此句模仿奥菲利娅所唱的歌:“毡帽在头杖在手,草鞋穿一双。”见《哈姆莱特》第4幕第5场。
[202]本书所写的故事发生于六月十六日(星期四),所以下星期二指二十一日(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
[203]这是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892)所作《五月女王》(1833) 一诗中的半句。全句是:“在快活的新年中,妈妈,这是最狂热欢乐的一天。”五月女王指在五朔节狂欢中扮演女王的姑娘。
[204]丁尼生由于写了组诗《悼念》(1850),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青睐,封他为桂冠诗人。一八八四年他还接受了男爵封号。凡受勋者,均在姓前冠以Lord(勋爵)这一尊称。这里,作者把Lord改为发音近似的Lawn(草地),此系草地网球之略语,暗喻诗人柔弱的性格。
[205]丑婆子,指维多利亚女王。
[206]、[208]原文为意大利语。
[207]德鲁蒙,见本章注[111]。
[209]这里,斯蒂芬在回忆当天早晨勃克?穆利根在海滨说的话。参看第一章注
[127]和有关正文。
[210]这是学变戏法的口吻。
[2l1]第十章中重新提到这艘帆船,参看该章注[199]及有关正文。
第四章
利奥波德·布卢姆先生吃起牲口和家禽的下水来,真是津津有味。他喜欢浓郁的杂碎汤、有嚼头的胗、填料后用文火焙的心、裹着面包渣儿煎的肝片和炸雌鳕卵。他尤其爱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那淡淡的骚味微妙地刺激着他的味觉。
当他脚步轻盈地在厨房里转悠,把她早餐用的食品摆在盘底儿隆起来的托盘上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腰子的事。厨房里,光和空气是冰冷的,然而户外却洋溢着夏晨的温煦,使他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煤块燃红了。
再添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三片,四片,成啦。她不喜欢把盘子装得满满的。他把视线从托盘移开,取下炉架上的开水壶,将它侧着坐在炉火上。水壶百无聊赖地蹲在那儿,噘着嘴。很快就能喝上茶了。蛮好。口渴啦。
猫儿高高地翘起尾巴,绷紧身子,绕着一条桌腿走来走去。
“喵!”
“哦,你在这儿哪。”布卢姆先生从炉火前回过头去说。
猫儿回答了一声“眯”,又绷紧身子,绕着桌腿兜圈子,一路眯眯叫着。它在我的书桌上踅行时,也是这样的。噗噜噜。替我挠挠头。噗噜噜。
布卢姆先生充满好奇地凝视着它那绵软的黑色身姿,看上去干净利落,柔滑的毛皮富于光泽,尾根部一块钮扣状的白斑,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双手扶膝,朝它弯下身去。
“小猫眯要喝牛奶喽,”,他说。
“喵!”猫儿叫了一声。
大家都说猫笨。其实,它们对我们的话理解得比我们对它们更清楚。凡是它想要理解的,它全能理解。它天性还记仇,并且残忍。奇怪的是老鼠从来不嗞嗞叫,好像蛮喜欢猫儿哩。我倒是很想知道我在它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高得像座塔吗?不,它能从我身上跳过去。
“它害怕小鸡哩,”他调侃地说,“害怕咯咯叫的小鸡。我从来没见过像小猫眯这么笨的小猫。”
“喵噢!”猫儿大声说了。
它那双贪馋的眼睛原是羞涩地阖上的,如今眨巴着,拉长声调呜呜叫着,露出乳白色牙齿。他望着它那深色眼缝贪婪地眯得越来越细,变得活像一对绿宝石。然后他到食具柜前,拿起汉隆[1]那家送牛奶的刚为他灌满的罐子,倒了一小碟还冒着泡的温奶,将它慢慢地撂在地板上。
“咯噜!”猫儿边叫着边跑过去舔。
它三次屈身去碰了碰才开始轻轻地舔食,有个词儿我想问问你。”
她从捧在手里的杯中呷了一大口茶,麻利地用毛毯揩拭了一下指尖,开始用发夹顺着文字划拉,终于找到了那个词儿。
“遇见了他什么?”他问。
“在这儿哪,”她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弯下身去,读着她那修得漂漂亮亮的大拇指甲旁边的字。
“MetempsyChosis?”
“是啊,他呆在家里哪,能遇见什么人呢?”[53]
“Metempsychosis,”他皱着眉头说,“这是个希腊字眼儿,从希腊文来的,意思就是灵魂的转生。”
“哦,别转文啦!”她说,“用普普通通的字眼告诉我!”
他微笑着,朝她那神色调皮的眼睛斜瞟了一眼。这双眼睛和当年一样年轻。就是在海豚仓[54]猜哑剧字谜后那第一个夜晚。他翻着弄脏了的纸页。《马戏团的红演员鲁碧》[55]。哦,插图。手执赶车鞭子的凶悍的意大利人。赤条条地呆在地板上的想必是红演员鲁碧喽。好心借与的床单。[56]怪物马菲停了下来,随着一声诅咒,将他的猎物架猛扔出去。内幕残忍透了。给动物灌兴奋剂。亨格勒马戏团的高空吊。[57]简直不能正眼看它。观众张大了嘴呆望着。你要是摔断了颈骨,我们会笑破了肚皮。一家子一家子的,都干这一行。从小就狠狠地训练,于是他们转生了。我们死后继续生存。我们的灵魂。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迪格纳穆的灵魂……
“你看完了吗?”他问。
“是的,”她说,“一点儿也不黄。她是不是一直在爱着那头一个男人?”
“从来没读过。你想要换一本吗?”
“嗯。另借一本保罗·德·科克[58]的书来吧。他这个名字挺好听。”
她又添茶,并斜眼望着茶水从壶嘴往杯子里淌。
必须续借卡佩尔街图书馆那本书,要不他们就会寄催书单给我的保证人卡尔尼[59]。转生,对,就是这词儿。
“有些人相信,”他说,“咱们死后还会继续活在另一具肉体里,而且咱们前世也曾是那样。他们管这叫作转生。还认为几千年前,咱们全都在地球或旁的星球上生活过。他们说,咱们不记得了。可有些人说,他们还记得自己前世的生活。”
黏糊糊的奶油在她的红茶里弯弯曲曲地凝结成螺旋形。不如重新提醒她这个词儿,轮回。举个例会更好一些。举个什么例子呢?
床上端悬挂着一幅《宁芙[60]沐浴图》。这是《摄影点滴》[61]复活节专刊的附录,是人工着色的杰出名作。没放牛奶之前,红茶就是这种颜色。未尝不像是披散起头发时的玛莉恩,只不过更苗条一些。在这副镜框上,我花了三先令六便士。她说挂在床头才好看。裸体宁芙们,希腊。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作例子也好嘛。
他一页页地往回翻。
“转生,”他说,“是古希腊人的说法。比方说,他们曾相信,人可以变成动物或树木。譬如,还可以变作他们所说的宁芙。”
正在用调羹搅拌着砂糖的她,停下手来。她定睛望着前方,耸起鼻孔吸着气。
“一股糊味儿,”她说,“你在火上放了些什么东西吗?”
“腰子!”他猛地喊了一声。
他把书胡乱塞进内兜,脚趾尖撞在破脸盆架上,朝着那股气味的方向奔出屋子,以慌慌张张的白鹳般的步子,匆忙冲下楼梯。刺鼻的烟从平底锅的一侧猛地往上喷,他用叉子尖儿铲到腰子下面,将它从锅底剥下来,翻了个个儿。只糊了一丁点儿。他拿着锅,将腰子一颠,让它落在盘子上,并且把剩下的那一点褐色汁子滴在上面。
现在该来杯茶啦。他坐下来,切了片面包,涂上黄油。又割下腰子糊了的部分,把它丢给猫。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叉子,边咀嚼边细细品尝着那美味可口的嫩腰子。烧得火候正好。喝了口茶。接着他又将面包切成小方块儿,把一块在浓汁里蘸了蘸,送到嘴里。关于年轻学生啦,郊游啦,是怎么写的来着?他把那封信铺在旁边摩挲平了,边嚼边慢慢读着,将另外一小方块也蘸上汁子,并举到嘴边。
最亲爱的爹爹:
非常非常谢谢您这漂亮的生日礼物。我戴着合适极了。大
家都说,我戴上这顶新的无檐软帽,简直成了美人儿啦。我
也收到了妈妈那盒可爱的奶油点心,并正在写信给她。点心
很好吃。照相这一行,现在我越干越顺当。科格伦先生为我
和他太太拍了一张相片,冲洗出来后,将给您寄去。昨天我
们生意兴隆极了。天气很好,那些胖到脚后跟的统统都来啦。
下星期一我们和几位朋友赴奥维尔湖作小规模的野餐。问妈
妈好,给您一个热吻并致谢。我听见他们在楼下弹钢琴哪。星
期六将在格雷维尔徽章饭店举行音乐会。有个姓班农的年轻
学生,有时傍晚到这儿来。他的堂兄弟还是个什么大名人,他
唱博伊兰(我差点儿写成布莱泽斯·博伊兰了)那首关于海
滨姑娘们的歌曲。告诉他[62],傻米莉向他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我怀着挚爱搁笔了。
热爱您的女儿
米莉
又及,由于匆忙,字迹潦草,请原谅。再见。
米
昨天她就满十五岁了。真巧,又正是本月十五号。这是她头一回不在家里过生日。别离啊。想起她出生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我跑到丹齐尔街去敲桑顿太太的门,喊她起床。她是个快活的老太婆。经她手接生来到世上的娃娃,想必多得很哩。她一开始就晓得可怜的小鲁迪[63]不长。——先生,天主是仁慈的。她立刻就知道了。倘若活了下来,如今他已十一岁了。
他神色茫然,带些怜惜地盯着看那句附言。字迹潦草,请原谅。匆忙。在楼下弹钢琴。她可不再是乳臭未干的毛丫头啦。为了那只手镯的事,曾在第四十号咖啡馆和她拌过嘴。她把头扭过去,不吃点心,也不肯说话。好个倔脾气的孩子。他把剩下的面包块儿都浸在浓汁里,并且一片接一片地吃着腰子。周薪十二先令六便士,可不算多。然而,就她来说,也还算不错哩。杂耍场舞台。年轻学生,他呷了一大口略凉了些的茶,把食物冲了下去。然后又把那封信重读了两遍。
哦,好的,她晓得怎样当心自己了。可要是她不晓得呢?不,什么也不曾发生哩。当然,也许将会发生。反正等发生了再说呗。简直是个野丫头。迈着那双细溜的腿跑上楼梯。这是命中注定的。如今快要长成了。虚荣心可重哩。
他怀着既疼爱又不安的心情朝着厨房窗户微笑。有一天我瞥见她在街上,试图掐红自己的腮帮子。她有点儿贫血,断奶断得太晚了。那天乘爱琳王号绕基什一周[64],那艘该死的旧船颠簸得厉害。她可一点儿也不害怕,那淡蓝色的头巾和头发随风飘动。
鬈发和两腮酒窝,
简直让你晕头转向。
海滨的姑娘们。撕开来的信封。双手揣在兜里,唱着歌儿的那副样子,活像是逍遥自在地度着一天假的马车夫。家族的朋友。他把“晕”说成了“云”。[65]夏天的傍晚,栈桥上点起灯火,铜管乐队。
那些姑娘,那些姑娘,
海滨那些俏丽的姑娘。
米莉也是如此。青春之吻,头一遭儿。早已经成为过去了。玛莉恩太太。这会子想必向后靠着看书哪,数着头发分成了多少绺,笑眯眯地编着辫子。
淡淡的疑惧,悔恨之情,顺着他的脊骨往下串。势头越来越猛。会发生的,是啊。阻挡也是白搭,一筹莫展。少女那俊美、娇嫩的嘴唇。也会发生的啊。他觉得那股疑惧涌遍全身。现在做什么都是徒然的。嘴唇被吻,亲吻,被吻。女人那丰满而如胶似漆的嘴唇。
她不如就呆在眼下这个地方。远离家门。让她有事儿可做。她说过想养只狗作消遣。也许我到她那儿去旅行一趟。利用八月间的银行休假日[66],来回只消花上两先令六便士。反正还有六个星期哪。也许没法弄到一张报社的乘车证。要么就托麦科伊[67]。
猫儿把浑身的毛舔得干干净净,又回到沾了腰子血的纸那儿,用鼻子嗅了嗅,并且大模大样地走到门前。它回头望了望他,喵喵叫着。想出去哩。只要在门前等着,迟早总会开的。就让它等下去好了。它显得烦躁不安,身上起了电哩。空中的雷鸣。是啊,它还曾背对着火,一个劲儿地洗耳朵来着。
他觉得饱了。撑得慌;接着,肠胃一阵松动。他站起来,解开裤腰带。猫儿朝他喵喵叫着。
“喵!”他回答,“等我准备好了再说。”
空气沉闷,看来是个炎热的日子。吃力地爬上楼梯到平台[68]那儿去,可太麻烦了。
要张报纸。他喜欢坐在便桶上看报。可别让什么无聊的家伙专挑这种时候来敲门。
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一份过期的《珍闻》[69]。他把报纸叠起来,夹在腋下,走到门前,将它打开。猫儿轻盈地蹿跳着跑上去了。啊,它是想上楼,到床上蜷缩作一团。
他竖起耳朵,听见了她的声音:
“来,来,小咪咪。来呀。”
他从后门出去,走进园子,站在那儿倾听着隔壁园子的动静。那里鸦雀无声。多半是在晾晒着衣服哪。女仆在园子里。[70]早晨的天气多好。
他弯下身去望着沿墙稀稀疏疏地长着的一排留兰香。就在这儿盖座凉亭吧。种上红花菜豆或五叶地锦什么的。这片土壤太贫瘠了,想整个儿施一通肥。上面是一层像是肝脏又近似硫磺的颜色。要是不施肥,所有的土壤都会变成这样。厨房的泔水。怎么才能让土壤肥沃起来呢?隔壁园子里养着母鸡。鸡粪就是头等肥料。可再也没有比牲口粪更好的了,尤其是用油渣饼来喂养的牛。牛粪可以做铺垫。最好拿它来洗妇女戴的羔羊皮手套。用脏东西清除污垢。使用炭灰也可以。把这块地都开垦了吧。在那个角落里种上豌豆。还有莴苣。那么就不断地有新鲜青菜吃了。不过,菜园子也有缺陷。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这里就曾招来成群的蜜蜂[71]和青蝇。
他继续走着。咦,我的帽子呢?想必是把它挂回到木钉上啦。也许是挂在落地衣帽架上了。真怪,我一点儿也记不得。门厅里的架子太满了。四把伞,还有她的雨衣。方才我拾起那几封信的时候,德雷格理发店的铃声响起来了。奇怪的是我正在想着那个人。除了润发油的褐色头发一直垂到他的脖颈上。一副刚刚梳洗过的样子。不知道今天早晨来不来得及洗个澡。塔拉街[72]。他们说,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个家伙把詹姆斯·斯蒂芬斯[73]放跑了。他姓奥布赖恩[74]。
那个叫德鲁加茨的家伙声音挺深沉的。那家公司叫阿根达斯什么来着?——好啦,大姐。[75]狂热的犹太教徒[76]。
他一脚踢开厕所那扇关不严的门。还得穿这条裤子去参加葬礼哪,最好多加小心,可别给弄脏了。门楣挺矮,他低着头走进去。门半掩着,在发霉的石灰浆和陈年的蜘蛛网的臭气中,解下了背带。蹲坐之前,隔着墙缝朝上望了一下邻居的窗户。国王在他的帐房里[77]。一个人也没有。
他蹲在凳架[78]上,摊开报纸,在自己赤裸裸的膝上翻看着。读点新鲜而又轻松的。不必这么急嘛。从从容容地来。《珍闻》的悬赏小说:《马查姆的妙举》,作者菲利普·博福伊[79]先生是伦敦戏迷俱乐部的成员。已经照每栏一基尼付给了作者。三栏半。三镑三先令。三镑十三先令六便士。[80]
他不急于出恭,从从容容地读完第一栏,虽有便意却又憋着,开始读第二栏。然而读到一半,就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就一边读着一边让粪便静静地排出。他仍旧耐心地读着,昨天那轻微的便秘完全畅通了。但愿块头不要太大,不然,痔疮又会犯了。不,这刚好。对。啊!便秘嘛,请服一片药鼠李皮[81]。人生也可能就是这样。这篇小说并未使他神往或感动,然而写得干净利索。如今啥都可以印出来,是个胡来的季节。他继续读下去,安然坐在那里闻着自己冒上来的臭味。确实利索。马查姆经常想起那一妙举,凭着它,自己赢得了大笑着的魔女之爱,而今她……开头和结尾都有说教意味。手拉着手。写得妙!他翻过来又瞅了瞅已读过的部分,同时觉出尿在静静地淌出来,心里毫无歹意地在羡慕那位由于写了此文而获得三镑十三先令六便士的博福伊先生。
也许好歹能写出一篇小品文。利·玛·布卢姆夫妇作。由一句谚语引出一段故事如何?可哪句好呢?想当初,她在换衣服,我一边看她梳妆打扮,一边把她讲的话匆匆记在我的袖口上。我们不喜欢一道换装。一会儿是我刮胡子,刮出了血,一会儿又是她,裙腰开口处的钩子不牢,狠狠地咬着下唇。我为她记下时间,九点一刻,罗伯兹付你钱了没有?九点二十分,葛莉塔·康罗伊[82]穿的是什么衣服?九点二十三分,我究竟着了什么魔,买下这么一把梳子!九点二十四分:吃了那包心菜,肚子胀得厉害。她的漆皮靴上沾了点土。于是轮流抬起脚来,用靴子的贴边灵巧地往袜筒上蹭。在义卖会舞会上,梅氏乐队[83]演奏了庞契埃利的《时间之舞》。[84]那是第二天早晨的事。你解释一下,早晨的时光,晌午,随后傍晚来临,接着又是晚上的时光。她刷牙来着。那是头一个晚上。[85]她脑子里还在翩翩起舞。她的扇柄还在咯嗒咯嗒响着。——那个博伊兰阔吗?——他有钱。——怎见得?——跳舞的时候,我发觉他呼出浓郁的、好闻的气味。那么,哼哼唱唱也是白搭。还是暗示一下为好。昨天晚上的音乐可妙哩。镜子挂在暗处。于是,她就用自己的带柄手镜在她那裹在羊毛衫里的颤巍巍的丰满乳房上敏捷地擦了擦。她照着镜子,然而眼角上的鱼尾纹却怎么也抹不掉。
黄昏时分,姑娘们穿着灰色网纱衫。接着是夜晚的时光,穿黑的,佩匕首,戴着只露两眼的假面具。多么富于诗意的构思啊,粉色,然后是金色,接着是灰色,接着又是黑色。也是那样栩栩如生。先是昼,随后是夜。
他把获奖小说吱啦一声扯下半页,用来揩拭自己。然后系上腰带和背带,扣上钮扣。他将那摇摇晃晃关不紧的门拽上,从昏暗中走进大千世界。
在明亮的阳光下,四肢舒展爽朗起来。他仔细审视着自己的黑裤子,裤脚、膝部、腿窝。丧礼是几点钟来看?最好翻翻报纸。
空中响起金属的摩擦声和低沉的回旋声。这是乔治教堂在敲钟。那钟在报时辰,黑漆漆的铁在轰鸣着。
叮当!叮当!
叮当!叮当!
叮当!叮当!
三刻钟了。又响了一下。回音划破天空跟过来。第三下。
可怜的迪格纳穆!
第四章 注释
[1]离布卢姆夫妇所住的埃克尔斯街七号最近的一家以汉隆为店名的牛奶店,坐落在下多尔塞特街二十六号。
[2]普列文是保加利亚北部的城市。在俄土战争(1877-1878)中, 俄军对土耳其人占领下的普列文进行围攻,土耳其人被迫投降。布卢姆的岳父特威迪当年曾在支援士耳其的英军中服役,以后又到西班牙南端的英国要塞直布罗陀服役。
[3]这个白纸片上印有“亨利?弗罗尔”字样,是布卢姆为了和一位叫作玛莎?克利弗德的女打字员秘密通信而用的化名。
[4]土豆是布卢姆亡母的纪念品。他总把它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
[5]一种半圆形或三角形的馅饼。
[6]可怕的土耳克,参看第一章注[42]。这里指此人长得像戏里的土耳克王。
[7]《自由人报》是一七八0年左右创办的一份爱尔兰报纸,一九三O 年停办。该报站在温和保守的立场上主张爱尔兰自治。以爱尔兰银行大楼(1800年英、爱议会合并前为爱尔兰议会大厦)后一轮太阳为其社论花饰。
[8]布卢姆以替《自由人报》拉广告为业。
[9]这里,布卢姆联想到一首爱尔兰歌谣(见第十二章注[189]),其主人公与这位老板同名。
[10]这一天是一九0四年六月十六日,日俄战争已打了四个月。
[ll]利特里姆是爱尔兰西北部康诺特省偏僻的郡,当地居民被看作是乡巴佬。
[12]亚当?S?芬德莱特尔斯是个经营茶叶和酒的商人,除了总公司 ,还开设了十一家分公司。丹尼尔?塔隆斯是个经营食品杂货和酒的商人,一八九九至一九00年任都柏林市市长。
[13]这是为了便于儿童记忆,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编成的一首歌。这里,原作中用拼音把此歌的唱腔表示出来了。
[14]伊尼施土耳克(爱尔兰语:公猪岛)、伊尼沙克(爱尔兰语:公牛岛)和伊尼施勃芬(爱尔兰语:白母牛岛)都是爱尔兰中部西岸的岛屿。
[l5]布卢姆山位于都柏林市以南五十五英里处,系同名山脉的主峰。
[16]太巴列湖即加利利海的异称,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部。《约书亚记》第19章第35节中曾提及基尼烈城,它坐落在加利利海西南,有时也把加利利海叫作基尼烈湖。本世纪初有些犹太企业家在此筹建犹太人聚居区。
[17]库西?蒙特斐奥雷(1784-1885),犹太裔慈善家。出身于意大利犹太商人世家,幼年随家到英国。他毕生致力于改善流浪于欧洲和中东的犹太人的处境。开办这座农场也是为了给犹太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18]据第十七章,布卢姆曾在牲畜市场附近住过,并于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间,在一个叫作约瑟夫?卡夫的牲畜业者手下当过雇员。
[19]原文作scapular,也作“肩衣”解。教徒们迷信褐色肩衣是保持贞操的护身符,故以崇敬圣母为宗旨的天主教在俗组织的年轻女子,把它作为虔诚的标志穿在身上。这里把女仆穿的无袖工作服比作肩衣。
[20]在一九0四年,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以上的男子才能当上都柏林市的警察,超过一般市民。
[2l]《求求你啦,警察先生,噢噢噢》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蒂利姐妹何在都柏林演唱的一首歌的标题,歌词作者为E?安德鲁斯。 “我在树林子里迷了路”则引自英国童话《树林里的娃娃们》。还有一首同名的民谣。
[22]布卢姆原想告诉德鲁加茨,他也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23]阿根达斯?内泰穆是希伯来文移民垦殖公司的译音。这是一九0 五年夏天创办的一个企业,旨在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当时属于土耳其帝国)定居。这里把日期提前了一年。
[24]雅法是以色列西部的港口。一九五0年与特拉维夫合并,改成特拉维夫-雅法,是以色列最大城市和商业、交通、文化中心。
[25]一狄纳穆等于一千平方米。以色列目前仍采用这种面积单位。下文中的西十五区,在第十五章中作西十三区(参看该章注[132])。
[26]香橼,原文作citron。布卢姆由此联想到住在圣凯文步道十七号的西特伦(Citron)。
[27]圣凯文步追是都柏林市城南的一条街。在布卢姆夫妇当年住过的西伦巴德街的拐角处。
[28]阿尔布图斯小街也距西伦巴德街不远。莫依塞尔住在该街二十号,因而与布卢姆是街坊。
[29]普莱曾茨是都柏林市城南的街道。
[3O]犹太教一年一度的住棚节(感恩节,开始于希伯来历第七个月的十五日)期间使用的香橼,不但一个碴儿也不能有,连栽培技术及环境也有各种讲究。
[31]黎凡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通称。指小亚细亚沿海地带和叙利亚。该词也是中东或近东的同义词。
[32]按这位挪威船长是个驼背,他叫都柏林的裁缝J?H?克尔斯为自己做了一件衣服,却抱怨说剪裁不得体。克尔斯反驳说,根本无法照着他的身材做衣服。参看艾尔曼著《詹姆斯?乔伊斯》(第23页)。
[33]这是天主教祷文《天主经》中的半句话,全句是:“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见《马太福音》第6章第l0节。
[34]据《创世记》第19章,所多玛与蛾摩拉是罪恶之城,天主使“燃烧着的硫磺从天上降落”,将其毁灭。遗址在今以色列境内死海南端附近利桑半岛以南的浅水之下。这原是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土地肥沃的地区,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系毁于地震时石油与天然气喷发燃烧导致的天灾。
[35]埃多姆(旧译以东),古代地名,与古以色列相邻,在今约旦西南部,死海与亚喀巴湾之间。
[36]参看《创世记》第19章第24至26节:所多玛和蛾摩拉城被毁后, “罗得的妻子回过头来看一看,就变成一根盐柱。”
[37]指爱尔兰大力士尤金?桑道(原名弗雷德里卡?马勒,1867-1925)所编排的健身操。第十七章中提到,布卢姆的书架上有一本桑道所著《体力与健身术》。
[38]托尔斯、巴特斯比、诺思和麦克阿瑟都是都柏林的房地产经纪人。
[39]这句话既指阳光,又隐喻米莉。参看第十四章注[243]至[245]及有关正文。下文中的波尔迪是利奥波德的爱称。
[40]语出自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的长诗《仙后》(1590-1596)。独眼的马尔贝科发现自己的妻子海伦诺尔与人通奸,他便死命地往前跑,眼睛却依然“盯着后面”。见该诗第8章第l0节第56段。
[41]这是苏格兰人喜戴的一种宽顶无檐软帽,通常用呢料做成,有点像贝雷帽,顶上有个毛线球儿。
[42]科格伦是开照相馆的,布卢姆的女儿米莉在他手下工作。
[43]年轻的学生指亚历克?班农,参看第一章注[123]。
[44]布莱泽斯?博伊兰是音乐家,系布卢姆之妻女高音歌手玛莉恩的代理人,与她有暧昧关系。他擅长唱哈里?B?诺里斯作词并谱曲的《海滨的姑娘们》(1899)一歌。
[45]搪须杯里有一种装置,可避免饮水时将胡子沾湿。
[46]德比瓷器是约于一七五O至一八四八年间在英国德比制造的一种瓷雕和餐具。
[47]这里套用爱尔兰诗人、歌词作家塞缪尔?洛弗(1797-1868)所作的诗(收于1835年出版的《爱尔兰传说与故事》),并把原诗中的“撒迪?布雷迪”改成“米莉
?布卢姆”,“布赖恩?加拉格尔虽有房子”改成“凯西?基奥虽有驴”。
[48]古德温是个钢琴师,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间曾为摩莉伴奏。下文中提到的那次音乐会是一八九三年举行的。[49]原文为意大利语,出自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所作歌剧《唐乔万尼》(1787)第1幕第3场中的二重唱。男主人公唐乔万尼引诱农村姑娘泽莉娜,说:“咱们将结婚,咱们将手拉着手前往……”J?C、 多伊尔,参看第六章注[33]。
[50]《古老甜蜜的情歌》(1884)是G?克利夫顿?宾厄姆(1859-1913) 作词、爱尔兰作曲家詹姆斯?莱曼?莫洛伊(1837-1909)配曲的一首歌曲。下文中的“酸臭的气味”,布卢姆在夜间重新提到。参看第十五章注[666]。
[51]、[52]原文为意大利歌词,是摩莉即将演唱的泽莉娜对唐乔万尼所作的答复,原作Vorreienonvorrei,意即,“我愿意,又不愿意”,表达了女主人公在受诱惑时的矛盾心绪。在这里,布卢姆却把vorrei(愿意)误作voglio(要)了。
[53]原文metemPsychosis系源于希腊文的外来语,意思是轮回、转生。 此词的前半截metem,与英语methim(遇见了他)发音相近,故不懂希腊文的玛莉恩有此误会。
[54]海啄仓是都柏林市西南郊的一条小巷,卢克和卡罗琳?多伊尔夫妇就住在这里。布卢姆与玛莉恩是在他们家初次相遇的。
[55]此书原名叫《鲁碧,根据一个马戏团女演员的生活写成的小说》( 伦敦,1889),作者为艾米?里德。这里还把马戏团老板恩里科的名字改成马菲。该书写一个十三岁上被卖给马戏团的小姑娘鲁碧被虐待致死的事。
[56]原文作Sheetkindlylent。扎克?鲍恩在《詹姆斯?乔伊斯的音乐暗喻》(1974,第88页)中指出,此句与英国枢机主教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所作的颂歌《云柱》(1833)中的诗句Leadkindlylight(光啊,仁慈地引导)发音相近。
[57]指查理?亨格勒(1820-1887)及其胞弟艾伯特所经营的马戏团的表演。该团在都柏林、爱丁堡、伦敦等六个城市均有固定场地,而不是搭棚做巡回演出。
[58]查理-保罗?德?科克(1793-1871),法国作家。所著反映巴黎生活的小说,略有色情描写,曾在欧洲风靡一时。他的全集出版于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四年间。
[59]当时都柏林确有个叫约瑟夫?卡尔尼的人,在卡佩尔街十四号经售书籍乐谱。
[60]宁芙是音译,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她们通常住在山林水泽中。
[6l]《摄影点滴》是一八九八年问世的伦敦一种周刊,每册一便士,逢星期四出版,所刊照片略带色情味道。
[62]他指博伊兰。
[63]鲁迪是布卢姆的儿子,生下来十一天就夭折了。桑顿太太是个接生婆。
[64]爱琳王号是一艘游览船,沿都柏林湾航行,并绕过基什的灯台船。基什,见第三章注[138]。
[65]歌词中的晕字,原文作swirls。他指博伊兰。因咬字不清,唱成swurls了。英文中无此字。
[66]银行假日指星期日外的公假日,在英国,一年有六次,即耶稣酥受难日、复活节次日、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五十天)次日、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圣诞节、圣诞节次日。
[67]麦科伊是布卢姆的朋友。这个人物曾出现在《都柏林人?圣恩》中,是个铁道办事员,在本书中是都柏林市的验尸官助手。
[68]指设在楼梯平台处的厕所。
[69]《珍闻?摘自世界最有趣的书报杂志》是一八八一年问世的一种周刊,每册一便士,逢星期四出版,被认为是现代通俗刊物的滥觞。
[70]这里套用爱尔兰一首儿歌。全段为;“国王在帐房里,数着他的钱币;王后在客厅里,吃面包和蜂蜜。女仆在园子里,晾晒着衣服呢;飞来只小黑鸟, 咬掉她的鼻尖。”
[71]布卢姆曾于五月二十三日被蜜蜂蜇过,他多次忆及此事。
[72]塔拉街是通往巴特桥的一条街,街上有公共澡堂。
[73]詹姆斯?斯蒂芬斯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志士,参看第二章注[54]。
[74] 和斯蒂芬斯打过交道的奥布赖恩有两个, 但均未直接参与救他出狱的活动。爱尔兰爱国主义者、青年爱尔兰运动领导人威廉?史密斯?奥布赖恩( 1803-1864),曾于一八四八年在蒂珀雷斯郡的巴林加里领导农民起义, 斯蒂芬斯也参加了。起义以失败告终,斯蒂芬斯逃脱,奥布赖恩被捕,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成为终身流放。一八五四年获释,住在布鲁塞尔。另一个叫詹姆斯?弗朗西斯?泽维尔?奥布赖恩(1828-1905)。他于一八五八年在美国参加了芬尼运动。南北战争期间,他在联邦军中当外科医师。战后赴爱尔兰,一八六七年在科克参加芬尼社起义,失败后被捕,一度判处死刑,后于一八六九年获释。
[75]布卢姆在回忆刚才肉铺老板德鲁加赤对买腊肠的邻居女仆说的话。
[76]据艾尔曼著《詹姆斯?乔伊斯》(第308页脚注) ,乔伊斯在意大利的底里雅斯特教过一个叫作摩西?德鲁加赤(与肉铺老板同姓)的年轻学生。那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起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有保障的家园”。
[77]“国王在帐房里”,参看本章注[70]。
[78]原文作cuckstool,可译为惩椅。旧时把奸商或荡妇绑在上面示众。
[79]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确实有个叫作菲利普?博福伊的人经常为《珍闻》撰稿。然而《马查姆的妙举》却是乔伊期的杜撰。
[80]这里,布卢姆在做心算。一基尼为二十一先令,一镑为二十先令。三栏是三镑三先令。再加上半栏。所以是三镑十三先令六便士,六便士相当于半先令。
[81]药鼠李是产于北美太平洋沿岸的一种植物,其树皮可制作缓泻剂。
[82]葛莉塔?康罗伊是《都柏林人?死者》的女主人公。
[83]乐队名,属于都柏林一家出售乐谱并教授音乐和钢琴的梅氏公司。
[84]阿米尔卡里?庞契埃利(1834-1886),意大利作曲家。《时间之舞》即出自他的著名歌剧《歌女》(又名《吉康达》,1876)第3幕的剧中剧。
[85]意思是,玛莉恩和博伊兰是自从那个晚上一道跳舞后开始接近的。
第五章
布卢姆先生沿着停在约翰·罗杰森爵士码头上的一排货车稳重地走去,一路经过风车巷、利斯克亚麻籽榨油厂和邮政局。要是把这个地址也通知她就好了。走过了水手之家。他避开了早晨码头上的噪音,取道利穆街。一个拾破烂的少年在布雷迪公寓[1]旁闲荡,臂上挎了一篮子(提梁是用绳子绑的)碎肉,吸着人家嚼剩的烟头。比他年纪小、额上留有湿疹疤痕的女孩朝他望着,懒洋洋地擦着个压扁了的桶箍。告诉他,吸烟可就长不高了。算啦,随他去吧!他这辈子反正也享不到什么荣华富贵。在酒店外面等着,好把爹领回家去。爹,回家找妈去吧。酒馆已经冷清下来,剩不下几位主顾啦。他横过汤森德街,打绷了面孔的伯特厄尔前面走过。厄尔,对,“之家”。阿列夫、伯特[2]。接着又走过尼科尔斯殡仪馆。葬礼十一点才举行,时间还从容。我敢说准是科尼·凯莱赫[3]替奥尼尔殡仪馆揽下今天这档子葬事的。科尼这家伙总是闭着眼睛唱歌,“有一回在公园里,我和她不期相遇,摸着黑儿真有趣。给警察盯上了哩,问她姓名和住址,她就哼唱了一通:我的吐啦噜,吐啦噜,呔。”哦,肯定是他兜揽下来的。随便找个地方花不几个钱把他埋掉算啦。“我的吐啦噜,吐啦噜,吐啦噜,吐啦噜。”
他在韦斯特兰横街的贝尔法斯特与东方茶叶公司的橱窗前停了下来,读着包装货物的锡纸上的商标说明:精选配制,优良品种,家用红茶。天气怪热的。红茶嘛,得到汤姆·克南[4]那儿去买一些。不过,在葬礼上不便跟他提。他那双眼茫然地继续读着,同时摘下帽子,安详地吸着自己那发油的气味,并且斯文地慢慢伸出右手去抚摩前额和头发。这是个炎热的早晨。他垂下眼皮,瞅了瞅这顶高级帽子衬里上绷着的那圈鞋皮的小小帽花。在这儿哪。他的右手从头上落下来,伸到帽壳里。手指麻利地掏出鞣皮圈后面的名片,将它挪到背心兜里。
真热啊,他再一次更缓慢地伸出有手,摸摸前额和头发,然后又戴上帽子,松了口气。他又读了一遍,精选配制,用最优良的锡兰[5]品种配制而成。远东。那准是个可爱的地方,不啻是世界的乐园;慵懒的宽叶,简直可以坐在上面到处漂浮。仙人掌,鲜花盛开的草原,还有那他们称作蛇蔓的。难道真是那样的吗? 僧伽罗人在阳光下闲荡,什么也不干是美妙的。成天连手都不动弹一下。一年十二个月,睡上六个月。炎热得连架都懒得吵。这是气候的影响。嗜眠症。怠惰之花。主要是靠空气来滋养。氮。植物园中的温室。含羞草。睡莲。花瓣发蔫了。大气中含有瞌睡病。在玫瑰花瓣上踱步。想想看,炖牛肚和牛蹄吃起来该是什么味道。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人的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呢?对啦,他仰卧在死海上,撑着一把阳伞,还在看书哪。盐分太重,你就是想沉也沉不下去。因为水的重量,不,浮在水面上的身体的重量,等于什么东西的重量来着?要么是容积和重量相等吧?横竖是诸如此类的定律。万斯在高中边教着书,边打着榧子。大学课程,紧张的课程[6]。提起重量,说真的,重量究竟是什么?每秒三十二英尺,每秒钟。落体的规律,每秒钟,每秒钟。它们统统都落到地面上。地球。重量乃是地球引力。
他掉转方向,溜溜达达地横过马路。她拿着香肠,一路怎样走来着?是照这样走的吧。他边走边从侧兜里掏出折叠起来的《自由人报》,打开来又把它竖着卷成棍状。每踱一步便隔着裤子用它拍一下小腿,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像是只不过顺路进去看看而已。每秒钟,每秒钟。每秒钟的意思就是每一秒钟。他从人行道的边石那儿朝邮政局门口投了锐利的一瞥。迟投函件的邮筒。倒可以在这儿投邮。一个人也没有。进去吧。
他隔着黄铜格栅把名片递过去。
“有没有给我的信?”他问。
当那位女邮政局长在分信箱里查找的时候,他盯着那征募新兵的招贴。上面是各兵种的士兵在列队行进。他把报纸卷的一端举起来按在鼻孔上,嗅着那刚印刷好的糙纸的气味。兴许没有回信。上一次说得过火了。
女邮政局长隔着黄铜格栅把他的名片连同一封信递了过来。他向她道了谢,赶快朝那打了字的信封瞟上一眼:
亨利·弗罗尔先生
本市
韦斯特兰横街邮政局转交
总算来了回信。他把名片和信塞到侧兜里,又望了望行进中的士兵。老特威迫的团队在哪儿?被抛弃的兵。在那儿,戴着插有鸟颈毛的熊皮帽。不,那是个掷弹兵。尖袖口。他在那儿哪。都柏林近卫步兵连队。红上衣。太显服了。所以女人才追他们呢。穿军装。不论对入伍还是操练来说,这样的军服都更便当些。莫德· 冈内来信提出,他们给咱们爱尔兰首都招来耻辱,夜间应当禁止他们上奥康内尔大街去。格里菲思的报纸如今也在唱同一个调子。这支军队长了杨梅大疮,已经糜烂不堪了。海外的或醉醺醺的帝国。他们看上去半生不熟,像是处于昏睡状态。向前看!原地踏步!贴勃儿:艾勃儿。贝德:艾德。[7]这就是近卫军。他从来也没穿过消防队员或警察的制服。可不是嘛,还加入过共济会哩。[8]
他慢慢腾腾地踱出邮政居,向右转去。难道靠饶舌就能把事情办好吗!他把手伸进兜里,一只食指摸索到信封的口盖,分几截把信扯开了。我不认为女人有多么慎重。他用指头把信拽出,并在兜里将信封揉成一团。信上用饰针别着什么东西,兴许是照片吧。头发吗?不是。
麦科伊走过来了。赶紧把他甩掉吧。碍我的事。就讨厌在这种时刻遇上人。
“喂,布卢姆。你到哪儿去呀?”
“啊,麦科伊。随便溜溜。”
“身体好吗?”
“好。你呢?”
“凑合活着呗,”麦科伊说。
他盯着那黑色领带和衣服,关切地低声问道,
“有什么……我希望没什么麻烦事儿吧。我看到你……”
“啊,没有,”布卢姆先生说,“是这样的,可怜的迪格纳穆,今天他出殡。”
“真的,可怜的家伙。原来是这样。几点钟呀?”
那不是相片。也许是一枚会徽[9]吧。
“十一点钟,”布卢姆先生回答说。
“我得想办法去参加一下,”麦科伊说,“十一点钟吗?昨天晚上我才听说。谁告诉我来着?霍罗翰。你认识‘独脚’吧?”[10]
“认识。”
布卢姆先生朝着停在马路对面格罗夫纳饭店门前的那辆座位朝外的双轮马车望去。脚行举起旅行手提箱,把它放到行李槽里。当那个男人——她的丈夫,也许是兄弟,因为长得像她——摸索兜里的零钱时,她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着。款式新颖的大衣还带那种翻领,看上去像是绒的。今天这样的天气,显得太热了些。她把双手揣在明兜里,漫不经心地站在那儿,活像是在马球赛场上见过的那一位高傲仕女。女人们满脑子都是身份地位,直到你触着她的要害部位。品德优美才算真美。为了屈就才那么矜持。那位可敬的夫人……而布鲁图是个可敬的人[11]。一旦占有了她,就能够使她服贴就范。
“我跟鲍勃·多兰在一块儿来着,他犯了老毛病,又喝得醉醺醺的了,还有那个名叫班塔姆·莱昂斯[12]的家伙。我们就在那边的康韦酒吧间。”
多兰和莱昂斯在康韦酒吧间。她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举到头发那儿。“独脚”进来了,喝上一通。他仰着脸,眯起眼睛,看见颜色鲜艳的鹿皮手套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烁着,也看见镶在手套背上的饰钮。今天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兴许周围的湿气使人能望到远处。这家伙还在东拉西扯。她有着一双贵夫人的手。到底要从哪边上车呢?
“他说:‘咱们那个可怜的朋友帕狄真是可惜呀!’‘哪个帕狄?’我说。‘可怜的小帕狄·迪格纳穆。’他说。”
要到乡间去,说不定是布罗德斯通[13]吧。棕色长统靴,饰带晃来晃去。脚的曲线很美。他没事儿摆弄那些零钱干什么?她发觉了我在瞅着她,那眼神儿仿佛老是在物色着旁的男人——一个好靠山。弓上总多着一根弦。
“‘怎么啦?’我说。‘他出了什么事?’我说。”
高傲而华贵,长统丝袜。
“晤,”布卢姆先生说。
他把头略微偏过去一点,好躲开麦科伊那张谈兴正浓的脸。马上就要上车了。
“‘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他死啦,’他说。真的,他就泪汪汪的了。‘是帕狄·迪格纳穆吗?’我说。乍一听,我不能相信。至少直到上星期五或星期四,我还在阿奇酒店见到了他呢。‘是的,’他说,‘他走啦。他是星期一去世的,可怜的人儿。’”
瞧哇!瞧哇!华贵雪白的长袜,丝光闪闪!瞧啊!
一辆沉甸甸的电车,叮叮噹噹地拉响警笛,拐过来,遮住了他的视线。
马车没影儿了。这吵吵闹闹的狮子鼻真可恶。觉得像是吃了闭门羹似的。“天堂与妖精”。[14]事情总是这样的。就在关键时刻。那是星期一,一个少女在尤斯塔斯街[15]的甬道里整理她的吊袜带来着。她的朋友替她遮住了那露出的部位。互助精神[16]。喂,你张着嘴呆看什么呀?
“是啊,是啊,”布卢姆先生无精打彩地叹了口气说,“又走了一个。”
“最好的一个,”麦科伊说。
电车开过去了。他们的马车驰向环道桥[17],她用戴着考究的手套的手握着那钢质栏杆。闪烁,闪烁,她帽子上那丝质飘带在阳光下闪烁着,飘荡着。
“你太太好吧?”麦科伊换了换语气说。
“啊,好,”布卢姆先生说,“好极了,谢谢。”
他随手打开那卷成棍状的报纸,不经意地读着,
倘若你家里没有,
李树[18]商标肉罐头,
那就是美中不足,
有它才算幸福窝。
“我太太刚刚接到一份聘约,不过还没有谈妥哪。”
又来耍这套借手提箱的把戏[19]了。倒也不碍事。谢天谢地,这套手法对我已经不灵啦。
布卢姆先生心怀友谊慢悠悠地将那眼睑厚厚的眼睛移向他。
“我太太也一样,”他说,“二十五号那天,贝尔法斯特的阿尔斯特会堂举办一次排场很大的音乐会,她将去演唱。”
“是吗?”麦科伊说,“那太好啦,老伙计。谁来主办?”
玛莉恩·布卢姆太太。还没起床哪。王后在寝室里,吃面包和。[20]没有书。她的大腿旁并放着七张肮脏的宫廷纸牌。黑发夫人和金发先生[21]。来信。猫蜷缩成一团毛茸茸的黑球。从信封口上撕下来的碎片。
古老
甜蜜的
情
歌,
听见了古老甜蜜的……
“这是一种巡回演出,明白吧,”布卢姆先生若有所思地说,“甜蜜的情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按照股份来分红。”
麦科伊点点头,一边揪了揪他那胡子茬儿。
“唔,好,”他说,“这可是个好消息。”
他移步要走开。
“喏,你看上去蛮健康,真高兴,”他说,“咱们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又能碰见哩。”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
“话又说回来啦,”麦科伊说,“在葬礼上,你能不能替我把名字也签上?我很想去,可是也许去不成哩。瞧,沙湾出了一档子淹死人的事件,也许会浮上来。尸体假若找到了,验尸官和我就得去一趟。我要是没到场,就请你把我的名字给塞上好不好?”
“好的,”布卢姆先生说着就走开了。“就这么办吧。”
“好吧,”麦科伊喜形于色地说,“谢谢你啦,老伙计。只要能去,我是会去的。喏,应付一下,写上C·P·麦科伊就行啦。”
“一准办到,”布卢姆先生坚定地说。
那个花招没能使我上当。敏捷地脱了身。笨人就容易上当。我可不是什么冤大头。何况那又是我特别心爱的一只手提箱,皮制的。角上加了护皮,边沿还用铆钉护起,并且装上了双锁。去年举办威克洛[22]艇赛音乐会时,鲍勃·考利把自己那只借给了他。打那以后,就一直没下文啦。
布卢姆先生边朝布伦斯威克街溜达,边漾出微笑。“我太太刚刚接到一份。”满脸雀斑、嗓音像芦笛的女高音。用干酪削成的鼻子。唱一支民间小调嘛,倒还凑合。没有气势。你和我,你晓得吗,咱们的处境相同。这是奉承话。那声音刺耳。难道他就听不出其中的区别来吗?想来那样的才中他的意哩。不知怎地却不合我的胃口。我认为贝尔法斯特那场音乐会会把他吸引住的。我希望那里的天花不至于越闹越厉害。她恐怕是不肯重新种牛痘了。你的老婆和我的老婆。
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
布卢姆先生在街角停下脚步,两眼瞟着那些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坎特雷尔与科克伦姜麦酒(加了香料的)。克勒利[23]的夏季大甩卖。不,他笔直地走下去了。嘿,今晚上演班德曼·帕默夫人的《丽亚》[24]哩。巴不得再看一遍她扮演这个角色。昨晚她演的是哈姆莱特[25]。女扮男装。说不定他本来就是个女的哩。所以奥菲利娅才自杀了。可怜的爸爸!他常提起凯特· 贝特曼[26]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在伦敦的阿德尔菲剧场外面足足等了一个下午才进去的。那是一八六五年——我出生前一年的事。还有里斯托里[27]在维也纳的演出。剧目该怎么叫来着?作者是莫森索尔。是《蕾洁》吧?不是的。[28]他经常谈到的场景是,又老又瞎的亚伯拉罕[29]听出了那声音,就把手指放在他的脸上。
拿单的声音!他儿子的声音!我听到了拿单的声音,他离开了自己的父亲,任他悲惨忧伤地死在我的怀抱里。他就这样离开了父亲的家,并且离开了父亲的上帝[30]。
每句话都讲得那么深沉,利奥波德。
可怜的爸爸!可怜的人!幸而我不曾进屋去瞻仰他的遗容。那是怎样的一天啊!哎呀,天哪!哎呀,天哪!嗬!喏,也许这样对他最好不过。
布卢姆先生拐过街角,从出租马车停车场那些耷拉着脑袋的驽马跟前走边。到了这般地步,再想那档子事也是白搭。这会子该给马套上秣囊了。要是没遇上麦科伊这家伙就好了。
他走近了一些,听到牙齿咀嚼着金色燕麦的嘎吱嘎吱声,轻轻地咀嚼着的牙齿。当他从带股子燕麦清香的马尿气味中走过时,那些马用公羊般的圆鼓鼓的眼睛望着他。这才是它们的理想天地。可怜的傻瓜们!它们一无所知,对什么也漠不关心,只管把长鼻头扎进秣囊里。嘴里塞得那么满,连叫都叫不出来了。好歹能填饱肚子,也不缺睡的地方。而且被阉割过,一片黑色杜仲胶在腰腿之间软软地耷拉下来,摆动着。就那样,它们可能还是蛮幸福的哩。一看就是些善良而可怜的牲口。不过,它们嘶鸣起来也会令人恼火。
他从兜里掏出信来,将它卷在带来的报纸里。说不定会在这儿撞上她。巷子里更安全一些。
他从出租马车夫的车棚前走边。马车夫那种流浪生活真妙。不论什么样的天气,也不管什么地点、时间或距离,都由不得自己的意愿。我要,又不[31]。我喜欢偶尔给他们支香烟抽。交际一下。他们驾车路过的时候,大声嚷出一言半语。他哼唱着:
咱们将手拉着手前往。[32]
啦啦啦啦啦啦。
他拐进坎伯兰街,往前赶了几步,就在车站围墙的背风处停下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米德木材堆放场。堆积起来的梁木。废墟和公寓。他小心翼翼地踱过 “跳房子”游戏的场地,上面还有遗忘下的跳石子儿。我没犯规[33]。一个娃娃孤零零地蹲在木材堆放场附近弹珠儿玩,用灵巧的大拇指弹着球。一只明察秋毫的母花猫,伊然是座眨巴着眼睛的斯芬克斯[34],呆在暖洋洋的窗台上朝这边望着,不忍心打搅他们。据说穆罕默德曾为了不把猫弄醒,竟然将斗篷剪掉一块。把信打开吧。当我在那位年迈的女老师开的学校就读时,也曾玩过弹珠儿,她喜爱木樨草。埃利斯太太的学校[35]。她丈夫叫什么名字来着?用报纸遮着,他打开了那封信。
信里夹的是花。我想是。一朵瓣儿已经压瘪了的黄花。那么,她没生我的气喽?信上怎么说?
亲爱的亨利:
我收到了你的上一封信,很是感谢。遗憾的是,你不喜
欢我上次的信。你为什么要附邮票呢?我非常生气。 我多么
希望能够为这件事惩罚你一下啊。我曾称你作淘气鬼,因为
我不喜欢那另一个世界[36]。请告诉我那另一个字真正的含
意。你在自己家里不幸福吗?你这可怜的小淘气鬼? 我巴不
得能替你做点什么。请告诉我,你对我这个可怜虫有什么看
法。我时常想起你这个名字有多么可爱。亲爱的亨利,咱们
什么时候能见面呢?你简直无法想像我多么经常地想念你。我
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像被你这么吸引过。弄得我心慌意乱。请
给我写一封长信,告诉我更多的事情。不然的话我可要惩罚
你啦,你可要记住。你这淘气鬼,现在你晓得了,假若你不
写信,我会怎样对付你。哦,我多么盼望跟你见面啊。亲爱
的亨利,请别拒绝我的要求,否则我的耐心就要耗尽了。到
那时候我就一古脑儿告诉你。现在,再见吧,心爱的淘气鬼。
今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所以一定要立即回信给苦苦思念你的
玛莎
附言:一定告诉我,你太太使用哪一种香水。我想知道。
他神情严肃地扯下那朵用饰针别着的花儿,嗅了嗅几乎消失殆尽的香气,将它放在胸兜里。花的语言。[37]人们喜欢它,因为谁也听不见。要么就用一束毒花将对方击倒。于是,他慢慢地往前踱着,把信重读一遍,东一个字、西一个词地念出声来。对你郁金香 生气 亲爱的 男人花 惩罚 你的 仙人掌 假若你不 请 可怜虫 勿忘草 我多么盼望 紫罗兰 给亲爱的 玫瑰 当我们快要 银莲花 见面 一古脑儿 淘气鬼 夜茎[38] 太太 玛莎的香水。读完之后,他把信从报纸卷里取出来,又放回到侧兜里。
他心中略有喜意,咧开了嘴。这封信不同于第一封。不知道是不是她亲笔写的。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像我这样的良家少女,品行端正的。随便哪个星期天,等诵完玫瑰经,不妨见见。谢谢你,没什么。谈恋爱时候通常会发生的那种小别扭。然后你追我躲的。就跟同摩莉吵架的时候那么麻烦。抽支雪茄烟能起点镇静作用,总算是麻醉剂嘛。一步步地来。淘气鬼。惩罚。当然喽,生怕措词不当。粗暴吗,为什么不?反正不妨试它一试,一步步地来。
他依然用指头在兜里摆弄着那封信,并且把饰针拔下。这不是根普通的饰针吗?他把它扔在街上。是从她衣服的什么地方取下来的,好几根饰针都别在一起。真奇怪,女人身上总有那么多饰针!没有不带刺的玫瑰。
单调的都柏林口音在他的头脑里响着。那天晚上在库姆[39],两个娘子淋着雨,互相挽着臂在唱:
哦,玛丽亚丢了衬裤的饰针。
她不知道怎么办,
才能不让它脱落,
才能不让它脱落。
饰针?衬裤。头疼得厉害。也许她刚好赶上玫瑰期间[40]。要么就是成天坐着打字的关系。眼睛老盯着,对胃神经不利。你太太使用哪一种香水?谁闹得清这是怎么回事!
才能不让它脱落。
玛莎,玛丽亚。如今我已忘记是在哪儿看到那幅画了。是出自古老大师之手呢,还是为赚钱而制出的赝品?他[41]坐在她们家里,谈着话。挺神秘的。库姆街的那两个姨子也乐意听的。
才能不让它脱落。
傍晚的感觉良好。再也不用到处流浪了。只消懒洋洋地享受这宁静的黄昏,一切全听其自然。忘记一切吧。说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和当地的奇风异俗。另一位头上顶着水罐,在准备晚饭:水果,橄榄,从井里打采的沁凉可口的水。那井像石头一样冰冷,像煞阿什汤的墙壁上的洞[42]。下次去参加小马驾车赛 [43],我得带上个纸杯子。她倾听着,一双大眼睛温柔而且乌黑。告诉她,尽情地说吧。什么也别保留。然后一声叹息,接着是沉默。漫长、漫长、漫长的休息。
他在铁道的拱形陆桥底下走着,一路掏出信封,赶忙把它撕成碎片,朝马路丢去。碎片纷纷散开来,在潮湿的空气中飘零。白茫茫的一片,随后就统统沉落下去了。
亨利·弗罗尔。你蛮可以把一张一百英镑的支票也这么撕掉哩。也不过是一小片纸而已。据说有一回艾弗勋爵[44]在爱尔兰银行就用一张七位数的支票兑换成百万英镑现款。这说明黑啤酒的赚头有多大,可是人家说,他的胞兄阿迪劳恩勋爵[45]依然得每天换四次衬衫,因为他的皮肤上总繁殖虱子或跳蚤。百万英镑,且慢。两便士能买一品脱黑啤酒,四便士能买一夸脱,八便士就是一加仑。不,一加仑得花一先令四便士。二十先令是一先令四便士的多少倍呢?大约十五倍吧。对,正好是十五倍。那就是一千五百万桶黑啤酒喽。
我怎么说起桶来啦?应该说加仑。总归约莫有一百万桶吧。
入站的列车在他的头顶上沉重地响着,车厢一节接着一节。在他的脑袋里,酒桶也在相互碰撞着,黏糊糊的黑啤酒在桶里迸溅着,翻腾着。桶塞一个个地崩掉了,大量混浊的液体淌出来,汇聚在一起,迂回曲折地穿过泥滩,浸漫整个大地。酒池缓缓地打着漩涡,不断地冒起有着宽叶的泡沫花。
他来到诸圣教堂那敞着的后门跟前。边迈进门廊,边摘下帽子,并且从兜里取出名片,塞回到鞣皮帽圈后头。唉呀,我本可以托麦科伊给弄张去穆林加尔的免费车票呢。
门上贴的还是那张告示。十分可敬的耶稣会会士约翰·库米布道,题目是:耶稣会传教士圣彼得·克莱佛尔[46]及非洲传道事业。当格莱斯顿[47]几乎已人事不醒之后,他们仍为他皈依天主教而祷告。新教徒也是一样。要使神学博士威廉·詹·沃尔什[48]皈依真正的宗教。要拯救中国的芸芸众生。不知道他们怎样向中国异教徒宣讲。宁肯要一两鸦片。天朝的子民。对他们而言,这一切是十足的异端邪说。他们的神是如来佛,手托腮帮,安详地侧卧在博物馆里。香烟缭绕。不同于头戴荆冠、钉在十字架上的。“瞧!这个人!”[49]关于三叶苜蓿,圣帕特里克想出的主意太妙了。[50]筷子[51]?康米。马丁·坎宁翰 [52]认识他。他气度不凡。可惜我不曾在他身上下过功夫,没托他让摩莉参加唱诗班,我却托了法利神父。那位神父看上去像个傻瓜,其实不然。他们就是被那么培养出来的。他总不至于戴上蓝眼镜,汗水涔涔地去给黑人施洗礼吧,他会吗?太阳镜闪闪发光,会把他们吸引住。这些厚嘴唇的黑人围成一圈坐着,听得入了迷。这副样子倒蛮有看头哩,活像是一幅静物画。我想,他们准是把他传的道当作牛奶那么舐掉了。
圣石发出的冰冷气息呼唤着他。他踏着磨损了的台阶,推开旋转门,悄悄地从祭坛背后走进去。
正在进行着什么活动,教友的聚会吧。可惜这么空空荡荡的。要是找个不显眼的位子,旁边有个少女倒不赖。谁是我的邻人呢?[53]听着悠扬的音乐,挤在一起坐上一个钟头。就是望午夜弥撒时遇见的那个女人,使人觉得仿佛上了七重天。妇女们跪在长凳上,脖间系着深红色圣巾[54],低看头。有几个跪在祭坛的栏杆那儿。神父嘴里念念有词,双手捧着那东西,从她们前边走过。他在每个人面前都停下来,取出一枚圣体。甩上一两下(难道那是浸泡在水里的不成? [55]),利利索索地送到她嘴里。她的帽子和头耷拉下去。接着就是第二个。她的帽子也立即垂下来。随后是旁边的那个:矮个子的老妪。神父弯下腰,把圣体送进她的嘴里,她不断地咕哝着。那是拉丁文。下一个。闭上眼,张开嘴。是什么来着?Corpus[56]: body。 Corpse[57]。用拉丁文可是个高明的主意。首先,那就会使这些女人感到茫然。收容垂死者的救济院[58]。她们好像并不咀嚼:只是把圣体吞咽下去。吃尸体的碎片,可谓异想天开,正投食人族之所好。
他站在一旁,望着蒙起面纱的她们,沿着过道顺序走来,寻找各自的座位。他走到一条长凳跟前,靠边儿坐下,帽子和报纸捧在怀里。我们还得戴那种活像是一口口深锅的帽子。我们理应照着头型缝制帽子。这儿,那儿,周围那些系着深红色圣巾的女人们依然低看头,等待圣体在她们的胃里融化。真有点像是无酵饼 [59],那种上供用的没有发酵的饼。瞧瞧她们。这会子我敢说圣体使她们感到幸福。就像是吃了棒糖似的。可不是嘛。对,人们管它叫作天使的饼子。这背后还有个宏大的联想,你觉得,心里算是有了那么一种神的王国。初领圣体者[60]。那其实只不过是一便士一撮的骗人的玩艺儿。可这下子她们就都感到是家族大团聚。觉得像是在同一座剧场里,同一道溪流中。我相信她们是这样感觉的,因而也就不大孤独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咱们的教团”了。多余的精力发泄个够,然后,像是狂欢了一场般地走了出来。问题在于,你得真心笃信它。卢尔德[61]的治疗,忘却的河流,诺克[62]的显圣,淌血的圣像[63]。一位老人在那个忏悔阁子旁边打盹儿哪,所以才鼾声不断。盲目的信仰。安然呆在那即将降临的天国怀抱里[64],一切痛苦都止息了。明年这个时候将会苏醒。
他望到神父把圣体杯收好,放回尽里边,对着它跪了片刻,身上那镶有花边的衣裙下边,露出老大的灰色靴底。要是他把里头的饰针弄丢了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后脑勺上秃了一块。他背上写的是I.N.R.I.[65]吗?不,是I·H·S·[66]。有一回我问了问摩莉,她说那是:“I have sinned.”要么就是:“I have suffered.”另外那个呢?是:“Iron nails ran in.”[67]
随便哪个星期天诵完玫瑰经之后,都不妨去见见。请别拒绝我的要求。她蒙着面纱,拎上一只黑色手提包,背着光,出现在暮色苍茫中[68]。她在脖颈间系着根丝带进堂,却暗地里干着另一种勾当,就是这么个性格。那个向政府告密、背叛“常胜军”的家伙,他叫凯里,每天早晨都来领圣体。就在这个教堂里。是啊,彼得·凯里。不,我脑子里想的是彼得·克拉弗。唔,是丹尼斯·凯里[69]。想想看。家里还有老婆和六个娃娃哪。可还一直在策划着那档子暗杀事件。那些“假虔诚”——这个绰号起得好——他们总是带着那么一副狡猾的样子。他们也不是正经的生意人。啊,不,她不在这里。那朵花儿,不,不在。还有,我把那信封撕掉了吗?可不是嘛,就在陆桥底下。
神父在涮圣爵,然后仰脖儿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葡萄酒。这要比大家喝惯了的吉尼斯黑啤酒或是无酒精饮料——惠特利牌都柏林蛇麻子苦味酒或者坎特雷尔与科克伦姜麦酒(加了香料的)都要来得气派。这是上供用的葡萄酒,一口也不给教徒喝;只给他们面饼。一种冷遇。这是虔诚的骗局,却也做得十分得体。不然的话,一个个酒鬼就都会蜂拥而至,全想过过瘾。整个气氛就会变得莫名其妙了。做得十分得体。这样做完全合理。
布卢姆先生回头望了望唱诗班。可惜不会有音乐了。这儿的管风琴究竟是由谁来按的呢?老格林有本事让那架乐器响起来,发出轻微颤音。[70]大家说他在加德纳街[71]每年有五十英镑的进项。那天摩莉的嗓子好极了,她唱的是罗西尼[72]的《站立的圣母》[73]。先由伯纳德·沃恩神父讲道:基督还是彼拉多?基督,可是不要跟我们扯上一个晚上。大家要听的是音乐。用脚打拍子的声音停下了。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曾关照她,要朝那个角落引颈高唱。我感觉到那空气的震颤,那洪亮的嗓门,那仰望着的听众。
什么人……[74]
有些古老的圣教音乐十分精采,像梅尔卡丹特的《最后七句话》[75]。莫扎特的《第十二弥撒曲》,尤其是其中的《荣耀颂》[76]。以前的教皇们热衷于音乐、艺术、雕塑以至各种绘画。帕莱斯特里纳[77]就是个例子。他们生逢盛世,享尽了清福。他们也都健康,准时吟诵《圣教日课》,然后就酿酒。有本笃酒[78]和加尔都西绿酒[79]。可是让一些阉人[80]参加唱诗班却大煞风景。他们唱出什么调调呢?听完神父们自己洪亮的男低音,再去听他们那种嗓音,会觉得挺古怪吧。行家嘛。要是被阉后就毫无感觉了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动于衷。无忧无虑。他们会发福的,对吧?一个个脑满肠肥,身高腿长。兴许是这样的吧。阉割也是个办法。
他看见神父弯下腰去吻祭坛,然后转过身来,祝福全体教友。大家在胸前面了十字,站起来。布卢姆先生四下里打量了一下,然后站起身,隔着会众戴起的帽子望过去。朗诵福音书时,自然要起立喽。随即又统统跪下。他呢,静悄悄地重新在长凳上落坐。神父走下祭坛,捧着那东西,和助祭用拉丁文一问一答着。然后神父跪下,开始望着卡片诵读起来,
“啊,天主,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81]
布卢姆先生为了听得真切一些,就朝前面探探头。用的是英语。丢给他们一块骨头。我依稀想起来了。上次是多久以前来望过弥撒?光荣而圣洁无玷的圣处女。约瑟是她的配偶。彼得[82]和保罗[83]。倘若你能了解这个中情节,就会更有趣一些。这个组织真了不起,一切都接班就绪,有条不紊。忏悔嘛,人人都想做。那么我就一古脑儿对您说出来吧。我悔改,请惩罚我吧。他们手握大权,医生和律师也都只能甘拜下风。女人最渴望忏悔了,而我呢,就嘘嘘嘘嘘嘘嘘。那么你喳喳喳喳喳喳了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低头瞧着指环,好找个借口。回音回廊,隔墙有耳。丈夫要是听见了,会大吃一惊的。这是天主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她就走出来了。其实,所忏悔的只不过是浮皮潦草。多么可爱的羞耻啊。她跪在祭坛前祷告,念着《万福玛利亚》和《至圣玛利亚》。鲜花,香火,蜡烛在融化。她把羞红的脸遮起。救世军[84]不过是赤裸裸的模仿而已。改邪归正的卖淫妇将当众演说:我是怎样找到上主的。那些坐阵罗马的家伙们想必是顽固不化的,他们操纵着整套演出。他们不是也搜刮钱财吗? 一笔笔遗赠也滚滚而来,教皇能够暂且任意支配的圣厅献金[85]。为了我灵魂的安息,敞开大门公开献弥撒。男女修道院。弗马纳[86]的神父站在证人席上陈述。对他吹胡子瞪眼睛是不灵的。所有的提问他都回答得恰到好处。他维护了我们神圣的母亲——教会的自由,使其发扬光大。教会的博士们编出了整套的神学。
神父祷告道:
“圣米迦勒总领天使,请尔护我于攻魔,卫我于邪神恶计。(吾又哀求天主,严儆斥之!)今魔魁恶鬼,遍散普世,肆害人灵。求尔天上大军之帅,仗主权能,麾入地狱。”
神父和助祭站起来走了。诸事完毕。妇女留下来念感谢经。
不如溜之乎也。巴茨[87]修士。他也许会端着募款盘前来:请为复活节捐款。
他站了起来。咦,难道我背心上这两颗钮扣早就开了吗?女人们喜欢看到这样。她们是决不会提醒你的。要是我们,就会说一声,对不起,小姐,这儿(哦) 有那么一点儿(哦)毛毛。要么就是她们的裙子腰身后边有个钩子开了,露出一弯月牙形[88]。倘若你不提醒一声,她们会气恼的: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可她们喜欢你更邋遢一些。幸而不是更靠下边的。他边小心翼翼地扣上钮扣,边沿着两排座位之间的通道走去。穿出正门,步入阳光中。他两眼发花,在冰凉的黑色大理石圣水钵旁边伫立片刻。在他前后各有一位信徒,悄悄地用手蘸了蘸浅浅的圣水。电车,普雷斯科特洗染坊的汽车,一位身穿丧服的寡妇。因为我自己就穿着丧服,所以马上就会留意到。他戴上帽子。几点钟啦?十点一刻。时间还从容。不如去配化妆水。那是在哪儿来着?啊,对,上一次去的是林肯广场的斯威尼药房。开药铺的是轻易不会搬家的。他们那些盛着绿色和金色溶液作为标志的瓶子太重了,不好搬动。汉密尔顿·朗药房,还是发大水的那一年开的张呢。离胡格诺派 [89]的教会墓地不远。赶明儿去一趟吧。
他沿着韦斯特兰横街朝南踱去。哎呀,处方在另外那条裤子里哪,而且那把大门钥匙我也忘记带了。这档子葬事真令人厌烦。不过,噢,可怜的伙计,这怪不得他。上次是什么时候给我开的处方呢?且慢。记得我是拿一枚金镑让他找的钱,想必是本月一号或二号喽。对,他可以查查处方存根嘛。
药剂师一页页地往回翻着。他好像发散出一股粗涩、枯萎的气味。脑壳萎缩了。而且上了年纪。炼金术士们曾四处寻找点金石。麻醉剂使你的神经亢奋起来,接着就使你衰老。然后陷入昏睡状态。为什么呢?是一种副作用。一夜之间仿佛就过了一生。会使你的性格逐渐起变化。从早到晚在草药、药膏、消毒剂中间消磨岁月。周围都是些雪花石膏般纯白的瓶瓶罐罐。乳钵与乳钵槌。Aq.Dist.FoL.Laur. Te Virid,[90]这气味几乎教你一闻就百病消除,犹如牙科医生的门铃。庸医[91]。他应该给自己治治病。干药糖剂啦,乳剂啦。头一个采下药草试看医治自己的那个人,可真得需要点勇气哩。药用植物。可得多加小心。这里有的是足以使你神志昏迷的东西。做个试验吧,能把蓝色的石蕊试纸变成红色。用氯仿处理。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酊剂。安眠药。春药。止痛用的鸦片糖浆对咳嗽有害处。要么是毛气孔被堵塞,要么就是粘痰反而会多起来。唯一的办法是以毒攻毒。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能找到疗法。大自然多么乖巧啊。
“大约两周以前吗,先生?”
“是的,”布卢姆先生说。
他在柜台跟前等待着,慢慢地嗅着药品那冲鼻子的气味以及海绵和丝瓜瓤那满是灰尘的干燥气味,得花不少时间来诉说自己这儿疼那儿疼呢。
“甜杏仁油、安息香酊剂,”布卢姆先生说,“还有香橙花液……”
这确实使她的皮肤细腻白净如蜡一般。
“还有白蜡,”他说。
那会使她的眸子显得格外乌黑。当我扣着袖口上的链扣的时候,她把被单一直拉到眼睛底下望着我,一派西班牙风韵,并闻着自己的体臭。这种家用偏方往往最灵不过:草莓对牙齿好,荨麻加雨水;据说还有在脱脂乳里浸泡过的燕麦片。皮肤的滋润剂。老迈的女王的儿子当中的一个——就是那位奥尔巴尼公爵吧?对,他名叫利奥波德[92]。他只有一层皮肤。我们有三层。更糟的是,还长着疣子、腱膜瘤和粉刺。然而,你也想要香水啊。你太太使用哪一种香水?西班牙皮肤 [93]。香橙花液多么清新啊。那些肥皂的味儿好香,是纯粹的乳白肥皂。还来得及到拐角处去洗个澡——土耳其式的蒸汽浴,外带按摩。泥垢总是积在肚脐眼里。要是由一位漂亮姑娘给按摩就更好了。我还想干那个。是啊,我。在浴缸里干。奇妙的欲望,我。把水排到水星。正经事同找乐子结合起来了。可惜没有时间按摩。反正这一整天都会感到爽快的。葬礼可真教人阴郁。
“哦,先生,”药剂师说,“那是两先令九便士。您带瓶子来了吗?”
“没带,”布卢姆先生说,“请给调配好。今天晚些时候我来取吧。我还要一块这种肥皂。多少钱一块?”
“四便士,先生。”
布卢姆先生把一块肥皂举到鼻孔那儿。蜡状,散发着柠檬的清香。
“我就要这块,”他说,“统共是三先令一便士。”
“是的,先生,”药剂师说,“等您回头来的时候一道付吧,先生。”
“好的,”布卢姆先生说。
他从药房里溜达出来,把卷起的报纸夹在腋下,左手握着那块用纸包着、摸上去凉丝丝的肥皂。
从他的腋窝下边传来班塔姆·莱昂斯的声音,并且伸过一只手:
“喂,布卢姆,有什么顶好的消息?这是今天的报纸吗?给咱看一眼。”
哎哟,他又刮了口髭!那长长的上唇透出一股凉意。为的是显得少相些。他看上去确实傻里傻气的。比我年轻。
班塔姆·莱昂斯用指甲发黑的黄色手指打开了报纸卷儿。这手也该洗一洗了,去去那层泥垢。早安。你用过皮尔牌肥皂吗[94]?他肩膀上落着头皮屑,脑袋瓜儿该抹抹油啦。
“找想知道一下今天参赛的那匹法国马的消息,”班塔姆·莱昂斯说,“他妈的,登在哪儿呢?”
他把折叠起来的报纸弄得沙沙响,下巴颏在高领上扭动着。长了须癣。领子太紧,头发会掉光的。还不如干脆把报纸丢给他,摆脱了拉倒。
“你拿去看吧,”布卢姆先生说。
“阿斯科特。金杯赛。等一等,”班塔姆·莱昂斯喃喃地说,“等一会儿。马克西穆姆二世[95]。”
“我正要把它丢掉呢,”布卢姆先生说。
班塔姆·莱昂斯蓦地抬起眼睛,茫然地斜瞅着他。
“你说什么来着?”他失声说。
“我说,你可以把它留下,”布卢姆先生回答道,“我正想丢掉[96]呢。”
班塔姆·莱昂斯迟疑了片刻,斜睨着,随后把摊开的报纸塞回布卢姆先生怀里。
“我冒冒风险看,”他说,“喏,谢谢你。”
他朝着康威角[97]匆匆走去。祝这小子成功。
布卢姆先生微笑着,将报纸重新叠成整整齐齐的四方形,把肥皂也塞了进去。那家伙的嘴唇长得蠢。赌博。近来这帮人成天泡在那儿。送信的小伙子们为了弄到六便士的赌本竟去偷窃。只要中了彩,一只肥嫩的大火鸡就到手了。你的圣诞节正餐的代价只是三便士。杰克·弗莱明就是为了赌博而盗用公款的,然后远走高飞去了美国。如今在开着一家饭店。他们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埃及的肉锅[98]。
他高高兴兴地朝那盖得像是一座清真寺的澡堂走去。红砖和尖塔都会使你联想到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原来今天学院里正举行运动会[99]。他望了望贴在学院运动场大门上的那张马蹄形海报:骑自行车的恰似锅里的鳕鱼那样蜷缩着身子[100]。多么蹩脚的广告!哪怕做成像车轮那样圆形的也好嘛。辐条上排列起“运动会、运动会、运动会”字样,轮毂上标上“学院”两个大字。这样一来该多醒目啊。
霍恩布洛尔正站在门房那儿。跟他拉拉关系。兴许只消点点头他就会放你进去转一圈哩。你好吗,霍恩布洛尔先生?你好吗,先生?
天气真是再好不过了。要是一辈子都能像这样该有多好。这正是宜于打板球[101]的天气。在遮阳伞下坐成一圈儿,裁判一再下令改变掷球方向。出局。在这里,他们是没有希望打赢的。六比零。然而主将布勒朝左方的外场守场员猛击出一个长球,竟把基尔达尔街俱乐部的玻璃窗给打碎了。顿尼溪集市[102]更合他们的胃口。麦卡锡一上场,我们砸破了那么多脑壳。[103]一阵热浪,不能持久。生命的长河滚滚向前,我们在流逝的人生中所追溯的轨迹比什么都珍贵。 [104]
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吧。一大浴缸清水,沁凉的陶瓷,徐缓地流着。这是我的身体。[105]
他预见到自己那赤裸苍白的身子仰卧在温暖的澡水之胎内,手脚尽情地舒展开来,涂满溶化了的滑溜溜的香皂,被水温和地冲洗着。他看见了水在自己那拧檬色的躯体和四肢上面起着涟漪,并托住他,浮力轻轻地把他往上推;看见了状似肉蕾般的肚脐眼;也看见了自己那撮蓬乱的黑色鬈毛在漂浮;那撮毛围绕着千百万个娃娃的软塌塌的父亲——一朵凋萎的漂浮着的花。
第五章注释
[1]布雷迪公寓是与利穆街交叉的一条巷子,两侧排列着简陋公寓房,故名。
[2]伯特厄尔、(Bethel)是希伯来语“上帝之家”(参看《创世记》 第28章第19节)的译音,系救世军总部。伯特是房子,厄尔是上帝。希伯来文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是aleph(阿列夫),第二个字母是beth(伯特)。
[3]科尼?凯莱赫是奥尼尔殡仪馆的经理,负责为迪格纳穆料理葬事。
[4]汤姆?克南是个茶叶等商品的推销员,曾出现在《都柏林人?圣恩》中。
[5]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下文中的“什么也不干是美妙的”,原文为意大利语。
[6]据第十七章,万斯为布卢姆的母校拉兹马斯?史密斯高中的教师 。这里的大学指大学预科。自一八七八年起,都柏林市教育局要求高中学生参加这种年度考试,成绩好的,可领到助学金。“打榧子”和“紧张的”,原文均为“crag”。这种双关语,中译文无法表达,只好各取一种含意。
[7]原文作:Table:able. Bed: ed. Table和Bed均为英语,意思是“桌子”、“床”。able和ed则是去掉首字的尾音。这种操练号令相当于左、右,左、右。
[8]“他”指爱德华七世。他于一八七四年成为共济会领导人,直到一九 0一年即位才辞去此职。共济会是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十七世纪初开始允许非石匠的名誉会员参加。一般说来,在使用拉丁语系语言的各国中,共济会吸引着自由思想家及反对教权者;在操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诸国,会员则多是白人新教徒。
[9]这是天主教在俗信徒组织(如公教进行会等)的会员所佩带的会徽, 有的将它当成护身符。
[10]“独脚”霍罗翰是《都柏林人?母亲》中的一个人物。他是爱尔兰共和国胜利会副干事,因跛了一条腿,遂有此外号。
[11]高傲仕女,指默雯?塔尔博伊,参看第十五章。布卢姆一时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可敬的”一词令他联想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尤利乌斯?恺撒》第3 幕第2场中安东尼所说的“布鲁图是个可敬的人”一语。
[12]班塔姆?莱昂斯曾出现在《都柏林人》中的《寄寓》一篇里。
[13]布罗德斯通是铁路终点站。布卢姆猜测那位夫人将在那里换乘火车。
[14]“天堂与妖精”是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1779-1852)的叙事诗《拉拉?鲁克,一首东方传奇》(1817)中的一个故事,被关在天堂门外的妖精,为了赎罪,把神最喜欢的礼物送上去,遂得以进门。
[15]尤斯塔斯街是都柏林市南部的一条通向河岸的大街,在都柏林城址附近。
[16]原文为法语。
[17]环道桥在都柏林市东部;横跨利菲河上的环行铁道。
[18]这条广告虽是虚构的,但当时都柏林确实有个名叫 乔冶?W?普勒姆垂(Plumtree)的老板开了一家罐头肉厂。此姓与英语的“李树”拼音相同。“把肉装入罐头”是都柏林粗俗俚语,指性交。第十七章中,布卢姆看到一只肉罐头空罐,暗指摩莉曾与博伊兰偷情。
[19]《都柏林人?圣恩》中提到麦科伊常以太太下乡办事为由,借去旅行包不还。
[20]这里把摇篮曲的一句作了改动,省去“蜂蜜”二字。参看第四章注[70]。
[21]宫廷纸牌,原文作courtcards,是coatcards的传讹。纸牌上的国王(金发先生)、王后(黑发夫人)等人像皆着外套,故名。
[22]威克洛是位于都柏林以南二十六英里的海滨市镇,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艇赛。
[23]克勒利是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大百货公司。
[24]班德曼?帕默夫人(1865-1905)。美国名演员,《自由人报》(1904年6月16日)载有她在都柏林的欢乐剧场扮演《被遗弃的丽亚》(1862)一剧中女主角丽亚的广告。该剧以十八世纪初叶的奥地利农村为背景,对反犹太主义进行了抨击,是美国剧作家约翰?奥古斯丁?戴利(1838-1899)根据德、奥地利剧作家所罗门?赫尔曼?莫森索尔(1821-1877)的剧本《底波拉》(1850)编译而成。
[25]一九0四年六月十六日的《自由人报》曾指出,帕默夫人十五日晚上在欢乐剧场扮演哈姆莱特这个角色时,演得“维妙维肖”。
[26]凯特?贝特曼(1843-1917),美国女演员,以扮演麦可白夫人著称。她在阿德尔菲剧场扮演丽亚获得巨大成功。但这是一八六三年的事,而不是文中所说的一八六五年。
[27]阿德莱德?里斯托里(1822-1906),颇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悲剧女演员,生于奥匈帝国,曾在维也纳扮演过丽亚这个角色。
[28]莫森索尔所写的戏应作《底波拉》(见本章注[24])。剧中人名均借自《创世记》,所以布卢姆搞混了。丽亚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第一个妻子。雅各原来想娶丽亚的妹妹蕾洁。但根据当地风俗,小女儿不能先嫁,所以做父亲的拉班便让大女儿顶替嫁了过去(见《创世记》第25、27、29节)。底波拉是丽百加(雅各之母)的奶妈(见《创世记》第35章第8节)。
[29]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在《被遗弃的丽亚》中,他是个双目失明的犹太老人,曾为拿单之父送葬。
[30]拿单是个变节的犹太人。他遗弃了丽亚(一个犹太姑娘),并隐瞒自己的身份,冒充基督教徒。亚伯拉罕识破了拿单的真实面目,因而被拿单扼死。
[31]原文为意大利语。此句不完整,参看第四章注[51]。
[32]原文为意大利语。参看第四章注[49]。
[33]玩“跳房子”游戏时,如果踩着了线,孩子们便喊“犯规了,犯规了”。这里是说明布卢姆走过场地时没踩着线。
[34]斯芬克斯是常见于古埃及和希腊的艺术作品和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物。
[35]据第十七章,布卢姆小时曾进过埃利斯太太创办的幼儿学校。
[36]原文中,玛莎把word(字)误写成了world(世界)。
[37]欧洲一向有给花赋以某种象征意义的传统。伦敦出版过一本无名氏所编的辞典《花的语言》,献辞写于一九一三年。其中对七百多种花的含意作了诠释。下面,布卢姆一面读玛莎的信,一面联想到一些花,例如玫瑰就象征着爱与美。
[38]夜茎是一种茄属有毒植物。
[39]库姆是圣柏特里克大教堂西边的一条街,现为贫民窟。
[40]玫瑰期间暗指经期。
[41]“他”指耶稣。据《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至42节,耶稣曾在玛莎和玛丽亚两姐妹家中做客。玛莎忙于接待,玛丽亚则“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玛莎要妹妹也来帮帮忙,耶稣却说,“玛莎!玛莎!你为许多事操心忙乱,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丽亚已经选择了最好的,没有人能从她手中夺走。”这里,打字员玛莎刚好与玛莎同名,玛丽亚又与歌中的女主角同名。
[42]阿什汤是凤凰公园的一座大门,旁边墙壁上有个洞。选民从洞里伸进手去,就可以拿到一把硬币。这样,他就可以发誓否认见过行贿者,或发生过此等事。
[43]每年一度的巴尔斯市里奇马匹展示会(参看苇七章注[32])期间,在凤凰公园的阿什汤大门外面曾经举行过小马驾车赛,后来取消。
[44]艾弗勋爵即爱德华?塞西尔?吉尼斯(1847-1927),为曾任都柏林市长的酿酒商本杰明?李?吉尼斯(1798-1868)之第三子,与其兄亚瑟同为吉尼斯公司股东。酿制烈性黑啤酒的吉尼斯公司是他们的祖父一七五九年在都柏林创立的。
[45]阿迪劳恩勋爵即亚瑟?吉尼斯(1840-1915),政治家,曾任皇家都柏林学会会长。
[46]圣彼得?克莱佛尔(1581-1654),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六一O年曾赴当时南美洲的主要奴隶市场卡塔赫纳(今哥伦比亚境内)传教。前文中的康米神父,见第十章注[1]。
[47]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历任四届首相。他一直赞同爱尔兰自治并曾于一八八六年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尽管在议会中遭到否决,却赢得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好感。
[48]威廉?詹?沃尔什(1841-1921),一八八五年任都柏林罗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
[49]原文是拉丁文,指耶稣。据《约翰福音》第19章,兵士给耶稣戴上荆冠后,罗马总督彼拉多指着耶稣,对众人说了此话。后来便转义为头戴荆冠的耶稣。
[50]圣帕特里克(活动时期约在5 世纪后半叶)是在爱尔兰建立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罗马教廷谥为圣徒。他用柄上长着三叶的苜蓿来象征天主的三位一体,此花遂成为爱尔兰的国花,每年二月十七日的圣帕特里克节,爱尔兰人均在襟上佩带之。
[51]“筷子”可能是由前文所提的中国人而联想到的,也可能是指下文提到的康米瘦得像筷子。
[52]马丁?坎宁翰是以都柏林堡的一个官员马修?凯恩为原型而塑造的,出现在《都柏林人?圣恩》中。
[53]这原是《路加福音》第10章第29节中法律教师问耶稣的话。这里, 则变成一位少女对坐到自己身旁的人感到的好奇。 等于在问:“坐在我旁边这个人是谁呀?”
[54]圣巾是天主教在俗组织聚会时系的肩巾。
[55]神父把圣体送进教友口中时,一般总先甩一两下,看上去像是把圣体上的水甩掉一般,因而引起这样的联想。
[56]Corpus,拉丁文,意思是身体、物体,也作尸体解。英文中,此词也指身体、躯体,并作为谐谑语,指尸体。
[57]body,英文,意思是身体、物体,也作尸体解。Corpse,英文,意思是尸体。
[58]指天主教慈善会修女所创办的圣母救济院。
[59]无酵饼,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第15节,天主要求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月,守无酵节;在节期的七天里,吃无酵饼。
[60]凡出生后就受洗者,通常在七岁时初领圣体。
[61]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省一城镇。一八五八年、一个女孩在该镇附近河流左岸洞穴中幻见到圣母玛利亚。从此,洞穴中的地下水被奉为神水,每年必有众多残疾人赴该地朝圣求治。
[62]诺克是爱尔兰康诺特省梅奥郡的戈尔韦湾附近一荒村。传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O年,圣母玛利亚数次显圣给孩村的天主教徒,使其疾病奇迹般地得以治愈。
[63]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像淌血的传说,见克拉拉?厄斯金?克莱门特所著《传说中的神话艺术手册》(波士顿,1891年版)。
[64]“安……里”一语、系套用范妮?克罗斯比作词、W?H?多恩配曲的《虔诚之歌》(1869)中的首句:“安然地呆在耶稣怀抱里”。只是将“耶稣”改为祷词“即将降临的天国”。
[65]这是拉丁文lesus Nazarenus Rex ludaeorum的首字,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之王。”
[66]这是拉丁文lesus Hominum Salvalor的首字,意思是:“万人的救主耶稣。”
[67]以上三句话均为英文,意思分别为:“我犯了罪”;“我受了苦”;“把铁钉扎了进去”。摩莉把拉丁字母当作英文,这么乱猜。
[68]“背着光,出现在暮色苍茫中”,引自英国剧作家威廉?施文克?吉尔伯特(1836-1911)与沙利文编写的喜剧《陪审团的审判》(1875)。原话是指借此能遮掩那位阔小姐的年衰貌丑等缺陷。
[69]此人实名詹姆斯?凯里(1845-1883),是“常胜军”的指导成员之一,曾参加凤凰公园的暗杀事件。被捕后,出卖同伙,致使其被绞死。由于害怕“常胜军”报复,他曾化名鲍尔,欲逃往南非,被帕特里克?奥唐奈击毙。他有个兄弟叫彼得,也与“常胜军”有关连。
[70]“轻微颤音”,原文为意大利语。
[71]指坐落于该街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
[72]乔亚其诺?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73]原文为拉丁文。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悲恸的圣母站立在十字架脚下。
[74]原文为拉丁文。这是《站立的圣母》第3段的开头。全句是:“什么人看见基督的母亲如此悲痛,能够不落泪呢?”
[75]萨弗里奥?梅尔卡丹特(1795-1870),生在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作曲家,编写过六十来个歌剧。《最后的七句话》是他根据《福音书》上所载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弥留之际说的七句话所谱的曲子。
[76]原文为拉丁文。
[77]帕莱斯特里纳(参看第一章注[110])创作了大量优美的宗教与世俗音乐,一五七八年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授予音乐大师称号。
[78]本笃酒是天主教本笃会教士所酿的一种甜酒,产于法国费康,亦名本尼迪克酒。
[79]这是天主教修会加尔都西会教士在法国境内加尔都西山谷所酿造的荨麻酒。
[80]过去梵蒂冈教廷唱诗班为了使男童歌手保持女高音或女低音声调,将其阉割。直到一八七八年教皇利奥十三世(1810-1908)登位,才明令禁止。
[81]见《诗篇》,第46篇第1节。
[82]彼得是早期基督教会所称耶稣十二门徒之首。
[83)保罗(活动时期1世纪),耶稣的使徒之一,基督教传教士。
[84]救世军的创办者是循道会牧师W?布斯。自一八六五年起, 他开始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中传教,一八七八年他将自己创立的组织易名为“救世军”。其宗教活动的特点之一,是皈依者当众忏悔。
[85]圣厅献金是一八七0年起实行的一种由教徒捐款作为教皇生活费的制度,一九三九年废止。
[86]弗马纳是北爱尔兰一郡。
[87]原文作Buzz,可作“忙来忙去”或“扒手”解。前文中的“圣米……地狱”为弥撒后所诵经文。
[88]“露出一弯月牙形”一语套用《哈姆莱特》第1幕第4场中哈姆莱特对霍拉旭所说的话。下文中的“更靠下面的”,原文作“更靠南面的”,即指更靠下面的裤钮。
[89]胡格诺派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的新教教派,长期惨遭迫害。十七世纪末,被迫大批逃亡到英格兰、爱尔兰、美洲等地。
[9O]Aq.Dist(蒸馏水)、FolLaur(月桂叶)、TeVirid(绿茶)均为拉丁文。
[91]原文作doctor Whack. doctor是医生。whacker含有弥天大谎意,即指庸医。
[92]利奥波德?奥尔巴尼公爵(1853-1884)、维多利亚女王的幼子。他患的实际上是血友病,世人则以为他是由于皮肤比一般人薄,才动辄出血不止。
[93]原文为法语。
[94]布卢姆看到莱昂斯的手脏,便联想起这句风靡一时的肥皂广告用语。
[95]阿斯科特是英格兰地名。在伯克郡温莎-梅登黑德区,距伦敦二十六英里。每年六月举行为期四天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胜者获金杯奖。布卢姆拿给莱昂斯看的六月十六日的《自由人报》上刊有参赛马匹的全部名单,马克西穆姆二世便是其中的一匹。
[96]英语中,throw away是“丢掉”的意思。莱昂斯满脑子都是赛马的事。这里他误以为希卢姆在劝他把赌注压在一匹名叫“丢掉”(Throwaway)的马身上。
[97]康威角指康威酒吧间。角(原文作er)为伦敦的塔特索尔马市场和赛马场的俗称。以后那些兼售马券的私营酒吧间也在店名后面加上er一词。
[98]据《出埃及记》第16章,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曾在旷野里挨饿,于是说:“在埃及,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肉……”作者用这个典故暗指新到一个地方去的人们不免怀念故土。
[99]指在三一学院(也叫都柏林大学,建于一五九一年,是爱尔兰最古老的学府)举行的赛车会。下文中的霍恩布洛尔是该校司阍。
[100]这里套用《约翰尼,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一歌中佩吉对伤兵约翰尼说的话。原词是,“你像条鳕鱼那样头尾都蜷缩在一起。”
[101]板球是英国夏季的国球,使用船桨式木板击球。
[102]顿尼溪是都柏林市以南一小镇。自十三世纪起,每年举行一次以酒色、赌斗著称的集市,一八五五年被禁止。顿尼溪集市后来遂成为扰嚷吵闹的代名词。
[103]“麦……壳”一语出自罗伯特?马丁所作的歌曲《恩尼斯卡锡》。恩尼斯卡锡是韦克斯福德郡的一个小镇。
[104]“生……贵”一语出自爱德华?菲茨勃尔(1792-1873)编写、爱尔兰作曲家威廉?文森特?华莱士(1813-1865)配乐的歌剧《玛丽塔娜》(1845)第2幕第1场。
[105]“这……体”,套用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见《路加福音》第22章第19节。
第六章 1
马丁·坎宁翰首先把戴着丝质大礼帽的头伸进嘎嘎作响的马车,轻捷地进去落座了。鲍尔[1]先生小心翼翼地弯着修长的身躯,跟在他后面也上了车。
“来吧,西蒙。”
“您先上,”布卢姆先生说。
迪达勒斯先生匆匆戴上帽子,边上车边说:
“好的,好的。”
“人都齐了吗?”马丁·坎宁翰问:“上车吧,布卢姆。”
布卢姆先生上了车,在空位子上落座。他反手带上车门,咣噹了两下,直到把它撞严实了才撒手。他将一只胳膊套在拉手吊带里,神情严肃地从敞着的车窗里眺望马路旁那一扇扇拉得低低的百叶窗[2]。有一副帘子被拉到一边,一个老妪正向外窥视。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又白又扁。她在感谢命运这一遭儿总算饶过了自已。妇女们对尸体所表示的兴趣是异乎寻常的。我们来到世上时给了她们那么多麻烦,所以她们乐意看到我们走。她们好像适合于干这种活儿。在角落里鬼鬼祟祟的。趿拉着拖鞋,轻手轻脚地,生怕惊醒了他。然后给他装裹,以便入殓。摩莉和弗莱明大妈[3]在往棺材里面铺着什么。再往你那边拽拽呀。我们的包尸布。你决不会知道自己死后谁会来摸你。洗身子啦,洗头啦。我相信她们还会给他剪指甲和头发,并且装在信封里保存一点儿。这之后,照样会长哩。这可是件脏活儿。
大家伫候着,谁也不吭一声儿。大概是在装花圈哪。我坐在硬邦邦的东西上面。唔,原来是我后裤兜儿里的那块香皂。最好把它挪一挪,等有机会再说。
大家全在伫候。过一会儿,前方传来了车轮的转动声,越来越挨近,接着就是马蹄声。车身颠簸了一下。他们的马车开始前进了,摇摇摆摆,吱嘎作响。后面也响起了另外一些马蹄的声音和车轱辘的吱吜声。马路旁的百叶窗向后移动;门环上蒙着黑纱的九号[4]那半掩着的大门,也以步行的速度过去了。
他们依然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膝盖抖动着。直到车子拐了个弯,沿着电车轨道走去,这时才打破了沉寂。特里顿维尔路。速度加快了。车轮在卵石铺成的公路上咯噔咯噔地向前滚动,像是发了疯似的玻璃在车门框里咔嗒咔嗒地震颤着。
“他这是拉着咱们走哪条路啊?”鲍尔先生隔看车窗边东张西望,边问。
“爱尔兰区,”马丁·坎宁翰说,“这是林森德。布伦斯威克大街。”
迪达勒斯先生朝车窗外望着,点了点头。
“这是个古老的好风习[5],”他说,“我很高兴如今还没有废除。”
大家隔看车窗望了望。行人纷纷脱便帽或礼帽,表示敬意呢。马车径过沃特利巷后就离开电车轨道,走上较为平坦的路。布卢姆先生定睛望望,只见有个身材细溜、穿着丧服、头戴宽檐帽的青年。
“迪达勒斯,你的一个熟人刚刚走过去了,”他说。
“谁呀?”
“你的公子和继承人。”
“他在哪儿?”迪达勒斯说着,斜探过身子来。
马车正沿着一排公寓房子驰去,房前的路面上挖出一条条明沟,沟旁是一溜儿土堆。在拐角处车身蓦地歪了歪,又折回到电车轨道上了,车轮喧闹地咯噔咯噔向前滚动。迪达勒斯先生往后靠了靠身子,说:
“穆利根那家伙跟他在一道吗?他的忠实的阿卡帖斯[6]!”
“没有,”布卢姆先生说,“就他一个人。”
“大概是看他的萨莉舅妈去啦,”迪达勒斯说,“古尔丁那一伙儿,喝得醉醺醺的小成本会计师,还有克莉西,爸爸的小屎橛子,知父莫如聪明的小妞儿。”
布卢姆先生望着林森德路凄然一笑。华莱士兄弟瓶厂:多德尔桥。
里奇·古尔丁和律师用的公文包。他管这事务所叫作古尔丁-科利斯- 沃德[7]。他开的玩笑如今越来越没味儿了。从前他可是个大淘气包。一个星期天早晨,他用饰针把房东太太的两顶帽子别在头上,同伊格内修斯·加拉赫[8] 一道在斯塔默街上跳起华尔兹舞,通宵达旦地在外边疯闹。如今他可垮下来了,我看他的背痛,就是当年埋下的根子。老婆替他按摩背。他满以为服点药丸就能痊愈。其实那统统都只不过是面包渣子。利润高达百分之六百左右。
“他跟一帮下贱痞子鬼混,”迪达勒斯先生骂道,“大家都说,那个穆利根就是个坏透了的流氓,心肠狠毒,堕落到了极点。他的名字臭遍了整个都柏林城。在天主和圣母的佑助下,我迟早非写封信给他老娘、姑妈或是什么人不可。叫她看了,会把眼睛瞪得像门一样大。我要隔肢他屁股![9]我说话算数。”
他用大得足以压住车轮咯咯声的嗓门嚷着:
“我绝不能听任她那个杂种侄子毁掉我儿子。他爹是个站柜台的,在我表弟彼得·保罗·麦克斯威尼的店里卖棉线带。我决不让他得逞。”
他住了嘴。布卢姆先生把视线从他那愤怒的口髭,移到鲍尔先生那和蔼的面容,以及马丁·坎宁翰的眼睛和严肃地摇曳着的胡子上。好一个吵吵闹闹、固执己见的人。满脑子都是儿子。他说得对。总得有个继承人啊。倘若小鲁迪还在世的话,我就可以看看他长大。在家里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穿着一身伊顿[10]式的制服,和摩莉并肩而行。我的儿子。他眼中的我。那必然会是一番异样的感觉。我的子嗣。纯粹是出于偶然。准是那天早晨发生在雷蒙德高台街的事。她正从窗口眺望着两条狗在“停止作恶”[11]的墙边搞着。有个警官笑嘻嘻地仰望着。她穿的是那件奶油色长袍,已经绽了线,可她始终也没缝上。摸摸我,波尔迪。天哪,我想得要死。这就是生命的起源。
于是,她有了身孕。葛雷斯顿斯[12]音乐会的邀请也只好推掉。我的儿子在她肚子里。倘若他活着,我原是可以一直帮助他的。那是肯定的。让他能够自立,还学会德语。
“咱们来迟了吗?”鲍尔先生问。
“迟了十分钟,”马丁·坎宁翰边看看表边说。
摩莉。米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就是单薄了一点。是个假小子,满嘴村话。呸,跳跳蹦蹦的朱庇特哪!你这天神和小鱼儿哪!可她毕竟是个招人疼的好姐儿,很快就要成为妇人啦。穆林加尔。最亲爱的爹爹。年轻学生。是啊,是啊,也是个妇人哩。人生啊,人生。
马车左摇右晃,他们四个人的身躯也跟着颠簸。
“科尼蛮可以给咱们套一辆更宽绰些的车嘛,”鲍尔先生说。
“他原是可以的,”迪达勒斯先生说,“要不是被那斜视症折腾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阖上了左眼。马丁·坎宁翰开始把腿下的面包渣子撢掉。
“这是什么呀,”他说,“天哪,是面包渣儿吗?”
“想必新近有人在这儿举行过野餐哩,”鲍尔先生说。
大家都抬起腿来,厌恶地瞅着那散发着霉臭、扣子也脱落了的座位皮面。迪达勒斯先生抽着鼻子,蹙眉朝下望望说:
“除非是我完全误会了……你觉得怎么样,马丁?”
“我也这么认为,”马丁·坎宁翰说。
布卢姆先生把大腿放下来。亏得我洗了那个澡。脚上感到很清爽。可要是弗莱明大妈替我把这双短袜补得更细一点就好了。
迪达勒浙先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这毕竟是,”他说,“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汤姆·克南露面了吗?”马丁·坎宁翰慢条斯理地捻着胡子梢儿,问道。
“来啦,”布卢姆先生回答说:“他跟内德·兰伯特[13]和海因斯[14]一道坐在后面哪。”
“还有科尼、凯莱赫本人呢?”鲍尔先生问。
“他到公墓去啦,”马丁·坎宁翰说。
“今天早晨我遇见了麦科伊,”布卢姆先生说,“他说他尽可能来。”
马车猛地停住了。
“怎么啦?”
“堵车了。”
“咱们这是在哪儿呢?”
布卢姆先生从车窗里探出头去。
“大运河,”他说。
煤气厂。听说这能治百日咳哩。亏得米莉从来没患上过。可怜的娃娃们! 痉挛得都蜷缩成一团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真够受的。相形之下,她患的病倒比较轻,不过是麻疹而已。煎亚麻籽[15]。猩红热。流行性感冒。我这是在替死神兜揽广告哪。可别错过这个机会。狗收容所就在那边。可怜的老阿索斯[16]! 好好照料阿索斯,利奥波德,这是我最后的愿望。愿你的旨意实现[17]。对坟墓里的人们我们总是唯命是从。那是他弥留之际潦潦草草写下的。狗伤心得衰竭而死。那是一只温和驯顺的家畜。老人养的狗通常都是这样的。
吧嗒一声一滴雨点落在他的帽子上。他缩回脖子。接着,一阵骤雨嘀嘀嗒嗒地落在灰色的石板路上。奇怪,稀稀落落的,就像是漏勺滤下来的。我料到会下。想起来啦,我的靴子咯吱咯吱直响来着。
“变天啦,”他安详地说。
“可惜没一直晴下去,”马丁·坎宁翰说。
“乡下可盼着雨哪,”鲍尔先生说,“太阳又出来啦。”
迪达勒斯先生透过眼镜凝视着那遮着一层云彩的太阳,朝天空默默地发出诅咒。
“它就跟娃娃的屁股一样没准儿,”他说。
“咱们又走啦。”
马车又转动起那硬邦邦的轱辘了。他们的身子轻轻地晃悠着。马丁·坎宁翰加快了捻胡须梢儿的动作。
“昨天晚上汤姆·克南真了不起,”他说,“帕迪·伦纳德[18]当面学他那样儿取笑他。”
“噢,马丁,把他的话都引出来吧,”鲍尔先生起劲地说,“西蒙,你等着听克南对本·多拉德唱的《推平头的小伙子》[19]所做的评论吧。”
“了不起,”马丁·坎宁翰用夸张的口气说,“马丁啊,他把那支纯朴的民歌唱绝了,是我这辈子所听到的气势最为磅礴的演唱。”
“气势磅礴,”鲍尔先生笑着说,“他最喜欢用这个字眼,还爱说‘回顾性的编排’。”[20]
“你们读了丹·道森的演说吗?”马丁·坎宁翰问。
“我还没读呢,”迪达勒斯先生说,“登在哪儿啦?”
“今天早晨的报纸上。”
布卢姆先生从内兜里取出那张报。我得给她换那本书。
“别,别,”迪达勒斯先生连忙说,“回头再说吧。”
布卢姆先生的目光顺着报纸过往下扫视着讣闻栏:卡伦、科尔曼、迪格纳穆、福西特、劳里、瑙曼、皮克。是哪个皮克[21]呢?是在克罗斯比——艾莱恩那儿工作的那家伙吗?不对,是厄布赖特教堂同事。报纸磨破了,上头的油墨字迹很快就模糊了。向“小花”[22]致以谢忱。深切的哀悼。遗族难以形容的悲恸。久患顽症,医治无效,终年八十八岁。为昆兰举行的周月追思弥撒。仁慈的耶稣,怜悯他的灵魂吧。
亲人亨利已遁去,
住进天室今月弥,
遗族哀伤并悲泣,
翘盼苍穹重相聚。
我把那个信封撕掉了吗?撕掉啦。我在澡堂子里看完她那封信之后,放在哪儿啦?他拍了拍背心上的兜。在这儿放得安安妥妥的。亲人亨利已遁去。趁着我的耐心还没有耗尽。
国立小学。米德木材堆放场。出租马车停车场。如今只剩下两辆了。马在打磕睡,肚子鼓得像壁虱。马的头盖上,骨头太多了。另一辆载着客人转悠哪。一个钟头以前,我曾打这儿经过。马车夫们举了举帽子。
在布卢姆先生这扇车窗旁边,一个弯着腰的扳道员忽然背着电车的电杆直起了身子。难道他们不能发明一种自动装置吗?那样,车轮转动得就更便当了。不过,那样一来就会砸掉此人饭碗了吧?但是另一个人都会捞到制造这种新发明的工作吧?
安蒂恩特音乐堂。眼下什么节目也没上演。有个身穿一套淡黄色衣服的男子,臂上佩带着黑纱。他服的是轻丧,不像是怎么悲伤的样子。兴许是个姻亲吧。
他们默默地经过铁道陆桥下圣马可教堂那光秃秃的讲道坊,又经过女王剧院。海报牌上是尤金·斯特拉顿[23]和班德曼·帕默夫人。也不晓得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去看《丽亚》。我原说是要去的。要么就去看《基拉尼的百合》[24]吧?由埃尔斯特·格莱姆斯歌剧团演出。做了大胆的革新。刚刚刷上去、色彩鲜艳的下周节目预告:《布里斯托尔号的愉快航行》[25]。马丁·坎宁翰总能替我弄到一张欢乐剧院的免费券吧。得请他喝上一两杯,反正是一个样。
下午他[26]就来了。她的歌儿。
普拉斯托帽店。纪念菲利普·克兰普顿爵士[27]的喷泉雕像。这是谁[28]呀?
“你好!”马丁·坎宁翰边说边把巴掌举到额头那儿行礼。
“他没瞧见咱们,”鲍尔先生说,“啊,他瞧见啦。你好!”
“是谁呀?”迪达勒斯先生问。
“是布莱泽斯·博伊兰,”鲍尔先生说,他正摘下帽子让他的鬈发透透风哪。
此刻我刚好想到了他。
迪达勒斯先生探过身去打招呼。红沙洲餐厅[29]的门口那儿,白色圆盘状的草帽闪了一下,作为回礼。潇洒的身影过去了。
布卢姆先生端详了一下自已左手的指甲,接着又看右手的。是呀,指甲。除了魅力而外,妇女们,她,在他身上还能看得到旁的什么呢?魅力。他是都柏林最坏的家伙,却凭着这一点活得欢欢势势。妇女们有时能够感觉出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本能。然而像他那种类型的人嘛。我的指甲。我正瞅着指甲呢。修剪得整整齐齐。然后,我就独自在想着。浑身的皮肉有点儿松软了。我能发觉这一点,因为我记得原先是什么样子。这是怎么造成的呢?估计是肉掉了,而皮肤收缩得却没那么快。但是身材总算保持下来了。依然保持了身材。肩膀。臀部。挺丰满的。舞会的晚上换装时,衬衣后摆竟夹在屁股缝儿里了。
他十指交叉,夹在双膝之间,感到心满意足,茫然地环视着他们的脸。
鲍尔先生问:
“巡回音乐会进行得怎样啦,布卢姆?”
“哦,好极啦,”布卢姆先生说,“我听说,颇受重视哩。你瞧,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你本人也去吗?”
“哦,不,”布卢姆先生说,“说实在的,我得到克莱尔郡[30]去办点私事。你要知道,这个计划是把几座主要城镇都转上一圈。这儿闹了亏空,可以上那儿去弥补。”
“可不是嘛,”马丁·坎宁翰说,“玛丽·安德森[31]眼下在北边哪。你们有能手吗?”
“路易斯·沃纳[32]是我老婆的经纪人,”布卢姆先生说,“啊,对呀, 所有那些第一流的我们都能邀来。我希望J·C.多伊尔和约翰·麦科马克[33]也会来。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还有夫人[34]哪,”鲍尔先生笑眯眯地说,“压轴儿的。”
布卢姆先生松开手指,打了个谦恭和蔼的手势,随即双手交叉起来。史密斯·奥布赖恩[35]。有人在那儿放了一束鲜花。女人。准是他的忌日喽。多福多寿。[36]马车从法雷尔[37]所塑造的那座雕像跟前拐了个弯。于是,他们就听任膝头毫无声息地碰在一起。
“靴子……”
一个衣着不起眼的老人站在路边,举着他要卖的东西,张着嘴,靴。
“靴子带儿,一便士四根。”
不晓得此人是怎么被除名的。本来他在休姆街开过自己的事务所。跟与摩莉同姓的那位沃德福德郡政府律师特威迪在同一座房屋里。打那时候起,就有了那顶大礼帽。住昔体面身份的遗迹。[38]他还服着丧哪。可怜的苦命人,潦倒不堪!像是守灵夜的鼻烟似的,被人踢来踢去。[39]奥卡拉汉已经落魄了 [40]。
还有夫人[41]哪。十一点二十分了。起床啦。弗莱明大妈已经来打扫了。她一边哼唱,一边梳理头发。我要,又不愿意。[42]不,应该是,我愿意,又不愿意。[43]她在端详自己的头发梢儿分叉了没有。我的心跳得快了一点儿。[44]唱到tre这个音节时,她的嗓音多么圆润,声调有多么凄切。鸫鸟。画眉。画眉一词正是用来形容这种歌喉的。
他悄悄地扫视了一下鲍尔先生那张五官端正的脸。鬓角已花白了。他是笑眯眯地提到夫人的,我也报以微笑。微微笑,顶大用。也许只是出于礼貌吧。蛮好的一个人。人家说他有外遇,谁晓得是真是假?反正对他老婆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然而他们又说——是什么人告诉我的来着?并没有发生肉体关系。谁都会认为,那样很快就会吹台的。对啦,是克罗夫顿[45]。有个傍晚撞见他正给她带去一磅牛腿扒。她是干什么的来着?朱里饭店的酒吧女招待,要么就是莫伊拉饭店的吧?
他们从那位披着八斗篷的解放者[46]的铜像下面经过。
马丁·坎宁翰用臂肘轻轻地碰了碰鲍尔先生。
“吕便支族的后裔[47],”他说。
一个留着黑胡须的高大身影,弯腰拄着拐棍,趔趔趄趄地绕过埃尔韦里的象记商店[48]拐角,只见一只张着的手巴掌弯过来放在脊梁上。
“保留了原始的全部英姿,”鲍尔先生说。
迪达勒斯先生目送着那抱着沉重脚步而去的背影,温和地说:
“就欠恶魔没弄断你那脊梁骨的大筋啦!”
鲍尔先生在窗边一手遮着脸,笑得弯了腰。这时马车正从格雷[49]的雕像前经过。
“咱们都到他那儿去过了,”马丁·坎宁翰直率地说。
他的目光同布卢姆先生的相遇。他捋捋胡子,补上一句:
“喏,差不多人人都去过啦。”
布卢姆先生望着那些同车人的脸,抽冷子热切地说了起来:
“关于吕便·杰和他儿子,有个非常精彩的传闻。”
“是船家那档子事吗?”鲍尔先生问。
“是啊。非常精彩吧?”
“什么事呀?”迪达勒斯先生问,“我没听说。”
“牵涉到一位姑娘,”布卢姆先生讲起来了,“于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打定主意把儿子送到曼岛[50]上去。可是爷儿俩正……”
“什么?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小伙子吗?”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爷儿俩正要去搭船,他却想跳下水去淹死……”
“淹死巴拉巴[51]!老天爷,我但愿他能淹死!”
鲍尔先生从那用手遮住的鼻孔里发出的笑声持续了好半晌。
“不是,”布卢姆先生说,“是儿子本人……”
马丁·坎宁翰粗暴地插嘴说,
“吕便·杰和他儿子沿着河边的码头往下走,正准备搭乘开往曼岛的船,那个小骗子忽然溜掉,翻过堤坝纵身跳进了利菲河。”
“天哪!”迪达勒斯先生惊吓得大吼一声,“他死了吗?”
“死!”马丁·坎宁翰大声说,“他可死不了!有个船夫弄来根竿子,钩住他的裤子,把他捞上岸,半死不活地拖到码头上他老子跟前。全城的人有一半都在那儿围观哪。”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最逗的是……”
“而吕便·杰呢,”马丁·坎宁翰说,“为了酬劳船夫救了他儿子一条命,给了他两个先令。”
从鲍尔先生手下传来一声低微的叹息。
“哦,可不是嘛,”马丁·坎宁翰斩钉截铁地说,“摆出大人物的架势,赏了他一枚两先令银币。”
“非常精彩,对吗?”布卢姆先生殷切地说。
“多付了一先令八便士,”迪达勒斯先生用冷漠的口吻说。
鲍尔先生忍俊不禁,马车里回荡着低笑声。
纳尔逊纪念柱[52]。
“八个李子一便士!八个才一便士!”
“咱们最好显得严肃一些,”马丁·坎宁翰说。
迪达勒斯先生叹了口气。
“不过,说实在的,”他说,“即便笑一笑,可怜的小帕狄也不会在意的。他自己就讲过不少非常逗趣儿的话。”
“天主宽恕我!”鲍尔先生用手指揩着盈眶的泪水说,“可怜的帕迪!一个星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跟平素一样那么精神抖擞呢。我再也设想到会这么乘马车给他送葬。他撇下咱们走啦。”
“戴过帽子[53]的小个儿当中,难得找到这么正派的,”迪达勒斯先生说,“他走得着实突然。”
“衰竭,”马丁·坎宁翰说,“心脏。”
他悲痛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满脸通红,像团火焰。威士忌喝多了。红鼻头疗法。拼死拼活地灌,把鼻头喝成灰黄色的了。为了把鼻头变成那种颜色,他钱可没少花。
鲍尔先生定睛望着往后退去的那些房屋,黯然神伤。
“他死得真是突然,可怜的人,”他说。
“这样死再好不过啦,”布卢姆先生说。
大家对他膛目而视。
“一点儿也没受罪,”他说,“一眨眼就都完啦。就像在睡眠中死去了似的。”
没有人吭气。
街的这半边死气沉沉。就连白天,生意也是萧条的:土地经纪人,戒酒饭店[54],福尔克纳铁路问讯处,文职人员培训所,吉尔书店,天主教俱乐部,盲人习艺所。这是怎么回事呢?反正有个原因。不是太阳就是风的缘故。晚上也还是这样。只有一些扫烟囱的和做粗活的女佣。在已故的马修神父[55]的庇护下。巴涅尔纪念碑的基石。衰竭。心脏。[56]
前额饰有白色羽毛的几匹白马,在街角的圆形建筑那儿拐了个弯儿,飞奔而来。一口小小的棺材一闪而过。赶看去下葬哩。一辆送葬马车。去世的是未婚者。已婚者用黑马。单身汉用花斑马。修女用棕色的。
“实在可惜,”马丁·坎宁翰先生说,“还是个娃娃哩。”
一张侏儒的脸,像小鲁迪的那样紫红色而布满皱纹。一副侏儒的身躯,油灰一般软塌塌的,陈放在衬了白布的松木匣子里。费用是丧葬互相会给出的。每周付一便士,就能保证一小块草地。咱们这个小乞丐。小不点儿。无所谓。这是大自然的失误。娃娃要是健康的话,只能归功于妈妈。否则就要怪爸爸[57]。但愿下次走点运。
“可怜的小家伙,”迪达勒斯先生说,“他总算没尝到人世间的辛酸。”
马车放慢速度,沿着拉特兰广场的坡路往上走。骨骼咯咯响,颠簸石路上。不过是个穷人,没入肯认领[58]。
“在生存中,”[58]马丁·坎宁翰说。
“然而最要不得的是,”鲍尔先生说,“自寻短见的人。”
马丁·坎宁翰匆匆地掏出怀表,咳嗽一声,又塞了回去。
“给一家人带来莫大的耻辱,”鲍尔先生又补上一句。
“当然是一时的精神错乱,”马丁·坎宁翰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应该用更宽厚的眼光看这个问题。”
“人家都说干这种事儿的是懦夫,”迪达勒斯先生说。
“那就不是咱们凡人所能判断的了,”马丁·坎宁翰说。
布卢姆先生欲言又止。马丁·坎宁翰那双大眼睛,而今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他通情达理,富于恻隐之心,天资聪颖。长得像莎士比亚。开口总是与人为善。本地人对那种事儿和杀婴是毫不留情的。不许作为基督教徒来埋葬。早先竟往坟墓中的死者心脏里打进一根木桩[60],惟恐他的心脏还没有破碎。其实,他们有时也会懊悔的,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在河床里发现他的时候,手里还死命地摸住芦苇呢。他[61]瞅我来着。还有他那娘儿们——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一次次地为她把家安顿好,然而几乎一到星期六她就把家具典当一空,让他去赎。他过着像是在地狱里一般的日子。即便是一颗石头做的心脏,也会消磨殆尽的。星期一早晨,他又用肩膀顶着轱辘重新打鼓另开张。老天爷,那天晚上她那副样子真有瞧头。迪达勒斯告诉过我,他刚好在场。她喝得醉醺醺的,抡着马丁的雨伞欢蹦乱跳。
他们称我作亚洲的珍宝,
亚洲的珍宝
日本的艺妓[62]。
他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他明白。骨骼咯咯响。
验尸的那个下午。桌上摆着个贴有红标签的瓶子。旅馆那个房间里挂着一幅幅狩猎图。令人窒息的气氛。阳光透过威尼新式软百叶帘射了进来。验尸官那双毛茸茸的大耳朵泍浴在阳光下。茶房作证。起先只当他还睡着呢。随后见到他脸上有些黄道道。已经滑落到床脚了。法医验明为:服药过量。意外事故致死。遗书:致吾儿利奥波德。
再也尝不到痛苦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无人肯认领。
马车沿着布莱辛顿街辘辘地疾驰着。颠簸石路上。
“我看咱们正飞跑着哪,”马丁·坎宁翰说。
“上天保佑,可别把咱们这车人翻在马路上,”鲍尔先生说。
“但愿不至于,”马丁·坎宁翰说,“明天在德国有一场大赛——戈登、贝纳特[63]。”
“唉呀,”迪达勒斯先生说,“那确实值得一看。”
当他们拐进伯克利街时,水库附近一架手摇风琴迎面送来一阵喧闹快活的游艺场音乐,走过去后,乐声依然尾随着。这儿可曾有人见过凯利?[64]凯歌的凯,利益的利。接着就是《扫罗》中的送葬曲[65]。他坏得像老安东尼奥,撇下了我孤苦伶仃![66]足尖立地旋转!仁慈圣母玛利亚医院[67j。这是埃克尔斯街,我家就在前边。[68]一座庞大的建筑,那里为绝症患者所设的病房。真令人感到鼓舞。专收垂死者的圣母济贫院。太平间就在下面,很便当。赖尔登老太太[69]就是在那儿去世的。那些女人的样子好吓人呀。用杯子喂她东西吃,调羹在嘴边儿蹭来蹭去。然后周围屏遮起她的床,等着她咽气。那个年轻的学生 [70]多好啊,那一次蜜蜂蜇了我,还是他替我包扎的。他们告诉我,如今他转到产科医院去了。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马车急转了个弯,蓦地停住了。
“又出了什么事?”
身上打了烙印的牛,分两路从马车的车窗外走过去,哞哞叫着,无精打采地挪动着带脚垫的蹄子,尾巴在瘦骨嶙嶙、巴着粪的屁股上徐徐地甩来甩去。打了猪红色印证的羊,吓得咩咩直叫,在牛群外侧或当中奔跑。
“简直像是移民一样,”鲍尔先生说。
“嘚儿!”,马车夫一路吆喝着,挥鞭啪啪地打着牲口的侧腹。
“嘚儿!躲开!”[71]
这是星期四嘛。明天该是屠宰日啦。怀仔的母牛。卡夫[72]把它们按每头约莫二十七镑的代价出售。兴许是运到利物浦去的。给老英格兰的烤牛肉 [73]。他们把肥嫩的牛统统买走了。这下子连七零八碎儿都没有了,所有那些生料——皮啦,毛啦,角啦。一年算下来,蛮可观哩,单打一的牛肉生意。屠宰场的下脚料还可以送到鞣皮厂去或者制造肥皂和植物黄油。不晓得那架起重机如今是不是还在克朗西拉[74]从火车上卸下那些次等的肉。
马车又穿过牲畜群继续前进了。
“我不明白市政府为什么不从公园大门口铺一条直通码头的电车道?”布卢姆先生说,“这么一来,所有这些牲口就都可以用货车运上船了。”
“那样也就不至于堵塞道路啦,”马丁·坎宁翰说。“完全对,他们应该这么做。”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找还常常转另外一个念头:要像米兰市那样搞起市营的殡仪电车[75],你们晓得吧。把路轨一直铺到公墓门口,设置专用电车——殡车、送葬车,全齐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可是个奇妙的主意,”迪达勒斯先生说,“再挂上一节软卧和高级餐车。”
“对科尼来说,前景可不美妙啊,”鲍尔先生补充了一句。
“怎么会呢?”布卢姆先生转向迪达勒斯先生问道,“不是比坐双驾马车奔去体面些吗?”
“嗯,说得有点儿道理,”迪达勒斯先生承认了。
“而且,”马丁·坎宁翰说,“有一次殡车在敦菲角[76]前面拐弯的时候翻啦,把棺材扣在马路上。像那样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那回太可怕啦,”鲍尔先生面呈惧色地说,“尸首都滚到马路上去了。可怕啊!”
“敦菲领先,”迪达勒斯先生点着头说,“争夺戈登·贝纳特奖杯。”
“颂赞归于天主!”马丁·坎宁翰虔诚地说。
第六章 2
咕咚!车子翻了。一副棺材扑通一声跌到路上,崩开了。帕狄· 迪格纳穆身着过于肥大的褐色衣服,被抛出来,僵直地在尘埃中打滚。红脸膛如今已呈灰色。嘴巴咧开来,像是在问究竟出了啥事儿。完全应该替他把嘴阖上,张着的模样太吓人了。内脏也腐烂得快。把一切开口都堵上就好得多。对,那也堵起来。用蜡。括约肌松了,一古脑儿封上。
“敦菲酒馆到啦,”当马车向右拐的时候,鲍尔先生宣告说。
敦菲角。停看好几辆送葬回来的车。人们在借酒浇愁。可以在路过歇上一会儿。这是开酒店的上好地点。估计我们归途会在这儿停下来,喝上一杯,为他祝祝冥福,大家也聊以解忧。长生不老剂[77]。
然而假定现在发生了这样一档子事。倘若翻滚的当儿,他身子给钉子扎破了,他会不会流血呢?我猜想,也许流,也许不流。要看扎在什么部位了。血液循环已经停止了。然而碰着了动脉,就可能会渗出点儿血来。下葬时,装裹不如用红色的——深红色。
他们沿着菲布斯巴斯街默默前进。刚从公墓回来的一辆空殡车迎面擦过,马蹄嘚嘚嘚响着,一派轻松模样。
克罗斯冈斯桥;皇家运河。
河水咆哮着冲出闸门。一条驶向下游的驳船上,在一堆堆的泥炭当中,站着条汉子,船闸旁的纤路上,有一匹松松地系着缰绳的马。布加布出航[78]。
他们用眼睛盯着他。他乘了这条用一根纤绳拽着的木排,顺着涓涓流淌、杂草蔓生的河道,涉过苇塘,穿过烂泥,越过一只只堵满淤泥的细长瓶子,一具具腐烂的狗尸,从爱尔兰腹地漂向海岸。阿斯隆、穆林加尔、莫伊谷[79],我可以沿着运河徒步旅行去看望米莉。要么就骑自行车前往。租一匹老马,倒也安全。雷恩[80]上次拍卖的时候倒是有过一辆,不过是女车。发展水路交通。詹姆斯·麦卡恩[81]以用摆渡船把我送过渡口为乐。这种走法要便宜一些。慢悠悠地航行。是带篷的船。“可以坐去野营。还有灵柩船,从水路去升天堂。也许我不写信就突然露面。径由莱克斯利普和克朗西拉,通过一道接一道船闸顺流而下,直抵都柏林。从中部的沼泽地带运来了泥炭。致敬——他举起褐色草帽,向帕狄·迪格纳穆致敬。
他们的马车从布赖恩·勃罗马酒家[82]前经过。墓地快到了。
“不晓得咱们的朋友弗格蒂[83]情况怎样了,”鲍尔先生说。
“不如去问问汤姆·克南·”迪达勒斯先生说。
“怎么回事?”马丁·坎宁翰说,“把他撇下,听任他去抹眼泪吧,是吗?”
“形影虽消失,”迪达勒斯先生说,“记忆诚可贵[84]”。
马车向左拐,走上芬格拉斯路[85]。
右侧是石匠作坊。最后一段工序。狭长的场地,密密匝匝地挤满默默无言的雕像。白色的,悲恸的。有的安详地伸出双手,有的忧伤地下跪,手指着什么地方。还有削下来的石像碎片。在一片白色沉默中哀诉着。为您提供最佳产品。纪念碑建造师及石像雕刻师托马斯·H·登纳尼。
走过去了。
教堂同事吉米·吉尔里的房屋前,一个老流浪汉坐在人行道的栏石上,一边嘟囔着,一边从他那双开了口、脏成褐色的大靴 子里倒着泥土和石子儿。他已走到人生旅途的尽头。
车子经过一座接一座荒芜不堪的花园[86],一幢幢阴森森的房屋。
鲍尔先生用手指了指。
“那就是蔡尔兹被谋杀的地方,”他说,“最后那幢房子。”
“可不是嘛,”迪达勒斯先生说,“可怕的凶杀案。西摩·布希[87]让他免于诉讼。谋杀亲哥哥。或者据说是这样。”
“检查官没有掌握证据,”鲍尔先生说。
“只有旁证,”马丁·坎宁翰补充说,“司法界有这么一条准则,宁可让九十九个犯人逃脱法网,也不能错判一个无辜者有罪。[88]”
他们望了望。一座凶宅。它黑魆魆地向后退去。拉上了百叶窗,没有人住,花园里长满了杂草。这地方整个都完了。被冤枉地定了罪。凶杀。凶手的形象留在被害者的视网膜上。人们就喜欢读这类故事。在花园里发现了男人的脑袋啦。她的穿着打扮啦。她是怎样遇害的啦。新近发生的凶杀案。使用什么凶器。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线索。一根鞋带。要掘墓验尸啦。谋杀的内情总会败露[89]。
这辆马车太挤了。她可能不愿意我事先不通知一声就这么忽然跑来。对女人总得谨慎一些。她们脱裤衩时,只要撞上一回,她们就永远也不会饶恕你。她已经十五岁了嘛。
前景公墓[90]的高栅栏像涟漪般地从他们的视野里淌过。幽暗的白杨树林,偶尔出现几座白色雕像。雕像越来越多起来,白色石像群集在树间,白色人像及其断片悄无声息地竖立着,在虚空中徒然保持着各种姿态。
车轮的钢圈嘎的一声蹭着人行道的栏石,停了下来。马丁·坎宁翰伸出胳膊,拧转把手,用膝盖顶开了车门。他下了马车,鲍尔先生和迪达勒斯先生跟着也下去了。
趁这会子把肥皂挪个窝儿吧。布卢姆先生的手麻利地解开裤子后兜上的钮扣,将巴在纸上的肥皂移到装手绢的内兜里。他边跨下马车,边把另一只手攥着的报纸放回兜里。
简陋的葬礼,一辆大马车,三辆小的。还不都是一样。抬棺人,金色缰绳,安魂弥撒,放吊炮。为死亡摆排场。殿后的马车对面站着个小贩,身旁的手推双轮车上放着糕点和水果。那是些西姆内尔糕饼[91],整个儿粘在一起了。那是给死者上供用的糕点。狗饼干[92]。谁吃?正从墓地往外走的送葬者。
他跟随着同伴们。接着就是克南先生和内德·兰伯特。海因斯也走在他们后面。科尼·凯莱赫站在敞着门的灵车旁边,取出一对花圈,并将其中的一个递给了男孩子。
刚才那个娃娃的送葬行列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
从芬格拉斯[93]那边来了一群马,吃力地迈着沉重的步子,拖着一辆载有庞大花岗石的大车,发出的嘎嘎响声打破了葬礼的沉寂,走了过去。在前边领路的车把式向他们点头致意。如今是灵柩了。尽管他已死去,却比我们先到了。[94]马扭过头来望着棺材,头上那根羽毛饰斜插向天空。它两眼无神:轭具勒紧了脖子,像是压迫着一根血管还是什么的。这些马晓不晓得自己每天拉车运些什么到这儿来?每天准有二三十档子葬事。新教徒另有杰罗姆山公墓。普天之下,每分钟都在举行着葬礼。要是成车地用铁锨铲进土星,就会快上好几倍。每小时埋上成千上万。世界上人太多了。
送葬者从大门里走了出来。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姑娘。妇女的相貌刁悍,尖下巴颏儿,看上去是个胡乱讨价还价的那号人,歪戴着一顶软帽。小姑娘满脸灰尘和泪痕,她挽着妇人的臂,仰望着,等待要她号哭的信号。鱼一般的脸,铁青而毫无血色。
殡殓工们把棺材扛在肩上,抬进大门。尸体沉得很。方才我从浴缸里迈出来,也觉得自己的体重增加了。死者领先,接着是死者的朋友。科尼·凯莱赫和那个男孩子拿着花圈跟在后面。挨着他们的是谁?啊,是死者的内弟。
大家都跟着走。
马丁·坎宁翰悄声说:
“当你在布卢姆面前谈起自杀的事来时,我心里感到万分痛苦。”
“为什么?”鲍尔先生小声说,“怎么回事?”
“他父亲就是服毒自杀的,”马丁·坎宁翰跟他交头接耳地说,“生前在恩尼斯[95]开过皇后饭店。你不是也听见他说要去克莱尔吗?那是忌辰。”
“啊,天啊!”鲍尔先生压低嗓门说,“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是服毒吗?”
他回过头去,朝那张有着一双沉思的乌黑眼睛的脸望去。那人边说话,边跟着他们走向枢机主教的陵墓[96]。
“上保险了吗?”
“我想一定上啦,”克南先生说,“然而保险单已经抵押出去,借了一大笔钱。马丁正想办法把那个男孩子送到阿尔坦[97]去。”
“他撇下了几个孩子?”
“五个。内德·兰伯特说过,他要想方设法把一个女孩子送进托德[98]去。”
“真够惨的,”布卢姆轻声说,“五个幼小的孩子。”
“对可怜的妻子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克南先生又补上一句。
“说得是啊,”布卢姆先生随声附和道。
如今,她胜利地活过了他。
他低头望了望自己涂油擦得锃亮的靴子。她的寿数比他长。失去了丈夫。对她来说,这死亡比对我关系重大。总有一个比另一个长寿。明智的人说,世上的女人比男人多。[99]安慰她吧:你的损失太惨重了。我希望你很快就跟随他而去。只有对信奉印度教的寡妇才能这么说。[100]她会再婚的。嫁给他吗?不。然而谁晓得以后会怎样呢?老女王去世后,就不兴守寡了。用炮车运送。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福洛格摩举行的追悼仪式。[101]可后来她还是在软帽上插了几朵紫罗兰。 在心灵深处[102],她毕竟好虚荣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影子。女王的配偶而已,连国王也不是。她儿子的位分才是实实在在的。那可以有新的指望[103];不像她想要唤回来而白白等待着的过去。过去是永远也不复返了。
总得有人先走。孤零零地入土,不再睡在她那温暖的床上了。
“你好吗,西蒙?”内德·兰伯特一边握手,一边柔声地说,“近一个月来,连星期天也一直没见着你啦。”
“从来没这么好过。科克这座城市[104]里,大家都好吗?”
“复活节的星期一,我去看科克公园的赛马[105]了,”内德·兰伯特说,“还是老一套,六先令八便士[106]。我是在狄克·蒂维家过的夜。”
“狄克这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好吗?”
“他的头皮和苍天之间己经毫无遮拦啦,”内德·兰伯特回答说。
“哎呀,我的圣保罗!”迪达勒斯先生抑制着心头的惊愕说,“狄克·蒂维歇顶了吗?”
“马丁正在为那些孩子们募集一笔捐款,”内德·兰伯特指着前边说,“每人几先令。让他们好歹维持到保险金结算为止。”
“对,对,”迪达勒斯先生迟迟疑疑地说,“最前面的那个是大 儿子吧?”
“是啊,”内德·兰伯特说,“挨着他舅舅。后面是约翰·亨利·
门顿[107]。他认捐了一镑。”
“我相信他会这么做的,”迪达勒斯先生说,“我经常对可怜的 帕狄说,他应该在自己那份工作上多下点儿心。约翰·亨利并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
“他是怎么砸的饭碗?”内德·兰伯特问道,“酗酒,还是什么?”
“很多好人都犯这个毛病,”迪达勒斯先生叹了口气说。
他们在停尸所小教堂的门旁停下了。 布卢姆先生站在手执花圈的男孩儿后面,俯视着他那梳理得光光整整的头发和那系着崭新的硬领、有着凹沟的纤细脖颈。可怜的孩子!也不晓得当他爸爸咽气时,他在不在场? 双方都不曾意识到死神即将来临。弥留之际才回光返照,最后一次认出人来。多少未遂的意愿。我欠了奥格雷狄三先令[108]。他能领会吗?殡殓工把棺材抬进了小教堂。他的头在哪一端?
过了一会儿,他跟在别人后头走进去,在透过帘子射进来的日光下眨巴着眼儿。棺材停放在圣坛前的柩架上,四个角各点燃一支高高的黄蜡烛。它总是在我们的前边。科尼·凯莱赫在四个角各放了只花圈,然后向那男孩子打了个手势,让他跪下。送葬者东一个西一个地纷纷跪在祈祷桌前。布卢姆先生站在后面,离圣水盂不远。等大家都跪下后,才从兜里掏出报纸摊开来,小心翼翼地铺在地上,屈起右膝跪在上面。他将黑帽子轻轻地扣在左膝上,手扶帽檐,虔诚地弯下身去。
一名助祭提着盛有什么的黄铜桶[109],从一扇门后面走了进来, 白袍神父跟在后面。他一只手整理着祭带,另一只手扶着顶在他那癞哈蟆般的肚子上的一本小书。谁来读这本书?白嘴鸦说:我。[110]
他们在柩架前停下步子。神父嗄声流畅地读起他那本书来。
科菲神父。我晓得他的姓听上去像“棺材”[111]。哆咪内呐眯内[112]。他的嘴巴那儿显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健壮的基督教徒[113]。 任何人斜眼瞧他都要遭殃。因为他是神父嘛。你要称作彼得[114]。迪达勒斯曾说 ,他的肚子会横着撑破的,就像是尽情地吃了三叶草的羊似的。挺着那么个大肚子,活像一只被毒死的小狗。那个人找到了最有趣儿的说法。哼,横里撑破。
求你不要审问我,你的仆人。[115]
用拉下文为他们祷告,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价抬高了些。安魂弥撒。身穿绝妙的号丧者[116]。黑框信纸。你的名字已经列在祭坛名单[117]上。这地方凉飕飕的。可得吃点好的才行。在昏暗中一坐就是整个上午, 磕着脚后跟,恭候下一位。连眼睛都像是癞哈蟆的。是什么使他胀成这样呢?摩莉一吃包心菜就肚胀。兴许是此地的空气在作怪。看来弥漫着疠气。这一带必定充满了在地狱里般的疠气。就拿屠夫来说吧:他们变得像生牛排似的。是谁告诉我来着?是默文·布朗[118]。 圣沃伯格教堂有一架可爱的老风琴,已经历了一百五十个星霜。在教堂地下灵堂里,必须不时地在棺材上凿个窟窿,放出疠气,点燃烧掉。蓝色的,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只要吸上一口,你就完蛋啦。
我的膝盖硌得疼了。唔。这样就好一些了。
神父从助祭提着的桶里取出一根顶端呈圆形的棍子,朝棺材上甩了甩。然后他走到另一头,又甩了甩。接着他踱了回来,将棍子放回桶里。你安息前怎样,如今还是怎样。一切都有明文规定,他照办就是了。
不要让我们受到诱惑。[119]
助祭尖声细气地应答着。[120]我常常觉得,家里不如雇个小男仆。最大不超过十五岁。再大了,自然就……
那想必是圣水。洒出来的是永眠。这份差事他准干腻了。成天朝送来的所有的尸首甩那牢什子。要是他能看到自己在往谁身上洒圣水,也不碍事嘛。每迎来一天,就有一批新的,中年汉子,老妪,娃娃,死于难产的孕妇,蓄胡子的男人,秃顶商人,胸脯小得像麻雀的结核病姑娘。他成年为他们作同样的祷告,并且朝他们洒圣水,安息吧。如今该轮到迪格纳穆了。
在天堂里。[121]
说是他即将升天堂或已升入天堂。对每个人都这么说。这是一份令人厌烦的差事。可是他总得说点儿什么。
神父阖上圣书走了,助祭跟在后面。科尼·凯莱赫打开侧门,掘墓工进来,重新抬起棺材,抬出去装在他们的手推车上。 科尼·凯莱赫把一只花圈递给男孩儿,另一只递给他舅舅。大家跟在他们后面, 走出侧门,来到外边柔和的灰色空气中。布卢姆先生殿后。他又把报纸折好,放回兜里,神情严肃地俯视着地面,直到运棺材的手推车向左拐去。金属轱辘磨在砂砾上,发出尖锐的嘎嘎声。一簇靴子跟在手推车后面踏出钝重的脚步声,沿着墓丛间的小径走去。
咯哩嗒啦咯哩嗒啦硲噜。主啊,我绝不可在这儿哼什么小曲儿。
“奥康内尔的圆塔[122],”迪达勒斯先生四下里望了望说。
鲍尔先生用柔和的目光仰望着那高耸的圆锥形塔的顶端。
“老丹·奥[123]在他的人民当中安息哪,”他说,“然而他的心脏却埋在罗马[124]。这儿埋葬了多少颗破碎的心啊,西蒙!”
“她[125]的坟墓就在那儿,杰克,”迪达勒斯先生说,“我不久就会神腿儿躺在她身边了。任凭天主高兴,随时把我接走吧。”
他的精神崩溃了,开始暗自哭泣,稍打着趔趄。鲍尔先生挽住他的胳膊。
“她在那儿安息更好,”他体贴地说。
“那倒也是,”迪达勒斯先生微弱地喘了口气说,“假若有天堂的话,我猜想她淮是在那里。”
科尼·凯莱赫从行列里跨到路边,让送葬者抱着沉重的脚步从他身旁踱过去。
“真是个令人伤心的场合,”克南先生彬彬有礼地开口说。
布卢姆先生阖上眼,悲恸地点了两下头。
“别人都戴上帽子啦,”克南先生说,“我想,咱们也可以戴了吧。咱们在后尾儿。在公墓里可不能大意。”
他们戴上了帽子。
“你不觉得神父先生念祷文念得太快了些吗?”克南先生用嗔怪的口吻说。
布卢姆先生注视着他那双敏锐的、挂满血丝的眼睛,肃然点了点头。诡谲的眼睛,洞察着内心的秘密。我猜想他是共济会的,可也拿不准。又挨着他了。咱们在末尾。同舟共济[126]。巴不得他说点儿旁的。
克南先生又加上一句:
“我敢说杰罗姆山公墓举行的爱尔兰圣公会[127]的仪式更简朴,给人的印象也更深。”
布卢姆先生谨慎地表示了同意。当然,语言又当作别论。[128]
克南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129]这话触动人的内心深处。”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
也许会触动你的心,然而对于如今脚尖冲着雏菊、停在六英尺见长、二英尺见宽的棺材里面的那个人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触动不了他的心。寄托感情之所在。一颗破碎了的心。终归是个泵而已,每天抽送成千上万加仑的血液。直到有一天堵塞了,也就完事大吉。此地到处都撂着这类器官,肺、心、肝。生了锈的老泵,仅此而已。复活与生命。人一旦死了,就是死了。末日的概念。[130]去敲一座座坟墓,把他们都喊起来。“拉撒路,出来!”[131]然而他是第五个出来的,所以失业了。[132]起来吧!这是末日!于是,每个人都四下里摸索自己的肝啦,肺啦以及其他内脏。那个早晨要是能把自己凑个齐全,那就再好不过了。颅骨里只有一英钱粉末。每英钱合十二克。金衡制[133]。
科尼·凯莱赫和他们并排走起来。
“一切都进行得头等顺利,”他说,“怎么样?”
他用眼睛不慌不忙地打量着他们。警察般的肩膀。吐啦噜吐啦噜地哼着小调儿。
“正应该这样,”克南先生说。
“什么?呃?”科尼·凯莱赫说。
克南先生请他放心。
“后面那个跟汤姆·克南一道走着的汉子是谁?”约翰·亨利·门顿问,“看来挺面熟。”
内德·兰伯特回过头去瞥了一眼。
“布卢姆,”他说,“原先,不,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个名叫玛莉恩·特威迪夫人的女高音歌手。她就是此人的老婆。”
“啊,可不是嘛,”约翰·亨利·门顿说,“我己经好久没见到她了。她长得蛮漂亮。我跟她跳过舞;哦,打那以后,已过了十五个——啊,十七个黄金年月啦。那是在圆镇的马特·狄龙[134]家。当年她可有搂头啦。”
他回头隔着人缝儿望去。
“他是什么人?”他问,“做什么的?他干过文具行当吧?一天晚上我跟他吵过架,记得是在滚木球场上。”
内德·兰伯特笑了笑。
“对,他干过那一行,”他说,“在威兹德姆·希利的店里,推销吸墨纸。”
“天哪,”约翰·亨利·门顿说,“她干吗要嫁给这么一个上不了台盘的家伙呢?当年她劲头可足啦。”
“如今也不含糊,”内德·兰伯特说,“他管拉些广告。”
约翰·亨利·门顿那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手推车转进一条侧径。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在草丛里伫候,举举帽子来表示敬意。掘墓工们也用手碰了一下便帽。
“约翰·奥康内尔,”鲍尔先生欣然说,“他从来没忘记过朋友。”
奥康内尔先生默默地和每一个人握了手。迪达勒斯先生说,
“我又来拜望您啦。”
“我亲爱的西蒙,”公墓管理员悄声回答说,“我压根儿不希望您来光顾!”
他向内德·兰伯特和约翰·亨利·门顿致意后,就挨着马丁·坎宁翰继续往前走,还在背后摆弄着两把长钥匙。
“你们听说过关于库姆街的马尔卡希那档子事吗?”他问道。
“我没听说,”马丁·坎宁翰说。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戴着大礼帽的脑袋凑过去,海因斯侧耳静听。管理员的两个大拇指勾在打着弯儿的金表链上。他朝着他们那一张张茫然的笑脸,用谨慎的口吻讲开了。
“人们传说着这么个故事,”他说,“一个大雾弥漫的傍晚,一对醉鬼到这儿来寻找一个朋友的坟墓。他们打听库姆街的马尔卡希,人家便告诉他们那人埋在哪儿。他们在雾里摸索了好一阵子,果真找到了坟墓。一个醉鬼拼出了死者的姓名:特伦斯·马尔卡希。另一个醉鬼却朝死者遗孀托人竖起的那座救世主雕像直眨巴眼儿。”
管理员翻起眼睛,冲着他们正走边的一座坟墓瞅了一眼。接着说:
“他睁大了眼朝那座圣像望了好半晌之后说:‘一点儿也不像那个人。’又说:‘不管是谁雕的,反正这不是马尔卡希。’”
大家听了,报以微笑。接着他就迟到后面,去和科尼·凯莱赫攀谈,收下对方递过来的票据,边走边翻看看。
“全都是故意讲的,”马丁·坎宁翰向海因斯解释说。
“我晓得,”海因斯说,“我也注意到了。”
“为的是让大鼓起劲儿来,”马丁·坎宁翰说,“纯粹是出于好心,决没有旁的用意。”
布卢姆先生欣赏管理员那肥硕、魁梧的身躯。人人都乐意和他往来。约翰·奥康内尔为人正派,是个道地的好人。他身上挂的那两把钥匙就像是凯斯 [135] 商店的广告似的。不必担心有人会溜出去。不需要通行证。得到人身保护。葬礼结束后,我得办理一下那份广告。那天我写信给玛莎的时候,她闯了进来。我用一个信封遮住了,上面写没写鲍尔斯桥[136]呢?但愿没有被丢进死信保管处。最好刮刮脸。长出灰胡子茬儿了,那是头发变灰的兆头。脾气也变坏了。灰发中央着银丝。[137]想想看,给这样的人做老婆!我纳闷他当年是怎么壮起胆子去向人家姑娘求婚的。来吧,跟我在坟场里过日子。用这来诱惑她。起初她也许还会很兴奋呢。向死神求爱。这里,夜幕笼罩下,四处躺着死尸。当坟地张大了口的时候,鬼魂从坟墓里出来。[138]我想,丹尼尔·奥康内尔准是其后裔。是谁来看, 常说丹尼尔是个奇怪的、生殖力旺盛的人[139],同时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天主教徒,像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矗立在黑暗中。鬼火。坟墓里的疠气。必须把她的心思从这档子事排遣开才行。不然的话,休想让她受孕。妇女尤其敏感得厉害。在床上给她讲个鬼故事,哄她入睡。你见过鬼吗?喏,我见过。那是个漆黑的夜晚。时钟正敲着十二点。然而只消把情绪适当地调动起来,她们就准会来接吻的。在土耳其,坟墓里照样有窑姐儿。只要年轻的时候就着手,凡事都能学到家。在这儿你兴许还能够勾搭上一位小寡妇呢。男人就好这个。在墓碑从中谈情说爱。罗密欧 [140]。给快乐平添情趣。 在死亡中,我们与生存为伍。[141]两头都衔接上了。那些可怜的死者眼睁睁望着,只好干着急呗。那就好比让饥肠辘辘者闻烤牛排的香味,馋得他们心焦火燎。欲望煎熬着人。摩莉很想在窗畔搞来着。反正管理员已有了八个孩子。
他此生已见过不少人入土,躺到周围一片片的茔地底下。神圣的茔地。倘若竖着埋,就必然可以省出些地方。坐着或跪着的姿势可就省不了。站着埋吗? [142]要是有朝一日大地往下陷,他的脑袋兴许会钻出地面,手还指着什么地方。地面底下一准统统成了蜂窝状,由一个个长方形的蜂房所构成。而且他把公墓收拾得非常整洁:又推草坪,又修剪边沿。甘布尔少校[143]管这座杰罗姆山叫作他自已的花园。可不是嘛。应该栽上睡眠花。马期天斯基[144]曾告诉我说,中国茔地上种着巨大的罂粟,能够采到优等鸦片。植物园就在前边。正是侵入到土壤里的血液给予了新生命。据说犹太人就是本着这个想法来杀害基督教徒的男孩儿的。[145]人们的价码各不相同。保养得好好的、肥肥胖胖的尸体,上流人士,美食家,对果园来说是无价之宝。今有新近逝世的威廉·威尔金森(审计员兼会计师)的尸体一具,廉价处理,三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谨此致谢。
我敢说,有了这些尸肥,骨头、肉、指甲,这片土壤一定会肥沃极了。一座座存尸所。令人毛骨悚然。都腐烂了,变成绿色和粉红色。在湿土里,也腐烂得快。瘦削的老人不那么容易烂。然后变成像是牛脂一般的、干酪状的东西。接着就开始发黑,渗出糖浆似的黑液。最后干瘪了。骷髅蛾[146]。当然,细胞也罢, 旁的什么也罢,还会继续活下去。不断地变换着。实际上是物质不灭。没有养分的话,就从自己身上吸吮养分。
但是准会繁殖出大量的蛆。土壤里确实有成群的蛆蠕动着。简直让你“云”头转向。海滨那些漂亮的小姑娘。[147]他心满意足地望着这一切。想到其他所有的人都比他先入土,给予他一种威力感。不晓得他是怎样看待人生的。嘴里还一个接一个地嘣出笑话,暖一暖心坎上的褶子。有这么个关于一张死亡公报的笑话:“斯珀吉昂今晨四时向天堂出发。现已届晚间十一时(关门时间),尚未抵达。彼得。[148]”至于死者本人,男的横竖爱听个妙趣横生的笑话,女的想知道什么最时新。来个多汁的梨,或是女士们的潘趣酒[149],又热和又浓烈又甜。可以搪潮气。你有时候也得笑笑,所以不如这么做。《哈姆莱特》中的掘基人[150]。 显示出对人类心灵的深邃理解。关于死者,起码两年之内不敢拿他们开玩笑。关于死者,除了过去,什么也别说。[151] 等出了丧期再说。难以想象他本人的葬礼将是怎样的。像是开个玩笑似的。他们说,要是念念自己的讣告,就能延年益寿。使你返老还童,又多活上一辈子。
“明天你有几档子?”管理员问。
“两档子,”科尼·凯莱赫说,“十点半和十一点。”
管理员将票据放进自己的兜里。手推车停了下来。送葬者分散开来,小心翼翼地绕过茔丛,踱到墓穴的两侧。掘墓人把棺材抬过来,棺材前端紧贴着墓穴边沿撂下,并且在棺材的周围拢上绳子。
要埋葬他了。我们是来埋葬愷撒的。他的三月中或六月中[152]。他不晓得都有谁在场,而且也不在乎。
咦,那边那个身穿胶布雨衣[153]、瘦瘦高高的蠢货是谁呀?我倒想知道一下。要是有人告诉我,我情愿送点薄礼。总会有个你再也想不到的人露面。一个人能够孤零零地度过一生。是呀,他能够。尽管他可以为自己挖好墓穴,但他死后还是得靠什么人为他盖土。我们都是这样。只有人类死后才要埋葬。不,蚂蚁也埋葬。任何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埋葬遗体。据说鲁滨孙·克鲁索过的是顺从于大自然的生活。喏,可他还是由“星期五”埋葬的呢。[154]说起来,每个星期五都埋葬一个星期四哩。
哦,可怜的鲁滨孙·克鲁索!
你怎能这样做?[155]
可怜的迪格纳穆!这是他最后一遭儿了,躺在地面上,装在棺材匣子里。想到所有那些死人,确实像是在糟踏木料。全都让虫子蛀穿了。他们蛮可以发明一种漂亮的尸架,装有滑板,尸体就那样哧溜下去。啊,他们也许不愿意用旁人使过的器具来入土。他们可挑剔得很哪。把我埋在故乡的土壤里。从圣地取来的一把土。[156]只有母亲和死胎才装在同一口棺材里下葬。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为的是即便入土之后,也尽可能多保护婴儿一些日子。爱尔兰人的家就是他的棺材[157]。在地下墓窟里使用防腐香料,跟木乃伊的想法一样。
布卢姆先生拿着帽子站在尽后边,数着那些脱了帽子的脑袋。十二个。我是第十三个。不,那个身穿胶布雨衣的家伙才是第十三个呢。不祥的数目。那家伙究竟是打哪儿突然冒出来的?我敢发誓,刚才他并没在小教堂里。关于十三的迷信[158],那是瞎扯。
内德·兰伯特那套衣服是用柔软的细花呢做的,色调有点发紫。当我们住在伦巴德西街时,我也有过这样的一套。当年他曾经是个讲究穿戴的人,往往每天换上三套衣服。我那身灰衣服得叫梅西雅斯[159]给翻改一下。咦,他那套原来是染过的哩。他老婆——哦,我忘了他是个单身汉——兴许公寓老板娘应该替他把那些线头摘掉。[160]
棺材已经由叉开腿站在墓穴搭脚处的工人们徐徐地撂下去,看不到了。他们爬上来,走出墓穴。大家都摘了帽子。统共是二十人。
静默。
倘若我们忽然间统统变成了旁人呢。
远方有一头驴子在叫。要下雨了。驴并不那么笨。人家说,谁都没见过死驴。它们以死亡为耻,所以躲藏起来。我那可怜的爸爸也是在远处死的。
和煦的罄风围绕着脱帽的脑袋窃窃私语般地吹拂。人们唧唧喳喳起来。站在坟墓上首的男孩子双手捧着花圈,一声不响地定睛望着那黑魆魆、还未封顶的墓穴。布卢姆先生跟在那位身材魁梧、为人厚道的管理员后面移动脚步。剪裁得体的长礼服。兴许正在估量着,看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喏,这是漫长的安息。再也没有感觉了。只有在咽气的那一刹那才有感觉。准是不愉快透了。开头儿简直难以置信。一定是搞错了,该死的是旁的什么人。到对门那家去问问看。且慢,我要。我还没有。然后,死亡的房间遮暗了。他们要光。[161]你周围有人窃窃私语。你想见见神父吗?接着就漫无边际地胡言乱语起来。隐埋了一辈子的事都在谵语中抖搂出来了。临终前的挣扎。他睡得不自然。按一按他的下限睑吧。瞧瞧他的鼻子是否耸了起来,下颚是否凹陷,脚心是否发黄。既然他是死定了,就索性把枕头抽掉,让他在地上咽气吧。[162]在“罪人之死”那幅画里,魔鬼让他看一个女人。他只穿着一件衬衫,热切地盼望与她拥抱。《露西亚》 [163]的最后一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砰!他咽了气。终于一命呜呼。人们谈论你一阵子,然后就把你忘了。不要忘记为他祷告。祈祷的时候要惦记着他。甚至连巴涅尔也是如此,常春藤日[164] 渐渐被人遗忘了。然后,他们也接踵而去,一个接一个地坠入穴中。
眼下我们正为迪格纳穆灵魂的安息而祷告。愿你平平安安,没下地狱。换换环境也蛮好嘛。走出人生的煎锅,进入炼狱[165]的火焰。
他可曾想到过等待着他的那个墓穴?人们说,当你在阳光下打哆嗦时,就说明你想到了。有人在墓上踱步。传唤员来招呼你了:快轮到你啦。我在靠近芬格拉斯路那一带买下一块茔地,我的墓穴就在那里。妈妈,可怜的妈妈,还有小鲁迪也在那里永眠。
掘墓工们拿起铁鍬,将沉甸甸的土块儿甩到穴里的棺材上。布卢姆先生扭开他的脸。倘若他一直还活着呢?唷!哎呀,那太可怕啦!不,不,他已经死了,当然喽。他当然已经死啦。他是星期一咽气的。应该规定一条法律,把心脏扎穿,以便知道确已死亡;要么就在棺材里放一只电钟或一部电话,装个帆布做的通气孔也行。求救信号旗。以三天为限。夏天可搁不了这么久。一旦验明确实断了气,还是马上把棺材封闭起来的好。
土坷垃砸下去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已开始被淡忘了。眼不见,心也不想了。
管理员移动了几步,戴好帽子。真够了。送葬者们舒了口气,一个个悄悄地戴上帽子。布卢姆先生也把帽子戴好。他望到那个魁梧的身姿正灵巧地穿过墓丛的迷津拐来拐去。他静静地、把握十足地跨过这片悲伤的场地。
海因斯在笔记本上匆匆地记着什么。啊,记名字哪。然而所有的人他都认识啊。咦,朝我走过来了。
“我在记名字,”他压低嗓门说,“你的教名是什么来着?我没把握。”
“利,”布卢姆先生说,“利奥波德。你不妨把麦科伊的名字也写上。他托付过我。”
“查理,”海因斯边写边说,“我晓得。他曾经在《自由人报》工作过。”
是这样的。后来他才在收尸所找到了差事,当路易斯·伯恩[166]的帮手。 让大夫来验尸倒是个好主意。原来只是凭想象,这下子可以弄明真相了。他是星期二死的。[167]就那样溜了。收了几笔广告费,就携款逃之夭夭。查理, 你是我亲爱的人。[168]所以他才托付我的。啊,好的,不碍事的,我替你办就是了,麦科伊。劳驾啦,老伙计,衷心感谢。一点儿都没破费,还让他领了我的情。
“我想打听一下,”海因斯说,“你认识那个人吗?那边的那个穿,身穿……”
他东看看西望望。
“胶布雨衣。是的,我瞅见他了,”布卢姆先生说,“现在他在哪儿呢?”
“焦勃雨伊,”海因斯边草草记下边说,“我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他的姓吧?”
他四下里望了望,走开了。
“不是,”布卢姆先生开口说。他转过身去,想拦住海因斯,“喂,海因斯!”
没听见。怎么回事?他到哪儿去啦?连个影儿都没有了。喏,可真是。这儿可曾有人见过?凯歌的凯,利益的利。[169]消失了踪影。天哪,他出了什么事?
第七个掘墓人来到布卢姆先生身旁,拿起一把闲着的铁鍬。
“啊,对不起!”
他敏捷地闪到一边去。
墓穴里开始露出潮湿的褐色泥土。逐渐隆起。快堆完了。湿土块垒成的坟头越来越高,又隆起一截。掘墓工们停下了挥鍬的手。大家再度脱帽片刻。男孩儿把他的花圈斜立在角落里,那位舅爷则将自己那一只放在一块士坷垃上。掘墓工们戴上便帽,提着沾满泥土的铁鍬,朝手推车走去。接着,在草皮上轻轻地磕打一下鍬刃,拾掇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弯下腰去摘缠在鍬把上的一缕长草。另一个离开伙伴们,把鍬当作武器般地扛着,缓步走去,铁刃闪出蓝光。还有一个在坟边一声不响地卷着拢棺材用的绳子。他的脐带。那位舅爷掉过身去要走时,往他那只空着的手里塞了点儿什么。默默地致谢。您费心啦,先生。辛苦啦。摇摇头。我明白。只不过向你们大家表表寸心。
送葬者们沿了弯弯曲曲的小径徐徐地走着,不时地停下来念念墓上的名字。
“咱们弯到首领[170]的坟墓那儿去看看吧,”海因斯说,“时间还很从容。”
“好的,”鲍尔先生说。
他们向右拐,一路在缓慢思索着。鲍尔先生怀着敬畏的心情,用淡漠的声调说:
“有人说,他根本就不在那座坟里。棺材里装满着石头。说有一天他还会来的。”
海因斯摇了摇头。
“巴涅尔再也不会来啦,”他说,“他的整个儿肉体都在那里。愿他的遗骨享受安宁。”
布卢姆先生悄悄地沿着林荫小径向前踱去。两侧是悲恸的天使,十字架,断裂的圆柱[171],家茔、仰望天空做祷告的希望的石像,还有古爱尔兰的心和手。倒不如把钱花在为活人办点慈善事业上更明智一些哩。为灵魂的安息而祈祷。难道有人真心这么祷告吗?把他埋葬,一了百了。就像用斜槽卸煤一样。然后,为了节省时间,就把他们都凑在一堆儿。万灵节[172]。二十七日我要给父亲上坟。给园丁十先令。他把茔地的杂草清除得一干二净。他自己也上了岁数,还得弯下腰去用大剪刀咯吱咯吱修剪。半截身子已经进了棺材。某人溘然长逝。某人辞世。 [173 ]就好像是他们都出于自愿似的。他们统统是被推进去的。某人翘辫子。倘若再写明这些死者生前干的是哪一行,那就更有趣了。某某人,车轮匠。我兜售软木。 [174]我破了产,每镑偿还五先令了事。要么就是一位大娘和她的小平底锅:爱尔兰炖肉是我的拿手好菜。乡村墓园挽歌非那一首莫属,究竟是华兹华斯还是托马斯·坎贝尔作的呢?[175]照新教徒的说法就是进入安息。[176]老穆伦大夫常挂在嘴上的是:伟大的神医召唤他回府。喏,这是天主为他们预备的园地。[177] 一座舒适的乡间住宅。新近粉刷油漆过。对于静静地抽烟和阅读《教会时报》[178]来说,是个理想的所在。他们从来不试图把结婚启事登得漂亮些。挂在门把手上的生锈的花圈,花冠是用青铜箔做的。花同样的钱,可就更经久了。不过,还是鲜花更富诗意。金属的倒是永不凋谢,可渐渐地就令人生厌了。灰毛菊 [179],索然无味。
一只鸟儿驯顺地栖在白杨树枝上,宛如制成的标本似的。就像是市政委员胡珀[180]送给我们的结婚礼品。嘿!真是纹丝儿不动。它晓得这儿没有朝它射来的弹弓。死掉的动物更惨。傻米莉把小死鸟儿葬在厨房的火柴匣里,并在坟上供个雏菊花环,铺一些碎瓷片儿。
那是圣心[181],裸露着的。掏出心来让人看。应该把它放得靠边一点,涂成鲜红色,像一颗真的心一般。爱尔兰就是奉献于它或是类似东西的。看来一点儿也不满意。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难道鸟儿会来啄它吗?就像对拎着一篮水果的男孩那样?然而他说不会来啄,因为鸟儿理应是怕那个男孩的。那就是阿波罗 [182]。
这许多![183]所有这些人,生前统统在都柏林转悠过。信仰坚定的死者们。我们曾经像你们现在这样。[184]
而且你又怎么能记得住所有的人呢?眼神,步态,嗓音。声音嘛,倒是有留声机。在每座坟墓里放一架留声机,或是保管在家里也行。星期天吃罢晚饭,放上可怜的老曾祖父的旧唱片。喀啦啦!喂喂喂 我高兴极啦 喀啦喀 高兴极啦能再见到 喂喂 高兴极啦 喀噗嘶嘘。会使你记起他的嗓音,犹如照片能使你忆起他的容貌一样。不然的话,相隔那么十五年,你就想不起他的长相了。譬如谁呢?譬如我在威兹德姆·希利的店里时死去的一个伙计。
吱嚕吱嚕!石头子儿碰撞的声音。且慢。停下来!
他定睛看看一座石砌墓穴。有个什么动物。哦。它在走动哪。
一只胖墩墩的灰鼠[185]趔趔趄趄地沿着墓穴的侧壁爬过去,一路勾动了石头子儿。它是个曾祖父,挺在行哩。懂得窍门。这只灰色的活物想扁起身子钻到石壁脚板下,硬是扭动着身子挤进去了。这可是藏匿珍宝的好场所。
谁住在这儿?罗伯特·埃默里的遗体安葬于此。罗伯特·埃米特是在火炬映照下被埋葬在这儿[186]的吧?老鼠在转悠哪。
如今,尾巴也消失了。
像这么个家伙,三下两下就能把一个人吃掉。不论那是谁的尸体,连骨头都给剔得干干净净。对它们来说,这就是一顿便饭。尸体嘛,左不过是变了质的肉。对,可奶酪又是怎样呢?是牛奶的尸体。我在那本《中国纪行》里读到:中国人说白种人身上有一股尸体的气味。最好火葬。神父们死命地反对。[187] 他们这叫吃里扒外。焚尸炉和荷兰铁皮烤肉箱的批发商。闹瘟疫的时期,把尸首扔进生石灰高温坑里去销毁。煤气屠杀室。本是尘埃,还原归于尘埃。[188]要么就海葬。 帕西人的沉默之塔在哪里?被鸟儿啄食。[189]土,火,水。人家说,论舒服莫过于淹死。刹那间自己的一生就从眼前闪过去了。然而一旦被救活可就不妙了。不过,空葬是行不通的。从一架飞行器往下投。每逢丢下一具尸体时,不晓得消息会不会就传开了。地下通讯网。我们还是从它们那儿得到的消息呢。这也不足为奇。它们对于像这样一顿正餐已习以为常。人们还没真正咽气,苍蝇就跟踪而至了。迪格纳穆这次,它们也是闻风而来。它们才不介意那臭味呢。盐白色的尸首,软塌塌,即将溃烂,气味和味道都像是生的白萝卜。
大门在前面发着微光,还敞着哪。重返尘世。这地方已经呆够了。每来一次,都更挨近一步。上回我到这儿来,是给辛尼柯太太[190]送葬。还有可怜的爸爸。致命的爱。我从书中得知,有人夜里提着灯去扒坟头,找新埋葬了的女尸,甚至那些已经腐烂而且流脓的墓疮。读罢使你真感到毛骨悚然。我死后将会在你面前出现。我死了,你会看到我的幽灵。我死后,将阴魂不散。死后有另一个叫作地狱的世界。她信里写道,我不喜欢那另一个世界[191]。我也不喜欢。还有许许多多要看要听要感受的呢。感受到自己身边那热乎乎的生命。让他们在爬满了蛆的床上长眠去吧。他们休想拉我去参加这个回合。热乎乎的床铺,热乎乎的、充满活力的生活。
马丁·坎宁翰从旁边的一条小径里出现了,他正和什么人一本正经地谈着话。”
那想必是个律师,挺面熟。姓门顿,名叫约翰·亨利,是个律师,经管宣誓书和录口供的专员。迪格纳穆曾在他的事务所里工作过。好久以前了,在马特·狄龙家。快活的马特,欢乐的晚宴。冷冻禽肉,雪茄烟,坦塔罗斯酒柜[192]。马特确实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对,是门顿。那天傍晚在滚木球的草地上,由于我的球滚进他的内线,他就大发雷霆。纯粹是出于偶然,滚了个偏心球。于是他把我恨之入骨。一见面就引起仇恨。摩莉和芙洛伊·狄龙在一棵丁香树下挽着胳膊笑。男人向来如此,只要有女人在场,就感到耻辱。
咦,他的帽子有一边瘪下去啦,是在马车里碰的吧。
“先生,对不起,”布卢姆先生在他们旁边说。
他们停下了脚步。
“你的帽子瘪下去一点儿,”布卢姆先生边指了指边说。
约翰·亨利·门顿纹丝儿不动,凝视了他片刻。
“那个地方,”马丁·坎宁翰帮着腔,也用手指了指。
约翰·亨利·门顿摘下礼帽,把瘪下去的部分弄鼓起来,细心地用上衣袖子把丝质帽面的绒毛捋了捋,然后又戴上了。
“现在好啦,”马丁·坎宁翰说。
约翰·亨利·门顿点了点头,表示领情。
“谢谢你,”他简短地说。
他们继续朝大门走去。布卢姆先生碰了个钉子,灰溜溜地挨后几步,免得听到他们的谈话。马丁一路指手划脚。他只消用一个小指头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弄那样一个蠢货,而本人毫无察觉。
一双牡蛎般的眼睛。管它呢,以后他一旦明白过来,说不定就会懊悔的。只有这样才能摆布他。
谢谢。今天早晨咱们多么了不起啊!
第六章注释
[1]杰克?鲍尔这个人物曾在《都柏林人?圣恩》中出现过,他供职于都柏林堡(英国殖民统治机构)内的皇家爱尔兰警察总署。
[2]根据爱尔兰风俗,左近有人家出殡时,店铺一律停业,住户则把百叶窗拉低,以示哀悼。
[3]弗莱明大妈是经常到布卢姆家做些家务活儿的女人,这里布卢姆是在回忆他们的独子鲁迪夭折后的情景。前文中的“趿拉着拖鞋”是意译,音译为斯利珀斯莱珀,民谣《狐狸》中的贫穷的老妪(参看第一章注[63]),象征爱尔兰。
[4]他们为之送葬的迪格纳穆?生前就住在纽布里奇大街九号。
[5]好风习指的是出殡队伍故意从繁华地区经过,以便让更多的路人向死者表示哀悼。
[6]原文为拉丁文。阿卡帖斯是埃涅阿斯的忠实、勇敢的同伴。埃涅阿斯是罗马神话中所传特洛伊和罗马的英雄,关于他的传说,见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埃涅阿斯纪》。此处老西蒙把自己的儿子斯蒂芬比作埃涅阿斯,把穆利根比作阿卡帖斯。
[7]古尔丁(参看第三章注[32])是科利斯-沃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成本会计师。他却把自已的姓加在事务所前面,以便让人认为他是大老板。
[8]伊格内修?加拉赫是曾出现在《都柏林人?一朵浮云》中的一个记者。 据本书第七章“伟大的加拉赫”一节,凤凰公园暗杀事件发生后,他由于搞到了独家新闻而出了名。
[9]语出自《亨利四世(下)》第2幕第1场。 当野猪头酒店老板娘带着差役来拘捕福斯塔夫时,他骂道:“滚开,你这贱婆娘!……我要膈肢你屁股!”
[10]伊顿学院是英国贵族公学,设在伯克郡伊顿镇。
[11]里奇蒙?布赖德韦尔监狱的门上写有“停止作恶,学习行善”这一标语。语出自《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1章第16至17节。十九世纪末叶,监狱并入韦林顿营房内。布卢姆夫妇住在雷蒙德高台街时,与那所营房遥遥相对。
[12]葛雷斯顿斯是都柏林市以南二十英里处的高级海滨浴场。
[13]内德?兰伯特是布卢姆的熟人,在一家种籽谷物商店工作。
[14]海因斯(即约瑟夫?麦卡西?海因斯)曾出现在《都柏林人?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中。他追随巴涅尔,在其逝世纪念日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长诗。 其实是乔伊斯本人九岁时,听到巴涅尔逝世的噩耗而写的,经过加工,放在这篇小说的末尾。
[15]当时爱尔兰人煎亚麻籽当汤药喝。
[l6]指都柏林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所办的狗收容所,设在大运河码头上。阿索斯是布卢姆的父亲所养的狗。他父亲自杀前在遗书中曾将这条狗托付给他。
[17]语出自《路加福音》第11章第2节。这是耶稣教给门徒的经文中的一句,《天主经》即由此而来。
[18]帕迪?伦纳德曾出现在《都柏林人?无独有偶》中,他无所事事,成天泡在酒店里。
[19]本?多拉德是本地的一名歌手。本书第十一章有他演唱《推平头的小伙子》的场面。那是一首颂扬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歌谣。作者为爱尔兰历史经济学家、学者、诗人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1828-1907)。参看第二章注[58]。
[20]“回顾性的编排”,参看第十一章注[178]及有关正文。后文中的丹?道森,见第七章注[55]。
[21]皮克和下面的艾莱恩都是《无独有偶》中的人物。该作中还提到克罗斯比-艾莱恩律师事务所。
[22]小花指圣女小德肋撒(1873-1897),法国人,十五岁在利雪城加入加尔默罗会。她的自传《灵心小史》(她自称“天主的小花”)于一八九七年出版后,有些天主教徒深为推崇,誉为“小花”精神。下面,布卢姆从报上那首小诗联想到他用亨利?弗罗尔这个假名字和玛莎通信的事。
[23]尤金?斯特拉顿(1861-1918),出生于美国的黑人歌手,喜剧演员,后在英国成名,当时正在都柏林演出。
[24]《基拉尼的百合》(1862)是根据出生于爱尔兰的美国剧作家戴恩?鲍西考尔特(1822-1890)的剧本《金发少女》(1860,原文为爱尔兰语, 音译为科伦?鲍恩)改编的一出以情节取胜的爱尔兰歌剧。
[25]《布里斯托尔号的愉快航行》是一出音乐喜剧,当时正在皇家剧院上演。
[26]“他”指布莱泽斯?博伊兰。
[27]菲利普?克兰普顿爵士(1777-1858),都柏林的一位外科医生。
[28]“谁”也指布莱泽斯?博伊兰。
[29]这个餐厅因供应从爱尔兰西岸克莱尔郡红沙洲捕来的牡蛎而得名。它宣传说,那是全爱尔兰最鲜嫩的牡蛎。
[30]据第十七章,布卢姆的父亲于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克莱尔郡自杀身死,他准备前往为亡父的十九周年忌辰祭奠。 [31]玛丽?安德森(1859-1940),美国女演员,一八九0年定居英国,继续积极从事戏剧活动。当时正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花园一景)。
[32]路易斯?沃纳当时正在贝尔法斯特为玛丽?安德森的演出担任指挥与伴奏。
[33]J?C?多伊尔是男中音歌手。约翰?麦科马克(1884-1945),出生于爱尔兰的男高音歌手,在伦敦成名。
[34]原文为法语。
[35]指竖在街头的威廉?史密斯?奥布赖恩(1803-1864)的雕像。他是爱尔兰爱国主义者,青年爱尔兰运动领导人,死于六月十六日。因此,这一天刚好是他的忌日。
[36]原文作:For many happy returns。原是用在生日或喜庆的祝贺语,很少用在忌日。
[37]即托马斯?法雷尔(1827-1900),爱尔兰雕刻家。
[38]当时确实有个叫作亨利?R?特威迪的。他在沃德福德郡担任首席检察官,在都柏林休姆街拥有自己的事务所。关于他落魄的晚景,未见记载。“往昔……遗迹”一语引自爱尔兰歌曲《我爹戴过的帽子》,作者为约翰尼?佩特森。
[39]守灵夜吸鼻烟原是为了压住死亡气息,把它踢来踢去表示没派上正当用场。
[40]美国剧作家威廉?贝尔?伯纳德(1807-1875)的二幕滑稽戏《他已穷途末路》(1889)中的主要角色叫作费利克斯?奥卡拉汉。他原是个乡绅,后来落魄。
[41]这里和下文中的“夫人”原文均为法语。
[42]、[43]原文为意大利语。后一句中,布卢姆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参看第四章注[51]、[52]。
[44]原文为意大利语。这是《伸给她》二重唱中女主角泽尔丽娜对男主角唐乔万尼所唱的歌词。
[45]克罗夫顿是《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以J?T?A?克罗夫顿(1838-1907)为原型而塑造的。这人与乔伊斯之父约翰?斯?乔伊斯(作品中的西蒙?迪达勒斯的原型)在都柏林税务局共过事。
[46]解放者指丹尼尔?奥康内尔,参看第二章注[51]。此处指竖立于奥康内尔大桥桥头的铜像。系由爱尔兰雕刻家约翰?亨利?弗利(1818-1874)所塑。
[47]吕便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吕便支族是离开埃及后,在迦南定居下来的古以色列十二支族之一,见《旧约?民数词》第1章。这里指正从街上走过去的吕便?杰
?多德。据认为出卖耶稣的犹太即属于吕便支族。这里,此人不但放高利货,而且刚好也姓吕便,所以把他说成是吕便的后裔。
[48]象记商店是一家出售防水用具的商店。
[49]约翰?格雷爵士(1816-1875),《自由人报》的经理,因倡议在都柏林市铺设自来水管有功。
[50]曼岛(又译为马恩岛)位于英格兰西北岸外,爱尔兰海上,由英国政府管理并享有很大自冶权。现政府由代理总督(由曼岛领主委任)和上下议院组成。
[51]巴拉巴是个罪恶累累的囚犯,根据民众的要求,他被释放,耶稣却代他受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见《马太福音》第27章。在英国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的诗剧《马耳他岛的犹太人》(1589)中,主角巴拉巴落入一锅滚水中而死,而那原是他用来陷害敌人的。
[52]这是为了纪念纳尔逊的战功而于一九O八年在奥康内尔街的十字路口建立的纪念柱。柱上有他的雕像。一九六六年被毁。
[53]关于帽子的趣意,参看本章注[38]。
[54]指都柏林的爱丁堡戒酒饭店。这家饭店一概不供应酒类。
[55]西奥博尔德?马修神父(1790-1861),爱尔兰天主教司铎,嘉布遣小兄弟会分会会长。他在全爱尔兰奔走游说,劝人戒酒,成绩昭著,故有“戒酒便徒”之称。他的雕像也立在奥康内尔街上。
[56]巴涅尔纪念碑的基石早在一八九九年就安置好了,然而直至一九一一年才竖立起由美国雕刻家奥古斯塔斯?圣-高丹斯设计的纪念碑。巴涅尔死于由急性肺炎而导致的心力衰竭。
[57]根据古老的犹太信条,孩子的健康决定于父亲是否强壮。犹太法律指出,一个男人必须儿女双全,并要求这些儿女也能够繁衍后代。
[58]“骨骼咯咯响……”没入肯认领”这四句诗摘自英国诗人 托马斯?诺埃尔(1799-1861)所作的《为穷人驾灵车》。全诗描写一个马车夫赶着用一匹马拉着的破灵车,把穷人的遗骸送往教堂墓地。
[59]这里,马丁?坎宁翰只引用了祷文的上半句,下半句是:“我们与死亡为伍。”
[60]直到十九世纪初叶,爱尔兰民间还迷信自杀者的阴魂会像妖精那样回到人间来作祟。只有往尸体的心脏里打进一根木桩,才能防止。
[61]“他”指马丁?坎宁翰。《都柏林人?圣恩》中提及他的妻子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六次把家具典当一空。
[62]引自轻歌剧《艺妓》中的曲子《亚洲的珍宝》,脚本作者为哈里?格林班克,詹姆斯?菲利普作曲。
[63]指一年一度的国际汽车赛,胜者可获得戈登?贝纳特奖杯。戈登?贝纳特(1841-1918)是美国《纽约先驱报》的主编,毕生奖励各种运动竞赛。
[64]这是美国人威廉?J?麦克纳根据英国歌曲《来自曼岛的凯利》(1908) 改编的俗谣《这儿可曾有人见过凯利?》(1909)的首句,下一句是:“来自绿宝石岛的凯利。”绿宝石岛是爱尔兰别名。
[65]《扫罗》是德国(后来入了英国籍)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1685-1759)取材于《圣经》的清唱剧,一七三九年在伦敦首次演出。送葬曲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66]有关凯利的歌前面都冠以一首序歌,叙述一个像凯利一样忘恩负义的意大利冰淇淋商人的故事。“他坏得像……伶仃”是其中的两句。
[67]原文为拉丁文。这家医院(参看第一章注[37])位于伯克利街和埃克尔斯街的交叉处。
[68]布卢姆夫妇住在埃克尔斯街七号。
[69]赖尔登老太太这个人物曾以丹特这个名字出现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1章中。
[70]此人名叫迪克森,是个曾在仁慈圣母医院见习的医科学生,在本书第十四章中,布卢姆又与他重逢。
[71]在《奥德修纪》卷11中,奥德修在阴间看见奥瑞翁赶着他生前在荒山上杀掉的野兽,走过永不凋枯的草原;他手里拿着折不断的铜杖。
[72]即约瑟夫?卡夫,参看第四章注[18]。
[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亨利?菲尔丁(l707-1754)的早期剧作《现代丈夫》(1732)第3幕第2场中有一首题为《老英格兰的烤牛肉》的诗,后由R?莱弗里奇配曲,成为流行歌曲。全诗大意是说,英国人由于爱吃烤牛肉,身心健康, 士兵也勇敢。这里把原诗中的“of”改成“for”,意思就变成“给老英格兰的烤牛肉” 了。
[74]克朗西拉是位于都柏林以西七英里处的铁路联轨点。
[75]米兰市修有一条专供殡仪电车行驶的七英里长的路轨。从市中心直通到郊外的坟地附近。
[76]敦菲角位干北环路和菲布斯博罗路的交叉口上。由于这里曾有过一座由托马斯?敦菲开的同名酒吧,故名。在一九O四年,酒吧改由约翰?多伊尔经营。
[77]爱尔兰人称威士忌为长生不老剂。西欧古代的炼金术师曾相信红葡萄能使人长生不老。英国剧作家卞?琼森(1572?-1637)的戏剧《炼金术师》第2幕第1场中有个名句:“醇粹的红葡萄酒,我们叫做长生不老剂。”
[78]《布加布出航》是J?P?鲁尼所作的一首讽刺诗,写一个舵手在睡梦中驾着一条名叫“布加布”的驳船运送泥炭。运河上风平浪静,水手们却幻想船在惊涛骇浪中行驶。
[79]阿斯隆、穆林加尔和莫伊谷是位于爱尔兰皇家运河沿岸从西至东的三座城市。
[80]指雷恩拍卖行,老板为P?A?雷恩。
[81]詹姆斯?麦卡恩,爱尔兰大运河公司董事长,他已于布卢姆回顾此事的四个月前(即1904年2月12日)逝世。
[82]这是一家以布赖恩?勃罗马(926-1014)命名的酒馆。他是爱尔兰西南部芒斯特地方的大王,曾击败盘踞在爱尔兰的丹麦人。这一带是古战场。
[83]弗洛蒂是《都柏林人?圣恩》中的一个人物,经营一月食品杂货店。汤姆?克南是他的朋友,曾从他的店里赊购,一直没付款。
[84]“形影……诚可贵”是常见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墓碑和.99lib?讣文上的用语,还曾编入乔冶?林利(1798-1825)的歌曲《你的记忆诚可贵》(1840)。
[85]在位于葛拉斯涅文的前景公墓前,路分两岔。右边是葛拉斯涅文路,左边是通往芬格拉斯路的墓地路。
[86]哈姆莱特因父王死后母亲改嫁给小叔子,在独白中把世界比作“荒芜不堪的花园”,见《哈姆莱特》第1幕第2场。下文中的“一座凶宅”即指托马斯?蔡尔兹被谋杀的房子。
[87]西摩?布希是爱尔兰的著名律师。塞缪尔?蔡尔兹被控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谋杀亲兄托马斯,布希任其辩护律师。次年十月塞缪尔被宣告无罪。
[88]英国法律诠释家威廉?布莱克斯顿(1723-1780)曾说过:“宁可让十个犯人逃脱法网,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马丁?坎宁翰把这句话和耶稣的话(“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引起的喜悦要大于为九十九个不需悔改的好人感到的喜悦”,参看《路加福音》第15章第6节)拉扯在一起了。
[89]哈姆莱特利用让篡位的叔叔看戏的机会来观察他是否为杀害乃兄的真凶,并作了这样的独白,“谋杀干得再诡秘,内情总会……败露。”见《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
[90]前景公墓即送葬队伍的目的地。
[91]一种葡萄干糕饼,得名于兰伯特?西姆内尔。参看第三章注[153]。
[92]喂狗用的硬饼干,搀以骨粉等制成。这里,因西姆内尔糕饼的外皮很硬,所以比作狗饼干。
[93]芬格拉斯是位于公墓西北方的一个村落,这一带有采石场。
[94]这段描写使人联想到《奥德修纪》卷11第4 段中奥德修在阴间遇见埃尔屏诺的鬼魂的场面。他问鬼魂:“埃尔屏诺,你怎么已经来到了幽暗的阴间?你的步行看来比我们的黑船还快呢。”(引自杨宪益译本,第133页)
[95]恩尼斯是爱尔兰克莱尔郡的一个镇子。
[96]指爱德华?麦凯布枢机主教(1816-1885)的陵墓。
[97]阿尔坦是位于都柏林市东北部一英里的一个村子,那里有天主教办的一所儿童救济院。
[98]托德-伯恩斯公司的简称,是都柏林的一家绸布衣帽店。乔伊斯本人的一个胞妹梅就曾在此做过工。
[99]“明智的……人多”,语出自默雷和利所作的一首题为《三女对一男》的滑稽歌曲。
[100]印度某些地区的习俗,寡妇为亡夫举行火葬时,也要当众跳进火堆自焚以殉夫。
[101]老女王指维多利亚女王(参看第一章注[105])。她于一八六一年丧偶,遂在福洛格摩建陵安葬亡夫阿尔伯特亲王,并终身守寡。她本人去世后,根据遗愿,灵柩用炮车运送,遗体与亡夫合葬。
[102]紫色象征真挚的爱,服丧时,可用以代替黑色。“心灵深处”,见《哈姆莱特》第3幕第2场中哈姆莱特对霍拉旭所说的话。
[103]指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参看第二章注[50])能够继承王位。
[104]《科克这座城市》(1825)是托马斯?克罗夫顿?克罗克(1798-1854)所作歌曲名,内容炫耀当地的吃喝玩乐。科克是爱尔兰芒斯特省科克郡的首府。
[105]一年一度的科克公园赛马活动的高峰是复活节星期一,即复活节的次日(1904年为4月4日)。
[106]这是当时把一个被处死的罪犯之尸体运到坟地,并按照基督教徒的礼节予以埋葬所需费用。这里,把“六先令八便士”当作“一点儿也没变”的代用语。
[107]约翰?亨利?门顿的原型是都柏林的一个同名律师,在小说中,迪格纳穆生前一度在他的事务所任职。
[108]爱尔兰有一首滑稽歌曲名《我欠了奥格雷狄十块钱》(1887)。作者为哈里?肯尼迪。写一个小裁缝奥格雷狄怎样也讨不回一个失业者(“我”)欠他的钱。
[1O9]黄铜桶里装的是圣水,以及用来蘸圣水往棺材上洒的一根棍子。
[110]这是一首由十四段组成的童谣《公知更鸟》中的两句。作者不详, 据说是艾奥纳和彼得?奥佩搜集整理的。第一段是: “谁杀了公知更鸟?/麻雀说:是我。/用我的弓箭。/我杀了公知更鸟。”与本文有关的是第六段:“谁来当神父?/白嘴鸦说,我。/带着我的小书,/我来当神父。” 语句略有出入,不知是布卢姆记错了,还是流传的版本不同。
[111]英文里,棺材(coffin)读作科芬,与科菲(coffey)发音相近。
[l12]这句拉丁文祷词原作ln nomine Domini(因主之名)。布卢姆却听成是Domine namine。Domine是“主”,namine则无此字。
[113]一八五七年左右,英国教会里以牧师、小说家、诗人查尔斯?金斯利(1819-1875)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基督教徒必须有健壮的身体,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并取得真正的宗教信仰。
[114]这是耶稣初次见到西门后所说的话。见《约翰福音》第1章第42节。彼得意即“磐石”,指要把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从此,西门易名彼得。天主教会奉他为第一代教皇。
[115]原文为拉丁文。见《诗篇》第143篇第2节。这是做完安魂弥撒后,即将把棺材往坟地里抬时念的经文首句。
[116]花钱雇来的号丧人,身穿廉价的黑色绉纱丧服。
[117]这是供参加丧礼者签名的本子或单子。
[1l8]当时都柏林有个名叫默文?布朗的音乐教师和风琴手。《都柏林人?死者》中也有个姓布朗的人物。
[119]原文为拉丁文,系《天主经》的倒数第二句。见《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
[120]这里,助祭照例吟诵《天主教》的最后一句:“乃救我于凶恶,啊们。”
[l21]原文为拉丁文。这是准备下葬时所念的经文中的词句。
[122]奥康纳尔去世后,遗体最初安葬在公墓中央的一座被深沟圈起的圆坛里。后来为了纪念他,就在这座公墓里建造了一座一百六十英尺高的圆塔。一八六九年,他的遗体又被移葬在该塔的地下灵堂里。
[123]丹?奥是丹尼尔?奥康内尔的简称。
[124]奥康内尔于一八四七年在日内瓦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心脏葬于罗马,遗体则运回都柏林。
[125]她指西蒙?迪达勒斯的亡妻玛丽?古尔丁?迪达勒斯。
[126]同舟共济,这里指的是送葬者中只有他本人和克南两个人不信天主教,处境相同。
[127]爱尔兰圣公会是新教,一五三七被定为爱尔兰国家教会, 但教徒人数只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弱。天主教徒则占五分之四。因此,于一八六九年撤销了其国家教会地位,从此实行自养。
[128]爱尔兰圣公会举行仪式时使用英语,不用拉丁文。
[129]这是耶稣对玛莎所说的话,见《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
[130]据《约翰福音》第6章第40节,耶稣对群众说,天主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耶稣“而信他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耶稣)要使他们复活”。
[131]据《约翰福音》第1l章第39至44节,玛莎的弟弟已入葬了四天,但耶稣叫人把挡在墓穴口的石头挪开,大声喊:“拉撒路,出来!”死者便复活并走了出来。
[132]《圣经》英译本中的“cameforth”(走出来了)与“camefourth”(第四个出来)谐音。这里是文字游戏,说他是“camefifth”(第五个出来)的,所以失业了。2l4
[133]金衡制是英、美用来量金、银、宝石的重量单位。每英镑合十二英两,每英两合二十英钱,每英钱合二十四谷(格令)。克为公制重量单位,每克约合十五谷半。
[134]圆镇一名得自都柏林市南郊特列纽亚村的一圈住宅。马特?狄龙是都柏林市的参议员。后文中的约翰?奥康内尔在第十五章中重新出现(见该章注[179]及有关正文)。
[135]英文里,keys(钥匙)与凯斯(Keyes)谐音。后文中的“人身保护”,原文为拉丁文。
[136]鲍尔斯桥在都柏林市东南郊外。
[137]这里套用一首题为《金发中夹着银丝》(1874)的歌曲。该歌颂扬一对年老的恩爱夫妻,由埃本?E?雷克斯福德作词,哈特?皮斯?丹克斯(1834-1903)配曲。
[138]“当……来”一语出自《哈姆莱特》第3幕第2场。此刻王子已打定主意要报杀父之仇,用这段自白来表露心迹。
[139]至今都柏林还有关于丹尼尔?奥康内尔曾有过一大批私生子的传说,故称他为“爱尔兰之父”。
[140]指罗密欧掘开墓门,见到服了安眠药后昏睡中的朱丽叶。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5幕第8场。
[141]这是把“在生存中,我们与死亡为伍”一语倒过来说的。参看本章注[59]。
[142]古代爱尔兰王和酋长的遗体有时是全身披挂,面部朝着敌国的方向,以站立的姿势入殓的。
[143]甘布尔少校是杰罗姆山公墓的管理员。
[144]马斯天斯基是布卢姆的街坊。
[145]一九一二年在沙俄统治下的基辅,有个名叫门德尔?贝利斯的犹太人,由于涉嫌为了取鲜血用在逾越节的宴会上而杀害了一个基督教徒的男孩子,从而受审。西方世界认为这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蓄意诬陷,引起公愤,贝利斯因而获释。但本书是写一九0四年发生的事。时间上有出入。
[146]一种飞蛾,背上有酷似头盖骨的纹,故名。L147]这两句均引自博伊兰关于海滨姑娘的歌(博伊兰曾把“晕”唱成“云”)。第二句略有出入。参看第四章注[65]及有关正文。
[148]据西方民间传说,耶稣的门徒彼得为天堂司阍。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第8幕第4场中,培尔就哄着弥留之际的母亲说,他要送她升天堂,彼得正在守着天堂的大门。
[149]潘趣酒是在葡萄酒里掺上果汁、香料、奶、茶、糖等做成的软性饮料。
[150] 《哈姆莱特》第5幕第1场中,由两个小丑扮演的掘墓工说了一些既荒唐又似是富于哲理的话。
[151]原文为拉丁文谚语。这里,布卢姆记错了一个字,原应作:“关于死者,除了好话,什么也别说。”
[152]“我……的”一语出自莎士比亚悲剧《尤利乌期?恺撒》第3章第2场。古代罗马统帅恺撒被共和党人刺杀后,恺撒的拥护者安东尼向民众发表演说,煽动人民,把共和党人逐出罗马。这句话出现在演说的开头部分。作者引用时把原句中的“我”改成了“我们”。月中是古罗马历三、五、七、十月中的第十五日,以及其他各月中的第十三日。三月中是恺撒遇刺日,六月中是迪格纳穆的忌日。
[l53]这个身穿胶布雨衣的人在书中数次出现,艾尔曼在《詹姆斯?乔伊斯》(第516页注)中说,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为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任收税官时的同事W?韦瑟厄普。
[154]鲁滨孙?克鲁索是笛福(1660-1731)的同名小说(1719)中的主人公。 他流落到荒岛后,在星期五那天从吃人生番手中救下一个土著,取名“星期五”。但在原作中,他并非由“星期五”埋葬,而是搭乘一艘英国船返国的。
[155]这是一首题名《可怜的老鲁滨孙?克鲁索》的歌曲的第一句和第四句,引用时略作了改动。原歌为:“可怜的老鲁滨孙?克鲁索失踪了,/人家说是到了一座岛屿,/他偷了一只公山羊的皮,/我不晓得他怎能这样做。”
[156]犹太人渴望死后能把遗体运回圣地巴勒斯坦去埋葬,至少也要在棺材里放进一把从该地取来的泥土陪葬。
[157]这里,作者诙谐地模拟英国谚语,英格兰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
[158]按耶稣被害前夕曾和十二门徒共进晚餐。因此,西方至今仍流传着以十三为不吉的迷信。
[159]当时在都柏林确实有个名叫乔治?R?梅西雅斯的裁缝。
[160]按染衣服时呢料能吸进紫色染料,而线染过后便发亮。所以这里说,应该把线头摘掉,这样就看不出是柒过的了。
[16l]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弥留之际曾说:“亮一些!再亮一些!”
[162]“既然……吧”一语出自法国小说家埃米尔?左拉(1860-1902)的《土地》(1887)。这部长篇小说描述一个老农惨死在贪图其田产的儿子及儿媳手中。
[163]《露西亚》是盖塔诺?多尼塞蒂(1797-1848)根据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长篇历史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1819)改编而成的歌剧,一八四三年在伦敦上演。在最后一幕中,男主角知晓自己的情人露西亚因被迫出嫁,已神经错乱而死,就也自寻短见。
[164]每年到了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的忌日(10月6日),他的支持者们总佩带常春藤叶作为悼念,故名。参看《都柏林人?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
[165]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一般人死后,灵魂要先下炼狱,以便把罪恶赎净。善人死后灵魂直接升天堂,恶人则下地狱。
[166]当时确实有个叫作路易斯?A?伯恩的医学博士,在都柏林市担任验尸官。
[167]这里,布卢姆想起了当天早晨在海滩上,船老大曾告诉他九天前(即上星期二)有人淹死的事。参看第一章注[122]及有关正文。他与雅典画家阿波罗多罗斯(活动时期公元前5世纪)搞混了。古代文献中提到他的《奥德修斯》等画作、无一传世。比他稍晚一些的古稀腊著名画家宙克?西斯(?-约公元前400)曾创作过一些风俗画,如《持葡萄的男孩》。传说葡萄画得以假乱真,引来一些小鸟啄它。画家本人说,倘若男孩也画得同样通真,鸟儿就会吓得不敢来啄食了。这里,作者把传说作了一些改动。
[183]语出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3篇。全句是:“我要是不看见,真不会相信死神已经办完了这许多!”原作指的是地狱中的幽灵,这里则是坟墓累累之意。
[184]这是常见的墓志铭,下面往往还有一句:“你们也即将像我们现在这样。”是死者(自称“我们”)对活人讲话的口吻。
[185]此鼠在第十五章(见该章注[186])中重新出现。
[186]墓碑上的罗伯特?埃默里这个名字使布卢姆想起同名而姓的发音也近似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埃米特曾参加一七九一年成立的以解放天主教和实现议会改革为宗旨的爱尔兰政治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并曾率领一批抗英起义者,向都柏林堡进军。事败后被捕,定为叛国罪,被处绞刑。“这儿”指墓穴。埃米特被处死后,相传其遗体被转移到都柏林的圣迈肯教堂或葛拉斯涅文的这座前景公墓,秘密安葬。然而一九O三年(埃米特逝世l00周年),人们来此寻取他的骸骨时却毫无所得。
[187]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要在世界末日复活。所以神父反对火葬。
[188]这里套用《创世记》第3章第19节中造物主对亚当说的话:“你是用尘土造的,你要还原归于尘土。”
[189] 帕西人是公元七、八世纪为逃避穆斯林压迫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拜火教(亦名袄教或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后裔。拜火教徒把尸体置于塔上,待尸肉被鸟啄食后,将骨骼密封在罐中。
[l90]辛尼柯太太是《都柏林人?悲痛的往事》中的一个人物,系辛尼柯船长的夫人。她因得不到爱情的温暖而酗酒,在横跨铁道时被火车轧死。
[l91l这是布卢姆当天早晨收到的玛莎来信中的话,参看第五章注[36]。
[192]坦塔罗斯是希腊传说中宙斯的儿子。《奥德修纪》卷11中提到尤利西斯看见他在冥界所受的酷刑,他站在齐下巴的水里,但每当他张口想喝,那水就退去。他头上挂着累累果实,但只要他伸手去拿,风就把果实吹向云霄。这里指有着暗锁、不能任意取饮的玻璃酒柜。
第七章
在希勃尼亚[1]首都中心一辆辆电车在纳尔逊纪念柱前减慢了速度,转入岔轨,调换触轮, 重新发车,驶往黑岩、国王镇和多基、克朗斯基亚、拉思加尔和特勒努尔、帕默斯顿公园、上拉思曼斯、沙丘草地、拉思曼斯、林森德和沙丘塔以及哈罗德十字路口。都柏林市联合电车公司那个嗓音嘶哑的调度员咆哮着把电车撵走:
“开到拉思加尔和特勒努尔去!”
“下一辆开往沙丘草地!”
右边是双层电车,左边是辆单层电车。车身咣咣地晃悠着,铃铛丁零零地响着,一辆辆地分别从轨道终点发车,各自拐进下行线,并排驶去。
“开往帕默斯顿公园的,发车!
王冠佩带者
中央邮局的门廊下,擦皮鞋的边吆喝着边擦。亲王北街上是一溜儿朱红色王室邮车,车帮上标着今上御称的首字E·R·[2]。成袋成袋的挂号以及贴了邮票的函件、明信片、邮筒和邮包,都乒啷乓啷地被扔上了车,不是寄往本市或外埠,就是寄往英国本土或外国的。
新闻界人士
穿粗笨靴子的马车夫从亲王货栈[3]里推出酒桶,滚在地上发出钝重的响声,又哐噹哐噹码在啤酒厂的平台货车上。由穿粗笨靴子的马车夫从亲王货栈里推滚出来的酒桶,在啤酒厂的货车上发出一片钝重的咕咚咕咚声。
“在这儿哪,”红穆雷[4]说,“亚历山大·凯斯。”
“请你给剪下来,好吗?”布卢姆先生说,“我把它送到电讯报报馆去。”
拉特利奇的办公室的门嘎地又响了一声。小个子戴维·斯蒂芬斯[5]严严实实地披着一件大斗篷,鬈发上是一顶小毡帽,斗篷下抱着一卷报纸,摆出一副国王信使的架势踱了出去。
红穆雷利利索索地用长剪刀将广告从报纸上铰了下来。剪刀和浆糊。
“我到印刷车间去一趟,”布卢姆先生拿着铰下来的广告说。
“好哇,要是他需要一块补白的话,”红穆雷将钢笔往耳朵上一夹,热切地说,“我们想法安排一下吧。”
“好的,”布卢姆先生点点头说,“我去说说看。”
我们。
沙丘奥克兰兹的
威廉·布雷登[6]阁下
红穆雷用那把大剪刀碰了碰布卢姆先生的胳膊,悄悄地说:
“布雷登。”
布卢姆先生回过头去,看见穿着制服的司阍摘了摘他那顶印有字母的帽子。这当儿,一个仪表堂堂的人[7]从《自由人周刊·国民新闻》和《自由人报·国民新闻》的两排阅报栏之间走过来。发出钝重响声的吉尼斯啤酒[8]桶。他用雨伞开路,庄重地踏上楼梯,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是一派严肃神色。他那穿着高级绒面呢上衣的脊背,一步步地往上升。脊背。西蒙·迪达勒斯说,他的脑子全都长在后颈里头了。他背后隆起一棱棱的肉。脖颈上,脂肪起着褶皱。脂肪,脖子,脂肪,脖子。
“你不觉得他长得像咱们的救世主吗?”红穆雷悄悄地说。
拉特利奇那间办公室的门吱吜吜地低声响着。为了通风起见,他们总是把两扇门安得对开着。一进一出。
咱们的救世主。周围镶着络腮胡子的鸭蛋脸,在暮色苍茫中说着话儿。玛丽和玛尔塔。男高音歌手马里奥[9]用剑一般的雨伞探路,来到脚光跟前。
“要么就像马里奥,”布卢姆先生说。
“对,”红穆雷表示同意,“然而人家说,马里奥活脱儿就像咱们的救世主哩。”
红脸蛋的耶稣·马里奥穿着紧身上衣,两条腿又细又长。他把一只手按在胸前,在歌剧《玛尔塔》[10]中演唱着:
回来吧,迷失的你,
回来吧,亲爱的你![11]
牧杖与钢笔
“主教大人今儿早晨来过两次电话,”[12]红穆雪板着面孔说。 他们望着那膝盖、小腿、靴子依次消失。脖子。
一个送电报的少年脚步轻盈地踅进来,往柜台上扔下一封电报,只打了声招呼就匆匆地走了,
“《自由人报》!”
布卢姆先生慢条斯理地说:
“喏,他也是咱们的救世主之一。”
他掀起柜台的活板,穿过一扇侧门,并沿着暖和而昏暗的楼梯和过道走去,还经过如今正回荡着噪音的一个个车间,一路脸上泛着柔和的微笑。然而,难道他挽救得了发行额下跌的局面吗?咣噹噹。咣噹噹。
他推开玻璃旋转门,走了进去,迈过散布在地上的包装纸,穿过一道轮转机铿锵作响的甬路,走向南尼蒂[13]的校对室。
海因斯也在这里,也许是来结讣告的账吧。咣噹噹。咣噹。
讣告
一位至为可敬的都柏林市民仙逝
谨由衷地表示哀悼
今天早晨,已故帕特里克·迪格纳穆先生的遗体。机器。倘若被卷了进去,就会碾成齑粉。如今支配着整个世界。他[14]这部机器也起劲地开动着。就像这些机器一样,控制不住了,一片混乱。一个劲儿地干着,沸腾着。又像那只拼命要钻进去的灰色老鼠。
一份伟大的日报是怎样编印出来的
布卢姆先生在工长瘦削的身子后面停下脚步来,欣赏着他那贼亮的秃脑瓢儿。
奇怪的是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祖国。爱尔兰啊,我的祖国。学院草地的议员。他竭力以普通一工人的身份,使报纸兴旺起来。[15]周刊全靠广告和各种专栏来增加销数,并非靠官方公报[16]发布的那些陈旧新闻。诸如一千XX年政府发行的官报。安妮女王驾崩[17]等等。罗森纳利斯镇区的地产,廷纳欣奇男爵领地[18]。有关人士注意:根据官方统计从巴利纳出口的骡子与母驴的数目一览表[19]。园艺琐记[20]。漫画[21]。菲尔·布莱克在周刊上连载的《帕特和布尔》的故事。托比大叔为小娃娃开辟的专页。乡下佬问讯栏。亲爱的编辑先生,有没有治肚胀的灵丹妙剂?编这一栏倒不赖,一边教人,一边也学到很多东西。人间花絮。《人物》[22]。大多是照片[23]。黄金海岸上,丽人们穿着泳装婷婷玉立。世界上最大的氢气球。一对姐妹同时举行婚礼,双喜临门。两位新郎脸对着脸,开怀大笑。其中一个就是排字工人卡普拉尼[24],比爱尔兰人还更富于爱尔兰气质。
机器以四分之三拍开动着。咣噹,咣噹,咣噹。倘若他在那儿突然中了风,谁都不晓得该怎样关机器,那它就会照样开动下去,一遍遍地反反复复印刷,整个儿弄得一塌糊涂。可真得要一副冷静的头脑。
“喏,请把这排在晚报的版面上,参议员先生,”海因斯说。
过不久就会称他作市长大人[25]啦。据说,高个儿约翰[26]是他的后台。
工长没有答话。他只在纸角上潦潦草草地写上“付排”二字,并对排字工人打了个手势。他一声不响地从肮脏的玻璃隔板上面把稿纸递过去。
“好,谢谢啦,”海因斯边说边走开。
布卢姆先生挡住了他的去路。
“假若你想领钱,出纳员可正要去吃午饭哪,”他说着,翘起大拇指朝后指了指。
“你领了吗?”海因斯问。
“唔,”布卢姆先生说,“赶快去,还来得及。”
“谢谢,老伙计,”海因斯说,“我也去领。”
他急切地朝《自由人报》编辑部奔去。
我曾在弥尔酒店里借给他三先令。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这是第三回提醒他了。
我们看见广告兜揽员在工作
布卢姆先生将剪报放在南尼蒂先生的写字台上。
“打扰您一下,参议员,”他说,“这条广告是凯斯的,您还记得吗?”
南尼蒂对着那则广告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他希望七月里登出来,”布卢姆先生说。
工长把铅笔朝剪报移动。
“等一等,”布卢姆先生说,“他想改动一下。您知道,凯斯,他想在上端再添两把钥匙。”
这噪音真讨厌。他听不见啊,南南。得有钢铁般的神经才行。兴许他能理解我的意思。
工长掉过身来,好耐着性子去倾听。他举起一只胳膊肘,开始慢慢地挠他身上那件羊驼呢夹克的腋窝底下。
“就像这个样子,”布卢姆先生在剪报上端交叉起两个食指比划着。
让他首先领会这一点。布卢姆先生从他用指头交叉成的十字上斜望过去,只见工长脸色灰黄,暗自思量他大概有点儿病。那边,恭顺的大卷筒在往轮转机里输送大卷大卷的印刷用纸。铿锵锵、铿锵锵地闹腾吧。那纸要是打开来,总得有好几英里长。印完之后呢?哦,包肉啦,打包裹啦,足能派上一千零一种用场。
每逢噪音间歇的当儿,他就乖巧地插上一言半语,并在遍体斑痕的木桌上,麻利地面起图样。
钥匙议院[27]
“您瞧,是这样的,这儿有两把十字交叉的钥匙[28]。再加上个圈儿,字号写在这儿:亚历山大·凯斯,茶叶、葡萄酒及烈酒商什么的。”
对他的业务,最好不要去多嘴多舌。
“参议员,您自己晓得他的要求。然后在上端,把钥匙议院这几个铅字排成个圆圈。您明白吧?您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工长把挠个不停的手移到下肋部,又悄悄地挠着那儿。
“这个主意,”布卢姆先生说,“是从钥匙议院得来的。您晓得,参议员,是曼克斯议会。这暗示着自治。从曼岛会引来游客的,您瞧,会引人注目的。您能办得到吗?”
也许我可以问问他“voglio”[29]这个字该怎样发音。可要是他不晓得,那只不过是把他弄得很尴尬而已。还是不要问为好。
“我们能办到,”工长说,“你有图案吗?”
“我可以弄来,”布卢姆先生说,“基尔肯尼的一家报纸上登过。他在那儿也开了一家店。我跑一趟去问问他就是了。喏,您可以那么办,再附上一小段,引起注意就成了。您知道通常的写法是:‘店内经特许供应高级酒类,以满足顾客多时的愿望’什么的。”
工长沉吟了片刻。
“我们能办到,”他说,“每隔三个月让他跟我们续订一次合同吧。”
这时,一个排字工人给他送来一份软塌塌的毛样。他一声不响地开始校对。布卢姆先生站在他身边,听着机器发出的震响,望着那些在活字分格盘旁一声不响地操作着的排字工人。
缀字校正
他自己非拼写得准确无讹不可。校对热。今天早晨马丁·坎宁翰忘记给我们出他那个拼写比赛的难题了。“看一个焦虑不安的行商在墓地的墙下,测量一只削了皮的梨有多么匀称所感到的无比困惑,是饶有趣味的。”[30]有些莫名其妙,对不?把“墓地”一词加进去,当然是为了“匀称”。[31]
当他戴上那顶大礼帽时,我本该说声谢谢。我应该扯一扯旧帽子什么的。可不,我本来可以这么说:“看上去还跟新的一样哩。”倒想看看他脸上会有什么反应。
吱。第一部印刷机那最下面的平台把拨纸器吱的一声推了出来,上面托着第一撂对折的报纸。它就这样吱的一声来引起注意,差不多像个活人了。它竭尽全力来说着话。连那扇门也吱吱响着,在招呼人把它关上。每样东西都用各自的方式说话。吱。
著名的神职人员
不定期的撰稿者
工长突如其来地把毛样递过来说:
“等一下。大主教的信在哪儿呢?还得在{电讯报}上重登一遍。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人在哪儿?”
他朝周围那一部部只顾轰鸣却毫无反响的机器望了望。
“先生,是蒙克斯吗?”铸宇间一个声音问道。
“嗯。蒙克斯在哪儿?”
“蒙克斯!”
布卢姆先生拿起他那份剪报。该走了。
“那么,我把图案弄来,南尼蒂先生,”他说,“我知道你准会给它安排个好位置。”
“蒙克斯!”[33]
“哦,先生。”
每隔三个月,续订一次合同。我先得去吸口新鲜空气。好歹试试看吧。八月见报吧。是个好主意:在巴尔斯布里奇举办马匹 展示会[32]的月份。旅游者会前来参加展示会的。
排字房的老领班
穿过排字房时,他从一个戴眼镜、系了围裙的驼背老人身边走过。那就是排字房的老领班蒙克斯。他这辈子想必亲手排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消息:讣告、酒店广告、讲演、离婚诉讼、打捞到溺死者。如今,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我敢说,这是个处世稳重、一丝不苟的人,银行里多少总有些积蓄。老婆做得一手好菜,衣服洗得干净。闺女在客厅里踩着缝纫机。相貌平庸的简,从不惹是生非。
逾越节[34]到了
他停下脚步,望着一个排字工人利利索索地分字模。先得倒过来读。他读起来快得很。这功夫是练出来的。穆纳格迪·克里特怕。可怜的爸爸曾经拿着{哈加达}书[35],用手指倒指着念给我听。逾越节[36]。明年在耶路撒冷。唷,哎呀!经过漫长的岁月,吃尽了苦头。我们终于被领出埃及的士地,进入了为奴之家[37]。哈利路亚[38]。以色列人哪,你们要留心听!上主是我们的上帝。[39]不,那是另一档子事。还有那十二个弟兄,雅各的儿子们[40]再就是羔羊[41]、猫、狗、杖[42]、水[43]和屠夫。然后,死亡的天使杀了屠夫,屠夫杀了公牛,狗杀了猫[44]。乍一听好像有点儿莫名其妙,其实再探究一下就会明白,这意味着正义:大家都在相互你吃我,我吃你。这毕竟就是人生。这活儿他干得多快啊。熟能生巧。他像在用指头读着原稿似的。
布卢姆先生从那咣噹咣噹的噪音中踱出,穿过走廊,来到楼梯平台。现在我打算一路搭电车前往。也许能找到他吧。不如先给他挂个电话。号码呢?跟西特伦家的门牌号码一样:二八。二八四四。
只再挪一次,那块肥皂
他走下露天的楼梯。是哪个讨厌鬼用火柴在墙上乱涂一气?看上去仿佛是为了打赌而干的。这些厂房里总是弥漫着浓烈的油脂气味。当我呆在汤姆[45]隔壁的时候,就老是闻到这种温吞吞的鳔胶气味。
他掏出手绢来搌了搌鼻孔。香橼柠檬?啊,我还在那儿放了块肥皂呢。在那个兜儿里会弄丢的。他放回手绢时取出肥皂,然后把它塞进裤后兜,扣上钮扣。
你太太使用哪一种香水?我还来得及乘电车回家一趟。借口说忘了点儿东西。在她换衣服之前,瞧上一眼。不。这儿。不。
抽冷子从《电讯晚报》的编辑部里传出一阵刺耳的尖笑声。我知道那是谁。怎么啦?溜进去一会儿,打个电话吧。那是内德·兰伯特。
他踅了进去。
爱琳[46],银海上的绿宝石
“幽灵走来了,”[47]麦克休教授嘴里塞满饼干,朝那积着尘埃的窗玻璃低声咕依。
迪达勒斯先生从空洞洞的壁炉旁朝内德·兰伯特那张泛着冷笑的脸望去,尖酸地问:
“真够呛,这会不会使你的屁股感到烟薰火燎呢?”
内德·兰伯特坐在桌子上,继续读下去:
“再则,请注意那打着漩涡蜿蜒曲折地哗哗淌去的泪泪溪流与拦住去路的岩石搏斗,在习习西风轻拂下,冲向海神所支配的波涛汹涌的蔚蓝领国;沿途,水面上荡漾着灿烂的阳光,两边的堤岸爬满青苔,森林中的巨树那架成拱形的繁叶[48],将荫影投射于溪流那忧郁多思的胸脯上。怎么样,西蒙?”他从报纸的上端望着问,“挺出色吧?”
“他调着样儿喝酒,”迪达勒斯先生说。
内德·兰伯特边笑边用报纸拍着自己的膝盖,重复着:
“忧郁多思的胸脯和蒙在屁股上的繁叶。真够绝的了!”
“色诺芬[49]俯瞰马拉松[50],”迪达勒斯先生说,他又瞧了瞧壁炉和窗户,“马拉松濒临大海。[51]”
“行啦,”麦克休教授从窗旁人声说,“我再也不想听那套啦。”
他把啃成月牙形的薄脆饼干吃掉,还觉得饿,正准备再去啃拿在另一只手里的饼干。
咬文嚼字的玩艺儿。吹牛皮,空空洞洞。依我看,内德·兰伯特准备请一天假。每逢举行葬礼,这一天就整个儿被打乱了。人家说,他有势力。大学副校长 ——老查特顿[52]是他的伯祖父或曾伯祖父。据说眼看就九旬了。也许报馆为这位副校长的噩耗所写的短评老早就准备好了。他简直就是为了刁难他们才活得这么长。说不定他自己倒会先死哩。约翰尼,替你伯父让路吧[53]。赫奇斯·艾尔·查特顿阁下。每逢该交租金的日子,老人就用他那颤巍巍的手给他签上一两张字迹古怪的支票。老人一旦踹了腿,他就可以发一笔横财。哈利路亚。
“又一阵发作吧,”内德·兰伯特说。
“什么呀?”布卢姆先生说。
“新近发现的西塞罗[54]断简残篇,”麦克休教授煞有介事地回答说,“《我们美丽的国土》。”
简单然而扼要
“谁的国土?”布卢姆先生简捷地问。
“问得再中肯不过了,”教授边咀嚼着边说,“并且在‘谁的’上加重了语气。”
“丹·道森[55]的国土,”迪达勒斯先生说。
“指的是他昨天晚上的演说吗?”布卢姆先生问。
内德·兰伯特点了点头。
“且听听这个,”他说。
这当儿,门被推开了,球形的门把手碰着了布卢姆先生的腰部。
“对不起,”杰·杰·奥莫洛伊边走进来边说。
布卢姆先生敏捷地往旁边一闪。
“不客气,”他说。
“你好,杰克。”
“请进,请进。”
“你好。”
“你好吗,迪达勒斯?”
“蛮好。你呢?”
杰·杰·奥莫洛伊摇了摇头。
伤 心
在年轻一辈的律师中间他曾经是最精明强干的一位。如今患了肺病,可怜的伙计。从他脸上那病态的潮红看,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究竟是怎么回事?为金钱发愁吧。
“或者,倘若我们攀登重岩叠嶂的峰巅。”
“你的气色异常地好。”
“能见见主编吗?”杰·杰·奥莫洛伊边往里屋瞅边问。
“当然可以,”麦克休教授说,“可以见他并且谈谈。他正在自己屋里跟利内翰[56]在一起。”
杰·杰·奥莫洛伊踱到办公室里那张斜面写字台前,从后往前翻看着用浅粉色纸印刷的报纸合订本。
本来或许可以有所成就的,可是业务荒疏了,灰心丧气,贪起赌来。弄得债台高筑。播下风,收割的是暴风。[57]过去,狄·与托·菲茨杰拉德[58] 事务所常常付给他优厚的预约辩护费。他们是为了显示智力而戴假发的。就像是坐落于葛拉斯涅文的竖像似的,炫耀着自己的头脑。他想必是跟加布里埃尔·康罗伊一道为《快报》[59]撰写一些文章。此人博学。迈尔斯·克劳福德是以在《独立报》[60]上写文章起家的。那些报人只要一听说哪儿有空子可钻,马上就见风使舵,煞是可笑。风信鸡。嘴里一会儿吹热气,一会儿又吹冷风![61]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好了。听到第二个故事之前,觉得头一个也蛮好。在报上彼此猛烈地开笔仗,然后一切都被淡忘。一转眼就又握手言欢。
“喂,请你们务必听听吧,”内德·兰伯特央求说。“或者,倘若我们攀登重岩叠嶂的峰巅……”
“言过其实!”教授暴躁地插嘴说,“这种夸夸其谈的空话己经听够啦!”
内德·兰伯特继续读下去:
“峰巅,巍然耸立。我们的灵魂恍若沫浴于……”
“还不如沫浴一下他的嘴巴呢,”迪达勒斯先生说,“永恒的上帝,难道他还能从中得到些报酬吗?”
“沫浴于爱尔兰全景那无与伦比的风光中。论美,尽管在其他以秀丽见称的宝地也能找到被人广为称颂的典型,然而我们温柔、神秘的爱尔兰在黄昏中那无可比拟的半透明光辉,照耀着郁郁葱葱的森林,绵延起伏的田野,和煦芬芳的绿色牧场。所有这些,真是举世无双的……”
“月亮,”麦克休教授说,“他忘记了《哈姆莱特》[62]。”
他家乡的土话
黄昏辽远而广阔地笼罩着这片景色,直到月亮那皎洁的球体喷薄欲出,闪烁出它那银色的光辉……
“哦!”迪达勒斯先生绝望地呻吟着,大声说,“狗屁不值!足够啦,内德,人一生时光有限啊!”
他摘下大礼帽,不耐烦地吹着他那浓密的口髭,把手指扎煞开来,活像一把威尔士梳子[63]梳理着头发。
内德·兰伯特把报纸甩到一旁,高兴地暗自笑着。过了一会儿,麦克休教授那架着黑框眼镜、胡子拉碴的脸上,也漾起刺耳的哄笑。
“夹生面包·大傻瓜[64]!”他大声说。
韦瑟厄普[65]如是说
此文如今白纸黑字己经印了出来,自然尽可以挖苦它一通,可是这类货色就像刚出锅的热饼一样脍炙人口哩。他干过面包糕点这一行,对吧?所以大家才管他叫作“夹生面包·大傻瓜”。反正他也己经赚足了。闺女跟内地税务署的那个拥有小轿车的家伙订了婚。乖巧地让他上了钩,还大张宴席,应酬款待。韦瑟厄普一向说:用酒肉把他们置于掌心。
里屋的门猛地开了,一张有着鹰钩鼻子的红脸膛伸了进来,头上是一撮羽毛似的头发,活像个鸡冠。一双蓝色、盛气凌人的眼睛环视着他们,并且粗声粗气地问:
“什么事?”
“冒牌乡绅[66]亲自光临!”麦克休教授堂哉皇哉地说。
“去你的吧,你这该死的老教书匠!”主编说,算是跟他打了招呼。
“来,内德,”迪达勒浙先生边戴帽子边说,“这事完了之后[67],我非得去喝上一盅不可啦。”
“喝酒!”主编大声说,“望完弥撒之前,什么也别想喝。”
“说得蛮对,”迪达勒斯先生说着就往外走,“来呀,内德。”
内德·兰伯特贴着桌边哧溜了下来。主编的一双蓝眼睛朝着布卢姆先生那张隐隐含着一丝笑意的脸上瞟去。
“你也跟我们一道来吗,迈尔斯?”内德·兰伯特问。
回顾难忘的战役
“北科克义勇军!”主编跨着大步走到壁炉台跟前,大声嚷着,“咱们连战连胜!北科克和西班牙军官们!”
“是在哪儿呀,迈尔斯?”内德·兰伯特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鞋尖问。
“在俄亥俄!”主编吼道。
“可不是嘛,没错儿,”内德·兰伯特表示同意。 ·
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跟杰·杰·奥莫洛伊打耳喳说:
“酒精中毒,真可悲。”
“俄亥俄!”主编仰起红脸膛儿,用尖锐的最高音嚷道,“我的俄亥俄[68]!”
“地地道道的扬抑扬音步!”教授说,“长,短,长。”
哦,风鸣琴[69]!
他从背心兜里掏出一卷清除牙缝的拉线[70],扯下一截,灵巧地用它在那未刷过的两对牙齿之间奏出声来:
“乒乓,乒乓。”
布卢姆先生看见时机正好,就走向里屋。
“借光,克劳福德先生,”他说,“为了一件广告的事,我想打个电话。”
他走了进去。
“今天晚上那篇社论怎么样?”麦克休教授问。他走到主编前,一只手牢牢地按在他的肩头。
“那样就行啦。”迈尔斯·克劳福德较为平静地说,“喂,杰克,不用着急。那样就可以啦。”
“你好,迈尔斯,”杰·杰·奥莫洛伊说,他手一松,合订本的几页报纸就又软塌塌地滑回去了, “加拿大诈骗案[71]今出登来了吗?”
里屋电话铃在丁零零响着。
“二八……不,二0……四四……对。”
看准赢家
利内翰拿着《体育》[72]的毛样从里面的办公室走了出来。
“谁想知道哪匹马准能得金杯奖?”他问,“就是奥马登所骑的那匹“权杖”。”
他把毛样朝桌上一掼。
打赤脚沿着过道跑来的报童的尖叫声忽然挨近了,门猛地被推开。
“安静点儿,”利内翰说,“我听到脚步声啦。”
麦克休教授跨大步走过去,一把拽住那个战战兢兢的少年的脖领,旁的孩子们赶紧沿着过道往外逃,冲下楼梯。那些毛样被穿堂风刮得沙沙响,蓝色的潦草字迹在空中飘荡,然后落到桌子底下。
“不是我,先生。是我背后那个大个子猛推了我一下,先生。”
“把他赶出去,关上门,”主编说, “正在刮台风哪。”
利内翰开始从地板上抓起毛样,两次蹲下去时全嘟嘟嚷嚷的。
“我们在等赛马特辑哪,先生,”报童说,“帕特·法雷尔猛推了我一把,先生。”
他指了指从门框后面窥伺着的两张脸。
“就是他,先生。”
“快给我滚,”麦克休教授粗暴地说。
他把少年胡乱搡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杰·杰·奥莫洛伊沙沙地翻着那合订本,边咕哝边查找:
“下接第六页第四栏。”
“对,这里是《电讯晚报》,”布卢姆先生在里间办公室里打着电话,“老板呢?……是的,《电讯》 ……到哪儿去啦?澳!哪家拍卖行?……啊!我明白啦。好的,我一定能找到他。”
接着是一次相撞
他刚挂上电话,那铃又丁零一声响了。他赶忙走进外屋,恰好跟又一次捡起毛样正在直起腰来的利内翰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先生[73],”利内翰说,他紧紧抓了布卢姆先生一把,做了个鬼脸。
“都怪我,”布卢姆先生说,他听任对方抓住自己。“没伤着你吗?都怪我太急啦。”
“我的膝盖,”利内翰说。
他做出一副滑稽相,边揉着膝盖边哼哼卿卿地说:
“年岁[74]不饶人啊。”
“对不起,”布卢姆先生说。
他走到门边,把门推开一半,又停下来了。杰·杰·奥莫洛伊还在翻看着那沉甸甸的纸页。两个蹲在大门外台阶上的报童发出的尖声喊叫和一只口琴吹奏出的音响,在空洞洞的过道里回荡着:
我们是韦克斯福德的男子汉,
凭着胆量和双臂酣战。[75]
布卢姆退场
“我要跑一趟巴切勒步道,”布卢姆先生说,“张罗一下凯斯这则广告。想把它定下来。听说他正在狄龙拍卖行那儿哪。”
他望着他们的脸,迟疑了片刻。主编一手支着头,倚着壁炉架,突然将一只臂往前一伸。
“走吧!”他说,“世界在你前面呢。”[76]
“一会儿就回来,”布卢姆边说边匆匆往外走。
杰·杰·奥莫洛伊从利内翰手里接过毛样来读。他轻轻地把它们一页页地吹开,不加评论。
“他准能拉到那宗广告,”他透过黑框眼镜,从半截儿窗帘上端眺望着说,“瞧,那帮小无赖跟在他后面呢。”
“在哪儿?让我瞧瞧。”利内翰边说,边朝窗口跑去。
街头行列
他们两个人面泛微笑,从半截儿窗帘上端眺望那些跳跳蹦蹦地尾随着布卢姆先生的报童们。最后一个少年在和风中放着一只尾巴由一串白色蝴蝶结组成的风筝,像是嘲弄一般在东倒西歪地摆来摆去。
“瞧,那群流浪儿跟在他后面大喊大叫,”利内翰说,“真逗!快把人笑死了。喔,肋骨都笑拧了!学他那扁平足的走法。耍着各种小把戏,乖巧得连云雀都逮得着。”
他以矫捷而滑稽的玛祖卡舞步从壁炉前滑过,来到杰·杰·奥莫洛伊跟前。奥莫洛伊把毛样递到他那摊开来的手里。
“怎么啦?”迈尔斯·克劳福德吃惊地说,“另外两位哪儿去啦?”
“谁?”教授转过身来说,“他们到椭圆酒家[77]喝点儿什么去了。帕迪·胡珀[78]和杰克·霍尔[79]也在那儿。是昨天晚上来的。”
“那就走吧,”迈尔斯·克劳福德说,“我的帽子呢?”
他趔趔趄趄地走进后面的办公室,撩起背心后面的衩口,玎玲噹啷地从后兜里掏出钥匙。钥匙又在半空中响了一下,当他锁书桌抽屉时,它们碰在木桌上又响了。
“他的病情不轻哪,”麦克休教授低声说。
“看来是这样,”杰·杰·奥莫洛伊说。他掏出个香烟盒,若有所思地念叨着,“然而也未必如此。谁的火柴最多?”
和平的旱烟袋[80]
他敬一支烟给教授,自己也拿了一支。利内翰赶紧划了根火柴,依次为他们点燃了香烟。杰·杰·奥莫洛伊又打开烟盒来让。
“谢谢你[81]”利内翰说着,拿了一支。
主编从里面的办公室走了出来,草帽歪戴在额头上。他凛然地指着麦克休教授,背诵了两句歌词:
地位名声将你蛊惑,
使你醉心的是帝国[82]。
教授那长嘴唇抿得紧紧的,嘻笑着。
“呃?你这暴戾的老罗马帝国?”迈尔斯·克劳福德说。
他从开着盖儿的烟盒里取了一支香烟。利内翰立刻殷勤地为他点上,并且说:
“静一静,听听我这崭新的谜语!”
“罗马帝国[83]呗。”杰·杰·奥莫洛伊安详地说,“听上去要比不列颠的或布里克斯顿[84]文雅一些。这个词儿不知怎地使人想到火里的脂肪。”
迈尔斯·克劳福德噗的一声猛地朝天花板喷出第一口烟。
“对呀,”他说,“咱们是脂肪。你和我就是火星的脂肪。咱们的处境甚至还不如地狱里的雪球呢。”
罗马往昔的辉煌[85]
“且慢,”麦克休教授从从容容地举起瘦削得像爪子一样的两只手说,“咱们可不能被词藻,被词藻的音调牵着鼻子走。咱们心目中的罗马是帝国的,专制的,专横的[86]。”
稍顿了顿,他又以雄辩家的派头,摊开那双从又脏又破的衬衫袖口里伸出的胳膊:
“他们的文明是什么?我承认它是庞大的,然而是粗鄙的。厕所[87]。下水道。犹太人在荒野里以及山顶上说,‘这是个适当的地 方,我们为耶和华筑一座圣坛吧。’罗马人,正如跟他亦步亦趋的英格兰人一样,每当踏上新岸(他从未踏上过我们的岸边),就一味地执着于修厕所。身穿宽大长袍的他,四下里打量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个适当的地方,我们装个抽水马桶吧。’”
“他们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了,”利内翰说,“据《吉尼斯》第一章[88]咱们古老的祖先对流水曾有过偏爱。”
“他们生来就是绅士,”杰·杰、奥莫洛伊咕依道,然而,咱们也有·《罗马法》[89]。”
“而庞修斯·彼拉多[90]那部法典的先知,”麦克休教授回答说。
“你晓得税务法庭庭长帕利斯[91]那档子事吗?”杰·杰·奥莫洛伊问;“ “那是在王家大学[92]的宴会上。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
“先听我的谜语吧,”利内翰说, “你们准备好了吗?”
身着宽松的多尼格尔[93]灰色花呢衣服、个子高高的奥马登·伯克[94]先生从过道里走了进来。斯蒂芬·迪达勒斯跟在他后面,边进屋边摘下帽子。
“请进,小伙子们!”[95]利内翰大声说。
“我是前来护送一个求情者的,”奥马登·伯克先生悦耳的声调说,“这位青年在饱有经验者的引导下,来拜访一名声名狼藉者了。”
“你好吗?”主编说着,伸出一只手来, “请进。你家老爷子刚走。”
? ? ?
利内翰对大家说:
“静一静!哪一出歌剧跟铁路线相似?考虑,沉思,默想,解决了再回答我。”
斯蒂芬一面把打字信稿递过去,一面指着标题和署名。
“谁?”主编问。
撕掉了一个角儿。
“加勒特·迪希先生,”斯蒂芬说。
“又是那个矫情鬼,”主编说,“这是谁撕的?他忽然想解手了吗?”
扬起火焰般的帆,
从南方的风暴中乘快船,
他来了,苍白的吸血鬼,
跟我嘴对嘴地亲吻。[96]
“你好,斯蒂芬,”教授说,他凑过来,隔着他们的肩膀望去,“口蹄疫?你改行了吗?……”
阉牛之友派“大诗人”[97]呐。
在一家著名餐馆里闹起的纠纷
“您好,先生,”斯蒂芬涨红了脸回答说,“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加勒特·迪希先生托我……”
“哦,我认识他,”迈尔斯·克劳福德说,“我也认识他老婆。 是个举世无双的凶悍老泼妇。天哪,她淮是害上了口蹄疫!那天晚上,她在‘金星嘉德’饭店里,把一盆汤全泼到侍者脸上啦。哎呀!”
一个女人把罪恶带到人世间。为了墨涅拉俄斯那个跟人私奔了的妻子海伦,希腊人竟足足打了十年仗。布雷夫尼大公奥鲁尔克。[98]
“他是个鳏夫吗?”斯蒂芬问。
“啊,跟老婆分居着哪,”迈尔斯·克劳福德边浏览着打字信稿边说。“御用马群。哈布斯堡[99]。一个爱尔兰人在维也纳的城堡跟前救了皇帝一命。可不要忘记!爱尔兰的封蒂尔柯涅尔伯爵马克西米连·卡尔·奥唐奈。[100]为了封国王作奥地利陆军元帅,而今把他的嗣子派了来。[101]那儿迟早总有一天会出事。‘野鹅’[102]。啊,是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可不要忘记这一点!”
“关键在于他忘没忘记,”杰·杰·奥莫洛伊把马蹄形的镇纸翻了个过儿,安详地说,“拯救了王侯,也不过赢得一声道谢而已。”
麦克休教授朝他转过身来。
“不然的话呢?”他说。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说吧,”迈尔斯·克劳福德开口说,“有一天,一个匈牙利人[103]……”
失 败 者
被提名的高贵的侯爵
“我们一向忠于失败者[104],”教授说,“对我们来说,成功乃是智慧与想象力的灭亡。我们从来不曾效忠于成功者。只不过侍奉他们就是了。我教的是刺耳的拉丁文。我讲的是这样一个民族的语言,他们的智力的顶点乃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这么一条格言。物质占支配地位。主啊![105]主啊!这句话的灵性何在?主耶稣还是索尔兹伯里勋爵[106]?伦敦西区一家俱乐部里的沙发[107]。然而希腊文却不同!”
主啊,怜悯我们吧![108]
开朗的微笑使他那戴着黑框眼镜的两眼炯炯有神,长嘴唇咧得更长了。
“希腊文!”他又说,“主![109]辉煌的字眼!闪米特族和撒克逊族都不晓得的母音[110]。主啊[111]!智慧的光辉。我应该教希腊文—— 教这心灵的语言。主啊,怜悯我们吧![112]修厕所的和挖下水道的[113]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主宰。我们是溃败于特拉法尔加[114]的欧洲天主教骑士精神的忠实仆从,又是在伊哥斯波塔米随着雅典舰队一道沉没了的精神帝国[115]——而不是统治权[116]——的忠实仆从。对,对,他们沉没了。皮勒斯被神谕所哄骗[117],孤注一掷,试图挽回希腊的命运。这是对于失败者的效忠啊。”
他离开了他们,跨着大步走向窗口。
“他们开赴战场,”奥马登·伯克先生用阴郁的口吻说,“然而总吃败仗。”[118]
“呜呜!”利内翰低声哭泣着,“演出[119]快要结束的时候,竟被一片瓦击中。[120]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皮勒斯!”
然后,他跟斯蒂芬打起耳喳来。
利内翰的五行打油诗
学究麦克休好气派,
黑框眼镜成天戴,
醉得瞧啥皆双影,
何必费事把它戴?
我看不出这有啥可笑[121],你呢?
穆利根说,这是为了悼念萨卢斯特[122]。他母亲死得像头牲口[123]。
迈尔斯·克劳福德把那几张信稿塞进侧兜里。
“这样就可以啦,”他说,“回头我再读其余的部分。这样就可以啦。”
利内翰摊开双手表示抗议。
“还有我的谜语呢!”他说,“哪一出歌剧跟铁路线相似?”
“歌剧?”奥马登·伯克先生那张斯芬克斯般的脸把谜语重复了一遍。
利内翰欢欢喜喜地宣布说”
“《卡斯蒂利亚的玫瑰》。你懂得它俏皮在什么地方吗?谜底是,并排的铸铁。嘻嘻嘻。”[124]
他轻轻戳了一下奥马登·伯克先生的侧腹。奥马登·伯克先生假装连气儿都透不过来了,手拄阳伞,风度优雅地朝后一仰。
“帮我一把!”他叹了口气,“我虚弱得很。”
利内翰踮起脚尖,赶紧用毛样沙沙沙地扇了搧他的脸。
教授沿着合订本的架子往回走的时候,用手掠了一下斯蒂芬和奥莫洛伊先生那系得稀松的领带。
“过去和现在的巴黎,”他说,“你们活像是巴黎公社社员。”
“像是炸掉巴士底狱的家伙[125],”杰·杰·奥莫洛伊用安详的口吻挖苦说,“要不然,芬兰总督就是你们暗杀的吧?看上去你们仿佛干了这档子事——干掉了博布里科夫将军。[126]”
“我们仅仅有过这样的念头罢了,”斯蒂芬说。
万紫千红[127]
“这里人材济济,”迈尔斯·克劳福德先生说,“法律方面啦,古典方面啦……”
“赛马啦,”利内翰插嘴道。
“文学,新闻界。”
“要是布卢姆在场的话,”教授说,“还有广告这高雅的一行哩。”
“还有布卢姆夫人,”奥马登·伯克先生加上一句,“声乐女神。都柏林的首席歌星。”
利内翰大咳一声。
“啊嗨!”他用极其细柔的嗓音说,“哎,缺口新鲜空气!我在公园里感冒了,大门是敞着的。”
“你能胜任!”
主编将一只手神经质地搭在斯蒂芬的肩上。
“我想请你写点东西,”他说,“带点刺儿的。你准能胜任!一看你的脸就知道。青春的词汇里[128]……”
从你的脸上就看得出来。从你的眼神里也看得出来。你是个懒散、吊儿郎当的小调皮鬼。[129]
“口蹄疫!”主编用轻蔑口吻谩骂道,“民族主义党在勃里斯-因-奥索里召开大会[130]。真荒唐!威胁民众!得刺他们两下!把我们统统写进去,让灵魂见鬼去吧。圣父圣子和圣灵,还有茅坑杰克·麦卡锡[131]。”
“咱们都能提供精神食粮,”奥马登·伯克先生说。
斯蒂芬抬起两眼,目光与那大胆而鲁莽的视线相遇。
“他[132]要把你拉进记者帮呢!”杰·杰·奥莫洛伊说。
了不起的加拉赫[133]
“你能胜任,”迈尔斯·克劳福德为了加强语气,还擦起拳头,又说了一遍,“等着瞧吧,咱们会使欧洲大吃一惊。还是依格内修斯·加拉赫丢了差事之后,在克拉伦斯[134]当台球记分员时经常说的。加拉赫才算得上是个新闻记者呢。 那才叫作笔杆子。你晓得他是怎样一举成名的吗?我告诉你吧。 那可是报界有史以来最精采的一篇特讯哩。八一年[135]五月六日,‘常胜军’时期, 凤凰公园发生了暗杀事件[136]。你那时大概还没有出生[137]呢。我找给你看看。”
他推开人们,踱向报纸合订本。
“喂,瞧瞧,”他回过头来说,“《纽约世界报》[138]拍了封海底电报来约一篇特稿。你还记得当时的事吗?”
麦克休教授点了点头。
“《纽约世界报》哩,”主编兴奋地把草帽往后推了推说,“案件发生的地点。蒂姆·凯里,我的意思是说,还有卡瓦纳、乔·布雷迪[139]和其他那些人。‘剥山羊皮’[140]赶马车经过的路程。写明整个路程,明白吧?”
“‘剥山羊皮’,”奥马登·伯克先生说,“就是菲茨哈里斯。听说他在巴特桥那儿经营着一座马车夫棚[141]。是霍罗翰告诉我的。你认识霍罗翰吗?”
“那个一瘸一拐的吧?”迈尔斯·克劳福德说。
“他告诉我说,可怜的冈穆利也在那儿,替市政府照看石料,守夜的。”
斯蒂芬惊愕地回过头来。
“冈穆利?”他说。“真的吗?那不是家父的一个朋友吗?”
“不必管什么冈穆利了!”迈尔斯·克劳福德气愤地大声说,“就让冈穆利去守着他那石头吧,免得它们跑掉。瞧这个。依纳爵·加拉赫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凭着天才和灵感,他马上就拍了海底电报。你有二月十七号的《自由人周刊》吗? 对,翻到了吗?”
他把合订本胡乱往回翻着,将手指戳在一个地方。
“掀到第四版,请看布朗梦想[142]的广告。找到了吗?对。”
电话铃响了。
远方的声音
“我去接,”教授边走向里屋,边说。
“B代表公园大门[143]。对。”
他的手指颤悠悠地跳跃着,从一个点戳到另一个点上。
“T代表总督府。 C是行凶地点。 K是诺克马龙大门[144l。”
他颈部那松弛的筋肉像公鸡的垂肉般颤悠着。没有浆好的衬衫假前脑一下子翘了起来,他猛地将它掖回背心里面。
“喂?是《电讯晚报》。喂?……哪一位?……是的……是的……是的。”
“F至P是‘剥山羊皮’为了证明他们当时不在犯罪现场而赶车走边的路线。英奇科尔、圆镇、风亭、帕默斯顿公园、拉尼拉。符号是F·A·B·P·。懂了吧?X是上利森街的戴维酒吧[145]。”
教授出现在里屋门口。
“是布卢姆打来的,”他说。
“叫他下地狱去吧,”主编立刻说,“X戴维酒吧,晓得了吧?”
伶俐极了
“伶俐……”利内翰说,“极了。”
“趁热给他们端上来,”迈尔斯·克劳福德说,“血淋淋地和盘托出。”
你永远不会从这场恶梦中苏醒过来。[146]
“我瞧见了,”主编自豪地说,“我刚好在场。迪克·亚当斯[147]是天主把生命的气吹进去[148]的科克人当中心地最他妈善良的一位。他和我本人都在场。”
利内翰朝空中的身影鞠了一躬,宣布说:
“太太,我是亚当。在见到夏娃之前曾经是亚伯。”[149]
“历史!”迈尔斯·克劳福德大声说,“亲王街的老太婆[150]打头阵。读了这篇特稿,哀哭并咬牙切齿。[151]特稿是插在广告里的。格雷戈尔· 格雷[152]设计的图案。他从此就扶摇直上。后来帕迪·胡珀在托·鲍面前替他说项,托·鲍就把他拉进了《星报》[153]。如今他和布卢门菲尔德 [154]打得火热。这才叫报业呢!这才叫天才呢!派亚特[155]!他简直就是大家的老爹!”
“黄色报纸的老爹,”利内翰加以证实说,“又是克里斯·卡利南[156]的姻亲。”
“喂?听得见吗?嗯,他还在这儿哪。你自已过来吧。”
“如今晚儿,你可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新闻记者呀,呃?”主编大声说。
他呼啦一下把合订本合上了。
“很得鬼,”[157]利内翰对奥马登·伯克先生说。
“非常精明,”奥马登·伯克先生说。
麦克休教授从里面的办公室走了出来。
“说起‘常胜军’,”他说,“你们晓得吗,一些小贩被市记录法官[158]传了去……”
“可不是嘛,”杰·杰·奥莫洛伊热切地说,“达德利夫人[159]为了瞧瞧被去年那场旋风[160]刮倒了的树,穿过公园走回家去。她打算买一张都柏林市一览图。原来那竟是纪念乔·布雷迪或是‘老大哥’[161]或是‘剥山羊皮’的明信片。而且就在总督府大门外出售
着哩,想想看!”
“如今晚儿这帮家伙净抓些鸡毛蒜皮,”迈尔斯·克劳福德说,“呸!报业和律师业都是这样!现在吃律师这碗饭的,哪里还有像怀持赛德[162]、 像伊萨克·巴特[163]、像口才流利的奥黑根[164那样的人呢?呃?哎,真是荒唐透顶!呸!只不过是撮堆儿真的货色!”
他没再说下去。嘴唇却一个劲儿地抽搐着,显示出神经质的嘲讽。
难道会有人愿意跟那么个嘴唇接吻吗?你怎么知道呢?那么你为什么又把这写下来呢?
韵律与理性
冒斯,扫斯。冒斯和扫斯之间多少有些关联吧?要么,难道扫斯就是一种冒斯吗?准是有点儿什么。扫斯,泡特,奥特,少特,芝欧斯。[165]押:两个人身穿一样的衣服,长得一模一样,并立着。[166]
……给你太平日子,
……听你喜悦的话语,
趁现在风平浪静的一刻。[167]
但丁瞥见少女们三个三个地走了过来。着绿色、玫瑰色、枯叶色的衣服,相互搂着;穿过了这样幽暗的地方[168],身着紫红色、紫色的衣服,打着那和平的金光旗[169],使人更加恳切地注视[170]的金光灿烂的军旗,走了过来。可我瞧见的却是一些年迈的男人,在黯夜中,忏悔着自己的罪行,抱着铅一般沉重的脚步:冒斯、扫斯;拖姆、卧姆。[171]
“说说你的高见吧,”奥马登·伯克先生说。
一天应付一天的就够了……
杰·杰·奥莫洛伊那苍白的脸上泛着微笑,应战了。
“亲爱的迈尔斯,”他说,一边丢掉纸烟,“你曲解了我的话。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而言,我并不认为第三种职业[172]这整个行当都是值得辩护的。 然而你的科克腿[173]被感情驱使着哪。为什么不把亨利·格拉顿[174]弗勒德[175], 以及狄靡西尼[176]和埃德蒙·伯克[177]也抬出来呢?我们全都晓得伊格内修斯· 加拉赫,还有他那个老板,在查佩利佐德出版小报的哈姆斯沃思[178]; 再有就是他那个出版鲍厄里通俗报纸的美国堂弟[179]。《珀迪·凯利要闻汇编》、《皮尤纪事》以及我们那反映敏捷的朋友《斯基勃林之鹰》[180],就更不用说了。 何必扯到怀特赛德这么个法庭辩论场上的雄辩家呢?编报纸,一天应付一天的就够了[181]。”
同往昔岁月的联系
“格拉顿和弗勒德都为这家报纸撰过稿,”主编朝着他嚷道,“爱尔兰义勇军[182]。你们如今都哪儿去啦?一七六三年创刊的。卢卡斯大夫。像约翰·菲尔波特·柯伦[183]这样的人,如今上哪儿去找呀?呸!”
“喏,”杰·杰·奥莫洛伊说,“比方说,英国皇家法律顾问布什[184]。”
“布什?”主编说,“啊,对。布什,对。他有这方面的气质。肯德尔·布什[185]我指的是西摩·布什。”
“他老早就该升任法官了,”教授说,“要不是……唉,算啦。”
杰·杰·奥莫洛伊转向斯蒂芬,安详而慢腾腾地说:
“在我听到过的申辩演说中,最精采的正是出自西摩·布什之口。那是在审理杀兄事件一一蔡尔兹凶杀案。布什替他辩护来着。”
注入我的耳腔之内。[186]
顺便问一下,是怎样发觉的呢?他是正在睡着的时候死的呀。还有另外那个双背禽兽[187]的故事呢?
“演说的内容是什么?”教授问。
意大利,艺术的女王[188]
“他谈的是《罗马法》的证据法,”杰·杰·奥莫洛伊说, “把它拿来跟古老的《摩西法典》一一也就是说,跟《同态复仇法》[189]一一相对照。于是,他就举出安置于罗马教廷的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摩西》作例证。”
“嗬。”
“讲几句恰当的话,”利内翰作了开场白,“请肃静!”
静场,杰·杰·奥莫洛伊掏出他的香烟盒。
虚妄的肃静。其实不过是些老生常谈。
那位致开场白的取出他的火柴盒,若有所思地点上一支香烟。
从此,我[190]经常回顾那奇怪的辰光,并发现,划火柴本身固然是很小的一个动作,它却决定了我们两个人那以后的生涯。
干锤百炼的掉尾句
杰·杰·奥莫洛伊字斟句酌地说下去:
“他是这么说的:那座堪称为冻结的音乐[191]的石像, 那个长了犄角的可怕的半神半人的形象[192],那智慧与预言的永恒象征。 倘若雕刻家凭着想象力和技艺,用大理石雕成的那些净化了的灵魂和正在净化着的灵魂的化身,作为艺术品有永垂不朽的价值的话,它是当之无愧的。”
他挥了挥细长的手,给词句的韵律和抑扬平添了一番优雅。
“很好!”迈尔斯·克劳福德立刻说。
“非凡的灵感,”奥马登·伯克说。
“你喜欢吗?”杰·杰·奥莫洛伊问斯蒂芬。
那些词藻和手势的优美使得斯蒂芬从血液里受到感染。他涨红了脸,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杰·杰·奥莫洛伊把那烟盒伸向迈尔斯·克劳福德。利内翰像刚才那样为大家点燃香烟,自己也当作战利品似地拿了一支,并且说:
“多多谢谢嘞。”
高风亮节之士
“马吉尼斯教授[193]跟我谈到过你,”杰·杰·奥莫洛伊对斯蒂芬说,“对于那些神秘主义者[194],乳白色的、沉寂的[195]诗人们以及神秘主义大师A· E·[196],你真正的看法是怎样的?这是那个姓勃拉瓦茨基[197]的女人搞起来的。她是个惯于耍花招的老婆子。A·E·曾跟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198]说,你曾在凌晨去看他,向他打听过心理意识的层次。马吉尼斯认为你是在嘲弄A· E·。马吉尼斯可是一位高风亮节之士哩。”
谈到了我。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些什么?他是怎样谈论我的?不要去问。
“不抽,谢谢,”麦克休教授边推开香烟盒边说,“且慢,我只说说一件事。我平生听到的最精采的一次演说,是约翰·弗·泰勤[199]学院的史学会上发表的[200]法官菲茨吉本[201]先生一一现任上诉法庭庭长一一刚刚讲完。所要讨论的论文(当时还是蛮新鲜的)是提倡复兴爱尔兰语[202]。”
他转过身来对迈尔斯·克劳福德说:
“你认识杰拉尔德·菲茨吉本。那么你就不难想象出他演说的格调了。”
“听说眼下他正跟蒂姆·希利[203]一道,”杰·杰·奥莫洛伊说,“在三一学院担任财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哪。”
“他正跟一个穿长罩衫的乖娃儿[204]在一起哪。”迈尔斯·克劳福德说,“讲下去吧,呃?”
“那篇讲演嘛,你们注意听着,”教授说,“是雄辩家完美的演说词。既彬彬有礼,又奔放豪迈,用语洗练而流畅。对于新兴的运动虽然还说不上是把惩戒的愤怒倾泄出来,[205]但总归是倾注了高傲者的侮辱。 当时那还是个崭新的运动呢。咱们是软弱的,因而是微不足道的。”
他那长长的薄嘴唇闭了一下。但他急于说下去,就将一只扎煞开来的手举到眼镜那儿,用颤巍巍的拇指和无名指轻轻扶了一下黑色镜框,使眼镜对准新的焦点。
即席演说
他恢复了平素的口吻,对杰·杰、奥莫洛伊说:
“你应该知道,泰勒是带病前往的。我不相信他预先准备过演说词,因为会场上连一个速记员都没有。他那黝黑瘦削的脸上,胡子拉碴,肮里肮脏的。松松地系着一条白绸领巾,整个来说,看上去像个行将就木之人(尽管并不是这样)。
此刻他的视线徐徐地从杰·杰·奥莫洛伊的脸上转向斯蒂芬,然后垂向地面,仿佛若有所寻。他那没有浆洗过的亚麻布领子从弯下去的脖颈后面露了出来,领子已被枯草般的头发蹭脏了。他继续搜寻着,并且说:
“菲茨吉本的演说结束后,约翰·弗·泰勒站起来反驳他。据我的回忆,大致是这么说的。”
他坚毅地抬起头。眼睛里又露出沉思的神色。迟钝的贝壳在厚实的镜片中游来游去,在寻找着出口。
他说:
“主席先生,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刚才听到我那位学识渊博的朋友对爱尔兰青年所发表的演说,佩服之至。我仿佛被送到离这个国家很远的一个国家,来到离本时代很远的一个时代;我仿佛站在古代埃及的大地上, 聆听着那里的某位祭司长对年轻的摩西训话。”
听众指间一动也不动地夹着香烟,聆听着。细微的轻烟徐徐上升,和演说一道绽开了花。让香烟袅袅上升[206]。这就要说出崇高的言词来了。 请注意。你自己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我好像听见那位埃及祭司长把声音提高了,带有自豪而傲慢的腔调。我听见了他的话语,并且领悟了他所启迪的含义。”
教父[207]们所示
我受到的启迪是:这些事物固然美好,却难免受到腐蚀;只有无比美好的事物,抑或并不美好的事物,才不可能被腐蚀。[208]啊,笨蛋!这是圣奥古期丁的话哩。
“你们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语言?你们不过是一介牧民,我们却是强大的民族。你们没有城市,更没有财富。我们的都市里,人群熙攘;有着三至四层桨的大帆船[209],满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驶入全世界各个已知的海洋。你们刚刚脱离原始状态,而我们却拥有文学、僧侣、悠久的历史和政治组织[210]。”
尼罗河。
娃娃,大人,偶像。[211]
婴儿的奶妈们跪在尼罗河畔。[212]用宽叶香蒲编的摇篮。格斗起来矫健敏捷[213]的男子。长着一对石角[214],一副石须,一颗石心。
“你们向本地那无名的偶像[215]祷告。我们的寺院却宏伟而神秘, 居住着伊希斯和俄赛里斯,何露斯和阿蒙一端。[216]你们信仰奴役、畏惧与谦卑;我们信仰雷和海洋。以色列人是孱弱的,子孙很少;埃及人口众多,武力令人生畏。 你们被称作流浪者和打零工的;世界听到我们的名字就吓得发抖。”
演说到此顿了一下,他悄悄地打了个饿嗝,接着又气势澎湃地扬起了嗓门:
“可是,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倘若年轻的摩西聆听并接受这样的人生观;倘若他在如此妄自尊大的训诫面前俯首屈从,精神萎顿,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领着选民离开他们被奴役的地方了[217],更不会白天跟着云柱走。[218]他决不会在雷电交加中在西奈山顶与永生的天主交谈。[219] 更永远不会脸上焕发着灵感之光走下山来,双手捧着十诫的法版,而那是用亡命徒的语言镌刻的。”
他住了口,望着他们,欣赏着这片寂静。
不祥之兆——对他而言!
杰·杰·奥莫洛伊不无遗憾地说:
“然而,他还没进入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就去世啦。”[220]
“当时一来得一突然一不过一这病一拖延一已久一早就一频频一预期到会因吐血症一致死的,”[221]利内翰说,“他本来是会有锦绣前程的。”
传来了一群赤足者奔过走廊,并吧哒吧哒地上楼梯的声音。
“那才是雄辩之才呢,”教授说,“没有一个人反驳得了。”
随风飘去[222]。位于马勒麻斯特和塔拉那诸王的军队。连绵数英里的柱廊,侧耳聆听。保民官怒吼着,他的话语随风向四方飘去。 人们隐蔽在他的嗓音里。[223]业已消逝了的音波。阿卡沙秘录[224]——它记载着古往今来在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一切。爱戴并称赞他。不要再提我。
我有钱。[225]
“先生们,”斯蒂芬说,“作为下一项议程,我可不可以提议议会立即休会?”
“你叫我吃了一惊。这该不会是法国式的恭维[226]吧?” 奥马登·伯克先生问道,“打个比喻吧,我认为现在正是古老客栈里的那只酒甕使人觉得无比枢意的时刻哩。”
“那么,就明确地加以表决。凡是同意的,请说‘是’,”利内翰宣布说,“不同意的,就说‘不’。一致通过。到哪家酒馆去呢?……我投穆尼[227]一票!”
他领头走着,并告诫说:
“咱们是不是要断然拒绝喝烈性酒呢?对,咱们不喝。无论如何也不。”
奥马登·伯克先生紧跟在他后面,用雨伞戳了他一下,以表示是同伙,并且说:
“来,麦克德夫!”[228]
“跟你老子长得一模一样!”主编入声说着,拍了拍斯蒂芬的肩膀。“咱们走吧。那串讨厌的钥匙哪儿去啦?”
他在兜里摸索着,拽出那儿页揉皱了的打字信稿。
“口蹄疫。我晓得。那能行吧。登得上的。钥匙哪儿去了呢?有啦。”
他把信稿塞回兜里,走进了里间办公室。
寄予希望
杰·杰·奥莫洛伊正要跟他往里走,却先悄悄地对斯蒂芬说:
“我希望你能活到它刊登出来的那一天。迈尔斯,等一下。”
他走进里间办公室,随手带上了门。
“来吧,斯蒂芬,”教授说,“挺好的,对吧?颇有预言家的远见。特洛伊不复存![229]对多风的特洛伊[230]大举掠夺。世上的万国。 地中海的主人们而今已沦落为农奴[231]。”
走在顶前面的那个报童紧跟在他们后面。吧哒吧哒地冲下楼梯,奔上街头,吆喝着:
“赛马号外!”
都柏林。我还有许许多多要学的。
他们沿着阿贝街向左拐去。
“我也有我的远见,”斯蒂芬说。
“呃?”教授说,为了赶上斯蒂芬的步伐,他双脚跳动着,“克劳福德会跟上来的。”
另一个报童一个箭步从他们身旁蹿了过去,边跑边吆喝着:
“赛马号外!”
亲爱而肮脏的都柏林[232]
都柏林人。
“两位都柏林的维斯太[233],”斯蒂芬说,“曾经住在凡巴利小巷[234]里。一个是五十岁,另一个五十三。”
“在什么地方?”教授问。
“在黑坑[235]口外,”斯蒂芬说。
湿漉漉的夜晚,飘来生面团气味,引人发馋。倚着墙壁。她那粗斜纹布围巾下面,闪烁着一张苍白的脸。狂乱的心。阿卡沙秘录。快点儿呀,乖乖![236]
讲出来吧,果敢地。要有生命。[237]
“她们想从纳尔逊纪念柱顶上眺望都柏林的景色。她们在红锡做的信箱型攒钱罐里存起了三先令十便士。从罐里摇出几枚三便士和一枚六便士的小银币,又用刀刃拨出些铜币。两先令三便士是银币,一先令七便士是铜币。然后戴上软帽,穿上最好的衣服,还拿了雨伞,防备下雨。”
“聪明的处女们[238],”麦克休教授说。
粗鄙的生活
“她们在马尔巴勒的北城食堂,从老板娘凯持·科林新手里头了一先令四便士的腌野猪肉和四片面包。在纳尔逊纪念柱脚下,又从一个姑娘手里头了二十四个熟李子,为了吃完咸肉好解渴。她们付给把守旋转栅门的人两枚三便士银币,然后打着趔趄,慢慢腾腾地沿着那螺旋梯攀登,一路咕依着,气喘吁吁,都害怕黑暗,相互鼓着劲儿。这个问那个带没带上咸肉,并赞颂着天主和童贞圣母玛利亚。忽而说什么干脆下去算了,忽而又隔着通气口往外瞧。荣耀归于天主。她们再也没想到纪念柱会有这么高。
“有一个叫安妮·基恩斯,另一个叫弗萝伦斯·麦凯布[239]。安妮·基恩斯患腰肌病,擦着一位太太分给她的路德圣水——一位受难会[240]神父送给那位太太一整瓶。弗萝伦斯·麦凯布每逢星期六晚饭时吃一只猪蹄子,干一瓶双X牌啤酒[241]。”
“正好相反,”教授点了两下头说,“维斯太贞女们。我仿佛能够看见她们。咱们的朋友在磨蹭什么哪?”
他回过头去。
一群报童连蹦带跳地冲下台阶,吆喝着朝四面八方散去,呼扇呼扇地挥着白色报纸。紧接着,迈尔斯·克劳福德出现在台阶上,帽子像一道光环,镶着他那张红脸。他正在跟杰、杰·奥莫洛伊谈着话。
“来吧,”教授挥臂大声嚷道。
他又和斯蒂芬并肩而行。
“是啊,”他说,“我仿佛看得见她们。”
布卢姆归来
在《爱尔兰天主教报》和《都柏林小报》[242]的公事房附近,布卢姆先生被卷进粗野的报童们的旋涡里,气儿都透不过来了。他招呼道:
“克劳福德先生!等一等!”
“《电讯报)》!赛马号外!”
“什么呀?”迈尔斯·克劳福德退后一步说。
一个报童冲着布卢姆的脸嚷道:
“鲁思迈因斯的大惨剧!风箱叼住了娃娃!”
会见主编
“就是这份广告的事儿,”布卢姆先生推开报童们,呼哧呼哧地挤向台阶,并从兜里掏出剪报说,“我刚刚跟凯斯先生谈过。他说,他要继续刊登两个月广告,以后再说。然而他还想在星期六的《电讯报》上登一则花边广告,好引人注目。要是来得及的话,他想把《基尔肯尼民众报》[243]的图案描摹下来。这,我己经告诉南尼蒂参议员了。我可以从国立图书馆弄到这图案。‘钥匙议院’,你明白吧。他姓凯斯。刚好谐音[244]。然而他实际上己经答应续登了。不过,他要求给弄得花哨一点。你有什么话要我捎给他吗,克劳福德先生?”
吻我的屁股[245]
“请你告诉他‘吻我的屁股’好吗?”迈尔斯·克劳福德边说边摊开胳膊,加强了语气,“马上去告诉他这是条直接来自马房的消息。”
怪心烦的。留神着点狂风。相互挽着胳膊,大家一道出去喝酒。头戴水手帽的利内翰也跟在后面,想捞上一盅。他像往常一样拍马屁。令人纳闷的是,竟然由小迪达勒斯带头。今天他穿了双好靴子。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连脚后跟都露出来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膛过烂泥。这小子就是这么大大咧咧。他在爱尔兰区干什么来着?
“喏,”布卢姆先生把视线移回来说,“要是我能够把图案弄到手,我认为是值得为它写上一段的。他想必会刊登广告。我要对他说……”
吻我高贵的爱尔兰屁股[z46]
“他可以吻我高贵的爱尔兰屁股,”迈尔斯·克劳福德回过头来大声嚷道,“告诉他吧,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
正当布卢姆先生站在那儿琢磨着该怎样回答才好并正要泛出笑容的当儿,对方已跨着大步一颠一颠地走掉了。
筹 款
“囊空如洗,[247]杰克,”他把手举到下巴颏那儿说,“水已经淹到我这儿啦。我自己也是穷得一筹莫展。上礼拜找还在找个人出面在我的借据上签字担保呢! 对不起,杰克。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请你务必体谅我这苦衷。要是好歹能够筹到钱,我一定乐意帮你忙。”
杰·杰·奥莫洛伊把脸一耷拉,默默地继续踱着步。他们追上前面的人,和他们并肩而行。
“当她们吃完腌肉和面包,用包面包的纸把二十个指头擦干净之后,就靠近了栅栏。”
“你听了会开心的,”教授向迈尔斯·克劳福德解释道,“两个都柏林老枢爬到纳尔逊纪念柱顶上去啦。”
了不起的圆柱!——一瞒珊走路者如是说
“这可是挺新鲜,”迈尔斯·克劳福德说,“够得上是条新闻素材。简直就像是到达格尔[248]去参加皮匠的野餐会。两个刁婆子,后来呢?”
“可是她们都害怕柱子会倒下来,”斯蒂芬接下去说,“她们眺望着那些屋顶,议论着哪座教堂在哪儿,拉思曼斯的蓝色拱顶[249],亚当与夏娃教堂[250],圣劳伦斯·奥图尔教堂[251]瞧着瞧着,她们发晕了。于是,撩起了裙子……”
有点无法无天的妇女
“大家安静下来!”迈尔斯·克劳福德说,“谁作诗也不许破格。如今咱们是在大主教的辖区里哪。”
“她们垫着条纹衬裙坐了下去,仰望着独臂奸夫[252]的那座铜像。”
“独臂奸夫!”教授大声说, “我喜欢这种说法。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据信,三位女士赠予都柏林市民
高速陨石及催长粒肥
“后来她们的脖子引起了痉挛,”斯蒂芬说,“累得既不能抬头,也不能低头或说话。她们把那袋李子放在中间,一枚接一枚地掏出来吃。用手绢擦掉从嘴里淌下的汁子,慢悠悠地将核儿吐到栅栏之间。”[253]
他猛地发出青春的朗笑声,把故事结束了。利内翰和奥马登·伯克先生闻声回过头来,招招手,带头向穆尼酒馆走去。
“完了吗?”迈尔斯·克劳福德说,“只要她们没干出更越轨的事就好。”
智者派[254]使傲慢的海伦丢丑
斯巴达人咬牙切齿
伊大嘉人断言潘奈洛佩[255]乃天下第一美人
“你使我联想到安提西尼[256],”教授说,“智者派高尔吉亚[257]的门徒。据说,谁也弄不清他究竟是对旁人还是对自己更加怨恨。他是一位贵族同一个女奴所生之子。他写过一本书,其中从阿凯人[258]海伦那儿夺走了美的棕榈枝,将它交给了可怜的潘奈洛佩。”
贫穷的潘奈洛佩。潘奈洛佩·里奇。[259]
他们准备横穿过奥康内尔街。
喂,喂,总站!
八条轨道上,这儿那儿停着多辆电车,触轮一动也不动。有往外开的,也有开回来的。拉思曼斯、拉思法纳姆[260]、黑岩国王镇,以及多基、沙丘草地、林森德;还有沙丘塔、唐尼布鲁克[261]、帕默斯顿公园,以及上拉思曼斯,全都纹丝不动。由于电流短路的缘故,开不出去了。出租马车、街头揽座儿的马车、送货马车、邮件马车、私人的四轮轿式马车,以及一瓶瓶的矿泉汽水在板条箱里恍当恍当响的平台货车,全都由蹄子碍碍响的马儿拉着,咯哒咯哒地疾驰而去。
叫什么?——一还有——一在哪儿?
“然而,你管它叫什么?”迈尔斯·克劳福德问道,“她们是在哪儿买到李子的?”
老师说要维吉尔风格的,
大学生[262]为摩西老人投一票
“管它叫作一一且慢,”教授张大了他那长长的嘴唇,左思右想,。管它叫作一一让我想想。管它叫作:《神赐与我们安宁》[263]怎么样?”
“不,”斯蒂芬说,“我要管它叫《登比斯迦眺望巴勒斯坦[264],要么就叫它《李子寓言[265]》。”
“我明白了,”教授说。
他朗声笑了。
“我明白啦,”他带着新的喜悦重复了一遍,“摩西和神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他对杰·杰·奥莫洛伊又补了一句:“这还是咱们启发他的呢。”
在这个明媚的六月日子里,
霍雷肖[266]在众目睽睽之下
杰·杰·奥莫洛伊疲惫地斜睨了铜像一眼,默不作声。
“我明白啦,”教授说。
他在竖有约翰·格雷爵士[267]的街心岛上停下脚步,布满皱纹的脸上泛着苦笑,仰望那高耸的纳尔逊。
对轻佻的老妪来说,缺指头简直太逗乐了。
安妮钻孔。 弗萝[268]遮遮掩掩
然而,你能责备她们吗?
“独臂奸夫,”他狞笑着说,“不能不说是挺逗乐的。”
“要是能让人们晓得全能的天主的真理的话,”迈尔斯·克劳福德说,“两位老太婆也觉得挺逗乐的。”
第七章注释
[l]希勃尼亚是拉丁文中对爱尔兰的称谓,多用于文学作品中。
[2]E?R?是Edwardus Rex(爱德华王的拉丁文称呼)的首字。
[3]这是坐落在北亲王街十七号的一家货栈。
[4]红穆雷是约翰?穆雷的绰号,系乔伊斯以他那个在《自由人报》会计科工作的同名二舅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参看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19页)。
[5]戴维?斯蒂芬斯是作者根据都柏林一个同名的报亭老板塑造的形象。当爱德华七世于一九0三年访问爱尔兰时,他曾和国王打过交道,从那以后便以国王的信使自居。
[6]威廉?布雷登(1865一1933),爱尔兰律师,《自由人报》主编(1892一1916)。
[7]指威廉?布雷登。
[8]吉尼斯啤酒,参看第五章注[44]。
[9]乔万尼?马蒂乌?马里奥(1810一1883),意大利歌手,出身贵族家庭,一八七一年最后一次演出。当时布卢姆才五岁。
[lO]《玛尔塔》(1847)是法国歌剧作曲家弗里德里希?弗赖赫尔封?弗洛托(1812一1883)用德文写的五幕轻歌剧,后译成意大利文。写英国安妮女王宫廷里的宫女哈丽特装扮成村女,化名玛尔塔,来到里奇蒙集市,遇到富裕农场主莱昂内尔并相爱。玛尔塔一度逃跑,致使莱昂内尔神经失常,直到把集市上初次相见的情景扮演给他看,他才恢复理智,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11]这两行摘自《玛尔塔》第4幕中莱昂内尔的咏叹调。
[l2]艾尔曼在《詹姆斯?乔伊斯》一书(第288页)中说,这里的主教大人指都柏林大主教威廉?]?沃尔什(1841一1921)。 一八八九年他曾带头谴责巴涅尔(参看第二章注[81]),因而惹怒了支持巴涅尔的《自由人报》发行人托马斯?塞克斯顿。多年来,他的报纸处处贬低沃尔什。沃尔什经常提出抗议。“打了两次电话”即指此事。牧杖见第三章注[27]。
[13]约瑟夫?帕特利克?南尼蒂(1851一1915),在爱尔兰出生的意大利人,当时在《自由人报》社担任排字房工长。他又是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兼都柏林市政委员(1900一1906)。
[14]他指南尼蒂。
[15]学院草地是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区。南尼蒂常说,他并不是个职业政治家,而是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工人。
[16]官方公报指每星期二、五出版的《都柏林公报》,它是经英国政府文书局印刷和发行的。
[17]英国女王安妮于一七一四年逝世的消息早已家喻户晓后,英国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1672一1719)所办刊物《旁观者》才报道说:“安妮女王驾崩。”从此,这个句子遂成为“过时消息”的代用语。
[18)廷纳欣奇男爵领地位于都柏林市东南十二英里处。一七九七年,爱尔兰议会把它奖给了亨利?格拉顿(1746一1820)。他曾于一七八二年领导斗争,迫使英国准许爱尔兰立法独立。
[l9]巴利纳是爱尔兰马尤郡的一应小商埠。《自由人周刊》辟有“市场新闻”专栏。
[20]《自由人周刊》有一栏题为“园艺琐记”,专门探讨农业及畜牧业方面的问题。
[2l]指《自由人周刊》所编的“我们的漫画”专辑。通常刊登的并非讽刺画,而是政治讽刺诗。
[22]《人物》是托马斯?鲍尔?奥康纳(1848一1929)主编的每册一便士、逢星期三出版的周刊。奥康纳是个爱尔兰新闻记者、报刊经营者及政治家,另外还在伦敦主编《太阳》、《星报》、《星周刊》等报刊。
[23]大多是照片,指的是本世纪初《自由人周刊?国民新闻》照相感光制版副刊。
[24]文森特?卡普拉尼在《詹姆斯?乔伊斯与我的祖父》(1982)一文中说,本世纪初他的祖父文森特?梅诺蒂?卡普拉尼(约1869一1932)参加了《自由人报》印刷工会。他和胞弟曾与一对奥康纳姐妹同时举行婚礼。
[25]一九0六年,南尼蒂任都柏林市市长。
[26]高个儿约翰指范宁。他是小说中虚构的都柏林市副行政长官。《都柏林人》中的《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里就曾提到他。另一篇《恩宠》中,说他是“注册经纪人,市长竞选的幕后决策者”。
[27]钥匙议院指曼岛{参看第六章注[50])下议院。
[28]钥匙议院的原文是House of Keys。院徽的图案由两把十字交叉的钥匙构成。KeyeS(凯斯)与keys发音相近。亚历山大?凯斯所开的店叫House of Keyes(凯斯商店),所以他把议院的这个微记用在店铺的广告中了。
[29]这是意大利文,意思是“要”。参看第四章注[52]。
[30]“看一个……味的”:这里,作者把原文拆开,插进一些说明。
[3l]英语中,墓地(cemetery)与匀称(symmetry)发音相近。
[32]巴尔斯布里奇位于都柏林东南郊。自一七三一年起,每年在这里举办马匹展示会?吸引世界各地的马匹爱好者。一九0四年是在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的。
[33]关于蒙克斯,在第十六章有续笔(见该章注[194]及有关正文)。
[34]逾越节是犹太民族的主要节期,约在阴历三、四月间。犹太人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据《出埃及记》第12章,天主叫犹太人宰羊把血涂在门楣上,天使击杀埃及人的头生子和头生的牲畜时,见有血迹的人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随后,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摆脱了奴役。
[35]《哈加达》书是犹太教法典中的传说部分,载有《出埃及记》故事及礼仪。
[36]原文为希伯来文。按希伯来文是自右至左写,所以说是“倒指着”。
[37] 《出埃及记》第l3章第8节有“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之句。第14节又有“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之句。与这里的意思刚好相反。
[38]原文为希伯来文,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用语?,赞美神的意思。
[39]原文为希伯来文,系赞美歌,见《旧约?申命记》第6章第4节。
[40]雅各(以色列入的祖先)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见《出埃及记》第1章。
[41]羊羔,见《出埃及记》第12章第3节。
[42]杖,见《出埃及记》第7至8章。写亚伦用手中的杖一击地,就使埃及遍地的灰尘都变成虱子。
[43]水,见《出埃及记》第17章第6节。以上均指《出埃及记》中的故事。
[44]语搞自逾越节中唱的《查德?加迪亚》(希伯来语,意思是《一只小羚羊》)。此歌以弱肉强食为主题,而排在末位、受害最深的小羚羊象征着以色列老百姓。
[45]指亚历山人?汤姆印刷出版公司。《自由人报》社与该公司之间仅相隔一座楼。
[46]爱琳(Erin)是爱尔兰古称,由盖尔语爱利(Eire)演变而来。至今仍用作富有诗意的称呼。
[47]《电讯晚报》的出纳员名叫拉特利奇。每逢发薪日,他就到各间办公室去转一趟,亲自把工资发到每个人手里。人们戏称他为“幽灵走来了”。乔伊斯借麦克休教授之口把此事写了进去。(见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289页。)
[48]架成拱形,原文作overarg。兰伯特故意把它读成相近的overarsing。按over含有“蒙在……上面”之意,而arsing则是他杜撰的,系将名词arse(屁股)写成了进行式。
[49]色诺芬(参看第一章注[14])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出生于呵提卡一个雅典人家庭。苏格拉底于公元前三九九年被处死后,色诺芬曾参加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所指挥的部队,他们在科罗尼亚战役中打败了希腊联军。
[50]乌拉松是希腊东南部阿提卡东北岸的一片平原。这里是古战场,公元前四九0年,雅典军队曾在此击败前来进犯的波斯大军。
[51]这里套用拜伦的长诗《唐磺》(1818一1823)第3章的诗句。原诗作:“群山俯瞅乌拉松,乌拉松濒临大海。”
[52]赫奇斯?艾尔?查特顿(1820一1910),都柏林大学副校长,历任副检察长(1866)、首席检察官(1867)等职。
[53]这里套用十九世纪末叶流行的一首歌曲,只是把原歌中的“汤米”改成了“约翰尼”。
[54]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一前43), 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作家。他的演说辞内容充实,说服力强,讲究层次和对称。教授为了讽刺丹?道森那篇演说词内容空虚,故意把它说成是西塞罗的文章。
[55]查理?丹?追森(参看第六章注[20])是都柏林面包公司老板,曾任都柏林市市长(1882一1883),一九0四年任都柏林市政府收税官。
[56]利内翰是曾出现在《都柏林人?两个浪子》中的一个人物,系浪子之一,既没有正当职业,也未成家。
[57]语出自《旧约?何西阿书》第8章第7节。意思是种下恶行,必收十倍的恶报。
[58]当时都柏林确实有个叫作托马斯?菲茨杰拉德的律师。与狄?菲茨杰拉德共同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
[59]加布里埃尔?康罗伊是《都柏林人?死者》中的一个人物,经常为《每日快报》撰写文艺评论,就像乔伊斯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作的那样。《快报》为《每日快报》(1851一1921)的简称。这是爱尔兰的一家立场保守的报纸,不鼓励民族独立。
[60]《爱尔兰独立日报》的简称。这是巴涅尔垮台后创办的报纸,但他逝世后两十月(即1891年12月18日)才出版。不久就由反对巴涅尔的人们接管,开始持极端保守的立场。一九00年落入威廉?马丁?墨菲(1844一1921)之手。墨菲是个铁路承包商,一度被选入议会(1885-1892),一八九0年与巴涅尔反目。
[61]语出自《伊索寓言?人和羊人》。羊人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山野小神。他和一个人交朋友,看见此人把手放在嘴上呵气取暖,又嫌食物太烫, 用嘴把它吹凉。羊人认为他反复无常,便说了这句话,遂和他绝了交。
[62]在《哈姆莱特》一剧第1幕第1场中,霍拉旭说:“支配潮汐的月亮……”后来又说:“可是确,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丹?道森这篇文章只描述了月夜的爱尔兰,并没有像霍拉旭那样继续写迎来曙光的爱尔兰,所以麦克休说“他忘记了《哈姆莱特》”。
[63]威尔士梳子指五个手指。这是对威尔士人的贬语,说他们粗野,不整洁,用手代替梳子。
[64]原文作Doughy Daw。Doughy的意思是夹生。Daw可作傻瓜解。这里, 教授故意用与文章作者丹?道森(Dan Dawson)的姓名相近的这样两个词来挖苦他。
[65]韦瑟厄普,见第六章注[153]。
[66]冒牌乡绅原是弗朗西斯?希金斯《1746-1802》的绰号,这里以此戏称《自由人报》主编。希金斯本是都柏林市的一名公务员,冒充乡绅,与一个有地位的年轻女子结婚。接着又以开赌场起家,当上了《自由人报》老板,并利用报纸版面诽谤爱尔兰爱国志士。他还把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参看第十章注[143])躲藏的地方向当局告了密,获得一千英镑奖赏。
[67]指参加葬礼之后。
[68]主编所提到的北科克义勇军,在一七九八年的爱尔兰反英起义中曾站在英军一边。他们接连吃败仗。这支军队跟北美洲的俄亥俄风马牛不相及。一七五五年,英国倒是曾派爱德华?布雷多克少将(1695-1755)赴弗吉尼亚,任驻北美的英军指挥官。为了将法国人逐出俄亥俄盆地,他率兵远征迪凯纳堡(即今匹兹堡)的法国据点。但中途遭法军及其印第安盟军的突袭,远征遂以失败告终。
[69]风鸣琴是靠风力鸣响的一种弦乐器。原文作HarPEolian,也作“风神的竖琴”解。凯尔特吟游诗人喜奏竖琴,它是爱尔兰这个国家的象征。在土话中,“竖琴”也指爱尔兰天主教徒。
[70]清除留在牙缝中的食物碎屑用的细棉线。
[71]加拿大诈骗案指当时有个化名萨菲诺?沃特的人,被控以替扎列斯基等人购买赴加拿大的船票为名,诈骗钱财。
[72]《体育》是《自由人报》社逢星期六发行的售价一便士的小报,专载每周所有的体育消息。这一期是赛马特辑。
[73]原文为法语。
[74]原文作A?D?为拉丁文AnnoDomini(吾主之年)的简称。原指纪元后,口语中,有时亦指“老年”、“衰龄”。 [75]韦克斯福德是爱尔兰东南瑞伦斯特省一郡,也指该郡海湾和首府。 这两句歌词出自爱尔兰民谣《韦克斯福德的男子汉》(1798)。这首民谣描述了在 一七九八年爆发的民众起义中,韦克斯福德的男子汉们怎样在奥拉尔特镇击溃北科克义勇军(参看本章注[68])。
[76]这里套用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失乐园》(1667)中描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诗句,“整个世界在他们前面。”
[77]椭圆酒家坐落在《自由人报》社南边。
[78]帕迪?胡珀是都柏林一记者,在《自由人报》担任新闻通讯员。
[79]杰克?霍尔是都柏林一记者,以善于讲轶事掌故著称。
[80]原文作calumet,系印第安人谈判时使用的一种长杆旱烟袋,象征着和平。
[81]原文为法语。
[82]语出自《卡斯蒂利亚的玫瑰》(1857)第3 幕中化装成赶骡人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曼纽尔唱给“卡斯蒂利亚的玫瑰”艾尔微拉听的咏叹调。这部歌剧的作者为英裔爱尔兰歌唱家、作曲家迈克尔?威廉?巴尔夫(1808-1870)。
[83l原文为拉丁文。
[84]布里克斯顿位于伦敦西南部兰姆贝斯区。在本世纪初,此地曾被认为是枯燥乏味的工业化地区的典型。
[85]语出自美国诗人、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的《献给海伦》(1831、1845)一诗的第2段。
[86]英文中,帝国的(imperial)、专横的(imperious)、强制的(imperative)这三个形容词的语根都是imper。
[87]原文为拉丁文。
[88]原文作“thefirstchapterofGuinnes”。这是双关语。英文里,《创世记》作Genesis,而吉尼斯(参看本章注[8])作Guinness,发音相近。直译就是:《吉尼斯》第1章。暗指爱尔兰人热衷于喝吉尼斯公司所酿造的烈牲黑啤酒。
[89]《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总称。其中最早的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颁布的《十二表法》,系一部保护私有制反映商品生产最完备、最典型的古代法律,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有较大影响。
[90]庞修斯?彼拉多,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驻犹太地方的总督(约26-约36在职)。据《新约》记载,耶稣是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91]指克里斯托弗?帕利斯(1831-1920),爱尔兰律师,税务法庭(于1873年归并高等法院)庭长。
[92]王家大学是一八八0年创立于都柏林的一个审核并认可学位的机构。
[93]多尼戈尔是爱尔兰多尼龙尔郡的海港和商业城镇,生产手织花呢。
[94]奥马登?伯克这个人物曾出现在《都柏林人?母亲》中。
[95]原文为法语。
[96]“扬起……亲吻”,这四句诗系斯蒂芬根据《我的忧愁在海上》(参看第三章注[169])一诗的末段润色加工而成。
[97]参看第二章注[85]。
[98]奥鲁尔克,参看第二章注[80]。
[99]指哈布斯堡王朝(lO2O-1919),即奥地利帝国,系欧洲最大的王朝之一。
[lO0]封蒂尔柯涅尔伯爵马克西米连?卡尔?奥唐奈是个爱尔兰移民之子,一八一二年生在奥地利,任奥地利皇帝(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 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48-1916在位)的侍从武官。 一八五三年他陪皇帝沿着维也纳周围的堡垒散步。一天,他及时击倒了一个刺伤皇帝的匈牙利裁缝,皇帝说他救了自己一命。
[101]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爱德华七世于一九0三年对奥匈帝国作国事访问时,在维也纳将英国陆军元帅头衔授与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一九0 四年六月九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奥地利大公弗兰茨?裴迪南(1863-1914)对英国作国事访问时,回赠给爱德华七世一根奥地利陆军元帅官杖。
[102]“野鹅”,参看第三章注[68]。
[lO3]指对奥地利皇帝行刺的匈牙利裁缝,参看本章注[l00]。
[104]创造了真正的文化的希腊却败在罗马手下。克劳福德作为英国的属国爱尔兰的一个公民,这里把英国比作罗马。
[105]原文为拉丁文。
[106]英文中,勋爵和主(指耶稣、天主)均为Lord。 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勋爵(1830-1903)是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三次出任首相。他主张不对爱尔兰作任何让步。
[107]伦敦西区是繁华地带,有上层人士的俱乐部。此处指索尔兹伯里等人坐在那里舒适的沙发上行使对爱尔兰的统治权。
[108]原文为希腊文。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用作弥撒的起始语。(109]原文为希腊文。
[ll0]闪米特族是分布在亚洲西南部的大种族,古代包括希伯来人、亚迷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巴比伦人等。撒克逊族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文,古时居住在今石勒苏益格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这里指盎格鲁-撒克逊族。闪米特族和撒克逊族都不晓得的母音,即希腊文第二十个字母upsilon, 这是希伯来字母和英文字母中所没有的。英文中用u和y来代替。
[111]、[112]原文为希腊文。
[113]修厕所的暗指罗马,挖下水道的暗指英国。
[114]特拉法尔加是加的斯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一个海角。一八0五年,法、西舰队在此溃败于纳尔逊麾下的英国舰队,损失了约二十艘舰船。
[115]伊哥斯波塔米是古代色雷斯的一条河流,它注入甘勒斯潘海峡。公元前四0五年,来山得率领的斯巴达舰队偷袭雅典海军的停泊地, 使其几乎全军覆没,次年雅典被迫投降。精神帝国即指希腊。
[116]原文为拉丁文。
[117]皮勒斯(参看第二章注[1])曾出兵攻打马其顿,把雅典从德米特里的包围中解救出来,又忍受惨重伤亡,打败罗马军队。后来在梦中接受神谕,误以为必胜无疑,就去大举进攻斯巴达,结果死于阿尔戈斯巷战中。
[118]“他们开赴战场, 然而总吃败仗”一语出自马修?阿诺德的讲演稿《论凯尔特文学研究》(1867)的引言。叶芝曾用此语作为收在《玫瑰集》(1893)中一首诗的标题。
[119]原文为法语。
[120]参看第二章注[15]。
[121]可笑,原作乔?米勒。此人是英王乔冶一世(1714-1727在位) 时代享有盛名的喜剧演员。在十九世纪,他的笑话集多次再版,从而使他的名字在俚语中即成为“笑话”的代名词。
[122]即盖乌斯?萨卢斯特斯?克里斯普斯(公元前86-公元前35), 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穆利根的话含有挖苦意,因萨卢斯特结束政治生涯后虽在历史著作中揭露了罗马政治的腐败,但他本人从政期间(他曾任保民官、行政官、行省总督)也曾巧取豪夺。
[123]这是穆利根说过的话,参看第一章注[37]及有关正文。
[124]《卡斯蒂利亚的玫瑰》,见本章注[82]。原文中,“TheRoseofCastile”这一剧名与“Rowsofcaststeel”(“并排的铸铁”)读音相近。
[125]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群众攻占了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狱,革命政府下令将它拆毁。
[126]尼古拉?博市里科夫(1839-1904)原为俄国陆军将官,一八九八年任俄国驻芬兰大公国总督。由于他大肆镇压芬兰人的消极抵抗,一九0四年六月十六日上午(都柏林时间为清晨)被反对俄国的芬兰人所刺杀。
[127]原文为拉丁文。
[128]语出自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1803-1873)的戏剧《黎塞留》(1838)第3幕第1场中的台词,下半句是:“没有失败一词”。
[129]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书第1章中,斯蒂芬因打碎了限镜,无法完成作业。教导主任多兰神父对他说:“懒惰的小捣蛋鬼。我从你的脸上就看得出你是个捣蛋鬼。懒散、吊儿郎当的小调皮鬼!”
[130]勃里斯-因-奥索里是爱尔兰王后郡的市镇, 位于都柏林西南六十六英里处。一八四三年,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奥康内尔曾在此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约翰?雷德蒙(1856-1918)曾于一九0 四年试图恢复奥康内尔当年举办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集会,然而毕竟要逊色多了。
[131]杰克?麦卡锡是《自由人报》一记者。杰克与茅坑(jakes)同音。
[132]他指主编迈尔斯?克劳福德。
[133]加拉赫,参看第六章注[8]。
[134]指都柏林的克拉伦斯商业饭店。
[135]这里,克劳福德把年份搞错了。按照史实,应作一八八二年。 转年二月十日,“常胜军”成员之一的彼得?凯里在法庭上作证,供述了所有参与作案的人。
[136]暗杀事件,参看第二章注[81]。
[137]本书第十七章中说,斯蒂芬出生于一八八二年。乔伊斯本人也出生于一八八二年的二月二日。
[138]《纽约世界报》是美国金融家杰伊?古尔德在一八七六年创办的日报。一八八二年五月七、八两日,用了不少篇福来报道凤凰公园暗杀案。
[139]以上三个人都是“常胜军”成员。据法庭上的证词,乔?布雷迪为主凶,他将两个被害人刺倒在地。蒂姆?凯里割断了他们的喉咙。作案者乘的出租马车是迈克尔?卡瓦纳驾驭的。
[140]“剥山羊皮”即杰姆斯?菲茨哈里斯的外号。他曾宰掉一只心爱的山羊以卖皮偿还酒债,遂有此绰号。参与凤凰公园暗杀案后,他赶一辆用以迷惑警方的出租马车,取直道从公园来到都柏林。他被判无期徒刑,一九0二年假释出狱。
[l41]在一九0四年,巴特桥是都柏林架在利菲河上的桥梁中尽东头的一应。实际上“剥山羊皮”并不是那个马车夫棚的老板,他像下文中提到的冈穆利(一个穷困落魄的中产户)那样,也为都柏林市政府看管石料。
[142]布朗森是伦敦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143]公园大门指凤凰公园东南距都柏林中心区最近的大门。
[144]诺克马龙大门是凤凰公园尽西头的大门。
[145]这些作案的“常胜军”曾在都柏林郊外的戴维酒吧停下来喝酒。
[146]参看第二章注[76]。
[147]迪克?亚当斯(生于1846年),先后任《科克观察报》和《自由人报》记者。一八七三年成为爱尔兰律师团的一名成员。在凤凰公园暗杀案中,他曾大力为杰姆斯?菲茨哈里斯等人辩护。
[148]这里套用《创世记》第2章第7节:“后来,天主……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
[149]这是文字游戏。原文作:“Madam,I’mAdam.And Able was I ere l saw Elba.这两个短句子,从哪头念都一样,中间用“and”相连接。Eva(夏娃)与Elba读音相近,亚当与夏娃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亚伯(Abel)又与Able读音相近,所以可读作:“我是亚当,在见到夏娃之前曾是亚伯。”另一种读法是,由于拿破仑曾说过他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一词,他失败后被流放到厄尔巴(Elba)岛上,同时他又是个阳萎者,把这几种因素揉在一起,将前面的短句重新组合成:Madam,l mad am.(疯了,我疯了。)后面的短句则理解成:“在见到厄尔巴之前,我是不知道不可能一词的。”Able语意双关。既可理解为:“能够做到”,也可理解为:“并非阳萎”。
[150]亲王街的老太婆是《自由人报》的绰号。
[151]“哀哭并咬牙切齿”一语出自《马太福音》第8章第12节。
[152]格雷戈尔?格雷是当时都柏林一美术家。
[158]托?鲍?是托马斯?鲍威尔?奥康纳(见本章注[22])的简称。《星报》是他于一八八八年创办的,他本人主编了两年。
[154]拉尔夫?D?布卢门菲尔德(1864-1948),生在美国的报人,一九0四年成为伦敦《每日快报》编辑。
[155]费利克斯?派亚特(1810-1889),法国的一个社会革命家、新闻记者。一八七一年被卷入巴黎公社起义的漩涡中,后逃往伦敦,为几家报纸撰稿,并主编了几种革命刊物。
[156]克里斯?卡利南是都柏林一记者。
[157]这是文字游戏。利内翰把“Damnclever”(鬼得很)一词的首字互相调换,变成“deve”。
[158]按一九0四年六月九日的《自由人报》报道说,尽管自一九0三年十一月以来,警察当局三令五申,予以禁止,小贩们仍热衷于出售有关凤凰公司暗杀案的明信片和纪念品。记录法官是季审法院中最初在审判时担任记录、以后对提交季审法院的刑事案件负责单独预审者。
[159]当时的爱尔兰总督达德利伯爵(1866-1932)的夫人。
[160]指一九0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刮的一场都柏林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台风。
[161]“老大哥”是帕特里克?泰南的绰号。他是新闻记者,曾于一九0四年创办《爱尔兰“常胜军”及其时代》报,支持民族主义秘密团体“常胜军”。
[162]詹姆斯?怀特赛德(1804-1876),爱尔兰高级律师,以雄辩和为丹尼尔?奥康内尔(1844)以及斯密斯?奥布赖恩(1848)辩护闻名于世。一八六六年成为爱尔兰高等法院院长。
[163]伊萨克?巴特(1813-1879),爱尔兰高级律师,政治家,也是雄辩家,曾为史密斯?奥布赖恩(1848)和芬尼社社员们(1865-1866)进行辩护。
[164]托马斯?奥黑根(1812-1885),爱尔兰高级律师,法律专家,是头一个被委任为爱尔兰大法官(1868-1874,1880-1881)的天主教徒。因在一八八一年通过《爱尔兰土地法案》时,为爱尔兰热烈辩护而名声大噪。
[165]这里,作者是在语音上作文章。冒斯(mouth,嘴)、扫斯(south,南)、泡特(pout,噘嘴)、奥特(out,向外)、少特(shout,呼喊)、芝歇斯(drouth,干旱)均为英语叠韵单词的译音。
[166]参看《(神曲?净界》)第29篇:“我看见两个老人,衣服式样不同,但是在态度上是同样庄重而可敬的。”
[167]“给你太平……的一刻”,原文为意大利语。出自《神曲?地狱》第5篇。
[168]“穿过……幽暗的地方”,原文为意大利语,出自《神曲?地狱》第5篇。
[169]“打着……金光旗”,原文为意大利语,出自《神曲?天堂》第31篇。金光旗是天使加百列赐给古时法兰西王的军旗,金地烈火图案。据认为打着此旗,无往而不胜。
[170]“更加……注视”,原文为意大利语,出自《神曲?天堂》第31篇。
[171]拖姆(tomb,坟墓)、卧姆(womb,子宫)为英语叠韵单词的译音。
[17Z]第三种职业指律师、文人、记者、政论家等著述家;第一二种为神职人员和医务人员。
[173]克劳福想是科克人,这里把他和关于科克腿的阿尔斯特歌谣拉扯在一起。科克(Cork)是双关语,既是地名,又作“”软木”解。该歌谣的大意是:有个荷兰商人抬脚去踢个穷亲戚,却踢到一只小木桶上,把腿弄断了,只得装一条软木假腿,结果跑个不停,使他不得安宁。
[174]亨利?格拉顿(1746-1820),早年为律师。一七七五年进入爱尔兰议会,不久即以卓越的口才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一七八二年迫使英国给予爱尔兰立法独立。
[175]亨利?弗勒德(1732-1791),爱尔兰政治家,有演说天才。他是英国议会和爱尔兰议会议员,曾协助格拉顿迫使英国政府放弃对爱尔兰贸易的种种限制(1779)。
[176]狄靡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希腊政治家,伟大的雄辩家,长期为人撰写状纸。他的演说《金冠辞》被认为是历史上雄辩术的杰作。
[177]埃待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生于都柏林。他善于辞令,一七七四年当选为议会议员,极力主张英国放宽对爱尔兰的经济控制并允许爱尔兰在立法上的独立。
[178]艾尔弗雷德?C?哈姆斯沃思(1865-1922),英国编辑、出版家。他出生在都柏林西边的查佩利佐德。
[179]指美国出版家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他不是哈姆斯沃思的堂弟,而是朋友。这里套用汤姆?泰勒(1817-1880)所写的《我们的美国堂弟》(1858)一戏的剧名。普利策于一八八三年接手《纽约世界报》(参看本章注
[138]),他对报馆人员说,今后要面向鲍厄里(纽约市下曼哈顿区的一个街区。1880年后变成了贫民窟所在地)。
[180]《珀迪?凯利要闻汇编》是都柏林的一份幽默周刊(1832-1834)。《皮尤的遭遇》(1700-约1750)是都柏林最早的一份日报。《斯基勃林之鹰》(约1840-1930)是一份周报,在一九0四年,易名《科克郡之鹰》。
[181]这里套用《马太福音》第6章第34节: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82]爱尔兰义勇军是一七七八年为了防备法军入侵而组织起来的。一七八二年曾支援格拉顿争取爱尔兰议会独立的斗争。
[183]查尔斯?卢卡斯(1713-1771),爱尔兰医生,爱国主义者,经常为《自由人报》撰稿。约翰?菲尔波特?柯伦(1750-1817),爱尔兰律师、政治家。爱尔兰争取自由的重要鼓吹者和拥护者。爱尔兰爱国志士亨利?格拉顿的朋友和同盟者。
[184]指西摩?布什(1853-1922)。他原是高级法庭的爱尔兰律师,后与布卢克爵士夫人姘居。爵士以控告布什犯通奸罪相威胁,故于一九0一年移居英国。一九0四年任英国王室法律顾问。
[185]查尔斯?肯德尔?布什(1767-1843),爱尔兰律师,雄辩家。亨利?格拉顿的支持者。一八二二年任爱尔兰民事法院院长。
[186]这是哈姆莱特王子之父的亡灵对他说的话。亡灵说,自己的兄弟怎样把毒药注入他的耳腔,害死他后娶了王后,见《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
[187]“双背禽兽”暗喻男女交媾(见《奥瑟罗》第1幕第1场)。在《哈姆菜特》第1幕第5场中,亡灵对哈姆莱特王子说,克劳狄斯是个“奸淫的畜生”,而王后只是“外表上装得非常贞淑”。斯蒂芬把亡灵的话理解为:克劳狄斯早在哈姆莱特王在世期间就与王后勾搭成奸。
[188]原文为意大利语。
[189]原文为拉丁文。指惩罚暴行要以命偿命,以牙还牙。见《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至25节。下文中提到的《摩西》,指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一三至一五一六年间所雕的石像。都柏林法院的门廊里也有一座《摩西》石像。
[l90]“我”指斯蒂芬。
[191]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1775-1854)在《艺术哲学》中说:建筑乃是“空间的音乐,犹如冻结的音乐”。
[192]“半神半人的形象”一语出自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之歌》(1789)中的《神圣的形象》。
[193]威廉?马吉尼斯实有其人,为都柏林大学教授,乔伊斯曾受教于他。他赏识乔伊斯的才华,并认为乔伊斯是为了嘲弄拉塞尔才与他接近的。(见马文?马加拉内尔编集的《詹姆斯?乔伊斯杂录》,1962。)
[194]指二十世纪初叶着迷于神秘主义和通神学的一批文人。拉塞尔是一九0四年经海伦娜?勃拉瓦茨基所认可的通神学会都柏林大白屋支部(又名大雅利安支部)的成员。
[195]“乳白色的”和“沉寂的”是拉塞尔本人以及受他影响的年轻诗人(如埃拉?扬)在诗中喜用的词句。
[196]A?E?是拉塞尔的笔名,参看第三章注[lO9]。
[197]海伦娜?佩带罗夫娜?勃拉瓦茨基(1831-1891),俄国文通神学家、著作家,一度嫁给俄国军官勃拉瓦茨基,不久便分手。一八七五年与奥尔科特等人共同建立通神学会。一八七九年赴印度,三年后创办该会杂志《通神学家》,自任主编(1879-1888)。她研究神秘主义和招魂术,多年来足迹遍及亚、欧两洲及美国。晚年在伦敦潜心写作。
[198]美国记者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尼利厄斯?韦安特教授。韦安特曾于一九0二年夏访问拉塞尔,并在《爱尔兰戏剧与剧作家》(1913)一书中,谈及一个不满二十一岁的少年(即指乔伊斯)夜间在街上等着拉塞尔,向他打招呼,并跟他探讨文学艺术问题。接着,少年懊丧地叹气并断然说,A?E?当不成他的救世主。
[199]约翰?弗?泰勒(约1850-1902),爱尔兰记者,并为出席高等法院的律师。
[2O0]指一七七0年创立的三一学院史学会,泰勒是在一九0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这个演说的。该史学会所举行的大学讨论会是爱尔兰乃至大不列颠历史最悠久的。
[201]杰拉尔德?菲茨吉本(1837-1909)于一八七八竿任上诉法庭庭长。他虽然是个爱尔生人,在任国民教育督察时,却试图使爱尔兰英国化。
[202]爱尔兰语及盖尔语,参看第九章注[180]。
[203]蒂摩西(蒂姆为爱称)?迈克尔?希利(1855-1931),爱尔兰政治家,曾当过巴涅尔(见第二章注[81])的助手。然而巴涅尔一失势,他又成为带头将其赶下台的人们中的一个。
[204]乖娃儿指希利。在十九世纪,三四岁以下的男童多着长罩衣。这里是挖苦希利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来谴责巴涅尔所谓“道德败坏”的罪行。
[205]这里套用《启示录》第16章第1节语:“把那七碗天主的愤怒倾泄在地上。”
[206]“让……上升”出自辛白林对预言者所讲的话,见莎士比亚的《辛白林》第5幕第5场。
[207]教父是对早期基督教会领袖的称呼,这里指圣奥古斯丁(354-430)。他曾于三九六至四三0年任罗马帝国非洲领地希波(即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主教,是当时西方教会最杰出的思想家。
[208]“我受到……腐蚀”,出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7卷。下面的句子是:“因此,倘若把事物中美好的部分统统剥夺掉,它们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只要它们存在,它们就是美好的。因此,凡是存在的东西,就都是美好的。”
[209]古代由奴隶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
[210]这里表现出乔伊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把埃及比作英国,把爱尔兰人比作被其奴役的犹太人。
[211]据《出埃及记》第1至4章,埃及王曾下令将希伯来人的新生男婴统统扔进尼罗河。有一对夫妇用蒲草编了只篮子,将自己的男婴放进去,然后把篮子藏在河边芦苇丛里。娃娃被埃及王的女儿所收养。公主说:“我从水里把这孩子拉上来,就叫他摩西吧。”在希伯来语中,“摩西”与“拉出”,发音相近。摩西长大后,被推崇为犹太人的领袖,成为该民族的偶像般的人物。
[212]参看《出埃及记》第2章第7至10节。当埃及公主打开篮子,发现里面的男婴后,藏在暗处的婴儿的姐姐走出来,问她:“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女人来做他的奶妈?”公主说:“好啊。”于是,那个女孩就把婴儿的生母找来。公主托她把娃娃抚养大。孩子长大后,公主才正式收养他作自己的儿子。
[213]据《出埃及记》第2章第11至12节,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希伯来同胞,便下手杀了那埃及人,把尸首埋在沙里。
[214] 《出埃及记》第34章第29节有“当摩西带着十诫的法版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之句,而圣哲罗姆(347-419或420)把《圣经?旧约》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时,却将“发光”误译为“长了犄角”。结果以讹传讹,米开朗琪罗(1396-1472)的雕塑《摩西》以及出自大多数中世纪画家之手的摩西的造型,均长着一对犄角。
[215]十九世纪末叶西方研究《圣经》的学者一般认为,犹太人的一神教起源于住在西奈山附近、相信这座神圣的山上有位雅赫维神(意即“万有之主”)的那些部族。摩西与其说是一个人物,毋宁说是这些部族的象征性代表。
[216]伊希斯是古埃及主要女神之一,司众生之事,能起死回生。俄赛里斯是古埃及主神之一,他统治死者。何露斯是古埃及宗教所奉之神,其形象似隼,太阳和月亮是他的双目。阿蒙一瑞是古埃及的国神,号称众神之王。其像如人,有时生有公羊头,与妻子穆特和养子柯恩苏共为底比斯的三神。
[217]摩西对以色列人民说:“要牢记这一天;这一天你们离开了埃及――你们被奴役过的地方。”见《出埃及记》第13章第3节。
[218]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白天,上主走在他们前面,用云柱指示方向……”参看《出埃及记》第13章第21节。
[219]参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16至22节。
[220]“他”指摩西。据《申命记》第34章,上主让摩西从摩押平原的比斯迦山峰上俯瞰迦南(巴斯斯坦及相毗连的腓尼基一带的古称)全境,并对他说,这就是应许给他后代的土地,“但是你不能进去。”摩西死在摩押地,终生未能进入迦南。
[221]“预期到会致死的-吐血症”,原文作expectorated-demise。这是文字游戏。“Ex-pectorat”作“吐痰、吐血”解,“demise”作“死亡”解。“Expectorated”一词,语意双关,如果去掉中间的“ora”三个字母,就成了“expected”,作“预期”解。
[222]“随风飘去”一词出自英国颓废派诗人欧内斯特?道森(1867-1900)的题名《在好西纳拉的魔力下,我不再是过去的自己》(1896)的诗。
[223]“位于马勒麻斯特……嗓音里”影射奥康内尔的活动。奥康内尔曾以爱尔兰人民的保民官(古罗马各种军事和民政官员的总称。其职责是保护人民,反对行政长官发布的命令)自况。这里还显然把聚集的群众比作古代诸王的军队。“人们隐蔽在他的嗓音里”指的是他作为爱尔兰律师,能够把法庭当成民族主义的讲坛,以表达人民的心声。奥康内99lib?尔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一系列大规模群众集会,其中声势最浩大的是一八四三年在马勒麻斯特(都柏林西南35英里处的山寨围垣)和塔拉(都柏林西北21英里处的一应矮山,属米斯郡,系爱尔兰古都所在地,有王宫遗址)举行的两次集会,号召爱尔兰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柱廊原指希腊思想家、斯多葛哲学派创立者、季蒂昂的芝诺(约公元前335-约前263)讲学的地方(斯多阿?波伊奇列,意即“彩色的柱廊”)。此外则指聚在一起听奥康内尔讲演的数十万乃至一百万群众。
[224]阿卡沙是神秘学名词。指关于太初以来人间一切事件、活动、思想和感觉的形象记录。据说是印在阿卡沙(即人类所感觉不到的一种星光――液态以太)上。照神秘学的说法,只有少数鬼魂附体者才能感受得到阿卡沙秘录。
[225]从“随风飘去”到“我有钱”,是斯蒂芬的思想活动。“爱戴并赞美他”,套用《辛白林》第5幕第5场中辛白林对预言者所说的“让我们赞美神明”(下面紧接本章注[206]中所引的“让香烟袅袅上升”)。最后的“我有钱”,指当天斯蒂芬领了薪金。
[226]法国式的恭维――指言而无信。
[227]穆尼是位于《自由人报》社以东的一家酒馆。与斯蒂芬原约好中午跟穆利根、海恩斯在那里相聚的“船记”酒馆,相隔仅四个门。
[228]这是《麦克白》第5幕第8场中,篡夺了王位的麦克白与苏格兰贵族麦克德夫决斗时,麦克白所说的话。
[229]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埃涅阿斯记》第2卷。在迦太基女王狄多的央求下,埃涅阿斯对她诉说攻陷伊利昂城时的情景。
[230]“多风的特洛伊”一语出自丁尼生的《尤利西斯》(1842)一诗。
[231]指特洛伊城陷落后,希腊人成了地中海的主人,然而在一九0四年,希腊已沦为弱国。
[232]语出自爱尔生女作家西德尼?摩根夫人(1780-1859)。
[233]维斯太是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灶神。祭司长从七至十岁的童贞女中选六名,让她们主持对该神的国祭,叫作维斯太贞女。一经选中须供职三十年,其间必须坚守童贞。期满后方可嫁人。此词转义为重贞女或尼姑。
[234]、[235]凡巴利小巷和黑坑都位于都柏林的自由区(参看第三章注[16])。
[236]这里,斯蒂芬在回忆自己夜间路遇妓女的经历。
[237]这里模仿《创世记》第1章第3节中的语调。原句是:天主命令,要有光,就有了光。
[238]典出自耶稣所讲的十个处女挑着油灯去迎接新郎的比喻。其中五个聪明的另外还带了油,就得以和新郎一起进去赴宴。另外五个笨的因没带够油,未能进去赴宴。见《马太福音》第25章。
[239]第三章第106页第10行提到一位来自自由区的弗萝伦斯?麦凯布。
[240]耶稣受难会是一七三七年由意大利的保罗?弗朗西斯科?丹内(1697-1775)创建的天主教修会。
[241]吉尼斯啤酒公司酿造的双X牌啤酒是供内销的,三X牌则是供出口的。
[242]《爱尔兰天主教报》和《都柏林小报》都是每逢星期四出版的周报。
[243]《基尔肯尼民众报》是每逢星期六在基尔肯尼出版的周报。
[244]钥匙(keys)与凯斯(Keyes)谐音。
[245]原文作:K?M?A?为kiss my arse的首字。这是门徒们对魔鬼表示恭顺的方式。
[246]原文作:K?M?R?I?A.为kiss my royal Irish arse的首字。
[247]原文为拉丁文。法律用语,指欠债者无财物可变卖抵债或作抵押。按刚才在办公室里,杰?杰?奥莫洛伊曾向克劳福德开口借过钱。
[248]达格尔是都柏林以南十二英里处的一道风光绮丽的峡谷。
[249]拉思曼斯是都柏林的准自治市。蓝色拱顶指一八五0年建立的圣母堂,距纳尔进纪念圆柱两英里。
[250]指距纳尔逊纪念圆柱半英里多的方济各教堂。由于天主教信仰遭到英国统治者的压制,方济各会的神父们于一六一八年在罗斯玛丽巷建立了一应“地下”教堂。教徒们望弥撒时,假装到该巷的一家名叫亚当与夏娃的客栈去。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人们至今仍把附近的一座圣方济各教堂称作亚当与夏娃教堂。
[251]圣劳伦斯?奥图尔(113Z-1180),爱尔兰的主保圣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座教堂在纪念圆柱附近。
[252]奸夫指纳尔逊。一七九七年在和西班牙舰队进行海战时,他右臂受伤,后截肢。一七九八年,他与英国驻那不靳斯公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1730-1803)之妻艾玛(约1765-1815)发生崦凉叵担此事成为当时英国政界一大丑闻。
[253]见《马太福音》第13章第3至9节中耶稣对群众所讲撒种的寓言。“有些种子落在好土壤里,长大结实,收成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也有三十倍的。”这里把吐李子核儿和撒种子联系在一起了。
[254]智者派指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古希腊的一些演说家、作家和教师。后来此间衍成为“强词夺理的诡辩者”的替代语。
[255]潘奈洛佩是伊大嘉国王奥德修之妻,以贞节著称。
[256]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5),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创始人。他抨击社会上的蠢事和不平,并号召人们克己自制。此派人生活刻苦,衣食简朴。
[257]高尔吉亚(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27-约前399),希腊智者派和雄辩家。
[258]阿凯人指希腊人。古希腊有几个地区叫作阿凯斯(包括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部地区)。
[259]潘奈洛佩?里奇(约1562-1607),英国贵妇人。一五八一年嫁给里奇勋爵,后离婚,改嫁蒙乔伊勋爵。宫廷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554-1586)曾与她相爱,并为她写了一组十四行诗《爱星者和星星》(1582)。“星”的就是她。她为人风流,与奥德修那个从一而终的妻子形成对照,正如她的姓里奇(Rich,意即“阔绰”)与“贫穷”(poor)形成对照。
[260]拉思法纳姆是都柏林郊外一村庄,距都柏林中央区以南三英里。
[261]唐尼布鲁克是距纪念圆柱东南二英里的村庄。
[262]原文作sophomore,即大学二年级学生。
[263]原文为拉丁文。语出自维吉尔的《牧歌》。
[264]指摩西从比斯迦山峰上俯瞰迦南一事,参看本章注[220]。
[265]耶稣喜欢用寓言来教导门徒,参看本章注[253]。照基督教的说法,李子象征忠诚与独立。
[266]霍雷肖是纳尔逊的教名。
[267]约翰?格雷爵士(参看第六章注[49])的雕像坐落在街心岛上。
[268]弗萝是弗萝伦斯的爱称。
第八章 1
菠萝味硬糖果,蜜饯柠檬,黄油糖块。一个被糖弄得黏糊糊的姑娘正在为基督教兄弟会的在俗修士[1]一满杓一满杓地舀着奶油。学校里要举行什么集会吧。让学童享一次口福吧,可是对他们的肠胃并不好。国王陛下御用[2]菱形糖果及糖衣果仁制造厂。上帝拯救我们的……[3]坐在宝座上,把红色的枣味胶糖嘬到发白为止。
一个神色阴郁的基督教青年会[4]的小伙子,站在格雷厄姆·莱蒙的店铺溢出来的温馨、芳香的水蒸气里,留心观察着过往行人,把一张传单塞到布卢姆先生手里。
推心置腹的谈话。
布卢……指的是我吗?不是。
羔羊的血。[5]
他边读边迈着缓慢的步子朝河边走去。你得到拯救了吗?在羔羊的血里洗涤了一切罪愆。上主要求以血做牺牲。分娩,处女膜,殉教,战争,被活埋在房基下者,献身,肾脏的燔祭,德鲁伊特的祭台。[6]。以利亚来了。[7]锡安教会的复兴者约翰·亚历山大·道维博士[8]来了。
来了!来了!!来啦!!!
大家衷心欢迎。
这行当挺划算。去年,托里和亚历山大[9]来了。一夫多妻主义。他的妻子会阻拦的。我是在哪儿见到伯明翰某商行那个夜光十字架的广告来看?我们的救世主。半夜醒来,瞥见他悬挂在墙上。佩珀显灵的手法。[10]把铁钉扎了进去。[11]
那准是用磷做的。比方说,倘若你留下一段鳕鱼,就能看见上面泛起一片蓝糊糊的银光。那天夜里我下楼到厨房的食橱去。那里弥漫着各种气味,一打开橱门就冲过来,可不好闻。她想要吃什么来看?乌拉加葡萄干[12]。她在思念西班牙。那是鲁迪出生以前的事。那种蓝糊糊、发绿的玩艺儿就是磷光。对大脑非常有益。
他从巴特勒这座纪念碑房[13]的拐角处眺望巴切勒步道。迪达勒斯的闺女还呆在狄龙的拍卖行外面呢。准是出售什么旧家具来了。她那双眼睛跟她父亲的一模一样,所以一下子就认得出来。她闲荡着,等候父亲出来。母亲一死,一个家必然就不成其为家了。他有十五个孩子,几乎每年生一个。这就是他们的教义 [14],否则神父就不让那可怜的女人忏悔,更不给她赦罪。生养并繁殖吧[15]。你可曾听到过如此荒唐的想法?连家带产都吃个精光。神父本人反正用不着养家糊口。他们享受丰足的生活[16]。神父的酒窖和食品库。我倒是想看看他们在赎罪日[17]是否严格遵守绝食的规定。十字面包[18]。先吃上一顿饭,再着补一道茶点,免得晕倒在祭坛前。你可以去问问一位神父所雇用的管家婆。绝对打听不出来的。正如从她的主人那里讨不到英镑、先令或便士。他独自过得蛮富裕,从来不请客。对旁人一毛不拔。连家里的水都看得很严。你得自带黄油抹面包。[19]神父大人,闭上你的嘴。
天哪,那个可怜的小妞儿,衣服破破烂烂的。她看上去好像营养也不良。成天是土豆和人造黄油,人造黄油和土豆。[20]当他们感觉到的时候,就已来不及了。布丁好坏,一尝便知。这样,身体会垮的。
当他来到奥康内尔桥头时,一大团烟像羽毛般地从栏杆处袅袅升起。那是啤酒厂的一艘驳船,载有供出口的烈性黑啤酒,正驶向英国。我听说海风会使啤酒变酸的。哪一天我要是能通过汉考克弄到一张参观券就好啦,去看看那家啤酒公司[21]该多么有趣。它本身就是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排列着大桶大桶的黑啤酒,一派宏伟景象。老鼠也蹿了进来,把肚皮喝得胀鼓鼓的,大得宛若一条柯利狗[22],漂在酒面上。啤酒喝得烂醉如泥。一直喝到像个基督徒那样[23]呕吐出来。想想看,让我们喝这玩艺儿!老鼠,大桶。喏,倘若我们晓得这一切,可就……
他朝下面望去,瞥见几只海鸥使劲拍着翅膀,在萧瑟的码头岸壁间兜着圈子。外面正闹着天气。倘若我纵身跳下去,又将会怎样?吕便·杰的儿子想必就曾灌进一肚子那样的污水。多给了一先令八便士[24]。嘻嘻嘻。西蒙·迪达勒斯的话说得就是这样俏皮。他也确实会讲故事。
海鸥兜着圈子,越飞越低,在寻找猎物。等一等。
他把揉成一团的纸[25]朝海鸥群中掷去。以利亚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前来。海鸥们根本不予理睬。受冷落的纸团落在汹涌浪涛的尾波上,沿着桥墩漂向下游。它们才不是什么大笨蛋呢。有一天我从爱琳王号[26]上也扔了块陈旧的点心,海鸥竟在船后五十码的尾流中把它叼住了。它们鼓翼兜着圈子飞翔,就这样凭着智慧生存下来。
海鸥啊饿得发慌,
飞翔在沉滞的水上。
诗人就这样合辙押韵。莎士比亚却不用韵体。他写的是无韵诗。语言流畅,思想宏伟。
哈姆莱特,我是你父亲的灵魂,
注定在地上游行相当一个时期。[27]
“两个苹果一便士!两个一便士!”
他的视线扫过排列在货摊上那些光溜溜的苹果。这个季节嘛,准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果皮发亮,想必是用抹布或手绢擦的。
且慢。还有那些可怜的鸟儿哪。
他又停下脚步来,花一便士从卖苹果的老妪手里买了两块班伯里[28]点心,掰开那酥脆的糕饼,一块块地扔进利菲河。瞧见了吗?起初是两只,紧接着所有的海鸥都悄悄地从高处朝猎物猛扑过去,全吃光了。一丁点儿也没剩。他意识到它们的贪婪和诡诈,就将手上沾的点心渣儿掸下去。它们未曾指望会有这样的口福。吗哪[29]。所有的海鸟——海鸥也罢,海鹅也罢,都靠食鱼而生,连肉都带鱼腥味了。安娜·利菲[30]的白天鹅有时顺流而下,游到这里,就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炫耀一番。人各有所好。也不晓得天鹅的肉是什么滋味儿。鲁滨孙·克鲁索只得靠它们的肉为生呢。[31]
它们有气无力地拍翅兜着圈子。我再也不去给你们啦。一便士的就蛮够啦。你们本该好好地向我道声谢的,可是连“呱”的一声都没叫。而且它们还传染口蹄疫。倘若净用栗子粉来喂火鸡,肉也会变成栗子味的。吃猪就像猪。然而咸水鱼为什么不咸呢?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扫视着河面,想寻求个答案。只见一般划艇停泊在形似糖浆的汹涌浪涛上,懒洋洋地摇晃着它那灰胶纸拍板。
吉诺批发店[32]
11
裤子
那倒是个好主意。也不晓得吉诺向市政府当局交租金不。你怎么可能真正拥有水呢?它不断地流,随时都变动着,我们在流逝的人生中追溯着它的轨迹。因为生命是流动的。任何场所统统适合登广告。每一应公用厕所都有治淋病的庸医的招贴。而今完全看不到了。严加保密。亨利·弗兰克斯大夫[33]。跟舞蹈师傅马金尼[34]的自我广告一样,一分钱也不用花。要么托人去贴,要么趁着深更半夜悄悄跑进去,借解钮扣的当儿,自己把它贴上。麻利得就像夜晚躲债的。这地方再合适不过了。“禁止张贴广告”、“邮寄一百零十粒药丸”。有人服下去,心里火烧火燎的。
倘若他……
哦!
呃?
不……不。
不,不。我不相信。他该不至于吧?
不,不。
布卢姆先生抬起神情困惑的眼睛,向前踱去。不要再想这个了。一点钟过了。港务总局的报时球已经降下来了。邓辛克[35]标准时间。罗伯特·鲍尔爵士 [36]的那本小书饶有趣味。视差。我始终也没弄清楚这个词的意思。那儿有个神父,可以去问问他。这词儿是希腊文:平行,视差。我告诉她什么叫作“轮回” 之前,她管它叫“遇见了他尖头胶皮管”[37]。哦,别转文啦!
布卢姆先生想起“哦,别转文啦!”这句话,朝着港务总居的两扇窗户泛出微笑。她的话毕竟是对的。用夸张的字眼来表达平凡的事物,只不过是取其音调而已。她讲话并不俏皮,有时候还挺粗鲁。我只是心里想想的话,她却脱口捅了出来。但是倒也不尽然。她常说,本·多拉德有着一副下贱的桶音[38]。他那两条腿款跟桶一样,他仿佛在往桶里唱歌。喏,这话不是说得蛮俏皮吗!他们通常管他叫“大本钟”[39]。远不如称他作“下贱的桶音”来得俏皮。他们饭量大如信天翁。一头牛的脊肉,一顿就吃光。他喝上等巴斯啤酒的本事也不含糊。是只啤酒桶。怎么样?俏皮话说得都很贴切吧。
一排穿白罩褂、胸前背后挂着广告牌的人正沿着明沟慢慢地朝他走来。每个人都在广告牌上斜系着一条猩红的饰带。大甩卖。他们正像今天早晨那位神父一样:我们犯了罪。我们受了苦[40]。他读着分别写在他们那五顶白色高帽上的红字母:H·E·L·Y·’S。威兹德姆。希利商店。[41]帽子上写着Y的男子放慢脚步,从胸前的广告牌下面取出一大块面包塞到嘴里,边走边狼吞虎咽着。我们每天在主食上花三先令,沿着明沟,穿街走巷。靠面包和稀稀的麦片粥,勉强把皮和骨连在一起。他们不是博伊——不,而是默·格拉德[42]的伙计。反正招徕不了多少顾客。我曾向他建议,让两个美女坐在一辆透明的陈列车里写信,并摆上笔记本、信封和吸墨纸。我敢断定,那准会轰动。美女写字,马上就会引人注目。人人都渴望知道她在写什么。要是你站在那里望空发楞,就会有二十个人围上来。谁都想参与别人的事,女人也是如此。好奇心。盐柱[43]。希利不肯接受这个主意,因为这不是他首先想出来的。找还建议做个墨水瓶的广告,用黑色赛璐珞充当流出来的墨水渍。他在广告方面的想法就像在讣告栏底下刊登李树商标肉罐头,冷肉部。你不能小看它们。什么?敝店的信封。——喂,琼斯,你到哪儿去呀?——鲁滨孙,我不能耽误,得赶紧去买唯一靠得住的坎塞尔牌消字灵,戴姆街八十五号希利商店出售的。幸而我不再在那儿干了。去那些修道院收帐可真是件苦差事。特兰奎拉女修道院[44]。那儿有个漂亮的修女,一张脸长得可真俊。小小的头上包着尖头巾,非常合适。修女?修女?从她的眼神来看,我敢说她曾失过恋。跟那种女人是很难讨价还价的。那天早晨她正在祈祷的时候,我打扰了她。但是她好像蛮乐意跟外界接触。她说,这是我们的大日子。迦密山[45]的圣母节。名字也挺甜,像糖蜜[46]。她认识我,从她那副样子也看得出,她认识我。要是她结了婚,就不会这样了。我估计修女们确实缺钱。尽管如此,不论煎什么,她们仍旧用上等黄油。她们可不用猪油。吃大油吃得我直烧心。她们喜欢里里外外抹黄油。摩莉掀起头巾,在品尝黄油。修女?她叫帕特·克拉费伊,是当铺的女儿。人们说,铁蒺藜就是一位尼姑发明的[47]。
当那个帽子上写着带有撇号的S字[48]的人拖着深重的脚步走过去后,他才横穿过韦斯特莫兰街。罗弗自行车铺。今天举行赛车会[49]。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来看?是菲尔·吉利根[50]去世的那一年。我们住在伦巴德西街。且慢,当时我正在汤姆[51]的店铺来着。我们结婚那一年,我在威兹德姆·希利的店里找到了工作。六年。他是十年前——九四年[52]死的。对,就是阿诺特公司着大火的那一年。维尔·狄龙正任市长[53]。格伦克里的午餐会 [54]。市参议员罗伯特·奥赖利在比赛开始前,将葡萄酒全倒进汤里。吧唧吧唧替内在的参议员把它舔干净[55]。简直听不清乐队在演奏什么。主啊,所赐万惠,我等……[56]那时候,米莉还是个小娃娃哩。摩莉身穿那件钉着盘花饰扣的灰象皮色衣服。那是男裁缝的手艺,钉了包扣。她不喜欢这身衣服,因为她头一回穿它去参加合唱队在糖锥山[57]举行的野餐会那一天,我把脚脖子扭伤了。就好像该怪它似的。老古德温的大礼帽仿佛是用什么黏糊糊的东西修补过的。那也是给苍蝇开的野餐会哩。她从未穿过剪裁这么得体的衣服。不论肩膀还是臀部,都像戴手套一样,刚好合身。那阵子她的体态开始丰腴了。当天我们吃的是兔肉馅饼。大家都追着她看。
幸福啊。当时我们可比现在幸福。舒适的小房间,四周糊着红色墙纸。是在多克雷尔那家店[58]里买的,每打一先令九便士。给米莉洗澡的那个晚上,我买了一块美国香皂,接骨木花的。澡水散发出馨香的气味。她浑身涂满肥皂,真逗。身材也蛮好。如今她正干着照相这一行。我那可怜的爹告诉我,他曾搞过一间银板照相的暗室[59]。这也是一种祖传的兴趣吧。
他沿着人行道的边石走去。
生命的长河[60]。那个活像是神父的家伙姓什么来着?每逢路过的时候,他总是斜眼望着我们家。视力不佳,女人。曾在圣凯文步道的西特伦[61]家住过一阵子。姓彭什么的。是彭迪尼斯吗?近来我的记性简直。彭……?当然喽,那是多年以前的事啦。也许是电车的噪音闹的。哦,要是连每天见面的排字房老领班姓什么都记不起来的话[62]。
巴特尔·达西[63]是当时开始出名的男高音歌手。排练后,总送她回家。他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用发蜡把胡子捻得挺拔。他教会了她《南方刮来的风》这首歌。
风刮得很猛的那个晚上,我去接她。古德温的演奏会刚在市长官邸的餐厅或橡木室里举行完毕。分会正在那里为彩票的事开着碰头会[64]。他和我跟在后面走。我手里拿着她的乐谱,其中一张被刮得贴在高中校舍的栏杆上。幸亏没刮跑。这种事会破坏她整个儿晚上的情绪。古德温教授跟她相互挽着臂走在前面。可怜的老酒鬼摇摇晃晃,脚步蹒跚。这是他的告别演奏会了,肯定是最后一次在任何舞台上露面。也许几个月,也许是永远地[65]。我还记得她冲着风畅笑,竖起挡风雪的领子。记得吧?在哈考特街角上,一阵狂风。呜呜呜!她的裙子整个儿被掀起,她那圆筒形皮毛围巾把老古德温勒得几乎窒息而死。她被风刮得涨红了脸。记得回家后,我把火捅旺,替她煎了几片羊腿肉当晚餐,并浇上她爱吃的酸辣酱。还有加了糖和香料、烫热了的甘蔗酒。从壁炉那儿可以瞥见她在卧室里正解开紧身褡的金属卡子。雪白的。
她的紧身褡嗖的一声轻飘飘地落在床上。总是带着她的体温。她一向喜欢松开一切束缚。她在那儿坐到将近两点钟,一根根地摘下发卡。米莉严严实实地裹在小床里。幸福啊,幸福,就在那个夜晚……
“哦,布卢姆先生,你好吗?”
“哦,你好吗,布林太太[66]?”
“抱怨也是白搭。摩莉近来怎么样?我好久没见着她啦。”
“精神抖擞,”布卢姆先生快活地说,“喏,知道吗,米莉在穆林加尔找到工作啦。”
“离开家啦?可真了不起!”
“可不是嘛,在一家照相馆里干活儿。像火场一样忙得团团转。您府上的孩子们好吗?”
“个个都有一张吃饭的嘴,”布林太太说。
她究竟有多少儿女呢?眼下倒不像是在身怀六甲。
“你戴着孝哪。难道是……?”
“没有,”布卢姆先生说,“我刚刚参加了一场丧礼。”
可以想象,今天一整天都会不断有人问起,谁死啦?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反正躲也躲不掉。
“嗳呀妈呀!”布林太太说,“我希望总不是什么近亲。”
倒也不妨让她表表同情。
“姓迪格纳穆的,”布卢姆先生说,“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死得十分突然,可怜的人哪。我相信得的是心脏病。葬礼是今天早晨举行的。”
你的葬礼在明天,
当你穿过裸麦田[67]。
嗨唷嗬,咿呀嗨,
嗨唷嗬……
“老朋友死了真令人伤心,”布林太太说,她那女性的眼睛里露出悲怆的神色。
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吧。还是适可而止。轻轻地问候一声她老公吧。
“你先生——当家的好吗?”
布林太太抬起她那双大眼睛。她的眼神倒还没失去往日的光泽。
“哦。可别提他啦!”她说,“他这个人哪,连响尾蛇都会被他吓倒的。眼下他在餐馆里拿着法律书正在查找着诽谤罪的条例哪。我这条命早晚会送在他手里。等一等,我给你看个东西。”
一股热腾腾的仿甲鱼汤蒸气同刚烤好的酥皮果酱馅饼和果酱布丁卷的热气从哈里森饭馆里直往外冒。浓郁的午餐气味刺激着布卢姆先生的胃口。为了做美味的油酥点心,就需要黄油、上等面粉和德梅拉拉沙糖[68]。要么就和滚烫的红茶一道吃。气味或许是这个妇女身上散发出来的吧?一个赤脚的流浪儿站在格子窗跟前,嗅着那一股股香味。借此来缓和一下饥饿的煎熬。这究竟是快乐还是痛苦呢?廉价午餐。刀叉都锁在桌上[69]。
她打开薄皮制成的手提包。帽子上的饰针:对这玩艺儿得当心点儿——在电车里可别戳着什么人的眼睛。乱找一气。敞着口儿。钱币。请自己拿一枚吧。她们要是丢了六便士,那可就麻烦啦。惊天动地。丈夫吵吵嚷嚷:“星期一我给你的十先令哪儿去啦?难道你在养活你弟弟一家人吗?脏手绢。药瓶。刚掉下去的是喉咙片。这个女人要干什么?……
“准是升起了新月,”她说,”一到这时候老毛病就犯啦。你猜他昨儿晚上干什么来着?”
她不再用手翻找了。她惊愕地睁大了一双眼睛盯着他,十分惊愕,可还露着笑意。
“怎么啦?”布卢姆先生问。
让她说吧。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我相信你的话,相信我吧。
“夜里,他把我叫醒啦,”她说,“他做了个梦,一场噩梦。”
消化不良呗。
“他说,黑桃幺[70]走上楼梯来啦。”
“黑桃幺!”布卢姆先生说。
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明信片。
“念念看,”她说,“他今天早晨接到的。”
“这是什么?”布卢姆先生边接过明信片,边说,“万事休矣。”
“万事休矣:完蛋[71],”她说,“有人在捉弄他。不论是谁干的,真是太缺德啦。”
“确实是这样,”布卢姆先生说。
她把明信片收回去,叹了口气。
“他这会子就要到门顿先生的事务所去。他说他要起诉,要求赔偿一万镑。”
她把明信片叠好,放回她那凌乱的手提包,啪的一声扣上金属卡口。
两年前她穿的也是这件蓝哔叽衣服,料子已经褪色了。从前它可风光过。耳朵上有一小绺蓬乱的头发。还有那顶式样俗气的无檐女帽上头还缀了三颗古色古香的葡萄珠,这才勉强戴得出去。一位寒酸的淑女。从前她可讲究穿戴啦。如今嘴边已经出现了皱纹。才比摩莉大上一两岁。
那个女人从她身旁走过去的时候,曾用怎样的眼神瞅她!残酷啊。不公正的女性[72]。
他依然盯着她,竭力不把心头的不悦形之于色。仿甲鱼汤、牛尾汤、咖哩鸡肉汤的气味冲鼻。我也饿了。她那衣服的贴边上还沾着点心屑呢,腮帮子上也巴着糖渣子。填满了各色果品馅儿的大黄酥皮饼[73]。那时候她叫乔西·鲍威尔。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海豚仓的卢克·多伊尔家玩过哑剧字谜[74]。万事休矣,完蛋。
换个话题吧。
“最近你见着博福伊太太了吗?”布卢姆先生问。
“米娜·普里福伊吗?”她说。
我脑子里想的是非利普·博福伊。戏迷俱乐部。马查姆经常想起那一妙举[75]。我拉没拉那链儿呢?[76]拉了,那是最后一个动作。
“是的。”
“我刚才顺路去探望了她一下,看看她是不是已分娩了。眼下她住进了霍利斯街的妇产医院。是霍恩大夫[72]让她住院的。她已足足折腾了三天。”
“哦,”布卢姆先生说,“我听了很难过。”
“可不是嘛,”布林太太说,“家里还有一大帮娃娃哪。护士告诉我,是不常见的难产。”
“哎呀,”布卢姆先生说。
他的目光表露着深切的怜悯,全神贯注地倾听她这个消息,同情地砸着舌头:“啧!啧!”
“我听了很难过,”他说,“怪可怜的!三天啦!够她受的!”
布林太太点了点头。
“从星期二起,阵痛就开始啦……”
布卢姆先生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尖儿,提醒她说:
“当心!让这个人过去吧。”
一个瘦骨嶙峋的人从河边沿着人行道的边石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隔着系有沉甸甸的带子的单片眼镜,茫然地凝视着阳光。一顶小帽像头巾一般紧紧地箍在他头上。迈一步,夹在腋下的那件折叠起来的风衣、拐杖和雨伞就晃荡一阵。
“瞧他,”布卢姆先生说,“总是在街灯外侧走路。瞧啊!”
“我可以问一下他是谁吗?”布林太太说,“他是个半疯儿吗?”
“他名叫卡什尔·博伊尔·奥康内尔·菲茨莫里斯·蒂斯代尔·法雷尔[78],”布卢姆先生笑眯眯地说,“瞧啊!”
“这串儿够长的啦,”她说,“丹尼斯迟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突然闭上了嘴。
“他出来啦,”她说,“我得跟着他走。再见吧。请代我向摩莉问候一声,好吗?”
“好的,”布卢姆先生说。
他望着她一路躲闪着行人,走到店铺前面去。丹尼斯·布林身穿紧巴巴的长礼服,脚登蓝色帆布鞋,腋下紧紧地夹着两部沉甸甸的大书,从哈里森饭馆里抱着脚步走了出来。像往常一样,仿佛是一阵风把他从海湾刮来的似的。他听任她赶上自己,并没有感到意外,一路朝她掀起他那脏巴兮兮的灰胡子,摆动着皮肉松弛的下巴,热切地说着什么。
疯狂[79]。完全疯啦。
布卢姆先生继续轻松愉快地走去。瞥见前面阳光下那顶像头巾一般紧紧地箍在头上的小帽,还有那大摇大摆地晃荡着的拐杖、雨伞和风衣。瞧瞧他!又离开了人行道。这也是在世上鬼混的一种方式。还有另一个披头散发、衣衫槛褛的老疯子,到处闲荡。如果跟这种人一道过日子,必然够呛。
万事休矣,完蛋。那准是阿尔夫·柏根或里奇·古尔丁干的。毫无疑问,是在苏格兰屋[80]开着玩笑写的。他正前往门顿的事务所。一路用那双牡蛎般的眼睛瞪着明信片的那副样子,足以让众神人饱眼福。
他从爱尔兰时报[81]社前走过。那儿兴许还放着其他应征者的回信哩。我倒巴不得统统给答复了。这制度倒是替罪犯大开方便之门:暗码。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那边那个戴眼镜的职员并不认识我。啊,就把他们先撂在那儿,慢慢儿来吧。光是把那四十四封信测览一遍就够费事的了。招聘一名精干的女打字员,协助一位先生从事文字工作。找曾管你叫淘气鬼,因为我不喜欢那另一个世界。请告诉我它的含意。请告诉我,你太太使用哪一种香水[82]。告诉我世界是谁创造的。她们就像这样劈头盖脑地向你提出各种问题。另外一个叫莉齐·特威格[83],说是,我的文学作品有幸受到著名诗人A·E·(乔·拉塞尔先生)的赞赏。她边呷着浑浊的茶,边翻看一本诗集,连梳理头发的工夫都没有。
这家报纸登小广告赛过任何一家。如今扩大到各郡。聘请厨师兼总管家,一级烹调,并有女仆打下手。征聘性格活泼的酒柜侍者。今有品行端正的女青年(罗马天主教徒),愿在水果店或猪肉铺觅职。那份报纸是詹姆斯·卡莱尔[84]创办的,百分之六点五的股息。买科茨公司的股票大赚了一笔。一步一步地来。老奸巨滑的苏格兰守财奴。净写一些溜须拍马的报道。我们这位宽厚而深孚众望的总督夫人啦。如今,他连《爱尔兰狞猎报》[85]也给买下来了。蒙卡什尔夫人产后已完全康复,昨日率领医院俱乐部的一批猎犬骑马前往拉思奥斯参加放猎大会[86]。不能食用的狐狸[87]。也有专为果腹而狞猎的。恐怖感能使猎物的肉变得松软多汁。她的骑法就跟男子汉一样,叉开腿跨在马背上。这是一位能够拔山扛鼎的女狞猎家。侧鞍也罢,后鞍也罢,她一概不骑,乔可决不要[88]!集合时她首先赶了来。及至杀死猎物时,她也亲临现场。有些女骑手简直健壮得像母种马一样。她们在马房周围大摇大摆地转悠。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一杯不兑水的白兰地一饮而尽。今天早晨呆在格罗夫纳饭店前的那个女人嗖的一下就上了马车。嘘——嘘。她敢骑在马上跨过一道石墙或有着五根横木的障碍物[89]。那个瘪鼻子的电车司机想必是故意使的坏。[90]她究竟长得像谁呢?对啦!像是曾经在谢尔本饭店把自己的旧罩衫和黑色衬衣卖给我的那位米莉亚姆·丹德拉德太太[91]。离了婚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我摆弄它们时,她毫不理会。大概把我看成她的衣服架子了。我是在总督的宴会上遇到她的。公园护林人斯塔布新[92]把我和《快报》[93]的维兰带进去参加了。吃的是那些达官贵人的残羹剩汤。一顿有肉食的茶点。我把蛋黄酱当炸乳蛋羹,浇在李子布丁上了。打那以后,她一定耳鸣了好几个星期。我恨不得当她的公牛。她是个天生的花魁。谢天谢地,看孩子可别找她。
可怜的普里福伊太太!丈夫是个循道公会[94]教徒。他说的虽然是疯话,其中却包含着哲理[95]。中午吃教育奶场[96]所生产的番红花甜面包,喝牛奶和汽水。基督教青年会。边吃边看着记秒表,每分钟嚼三十二下,然而他那上细下圆的羊排状络腮胡子还是长得密密匝匝。据说他的后台挺硬。酉奥多的堂弟在都柏林堡[97]。家家都有个显赫的亲戚。每年他总给她一株茁壮的一年生植物[98]。有一次,我看见他光着头正领着一家人从“三个快乐的醉汉”酒馆前大踏步走边。大儿子还用买东西的网兜提着一个。娃娃们大哭大叫。可怜的女人!她得年复一年,整日整夜地喂奶。这些禁酒主义者是自私自利的。马槽里的狗 [99]。劳驾,红茶里我只要一块糖就够了。
他在舰队街的十字路口停下来。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到罗依[100]吃上一客六便士的份饭吧?还得到国立图书馆去查阅那条广告呢。倒不如到伯顿[101]去吃那八便士一客的,刚好路过那里。
他从博尔顿的韦斯特莫兰店[102]前走边。茶。茶。茶。我忘了向汤姆·克南定购茶叶啦。
咂咂咂,嗞嗞嗞!想想看,她在床上哼了三天,额头上绑着一条泡了醋的手绢,挺着个大肚子。唉!简直太可怕了!胎儿的脑袋大大啦,得用钳子。在她肚子里弯曲着身子,摸索着出口,盲目地试图往外冲。要是我的话,准把命送啦。幸而摩莉十分顺产。他们应该发明点办法来避免这样。生命始于分娩的痛苦。昏睡分娩法。维多利亚女王就使用过这种办法。她生了九胎[103]。一只多产的母鸡。老婆婆以鞋为家,生下一大群娃娃[104]。倘若他患的是肺病呢。现在该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了,而别去写什么“忧郁多思的胸脯闪着银白色光辉”[105]这类的空话了。那是哄傻子的空话。他们完全不用伤筋动骨,三下两下就能盖起一座大医院。从各种税收中,按复利借给每一个出生的娃娃五镑。按五分利计算,到了二十一岁就积累成一百零五先令了。英镑挺麻烦的,得用十进法乘二十。要鼓励大家存钱。二十一年内可存上一百一十多先令[106]。想在纸上好好计算一下。数目相当可观哩,比你想像的要多。
死胎当然不算数。连户口都不给上嘛。那是徒劳。
两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呆在一起,煞是可笑。摩莉和莫依塞尔太太[107]。母亲们的聚会。肺结核暂且收敛,随后又回来了。分娩后,她们的肚皮一下子就扁平了!温和的眼神。卸下了个大包袱的感觉。产婆桑顿老大娘是个快活的人儿[108]。她说:这些都是我的娃娃。喂娃娃之前,她总先把奶面糊糊的肚子放在自己嘴里尝尝。哦,好吃,好吃。替老汤姆·沃尔的儿子接生的时候,她把手扭伤了。那是他头一次亮相。脑袋活像个获奖的老倭瓜。爱生气的穆伦大夫 [109]。人们随时都来敲门喊醒他。“求求您啦,大夫。我内人开始阵痛啦。”至于谢礼呢,一连拖欠几个月。那是你老婆的出诊费呀。净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医生大多是好心肠的。
爱尔兰国会大厦[110]那老高老大的门前,一簇鸽子在飞来飞去。它们吃饱了在嬉戏。咱们撒到哪个人身上呢?我挑那个穿黑衣服的家伙。撒了。好运道。从空中往下撒,该是多么过瘾啊。有一回,阿普约翰、我本人和欧文·戈德堡[111]爬上古斯草地附近的树,学猴子玩。他们叫我青花鱼[112]。
一队警察排成纵队,迈着正步从学院路走了过来。一个个吃得脸上发热,汗水顺着钢盔往下淌,轻轻地拍打着警棍。饭后,皮带底下塞满了油汪汪的浓汤。警察的日子通常过得蛮快活[113]。他们分成几股散开来,边敬礼边回到各自的地段上去。放他们出去填饱肚子。最好是在吃布丁的时候去袭击,正进餐的当儿给他一拳头。另一队警察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来,绕过三一学院的栅栏,走向派出所。饲料槽在等着他们。准备迎接骑兵队。准备迎接浓汤。
他从汤米·穆尔那捣鬼[114]的指头底下横穿过去。他们把他这座铜像竖在一座小便池上,倒是做对了。众水汇合[115]。应该给妇女也修几座厕所。她们总是跑进点心铺,佯说是:“整理一下我的帽子。”世界纵然辽阔,惟数此峡……这是朱莉娅·莫尔坎[116]演唱的拿手歌曲。直到最后的时刻,她的嗓音始终都保持得洪亮如初。她是迈克尔·巴尔夫[117]的女弟子吧?
他目送着最后一名警察那穿着宽宽的制服上衣的背影。干这行当,就得对付一批棘手的主顾。杰克·鲍尔可以告诉你一桩事[118]。他爹就是一名便衣刑警。要是一个家伙在被抓的时候给了他们麻烦,等那人进了拘留所,就狠狠地让他尝尝厉害。干的是那种差事嘛,倒也难怪他们。尤其是年轻警察。乔·张伯伦在三一学院被授予学位的那一天,那个骑警为他可费了大事[119]。这是千真万确!他的马蹄沿着阿贝街一路嘚嘚嘚地朝我们逼来。幸而我灵机一动,一个箭步蹿进曼宁酒吧去,不然我准会惹上麻烦。他真是飞奔而来,想必是栽在人行道的鹅卵石上撞破了脑壳。我悔不该被卷进那批医学院学生当中。还有三一学院那些戴学士帽的一年级学生。反正就是想闹事。不过,这下子我倒结识了小迪克森。我被蜜蜂蜇了的那回,就是他在仁慈圣母医院替我包扎的。如今他在霍利斯街,普里福伊太太就在那儿。轮中套轮。[120]警笛的响声至今还萦回在我耳际。大家仓惶逃走。他为什么单单盯上了我呢?他对我说,你被捕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支持布尔人[121]!”
“为德威特[122]三欢呼!”
“把乔·张伯伦吊死在酸苹果树上![123]”
蠢才们。成群的野小子们声嘶力竭地喊叫。醋山岗[124]。奶油交易所的乐队[125]。不出几年,其中半数就必然将成为治安法官[126]和公务员。一打起仗来,就手忙脚乱地参军。就是这些人,过去经常说,哪怕上高高的断头台。[127]
你决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说话。科尼·凯莱赫的眼神活像是哈维·达夫[128]。活像是那个密告“常胜军”计划的彼得——不对,是丹尼斯——不对,是詹姆斯·凯里[129],其实他是市政府的官员。他煽动莽撞的小伙子去刺探情报,暗地里地却不断从都柏林堡领取情报活动津贴。快别再跟他来往了吧,危险哩。这些穿便衣的家伙怎么老是缠住女佣啊?平素穿惯制服的人,一眼就认得出来。把女佣推得紧紧贴着后门,粗鲁地挑逗一番。接着就干起正事了。来的那位先生是谁呀?少爷说过什么没有?从钥匙孔里偷看的汤姆[130]。做囮子的野鸭。血气方刚的年轻大学生抚摩着正在熨衣服的她那丰腴的胳膊,同她起腻。
“这些是你的吗,玛丽?”
“我才不穿这样的呢,……住手,不然我就向太太告你的状。深更半夜还在外面游荡。”
“好日子快要到来了,玛丽。你等着瞧吧。[131]”
“喏,你同那快要到来的好日子一道给我滚吧。”
还有酒吧间的女招待。纸烟店的姑娘。
詹姆斯·斯蒂芬斯的主意再高明不过了。他了解对方。他们每十个人分作一组,所以一个成员就是告密也超不出本组范围[132]。新芬[133]。要是想开小差,就准会挨一刀。有只看不见的手。[134]留在党内呢,迟早会被刑警队枪杀。看守的闺女帮助他从里奇蒙越狱,乘船离开拉斯科[135]。他曾在警察的鼻子底下住进白金汉宫饭店[136]。加里波第[137]。
你得有点儿个人魅力才行,像巴涅尔那样。阿瑟·格里菲思是个奉公守法的人,然而不孚众望。要么就海阔天空地谈论“我们可爱的祖国”。腊肉烧菠菜 [138]。都柏林面包公司的茶馆。那些讨论会[139]。说共和制乃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又说什么国语问题应该优先于经济问题。[140]还说你的女儿们可曾把他们勾引到你家来呢?肉啊酒的,让他们填饱肚子。米迦勒节的鹅[141]。为你准备了一大堆调好了味的麝香草,塞在鹅的肚皮里。趁热再吃一夸脱鹅油吧。半饥半饱的宗教狂们。揣上个一便士的面包卷[142],就跟着乐队走它一遭儿。东道主忙于切肉,顾不得作感恩祷告啦。一想到另一个人会为你付钱,就吃得格外香。毫不客气。请把那些杏子——其实是桃子一一递过来。那个日子不太遥远了。爱尔兰自治的太阳正从西北方冉冉升起。
走着走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乌云徐徐地遮住太阳,三一学院那阴郁的正面被暗影所笼罩。电车一辆接一辆地往返行驶,叮叮当当响着。说什么也是白搭。日复一日,事物毫无变化。一队警察开出去,又开回来。电车来来往往。那两个疯子到处徘徊。迪格纳穆被车载走了。麦娜·普里福伊挺着大肚皮躺在床上,呻吟着,等着娃娃从她肚子里被拽出来。每秒钟都有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出生,每秒钟另外又有一个死去。自从我喂了那些鸟儿,已经过了五分钟。三百人翘了辫子,另外又有三百个呱呱落地,洗掉血迹。人人都在羔羊的血泊中被洗涤,[143]妈啊啊啊地叫着。
整整一座城市的人都死去了,又生下另一城人,然后也死去。另外又生了,也死去。房屋,一排排的房屋;街道,多少英里的人行道。堆积起来的砖,石料。易手。主人转换着。人们说,房产主是永远不会死的。此人接到搬出去的通知,另一个便来接替。他们用黄金买下了这个地方,而所有的黄金还都在他们手里。也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诈骗的。日积月累发展成城市,又逐年消耗掉。沙中的金字塔。是啃着面包洋葱[144]盖起来的。奴隶们修筑的中国万里长城。巴比伦。而今只剩下巨石。圆塔。此外就是瓦砾,蔓延的郊区,偷工减料草草建成的屋舍。柯万用微风盖起来的那一应蘑菇般的房子[145]。只够睡上一夜的蔽身处。
大是毫无价值的。
这是一天当中最糟糕的时辰。活力。慵懒,忧郁。我就恨这个时辰。只觉得像是被谁吞下去又吐了出来似的。
学院院长的宅第。可敬的萨蒙博士。鲤鱼[146]罐头。严严实实地装在那个罐头里[147]。活像是小教堂的停尸所。即便给我钱,我也不愿意去住那样的地方。今天要是有肝和熏猪肉就好了。大自然讨厌真空状态。
太阳徐徐从云彩间钻出,使街道对面沃尔特·塞克斯顿店那橱窗里的银器熠熠发光。约翰·霍华德·巴涅尔连看也没看一眼就从橱窗前走过去了。
这是那一位的弟弟[148],跟他长得一模一样。那张脸总是在我眼前晃。这是个巧合。当然,有时你也会想到某人数百次,可就是碰不见他。他那走路的样儿,活像个梦游者。没有人认识他。今天市政府准是在召开什么会议。据说自从他就职以来,连一次也没穿过市政典礼官的制服。他的前任查理·卡瓦纳总是戴着翘角帽,头发上撒了粉,刮了胡子,得意洋洋地骑着高头大马上街。然而,瞧瞧他走路时那副狼狈相,仿佛是个在事业上一败涂地的人。一对荷包蛋般的幽灵的眼睛。我好苦恼。啊,伟人的老弟。乃兄的胞弟。他要是跨上了市政典礼官的坐骑,那才神气呢。兴许还要到都柏林面包公司去喝杯咖啡,在那儿下下象棋。他哥哥曾把部下当作“卒”来使用。对他们一概见死不救。人们吓得不敢说他一句什么。他那眼神让人见了毛骨悚然。这就是他引人瞩目的地方。名气。整个家族都有点儿神经病。疯子范妮[149],另外一个妹妹就是迪金森太太[150],给马套上猩红色挽具,赶着车子到处跑。她昂首挺胸,活像是马德尔外科医生[151]。然而在南米斯郡,这位弟弟还是败在大卫·希伊[152]手下了。他曾申请补上奇尔特恩分区·的空缺[153],然后引退成为官吏。爱国主义者的盛宴,在公园里剥桔皮吃[154]。西蒙·迪达勒斯曾经说过,他们要是把这个弟弟拉进议会,巴涅尔就会从坟墓里回来,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拖出下议院。
“说到这双头章鱼[155],一个脑袋长在世界的尽头忘记来到的地方,而另一个脑袋则用苏格兰口音讲话。上面长的八腕……”
有两个人沿着便道的边石走,从背后赶到布卢姆先生前面去了。胡子[156]和自行车,还有一位年轻女人。
哎呀,他也在那儿。这可真是凑巧了。是第二回。未来的事情早有过预兆。[157]承蒙著名诗人乔·拉塞尔先生的赞赏。跟他走在一起的说不定就是莉齐 ·特威格哩。A·E·[158]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兴许是名姓的首字:艾伯特、爱德华[159],阿瑟·埃德蒙[160],阿方萨斯·埃比或埃德或埃利 [161]或阁下[162]。他说什么来着?世界的两端用苏格兰口音讲话。八腕:章鱼。大概是什么玄妙的法术或象征含义吧。他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她一声不响地聆听着。给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先生当个助手。
他目送着那位穿手织呢衣服[163]的高个子,以及他的胡子和那辆自行车,还有他身旁那仔细聆听着的女人。他们是从素饭馆[164]走出来的,只吃了些蔬菜和水果,不吃牛排。你要是吃了,那头母牛的双眼就会永远盯着你。他们说,素食更有益于健康。不过,老是放屁撒尿。我试过。成天净跑厕所了。跟患气胀病[165]一样糟糕。通宵达旦地做梦。他们为什么把给我吃的那玩艺儿叫作坚果排[166]呢?坚果主义者,果食主义者。让你觉得你吃的像是牛腿扒。真荒谬。而且咸得很。是用苏打水煮的[167]。害得你整晚守在自来水笼头旁边。
她那双长袜松垮垮地卷在脚脖子上。我最讨厌这个样子,太不雅观了。他们统统是搞文学、有灵气的人。梦幻般的,朦朦胧胧的,象征主义的。他们是唯美主义者。就算是你所看到的食物会造成那种富于诗意的脑波,我也毫不以为奇。就拿那些连衬衫都被爱尔兰土豆洋葱炖羊肉般的黏汗浸透了的警察来说吧,你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也挤不出一行诗来。他甚至不晓得诗是什么。非得沉浸在某种情绪里才行。
梦幻一般朦胧的海鸥,
在沉滞的水土飞翔。[168]
他在纳索街角穿过马路,站在耶茨父子公司[169]的橱窗前,估计着双筒望远镜的价码。要么我到老哈里斯家去串门,跟小辛克莱[170]聊一聊吧? 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此刻多半正吃着午饭哪。得把我那架旧望远镜送去修理啦。戈埃兹棱镜片要六基尼。德国人到处钻。他们靠优惠条件来占领市场。削价抢生意。兴许能从铁路遗失物品管理处买上一架。人们忘掉在火车上和小件寄存处的物品之多,简直惊人。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女人也是这样。真是难以置信。去年到恩尼斯去旅行的时候,我只好替那个农场主的女儿捡起她的手提包,在利默里克[171]换车的当儿交给了她。还有无人认领的钱呢。银行屋顶上有一块小表 [172],是用来测试这些望远镜的。
他把眼睑一直耷拉到虹膜的底边。瞧不见。倘若你设想着表在那儿,你就好像能看见似的。然而还是瞧不见。
他掉转身去,站在两个布篷之间,朝太阳伸直了右臂,张开手。他已多次想这么尝试一下了。是啊,很完整。用小指头尖儿遮着太阳的圆盘[173]。淮是光线在这里聚焦的缘故。我要是有副墨镜就好了。那该多么有趣呀。我们住在伦巴德西街的时候,关于太阳的黑子,大家议论纷纷。那是可怕的爆炸形成的。今年将有日全蚀,秋季不定什么时候。
现在我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报时球是按照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降的。从邓辛克接上一根电线,用来操纵时钟。我一定得在某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去看一趟。我要是能弄到一封给乔利教授[174]的介绍信,或是找到一些有关他的家谱的资料才好呢。叫他出其不意地受到恭维。这挺灵。他会感到怡然自得。贵族总以做国王情妇的后裔为荣。他的女祖先。反正竭力阿谀。脱帽鞠躬,必然畅通无阻。[175]可不能一进去就信口开河地说些明知道不该说的话:视差是什么?结果款是:把这位先生领出去。
哎呀。
他又把右手垂到身边了。
关于这些,完全不摸头脑。纯粹是浪费时间。一个个气体球儿旋转着。相互交错,然后消失。亘古及今,周而复始。起初是气体,接着就是固体,然后是世界。冷却了,死去的硬壳四处漂流,冻僵的岩石宛如菠萝糖块[176]。月亮。她说:淮是升起了新月。我也相信是这样。
他从克莱尔屋[177]前走过。
且慢。两周前的星期日我们在那儿时是满月,所以今天应该刚好是新月。我们沿着托尔卡河往下游走去。费尔维尤那里适宜观赏月色。[178]她低吟着:五月的新月喜洋洋,宝贝。那个男人走在她的另一侧。肘。胳膊。他。萤光灯一闪一闪的,宝贝。[179]互相触摸。指头。这个提出要求。那个回答:好的。
别想下去了,别想下去了。既然必须这样,那就只好这样坝。必须[180]。
布卢姆先生呼吸急促,放慢脚步穿过亚当小巷。
他的心情好容易才宁静下来,神态安详地放眼望去。大白天在这条街上走着的,正是肩膀颇像酒瓶的鲍勃·多兰[181]。麦科伊曾说,他一年一度痛饮一遭。他们纵酒是为了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要么就是为了追女人[182]。跟相公们和妓女们在库姆街鬼混一阵,一年里的其他日子就像法官那么清醒。
对,果然不出所料。他正溜进帝国酒馆。消失了。光喝苏打水有益于他的健康。在惠特布雷德经营女王剧院之前,这里原是帕特·金塞拉开哈普剧院 [183]的地方。他仍保持着孩子气。按照戴恩·鲍西考尔待[184]的派头,在秋月般的脸上扣着一顶式样俗气的无檐圆帽。《三个俊俏姑娘放学了》。 [185]日子过得真快啊。呃?他的裙子底下露出长长的红裤子。酒徒们喝啊,笑啊,忽而喷溅出酒沫子,忽而又给酒呛住了。再给我满上吧,帕特。刺眼的红色。醉鬼门寻欢作乐。哄堂大笑,喷烟吐雾。摘下那顶白帽子。[186]他那双喝得挂满了血红的眼睛。现在他到哪儿去啦?在什么地方当叫化子呢。那把竖琴害得我们大家挨过饿。[187]
那阵子我更幸福一些。可那时的我究竟是我吗?或许难道现在的我才是我吗?当时我二十八,她二十三。我们从伦巴德西街搬走之后[188],起了点儿变化。鲁迪一死,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啦。没法叫时光倒流。那就像是想用手去攥住水似的。难道你想回到那个时期吗?刚开始的那个时期。真想吗?你在自己家里不幸福吗,你这可怜的小淘气鬼?她恨不得替我钉钮扣哩。我得写封回信。到图书馆去写吧。
格拉夫顿街上,花花哨哨地张挂着商店的遮阳篷,使他眼花·镣乱。平纹印花细布,穿绸衣的太太们和上了岁数的贵妇,还有发出一片叮当声的挽具,在灼热的街道[189]上低低地响着的马蹄声。那个穿白袜子的女人有着一双粗腿。但愿下场雨,把她弄得满脚烂泥。士里土气的乡巴佬。那些胖到脚后跟的统统都来啦。女人一发福,腿就那么臃肿。摩莉的腿看上去也不直溜。
他遛遛达达地从布朗·托马斯开的那爿绸缎铺的橱窗前走过。瀑布般的飘带。中国薄绢。从一只倾斜的雍口里垂下血红色的府绸。红艳艳的血。是胡格诺派教徒带进来的。事业是神圣的。嗒啦。嗒啦。那个合唱可精彩啦。嗒咧,嗒啦。得用雨水来洗。梅耶贝尔。咯啦。嘣嘣嘣。[190]
针插。我老早就催老婆去买一个了。她到处乱插。窗帘上也插了好儿根。
他挽了挽左袖:蜇的痕迹差不多看不见啦。今天就算了吧。得折回去取化妆水。也许等她过生日那天再去买吧。六、七、八,九月八日。差不多还有三个月呢。何况她未必喜欢。女人不肯捡起针来,说是那样就会把爱情断送掉。[191]
闪亮的绸缎,搭在纤细黄铜栏杆上一条条的衬裙,摆成辐射状的扁平长筒丝袜闪闪发光。
回忆过去是徒然的。该当怎样就怎样。把一切都向我讲了吧。
高嗓门。被太阳晒暖了的绸缎。马具叮当响。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女人:家庭和房子,丝织品,银器,多汗的水果,来自雅法的香料。移民垦殖公司[192]。全世界的财富。
一个温馨、丰腴的肉体在他的头脑里安顿下来。他的脑子屈服了,拥抱的芳香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的肉体隐然感到如饥似渴,默默地渴望着热烈的爱。
公爵街。终于到了。必须吃点儿什么。伯顿饭馆。那样就会舒坦一点。
他在剑桥[193]的犄角拐了弯,依然被那种感觉纠缠着。叮当声,马蹄声。馨香的肉体,温暖而丰满。吻遍了通身。默许了。在盛夏的田野里,在被压得缠在一起的篙草丛中,在公寓那嘀嘀嗒嗒漏着雨的门厅里,在沙发或咯吱咯吱响的床上。
“杰克,心肝儿!”
“宝贝!”
“吻我,雷吉!”
“我的乖!”
“宝宝!”
他心里坪坪跳着,推开了伯顿饭馆的门。一股臭气堵塞住他那颤巍巍的呼吸。冲鼻的肉汁,泥浆般的蔬菜。瞧瞧动物们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
人啊,人啊,人啊。
他们有的端坐在酒柜旁的高凳上,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有的坐在桌前,喊着还要添免费面包。狂饮劣酒,往嘴里填着稀溜溜的什么,鼓起眼睛,揩拭沾湿了的口髭。一个面色苍白、有着一张板油般脸色的小伙子,正用餐巾擦他那玻璃酒杯、刀叉和调羹。又是一批新的细菌。有个男人胸前围着沾满酱油痕迹的小孩餐巾,喉咙里呼噜噜地响着,正往食道里灌着汤汁。另一个把嘴里的东西又吐回到盘子上。那是嚼了一半的软骨,嘴里只剩齿龈了,想嚼却没有了牙。放在铁丝格子上炙烤的厚厚的一大片肋肉,囫囵吞下去拉倒。酒鬼那双悲戚的眼睛。他咬下一大口内,又嚼不动了。我也像那副样子吗?用别人看我们的眼睛来瞧瞧自己。[194]肚子饿了的就怒气冲天。牙齿和下巴活动着。别嚼啦!哎呀!一块骨头!在教科书的一首诗里写着:爱尔兰最后一位异教徒国王科麦克就是在博因河[195]以南的期莱镇上噎死的。不晓得他吃的是什么。想必是美味无比的佳希吧。圣帕特里克后来使他扳依基督
“烤牛肉和包心菜。”
“来一盘焖肉。”
男人的气味。啐上了唾沫的锯屑,甜丝丝、温吞吞的纸烟气味,嚼烟的恶臭,洒掉的啤酒,啤酒般的人尿味,发霉的酵母气味。
他快要呕吐了。
在这里,连一口也咽不下去。那个汉子在磨刀叉哪,打算把他面前的东西吃个一干二净。那老家伙在剔牙。一阵轻微的痉挛,肚子填得饱饱的,正在反刍。饭前饭后。饭后的祝祷文。望望这一幅画像,再望望那幅[197]。用浸泡得烂糟糟的面包片蘸肉汁来吃。干脆把盘子都舔个干净算啦,人啊!不要再这样啦!
他紧蹙鼻翼,四下里打量那些坐在凳子上对桌进食的人们。
“给咱来两瓶黑啤酒。”
“来盘罐头腌牛肉配包心菜。”
那家伙挑起满满一刀子包心菜,往嘴里塞,像是靠这来活命似的。-口就吞了下去。我看着都吓一跳。还不如用三只手来吃[198]呢。把肢体一根根地撕裂。这是他的第二天性。他是嘴里叼着一把银刀子生下来的。我认为这话挺俏皮。啊,不。银子就意味着生在阔人家。叼着一把刀子生下来的。可那么一来,隐喻就消失了。
一个腰带系得松松的侍者在唏哩哗啦地收走黏糊糊的盘子。法警长罗克[l99]站在柜台那儿,把他那大杯上冒起的啤酒泡沫吹掉。冒起了一大堆,黄黄地溅在他的靴子周围。一个就餐者直直地竖起刀叉,双肘倚着桌面,正准备吃下一道菜。他隔着摊在面前的那张污迹斑斑的报纸,正朝着食物升降机那边凝望。另一个家伙嘴里塞得满满的,在跟他谈着什么。很谈得来的知音。饭桌上的谈话。“星吃[期]一,我在芒[曼]切[彻]斯特银行[200]鱼[遇]见了特[他]。” “咦,是吗,真的呀?”
布卢姆先生迟迟疑疑地把两个手指按在嘴唇上。眼神里表示:
“不在这儿吃啦。别去看他。”
走吧。我就恨这种吃相下作的人。
他朝门口退去。到戴维·伯恩那儿去吃点快餐吧。先填上肚皮,好能走动。早饭吃得挺饱。
“这儿要烤牛肉和土豆泥。”
“再来一品脱黑啤酒。”
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埋头大吃。咕嘟咕嘟。吃下去。咕嘟咕嘟。往嘴里填。
第八章 2
他走出门外,吸到清新一些的空气,就朝格拉夫顿街折回去。要么吃,要么被吃掉。杀!杀!
假定几年以后成立起公共伙房,那会怎么样呢?大家都带上粥钵和饭盒,等人给盛,在街上就把自已那一份吞下去了。这里有约翰·霍华德·巴涅尔,比方说,还有三一学院院长,每一个母亲的儿子。[201]别提你们的院长们和三一学院院长。妇孺,马车夫,神父,牧师,元帅,大主教。来自艾尔斯伯里路,克莱德路,工匠住所,北都柏林联合救济院,市长乘着他那辆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马车,老女王坐着软轿。我的盘子空啦。请你排到我前面来。带上我们市政府的杯子,就跟菲利普·克兰普顿爵士的饮用喷泉一样。[202]用你的手绢擦掉细菌。下一个人又用他的来再擦上去一批。奥弗林神父会指出他们大家的愚昧无知。 [203]尽管如此,还是会打架的。人人都争头一份儿。孩子们争夺着巴在锅底儿上的那点残渣。得用凤凰公园那样大[204]的一口汤锅才行。用鱼叉叉起腌猪里脊和后腿肉来吃。你会憎恨周围的一切人。她把这叫作市徽饭店的客饭[205]。浓汤、肘子和甜食。永远也无法知晓你咀嚼的究竟是谁的思想。那么,所有这些盘子啦,叉子啦,又由谁来洗呢?到那时候兴许全都靠药片来充饥吧。牙齿就越来越糟了。
素食主义毕竟也有些道理,大地栽培出来的东西总是清香的。当然,大蒜挺臭,像那些意大利摇手风琴师的身上散发出的新鲜葱头、蘑菇和块菌的气味。也给动物带来痛苦。拔掉家禽的羽毛,把下水掏净。牲畜市场上那些不幸的牲口等着屠夫用斧子把它们的头盖骨劈成两半。哞!可怜的、浑身发抖的小牛。咩!打着趔趄的牛惠子。[206]煎白菜牛肉卷。屠夫的桶里装满了颤动着的肺脏。替咱把那爿胸脯肉从钩子上卸下来。啪嗒!刚砍下来的头和鲜血淋漓的骨头[207]。剥了皮、眼睛酷似玻璃珠儿般的羊,钩子勾在腰腿部位,从那堵着血淋淋的纸的鼻子里往锯屑上淌浓鼻涕。鞭打陀螺,让它们旋转个不停。娃娃们,可干万不要把它们胡乱抽碎。
他们给痨病患者开的药方是鲜血。什么时候都需要血。不知不觉之间病情就厉害起来了。趁着它还冒着热气儿,把那浓得像糖一样的血舔个干净。饿鬼们。
啊,我饿了。
他走进戴维·伯恩的店。这是一爿规规矩矩的酒吧。老板不喜欢饶舌。偶尔请你白喝上一盅,但次数少得就像四年一度的闰年。有一回他替我兑现了一张支票。
我吃什么好呢?他掏出怀表。现在让我想想看。啤酒兑柠檬汽水?
“喂,布卢姆,”大鼻子弗林[208]从他惯常坐的角落里说。
“哦,弗林。”
“近来怎么样?”
“好得很……让我想想看。来杯勃良第红葡萄酒[209]和……我想想看。”
架子上摆着沙丁鱼。光是望一望就几乎吃出了味道似的。三明治?在火腿和用它做成的食品上涂点芥末,夹在面包当中。[210]肉罐头。倘若你家里没有李树商标肉罐头呢?那可就美中不足了。[211]、多么愚蠢的广告!他们把这则广告插在讣告下面。这么一来,死者就统统爬上了李子树[212]。迪格纳穆的肉罐头。嗜食人肉者会就着柠檬和大米饭来用餐了。白种人传教师味道太咸了,很像腌猪肉。酋长想必会吃那精华的部分。由于经常使用,肉一定会老吧。他的妻子们全都站成一排,等着看效果。从前有过一位正统、高贵的黑皮肤老国王。他把可敬的麦克特里格尔先生的什么物儿吃掉了还是怎么了。有它才算幸福窝。天晓得是怎么搭配的。把胎膜、发霉的肺脏以及气管剁碎,搅和在一起来冒充。费多大劲也找不到一丝肉。清真食品。不能把肉和牛奶放在一道吃。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食品卫生。犹太教赎罪日的斋戒是内脏的一次春季大扫除。和平与战争取决于某人的消化力。各种宗教。圣诞节的火鸡和鹅。屠杀无辜。[213]吃啊,喝啊,快活一场。[214]然后济贫院的临时收容所遂告爆满。一个个头上缠着绷带。奶酪把本身以外的一切全消化掉。多螨的奶酪。[215]
“你们有奶酪三明治吗?”
“有的,先生。”
要是有的话,找还想来几颗橄榄。我更喜欢意大利产的。一杯高级勃良第葡萄酒会使我忘掉那档子事。那是润滑汕。一客美味的拌生菜,凉凉的,像是黄瓜。汤姆·克南善于烹调。做得有滋有味。纯的橄榄油。米莉替我在炸肉排旁添上一根嫩嫩的荷兰芹菜,端给我。要一颗西班牙葱头。天主创造了食物,魔鬼制造了厨子。[216]辣子镑蟹。[217]
“太太好吗?”
“蛮好,谢谢……那么,来一客奶酪三明治吧。你们有戈尔贡佐拉[218]奶酪吗?”
“有的,先生。”
大鼻子弗林饮着他那兑水烈酒。
“近来演唱了吗?”
瞧他那张嘴。简直能够往自己的耳朵里吹口哨了。再配上一双扇风耳。音乐。这方面他懂得的跟我的马车夫一般多。不过,还是告诉他的好。没什么害处,免费广告嘛。
“她已经订了合同,本月底就参加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你也许己经听说了吧。”
“没听说。哦,挺时髦的。谁是经纪人?”
侍者端上了盘子。
“多少钱?”
“七便士,先生……谢谢您,先生。”
布卢姆先生把他的三明治切成细条。麦克特里格尔先生。比那梦幻般的、奶油状的玩艺儿要好切一些。他那五百个妻子。她们尽情地得到了满足。
“要芥末吗,先生?”
“谢谢。”
他把三明治一条条揭起,抹满黄色的斑斑点点。得到了满足。我想起来了: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经纪人?”他说,“喏,那就像个公司,明白吧。资金大家摊,赚了钱大家分。”
“啊,现在我记起来了,”大鼻子弗林说,他把一只手伸进兜里去挠大腿窝的痒处,“是谁告诉我的来着?布莱泽斯·博伊兰也搀和进去了吧?”
芥末热辣辣地刺激着布卢姆先生的心脏。他抬起双眼,跟那座逼视着的挂钟打了个照面。两点钟。酒吧的钟快了五分钟。时间在流逝。指针在移动。两点钟。还不到。
这当儿他的小腹往上翻,随后又垂下去。越发热烈地渴望着,渴望着。
葡萄酒。
他闻着并啜着那醇和的汁液,硬逼着自己的喉咙一饮而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撂下。
“是的,”他说,“实际上他是发起人。”
没什么可怕的:这家伙没有头脑。
大鼻子弗林吸溜着鼻涕,挠着痒。跳蚤也正在饱餐着哪。
“杰克·穆尼[219]告诉我,他走了红运。迈勒·基奥在那次拳击比赛中又击败了贝洛港营盘的士兵[220],所以他赌赢了。真的,他还告诉我,他把那小子带到卡洛郡[221]去啦……”
但愿他那鼻涕别溜进他的玻璃杯里去。没有,他又把它吸回去了。
“听我说,比赛之前差不多一个月光景,就让他光嘬鸭蛋,天哪,听候底下的吩咐。用意是让他把酒戒掉,明白吗?哦,天哪,布莱泽斯可是个刁滑的家伙。”
戴维·伯恩从后面的柜台那儿走了过来。他的衬衫袖子打了裥,用餐巾抹着嘴唇,脸色红涨得像鲱鱼似的。微笑使他的鼻眼显得那么饱满。[222]活像是在欧洲防风根上抹了过多的大油。[223]
“他本人来啦,精神饱满,”大鼻子弗林说,“你能告诉我们哪匹马会赢得金杯吗?”
“我跟这不沾边儿,弗林先生,”戴维·伯恩回答说,“我绝不在马身上下赌注。”
“这你算做对啦,”大鼻子弗林说。
布卢姆先生把他那一条条的三明治吃掉。是新鲜干净的面包做的。呛鼻子的芥末和发出脚巴丫子味儿的绿奶酪,吃来既恶心可又过瘾。他嘬了几口红葡萄酒,觉得满爽口。里面并没搀洋苏木[224]染料。喝起来味道越发醇厚,而且能压压寒气。
精致安静的酒吧。柜台使用的木料也挺精致。刨得非常精致。我喜欢它那曲线美。
“我根本不想沾赛马的边儿,”戴维·伯恩说。“就是这些马,害得许许多多人破了产。”
酒商大发横财。他们获得了在店内供应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酒的特许证。正面我赢,反面你输。
“你说得有道理,”大鼻子弗林说。“除非你了解内情,不然的话,眼下没有不捣鬼的比赛。利内翰就得到了些内情。今天他把赌注压在‘权杖’上。霍华德 ·德·沃尔登爵士的坐骑‘馨芳葡萄酒’挺走红,它曾在埃普瑟姆[225]赢过。骑手是莫尔尼·卡农。两周以前,我要是把赌注下在‘圣阿曼’上,原是会以七博一获胜的。”
“是吗?”戴维·伯恩说。
他朝窗户走去,拿起小额收支帐簿翻看。
“这话一点儿不假,”大鼻子弗林吸溜着鼻涕说,“那可是一匹少见的名马。它老爹是‘圣弗鲁斯奎’。罗思柴尔德的这匹小母马曾在一场雷雨当中获胜,它耳朵里塞了棉花。骑师身穿蓝夹克,头戴淡黄色便帽。大个子本·多拉德和他那‘约翰·奥冈特’统统见鬼去吧!唉,是他拦住我,劝我别把赌注押在‘圣阿曼’上的。”
他无可奈何地喝着杯子里的酒,并且用手指顺着酒杯的槽花往下摸。
“唉,”他叹了口气说。
布卢姆先生站在那儿大吃大嚼,一面低头望着他叹气。笨脑瓜大鼻子。我要不要告诉他利内翰那匹马的事?他己经知道啦。不如让他忘掉。跑去会输掉更多钱的。傻瓜和他的钱。[226]鼻涕又往下人淌了。他吻女的时候,鼻子准是冰凉的。兴许她们还高兴呢。女人喜欢针刺般的胡子。狗的鼻子冰凉。市徽饭店里,赖尔登老太太[227]正带着她那条饥肠辘辘的斯凯更狗[228]。摩莉把它放在腿上抚摩着。啊,好大的狗,汪汪汪,汪,汪汪汪!
葡萄酒把嘴里那卷起来的面包心、芥末和令人一阵恶心的奶酪都浸软了。这可是好酒。我并不渴,所以味道就更醇香了。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刚洗完澡。喝上一两口就行了。然后,在六点钟左右我就可以……六点。六点。时光流逝得好快啊。她。
葡萄酒的奴火暖起他的血管。我太需要这杯酒了。近来觉得自己气色不佳。他那双不再饥饿了的眼睛打量着架子上那一排排的罐头:沙丁鱼、颜色鲜艳的龙虾大螯。人们专挑那古里古怪的东西吃。从贝壳和海螺里用针挑出肉来吃。还从树上捉。法国人吃地上的蜗牛。要不就在钩子上挂鱼饵,从海里钓。鱼可真傻,一千年也没学到乖。要是你不晓得随便往嘴里放东西有多么危险。有毒的浆果。犬蔷筏果。圆嘟嘟的,你会以为蛮安全。花哨刺目的颜色会引起你的警惕。大家传来传去就都知道了。先让狗吃吃看。会被那气味或模样吸引住。诱人的水果。圆锥形的冰淇淋。奶油。本能。就拿桔树林来说吧,也需要人工灌溉。布莱布特洛伊街 [229]。是啊,然而牡蛎怎么样呢?难看得像一口痰,外壳儿也肮里肮脏。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撬得开。是谁发现的?它们就靠从丢弃的残羹剩饭和下水道的污物长肥的。就着红岸餐馆的牡蛎喝香摈酒。倒是能促进性欲。春药。今天早晨他还在红岸餐馆来着。[230]在饭桌上他活像一只老牡蛎,一到床上身子兴许就变年轻了。不,六月没有“r”字,所以不吃牡蛎。[231]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发霉的食品。变了质的野味。用土锅炖的野兔肉。得失逮只野兔。中国人讲究吃贮放了五十年的鸭蛋,颜色先蓝后绿。一桌席上三十道菜。每一道菜都是好端端的,吃下去就搀在一起了。这倒是一篇投毒杀人案小说的好材料。是大公爵利奥波德 [232]吗?不,嗯。要么就是哈布斯堡王室后裔的一个叫作奥托的人吧?[233]是谁净吃自己脖颈后面的头皮呀?那是全城最廉价的午饭啦。当然喽,是贵族们,接着,其他人也都跟着赶起时髦来。米莉也说石油加面粉好吃。我自己也喜欢生面团。据说,为了怕跌价,他们把捕到的一半牡蛎又丢回大海里去啦。一便宜就没有买主啦。鱼子酱。那可是美味。盛在绿玻璃杯里的莱茵白葡萄酒。豪华盛宴。某某夫人。敷了脂粉的胸脯上挂着珍珠。高贵仕女。上流社会的名流。 [234]这帮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总点些特殊的菜肴。隐士则吃大盘大盘的豆食,这样好抑制肉欲的冲动。想了解我的话,就来同我一道就餐吧。王室御用的鲟鱼。[235]屠夫科菲从名誉郡长那里获得猎取森林中鹿类的权利。他将半头母牛孝敬了郡长。我曾瞥见摆在高等法院法官[236]府上厨房里的野味。戴白帽的大师傅[237]活像个犹太教教士。火烧鸭子[238]。帕穆公爵夫人式波纹形包心菜[239]。最好写在菜单上,好知道你吃了些什么。药味重了就会毁了肉汤。我有亲身体验。把它放在爱德华牌汤粉里做调料。为了他们,把鹅像傻瓜般地填喂[240]。将龙虾活活地扔进沸水里煮。请吃点雷鸟[241]。在高级饭店里当个侍者倒也不赖。接小费,穿礼服,净是些半裸的夫人们。杜比达特小姐[242],我可以给您再添点儿拧檬汁板鱼片吗?好的,再来点儿,而且她真地吃了。我估计她必是胡格诺派教徒家的。我记得有位,杜比达特小姐曾在基利尼[243]住过。我记得法语du dela[244]。但也许这就是同一条鱼哩,穆尔街的老米基·汉隆为了挣钱,曾把手指伸进那条鱼的腮里,开了膛掏出内脏。他连在支票上签名都不会。咧着嘴,只当是在画一幅风景画呢。默哎迈克尔,哧哎汉。[245]像一大筐翻毛生皮鞋那样愚蠢[246,却偏偏称有五万英镑。
两只苍蝇巴在窗玻璃上,嗡嗡叫着,紧紧膘在一块儿[247]。
热烘烘的葡萄酒在口腔里打了个转儿就咽下去,余味仍盘桓不已。把勃艮第葡萄放在榨汁器里碾碎。晒在炎日下。好像悄悄地触摸一下,勾起桩桩往事。触到他那润湿了的感官,使他回忆起来了。他们曾躲藏在霍斯那片野生的羊齿丛里。海湾在我们脚下沉睡着。天空。一片沉寂。天空。在狮子岬,海湾里的水面发紫,到了德鲁姆列克一带就变成绿色了。靠近萨顿那边又呈黄绿色。海底的原野,浮在海藻上那淡褐色条纹。一应座被淹没的都市。她披散着头发,枕着我的上衣。被石南丛中的蠼螋蹭来蹭去。我的手托着她的后颈。尽情地摆弄我吧。哎呀,大好啦!她伸出除了油膏、冰凉柔软的手摸着,爱抚着我,一双眼睛直勾勾地凝望着我。我心荡神移地压在她身上,丰腴的嘴唇大张着,吻着她。真好吃。她把嘴里轻轻地咀嚼得热乎乎的香籽糕[248]递送到我的嘴里。先在她口中用牙根嚼得浸透唾沫、又甜又酸、黏糊糊的一团儿。欢乐。我把它吞下了:欢乐。富于青春的生命。她把递过那一团儿的嘴唇噘起来。柔软、热乎乎、黏咂咂、如胶似漆的嘴唇。她的两眼像花儿一样,要我吧,心甘情愿的眼睛。小石子儿掉下来了。她躺在那儿纹丝儿不动。一只山羊,一个人也没有。在霍斯那高高的山丘上面,一只母山羊缓步走在杜鹃花丛中,醋栗一路坠落着。在羊齿草的屏障下,她被暖暖和和地围裹起来,漾着微笑。我狂热地压在她身上,吻她。眼睛,嘴唇,她那舒展的脖颈。女人那对乳房在修女薄呢[249]短上衣里面挺得鼓鼓的,怦怦悸动。肥大的奶头高耸着。我用热热的舌头舔着她。她吻了我。我被吻了。她委身于我,爱抚着我的头发。亲嘴儿,她吻了我。
我。而我现在呢。
紧紧膘在一块儿的苍蝇嗡嗡叫着。
他那低垂的眼睛沿着栎木板那寂然无声的纹理扫视。美丽。它画着曲线。曲线是美的。婀娜多姿的女神们。维纳新,朱诺。举世赞美的曲线。只要到图书馆和博物馆去,就能看见裸体女神伫立在圆形大厅里。有助于消化。不论男人瞧哪个部位,她们全不介意。一览无余。从来不言不语。我的意思是说,从来不对弗林那样的家伙说什么。倘若她真像加拉蒂亚对皮格马利翁[250]那样开了腔,她首先会说什么呢?凡人啊!马上就叫你乖乖就范了。跟众神一道畅饮甘露神酒吧,金盘子里盛的统统是神馔。可不像我们通常吃的那种六便士一份的午餐:炖羊肉、胡萝卜、芜菁和一瓶奥尔索普[251]。神酒,可以设想那就跟喝电光一样。神馔。按照朱诺的形象雕刻的女人那优美的神态。不朽的丽质。然而我们是往一个孔里填塞食品,又从后面排泄。食物,乳糜,血液,粪便,土壤,食物[252]。得像往火车头里添煤似的填塞食品。女神们却没有[253]。从来没见过。今天我倒要瞧一瞧。管理员不会理会的。故意失手掉落一样东西,然后弯下身去拾,好瞧瞧她究竟有没有。
从他的膀恍里点点滴滴地透出无声的信息,去解吗?不去解啦,不,还是去解了吧。作为一个男子汉,他拿定了主意把杯中物一饮而尽,然后起身走到后院去。边走边想:她们觉得自己就像是男人[254],但也曾委身于男人们,并且跟相恋的男人们睡觉。一个小伙子曾享用过她。
当他的皮靴声消失后,戴维·伯恩边看着帐簿边说:
“他是哪一行的?不是干保险这个行当的吗?”
“他早就不干那一行啦,”大鼻子弗林说,“他在给《自由人报》拉广告哪。”
“我跟他挺熟的,”戴维·伯恩说,“他是不是遭到什么不幸啦?”
“不幸?”大鼻子弗林说,“可没听说。怎么看出的?”
“我留意到他穿着丧服。”
“是吗?”大鼻子弗林说,“确实是这样。我问过他家里的人都好吗?你说得一点儿不错,他确实穿着丧服。”
“我要是看到一位先生在这方面遭到不幸,”戴维·伯恩用慈祥的口吻说,“我就绝不去碰这个话题。那只会又一次勾起他们的悲伤。”
“反正他也不是替老婆戴孝,”大鼻子弗林说,“前天我还碰见他正从约翰·怀思·诺兰的妻子在亨利大街上经营的那家爱尔兰牛奶坊里走出来,手里捧着一罐子奶油,带回去给心爱的太太。真的,她在吃上讲究极啦。胸脯丰满,可妖艳哩。”
“他在替《自由人报》做事情吗?”戴维·伯恩说。
大鼻子弗林噘起嘴来。
“他可不是靠拉广告的收入来买奶油的,一点儿没错。”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戴维·伯恩放下他的帐簿,走过来说。
大鼻子弗林用手指变戏法般地望空比划了几下,眨了眨眼。
“他加入共济会啦。”
“真的吗?”戴维·伯恩说。
“千真万确,”大鼻子弗林说,“古老、自由而众所公认的行会[255]。天主赐与光、生命和爱。他们帮了他一把。告诉我这话的是一位……喏,还是姑隐其名吧。”
“确有此事吗?”
“嗯,那可是个出色的组织,”大鼻子弗林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助你一臂之力。我晓得有个人正在千方百计想参加,然而他们那门关得可紧啦。他们绝不让女人参加,这一点着实做得对。”
戴维·伯恩边微笑边打哈欠边点头。
“啊——哧!”
“一回,有个女人躲在一应巨大的时钟里,”大鼻子弗林说,“想看看他们究竟搞些什么名堂。可他妈的,给他们发觉了,就把她拖了出来,让她当场宣誓,当上一名师傅。听说她是唐奈顿尔的圣莱杰家族里的一名成员[256]。”
戴维·伯恩打完哈欠后又坐了下来,泪汪汪儿地说:
“这是真的吗?他可是位规规矩矩、不多言不多语的先生呢。他常常光顾这里,可我从来没看见他——喏,酒后失态过。”
“连全能的天主都不能把他灌醉,”大鼻子弗林斩钉截铁地说,“每逢闹腾得过了火,他就开溜啦。你没见到他在瞧自己的表吗?啊,当时你不在座。要是你邀他喝上一盅,他就会先掏出怀表,看看该喝点儿什么。我敢说他确实是这样。”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戴维·伯恩说,“我看他是个牢靠的人。”
“他这个人不赖,”大鼻子弗林边吸溜着鼻涕边说,“还听说,他曾伸手去帮过一个伙伴的忙。平心而论,哦,布卢姆有种种长处。然而有一件事,他是绝对不干的。”
他把手指当作没有蘸墨水的钢笔,在那杯兑了水的烈性酒旁,作潦潦草草地签字的样子。
“我知道,”戴维·伯恩说。
“白纸黑字,他可绝对不肯,”大鼻子弗林说。
帕迪·伦纳德和班塔姆·莱昂斯走了进来。汤姆·罗赤福特[257]皱着眉头跟在后面,闷闷不乐地一只手按在紫红色背心上。
“你好,伯恩先生。”
“你们好,各位先生。”
他们在柜台那儿停下了脚步。
“谁来做东?”帕迪·伦纳德问道。
“反正我已经坐下啦,”[258]大鼻子弗林回答说。
“那么,喝什么好呢?”帕迪·伦纳德问。
“我要姜麦酒加冰块,”班塔姆·莱昂斯说。
“来多少?”帕迪·伦纳德大声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这个的?你要什么,汤姆?”
“下水道的干管怎么样啦?”大鼻子弗林边呷酒边问。
汤姆·罗赤福特用手紧紧按住胸骨,打了个嗝作为答复。
“劳驾给我杯清水好吗,伯恩先生?”他说。
“好的,先生。”
帕迪·伦纳德朝着他的酒友们瞟了一眼。
“哎呀,好没出息!”他说,“我在请什么样的人喝啊,凉水和姜麦酒!分明是两个酒徒,连伤腿上的威士忌都会舔个干净的家伙。他好像掌握着一匹能得金杯的骏马。万无一失啦。”
“是‘馨芳葡萄酒’吧?”大鼻子弗林问。
汤姆·罗赤福特从纸卷里往摆到他跟前的杯中撒了点粉末。
“这消化不良症真讨厌,”他在喝下之前说。
“小苏打很有效哩,”戴维·伯恩说。
汤姆·罗赤福特点点头,喝了下去。
“是‘馨香葡萄酒’吗?”
“什么也不要说!”班塔姆·莱昂斯使了个眼色,“我准备自己在那马上投五先令。”
“妈的,你要是个好汉,就告诉我们吧,”帕迪·伦纳德说,“这究竟是谁透露给你的?”
布卢姆先生一面往外走,一面伸了伸三个指头来致意。
“再见吧!”大鼻子弗林说。
其他人都掉过头去。
“就是那个人透露给我的,[259]”班塔姆·莱昂斯悄悄地说。
“呸!”帕迪·伦纳德鄙夷地说,“伯恩先生,我们还要两小瓶詹姆森威士忌,还有……”
“冰块姜麦酒,”戴维·伯恩彬彬有礼地补充说。
“唉,”帕迪·伦纳德说,“给娃娃个奶瓶嘬嘬。”
布卢姆先生边朝道森大街走去,边用舌头把牙齿舔净。必须是绿色的东西才行:比方说,菠菜。这样,就能用伦琴射线[260]透视办法来追踪了。
在公爵巷,一只贪吃的狗正往鹅卵石路面上吐着一摊令人恶心的肘骨肉,然后又重新热切地舔着。饕餮。把吞下的充分消化后,又怀着谢意把它吐了出来。第一次是香甜的,第二次蛮有滋味。布卢姆先生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反刍动物们。这是第二道菜肴。它们用上颚嚼动着,我倒是想知道汤姆·罗赤福特怎样对待他那项发明[261]的。对着弗林那张嘴去解释,是白费蜡。瘦人嘴巴长。应该有个人厅或什么地方,发明家可以聚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搞发明。当然缕,那样一来,各种怪人就会都来找麻烦了。
他哼唱着,用庄严的回声拉长了各小节的尾音:
唐乔万尼,你邀请我
今晚赴宴[262]。
觉得舒坦些了。勃良第。能够提神。最早酿酒的是谁呢?什么地方的一个心情忧郁的汉子。酒后撤疯。现在我得到国立图书馆去查查(基尔肯尼民众报)了。
威廉·米勒卫生设备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一具具光秃秃、干干净净的抽水马桶,把他的思绪又拉回来了。能做到的。吞进一根针去,盯着它一直落下去。有时又在几年后从肋骨里冒出来了。在体内周游一道,经过不断起着变化的胆汁导管,把忧郁喷了出去的肝脏,胃液,像管子般弯弯曲曲的肠子。然而那被试验的可怜虫老得站在那儿展示自己的内脏。这就是科学。
A ar teco.[263]
这里的“teco”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今晚”吧。
唐乔万尼,你邀请我,
今天同你共进晚餐,
泽,朗姆,泽,朗达姆。
不对头。[264]
凯斯。只要南尼蒂那儿顺顺当当,我就能有两个月的进项。这样就有两镑十先令——两镑八先令左右了。海因斯欠了我三先令。两镑十一先令。普雷斯科特染坊的运货马车就在那儿。要是拉到比利·普雷斯科特[265]的广告,那就能挣两镑十五先令。加在一起是五基尼左右。打着如意算盘吧。
可以给摩莉买条真丝衬裙,颜色正好配她那副新袜带。
今天。今天。不去想了。
然后到南方逛逛去。英国的海滨浴场怎么样?布赖顿[266],马盖特[267]。沐浴在月光下的码头。她的嗓音悠然飘荡。海滨那些俏丽的姑娘。一个睡意的流浪汉倚着约翰·朗酒吧的墙,边啃着结了一层厚痂指关节,边深深地陷入冥。巧手工匠,想找点活儿干。工钱低也行,给啥吃啥。
布卢姆先生在格雷糖果点心铺那摆着售不出去的果酱馅饼的橱窗跟前拐了弯,从可敬的托马斯·康内兰的书店前走过去。《我为什么脱离了罗马教会 [268]》。“鸟窝会”[269]的女人们在支持他。据说,土豆歉收的年头,她们经常施汤给穷孩子们,好叫他们改信新教。以前,爸爸曾到过马路对面那个使穷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公会。[270]他们用的是同样的诱饵。我们为什么脱离了罗马教会。
一个年轻的盲人站在那儿用根细杖敲着人行道的边石。没有电车的影子。他想横过马路。
“你想到对面去吗?”布卢姆先生问。
年轻的盲人没有回答。他那张墙壁般的脸上稍微皱起眉头,茫然地晃动了一下头。
“你现在是在道森大街上,”布卢姆先生说,“莫尔斯沃思大街就在对面。你想横穿过去吗?眼下什么过路的也没有。”
他的手杖颤悠悠地朝左移动。布卢姆先生目送着,就又瞥见普雷斯科特染坊的那辆载货马车还停在德拉格理发馆门前。上午我在同一个地方瞥见他那除了润发油的头,当时我刚好……马耷拉着脑袋。车把式正在约翰·朗酒吧里润着喉咙呢。
“那儿有一辆载货马车,”布卢姆先生说,“可是它一动也没动。我送你过去吧。你想到莫尔斯沃思大街去吗?”
“是的,”年轻人回答说,“南弗雷德里克大街。”
“来吧,”布卢姆先生说。
他轻轻地碰了一下盲青年那瘦削的肘部,然后拉着那只柔弱敏感的手,替他引路。
跟他搭讪一下吧。可别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会不相信你的话的。随便拉拉家常吧。
“雨不下啦。”
不吭声。
他的上衣污迹斑斑。他必是一边吃一边洒。对他来说,吃起东西来味道也完全不同。最初得用匙子一口一口地喂。他的手就像是娃娃的手。米莉的手也曾经是这样的。很敏感。他多半能凭着我的手估摸出我个头有多大。他总该有个名字吧?载货马车。可别让他的手杖碰着马腿。马累得正在打着盹儿。好啦,总算安安全全地过了马路。要从公牛后面,马的前面走。[271]
“谢谢您,先生。”
凭着嗓音,知道我是个男的了吧。
“现在行了吧?到了第一个路口就朝左拐。”
年轻的盲人敲敲边石,继续往前走。他把拐杖抽回来,又探一探。
布卢姆先生跟在盲人的脚后面走着。他穿着一套剪裁不得体的人字呢衣服。可怜的小伙子!他是怎么知道那辆载货马车就在那儿的呢?准是感觉到的。也许用额头来看东西。有一种体积感。一种比暗色更要黑一些的东西——重量或体积。要是把什么东西移开了,他能感觉得到吗?觉察出一种空隙。关于都柏林城,他想必有一种奇妙的概念,因为他总像那样敲黄石头走路。倘若没有那根手杖,他能够在两点之间笔直地走吗?一张毫无血色的、虔诚的脸,就像是许下愿要当神父似的。
彭罗斯[272]!那人就叫这个名字。
瞧,他们可以学会做多少事。用手指读书。为钢琴调音。只要他们稍微有点儿头脑,我们就会感到吃惊。一个残疾人或驼背的要是说出常人也会说的话,我们就会夸他聪明。当然,在其他方面他们的感官比我们灵敏。刺绣。编箩筐。大家应该帮帮他们。等摩莉过生日的时候,给她买一只针线筐吧。她就讨厌做针线活儿。也许会不高兴的。人们管他们叫瞎子。
他们的嗅觉也一定更敏锐。四面八方的气味都聚拢了来。每一条街各有不同的气味。每一个人也是这样。还有春天,夏天,各有不同的气味。种种味道呢?据说双目紧闭或者感冒头痛的时候,就品尝不出酒的味道。还说摸着黑抽烟,一点儿味道也没有。
比方说,对待女人也是如此。看不见就更不会害臊了。那个仰着头从斯图尔特医院[273]跟前走边的姑娘。瞧瞧我,穿戴得多么齐全。要是瞧不见她,该是多么奇怪啊。在他心灵的眼睛里,会映出一种形象。嗓音啦,体温啦。当他用手指摸她的时候,就几乎能瞥见线条,瞥见那些曲线了。比方说,他把手放在她头发上。假定那是黑色的。好的。我们就称它作黑色吧。然后移到她的白皮肤上。兴许感觉就有所不同。白色的感觉。
邮局。得写封回信。今天可真忙啦。用邮政汇票给她寄两先令去——不,半克朗吧。薄礼,尚乞哂纳。这儿刚巧有家文具店。且慢。考虑考虑再说。
他用一根手指非常缓慢地把头发朝耳后拢了拢。又摸了一遍。像是极为柔细的稻草。然后又用手指去抚摩一下右脸颊。这里也有茸毛,不够光滑。最光滑要算肚皮了。四下里没有人。那个青年正走进弗雷德里克大街。也许是到利文斯顿舞蹈学校去给钢琴调音哩。我不妨装出一副调整背带的样子。
他走边多兰酒吧,一边把手偷偷伸进背心和裤腰之间,轻轻拉开衬衫,摸了摸腹部那松弛的皱皮。然而我知道那颜色是黄中透白。还是找个暗处去试试吧。
他缩回了手。把衣服拽拢。
可怜的人哪!他还是个孩子呢。可怕啊。确实可怕。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他都做些什么梦呢?对他来说,人生就像是一场幻梦。生就那副样子,哪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那些妇孺参加一年一度的游览活动,在纽约被烧死、淹死[274]。一场浩劫。他们说,“业”[275]就是为了赎你在前世所犯下的宿孽,而轮回转生——遇见了他尖头胶皮管子。[276]哎呀,哎呀,哎呀。当然值得同情。然而不知怎地,他们总有点儿难以接近。
弗雷德里克·福基纳爵士[277]正步入共济会会堂。庄严如特洛伊[278]。他刚在厄尔斯福特高台街美美地吃过一顿午餐。司法界的一群老朽们都聚在一道,起劲地喝着大瓶大瓶的葡萄酒,海阔天空地谈论着法院啦,巡回裁判啦,慈善学校年鉴啦。“我判了他十年徒刑。”他也许对我喝的那种玩艺儿嗤之以鼻。他们喝的是瓶子上沾满尘埃、标着酿造年份的陈年老酒。关于记录官法庭该怎样主持公道,他自有看法。这是位用心良好的老人。警察的刑事诉讼卷宗里塞满了种种案件——他们为了提高破案率而捏造罪名。他要求他们纠正。对那些放债者毫不姑息。曾把吕便·杰狠狠地收拾了一顿。说起来他可不折不扣是个人们所说的可鄙的犹太人。这些法官权力很大。都是些戴假发、脾气暴躁的老酒鬼。就像爪子疼痛发炎的熊一样。愿天主可怜你的灵魂。[279]
哦,招贴画。麦拉斯义卖会。总督阁下。十六日,那就是今天啊。[280]为默塞尔医院募款。《弥赛亚》的首演[281]也是为了这个。对。亨德尔。到那儿去看看怎样?鲍尔斯桥。顺便到凯斯商店走一遭。像水蛭似的巴在他身上也没用。呆长了会讨嫌。在门口总会碰上熟人的。
布卢姆先生来到了基尔戴尔大街。首先得去图书馆。
在阳光底下戴着草帽。棕黄色皮鞋。卷边长裤。对,就是他[282]。
他的心轻轻地悸跳着,向右拐吧。博物馆。女神们。他向右拐了个弯。
是他吗?多半是。别看他了。酒上了我的脸。我为什么要……?太叫人发晕。对,就是他。走路的那个姿势。别看他啦。别看他啦。往前走吧。
他边大步流星地走向博物馆的大门,边抬起眼睛。漂亮的建筑。是托马斯·迪恩爵士[283]设计的。他没跟在我后边吧?
也许他没瞧见我。阳光正晃着他的眼睛。
他气喘吁吁,发出一声声短促的叹息。快点儿。冰冷的雕像群。那里挺僻静,不出一分钟我就安全了。
是啊,他没瞧见我。两点多啦。就在大门口那儿。
我的心脏!
他的眼睛直跳,直勾勾地望着奶油色石头的曲线。托马斯·迪恩爵士,希腊式建筑。
我要找样东西。
他那只焦躁的手急忙伸进一个兜里,掏出来一看,是读后没叠好的移民垦殖公司的广告。可放在哪儿了呢?
匆匆忙忙地找。
他赶快又将公司的广告塞了回去。
她说是下午。
我找的是那个。对,那个。所有的兜都翻遍了。手绢。《自由人报》。放在哪儿了呢?对啦。裤子。皮夹子。土豆。我放在哪儿了呢?
快点口。放轻脚步。马上就到啦。我的心脏。
他一边用手摸索着那不知放到哪儿去了的东西,一边念叨着还得去取化妆水。在裤兜里找到了肥皂,上面粘着温吞吞的纸。啊,肥皂在这儿哪。对,来到大门口了。
第八章 注释
[1]基督教兄弟会是天主教在俗修士的组织,致力于实用通俗教育,学校的经费募自民间。
[2]”国王陛下御用”为英国广告习用语。
[3]这是十六世纪编成的英国国歌首句的前年句,全句是:”上帝拯救我们正义的国王。”到了第十五章才点明,嘬糖者指爱德华七世(见该章注[882])。
[4]基督教青年会以通过团体活动来传教。一八四四年成立于伦敦,一八五一年传到北美。
[5]原文作Bloo。布卢姆,英文作Bloom,而”血”则为”blood”。布卢姆最初以为这里写的是他,及至看下去才知道是”血”。”羔羊的血”一语出自《启示录》第7章第14节:”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了。”
[6]德鲁伊特,见第一章注[47]。每逢有人病危或在战争中受重伤时, 德鲁伊特即为之献祭。办法是将活人装入人形的柳条笼里焚烧。一般使用罪犯,有时也使用无辜者。
[7]以利亚为活动于公元前九世纪的希伯来先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奉他为先知。中国穆斯林称之为伊利亚斯。《旧约全书》的结尾(《玛拉基书》第4章第5-6节)作:”在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要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要使父亲和子女重新和好,免得我来毁灭大地。”根据犹太教的信仰,以利亚的再度到来标志着弥赛亚(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世主)的来临,而根据基督教的信仰, 这也意味着基督再世。
[8]约翰?亚历山大。道维(1847-1907),以信仰疗法传教的美国布道家。他通过个人摆脱病痛的经验提出灵性疗法,成立国际神圣疗法协会。一九0一年纠结约五千信徒在距芝加哥约四十英里处建锡安城。同年以再世的以利亚自居。一九0四年六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他来到欧洲。一九O六年因滥用资金并宣扬一夫多妻主义等丑闻而为信徒们所唾弃。
[9]指美国一批以托里和亚历山大为首的信仰复兴运动者。一九0三至一九0五年间,他们到英国进行活动,并于一九0四年三、四月间前往都柏林。鲁本?阿切尔?托里(1856-1928)宣讲怎样研究《圣经》。查尔斯?麦卡勒姆?亚历山大(1867-1928)是个牧师,负责教堂音乐事宜。
[10]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人约翰?佩珀所想出的一套办法,他用灯光、黑帷幕和发磷光的服装等,以加强鬼戏的舞台效果。
[11]参看第五章注[67]。
[12]马拉加指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地中海沿岸省份,盛产葡萄,以用麝香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马拉加葡萄酒闻名于世。
[13]乔治?巴特勒所开的乐器制造厂在巴切勒步道口上,紧挨着立在奥康内尔桥头的奥康内尔纪念碑,所以人们称这座厂房作纪念碑房。
[l4]指天主教禁止教徒节制生育。
[15]“生养并繁殖吧”一语出自《创世记》第1章第28节。
[16]这原是埃及王劝以色列人约瑟把全家父老兄弟接到埃及来定居时所说的话。全句是:“我要把埃及最好的土地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丰足的生活。”见《创世记》第45章第18节。
[17]赎罪日是犹太教最隆重的节日,在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公历9、10月间)初十。《圣经》称赎罪日为圣安息日。从赎罪日前夕至赎罪日全天,犹太教徒都要进行祈祷和默念,禁绝饮食和男女之事。
[18]十字面包是大斋期(耶稣复活节之前四十天,也叫四旬斋)吃的一种果仁甜面包,上面有一层十字架形的糖衣饰纹。
[19]这是一首俚谣的首句。下面是:“自带茶叶和白糖,/但你会赴婚礼的。/你会去的,是不是?”
[2O]“土豆和……和土豆”一语出自民间唱词,表示贫苦人民的怨艾。
[21]指吉尼斯啤酒公司,参看第七章注[8]。
[22]柯利狗是十八世纪在英国培育成的一种使役犬,分牧羊和看门用的两种。
[23]“像个基督教徒那样”在这里有“像个正派人那样”的含意。
[24]在第六章中,马丁?坎宁翰提及吕便?杰给了救他儿子一命的人两先令。西蒙?迪达勒斯挖苦道:“多给了一先令八便士。”意思是:只给两便士就够了。
[25]指他方才拿到的那张传单。
[26]爱琳王号是船名,参看第四章注[64]及有关正文。
[27]“哈姆……时期”一语出自《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
[28]班伯里为英国牛津郡查韦尔区一城镇。数百年来以所产啤酒、奶酪和点心闻名。
[29]吗哪是希伯来文,为“是什么东西”的译音,系古以色列人漂泊荒野时天主所赐类似蜜饼的白色食物。见《出埃及记》第16章。
[30]安娜?利菲是利菲河(爱尔兰语:生命之河)的别称。通常是指流经都柏林市南部和西部景色幽美的上游。
[31]在中世纪的英国,天鹅肉是专供国王享用的美味。《鲁滨孙飘流记》(1719)中并未明说鲁滨孙吃过天鹅肉,只是提到当地“有不少种飞禽,肉很好吃。然而,除了那些叫作企鹅的以外,我一概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32]这是伦敦的服装商J?C?吉诺在都柏林所开设的批发成衣的分号。第二行的11代表十一先令,指每条长裤的价钱。
[33]亨利?弗兰克斯大夫是个英籍犹太人,一八五二年出生于曼彻斯特,一九0三年来到都柏林。
[34]据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365页), 舞蹈教师丹尼斯?杰?马金尼当时是个中年人,以讲究穿戴著称。
[35]邓辛克位于都柏林市西北方约五英里处。这里有一座一七八五年由三一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安德鲁斯博士捐赠的气象台,用气流操纵三一学院的钟。
[36]罗伯待?斯托尔?鲍尔爵士(1840-1913),天文学家, 毕业于三一学院,在母校任天文学教授。一八九二年改任剑桥大学天文学和几何学教授。这里指他的《天空的故事》(1885)一书。
[37]英文里,除了“transmigration”,另有个源于希腊文的外来语“metempsychosis”,也作“轮回”解,与“met him pike hoses”(遇见了他尖头胶皮管)读音相似,故有此误会。
[38]原文作base barreltone,是文字游戏。base既可作“下贱”解, 又可作“男低音”解。Barreltone的意思是“桶音”,与“barytone”(男中音)谐音。这里还有双关之意。多拉德胖得像是巴思(Bass)酒厂的酒桶。
[39]原文作BigBen,指英国议会大厦上的大钟。(40]神父身上的祭披背后写有l?H?S三个字母。本为拉下文“万人的教主耶稣”的首字。摩莉却按照英语把它理解为“我犯了罪”、“我受了苦”(参看第五章注[67])。这里,把“我”改成了“我们”。
[41]HELY(希利)是店老板的姓,后面加上“’S”,代表“的”,意思是“希利所开的店”。
[42]博伊指博伊兰。当时确有个叫默?格拉德的人,在都柏林市开一家广告公司。
[43]盐柱,指因好奇心而受到处罚。参看第四章注[36]。
[44]这是一八三三年由天主教的迦尔默罗会在拉思曼斯的特兰奎拉所创立的女修道院。
[45]迦密山是以色列西北部一道山岭。在《圣经》中,为先知以利亚与崇拜巴力神的众先知对证真伪之处。这里也是迦尔默罗会的发源地(约1156年)。
[46]这是文字游戏。迦密的原文作Carmel;而糖蜜的原文是caramel,这两个词发音相近。
[47]铁蒺藜实际上是由三个美国人(史密斯、亨特、凯利)不约而同地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间发明的。
[48]这是第五个挂广告牌的人,参看本章注[41]。
[49]指在三一学院(参看第五章注[99])举行的赛车会。
[50]第十七章中说明了菲尔?吉利根的死因。
[51]即亚历山大?汤姆印刷出版公司,参看第七章注[45]。
[52]这里,布卢姆想起他儿子鲁迪夭折于一八九四年的往事。
[53]维尔?狄龙实有其人,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间任都柏林市市长,死于一九0四年四月二日。
[54]这是为了给圣凯文感化院(后改名为格伦克里教养中心)募款而一年一度举行的午餐会。
[55]这里套用成语“喂内在的人”,意指吃精神食粮。
[56]“主呵,所赐万惠,我等”是天主教的《饭后祝文》。“我等”后面省略了“感激称颂”四字。
[57]糖锥山位于都柏林东南十四英里处。
[58]指坐落于斯蒂芬街上的托马斯?多克雷尔父子公司,经售窗玻璃并负责装修。
[59]据第十七章注[310]及有关正文,当年布卢姆的父亲还在匈牙利的塞斯白堡时,他的堂兄弟斯蒂芬?维拉格有过这样一间暗室。
[60]生命的长河,参看第五章注[104]。
[61]西特伦,参看第四章注[26]。
[62]此人最初见于第七章“排字房的老领班”一节。直到本章末尾(参看注[272])布卢姆才想起他姓彭罗斯。
[63]巴特尔?达西是个虚构的人物,曾出现在《都柏林人?死者》中。
[64]一八九三或一八九四年,布卢姆由于兜售匈牙利皇家特许彩票,差点儿被抓去坐牢。下文中的高中,指伊拉兹马斯?史密斯高中(创立于1870)。
[65]“也许……永远地”出自安妮?巴里?克劳福德作词、弗雷德里克?N?克劳奇配曲的《凯思琳?马沃宁》这首歌的第一段。
[66]布林太太是布卢姆的妻子摩莉的女友,原名乔西?鲍威尔。布卢姆曾和她逢场作戏。她后来嫁给了丹尼斯。
[67]“你的葬礼在明天”, 套用费利克斯?麦格伦农的《他的葬礼在明天》,将“他”改成了“你”。“当你穿过裸麦田”, 套用罗勃特?彭斯的诗句《穿过裸麦田》。
[68]圭亚那东部的德梅拉拉地区所产的蔗糖。
[69]每年冬季,都柏林基督教协会为贫民供应每顿仅一便士半的廉价午餐,每逢星期日免费供应早餐。就餐者站在柜台前吃,而餐具都用铁链锁住。
[70]算命的认为“黑桃么”是不祥(也许是死亡)的预兆。
[71]原文作U?p:up。关于此词,众说纷坛。狄更新的《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第24章中,曾用来指一个老妪即将死亡。 这里根据这一解释并参照布林的具体情况而译。
[72]双关语:原文作the unfair sex。按the fair sex指女性,fair的意思是“美好”或“公正”。
[73]酥皮饼,原文作tart,也有荡妇之意。
[74]海豚仓,见第四章注[54]。哑剧字谜是一种室内游.戏,分两组,一组用手势或动作表示一句话或一个词,由另一组来猜。
[75]在第四章末尾处,曾提到布卢姆读菲利普?博福伊的小说《马查姆的妙举》。“马查姆……妙举”是小说中的词句。
[76]当天早晨布卢姆是坐在恭桶上读那篇小说的,眼下他在回忆曾否抽水把马桶冲干净了。
[77]指安德鲁?J?霍恩,他曾任爱尔兰皇家医学院副院长,当时(1904)是坐落在霍利斯街的国立妇产医院两位名医之一。
[78]据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365页),不论前文中为哈利作活广告的那五个人还是这里的法雷尔这个人物,都是乔伊斯早年或以后回来作短期逗留时,在都柏林街头所见。
[79]原文为依地语,又称“意第绪语”或“犹太德语”。中欧和东欧大多数犹太人的主要口语。
[80]阿尔夫雷德?柏根实有其人,死于一九五一或一九五二年。一九0四年他担任都柏林行政司法副长官助理。苏格兰屋是都柏林的一家酒吧。
[81]《爱尔兰时报》是都柏林一家日报。布卢姆曾在这家报纸上刊登过征求女助手的小广告,从而和玛莎?克利佛德通起信来。
[82]“我曾……香水”引自玛莎来信,与原信略有出入。参看第五章注[36]。
[83]莉齐?特威格是拉塞尔的一个女弟子,一九0四年出版过诗集《歌与诗》,署名伊利斯?尼?克拉欧伊布欣。
[84]詹姆斯?卡莱尔是《爱尔兰时报》经理兼社长。
[85]《爱尔兰狞猎报「是供乡绅消遣的周报,每逢星期六出版。
[86]拉思奥斯是位于都柏林西北二十五英里处一村落。狞猎开始前,先将关在笼中的狐狸释放出来,供狞猎者追捕。
[87]套用王尔德的戏剧《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第1幕中伊林沃思爵士的话。他认为猎狐乃是拼命追逐那“不能食用者”。
[88]“乔可决不要!”一语出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都柏林流行的一首歌曲。
[89]指五至六英尺高、不易越过的障碍物。
[90]这里布卢姆回想起当天上午他正想隔着马路欣赏一个妇女抬腿上马车时,被一个狮子鼻司机开的电车挡住视线的事。见第五章注[14]及有关正文。
[91]在后文中,老鸨贝洛提到了米莉亚姆?丹德拉德太太,见第十五章[585]及有关正文。
[92]截至一九0一年,亨利?G?斯塔布斯一直在凤凰公园当护林人。
[93]《每日快报》的简称,参看第七章注[59]。
[94]也译作美以美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一七三七年由约翰?卫斯理(1703-1791)创立。教徒组成小组,小组成员的绰号为“循道者”。
[95]“他……哲理”,这里套用《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中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给予哈姆莱特王子的评语。
[96]指教育农场产品公司。该公司所开设的店铺供应“有益健康的食品”和“无酒精饮料”。
[97]都柏林堡建于十三世纪,参看第六章注[1]。
[98]暗指年年生孩子。
[99]这是《伊索寓言》里的故事。一只狗自己不吃草,却钻进饲料槽里,不让马吃草。
[100]这是酒商安德鲁?罗依所开的酒馆。
[101]指伯顿旅店。该店设有餐厅及弹子房。
[102]指威廉?博尔顿公司在韦斯特莫兰街所开设的店,经售食品杂货茶叶及酒类。
[108]维多利亚女王共生过四男五女。一八五三年生子时,她接受了昏睡分娩法――一种半麻醉的无痛分娩法。
[104]“老婆婆……娃娃”出自英国一首摇篮曲。后两句为:“只给汤喝没面包,狠抽一顿送上床。”下面的“他”指艾伯特。实际上他死于伤寒病。
[105]这里,布卢姆把丹?道森文中的两句话拼凑在一起。参看第七章的两节:“爱琳,银海上的绿宝石”和“他的家乡土话”。
[106]按五分利把五镑存上二十一年,连本带利可获十三镑十八先令。
[107]据路易斯?海曼所著《爱尔兰的犹太人;早期至一九一0年》(香农出版社,1972)第190页,莫依塞尔太太及其丈夫尼桑?莫依塞尔(1814-1909)住在西伦巴德街或附近一带。他们的儿子埃尔雅?沃尔夫?莫依塞尔(1856-1904)之妻巴瑟,与摩莉同在一八八九牛六月生女。
[108]“快活的人儿”一语套用一首儿歌。第一句是:“老王科尔是个快活的人儿”。
[109]参看第六章注[176]。
[110]一八00年以后,这座大厦改为爱尔兰银行,但人们习惯于沿用旧称。
[111]珀西?阿普约翰是个虚构的人物,系布卢姆少年时代的伙伴。第十七章中提到他在南非战争(1899-1902)中阵亡。欧文?戈德堡是布卢姆在伊拉兹马斯?史密斯高中时的同学。系以往在该校附近一同名人为原型而塑造的。
[112]原文(mackerel)作为俚语,含有“男妓”或“拉皮条”之意。
[122]克里斯琴?鲁道夫?德威特(1854-1922),南非布尔人的将军,政治家。
[123]“我们要把……树上!”套用《约翰?布朗的遗体》歌中的一句。约翰?布朗(1800-1859)是美国废奴主义领袖,因领导奴隶起义,被绞死。这是在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军所唱的纪念约翰?布朗的歌。原词是:‘我们要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酸苹果讨上!”杰夫(即杰裴逊)?戴维斯(1808-1889)是美国南方联盟(1861-1865)唯一的一任总统。
[124]醋山岗在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科西。在一七九八年的民众起义中, 起义军的指挥部即设在这里。当年六月二十一日被英军击溃。爱尔兰民谣《韦克斯福德的男子汉》(参看第七章注[75])末段有“战败在醋山岗,我们准备再打一场仗……”之句。
[125]奶油交易所是个奶场场主的同业公会,在爱尔兰的几座城市中设有分会。都柏林分会拥有一支乐队。布卢姆正回忆的那次游行示威,该乐队也参加了。
[126]十九世纪末叶,爱尔兰各地区(都柏林除外)共有六十四名治安法庭长官。由于待遇好,被视为最理想的职业。
[127]语出自T?D?沙利文(1827-1914)所作《天主保佑爱尔兰》。最后三句是:“哪怕上高高的断头台,我们战死沙场也心甘,只要是为了亲爱的爱尔兰!”
[128]哈维?达夫是《少朗》(1874)中的一个乔装成农夫的密探。该剧作者为出生于爱尔兰的美国剧作家戴恩?鲍西考尔特(1822-1890)。
[129]詹姆斯?凯里,参看第五章注[69]。
[130]此处的汤姆是泛称,尤指下流的偷看者。
[131]此语系套用英国歌曲作者亨利?拉塞尔(1813-1900)的《好日子快要到来了》一歌。原词是:“好日子快要到来了,再稍微等一等吧。”
[132]詹姆斯?斯蒂芬斯(参看第二章注[54])所创立的芬尼社,组织严密,每十人分为一组,各有组长。组内也只有直线联系。
[133]指在“新芬”这一口号下从事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芬尼社(亦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新芬党的创立者格里菲思即为芬尼社社员(参看第三章注[108])。
[134]《看不见的手》(1864)是英国戏剧家汤姆?泰勒(1817-1880)所写的情节剧。在戏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用砒霜将人们一个个毒死。
[135]拉斯科是都柏林以北十一英里处的港口,濒临爱尔兰海。 斯蒂芬及其支持者从这里乘煤船驶到苏格兰,上岸后改乘火车抵伦敦,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王官饭店住了一宵,次日乘船经法国转往美国。
[136]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王宫。这里,布卢姆为了渲染,故意把皇宫饭店说成是白金汉宫饭店。
[137]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一八六0年组织红衫党,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次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为意大利的复兴和统一而进行宣传和战斗。
[138]俚语中,转义指家常便饭,毫不稀奇。一首民歌有“肥胖的家禽,丝毫不稀奇”之句。
[139]参看第七章注[200]。
[140]意指对爱尔兰的独立事业而言,复兴爱尔兰语言比建立独立的爱尔兰经济还重要。
[141]米迦勒节是基督教节日。 西方教会定于每年九月二十九日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此节日有食鹅肉的习俗,据说是为了保证来年生活富裕。
[142]凡是跟着救世军(成立于1865年)的乐队走街串巷, 表示自己悔改的,均能领到一个值一便士的面包卷。
[143]照基督教的说法,用羔羊的血可以赎罪。参看本章注[5]。
[144]面包洋葱被视为典型的奴隶伙食。
[145]迈克尔?柯万是都柏林的一个建筑承包人,他在凤凰公园东边为都柏林工匠住房公司盖了一批廉价房屋。
[146]乔治?萨蒙(1819-1904)曾任三一学院院长(1888-1902)。他的姓萨蒙(Salmon)与鲑鱼拼法相同。一九0四年,尼?特雷尔(1838-1914)继他之后被任命为院长。
[147]都柏林俚语,“装在罐子里”指富有。
[148]那一位指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参看第二章注[81])。他的弟弟约翰?霍华德?巴涅尔(1843-1923)自一八九五年起,任爱尔兰伦斯特省南米斯郡的下议院议员,一九0三年被希伊击败。这之后, 他改任都柏林市政典礼官兼典当商代理人。
[149]范妮(弗朗西斯的简称)?伊莎贝拉?巴涅尔(1849-1882) 曾协助其兄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从事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能力很强,并擅长演说。后赴美,写了一批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诗。
[150]迪金森太太,原名埃术莉?巴涅尔(1841-1918)。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死后,她写了一部关于她哥哥的传记《一个爱国主义者的错误》。(爱尔兰时报》评论说,此书应改题名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妹妹的错误》。
[l51]约翰?S?马德尔是都柏林圣文森特医院的外科医生。
[152]大卫?希伊(1844-1932),南米斯郡的下议院议员(1903-1918)。
[153]位于贝德福德与赫特福德之间的奇尔特恩山区(属白金汉郡), 原是强盗窝。后设置了管理员在该分区巡逻,才消除了这一隐患。但这一空缺一直留给那些失去下议院议员席位的人们。布卢姆把约翰?霍华德?巴涅尔担任典礼官比作当管理员这一闲职。
[154]橙带党(e Order) 是一七九五年成立于北爱尔兰的一个秘密团体,旨在支持新教。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凤凰公园聚会时,故意剥桔子(e)吃,以表示爱尔兰一旦取得了统一与独立,橙带党必将被吞没。这里,原文作Eating epeels(吃桔皮), 恰与爱尔兰警察制度的制定者罗伯特?奥林奇?皮尔的姓名在拼法上相同。所以这又是“吃掉警察制度制定者”的双关语。
[155]双头章鱼指英国。两个脑袋即英国的伦敦和苏格兰的爱丁堡。暗指它们正在扼杀爱尔兰的经济。
[156]胡子指诗人乔?拉塞尔(A?E?)。他留着胡子,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处活动,对农民发表演说,并组织他们参加合作社。
[157]“未来的事情有过前兆”一语出自托马斯?坎贝尔(1777-1844)所作歌谣《给洛奇尔下的预告》(1802)。
[158]A.E.看第三章注[109]。
[159]艾伯特?爱德华指爱德华七世。
[160]指亚瑟?埃德蒙?吉尼斯,参看第五章注[45]。
[161]阿方萨斯,见第十五章注[663]。埃比(Eb)是埃比尼泽(Ebenezer)的简称埃德(Ed)是埃德加(Edgar)或埃德华(Edward)的简称。埃利(El)是埃利阿斯(Elias)的简称。
[162]原文作Esquire,首字为E。
[163]拉塞尔一向穿手织布或手织呢衣服,以示他相信爱尔兰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其家庭手工艺大有潜力。
[164]拉塞尔是个素食主义者。
[165]气胀病是以食草料为主的牛羊常患的疾病。
[166]坚果排是将坚果磨成粉做成的,供素食主义者食用。
[167]十九世纪末素食主义者以为用苏打水煮菜可以保持原来的养分和色泽。一九一二年维生素被发现后,方知这样做足以破坏蔬菜所含的养分。
[168]这两句诗在后文中由宁芙引用,见第十五章注[655]。
[169]耶茨父子公司制造光学与数学仪器。
[170]据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230页注), 乔伊斯认识老哈里斯(约1823-1909)及其孙子们。据海曼的《爱尔兰的犹太人》(第148至149页),威廉?辛克莱(1882-1938)是老哈里斯的孙子。在祖父的坚持下, 他是被当作一个犹太人培养大的。下文中的戈埃兹是一家德国光学仪器厂。
[171]恩尼斯是爱尔兰克莱尔郡首府,也是该郡的主要铁路和公路枢纽。 一八八六年布卢姆的父亲死在这里。利默里克是爱尔兰利默里克郡的郡级市、港口和首府。在都柏林西南一二三英里、恩尼斯西南四十八英里处。
[172]关于这块表的传说流传甚广,但它是否存在,迄未得到证实。
[173]据德鲁伊特(参看本章注[6])说,这样做能检验一个人有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174]查尔斯?贾斯帕?乔利(1864-1904),三一学院天文学教授,邓辛克气象台台长。该台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对外开放一天。
[175]爱尔兰谚语。意思是:谦恭的人远比傲慢的人吃得开。
[176]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1749-1827)认为,地球也将像月球那样冷却下去,以致全部生命必然消灭殆尽。
[177]原文为法语,是一家专做大礼服的裁缝店。
[178]托尔卡是都柏林北边的一条小河,在费尔维尤(Fairview)注入都柏林湾。这一带经过填海拓地,有费尔维尤游s场之称。这是双关语。费尔维尤又作美景解。
[179]“五月的……宝贝”以及“萤光灯……宝贝”均出自托马斯?穆尔的《哦,英俊少年》一诗。
[180]原文must是双关语。既指“必须”, 又指(大象等在交尾期间的)狂暴状态。这里,布卢姆在回忆他们夫妇同去赏月时,博伊兰也在场。他当时已在怀疑妻子和博伊兰有暧昧关系,从而引起种种联想。
[181]鲍勃?多兰这个人物曾在《都柏林人?寄寓》中出现。
[182]原文为法语。
[188]哈普剧院是边就餐边欣赏歌舞表演的游艺场。后转让给詹姆斯?W?惠特布雷德,改为女王剧院。
[184]戴恩?鲍西考尔特(1822-1890),为出生于都柏林的剧作家、演员。他凭看深刻的幽默感弥补了演技之不足。一八七二年移居美国。
[185]《三个俊俏姑娘放学了》是英国作曲家沙利文与吉尔伯特合作的轻歌剧《天皇》(1885)中的插曲。
[186]“摘下那顶白帽子”是穆尔与伯吉斯乐队所作滑稽演出中的一个噱头。
[187]“那把……挨饿”,套用托马斯?穆尔所作的《那把竖琴曾越过塔拉大厅》一歌。自古以来竖琴是爱尔兰的象征。
[188]据约翰?亨利?雷利所著《利奥波德与摩莉?布卢姆纪年:故事体的〈尤利西斯〉》(加州柏克利,1977),布卢姆生于一八六六年二月至五月之间,摩莉生于一八七0年九月八日。他们是一八九四年从西伦巴德街搬走的, 参看本书第十七章。
[189]按这条街是用花岗岩铺的。
[190]“事业……的”、“嗒啦……嘣”,原文均为意大利语。 这里,布卢姆站在橱窗前忽然想起《胡格诺派教徒》(1836)中的这些台词。该歌剧系一八一六年起定居于意大利的德国歌剧作曲家贾埃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 用德文所写。但十九世纪末叶,歌剧一般都用意大利语演唱。布卢姆忽何看见橱窗里有“绸子得用雨水来洗”的说明,想到雨水不含矿物,水质软。
[191]民间有一种迷信,认为如果一个姑娘捡起一根针、就会断送与原来男友之间的爱情,必须另交男友。
[192]雅法与移民垦殖公司,参看第四章注[23]、[24]
[193]指出售版画并配制镜框的剑桥公司。
[194]“用别人……自己”,套用罗伯特?彭斯的《致虱子:在教堂里一个女人的帽子上所见》(1786)。
[195]博因河在爱尔兰基尔代尔郡。博因河谷附近有塔拉山。
[196]科麦克王(约254-约277在位)是爱尔兰的开国元勋, 建郡于塔拉山。他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以致惹怒了德鲁依特(参看本章注[6]), 故意让他吞食大马哈鱼刺因而被卡死。圣帕特里克是四三二或四三三年才到爱尔兰来传教的, 当时的爱尔兰国王莱格海尔在塔拉宫接见了他。国王本人并未改信基督教,却答应不阻挠圣帕特里克的传教活动,所以这里说是“未能全盘接受”。布卢姆的记忆与史实不相符。
[197]这里是借哈姆莱特王子对母后说的话来形容人们的吃相。王子叫母后把先王(她的前夫)的肖像跟现在的国王克劳狄斯(她的第二个丈夫)的肖像相比。见《哈姆莱特》第3幕第4场。
[198]当一个小孩用手抓饭菜时,大人常挖苦说:“你要是有三只手就好啦。”
[199]后文中,本?多拉德曾提及此人,见第十章注[170]及有关正文。
[200]指都柏林市芒斯特[与伦斯特]银行。
[2Ol]“每一个母亲的儿子”出自《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中众人回答波顿的话。
[202]菲利普“克兰普顿爵士(参看第六章注[27])的雕像下面有座喷泉,那里备用的杯子与都柏林市政府所发给的一样。
[203]前面的“别提……院长”和这里的“弗林……无知”均出自艾尔弗雷德?珀西瓦尔?格雷夫斯(1846-1879)的《奥弗林神父会揭露他们大家的愚昧无知》(1879)一书。
[204]凤凰公园在一九0四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
[205]原文为法语。
[206]原文作bob,指未满月的小牛崽,照规定不许宰食,但仍避免不了被宰的命运。
[207]“刚砍……骨头”是爱尔兰民间故事里的妖魔鬼怪的形象。这两段使人联想到奥德修在阴府里遇见亡灵们的情景。他们得先喝坑里那乌黑的血,才能说话。见《奥德修纪》卷ll。
[208]大鼻子弗林是《都柏林人?无独有偶》里的一个人物。大鼻子是他的绰号,原文作Nosey,也含有好打听闲事之意。
[209]勃艮第葡萄酒产于法国中东部勃艮第地区,有红白二种,红的甘醇浓郁。[210]这里套用C?C?勃姆鲍所编《文学沃野拾遗,供好奇者鉴赏》(费城?1890)中的一首滑稽诗。该诗有“哈姆一族在那里聚集并繁衍生息”之句,这里改为:哈姆和他的后代在那里聚集并繁衍生息。(Ham and his desdant smusterred and bred there)。哈姆(Ham旧译为含)是《创世记》中挪亚的第二个儿子,与火腿同音,而desdants既作后代解,也作派生物解,musterred(聚集)与muslard(芥末)、bred(繁衍生息)与bread(面包)读音都近似,全句语意双关。
[211]“倘若……不足”和“有它……窝”均参看第五章注[18]及有关正文。
[212]爬上了李子树含有被逼入绝境之意。
[213]据《马太福音》第2章:由于星相家预言基督长大后要作犹太人的王, 希律王为了杀害他,而“派人把伯利恒和附近地区两岁以内的男孩子都杀掉。”天主教把十二月二十八日定为屠杀无辜婴儿纪念日。
[214]“吃啊,喝唱,快活一场”一语出自《旧约?传道书》第8章第15节。
[2l5]制造奶酪时使用晒干的小牛皱胃的内膜,所以十六世纪以来就有人说制造奶酪乃是消化的过程。奶酪上寄生着微小的螨,凡是它爬过之外,都留下一层粉状褐色外皮。
[216]套用英国作家约翰?泰勒(1580-1653)语。原为:天主送来了食物,魔鬼送来了厨子。“(《约翰?泰勒全集》)
[217]这是文字游戏。原文里,魔鬼是devil,而辣子螃蟹则是devilledcrab;devil与devilled读音相近。
[218]戈尔贡佐拉是意大利伦巴第区一城镇,以产奶酪著称。
[219]杰克?穆尼是鲍勃?多兰的内弟,这个人物曾在《都柏林人?寄寓》中出现。
[220]《自由人报》(1904年4月28、29日)曾登出广告说,军民之间将于四月二十九和二十两天进行拳击比赛。在二十九日的比赛中,基奥击败了第六龙旗兵团的加里。这里,乔伊斯把日期改为五月二十二日,将加里改成英国炮队的军士长珀西
?贝内特。贝洛港营盘是位于都柏林郊外的英国兵营。
[221]卡洛郡属爱尔兰伦斯特省。位于都柏林西南五十英里处。
[222]这是从剧《玛丽塔娜》(参看第五章注[104])中唐乔斯的唱词。
[223]欧洲防风根抹黄油是一道佳肴。抹了过多的质量次于黄油的大油,有假情假义意。
[224]洋苏木是豆科乔木,原产中美和西印度群岛。木材硬重,能从树心里提取一种同名黑色染料。
[225]埃普瑟姆-尤厄尔的简称。这是英国萨里郡的一区,位于伦敦西侧。一七三0年起盛行赛马。每逢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著名的埃普瑟姆赛马会。
[226]这是一句谚语的上半句。下半句为“相处不长”。
[227]赖尔登老太太,见第六章注[69]。
[228]斯凯i狗是苏格兰斯凯岛上产的一种i狗。
[229]原文为德语,意思是保持忠诚街。
[230]布卢姆想起当天早晨他曾瞧见博伊兰呆在红岸餐馆外面的事。
[231]指英语里,五、六、七、八这四个月没有“r”字。这期间牡蚜的味道不好,只宜在有“r”字的八个月中吃。
[232]巴伐利亚国王奥托一世(1848-1916)自一八七二年起发疯,于一八八六年即位,同年由大公爵利奥波德?封?巴耶恩(1821-1921)摄政。
[283]哈布斯堡王室是欧洲最大的王室之一,一O二O年建于今瑞士阿尔高州。其后裔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有个侄子名奥托。
[234]、[237]原文为法语。
[235]英王爱德华二世(1307-1327在位)曾宣布英国海域内的鲟鱼,概由王室享用。
[236]指安德鲁?马歇尔?波特爵士(1887-1919),一八八三至一九O七年间任爱尔兰高等法院法官。
[238]这是法国名菜。把鸭子浸泡在白兰地里,点燃后端上餐桌。
[239]“帕……式”,原文为法语。将牛肉末、香草、面包屑填入包心菜卷,烤熟而食。
[240]关在笼子里填喂的鹅,其肝格外肥大,宜用来做肥鹅肝饼。
[241]雷鸟是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一种松鸡类的鸟。
[242]据一八九四年二月二日的《自由人报》,杜比达特小姐曾在詹姆斯?W?惠特布雷德经营的女王皇家剧院演唱过《到基尔代尔去》。
[243]基利尼是都柏林以南的一个工业城市,濒临爱尔兰海。
[244]Du是dule(加在阴性名词前即为dela)的缩写,系法语的前置词(表示所属关系),相当于英语的ofthe(“……的”、“属于……的”)。
[245]这里描述老人一面在嘴里拼音,一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迈克尔(Michael)的那副神态。米基是迈克尔的简称。
[246]西方形容笨蛋为脑子长在脚上。一大筐翻毛生皮鞋,喻不知更要愚蠢多少倍。
[247]“紧紧膘在一块儿”一语,在后文中又用来形容博伊兰和摩莉,见第十五章注
[712]。下段中提到的霍斯,见第三章注[58]。
[248]指撒有芬香种子(如芝麻等)的糕饼。前面的“真好吃”一语,当天夜里又由莉迪亚?杜丝嘴里说出来,见第十五章注[7l3]。
[249]一种平纹薄毛呢,起初用来做修女披的头纱,故名。现在也用做衣料。
[250]据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他也是位雕刻家、 并爱上了他手雕的一座女性象牙雕像加拉蒂亚。后来女神让它变为活人,并与皮格马利翁结为夫妻。从罗马诗人奥维德到本世纪的萧伯纳,都曾在作品中采用这一题材。
[251]奥尔索普指都柏林的奥尔索普父子酿酒公司所生产的廉价瓶装啤酒。
[252]“食物……食物”这里套用乔达诺?布鲁诺在《关于原因、原则和一》(参看第二章注[86])中所阐述的物质循环不已的繁殖过程。
[253]指女神们没有肛门。
[254]在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中,维纳斯像男人追求女人那样来向阿都尼求爱。参看张谷若译文第6行:“拼却女儿羞容,凭厚颜,要演一出凰求凤。”第42行:“爱既无法使他就范,她就用力把他控制。”
[255]此句后面,本书海德一九八九年版(第145页倒12行)有“他还是名出色的会员呢”之句。
[256]共济会(参看第五章注[8])分会将成员划为三个主要等级:学徒、师兄弟、师傅。该会吸收过几名妇女。伊丽莎白?奥尔沃思(?-1773)是最早的一人。 她是第一任唐奈赖尔子爵阿瑟?圣莱杰的独女。据说她十七岁时,家里召开共济会的会议,给她撞见了。为了保守秘密,就让她入了会。尤金?伦赫夫所著《共济会》 (纽约?1934)一书中刊有她的画像。
[257]汤姆?罗赤福特是以一个搭救过下水道工人的同名工程师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参看第十章注[107]。
[258]这是双关语。英文standing一词,既可作“站看”(与“坐”相反)解,又可作“做东”(“请客”)解。这里,大鼻子弗林故意把它理解为前者。
[259]那个人指布卢姆。参看第五章注[96]及有关正文。
[260]在特定条件下,使一立方厘米空气产生一静电单位正或负离子的电离的辐射量为一伦琴,以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封?伦琴的姓氏命名。
[261]罗赤福特的发明,参看第十章注[103]及有关正文。
[262]原文为意大利语。这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1787年首演)中被杀死的骑士长亡灵的唱词。
[263]意大利语,意思是“今晚同你”。下面的“teco”是“同你”。
[264]布卢姆先用意人利语唱了一句,接着又用英语来唱,因而失去了原作的韵味,所以这里说不对头。
[265]在本书末尾,摩莉想到了布卢姆拉比利?普雷斯科特的广告事。参看第十八章。
[266]布赖顿位于伦敦以南五十一公里处,为英吉利海峡的海滨胜地。
[267]马盖特是英国肯特郡一城镇,位于泰晤士河口湾南面。十八世纪以来成为闻名的海滨浴场。
[268]《我为什么脱离了罗马教会》(伦敦,1883) 是查尔斯?帕斯卡尔?特勒斯弗尔?奇尼其(1809-1899)所写的小册子。他于一八三三年当上天主教神父,一八五八年皈依新教,成为加拿大长老会牧师。
[269]“鸟窝会”是个新教传道会,收养着一百七十名穷孩子。
[270]指附属于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伦敦公会的爱尔兰教会。
[271]意思是说,从公牛后面和马前面走才安全。因为公牛喜用犄角顶,马好尥蹶子。
[272]彭罗斯,参看本章注[62]。
[273]期图尔特医院是专门收留弱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的医院。
[274]据《自由人报》(1904年6月16日)、在美国的德国圣马丁路德教会主日学校当天组织一次乘汽船(“斯洛克姆将军”号)游览的活动。结果船在纽约港起火,烧死一O三O人,大部分是妇孺。
[275]“业”是佛教名词,系梵文karman(羯磨)的意译。佛教认为业发生后不会消除。它将引起善恶等报应。
[276]“遇见了他尖头胶皮管”,参看本章注[37]及有关正文。
[277]弗雷德里克?福基纳爵士(1831-1908),都柏林市记录法官(1876-1905),参看第七章注[158]。他曾任慈善学校(原名“蓝衣学校”)董事,并著有《文学杂记:慈善学校史;法院与巡回裁判的故事》(1909)。
[278]都柏林天主教大主教约翰?托马斯?特洛伊(1739-1828)曾对 一七九八年的起义发出过“庄严的声讨”。从那以后,人们总把他的名字和“庄严”一词联系在一起。
[279]“愿……魂”是审判长对被判死刑者说的套语。
[280]麦拉斯义卖会其实是在一九0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举办的。小说中为了行文方便,把日期移到六月十六日。
[281]《弥赛亚》是德国作曲家亨德尔(1685-1759)所作最为脍炙人口的圣乐,一七四二年四月十三日在都柏林首演,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282]他,指布莱泽斯?博伊兰。
[283]托马斯?迪恩爵士(1792-1871),爱尔兰建筑家,曾设计过三一学院博物馆(1857)和科克市以及其他城市的重要建筑物。
第九章 1
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公谊会教徒[1]-图书馆长文质彬彬地轻声说道:
“球门不是还有《威廉·迈斯特》那珍贵的篇章吗?一位伟大的诗人对另一位弟兄般的大诗人加以论述。[2]一具犹豫不决的灵魂,被相互矛盾的疑惑所撕扯,挺身反抗人世无边的苦难[3],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
他踏着橐橐作响的牛皮鞋[4],跳着五步舞[5]前进一步,又跳着五步舞[6],在肃穆的地板上后退一步。
一名工役悄悄地把门开了个缝儿,默默地朝他做了个手势。
“马上就来,”他说,踏着橐橐作响的鞋正要走开,却又踟蹰不前。“充满绮丽幻想而又不实际的梦想家,面临严峻的现实,就只有一败涂地。[7]我们读到这里,总觉得歌德的论断真是对极了。他的宏观分析是正确的。”
像是听了倍加响亮的分析,他踩着“科兰多”舞步[8]走开了。歇顶的他,在门旁耸起那双大耳朵,倾听着工役的每一句话,然后就走了。
只剩下两个人。
“德·拉帕利斯先生,”斯蒂芬冷笑着说,“直到死前一刻钟还活着。[9]”
“你找到那六个勇敢的医科学生了吗?”约翰·埃格林顿[10]以长者的刻薄口气问道,“好叫他们把《失乐园》[11]笔录下来。他管这叫作《魔鬼之烦恼》。[12]”
微笑吧。露出克兰利[13]微笑吧。
起初他为她搔痒,
接着就抚摩她,
并捅进一根女用导尿管。
因为他是个医科学生,
爽朗快活的老医……
“倘若是写《哈姆莱特》的话,我觉得你还需要再添上一个人物。对神秘主义者来说,七是个可贵的数字。威·巴把它叫作灿烂的七。[14]”
他目光炯炯,将长着赤褐色头发的脑袋挨近绿灯罩的台灯,在暗绿的阴影下,寻觅着胡子拉碴的脸——长着圣者的眼睛的奥拉夫般的脸。[15]他低声笑了。这是三一学院工读生[16]的笑。没有人理睬他。
管弦乐队的魔鬼痛哭,
淌下了天使般的眼泪。[17]
然而他以自己的屁股代替了号筒。[18]
他抓住我的愚行当作了把柄。
克兰利手下那十一名土生土长的威克洛[19]男子有志于解放祖国。豁牙子凯思林,她那四片美丽的绿野,她家里的陌生人。[20]还有一个向他致意的:“你好,拉比。[21]蒂那依利市[22]的十二个人。在狭谷的阴影下,他吹口哨吆唤他们。一个又一个夜晚,我把灵魂的青春献给了他。祝你一路平安。好猎手。[23]
穆利根收到了我的电报。[24]
愚行。一不做,二不休。
“咱们爱尔兰的年轻诗人们,”约翰·埃格林顿告诫说,“还得塑造出一位将被世人誉为能与萨克逊佬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相媲美的人物。尽管我和老本[25]一样佩服他,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这些纯粹属于学术问题,”拉塞尔从阴影里发表宏论。“我指的是哈姆莱特究竟是莎士比亚还是詹姆斯一世[26],抑或是艾塞克斯伯爵[27]这样的问题,就像是由教士们来讨论耶稣在历史上的真实性一样。艺术必须向我们昭示某种观念——无形的精神真髓[28]。关于一部艺术作品首要的问题是:它究竟是从怎样深邃的生命中涌现出来的。古斯塔夫·莫罗[29]的绘画表达了意念。雪莱最精深的诗句,哈姆莱特的话语,都能够使我们的心灵接触到永恒的智慧,接触到柏拉图的观念世界。其他左不过是学生们之间的空想而已。”
A·E·曾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这么说过。[30]唉,该死的!
“学者也得先当学生呀,”斯蒂芬极其客气地说,“亚理斯多德就曾经是柏拉图的学生。”
“而且他始终是那样,像我们所希望的,”约翰·埃格林顿安详地说,“我们仿佛总可以看到他那副腋下夹着文凭的模范生的样子。”
他又朝着现在正泛着微笑的那张胡子拉碴的脸,笑了笑。
无形的精神上的。父,道,圣息。万灵之父,天人[31]。希稣斯·克利斯托斯[32],美的魔术师,不断地在我们内心里受苦受难的逻备斯[33]。这确实就是那个。我是祭坛上的火。我是供牺牲的黄油。[34]
邓洛普[35],贾奇[36],在他们那样人当中最高贵的罗马人[37],A·E·阿尔瓦尔[38],高高在天上的那个应当避讳的名字:库·胡·[39]——那是他们的大师,消息灵通人士都晓得其真实面目。大白屋支部[40]的成员们总是观察着,留意他们能否出一臂之力。基督携带着新娘子修女[41],润湿的光,受胎于圣灵的处女,忏悔的神之智慧[42],死后进入佛陀的境界。秘教的生活不适宜一般人。芸芸众生必须先赎清宿孽。库珀·奥克利夫人[43]有一次瞥见了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姊妹海·佩·勃的原始状态。
哼!哼!呸!呸![44]可耻,冒失鬼![45]你不应该看,太太。当一个女人露出原始状态的时候,那是不许看的。
贝斯特[46]先生进来了。个子高高的,年轻,温和,举止安详。他手里文雅地拿着一本又新又大、洁净而颜色鲜艳的笔记本。
“那个模范学生会认为,”斯蒂芬说,“哈姆莱特王子针对自己灵魂的来世所作的冥想,那难以置信、毫不足取、平淡无奇的独白,简直跟柏拉图一样浅薄。”[47]
约翰·埃格林顿皱起眉头,怒气冲冲地说:
99lib.“说实在的,一听见有人把亚理斯多德跟柏拉图相比较,我就气炸了肺。”
“想把我赶出理想国的,”斯蒂芬问,“是他们两个当中的哪一个呢?”[48]
亮出你那匕首般的定义吧。马性者,一切马匹之本质也。他们崇敬升降流和伊涌[49]。神:街上的喊叫。逍遥学派[50]味道十足。空间:那是你非看不可的东西。穿过比人血中的红血球还小的空间,追在布莱克的臀部后面,他们慢慢爬行到永恒。这个植物世界仅只是它的影子。[51]紧紧地把握住此时此地,未来的一切都将经由这里涌入过去。[52]
贝斯特先生和蔼可亲地走向他的同僚。
“海恩斯走掉啦,”他说。
“是吗?”
“我给他看朱班维尔[53]的书来着。要知道,他完全热衷于海德的《康诺特情歌》。我没能把他拉到这儿来听听大家的议论,他到吉尔书店买这本书去了。”
我的小册子,快快前去,
向麻木的公众致意,
写作用贫乏寒伦的英语,
决不是我的原意。[54] “泥炭烟上了他的大脑,”约翰·埃格林顿议论道。
我们英国人觉得……[55]悔悟的窃贼。[56]走掉啦。我吸了他的纸烟。一颗璀璨的绿色宝石。镶嵌在海洋这指环上的绿宝石。[57]
“人们不晓得情歌有多么危险,”金蛋[58]拉塞尔用诡谲的口吻警告说,“在世界上引起的革命运动,原是在山麓间,在一个庄稼汉的梦境和幻象中产生的。 对他们来说,大地不是可供开拓的土壤,而是位活生生的母亲。 学院和街心广场那稀薄的空气会产生六先令一本的小说和沸艺场的小调。法国通过乌拉梅[59]创造了最精致的颓废之花,然而惟有灵性贫乏者[60],才能获得理想生活的启迪。比方说荷马笔下的腓依基人的生活。”
听罢这番话,贝斯特先生将那张不冲撞人的脸转向斯蒂芬。 “要知道,乌拉梅写下的那些精彩的散文诗,”他说,“在巴黎的时候,斯蒂芥·麦克纳[61]常朗读给我听。有一首是关于《哈姆莱特》的。[62]他说: 他边读一本写他自己的书,边漫步。[63]要知道:边读一本写他自己的书。他描述了一个法国镇子上演《哈姆莱特》的情景。要知道,是内地的一个镇子。他们还登了广告。”
他用那只空着的手优雅地比比画画,在虚空中写下小小的字:
哈姆莱特
或者
心神恍惚的男子
莎士比亚的剧作[64]
他对约翰·埃格林顿那再一次皱起来的眉头重复了一遍:
“要知道,莎士比亚的戏剧[65]哩。法国味十足。法国人的观点。哈姆莱特或者……[66]”
“心神恍惚的乞丐[67],”斯蒂芥替他把话结束了。
约翰·埃格林顿笑了。
“对,依我看就是这样,”他说,“毫无疑问,那是个优秀的民族,可在某些事物上,目光又短浅得令人厌烦。”[68]
豪华而情节呆板、内容夸张的凶杀剧。[69]
“罗伯特·格林曾称他作‘灵魂的刽子手’[70],”斯蒂芬说,“他真不愧为屠夫的儿子,[71]在手心上啐口唾沫,就抡起磨得锃亮的杀牛斧。[72]为了他父亲这一条命,葬送掉了九条[73]。我们在炼狱中的父亲。[74]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哈姆莱特们毫不迟疑地开枪。[75]第五幕那浴血的惨剧[76]乃是斯温伯恩先生在诗中歌颂过的集中营的前奏[77]。”
克兰利,我是他的一名沉默寡言的传令兵,离得远远地观望着战斗。
对凶恶敌人之妇孺,
只有我们予以宽恕……
夹在萨克逊人的微笑与美国佬的饶舌之间。魔鬼与深渊之间。
“他想把《哈姆莱特》说成是个鬼怪故事,”约翰·埃格林顿替贝斯特先生解释说,“像《匹克威克》里的胖小子似的,他想把我们吓得毛骨悚然。[78]
听着,听着,啊,听着![79]
我的肉身倾听着他的话,胆战心惊地听着。
要是你曾经……[80]
“什么是鬼魂?”斯蒂芬精神抖擞地说,“那不外乎就是一个人由于死亡,由于不在,由于形态的变化而消失到虚无飘渺中去。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与斯特拉特福[81]相距之远,一如今天堕落的巴黎之于纯洁的都柏林。谁是那个离开了幽禁祖先的所在[82]而返回到己把他遗忘了的世界上来的鬼魂呢?谁是哈姆莱特王呢?”
约翰·埃格林顿挪动了一下他那瘦小的身躯,向后靠了靠,在做出判断。
情绪激昂了。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就在这个时辰,”斯蒂芬迅疾地扫视了大家一眼,好让人们注意倾听他的话,“河滨的剧场升起了旗子。旁边的巴黎园里,萨克逊大熊在栏中吼叫着。跟德雷克一道航过海的老水手们,混在池座的观众当中,嚼着香肠。[83]”
地方色彩。把自己晓得的统统揉进去。让他们做同谋者。
“莎士比亚离开了西尔弗街那所胡格诺派教徒的房子,沿着排列在河岸上的天鹅槛定去。然而他并不停下脚步来喂那赶着成群小天鹅朝灯心草丛中走去的母天鹅。埃文河的天鹅[84]别有心思。”
场子的构图。[85]依纳爵·罗耀拉啊,赶快来帮助我吧!
“戏开台了。一个演员从暗处[86]踱了过来。他身披宫廷里哪位花花公子穿剩的铠甲,体格魁悟,有着一副男低音的嗓子。这就是鬼魂,是国王,又不是国王,[87]演员乃是莎士比亚。[88]他毕生的岁月不曾虚度,都倾注在研究《哈姆莱特》上了,以便扮演幽灵这个角色。他隔着绷了一层蜡布[89]的架子,呼唤着站在自己对面的年轻演员伯比奇[90]的名字:
哈姆莱特。啊,我是你父亲的阴魂……[91]并吩咐他听着。他是对儿子,自己的灵魂之子——王子,年轻的哈姆莱恃——说话;也对内身之子哈姆奈特[92]·莎士比亚说话——他死在斯特拉特福,以便让他的同名者获得永生。”
身为演员的莎士比亚,由于外出而做了鬼魂,身穿死后做了鬼魂的墓中的丹麦先王的服装[93],他可不可能就是在对亲生儿子的名字(倘若哈姆奈特·莎士比亚不曾夭折,他就成为哈姆莱特王子的双生兄弟了),说着自己的台词呢?我倒是想知道,他可不可能,有没有理由相信:他并不曾从这些前提中得出或并不曾预见到符合逻辑的结论:你是被废黜的儿子,我是被杀害的父亲,你母亲就是那有罪的王后,[94]娘家姓哈撒韦的安·莎士比亚?
“但是像这样来窥探一个伟大人物的家庭生活,那可……”拉塞尔不耐烦地开了腔。
你在那儿吗,老实人?[95]
“只有教区执事才对这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剧本在手。也就是说,当我们读《李尔王》的诗篇时,该诗作者究竟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干我们什么事?维利耶·德利尔曾说,我们的仆人们可以替我们活下去。[96]窥视并刺探演员当天在休息室里的飞短流长:诗人怎么酗酒啦,诗人如何负债啦。我们有《李尔王》,而那是不朽的。”
这话是说给贝斯特先生听的,他露出赞同的神色。
用你的波浪,你的海洋淹没他们吧,
马南南啊,马南南·麦克李尔……[97]
喂,老兄,你饿肚子的时候他借给你的那一镑钱哪儿去啦?[98]
哎唷,我需要那笔钱来着。
把这枚诺布尔[99]拿去吧。
去你的吧!你把大部分钱都花在牧师的女儿乔冶娜·约翰逊[100]的床上啦。内心的呵责。
你打算偿还吗?
嗯,当然。
什么时候?现在吗?
喏……不。
那么,什么时候?
我没欠过债。我没欠过债。
要镇定。他是从博伊恩河彼岸来的。在东北角上。[101]你欠了他钱。
且慢。已经过了五个月。分子统统起了变化。现在的我已换了个人。钱是另外那个我欠下的。
早过时啦![102]然而我,生命原理,形态的形态,由于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记忆之中,我恢然是我。[103]
我,曾经犯过罪,祈祷过,也守过斋戒。
康米从体罚中拯救过的一个孩子。[104]
我,我和我,我。
A·E·I·O·U·
“难道你想违反已经延续了三个世纪的传统吗?”约翰·埃格林顿用吹毛求疵的腔调问道,“至少她的亡灵已永远安息了。至少就文学来说,她还没出生之前就已去世。”
“她是在出生六十七年之后去世的,”斯蒂芥反驳说,“她看到他出世,以及离开人间。[105]她接受了他第一次的拥抱。她生下了他的娃娃们。在他弥留之际,她曾把几枚便士放在他眼睑上,好让他瞑目。”
母亲临终卧在床上。蜡烛。用布单罩起来的镜子。把我生到这世上的人躺在那里,眼睑上放着青铜币,在寥寥几朵廉价的花儿下。饰以百合的光明……[106]
我独自哭泣。
约翰·埃格林顿瞧着他那盏火苗纠缠在一起发出萤光的灯。[107]
“世人相信莎士比亚做错了一件事,”他说,“并尽快她用最巧妙的办法脱了身。”[108]
“那是胡扯!”斯蒂芬鲁莽地说,“天才是不会做错事的。他是明知故犯,那是认识之门。”
认识之门打开了,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走了进来,脚下的鞋轻轻地吱吱响着。他已歇顶,竖起耳朵,兢兢业业。
“很难想像,”约翰·埃格林顿卓有见识地说,“泼妇会是个有用的认识之门。苏格拉底从赞蒂贝[109]身上又认识到了什么呢?”
“辩证法[110]嘛,”斯蒂芬说,“还从他母亲那儿学会了怎样把思想带到人间。[111]他从另一个老婆默尔托[112](名字是无所谓的![113])——也就是说,‘好苏格拉底[114]的灵魂的分身[115]’——那儿学到了什么,任何男人或女人都永远不得而知。然而‘助产术’也罢,闺训[116]也罢,都末能从新芬党[117]的执政官与他们那杯毒芹下救他一命。[118]”
“可是安·哈澈韦呢?”贝斯特先生像是心不在焉似地以安详的口吻说,“是啊,我们好像忘记了她,正如莎士比亚本人也把她遗忘了。”
他的视线从冥思着的那个人的胡子扫到吹毛求疵者的脑壳,宛若在提醒他们,和颜悦色地责备他们,然后又转向那尽管无辜却受到迫害的罗拉德派[119]那粉红色的秃脑袋。
“他颇有点儿机智,”斯蒂芬说,“记忆力也不含糊。当他用口哨吹着《我撇下的姑娘》[120],朝罗马维尔[121]吃力地走着的时候,他的行囊里就装有记忆。即便那场地震不曾记载下来[122], 我们也应知道,该把蹲在窝里的可怜的小兔,猎犬的吠声,镂饰的缰绳,她那蓝色的窗户,[123]放在他一生的哪个时期。《维纳斯与阿都尼》中所描绘的那番记忆[124], 存在于伦敦每个荡妇的寝室里。悍妇凯瑟丽娜[125]长得丑吗?霍坦西奥说她又年轻又漂亮。难道你以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作者,一个热情的香客[126], 两眼竟长在脑后,单挑沃里克郡最丑的淫妇来跟自已睡觉吗?不错,他撇下了她,而获得了男人的世界[127]。然而由男童所扮演的女角儿们[128]是从一个男童 [129] 眼中看到的女人们。她们的生活、思想、语言,都是男人所赋予的。 难道他没选好吗?我觉得毋宁说他是被选的。[130]倘若其他女人能够从心所欲[131],安自有她的办法。[132]的的确确,她该受责难。[133]是她这个二十六岁的甜姐儿[134]对他进行引诱的。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135],灰眼女神[136]伏在少年阿都尼身上,屈就取胜。这就是厚脸皮的斯特拉特福荡妇,她曾把比自己年轻的情人[137]压翻在麦田里[138]。”
轮到我?什么时候?
来吧!
“裸麦地,”贝斯特先生欣喜快活地说,并且欣喜地、快活地高举着他那本新书。
然后,他喃喃地吟诵起来;那头金发使大家赏心悦目。
裸麦地的田垄间,
俊俏乡男村女眠。[139]
帕里斯,陶醉了的诱惑者。[140]
身穿毛茸茸的家织布衣的高个子[141]从阴影里站起来,掀开了他从合作社头来的怀表的盖子。
“看来我得到《家园报》去啦。”
去哪儿?到可开拓的土地上去。
“你要走了吗?”约翰·埃格林顿挑起眉毛问,“今儿晚上咱们在穆尔[142]家见面,好吗?派珀[143]要来哩。”
“派珀!”贝斯特先生尖声说,“派珀回来了吗?”
彼得·派珀噼噼啪啪地一点点挑选着啄食盐汁胡椒。[144]
“这就难说了。这是星期四嘛,我们还有会呢,要是我能及时脱身的话……”
道森套房里那间通神学家们的瑜伽魔室[145]。《揭去面纱的伊希斯》。[146]我们曾试图把他们这本巴利语[147]著作送进当铺。在暗褐色华盖的遮阴下,他盘腿坐在宝座上;在星界发挥机能的阿兹特克族的逻各斯[148],他们的超灵[149],大我[150]。已够入门资格的虔诚的秘义信徒们环绕着他,等待着启示。路易斯·H·维克托里[151]。T·考尔菲尔德·艾尔温[152]。莲花净土的少女们不断地注视着他们。[153]他们的松果体[154]熠熠发光。他内心里充满了神,登上宝座。芭蕉树下的佛陀。[155]吞入灵魂者,吞没者。[156]他的幽魂,她的幽魂,成群的幽魂。[157]他们呜呜哀号,被卷入漩涡,边旋转,边痛哭。[158]
万物精髓之琐事,
肉牢经年女魂栖。[159]
“他们说在文艺方面将有一桩惊人之举,”公谊会教徒一图书馆长友好而诚挚地说,“听说拉塞尔先生正在把我们年轻诗人的作品收成集子。[160]大家都在翘首企盼着哪。”
他借那圆锥形的灯光热切地扫视着。在灯光映照下,三张脸发着亮。
看吧,并且记在脑子里。
斯蒂芬俯视着横挂在他膝头的那根梣木手杖柄上的宽檐平顶帽。我的盔和剑。用两根食指轻轻地摸一下。亚理斯多德的试验。一个还是两个?必然性就在于此。人只能是自己,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161]所以,一顶帽子就是一顶帽子。[162]
听着。[163]
年轻的科拉姆和斯塔基[164]。乔治·罗伯茨[165]负责商务方面。朗沃思[166]会在《快邮报》上把它大棒一通的。噢,他会吗?我喜欢科拉姆的《牲畜商》。对,我认为他具有那种古怪的东西——天才。你认为他真有天才吗?叶芝曾赞美过他这句诗:宛如一只埋在荒漠中的希腊瓶。[167]是吗?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来。玛拉基·穆利根也要来的。穆尔托他把海恩斯带来。你听到过米切尔小姐讲的关于穆尔和马丁的笑话吗?她说,穆尔是马丁的浪荡儿。[168]讲得真是巧妙,令人联想到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西格尔逊博士[169]说,我们民族的史诗至今还没写出来。穆尔正是适当的人选。他是都柏林这里的一位愁容骑士[170]。奥尼尔·拉塞尔[171]穿一条桔黄色百褶短裙[172]吗?啊,对,他一定会讲庄重的古语。还有他那位杜尔西尼娅[173]呢?詹姆斯·斯蒂芬斯[174]正在写俏皮的小品文。看来我们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考狄利娅。考德利奥。李尔那最孤独的女儿。[175]
偏僻荒蛮。现在该上你最拿手的法国磨光漆了。[176]
“非常感谢你,拉塞尔先生,”斯蒂芬边站起身来边说,“劳驾请把这封信交给诺曼先生……”
“啊,好的。假若他认为这重要,就会刊用的。我们的读者来稿踊跃极了。”
“我知道,”斯蒂芬说,“谢谢啦。”
天老爷犒劳你。[177]猪猡的报纸[178]。阉牛之友派。
辛格也曾答应我,要为《达娜》杂志[179]写篇稿子。我们的文章会有读者吗?我认为会有的。盖尔语联盟[180]要点用爱尔兰语写的东西。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肯来。把斯塔基也带来吧。
斯蒂芬坐了下来。
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向那些告辞的人们打完招呼之后,就走过来了。他泛红着假面具般的脸说:
“迪达勒斯先生,你的观点极有启发性。”
他踮起脚尖,脚步声橐橐地踱来踱去,鞋跟有多么厚,离天就靠近了多少[181]。然后在往外走的一片嘈杂声的掩盖下,他低声说:
“那么,你认为她对诗人不忠贞吗?”
那张神色惊愕的脸问我。他为什么走过来呢?是出于礼貌,还是得到了什么内心之光?[182]
“既然有和解,”斯蒂芬说,“当初想必就有过纷争。”
“可不是嘛。”
穿着鞣皮紧身裤的基督狐。一个亡命徒,藏到枯树杈里,躲避着喧嚣。他没同母狐狸打过交道。孑然一身,被追逐着。他赢得了女人们的心,都是些软心肠的人们:有个巴比伦娼妇,还有法官夫人们,以及胖墩墩的酒馆掌柜的娘儿们。[183]“狐入鹅群”[184]。在“新地”大宅[185],有个慵懒的浪荡女人。想当初她曾经像肉桂那么鲜艳、娇嫩、可人,而今全部枝叶都已凋落,一丝不挂,对窄小的墓穴心怀畏惧,并且未得到宽恕。
“可不是嘛。那么,你认为……”
门在走出去的人们背后关上了。
一片静寂突然笼罩了这间幽深的拱顶斗室。是温暖和沉滞的空气带来的静寂。
维斯太[186]的一盏灯。
在这里,他冥想着一些莫须有的事,倘若恺撒相信预言家的警告而活下来的话,[187]那么他究竟会做些什么事呢?有可能发生的事。可能发生的、可能的情况的种种可能性。[188]不可知的事情。当阿戏留生活在女辈中间时,他用的是什么名字呢?[189]
我周围是封闭起来的思想,装在木乃伊匣里,填上语言香料保存起来。透特[190],图书馆的神,头戴月冠的鸟神。我听见那位埃及祭司长的声音[191]:在那一间间堆满泥板书的彩屋里。
这些思维是沉寂的。它们在人的头脑里却曾经十分活跃。沉寂,但是它们内部却怀着对死亡的渴望,在我耳际讲个感伤的故事,敦促我表露他们的愿望。
“毫无疑问,”约翰·埃格林顿沉吟一下说,“在所有的伟人中间,他是最难以理解的。除了他曾生活过并且苦恼过而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连这一点也不清楚。旁人经受我们的置疑[192]。其余的都遮在阴影之下[193]。”
“然而《哈姆莱特》这个作品多么富于个人色彩啊,对吗?”贝斯特先生申辩说,“要知道,我是说,这是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一种个人手记——我是说,他的生平。至于谁被杀或是谁是凶手,我倒丝毫也不在意……”
他把清白无辜的笔记本放在桌边上,面上泛着挑战似的微笑。用盖尔语所撰写的他的个人记录。船在陆上。我是个僧侣。[194]把它译成英文[195]吧,小个子约翰。[196]
小个子约翰·埃格林顿说:
“根据我听玛拉基·穆利根所谈起过的,对于这些奇谈怪论我是有准备的。不过我不妨忠告你,倘若你想动摇我对于莎士比亚就是哈姆莱特这一信念,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原谅我。[197]
斯蒂芬忍受着在皱起的眉毛下,严厉地闪着邪光的那双眼睛的剧毒。小王[198]。而一经它盯视,人就被蛊惑致死。[199]布鲁涅托[200]先生,我要为这句话而感谢你。
“正像我们,或母亲达娜[201],一天天地编织再拆散我们的身子,[202]”斯蒂芬说,“肉体的分子来来回回穿梭;一位艺术家也这样把自己的人物形象编织起来再拆散。尽管我的肉身反复用新的物质编织起来,我右胸上那颗胎里带来的痣[203]还在原先的地方。同样地,没有生存在世上的儿子的形象,通过得不到安息的父亲的亡灵,在向前望着。想象力迸发的那一瞬间,用雪莱的话来说,当精神化为燃烧殆尽的煤[204]那一瞬间,过去的我成为现在的我,还可能是未来的我。因此,在未来(它是过去的姊妹)中,我可以看到当前坐在这里的自己,但反映的却是未来的我。”
霍索恩登的德拉蒙德[205]帮助你度过了难关。
“是啊,”贝斯特先生兴致勃勃地说,“我觉得哈姆莱特十分年轻。[206]他对世事那股子激愤可能来自他父亲,可是跟奥菲利娅的那些段落肯定来自他本人。”
这可就大错特错啦。他在我的父亲之中,我在他的儿子之中。
“那颗疮是无从消失的,[207]”斯蒂芬笑着说。
约翰·埃格林顿绷着脸皱起眉头。
“倘若那是天才的胎记,”他说,“天才就成了市场上的滞销货啦。勒南[208]所称赞不已的莎士比亚晚年的戏剧,呈现出的可是另一种精神。”
“和解的精神,”公谊会教徒一图书馆长低声说。
“和解又从何谈起,”斯蒂芬说,“除非先有过纷争。”
话就说到这里。
“倘若你想知道,《李尔王》、《奥瑟罗》、《哈姆莱特》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可怕时刻,究竟被哪些事件罩上了阴影,你就得先留意这个阴影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消失的。在一场场可怕的风暴中,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的船翻了,他像另一个尤利西斯那样受尽磨难。[209]是什么给他的心带来慰藉呢?”
头戴红尖帽,受尽折磨,被泪水遮住了视线。[210]
“一个娃娃——放在他怀里的女孩儿玛丽娜[211]。”
“智者派容易误入外典[212]这一歧途的倾向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约翰·埃格林顿一语道破,“大道[213]固然冷清,然而它通向城市。”
好样儿的培根[214]。已经发了霉。莎士比亚即培根这一牵强附会的说法。[215]用密码来变戏法的[216]走在大道上。从事宏伟的探索的人们。到哪座城市去呀,各位好老爷?隐姓埋名:A·E·,永恒。马吉是约翰·埃格林顿[217]。太阳之东,月亮之西,[218]长生不老国[219]。两个人都脚蹬长靴,拄着拐杖。[220]
离都柏林[211]还有多远?
先生,还得走七十英里。
掌灯时分能到吗?
“布兰代斯认定,”斯蒂芬说,“它是晚期的头一部剧本。[222]”
“是吗?关于这一点,西德尼·李[223]先生——或照某些人的说法,原名叫西蒙·拉扎勒斯的——又怎么说呢?”
“玛丽娜是风暴的孩子[224],米兰达是奇迹[225],潘狄塔是失去了[226]。丢失了的,又还给他了;他女儿的娃娃。[227]配力克里斯曾说:‘我的最亲爱的妻子正像这个女郎一样。’[228]任何一个男人,倘若没有爱过母亲,他会爱女儿吗?[229]”
“做爷爷的艺术,”贝斯特先生开始咕哝道,“变得伟大的艺术……[230]”
[“他会不会参照自己年轻时代的记忆,在她身上看到另一个形象的新生呢?”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爱——是的。大家都晓得的字眼。[231]爱乃由于给予对方之欲望,使之幸福。要某物,则属对自己愿望之满足。][232]
“对于一个具有那种叫作天才的古怪东西的人来说,他的形象就是一切经验的基准,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的共鸣会触动他的心弦。跟他同一血统的其他男子的形象,会引起他的反感。他会从中看到大自然预示或重复他自己的那种不伦不类的尝试。”
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那宽厚的前额被希望点燃了,泛着玫瑰色。
“为了启发大家,我希望迪达勒斯先生会完成他的这一学说。我们还必须提到另一位爱尔兰注释者乔治·萧伯纳[233]先生。我们也不可忘记弗兰克·哈里斯[234]先生。他在《星期六评论》上所发表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着实精彩。说也奇怪,他也为我们描述了《十四行诗》[235]的作者和‘黑夫人’之间不幸的关系。受到这位女人青睐的情敌是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236]。我认为,倘若诗人非遭到拒绝不可,那么这样的拒绝——怎么说好呢?——似乎是和我们对于本来不应有的情况所抱观点毋宁是一致的。”[237]
他说完这番措词恰当的话之后,就在众人当中昂起温顺的头——一枚海雀蛋[238],大家争夺的猎物。
他使用丈夫那种老式辞句——就像浑家啦,内助啦。卿爱否,米莉亚姆?[239]爱汝夫否?[240]
“这也可能吧,”斯蒂芬说,“马吉喜欢引用歌德的一句话:“当心你年轻时所抱的愿望,因为到了中年就会变为现实。[241]他为什么派一个小贵族[242] 去向一个花姑娘[243]求婚呢?她是人人行驶的海湾[244],少女时代声名狼藉[245]的宫女。他本人是个语言贵族[246],成为一位卑微的绅士,他还写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他的自信心过早地被扼杀了。首先,他曾被压翻在麦田(可以说是裸麦地)里。打那以后,他在自己眼中再也不是赢者了,更不能在笑而躺下的游戏[247] 中取胜。不论怎样以唐磺[248]自居,也无济于事。后来再怎么弥补,也无法挽回最初的失败。他被野猪的獠牙咬伤了[249],悍妇即使输了, 她手中也还有那看不见的女性武器。我感觉,他的言词中有着刺激肉身使其陷入新的激情的东西。 这是比最初的激情还要晦暗的影子,甚至使他对自己的认识都模糊起来。 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两种狂乱汇成一股漩涡。
他们在倾听。我往他们的耳腔内注入。
“灵魂已经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睡觉的时候,毒草汁被注入耳腔。[250]然而在睡眠中遇害的人不可能了解自己是怎样被害的,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的灵魂以洞察来世的本事。倘若造物主不曾让他晓得,哈姆莱特王的鬼魂不可能知道毒杀以及促使这一行动的双背禽兽[251]的事。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辞(贫乏而且寒伧的英语[252])总是转到旁的方面,转到后面。既是凌辱者又是被凌辱者,既愿意又不愿意[253],从鲁克丽丝那蓝纹纵横的象牙球般的双乳[254],到伊摩琴袒露着的胸脯上那颗梅花形的痣[255],一直紧紧缠绕着他。为了逃避自己,他积累起一大堆创作。如今对这些都已厌倦了,就像一只舔着旧时伤口的老狗似的折回去了。然而,由于失对他来说就是得,他就带着丝毫不曾减弱的人性步入永恒。他所写下的智慧也罢,他所阐明的法则也罢,都没有使他受到教益。他的脸甲掀起来了。[256]如今他成为亡灵,成为阴影;他成为从艾尔西诺的峰岩间刮过去的风;或是各遂所愿[257],成了海洋的声音——只有作为影子的实体的那个人,与父同体的儿子,才听得见的声音。”
“啊们!”有个声音在门口回答说。
我的冤家呀,你找到我了吗?[258]
幕间休息[259]。
这时,形容猥琐、神态像副主教那样阴沉的勃克·穆利根身穿色彩斑斓的小丑服装,愉快地向笑脸相迎的人们走来。我的电报。[260]
“假若我没听错的话,你在谈论设有实质的脊椎动物[261]吧?”他问斯蒂芬。
他穿着淡黄色背心,把他摘下的巴拿马草帽当作丑角的帽子似的抡着,快活地致意。
大家向他表示欢迎。你尽管嘲弄他,也还是得侍奉他[262]。
一样嘲弄者,佛提乌,冒牌的小先知,[263]约翰·莫斯特[264]。
他,自我诞生之神,以圣灵为媒介,自己委派自己为赎罪者,来到自己和旁人之间,他受仇敌欺骗,被剥光衣服,遭到鞭笞,被钉在十字架上饿死,宛若蝙蝠钉于谷仓门上,听任自己被埋葬,重新站起,征服了地狱,[265]升入天堂。一千九百年来,坐于自己的实体之右。当生者全部死亡之日,将从彼而来,审判生死者。[266]
天 主
受 享 荣
福 于——天。[267]
他举起双手。圣器的帷幕垂下来了。啊,成簇的花儿!一座又一座又一座钟,响成一片。
“是呀,确实是,”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说,“那是一场最令人受教益的讨论。穆利根先生想必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自有他的高见。应该把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谈一谈。”
他一视同仁地朝四面八方微笑着。
勃克·穆利根困惑地左思右想。
“莎士比亚?”他说,“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那皮肉松弛的脸上闪过一丝开朗的微笑。
“没错儿,”他恍然大悟了,“就是写得像辛格[268]的那位老兄。”
贝斯特先生转向他。
“海恩斯找你哪,”他说,“你碰上他了吗?回头他要在都柏林面包公司跟你见面。他到吉尔书店买海德的《康纳特情歌》去了。”
“我是从博物馆穿过来的,”勃克·穆利根说,“他来过这儿吗?”
“‘大诗人’的同胞们也许对咱们这精彩的议论颇感厌烦了,”约翰·埃格林顿回答说,“我听说昨天晚上在都柏林,一位女演员[269]第四百零人次演出《哈姆莱特》。维宁[270]提出,这位王子是个女的。有没有人发现他是个爱尔兰人呢?我相信审判官巴顿[271]正在查找什么线索。他(指王子殿下,而不是审判官大人) 曾凭着圣帕特里克的名义起过誓[272]。”
“最妙的是王水德的故事《威·休先生的肖像》,”贝斯特先生举起他那出色的笔记本说,“他在其中证明《十四行诗》是一个名叫威利·休斯的八面玲珑的人写的。”[273]
“那不是献给威利·休斯的吗?”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问。
要不就是休依·威尔斯?威廉先生本人。[274]W·H。我是谁?
“我认为是为威利·休斯而写的,”贝斯特先生顺口纠正自己的谬误说,“当然喽,这全是些似是而非的话。要知道,就像休斯和砍伐和色彩,[275]他的写法独特。要知道,这才是王尔德的精髓呢。落笔轻松。”
他泛着微笑,轻轻地扫视大家一眼。白肤金发碧眼的年轻小伙子。王尔德那柔顺的精髓。[276]
你着实鬼得很。用堂迪希的钱[277]喝了三杯威士忌。
我花了多少?哦,不过几个先令。
为了让一样新闻记者喝上一通。讲那些干净的和不干净的笑话。机智。为了把他打扮自己的那身青春的华服弄到手,你不惜舍弃你的五种机智。[278] 欲望得到满足的面貌。[279]
机会是很多的。交情的时候,把她让给你吧。天神啊,让他们过一个凉快的交尾期吧。[280]对,把她当作斑鸠那样地疼爱吧。
夏娃在赤裸的小麦色肚皮下面犯的罪孽。一条蛇盘绕着她,龇着毒牙跟她接吻。[281]
“你认为这不过是谬论吗?”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在问,“当嘲弄者最认真的时候,却从未被认真对待过。”
他们严肃地讨论起嘲弄者的真诚。
勃克·穆利根又把脸一耷拉,朝斯蒂芬瞅了几眼。然后摇头晃脑地凑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封折叠着的电报。他那灵活的嘴唇读时露出微笑,带着新的喜悦。
“电报!”他说,“了不起的灵感!电报!罗马教皇的训渝!”
他坐在桌子灯光照不到的一角,兴高采烈地大声读着:
“伤感主义者乃只顾享受而对所做之事不深觉歉疚之火。[282]署名:迪达勒斯。你是打哪儿打的电报?窑子吗?不。学院公园?你把四镑钱都喝掉了吧?姑妈说是要去拜访你那位非同体的父亲。电报!玛拉基·穆利根。下阿贝街‘船记’酒馆。噢,你这个举世无双的滑稽演员!哦,你这个以教士自居的混蛋金赤!”
他乐呵呵地将电报和封套塞到兜里,却又用爱尔兰土腔气冲冲地说:
“是这么回事。好兄弟,当海恩斯亲自把电报拿进来的时候,他和我都正觉得苦恼烦闷来着。我们曾嘟囔说,要足足地喝上它一杯,让行乞的修士都会起魔障。我正转着这个念头,他呢,跟姑娘们黏糊起来了。我们就乖乖儿地坐在康纳里[283]那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地等下去,指望着每人喝上五六杯呢。”
他唉声叹气地说:
“我们就呆在那儿,乖乖[284],把舌头耷拉得一码长,活像那想酒想得发昏的干嗓子教士。你呢,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居然还给我们送来了这么个玩艺儿。”
斯蒂芬笑了。
勃克·穆利根像是要提出警告似地弯下腰去。
“流浪汉辛格[285]正在找你哪,”他说,“好把你宰了。他听说你曾往他那坐落在格拉斯特赫尔的房子的正门上撒尿。他趿拉着一双破鞋到处走, 说是要把你宰了。”
“我!”斯蒂芬喊道,“那可是你对文学做出的一桩贡献呀。”
勃克·穆利根开心地向后仰着,朝那黑咕隆咚偷听着的天花板大笑。
“宰了你!”他笑道。
在圣安德烈艺术街上,我一边吃着下水杂烩,一边望着那些严厉的怪兽形面孔。[286]用那对语言报以语言的语言,讲一通话。[287]莪相和帕特里克。[288]他在克拉玛尔森林遇见了抡着酒瓶的牧羊神。[289]那是圣星期五!杀人凶手爱尔兰人。他遇见了自己游荡着的形象。我遇见了我的。我在林中遇见一个傻子。[290]
“利斯特[291]先生,”一个工役从半掩着的门外招呼说。
“……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审判官先生马登在他的《威廉·赛伦斯少爷日记》中找到了狞猎术语……[292]啊,什么事?”
“老爷,来了一位先生,”工役走过来,边递上名片边说,“是《自由人报》社的。他是想看看去年的《基尔肯尼民众报》[293]合订本。”
“好的,好的,好的。这位先生在……?”
他接过那张殷勤地递过来的名片,带看不看地瞥了一眼,放下来,并没有读,只是瞟着,边问边把鞋踩得橐橐作响。又问:
“他在……?哦,在那儿哪!”
他快步跳着五步舞[294]出去了。在浴满阳光的走廊上,他不辞劳苦,热情地、口若悬河地谈着,极其公正、极其和蔼地尽着本分,不愧为一名最忠诚的“宽边帽”[295]。
“是这位先生吗?《自由人报》?《基尔肯尼民众报》?对。您好,先生。《基尔肯尼……》……我们当然有喽……”
一个男子的侧影耐心地等待着,耹听着。
“主要的地方报纸全都有……《北方辉格》、《科克观察报》、《恩尼斯科尔西卫报》[296]。去年。一九0三……请您……埃文斯,给这位先生领路……您只要跟着这个工役……要么,还是我自己……这边……先生,请您……”
口若悬河,尽着本分,他领先到放着所有地方报纸的所在。一个鞠着躬的黑影儿尾随着他那匆忙的脚后跟。
门关上了。
“犹太佬!”勃克·穆利根大声说。
他一跃而起,一把抓住名片。
“他叫什么名字?艾克依·摩西[297]吗?布卢姆。”
他喋喋不休地讲下去:
“包皮的搜集者[298]耶和华已经不在了。刚才我在博物馆里遇见过他。我到那儿是去向海泡里诞生的阿佛洛狄忒致意的。这位希腊女神从来没有歪起嘴来祷告过。咱们每天都得向她致敬。生命的生命,你的嘴唇点燃起火焰。[299]”
他突然转向斯蒂芬:
“他认识你。他认识你的老头子。哦,我怕他,他比希腊人还要希腊化。他那双淡色的加利利[300]眼睛总盯着女神中央那道沟沟。美臀维纳斯。[301]啊,她有着怎样一副腰肢啊!天神追逐,女郎躲藏。[302]”
“我们还想再听听,”约翰·埃格林顿征得贝斯特先生的赞同后说,“我们开始对莎[303]太太感兴趣了。在这之前,即便我们想到过她, 也不过把她看作是一位有耐心的克雨雪达[304],留守家中的潘奈洛佩[305]。”
“戈尔吉亚的弟子安提西尼[306],”斯蒂芬说,“从曼涅劳王的妻子、阿凯人海伦手里把美的标志棕榈枝拿过来,交给了可怜的潘奈洛佩。二十位英雄在特洛伊那匹母木马[307]里睡过觉。他[308]在伦敦住了二十年, 其间有个时期领的薪水跟爱尔兰总督一样多。他的生活是丰裕的。他的艺术超越了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封建主义艺术,[309]乃是饱满的艺术。热腾腾的鲜鱼馅饼、 绿杯里斟得满满的白葡萄酒、蜂蜜酱、蜜饯玫瑰、杏仁糖、醋栗填鸽、刺芹糖块。沃尔特·雷利爵士[310]被捕的时候,身上穿着值五十万法郎的衣服,包括一件精致的胸衣。放高利贷的伊丽莎·都铎[311]的内衣之多,赛得过示巴女王。[312]足足有二十年之久, 他徘徊在夫妻那纯洁缠绵的恩爱与娼妇淫荡的欢乐之间。你们可晓得曼宁汉姆那个关于一个市民老婆的故事吧,她看了迪克[313]·伯比奇在《理查三位》中的演出,就邀请他上自己的床。莎士比亚无意中听到了,没费多大力气[314]就制服了母牛。当伯比奇前来敲门的时候,他从阉鸡[315]的毯子下面回答说:‘征服者威廉已比理查三世捷足先登啦。’[316]快活的小夫人、情妇菲顿[317]噢的一声就骑了上去。[318]还有他那娇滴滴的婆娘潘奈洛佩·里奇。[319]这位端庄的上流夫人适合做个演员;而河堤上的娼妇,一回只要一便士。”
王后大道。再出二十苏吧。给你搞点小花样儿。玩小猫味?你愿意吗?[320]
“上流社会的精华。还有牛津的威廉·戴夫南特爵士[321]的母亲,只要是长得像金丝雀那样俊秀的男人,她就请他喝杯加那利酒[322]。”
勃克·穆利根虔诚地抬起两眼祷告道:
“圣女玛格丽特·玛丽·安尼科克[323]!”
“还有换过六个老婆的哈利的女儿。[324]再就是草地· 丁尼生、绅士诗人所唱的:附近邸舍的高贵女友。[325]这漫长的二十年间,你们猜猜,斯特拉持福的潘奈洛佩[326]在菱形窗玻璃后面都干什么来着?”
干吧,干吧,[327]干出成绩。他在药用植物学家杰勒德那座位于费特小巷的玫瑰花圃[328]里散步,赤褐色的头发已灰白了。像她的脉管一样蓝的风信子。[329]朱诺的艰睑,紫罗兰。[330]他散步。人生只有一次,肉体只有一具。干吧。专心致志地干。近处,在淫荡和污浊的臭气中,一双手放在白净的肉身上。
勃克·穆利根使劲敲着约翰·埃格林顿的桌子。
“你猜疑谁呢?”[331]他盘问。
“假定他是《十四行诗》里那位被舍弃的情人吧。被舍弃一回,就有第二回。然而宫廷里的那个水性扬花的女子是为了一个贵族——他的好友——而舍弃他的。[332]”
不敢说出口的爱。[333]
“你的意思是说,”刚毅的约翰·埃格林顿插进嘴去,“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爱上了一位贵族。”
蜥蜴们沿着古老的墙壁一闪而过。我在查伦顿[334]仔细观察过它们。
第九章 2
“好像是的,”斯蒂芬说,“为了这位贵族,并为所有其他特定的、未被耕耘过的处女的胎,[335]他想尽尽马夫对种马所尽的那种神圣职责。也许跟苏格拉底一样,不仅妻子是个悍妇,母亲也是个产婆呢。然而她,那个喜欢痴笑的水性扬花的女子,并不曾撕毁床头盟。[336]鬼魂[337]满脑子都是那两档子事:誓盟被破坏了,她移情于那个迟钝的乡巴佬——亡夫的兄弟身上。我相信可爱的安是情欲旺盛的。她向男人求过一次爱,就会求第二次。”
斯蒂芬在椅子上果敢地转了个身。
“证明这一点的责任在你们而不在我,”他皱着眉头说,“倘若你们否认他在《哈姆莱特》第五场里就给她打上了不贞的烙印,那么告诉我,为什么在他们结婚三十四年间,从迎娶那天直到她给他送殡,她始终只字没被提到过。这些女人统统为男人送了葬,玛丽送走了她的当家人约翰[338],安送走了她那可怜的、亲爱的威伦[339];尽管对于比她先走感到愤懑,他还是死在她前头了。琼送走了她的四个弟弟。[340]朱迪斯[341]送走了她丈夫和所有的儿子。苏珊也送走了她丈夫。[342]苏珊的女儿伊丽莎白呢,用爷爷的话说:先把头一个丈夫杀了,再嫁给第二个。[343]哦,对啦。有人提到过。当他在京都伦敦过着豪华的生活时,她不得不向她父亲的牧羊人借四十先令来还债。[344]你们解释好了。还解释一下‘天鹅之歌’[345],作者在诗中向后世颂扬了她。”
他面对着大家的沉默。
埃格林顿对他这么说:
你指的是遗嘱。
然而我相信法律家已做了诠释。
按照不成文法,她作为遗孀,
有权利继承遗产。法官们告诉我们,
他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
恶魔嘲弄他。
嘲弄者:
因此,他把她的名字
从最初的草稿中勾销了;然而他并未勾销对外孙女
和女儿们的赠予,
赠予他妹妹以及他在斯特拉特福和伦敦的挚友们的
礼物。因此,据我所知,
当他被提醒说,不要漏掉她的名儿
他才留给她
次好的
床。[346]
要点。[347]
留给她他那
次好的床
留给她他那
顶刮刮的床
次好的床
留给一张床。
喔啊!
“当时连俊俏的乡男村女[348]都几乎没什么家当,”约翰·埃格林顿说,“倘若我们的农民戏[349]反映得真实的话,他们至今也还是没有多少。”
“他是个富有的乡绅,”斯蒂芬说,“有着盾形纹章,还在斯特拉福德拥有一座庄园,在爱尔兰庭园有一栋房屋。他是个资本家和股东,证券发起人,还是个交纳什一税的农场主。倘若他希望她能在鼾声中平安地度过余生的话,为什么不把自己最好的床留给她呢?”
“他显然有两张床,一张最好的,另一张是次好的,”次好的贝斯特先生[350]乖巧地说。
“向饭桌和寝室告别,[351]”勃克·穆利根说得更透彻些,博得了大家一笑。
“关于一张张有名的床,古人说过不少话,”其次的埃格林顿噘起嘴来,像在床上那样地笑着,“让找想想看。”
“古人记载着那个斯塔基莱特的顽童和秃头的异教贤人的事,”斯蒂芬说,“他在流亡中弥留时,释放了他的奴隶们,留给他们资财,颂扬祖先, 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已合葬在亡妻的遗骨旁边,并托付友人好生照顾他生前的情妇(不要忘记内尔·格温·赫尔派利斯),让她住在他的别墅里。[352]”
“你认为他是这么死的吗?”贝斯特先生略表关切地问道,“我是说……”
“他是喝得烂醉而死的,”勃克·穆利根劈头就说,“一夸脱浓啤酒,就连国王也喜爱。[353]哦,我得告诉你们多顿[354]说了些什么!”
“说了什么?”最好的埃格林顿[355]问。
威廉、莎士比亚股份有限公司。[356]人民的威廉。详情可询:爱·多顿,海菲尔德寓所……[357]
“真可爱!”勃克·穆利根情意绵绵地叹息说,“我问他, 关于人们指责那位大诗人有鸡奸行为,他做何感想。他举起双手说,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当时的生活中充满了欣喜欢乐。[358]真可爱!
娈童。
“对美的意识使我们误人歧途,”沉浸在哀愁美中的贝斯特对正在变丑的埃格林顿说。
坚定的约翰严峻地回答道:
“博士可以告诉咱们那话是什么意思。你不能既吃了点心又还拿在手里。”[359]
你这么说吗?难道他们要从我们——从我这里夺去美的标志——棕搁枝[360]吗?
“还有对财产的意识,”斯蒂芬说,“他把夏洛克从他自己的长口袋[361]里拽了出来。作为啤酒批发商和放高利贷者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个小麦批发商和放高利贷的。当由于闹饥荒而引发那场暴动时,他手里存有十托德[362]小麦。毫无疑问,向他借钱的那帮人是切特尔·福斯塔夫所说的信仰各种教派的人。他们都说,他公平交易。为了讨回几袋麦芽的款,他和同一个剧团的演员打官司,作为贷款的利息,索取对方的一磅肉。不然的话,奥布里[363]所说的那个马夫兼剧场听差怎么能这么快地就发迹了呢?为了赚钱,他什么都干得出。女王的侍医、犹太佬洛佩斯[364]那颗犹太心脏被活生生地剜出来,在上绞刑架之后,大解八块,紧接着就是一场对犹太人的迫害。这和夏洛克事件不谋而合。《哈姆莱特》和《麦克白》与有着焚烧女巫的嗜好的伪哲学家的即位赶在同一个时期。 [365]在《爱的徒劳》中,被击败的无敌舰队[366]成了他嘲笑的对象。他的露天演出——也就是历史剧,在马弗京的一片狂热[367]中,粉墨登场了。当沃里克郡的耶稣会士受审判后,我们就听到过一个门房关于暧昧不清的说法。[368]‘海洋冒险号’从百慕大驶回国时,[369]勒南所称赞过的以我们的美国堂弟帕齐·凯列班[370]为主人公的那出戏写成了。继锡德尼之后,他也写了罄美的十四行诗组诗。[371]关于仙女伊丽莎白(又名红发贝斯),那位胖处女授意而写成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就让哪位德国绅士耗用毕生心血去从洗衣筐的尽底儿上搜集吧,以便探明它的深邃含义。[372]”
我觉得自己颇有领会。那么,把神学论理学语言学什么学掺合在一起再看看。撒着尿,撒了尿,撒着尿的,撒尿。[373]
“证明他是个犹太人吧,”约翰·埃格林顿有所期待地将了一军,“你们学院的院长说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374]
“我应该受到抑制。”[375]
“他是德国制造的[376]——”斯蒂芬回答说,“是一位用法国磨光漆[377]来涂饰意大利丑闻的高手。”
“一位拥有万众之心的人,”贝斯特先生提醒道,“柯尔律治[378]说他是一位拥有万众之心的人。”
泛言之,人类社会中,让众人之间存在友情,乃是至关重要的。[379]
“圣托马斯,”斯蒂芬开始说……
“为我等祈[380],”僧侣穆利根边瘫坐在椅子上,边呻吟道。
从那儿,他凄凉地吟起北欧古哀诗来:
“吻我屁股!我心脏的搏动![381]从今天起,咱们毁灭啦!咱们确实毁灭啦!”[382]
大家各自泛出微笑。
“圣托马斯……”斯蒂芬笑眯眯地说,“那部卷帙繁多的书,我是从原文披阅并赞赏的。他是站在不同于马吉先生所提到的新维也纳学派[383]的立场上,来谈乱伦的问题的。他以他持有的睿智而奇待的方法,把乱伦比作在情感方面的贪得无厌。他指出,血统相近者之间滋生的这种爱情,对于那些可能渴望它的陌生人,却贪婪地被抑制住了。基督教徒谴责犹太人贪婪,而犹太人是所有的民族中最倾向于近亲通婚的。这一谴责是愤怒地发出的。基督教戒律使犹太人成为巨富 (对他们来说,正如对罗拉德派一样,风暴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也用钢圈箍在他们的感情上。[384]这些戒律究竟是罪恶还是美德,神老爹[385]会在世界末日告诉我们的。然而一个人如此执着于债权,也同样会执着于所谓夫权。任何笑眯眯的邻居[386]也不可去贪图他的母牛、他的妻子、他的碑文或公驴。 [387]
“或是他的母驴,”勃克·穆利根接着说道。
“温和的威尔[388]遭到了粗暴的对待,”温和的贝斯特先生温和地说。
“哪个威尔呀?”勃克·穆利根亲切地打了句诨,“简直都掺混不清了。”
“活下去的意志,”约翰·埃格林顿用哲理解释道,“对威尔的遗孀——可怜的安来说,就是为了迎接死亡的遗嘱。”[389]
“安息吧![390]”斯蒂芬祷告说。
当年雄心壮志何在?
早已烟消云散。[391]
“尽管你们证明当时的床就像今天的汽车那样珍贵,而床上的雕饰也令七个教区感到惊异;却不能改变她——那蒙面皇后[392]穿着青衣僵硬地挺在那次好的床上这一事实。在晚年,她跟那些传福音的打得火热——其中的一个跟她一道住在‘新地’大宅,共饮那由镇议会付款的一夸脱白葡萄酒。然而,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就不得而知了。她听说自己有个灵魂。她读(或者请旁人读给她听)他那些沿街叫卖的廉价小册子。她喜欢它们更甚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她每天晚上跨在尿盆上撒尿,[393]驰想着《信徒长裤上的钩子和扣眼》以及《使最虔诚的信徒打喷嚏的最神圣的鼻烟盒》。[394]维纳斯歪起嘴唇祷告着。内心的呵责。悔恨之心。这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淫妇衰老后在寻觅着神的时代。”
“历史表示这是真实的,”编年学家埃格林顿引证说,[395]“时代不断地更迭。然而一个人最大的仇敌乃是他自己家里的人和家族[396],这话是有可靠根据的。我觉得拉塞尔是对的。我们何必去管他的老婆或者父亲的事呢?依我说,只有家庭诗人才过家庭生活。福斯塔夫并不是个守在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个胖骑士才是他所创造的绝妙的人物。”
瘦骨嶙嶙的他往椅背上靠了靠。出于羞涩,否定你的同族吧,[397]你这个自命清高的人。[398]他羞涩地跟那些不信神的人一道吃饭,还偷酒杯。 [399]这是住在阿尔斯特省安特里姆[400]的一位先生这样嘱咐他的。每年四季结帐时就来找他。马吉先生,有位先生要来见您。我?他说他是您的父亲,先生。请把我的华兹华斯[401]领进来。大马吉·马修[402]进来了。这是个满脸皱纹、粗鲁、蓬头乱发的庄稼汉[403],穿着胯间有个前兜的紧身短裤,[404]布袜子[405]上沾了十座树林的泥污,[406]手里拿着野生苹果木杖。[407]
你自己的呢?他认得你那老头子[408]——一个鳏夫。
我从繁华的巴黎朝临终前的她那肮脏的床头赶去。在码头上摸了摸他的手。他说着话儿,嗓音里含着新的温情。鲍勃·肯尼大夫[409]在护理她。那双眼睛向我祝福,然而并不了解我。
“一个父亲,”斯蒂芬说,“在抑制着绝望情绪,这是无可避免的苦难。他是在父亲去世数月之后写的那出戏。[410]这位头发开始花白、有着两个已届婚龄的女儿[411]的年方三十五岁的男子,正当人生的中途,[412]却已有了五十岁的人的阅历。倘若你认为他就是威登堡那个没长胡子的大学生, [413]那么你就必须把他那位七十岁的老母看作淫荡的王后。不,约翰·莎士比亚的尸体并不在夜晚到处徘徊。[414]它一小时一小时地腐烂下去。 [415]他把那份神秘的遗产[416]留给儿子之后,就摆脱了为父的职责,开始安息了。卜伽丘的卡拉特林[417]是空前绝后的一个自己认为有了身孕的男人。从有意识地生育这个意义上来说,男人是缺乏父性这一概念的。那是从唯一的父到唯一的子之间的神秘等级,是使徒所继承下来的。教会不是建立在乖巧的意大利智慧所抛给欧洲芸芸众生的那座圣母像上,而是建立在这种神秘上——牢固地建立在这上面。因为正如世界,正如大宇宙和小宇宙,它是建立在虚空之上,建立在无常和不定之上的。主生格和宾生格的母爱[418]也许是人生中唯一真实的东西。[419]父性可能是法律上的假定。谁是那位受儿子的爱戴,或是疼爱儿子的为人之父呢?”
你究竟要扯些什么呢?
我晓得。闭嘴。该死的。我自有道理。
越发。更加。再者。其后[420]。
你注定要这么做吗?
“难以自拔的肉体上的耻辱使父子之间产生隔阂。世上的犯罪年鉴虽被所有其他乱伦与兽奸的记录所玷污,却几乎还没记载过这类越轨行为。子与母、父与女、姐妹之间的同性恋,难以说出口的爱,侄子与祖母,囚犯与钥匙孔,皇后与良种公牛。[421]儿子未出世前便损害了美。出世之后,带来痛苦,分散爱情,增舔操劳。他是个新的男性:他的成长乃是他父亲的衰老;他的青春乃是他父亲的妒嫉;他的朋友乃是他父亲的仇敌。”
在王子街[422]上,我想过此事。
“在自然界,是什么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呢?是盲目发情的那一瞬间。”
我是个父亲吗?倘若我是的话?
皱缩了的、没有把握的手。
“非洲的撒伯里乌[423],野生动物中最狡猾的异教的开祖,坚持说,圣父乃是他自己的圣子。没有不能驾御的语言的斗犬阿奎那[424]驳斥了他。那么,倘若没有儿子的父亲就不成其为父亲,那么没有父亲的儿子能成真为儿子吗?当拉特兰·培根·南安普敦·莎士比亚[425]或错误的喜剧里的另一个同名 [426]诗人撰写《哈姆莱特》的时候,他不仅是自己的儿子之父,而且还由于他不再是儿子了,他就成为、自己也感到成为整个家庭之父——他自己的祖父之父,他那末出世的孙儿之父。顺便提一下,那个孙儿从未诞生过,因为照马吉先生的理解,大自然是讨厌完美无缺的。[427]”
埃格林顿两眼洋溢着喜悦,羞怯而恍然似有所悟地抬头望着。这个愉快的清教徒隔着盘绕在一起的野蔷薇,[428]乐呵呵地望着。
恭维一番。极偶然地。然而恭维一番吧。
“他本人就是他自己的父亲,[429]”儿子穆利根喃喃自语。 “且慢。我怀孕了。我脑中有个尚未出世的娃娃。明智女神雅典娜[430]!一出戏!关键在于这出戏![431]让我分娩吧!”
他用那双接生的手抱住自已突出的前额。
“至于他的家庭,”斯蒂芬说,“他母亲的名字还活在亚登森林里。[432]她的死促使他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写出伏伦妮姬的场景。[433]《约翰王》中少年亚瑟咽气的场面就描述了他的幼子之死。身着丧服的哈姆莱特王子是哈姆奈特·莎士比亚。我们晓得《暴风雨》、《配力克里斯》、《冬天的故事》中的少女们都是谁。埃及的肉锅克莉奥佩特拉[434]和克瑞西达[435]以及维纳斯都是谁,我们也猜得出。 然而他的眷属中还有一个被记载下来的人。”
“情节变得复杂啦,”约翰·埃格林顿说。
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震颤着,悄悄地走了进来。颤着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很快地颤着,颤着,颤着。[436]
门关上了。斗室。白昼。
他们倾听着。三个。他们。
我、你、他、他们。
来吧,开饭啦。
斯蒂芬
他有三个弟兄,吉尔伯持、埃德蒙、理查[437]。吉尔伯特进入老年后,对几个绅士说,有一次他去望弥撒,教堂收献金的送了他一张免票。于是他就去了,瞅见他哥哥——剧作家伍尔在伦敦上演一出打斗戏,背上还骑着个男人。[438]戏园子里的香肠[439]吉尔伯特吃得可开心啦。哪儿也见不到他。然而可爱的威廉却在作品里记下了一个埃德蒙和一个理查。
马吉·埃格林、约翰
姓名!姓名有什么意义?[440]
贝斯特
理查就是我的名字,你晓得吗?我希望你替理查说句好话。要知道,是为了我的缘故。
(笑声)
勃克·穆利根
(轻柔地,渐弱)[441]
于是,医科学生迪克
对他的医科同学戴维说了……[442]
斯蒂芬
他笔下的黑心肠的三位一体——那帮恶棍扒手:伊阿古、罗锅儿理查和《李尔王》中的爱德蒙,其中两个的名字都跟他们那坏蛋叔叔一样。何况当他写成或者正在撰写这最后一部戏的时候,他的胞弟爱德蒙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萨瑟克[443]。
贝斯特
我巴不得爱德蒙遭殃,我不要理查这个名字……
(笑声)
公谊会教徒利斯特
(恢复原速)可是他偷去了我的好名声……[444]
斯蒂芬
(渐快)他把自己的名字——威廉这个美好的名字,隐藏在戏里。这出戏里是配角,那出戏里又是丑角。就像从前的意大利画家在画布的昏暗角落里画上了自己的肖像似的,他在满是“威尔”字样的《十四行诗》[445]里, 表明了这一点。就像冈特·欧·约翰[446]一样,对他来说姓名是宝贵的,就像他拼命巴结到手的纹章——黑地右斜线[447]上绘有象征荣誉的[448]矛或银刃的纹章——那样宝贵。比当上本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这一荣誉还更要宝贵。姓名有什么意义?[449]那正是当我们幼时被告知自己的姓名,并把它写下来之际,所问过自己的。他诞生的时候,出现了一颗星[450],一颗晨星,一条喷火龙[451]。白天,它在太空中独自闪烁着,比夜间的金星还要明亮。夜里,它照耀在标志着他的首字W[452]、横卧于群星中的仙后座那三角形上。午夜,当他离开安·哈撒韦的怀抱,从肖特利[453]回去时, 他一边走在困倦的夏天田野上,一边放眼望着那低低地躺在大熊座东边的地平线上的这颗星。
两个人都感到满意,我也满意。
不要告诉他们,当那颗星消失的时候,他年方九岁[454]。
而且从她的怀抱当中。
等待着被求爱并占有。[455]哎,你这个懦夫,[456]谁会向你求爱呢?
读一读天空吧。虐己者。[457]斯蒂芬的公牛精神。[458]你的星座在哪里?斯蒂芬,斯蒂芬,面包要切匀。S·D·他的情妇。不错——他的。杰林多打定主意不去恋慕S·D·[459]
“迪达勒斯先生,那是什么呀?”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问道,“是天体现象吗?”
“夜间有星宿,”斯蒂芬说,“白天有云柱。”[460]
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斯蒂芬瞅了瞅自己的帽子、手杖和靴子。
斯蒂法诺斯[461],我的王冠。我的剑。他的靴子使我的脚变了形。买一双吧。我的短袜净是窟窿。手绢也一样。
“你善于在名字上做文章,”约翰·埃格林顿承认道,“你自己的名字也够别致的了。我看这就正好说明你这个喜欢幻想的性格。”
我、马吉和穆利根。
神话中的工匠。[462]长得像鹰的人。你飞走了。飞向哪里?从纽黑文到迪耶普[463],统舱客。往返巴黎。风头麦鸡。[464]伊卡洛斯。[465]父亲啊,帮助我吧。[466]被海水溅湿,一头栽下去,翻滚着。你是一只风头麦鸡,变成一只风头麦鸡。
贝斯特先生热切地、安详地举起他的笔记本来说:
“那非常有趣儿。因为,要知道,在爱尔兰传说中,我们也能找到弟兄这一主题。跟你讲的一模一样。莎士比亚哥儿仨。格林[467]里也有。要知道,那些童话里,三弟总是跟睡美人结婚,并获得头奖。”
贝斯特弟兄们当中最好[468]的。好,更好,最好。
公谊会教徒-图书馆长来到旁边,像弹簧松了似的突然站住了。
“我想打听一下,”他说,“是你的哪一位弟兄……假若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曾暗示说,你们弟兄当中有一个行为不轨……然而,也许我理解得过了头?”
他察觉到自己失言了,四下里望望大家,把底下的话咽了下
去。
一个工役站在门口嚷道:
“利斯特先生!迪宁神父[469]要见……”
“澳,迪宁神父!马上就来。”
他立刻把皮鞋踩得囊囊响,随即径直走了出去。
约翰·埃格林顿提出了挑战。
“喂,”他说,“咱们听听足下关于理查和爱德蒙有何高见。你不是把他们留到最后吗?”
“我曾请你们记住那两位高贵的亲族[470]——里奇叔叔和爱德蒙叔叔,”斯蒂芬回答说,“我觉得我也许要求得过多了。弟兄正像一把伞一样,很容易就被人忘记。”
风头麦鸡。
你的弟弟在哪儿?在药剂师的店里。[471]砥砥我者,他,还有克兰利,穆利根。[472]现在是这帮人。夸夸其谈。然而要采取行动。把言语付诸实践。他们嘲弄你是为了考验你。采取行动吧。让他们在你身上采取行动。
风头麦鸡。
我对自己的声音感到厌烦了,对以扫的声音感到厌烦了。[473]愿用我的王位换一杯酒。[474]
继续说下去吧。
“你会说,这些名字早就写在被他当作戏剧素材的纪年记里了。他为什么不采用旁的,而偏偏采用这些呢?理查,一个娘子养的畸形的罗锅儿,向寡妇安(姓名有什么意义?)求婚并赢得了她——一个婊子养的风流寡妇。三弟——征服者理查,继被征服者威廉之后而来。这个剧本的其他四幕,松松散散地接在第一幕后面。在莎士比亚笔下所有的国王中,理查是世界上的天使[475]中他唯一不曾怀着崇敬心情加以庇护的。《李尔王》中爱德蒙登场的插话取自锡德尼的《阿卡迪亚》,为什么要把它填补到比历史还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去呢?”[476]
“那是威尔惯用的手法,”约翰·埃格林顿辩护说,“我们现在就不可能把北欧神话和乔治·梅瑞狄斯的长篇小说的摘录连结在一起。穆尔就会说:‘这有什么办法呢?’[477]他把波希米亚搬到海边,[478]让尤利西斯引用亚理斯多德。”[479]
“为什么呢?”斯蒂芬自问自答,“因为对莎士比亚来说,撒谎的弟兄、篡位的弟兄、通奸的弟兄,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的弟兄,是总也离不开的题材,而穷人却不常跟他在一起。[480]从心里被放逐,从家园被放逐,自《维洛那二绅士》起,这个放逐的旋律一直不间断地响下去,直到普洛斯彼罗折断他那根杖,将它埋在地下数噚深处,并把他的书抛到海里。[481]他进入中年后,这个旋律的音量加强了一倍,反映到另一个人生,照序幕、展开部、最高潮部、结局 [482]来复奏一遍。当他行将就木时,这个旋律又重奏一遍。有其母必有其女。那时,他那个已出嫁的女儿苏珊娜被指控以通奸罪。[483]然而使他的头脑变得糊涂、削弱他的意志、促使他强烈地倾向于邪恶的,乃是原罪。照梅努斯的主教大人们说来,原罪者,正因为是原罪,尽管系旁人所犯,其中也自有他的一份罪愆。[484]在他的临终遗言里,透露了这一点。这话铭刻在他的墓石上。她的遗骨不得葬在下面。[485]岁月不曾使它磨灭。美与和平也不曾使它消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各个角落,都变幻无穷地存在着。[486]在《爱的徒劳》中,两次在《皆大欢喜》中,在《暴风雨》中,《哈姆莱特》中,《一报还一报》中 ——以及其他所有我还没读过的剧作中。”
为了把心灵从精神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他笑了。
审判官埃格林顿对此加以概括。
“真理在两者之间,”他斩钉截铁地说,“他是圣灵,又是王子。他什么都是。”[487]
“可不是嘛,”斯蒂芬说,“第一幕里的少年就是第五幕中的那个成熟的男人。他什么都是。在《辛白林》,在《奥瑟罗》中,他是老鸨[488],给戴上了绿头巾,他采取行动,也让别人在他身上采取行动。他抱有理想,或趋向堕落,就像荷西那样杀死那活生生的嘉尔曼。[489]他那冷酷严峻的理性就有如狂怒的依阿古,不断地巴望自己内心的摩尔人[490]会受折磨。”
“咕咕!咕咕!”穆利根用淫猥的声调啼叫着,“啊,可怕的声音!”[491]
黑暗的拱形顶棚接受了这声音,发出回响。[492]
“伊阿古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啊!”无所畏惧的约翰·埃格林顿喊叫着说,“归根结底,小仲马(也许是大仲马[493]吧?”说得对:天主之外,莎士比亚创造的最多。”
“男人不能使他感到喜悦;不,女人也不能使他感到喜悦,[494]”斯蒂芬说,“离开一辈子后,他又回到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从小到大 [495],他始终是那个地方的一名沉默的目击者。在那里,他走完了人生的旅途。他在地里栽下自己的那棵桑树,[496]然后溘然长逝。呼吸停止了。 [497]掘墓者埋葬了大哈姆莱特和小哈姆莱特。[498]国王和王子在音乐伴奏下终于死去了。遭到谋杀也罢,被陷害也罢,又有何干?因为不论他是丹麦人还是都柏林人,所有那些柔软心肠的人们都会为之哀泣,悼念死者的这份悲伤乃是她们不肯与之离婚的唯一的丈夫。倘若你喜欢尾声,那么就仔细端详一下吧。幸福的普洛斯彼罗[499]是得到好报的善人、丽齐[500]是外公的宝贝疙瘩;里奇叔叔这个歹徒按照因果报应的原则被送进坏黑人注定去的地方了。[501] 结局圆满,幕终。他发现,内在世界有可能实现的,外在世界就己经成为现实了。梅特林克说:‘倘若苏格拉底今天离家,他会发现贤人就坐在他门口的台阶上。倘若犹大今晚外出,他的脚会把他引到犹大那儿去。’[502]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许多时日,一天接一天。我们从自我内部穿行[503],遇见强盗,鬼魂,巨人,老者,小伙子,妻子,遗蠕,恋爱中的弟兄们,然而,我们遇见的总是我们自己。编写世界这部大书而且写得很蹩脚的那位剧作家(他先给了我们光,隔了两天才给太阳[504]),也就是被天主教徒当中罗马味最足的家伙称之为煞神[505]——绞刑吏之神的万物之主宰;毫无疑问,他什么都是,[506]存在于我们一切人当中:既是马夫,又是屠夫,也是老鸨,并被戴上了绿头巾。然而倘若在天堂实行节约,像哈姆莱特所预言的那样,那么就再也不要什么婚娶;或者有什么光彩的人,半阴半阳的天使,将成为自己的妻子。”[507]
“我发现啦!”[508]勃克·穆利根大声说,“我发现啦?”
他突然高兴了,跳起来,一个箭步窜到约翰·埃格林顿的书桌跟前。
“可以吗?”弛说,“玛拉基接受了神谕。[509]”
他在一片纸上胡乱涂写起来。
往外走的时候,从柜台上拿几张纸条儿吧。
“已经结婚的,”安详的使者贝斯特先生说,“除了一个人,都将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再结婚。”[510]
他这个未婚者对独身的文学士埃格林顿·约翰尼斯笑了笑。
他们没有家室,没有幻想,存着戒心,每天晚上边摸索各自那部有诸家注释的《驯悍记》,边在沉思。
“你这是谬论,”约翰·埃格林顿率直地对斯蒂芬说,“你带着我们兜了半天圈子,不过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法国式的三角关系。你相信自己的见解吗?”
“不,”斯蒂芬马上说。
“你打算把它写下来吗?”贝斯特先生问,“你应该写成问答体。知道吧,就像王尔德所写的柏拉图式的对话录。”
约翰·埃克列克提康[511]露出暖昧的笑容。
“喏,倘若是那样,”他说,“既然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还能指望得到报酬呢。多顿[512]相信《哈姆莱特》中有些神秘之处,然而他只说到这里为止。派珀在柏林遇见的勃莱布楚先生正在研究关于拉特兰[513]的学说,他相信个中秘密隐藏在斯特拉特福的纪念碑里。派珀说,他即将去拜访当前这位公爵,并向公爵证明,是他的祖先写下了那些戏剧。这会出乎公爵大人的意料,然而勃莱布楚相信自己的见解。
“我信,噢,主啊,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您帮助我”[514]就是说,帮助我去信,或者帮助我不去信。谁来帮助我去信?我自己。[515]谁来帮助我不去信呢?另一个家伙。
“在给《达娜》[516]撰稿的人当中,你是唯一要求付酬的。像这样的话,下一期如何就难说了。弗雷德·瑞安[517]还要保留些篇幅来刊登一篇有关经济学的文章呢。”
弗莱德琳。他借给过我两枚银币。好歹应付一下吧。经济学。
“要是付一基尼,”斯蒂芬说,“你就可以发表这篇访问记了。”
面带笑容正在潦潦草草写着什么的勃克·穆利根,这时边笑边站起来,然后笑里藏刀,一本正经地说:
“我到‘大诗人’金赤在上梅克伦堡街的夏季别墅那里去拜访过他,发现他正和两个生梅毒的女人——新手内莉和煤炭码头上的婊子罗莎莉[518]——一道埋头研究《反异教大全》[519]呢。”
他把话顿了一顿。
“来吧,金赤,来吧,飘忽不定的飞鸟之神安古斯[520]。”
出来吧,金赤,你把我们剩的都吃光了。[521]嗯,我把残羹剩饭和下水赏给你吃。
斯蒂芬站起来了。
人生不外乎一天接一天。今天即将结束了。
“今天晚上见,”约翰·埃格林顿说,“我们的朋友[522]穆尔说,务必请勃克·穆利根来。”
勃克·穆利根挥着那纸片和巴拿马帽。
“穆尔先生,[523]”他说,“爱尔兰青年的法国文学讲师。我去。来吧,金赤,‘大诗人’们非喝酒不可。你不用扶能走吗?”
他边笑着,边……
痛饮到十一点,爱尔兰的夜宴。
傻大个儿……
斯蒂芬跟在一个傻大个儿后面……
有一天,我们在国立图书馆讨论过一次。莎士。[524]然后,我跟在傻乎乎的他背后走。我和他的脚后跟挨得那么近,简直可以蹭破那上面的冻疮了。[525]
斯蒂芬向大家致意,然后垂头丧气地[526]跟着那个新理过发、头梳得整整齐齐、爱说笑话的傻大个儿,从拱顶斗室走入没有思想的灿烂骄阳中去。
我学到了什么?关于他们?关于我自己?
眼下就像海恩斯那样走吧。
长期读者阅览室。在阅览者签名簿上,卡什尔·博伊尔·奥康纳·菲茨莫里斯·菲斯德尔·法雷尔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写下了他那多音节的名字。研究项目:哈姆莱特发疯了吗?歇顶的公谊会教徒正在跟一个小教士虔诚地谈论着书本。
“啊,请您务必……那我真是太高兴啦……”
勃克·穆利根觉得有趣,自己点点头,愉快地咕哝道:
“心满意足的波顿。[527]”
旋转栅门。
难道是?99lib?……?饰有蓝绸带的帽子……?胡乱涂写着……?什么?……看见了吗?
弧形扶栏。明契乌斯河缓缓流着,一平如镜。[528]
迫克[529]·穆利根,头戴巴拿马盔,一边走着,一边忽高忽低地唱着:
约翰·埃格林顿,我的乖,约翰,[530]
你为啥不娶个老婆?
他朝半空中啐了一口,唾沫飞溅。
“噢,没下巴的中国佬!靳张艾林唐[531]。我们曾到过他们那戏棚子,海恩斯和我,在管子工会的会馆。我们的演员们正在像希腊人或梅特林克先生那样,为欧洲创造一种新艺术。阿贝剧院!我闻见了僧侣们阴部的汗臭味。”[532]
他漠然地啐了口唾沫。
一古脑儿全抛在脑后了,就像忘记了可恶的路希那顿鞭子一样。[533]也忘记了撇下那个三十岁的女人[534]的事。为什么没再生个娃娃呢?而且,为什么头胎是个女孩儿呢?
事后聪明。从头来一遍。
倔强的隐士依然在那儿呢(他把点心拿在乎里[535]),还有那个文静的小伙子,小乖乖[536],菲多那囝囝般的金发。[537]
呃……我只是呃……曾经想要……我忘记了……呃……
“朗沃思和麦考迪·阿特金森也在那儿[538]……”
迫克·穆利根合辙押韵,颤声吟着:
每逢喊声传邻里,
或听街头大兵语,
我就忽然间想起,
弗·麦考迪·阿特金森,
一条木腿是假的,
穿着短裤不讲道理,
渴了不敢把酒饮,
嘴缺下巴的马吉,
活了一世怕娶妻,
二人成天搞手淫。[539]
继续嘲弄吧。认识自己。[540]
一个嘲弄者在我下面停下脚步,望着我。我站住了。
“愁眉苦脸的戏子,”勃克·穆利根慨叹道,“辛格为了活得更自然,不再穿丧服了。只有老鸨、教士和英国煤炭才是黑色的。”[541]
他唇边掠过一丝微笑。
“自从你写了那篇关于狗鳕婆子格雷戈里的文章,”他说,“朗沃思就感到非常烦闷。哦,你这个好窥人隐私、成天酗酒的犹太耶稣会士!她在报馆里替你谋一份差事,你却骂她是蹩脚演员,写了那些蠢话。你难道不能学点叶芝的笔法吗?[542]”
他歪鼻子斜眼地走下楼梯,优雅地抡着胳膊吟诵着:
“我国当代一部最美的书。它令人想到荷马。”
他在楼梯下止住了步子。
“我为哑剧演员们构思了一出戏,”他认真地说。
有着圆柱的摩尔式大厅,阴影交错。九个头戴有标志的帽子的男人跳的摩利斯舞[543]结束了。
勃克·穆利根用他那甜润、抑扬顿挫的嗓音读着那个法
版:[544]
人人是各自的妻
或
到手的蜜月
(由三次情欲亢进构成的、国民不道德剧)
作者
巴洛基·穆利根[545]
他朝斯蒂芬装出一脸快乐的傻笑,说:
“就怕伪装得不够巧妙。可是且听下去。”
他读道,清晰地:[546]
登场人物
托比·托斯托夫(破了产的波兰人)
克雷布(土匪)[547]
医科学生迪克
和一石二鸟
医科学生戴维
老枢葛罗甘(送水者)
新手内莉
以及
罗莎莉(煤炭码头上的婊子)
他摇头晃脑地笑了,继续往前走,斯蒂芬跟在后面。他对着影子——对着人们的灵魂快快乐乐地说着话儿:
“啊,坎姆顿会堂[548]的那个夜晚啊!——你躺在桑椹色的、五彩续纷的大量呕吐物当中。为了从你身上迈过去,爱琳[549]的女儿们得撩起她们的裙子!”
“她们为之撩起裙子的,”斯蒂芬说,“是爱琳最天真无邪的儿子。”
正要走出门口的当儿,他觉出背后有人,便往旁边一闪。
走吧。现在正是时机。那么,去哪儿呢?倘若苏格拉底今天离开家,倘若犹大今晚外出。为什么?它横在我迟早会无可避免地要到达的空间。
我的意志。与我遥遥相对的是他的意志。中间隔着汪洋大海。
一个男人边鞠躬边致意,从他们之间穿过。
“又碰见了,”勃克·穆利根说。
有圆柱的门廊。
为了占卜凶吉,我曾在这里眺望过鸟群。[550]飞鸟之神安古斯。它们飞去又飞来。昨天晚上我飞了。飞得自由自在。人们感到惊异。随后就是娼妓街。他捧着一只淡黄色蜜瓜朝我递过来。进来吧。随你挑[551]。
“一个流浪的犹太人,[552]”勃克、穆利根战战兢兢地装出一副小丑的样子悄悄地说,“你瞅见他的眼神了吗?他色迷迷地盯着你哩。我怕你,老水手。[553]哦,金赤。你的处境危险呀。去买条结实的裤衩吧。”
牛津派头。
白昼。拱形桥的上空,悬着状似独轮手车的太阳。
黑色的脊背方着豹一般的步伐,走在他们前面,从吊门的[554]倒刺下边钻了出去。
他们跟在后面。
继续对我大放厥词吧,说下去。
柔和的空气使基尔戴尔街的房屋外角轮廓鲜明。没有鸟儿。两缕轻烟从房顶袅袅上升,形成羽毛状,被一阵和风柔和地刮走。
别再厮斗了。辛白林的德鲁伊特祭司们的安宁,阐释秘义:在辽阔的大地上筑起一应祭坛。
让我们赞美神明;
让袅袅香烟从我们神圣的祭坛爬入他们的鼻孔。[555]
第九章 注释
[1]公谊会(参看本章注[436]),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不设神职,没有教会组织或圣事仪式,所办学校着重科学教育。 这里的公谊会教徒指爱尔兰国立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威廉?利斯特(1855一1920)。他译过邓斯特尔所著《歌德传》(1883)。
[2]“珍贵的篇章”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824)第4部第l3章至第5部第12章,写威廉怎样翻译、 改编并参加《哈姆莱特》的演出(他本人扮演哈姆莱特王子)。利斯特等人认为歌德是借威廉之口阐述自己对《哈姆莱特》一剧的见解。
[3]“挺身反抗人世无边的苦难”,见《哈姆莱特》第3幕第1场中哈姆莱特的独白。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4部第13章末尾,威廉说:“莎士比亚要描写的正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者身上。……他是怎样的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最后几乎失却他当前的目标……”
[4]“脚踏牛皮鞋”,见《尤里乌斯?恺撒》第1幕第l场中市民乙所说的话。
[5]、[6]五步舞,见《第十二夜》第1幕第3场中托出对安健鲁所说的话。
[7]“充满……涂地”是威廉?迈斯特对哈姆莱特的评论。
[8]“踩着‘科生多’舞步”,见《第十二夜》第l幕第3场中托比对安德所说的话。
[9]德?拉帕利斯(1400一1452),法国著名将军,原名杰克?德?查邦尼斯。他是骑士团首领,精力非常充沛,受重伤后,一直活跃到咽气前一刻钟。部下为了纪念他,作了一首通俗歌曲。其中有“直到死前一刻钟还活跃”句,后来讹传为“还活着”,因此,“德?拉柏利斯的真理”便成了废话的代用语。
[lO)约翰?埃格林顿,原名威廉?柯克柏特里克?马吉(1868一1961),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敏锐的批评家,是神秘派作家之一。
[11] 《失乐园》(1667)是弥尔顿晚年双目失明后,口授给女儿们完成的。
[l2]《魔鬼之烦恼》(1897)是玛利?科雷利(玛利?麦凯的笔名,1855一1924)所著小说。这里,约翰?埃格林顿是借此来挖苦斯蒂芬竟然想重写《失乐圆》, 并把魔鬼描绘成支持人类与耶和华开展斗争的浪漫主义英雄。
[13]克兰利,参看第一章注[29]。据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118页),下面的诗引自戈加蒂(见本书第一章注[1])的一首未发表的淫诗《医科学生迪克 和医科学生戴维》。
[14]根据希伯来、希腊、埃及和东方传统,”七”被认为体现着完美与统一,而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也把”七”当作完美的数字。威?巴?即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灿烂的七”见他的《摇篮曲》(1895年版)。
[15]奥拉夫是基督教传来之前,古爱尔兰的博学大师兼诗人。这里指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拉塞尔。
[16]靠服侍院士们并做些杂务以取得免费待遇的学生。他们的标志是头戴红色便帽。
[17]“魔鬼痛哭”与“淌下了天使般的眼泪”,系模仿《失乐园》卷l中的诗句。
[18)原文为意大利文,出自《神曲?地狱》第21篇末句。
[l9]克兰利是以乔伊斯的朋友J?F?伯恩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参看第一章注[29])。克兰利曾说,在威克洛(爱尔兰伦斯特省一郡,东临爱尔兰海)找得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二个有志之士,就足以拯救爱尔兰。
[2O]在叶芝的剧本《豁才子凯思林》(1902)中,凯思林这个贫穷的老姻象征着失去自由的爱尔兰。她说她那四片美丽的绿野(指爱尔兰的四省,阿尔斯特、伦斯特、芒斯特、康诺特)都被夺走了。“家里的陌生人”,指英国入侵者。
[21]原文为拉丁文。这是犹大出卖耶稣后,为了让他带来的人逮捕耶稣而对耶稣所说的话。见《马太福音》第26章第49节。拉比是犹太教中对老师的尊称。也指犹太教教士,犹太法学家。
[22]蒂那依利市在威洛克郡。
[23]这里,斯蒂芬转念想到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领导人,诗剧家约翰?米林顿?辛格(1871一1909)的独幕剧《狭谷的阴影》(1903年首演)。 女主角诺拉嫌丈夫对她太冷淡,丈夫连声“祝你一路平安”都没说,就把她赶出家门。诺拉和她所爱的一个好猎手一道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
[24]这里,斯蒂芬想起他给穆利根打电报事。电文参看本章注[282]及有关正文。
[25]指本?琼森(约1572一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及评论家。他曾赞誉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但又批评他缺少“艺术”。
[26]詹姆斯一世(1568一162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1603一1625在位)。
[27]指埃塞克斯伯爵三世(1591一1646),英国军人,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28]“无形的精神真髓”是爱尔兰诗人(笔名A?E?)拉塞尔喜用的语汇。例如在《宗教与爱》(1904)中,他就用此词来称赞叶芝写诗的才华。
[29]古斯塔夫?莫罗(1826――1898),法国象征主义画家,被认为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
[30]这里,斯蒂芬想起了当天中午杰?杰?奥莫洛伊告诉他的事。参看第七章“高风亮节之士”一节。
[31]通神学以“父、道、圣息”为三位一体。道和“万灵之父”均指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即基督。见《约翰福音》第1章。天人指亚当。
[32]原文为希腊语,即耶稣?基督。
[33]逻各斯是希腊哲学、神学用语。《约翰福音》第1章说,耶稣基督是道(逻各斯)成了肉身。指蕴藏在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 的神圣之理。
[34]英国社会改革家贝赞特夫人(1847一1933),一度为费边社会主义者, 后改信海?佩?勃拉瓦茨基的学说,成为神智学者。她曾在印度居住多年,在《古代智慧》(伦敦,1897)一书中对祭燔的戒律也做了研究。斯蒂芬在这里套用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第6篇《钵迦伏诛记》中的话。
[35]丹尼尔?尼科尔?邓洛普,爱尔兰通神论者。曾主编《爱尔兰通神论者》(约1896一1915),并用阿雷塔斯这一笔名发表文章。
[36]威廉?Q?贾奇(1851一1896),爱尔兰裔美国通神论者,曾协助海?佩?勃拉瓦茨基建立通神学会。
[37]见《尤利乌斯?恺撒》第5幕第5场。这原是安东尼对勃鲁托斯的评语。
[38]原指古罗马的祭司团阿尔瓦尔弟兄会。其职责是每年主持献祭以祈祷土地肥沃。成员共十二人,从最高阶层选出。从事通神论者运动的也有十二人, 并起名密教派或阿尔瓦尔。
[39]指西藏人库特?胡米大圣。他是海?佩?勃拉瓦茨基的两位大师之一。
[40]大白屋支部,参看第七章注[194],信奉神秘主义的拉塞尔等人均为其成员。
[41]按天主教的说法,修女在精神上已嫁给基督,故终生保持独身。
[42]原文作sophia。按照通神论的说法,系指人格化了的神之智慧。此外即指耶稣基督。
[43]库珀?奥克利夫人(1854一?)的教名是伊莎贝尔。不论在印度(1884年起)还是伦敦(1890年起),均为海伦娜的得力助手。
[44]“哼!哼!。和“呸!呸!”分别套用《哈姆菜特》第1幕第2场和第2幕第2场中哈姆莱特的独白。
[45]原文为德语。
[46]理查德?欧文?贝斯特(1872一1959),爱尔兰国立图书馆副馆长,曾把法国教授玛利?亨利?达勃阿?德?朱班维尔(1827一1910)的 《爱尔兰神话始末与凯尔特神话》译成英文,一九0三年在都柏林出版。
[47]柏拉图的《理想国》末尾,既有对现世劳苦的回顾,又有关于来世的冥想。而哈姆莱特在第3幕第1场的独白中,表示既不愿再肩负生活的重担,对不可知的来世又顾虑重重。
[48]指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的《诗学》被视力对诗人的肯定。柏拉图在《理想国》第10卷“诗人的罪状”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从荷马起, 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并在后面提及“为什么要把诗从理想国驱逐出去”。 这些话被视力讥讽,但人们常认为那直接表达了柏拉图的想法。
[49]升降流和伊涌均为诺斯替教(融合多种信仰的通神学和哲学的宗教,盛行于2世纪)用语。诺斯替教义主要讲人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升降流指宇宙行星的运行,伊涌指至高神所溢出的一批精灵。下文中的“神:街上的喊叫”,参看第二章注[78]及有关正文。
[50]逍遥学派即亚理斯多德学派。因古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在学园内漫步讲学而得名。
[5l]这里套用但丁的《神曲?地狱》和威廉?布莱克的《弥尔顿》。在《地狱》第34篇末尾,维吉尔背着但丁,下降到恶魔的臀部,又掉转来向上爬, 从地狱返回人间。威廉?布莱克的《弥尔顿》第1篇:“比人血中的红血球还小的每个空间/通向永恒/这个植物世界仅只是其一抹阴影。”
[52]套用圣奥古斯丁(353一430)所著《论灵魂之不朽》中的“行动的意志属于现在,未来经由这里涌入过去”一语。
[53]参看本章注[46]。
[54]这是道格拉斯?海德(参看第三章注[169])的一首诗的第一节。第二行的“麻木”,原诗中作“有教养”。此诗收入其所著《早期盖尔文学的故事》(伦敦,1894)中。海德于一八九三年创立盖尔语联盟,另外还著有《爱尔兰文学史》(1899)。
[55]这是海恩斯在当天早晨前往海湾的路上对斯蒂芬所说的话。见第一章末尾。
[56]窃贼指英国人。
[57]这是约翰?菲尔波特?柯伦(1750――1817)所写《我的心在跳动》一诗的第二句。绿宝石象征爱尔兰。首句是:“好爱琳,你的绿胸起伏,多么诱人。”
[58]原文作auricegg,是通神学名词,指卓绝的思想家。见波伊斯?霍尔特所编《通神论术语辞典》(伦敦,1910)。
[59]斯蒂芬?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他认为完美形式的真谛在于虚无之中,诗人的任务就是去感知那些真谛并加以凝聚、再现。
[60]灵性贫乏者,见《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下文中的腓依基人,见《奥德修纪》卷6中庙西卡公主的故事。腓依基人的岛上四季都有水果,男人擅长驾船,女人善于纺织,王侯十分富有。
[61]斯蒂芬?麦克纳(1872一1954),爱尔兰新闻记者、语言学家、哲学研究者。
[62]指马拉梅的散文诗《哈姆莱特与福廷布拉》(1896)。
[63]原文为法语。《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有哈姆莱待王子边读着一本书上场的场面。詹姆斯?乔伊斯的“内心的独白”的写作技巧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笔下的独白。评论家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认为,就像马拉梅对哈姆莱待所做的评述那样,一部《尤利西斯》所记录的就是布卢姆和斯蒂芬“边读着自己心灵的书边漫步”的情景。马拉梅暗示说,假装发疯的哈姆莱特所读的正是“自己心灵的书”,这一点引起了贝斯特先生的兴趣。
[64]以上四行的原文为法语。
[65]、[66]原文为法语。
[67]《心神恍惚的乞丐》是英国小说家、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一1936)作词、阿瑟?沙利文配曲的一首歌(“恳请你掷入我的小铃鼓一先令,/为了奉调南方穿土黄军服的先生们。”),在南非战争期间演唱,曾为英国士兵募集二万五干英镑。这里,斯蒂芬是站在爱尔兰人反对英国扩张主义的立场来引用此词的。
[68]“优秀的民族”指法国民族、含有挖苦意味。指《哈姆莱特》本来是一出包含深邃哲理的戏,马拉梅却把哈姆莱特王子看作是“心神恍惚的男子”。
[69]“豪华……凶杀剧”一语,出自《哈姆莱特与福廷布拉》(见本章注[62]。
[70]罗伯特?格林(1558一1592),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小册子作者,也是散文作家之一。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1610)直接取材于格林的田园诗《潘多斯托》(1588)。他在自传性小册子《百万忏悔换取的四便士的智慧》(1592)里说,贪婪乃是“灵魂的刽子手”。这个小册子附有致三个同时代戏剧家的信,其中攻击莎士比亚是“一只自命不凡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美化他自己”。
[71]屠夫的儿子指莎士比亚。他父亲约翰(?一1601)做过鞣皮手套工匠。英国文物家约翰?奥布里(1629一1697)是头一个提出他当过屠夫的。
[72]原文作“wieldingthesleddedpoleaxe”。《哈姆莱特》第1幕第1场中,霍拉旭曾说他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有一次在谈判决裂后他把那些乘雪橇的波兰人击溃在冰上时的神情。这是双关语。Poleaxe是宰牛斧,而Pole则为波兰人;sledded原为“乘雪橇”,这里解作“磨得锃亮”。
[73]事实上,《哈姆菜特》一剧中先后共死掉八个人。
[74]《天主经》首句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里把“天上”改成了“炼狱”。在《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中,哈姆莱特父王的鬼魂曾向他描述自已在炼狱中所受火焰烧灼的情景。
[75]这里把《哈姆莱特》一剧末尾的流血惨剧比作南非战争中的杀戮。当时英国士兵均穿土黄色制服。一八八七年在科克郡的一场骚乱 (参看第十三章注[265])中,有个叫普伦基特的上尉喊出“毫不迟疑地开枪”的口令。从那以后,这便成为爱尔兰人反对英国高压政策的口号。
[76]《哈姆莱待》第5幕以埋葬奥菲利娅开头,以哈姆莱特等众人惨死告终。
[77]斯温伯恩(见第一章注[12])曾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哀悼本森上尉》(1901)向死在布尔俘虏营中的本森上尉致哀,并赞扬英军为包括妇孺在内的布尔市民建立了集中营。有人立即撰文批评了他。他反驳说,既然布尔人虐待了英国战俘,把他们关入集中营也是应该的。
[78]在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一1837)第8章中,胖小子乔(沃德尔先生的仆人)向沃德尔太太报告他看见沃德尔小组怎样和匹克威克派的一个成员愉情。他劈头就说:“我想把你吓得毛骨悚然。”
[79]“听着,听着,啊,听着!”一语出自《哈姆菜特》第1幕第5场里鬼魂对哈姆莱特王子所说的台词。
[80]这是鬼魂接上一句所说的话,全句是:“要是你曾经爱过你亲爱的父亲――”
[81]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位于伦敦西北,展沃里克郡。
[8Z]原文为拉丁文。据天主教的神学,指《旧约》中的长老和先知的灵魂被幽禁的地方。作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俚语,则指牢狱。见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八世》第5幕第4场。
[83]巴黎园指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坐落于环球剧场附近的熊园。萨克逊大熊是该园的一头著名的熊。参看《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第1幕第1场末尾斯兰德的台词。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约1540-1596),英国航海家,一五八八年他曾率领舰队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按:当时池座里的观众都站着看戏,并向小贩买各种零食。
[84]“埃文河的天鹅”即指莎士比亚。这是本?琼森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623)的序诗中,对莎士比亚的称誉。
[85]“场子的构图”一语出自依纳爵?罗耀拉的《圣功》(1548)。
[86]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全靠日光照明,没有灯光。靠近后台处有个顶棚,叫作暗处,便于上演幽灵出没的场面。
[87]“是国王,又不是国王”,见弗朗西斯?鲍蒙特(1584-1616)与约翰?弗莱彻(1579-1625)合写的同名悲喜剧(1611)。
[88]英国诗人、戏剧家尼古拉斯?罗(1674-1718)查明,莎士比亚曾扮演过《哈姆莱特》中的幽灵这一角色。
[89]蜡布是裹在遗体上防腐用的。“隔着……蜡布”指幽灵在冥界。
[90]理查德?伯比奇(约1567-1619),英国演员,莎士比亚戏剧主要角色扮演者,善于饰演悲剧角色(尤其是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在伦敦时间他交往密切,并在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件纪念品。
[91]这是鬼魂对哈姆莱特王子所说的话,见《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
[92]莎士比亚的妻子于一五八五年二月二日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名叫哈姆奈特,一五九六年八月,十一岁上夭折,女儿名朱迪斯。
[93]“身穿……的丹麦先王的服装”,套用霍拉旭对鬼魂说的话,参看《哈姆莱特》第1幕第1场。
[94]参看第七章注[187]。
[95]“你在……人?”哈姆莱特正要求霍拉旭等人对见到先王鬼魂一事宣誓严加保密时,听见鬼魂在地下帮腔说:“宣誓!”于是朝着地下说了这句话。见《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
[96]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1838-1883),法国诗人、剧作家、短篇小说家。“我们的仆人们可以替我们活下去”出自他的遗作《阿克塞尔《(1890)。 主人公阿克塞尔子爵与美人萨拉一见钟情。他建议二人一道自杀,并且说了这句话。 叶芝在《秘密的玫瑰》(1897)中以此话作为引语,并献给了拉塞尔。
[97]这两句诗出自拉塞尔的三幕诗剧《迪尔德丽》(1902年初次上演,1907年出版)。马南南?麦克李尔,参看第三章注[31]。
[98]按斯蒂芬欠了拉塞尔一英镑,迄未偿还。
[99]诺布尔是英国古金币(用到1461年为止),一诺布尔相当于旧制六先令八便士。
[100]在后文中,斯蒂芬对林奇提及乔治娜。参看第十五章注[689]。
[1Ol]拉塞尔生在位于爱尔兰东北角上的阿尔斯特郡。
[102]这是哈姆莱特对波洛涅斯说的话,表示他向自己报告的消息已经陈旧了。见《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
[103]生命原理是亚理斯多德的术语,表示使纯系潜在之物变为现实。灵魂(或生命机能)是亚理斯多德在其《论灵魂》中所说的有生命机体的生命原理。 关于形态,参看第二章注[24]。
[104]斯蒂芬小时在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读书期间,曾因打碎了眼镜,未能写作文,因而被教导主任多兰神父用戒尺打了手心。他向校长康米神父提出申诉,才得以免除进一步的惩罚。参看《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书第1章。下文中的A?E?I?O?U?是英文中的五个元音字母。英大打借条常用IOU(即Ioweyou)。这里,就含有“A?E?我欠你”之意。
[lO5]这里,“她”指莎士比亚的妻子安?哈撒韦。莎士比亚是十八岁时绪婚的,安生于一五五六年,比他大八岁。莎士比亚死于一六一六年,而安一直活到一六二三年。
[106]原文为拉丁文。
[107]“萤光”,参看第八章注[179]。
[108]“犯了错误”指莎士比亚与安结婚;“脱了身”指莎士比亚于一五八六年左右把妻儿留在家乡,只身出走伦敦。
[109]据说苏格拉底的妻子赞蒂贝是个有名的泼妇。
[110]指苏格拉底的方法和目的就是要通过争辩来发现真理。
[111]据说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产婆。苏格拉底接二连三地向同他交谈的人提问题,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引导对方认识真正的美德。换言之,帮助思想的产生(即“助产术”)。
[112]据说默尔托(阿里斯泰得斯之女)是苏格拉底的第一个妻子。
[113]原文是拉丁文。
[114]原文作Socratididion,为苏格拉底的爱称,也可译为“亲爱的苏格拉底”。
[115]《灵魂的分身》(1821)是雪莱一首诗的题目,原文作Epipsychidion,系希腊文的复合词。
[116]闺训,原文作caudlelectures。caudle是供病人饮用的滋养饮料。英国剧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1803-1857)的连载作品《幕训》(1846)中的女主人公考德尔(Caudle)夫人整夜整夜地在闺房中教训丈夫,乔伊斯便据此造了这个词。
[117]这里,新芬党指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古希腊民主政体。
[l18]公元前三九九年苏格拉底被控为“不敬神”。苏格拉底不服,进行申辩,然而法庭仍以微弱的多数票判处他死刑。友人劝他逃跑,但他说,判处虽违背事实,但这是合法法庭的判决,遂服下狱卒交给他的毒药死去。
[119]罗拉德派是英人对威克里夫一派人的谑称,意为喃喃祈祷者。威克里夫(约1330-1384)是英国神学家, 他倡导的非正统教义和社会理论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一二八0年左右, 威克里夫与牛津大学的一些同事成立了最早的罗拉德派。 一三九九年曾被当作异端分子镇压。这里指托马斯?威廉?利斯特(见本章注[l])。他是个罗拉德派和公谊会教徒,不信天主教,因而公众对他存着戒心。
[120]《我撇下的姑娘》是爱尔兰小说家、歌词作家塞缪尔?洛弗(1797-1868)所作歌曲。
[121]指伦敦,参看第三章注[161]。
[l22]莎士比亚最早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第一0四六至一0四八行有关于地震的描绘。一五八0年英国发生过大地震,当时莎士比亚年十六岁。
[123]“可怜的小兔”(第697行)、“镂饰的缰绳”(第87行)、“蓝色的窗户”(指眼睛,第482行)均见《维纳新与阿都尼》。
[124]指莎士比亚在家乡与安?哈撒韦谈情说爱的事。
[125]凯瑟丽娜是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中的女主人公,霍坦西奥是她的妹妹比恩卡的求婚者。
[126]《热情的香客》(1599)是一部诗集,共二十首(或二十一首诗),其中四、五首系莎士比业所写。
[127]“男人的世界”一语出自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的双诗《相逢在夜间/分手在清晨》(1845)中的后者。
[128]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女角概由男童扮演。莎士比亚死后四十四年(1660),英国舞台上才初次由女演员扮演(奥瑟罗)中的苔丝狄蒙娜。
[129]男童指年轻时代的莎士比亚。
[130]据丹麦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乔治?布兰代斯(1842-1927)的《威廉?莎士比亚》(伦敦,1898)第10页,安未婚先孕,所以女方急于成婚。她与莎士比亚结婚后不足六个月就生了大女儿苏姗。
[131]“从心所欲”,见《十四行诗》第143首末行。
[132]“安自有她的办法”,原文作Annhathaway,与莎士比亚妻子的姓名安?哈撒韦(AnnHathaway)是双关语。
[133]“的的确确,他们该受责难”是奥菲利亚发疯后所唱的歌词中的一句,这里把原歌中的“他们”改成了“她”。见《哈姆莱特》第4幕第5场。
[134]“二十岁的甜姐儿”原出自小丑唱的歌词。由于安与莎士比亚结婚时是二十六岁、这里把原歌中的“二十”改成了“二十六”。见《第十二夜》第2幕第3场。
[135]“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是麦克白的一句独白,见《麦克白》第一幕第3场。
[136]“灰眼女神”指维纳斯。在伊丽莎白时代,灰眼睛(grayeyes)的gray,指blue(蓝)。《维纳斯与阿都尼》第140行有“我两眼灰亮,转盼多风韵”之句。
[137]“比自己年轻的情人”,套用《第十二夜》第2幕第4场中公爵对薇奥拉所说的话。
[138]见《皆大欢喜》第5幕第3场的歌第1段:“一对情人并着肩,走边了青青麦田。”
[139]见《皆大欢喜》第5幕第3场的歌词第2段。
[140]帕里斯(参看第二章注[69])与巴黎拼法相同,故与第三章注[100]有关正文形成双关语。
[141]高个子指拉塞尔(A?E?)他是《爱尔兰家园报》的主编。
[142]乔治?奥古斯塔斯?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一九0一年迁居都柏林,为筹建阿贝剧院做出贡献。
[143]原文作Pipe。当时美国波士顿有个女通神学家,名利奥诺拉?派珀夫人。但据阿尔夫·麦克洛赫莱因考证,这里的PiPer系指威廉·J·斯坦顿·派珀(Pyper,1868-1941)。他热衷于复兴爱尔兰语,并对通神学有兴趣。
[144]一首儿童绕口令的头一句。
[145]据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回忆说,“喻伽魔室”是戈加蒂对会议厅或公共设施的叫法。
[146]伊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重要女神。《揭去面纱的伊希斯――古今科学与通神学奥秘诠释》(1876)一书系海?佩?勃拉瓦茨基所撰,被她的门徒们视力通神学的经典著作。
[147]巴利语起源于北印度,公元前一世纪,成为标准的国际佛教语言。海?佩?勃拉瓦茨基的很多活动是和奥尔科特(参看第七章注[197])共同开展的,所以这里用复数(“他们”)。“我们”则指乔伊斯和戈加蒂(见艾尔曼著《詹姆斯?乔伊斯》第174页)。
[148]海?佩?勃拉瓦茨基在《揭去面纱的伊希斯》一书中说, 墨西哥人与古代巴比伦及埃及人的传统甚至所信仰的神明等都有共同之处。因此,阿兹特克族的逻各斯(参看本章注[33])是宇宙真理(“宇宙宗教”)的基础。阿兹特克族系操纳华特尔语的民族。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曾在今墨西哥中、南部延立帝国。
[149]超灵是由美国作家、十九世纪超验主义文学运动领袖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创造的哲学用语。他认为真正的智慧是通过“自然”领会神旨,强调人可以通过道德本性和直觉认识真理,从而发展成为超验主义观点。
[l50]原文为梵语。在通神学中,指进入涅磐(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后世也称僧人逝世为“涅磐”)境界。
[151]路易斯?H?维克托里是十九世纪末叶的爱尔兰诗人,著有诗集《尘埃中的想象》(伦敦,1908)等。
[152]T?考尔菲尔德?艾尔温(1823-1892),爱尔兰诗人、作家。
[153]“莲花……他们”一语套用爱诺巴勃斯对阿格立巴所作关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初次见面的描述。参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2幕第2场。
[154]据通神学的说法,松果体(亦称松果腺,一种内分泌腺)原是人的“第三只眼睛”,能够透视心灵,后来退化为松果体。
[155]根据佛教传说,佛陀是坐在菩提树(并不是芭蕉树)下修行,断除烦恼而成佛的。
[156]吞入灵魂者,吞没者指普在超灵(即神)。通神学家认为万人灵魂与普在超灵本为一体,作为它的火花的每一灵魂反复投生,又被其吞没,轮回不已。
[l57]原文作“Hesouls,shesouls,shoalsofsouls”。读音与下面这首民歌相近:S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意思是:“她在海滨卖海贝。”
[158]“他的幽魂……痛哭”使人联想到《神曲?地狱》第5篇中的“把成群的幽魂飘荡着,播弄着,颠之倒之……呼号痛哭……”之句。
[159]“万物……女魂栖”是路易斯?H?维克托里(见本章注[151])所作《震撼灵魂的模仿》(收入其诗集《尘埃中的想象》)一诗的头两句,是悼念一个四岁上夭折的娃娃的,作者引用时把“四年”改为“经年”。
[160]拉塞尔所编的这部《新诗集》出版于一九0四年五月。 拉塞尔在诗中沤歌爱尔兰传奇中的英雄和神,对其他同辈诗人影响颇大。诗集共收录了乔治?罗伯茨、帕德里克?科拉姆等九个诗人的诗作,但并没有选乔伊斯的作品。 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74页)。
[161]“必然……东西”一语模仿亚理斯多德所著《形而上学》中的论断。
[162]“必然性……所以……帽子”一语套用《哈姆莱特》第5幕第1场中掘墓者中的口气:“要是水来到他的身上把他淹死了,那就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淹死; 所以,对于他自己的死无罪责的人,并没有缩短他自己的生命。”
[163]“听着”:紧接着的一大段,是斯蒂芬所听到的人们关于新筹办的杂志的对话。
[164]帕德里克?科拉姆(1881-1972),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他的抒情诗保持了爱尔兰民间文学传统。其回忆录《我们的朋友乔伊斯》(1959)是与妻子玛丽(1887?-l957)合著的。他的诗《牲畜商》被收入《新诗集》。詹姆斯?斯塔基(1879-1958),后易名修马斯?奥沙利文,爱尔兰抒情诗人、编辑。《新诗集》里收有他的五首诗。
[165]乔治?罗伯茨(?-1952),爱尔兰文人,后来任蒙塞尔出版公司总编辑。
[166]欧内斯特?维克托?朗沃思(1874-1935),《快邮报》编辑(1901-1904)。
[167]这是《新诗集》中的主诗《一幅肖像》(科拉姆作)中的一句;后易题为《四十年代的穷学者》(《荒漠》,都柏林,1907)。
[168]苏姗?米切尔(1866-1926)是受拉塞尔影响的女诗人,《新诗集》里收有她的诗作。爱德华?马丁(1859-1923)是爱尔兰戏剧家。苏姗在《乔冶?穆尔》(纽约,1916)一书中写道,穆尔是个“天生的文学强盗”,“对爱德华?马丁进行掠夺”(第103页),将其剧本《一个镇子的故事》(1902)改写,易名《弯枝》。叶芝在《自传》(纽约,1958)中说穆尔是个“农民罪犯”,马丁是个“农民圣人”。这里的浪荡儿,原文作wild oats。Sow one’s wild oats指年轻时生活放荡,尤其指婚前性关系混乱。苏姗使用这个譬喻则指马丁与穆尔交往会吃大亏。
[169]乔治?西格尔逊博士(1838-1925),爱尔兰学者,他所从事的爱尔兰古代文学的翻译介绍,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端倪。
[170]愁容骑士是堂吉诃德的别称。
[171]托马斯?奥尼尔?拉塞尔(1828-1908),语言学家,曾致力于复兴凯尔特语。
[172]当时有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认为桔黄色百褶短裙是古代爱尔兰的标准衣着,然而近年来学者们认为,这并非爱尔兰的传统服装,这个印象主要是小说中的描写所造成的。
[173]杜尔西尼姬是堂吉诃德幻想的意中人。
[174)杰姆斯?斯蒂芬斯(1882-1950),拉塞尔所发现的爱尔兰诗人?小说家。
[l75]考狄利亚是李尔王最小的女儿。她是唯一孝顺老王的,却被她那黑心的姐姐害死。见《李尔王》。“李尔那最孤独的女儿”出自托马斯?穆尔的《菲奥纽娅拉之歌》。穆尔诗中的李尔指爱尔兰海神麦克李尔(见第三章注[31]),其女菲奥纽娅拉被后母用妖术变成一只天鹅。所以这是双关语。考德利奥是意大利语,发音与考狄利亚相近,含意为“深重的悲哀”。
[176]“偏僻荒蛮”出自法国人波旁公爵之口,见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五世》第3幕第5场,指的是英国式的粗俗与用法国磨光漆来象征的法国式典雅相对照。
[177]“天老爷符劳你”出自小丑试金石之口,见《皆大欢喜》第5幕第4场。
[178]指《爱尔兰家园报》(见第二章注[83])。前文中提到的哈里?费利克斯?诺曼(1868-1947)是该报主编(1899?-1905)。
[179]辛格,见本章注[23]。《达娜――独立思考杂志》是由约翰?埃格林顿和爱尔兰经济学家、新闻记者、编辑弗雷德?瑞安(1876-1913)合编的一份小杂志(1904-1905)。达娜见本章注[201]。
[180]十九世纪后半叶, 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崛起使人们重新对爱尔兰的语言、文学、历史和民间传说发生兴趣。 当时盖尔语(爱尔兰语)作为一种口语己经衰亡,仅在穷乡僻壤使用。盖尔语联盟于一八九三年成立,为维护盖尔语而进行斗争,直到一九二二年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承认爱尔兰语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为止。
[181]“鞋跟有多么厚,离天就靠近了多少”引自哈姆莱特对优伶所说的话,见《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
[182]英国基督教公谊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1624-1691)把得自上帝的“内心之光”(灵感)置于教条和《圣经》之上。利斯特是公谊会教徒,所以才把他和福克斯扯在一起。
[183]原作这段十分隐晦,作者在这里把莎士比亚和乔治?福克斯联系起来了。基督狐:公谊会认为,基督作为“内心之光”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里,因而是一只神秘不可思议的狐狸。福克斯与狐狸拼法相同,故语意双关。福克斯喜欢穿爱尔兰与苏格兰高原地区的那种鞣皮紧身裤。他和他的追随者一向都不尊重官员,不起誓,不纳税,因而经常被捕。他本人曾八次入狱。为了逃避追捕者,有一次他曾藏在枯树杈里。莎士比亚也曾逃离家乡,去了伦敦。“没同母狐狸打过交道”,福克斯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莎士比亚在伦敦过的是单身生活,利斯特终身未娶。“A得了女人们的心”,福克斯擅长于使人们――尤其是妇女(包括几个声名狼藉者)皈依宗教。他称那些严肃地为灵魂寻觅旧宿者为“温柔的人们”。巴比伦的娼妇一典出自《启示录》第17章第5节,她额上写着一个隐秘的名号:“大巴比伦―― 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法官夫人”:福克斯与兰开夏的法官费尔的遗婿玛格丽特结婚(1669)。“酒馆掌柜的娘儿们”: 风传莎士比亚曾在约翰?达维楠所开的皇冠客栈下榻,爱上了老板娘。她后来生下诗人、戏剧家威廉?达维楠爵士(1606-1668)。
[184]“狐入鹅群”是一种棋戏,由十五只鹅对付一只狐狸。鹅不得后退,狐狸却可以任意活动。
[185]“新地”大宅指莎士比亚于一五九七年在斯特拉特福镇买下的房产。他隐退后住在这里。
[186]维新太,参看第七章注[233]。
[187]在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第1幕第2场中,有个预言家警告恺撒要当心二月十五日。恺撒未加理睬,结果在这一天就遇刺身死(参看第二章注[16])。
[188]参看第二章注[17]。
[189]阿戏留是荷马史诗《伊里昂纪》中的英雄人物。他小时,母亲听了预言家的话,怕他死在未来的特洛伊战争中,故把他装扮成女孩子。“当阿戏留……名字呢?”这里套用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于一六五八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的句子,并将原文中的“藏”改成了“生活”。
[190]透特是古埃及所奉的神,原是月神,后司计算及学问。据说他发明了语言和文字,并为诸神担任文书、译员及顾问。
[191]“听见那位埃及祭司长的声音”,见第七章“即席演说”一节的结尾处。
[192]“旁人经受我们的置疑”,出自马修?阿诺德的关于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见于他1844年8月1日写给简?阿诺德的信)。
[193]此语模仿哈姆莱特王子咽气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外仅余沉默而已。”见《哈姆莱特》第5幕第2场。
[194]、[195]原文是爱尔兰语。
[196]小个子约翰是乔治?穆尔给约翰?埃格林顿起的绰号。
[197]“原谅我”一语出自安东尼在恺撒的遗体前发表的演说,见《尤利乌斯?恺撒》第3幕第2场。
[198]小王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据说它住在非洲沙漠上,凭借日光和呼出的气息就能使人丧命。它状似蛇、蜥和龙。美洲热带地区江河、溪流附近的树上至今还栖居着一种“王蜥”,因与小王相像而得名。
[199]原文为意大利文,引自拉蒂尼的《宝藏集》第1卷。
[200]布鲁涅托?拉蒂尼(l220-1294),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学者。但丁在《神曲》中对他十分推崇。他曾用法文撰写过一部散文体百科全书《宝藏集》以及该书的意大利文简编。
[201]达娜,又名达努。从爱尔兰到东欧,都崇敬它为大地之母,即阴性之元,诸神都曾受她哺育。
[202]“一天天地……身子”,套用英国评论家沃尔特?佩特(1889-1894)所著《文艺复兴》(1873)中的“把我们不断地编织起来再拆散”一语。
[203]此句模仿《辛白林》第2幕第2场中阿埃基摩的台词:“在她的左胸还有一颗梅花形的痣……”
[204]雪莱在长篇论文《诗之辩护》(写于1821年,1840年出版)中写道:“从事创作的精神犹如即将燃尽的煤……”
[205]霍索恩登的威廉?德拉蒙德(1585-1649)是最早用英语写作的苏格兰诗人。因定居于霍索恩登的庄园,故名。收入他的诗集《锡安山之花》(1630)里的散文《丝柏丛》中有一段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反思。斯蒂芬关于“过去的我成为现在的我,还可能是未来的我”这段话,受其启发,所以这里说德拉蒙德帮助我度过了难关。
[206]《哈姆莱特》第5幕第1场中,掘基人(小丑甲)说他是“小哈姆莱特出世的那一天……开始干这营生”的,接着又说,他已干了三十年。所以哈姆莱特那时已三十岁了。
[207]这里的“痣”是指品性上的污点,或缺点的烙印,参看《哈姆莱特》第1幕第4场开头部分哈姆莱特的独白。
[208]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他称赞莎士比亚晚年的戏剧(尤其是《暴风雨》)是“成熟的哲学剧”。
[209]尤利西斯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一个人物。布生代斯在 《威廉?莎士比亚》一书中说:“配力克里斯是个富于浪漫精神的尤利西斯”(见该书第585页)。
[2l0]这句话是写约翰?埃格林顿的,同时也影射船只失事后的尤利西斯和配力克里斯。
[211]玛丽娜是《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的女主人公,配力克里斯亲王的女儿。
[212)智者派见第七章注[254]。外典是不列入正典《圣经》的经籍。早期基督教会所称外典指真伪未辨、不宜在公共场合诵读的著作。本世纪初有些学者认为《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是莎士比亚的外典,即怀疑它不是莎士比亚所写。见查尔斯?W?华莱士:《关于莎士比亚的新发现:人中之人莎士比亚》(1910)。
[213]英国诗人、思想家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称赞莎士比亚始终走在“人类感情的康庄大道上”(《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托马斯?米德尔顿?雷逊编,1930)。
[214]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散文家。培根(Ba)这个姓,与熏猪肉拼法一样。同时,培根在《新学问》(1603)第1部中劝人照《耶利米书》第6章第16节(“你们要站在路上察看,探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行事,所以这里说他思想旧得“已经发了霉”。
[215]十九世纪中叶有些学者认为莎剧艺术水平之高,非培根莫属。但莎剧是由莎士比亚剧团的两位演员收集成书的,同时代剧作家本?琼森还为这部全集写了献诗,因此怀疑派的观点不能成立。
[216]美国小说家、社会改革家伊格内修斯?唐纳利(1831-1901)在《大密码》(1887,芝加哥、伦敦)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密码》(1900)二书中,曾试图论证莎剧系培根所作。
[217]A?E?,见第三章注[109]。马吉,见本章注[10]。
[218]彼得“克里斯琴”阿斯布琼逊所编、由G?W?达桑译成英文(1859)的一部北欧民间故事集(1842-1845),以其中的一篇《太阳之东?月亮之西》为书名。
[219]长生不老国(原文为爱尔兰语)是爱尔兰神话中的国度,由安古斯神(掌管青春、美和诗的神)所统治。据爱尔兰传说,英雄、说唱诗人莪相曾旅居此地。后来他违反禁令,踏上故乡的土地,遂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再也不能返回长生不老国了。
[220]这里把A?E?和马吉比作朝香者。
[221]这里把一首儿歌中的巴比伦这一地名换成了都柏林。
[222]布兰代斯,见本章注[l3O]。莎士比亚晚期的五个剧本为:《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1608)、《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1)、《亨利八世》(1612)。
[223]西德尼?李(1859-1926),英国莎士比亚专家,著有《威廉?莎士比亚传》(伦敦,1898)等。
[224]配力克里斯之女玛丽娜是在风暴中诞生在海船上的。
[225]米兰达是《暴风雨》中的女主人公。那不勒斯王子腓迪南对她一见钟情,说:“哦,你是个奇迹!”见第1幕第2场。
[226]潘狄塔是《冬天的故事》中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的女儿,在襁褓中就被遗弃,由牧人扶养大。
[227]莎士比亚的大女儿苏珊娜与约翰?霍尔结婚,于一六O八年生了个女孩,起名伊丽莎白,刚好相当于他写作生涯末期的开始。
[228]这是配力克里斯对玛丽娜所说的话。见《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第5幕第1场。
[229]布兰代斯说莎士比亚最宠爱苏珊娜(见《威廉?莎士比亚》第677页),所以使她当了“主要继承人”(见第686页)。这里对此说予以反驳。
[230]《做爷爷的艺术》(1877)是法国诗人、小说家维克托?雨果(1802-1885)所著的一部儿童诗集。变得伟大的艺术,原文为法语。法语中,爷爷是“grandpere”。贝斯特只说到“grandp”,听上去就跟“grand”(伟大)同音了。
[231]当天早晨斯蒂芬在海滨上曾问过自已:“大家都晓得的那个字眼是什么来着?”参看第三章注[177],下文“爱乃……满足”,原文为拉丁文。是摘录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第一卷第九十一章中的几个句子而成。
[232][]内的两段系根据海德一九八九年版(第161页第5至9行)补译。
[233]萧伯纳在喜剧《十四行诗和“黑夫人”》(1910)中描述了莎士比亚和“黑夫人”之间不幸的关系。戏里把“黑夫人”写成是玛利?菲顿,序言中却又驳斥了这一观点。玛利?菲顿(1578-约1647)自一五九五年起, 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侍从宫女。有人认为她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神秘人物“黑夫人”的原型。
[234]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爱尔兰新闻记者、文学家。他编过好几种杂志,主要的是《星期六评论》(1894-1898)。他在一八五五年创刊的政治、文艺、科学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后辑成一书: 《莎士比亚真人及其悲惨生涯》(伦敦,1898)。
[235]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开头写诗人对一贵族青年的友谊的升沉变化,是献给一位W?H?先生的(第1-126首),其次写诗人对“黑夫人”的爱恋(第127-152首),最后两首(第153-154首)收尾。
[236]威廉?赫伯特(约1506-1570)是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他自一五六八年起任王室事务总管。
[237]指当时风行的一种说法,莎士比亚“热恋”着威廉?赫伯特(见布生代斯:《威廉?莎士比亚》,第714页)。
[238]海雀是北极的潜鸟,每逢产卵季节,只下一颗布满大理石彩纹的卵,一般视为罕物。这里是指利斯特的头所产生的思想像海雀卵一样斑斓多彩。
[239]米莉亚姆是希伯来语中的玛利。这里指玛利?菲顿。
[240]公谊会教徒喜用老式字眼。
[24l]“年轻时的愿望,到了中年就会变为现实”是歌德的自传著作《诗与真》(1811-1814)第二卷开头部分的话。
[242]小贵族指彭布罗克伯爵。哈里斯(见本意注[234])认为,莎士比亚爱上了玛利?菲顿,并请彭布罗克给牵线。结果菲顿反倒和彭布罗克相好了。莎士比亚遂同时失去了意中人和朋友(见《莎士比亚其人及其悲惨生涯》第202页)。
[243]“花姑娘”,见《亨利四世》下部第3幕第2场中乡村法官夏禄的台词。
[244]“人人行驶的海湾”,见《十四行诗》(第137首第6行)。
[245]“少女时代声名狼藉”:哈里斯(第213页)写道,玛利?菲顿早在十六岁上就结婚,并和私通的男人生过三个孩子。
[246]“语言贵族”,见丁尼生的《致维吉尔》(1882)第2段。
[247]“笑而躺下”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种纸牌游戏。
[248]唐璜是十四世纪左右西班牙传说中的一个人物,是浪荡子的典型。唐是西班牙语“先生”的译音,或译作堂。西班牙名字“璜”,相当于英语中的“约翰”。
[249]套用《维纳斯与阿都尼》(第1052、1056行):“野猪在他的嫩腰上扎的那个大伤口……无不染上他的血,像他一样把血流。”
[25O]“毒……耳腔”,见第七章注[186]。
[251]“双背禽兽”,见第七章注[187]。
[252]“贫乏、寒伧的英语”,见本章注[54]及有关正文。
[253]“既愿意,又不愿意”,套用泽莉娜的唱词,见第四章注[51]、[52]及有关正文。
[254]“蓝纹……双乳”,见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1594)第407行。
[255]“梅花形的痣”,见莎士比亚的戏剧《辛白林》(1609)第2幕第2场末尾。伊摩琴是英国国王辛白林的女儿,绅士波塞摩斯之妻。波塞摩斯的朋友阿埃基摩用卑鄙手段瞥见了伊摩琴胸脯上的痣,事后向波塞摩斯谎称伊摩琴曾委身于他。
[256]“他的脸……来了”,见《哈姆莱特》第1幕第2场。在原剧中,霍拉旭对哈姆莱特王子讲述自己所看到的哈姆莱特王的鬼魂的情况,这里的“他”,则指莎士比亚。
[257]“各遂所愿”是《第十二夜》的副标题。
[258]“我的……了吗?”见《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21章第20节。
[259]原文为法语。
[260]斯蒂芬所打的电报,参看本章注[282]及有关正文。
[261]“没有实质的脊椎动物”指方才斯蒂芬所谈论的“与父同体的儿子”,即耶稣。
[262]德国谚语,原文为德语。
[263]佛提乌,见第一章注[113D。玛拉基是纪元前五世纪的小先知,同时又是勃克?穆利根的第二个名字。这是双关语,也可理解为“骗子玛拉基”。
[264]约翰?莫斯特(1846-1906),德裔美国装订工人,无政府主义者。因主张对凤凰公园凶杀案的参加者处理从宽而深得爱尔兰人心。
[265]据外典(见本章注[212]),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一度前往地狱,解救被囚在那里的善人的灵魂。
[266]“自我……生死者”,此段系谐谑地模仿天主教《使徒信经》的文体,纳入了瓦伦廷(见第一章注[115])、撒伯里乌(见第一章注[116])等人的非正统见解。
[267]这是天主教《荣福经》中的第一句,见《路加福音》第2章第14节。
[268]叶芝曾称誉当时的爱尔兰戏剧家辛格为埃斯库罗期(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再世,这里穆利根故意说得比叶芝更加夸大,把辛格比作莎士比亚。
[269]女演员指班德曼?帕默夫人(见第五章注[24])。海报上说那是她在都柏林第四百零五(不是8)次演《哈姆莱特》。
[270]爱德华?佩森?维宁(1847-1920)在《哈姆莱持之谜――试图解决一个老难题》(费城,1881)一书中说,哈姆莱特原是个女儿身,为了继承丹麦国的王位而装扮成男子。
[271]邓巴?普伦凯特?巴顿(1853-1937)自一九00年起曾任爱尔兰最高法院审判官。当时正在查寻线索,最后出版了《爱尔兰与莎士比亚的联系》(都柏林,1919)。尽管他并未说哈姆莱特是爱尔兰人,却在第五章中指出,哈姆莱特当王子的时候适值丹麦人统治爱尔兰的时期(弦外之音是,哈姆莱特有可能是爱尔兰的丹麦王子)。在序言中,他说自己曾受了审判官马登(见本章注[292])的一篇文章的启迪。
[272]鬼魂消失后,哈姆莱特曾对霍拉旭说:“不,凭着圣帕特里克的名义……”见《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 [273]王尔德在《威?休?先生的肖像》(伦敦,1889)中提出,《十四行诗》是献给一个叫作威利?休斯(Wil1ieHughes)的少年演员的(见《十四行诗》第20页第 7行:“充满美色的男子,驾御着一切美色”)。最初这是由英国学者托马斯?蒂里特(1730-1786)提出来的。
[274]休依?威尔斯(HughieWills)、威廉先生本人(Mr.Wil1iamHimself)的首字均为W?H?W?H?即威廉?莎士比亚本人一说原是德国人巴伦斯特尔夫提出来的。
[275]休斯(Hughes)、砍伐(hews)、色彩(hues),在原文中都是谐音字。
[276]王尔德(Wilde)与粗犷(wild)谐音。他因同性恋问题栽跟头(见第三章注[187])后不久,《笨拙》杂志上刊载了一首题为《斯温伯恩论王尔德》的讽刺诗,其中有“诗人名叫王尔德,但其诗是柔顺的”之句。
[277]贝斯特和斯蒂芬在同一座学校教书,这一天他们都从迪希校长手里领了薪水。
[278]“青春的华服”见《十四行诗》第2首第3行;“五种机智”见第9行,意指所有的机智。
[279]“欲望……面貌”,见布莱克的小诗。头一句是:“男人对女人有何要求?”
[280]“天神……吧”是福斯塔夫对福德大娘所说的话。作者引用时,把“我”改成了“他们”。见《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5幕第5场开头部分。
[281]参看斯蒂芬关于夏娃的冥想(第三章注[19]、[2O]和有关正文),以及《创世记》第3章第1至6节中蛇怎样引诱夏娃吃果子的故事。
[282]这句话引自英国诗人、小说家梅瑞狄斯(1828-1909)的《理查?弗维莱尔的苦难》(伦敦,1859年初版,乔伊斯引自1875年德国托奇尼兹版)。该书描写弗维莱尔男爵按照贵族的传统教育儿子,表现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
[283]康纳里是“船记”酒馆老板。
[284]原文为爱尔兰语。穆利根这几段话模仿辛格剧本语言的特殊风格。威克洛郡(辛格的出生地)以及爱尔兰西部的方言是把爱尔兰句法和古英语结合而成。辛格根据它来创造了富于诗意的戏剧语言。
[285]辛格经常称自己为流浪汉。他自一八九四年起留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以后又五次前往阿兰群岛,从岛民的生活中汲取写作素材。他和乔伊斯是一九O三年二月在巴黎结识的(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23页)。
[286]这里,斯蒂芬在回忆他和辛格在巴黎相聚的情景,并把辛格的脸比作哥特式古典建筑檐口的怪兽形排水装置。
[287]原文为西班牙语。
[288]据爱尔兰传说,莪相(参看本章注[219])一直活到五世纪,曾与帕特里克相遇,并告以结束于三世纪的英雄时代的事。
[289]克拉玛尔森林在巴黎西郊。辛格说他在那儿的森林里有个奇遇,可与莪相和帕特里克的邂逅相比拟。
[290]“我在林……傻子”是杰奎斯对公爵说的话,见《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
[291]参看本章注[1]。
[292]在《亨利四世》下篇第3幕第2场中,乡村法官夏禄提到一个未出场的人物――在牛津读书的威廉?赛伦斯。爱尔兰高等法院审判官道奇森?汉密尔顿?马登(1840-1928)在《威廉?赛伦斯少爷日记――莎士比亚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研究》中认为,莎士比亚有着丰富的野外运动的知识,对拉特兰伯爵(1576-1612)和夏禄的家乡了如指掌,从而揣测拉特兰伯爵曾替莎士比亚代笔。
[293]见第七章注[243]。
[294]见本章注[5]。
[295]公谊会教徒喜戴宽边黑帽,故有此绰号。
[296]《北方辉格》是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日报。《科克观察报》是科克的一家日报。《恩尼斯科尔西卫报》是恩尼斯科尔西(威克斯福德的一个市镇)的一家周报,每逢星期六出版。
[297]艾克依?摩西是十九世纪末叶爱尔兰人对试图挤进中产阶级的犹太人的蔑称。
[298]包皮的搜集者耶和华,见第一章注[61]。
[299]“生命的……火焰”,见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完成于1820,出版于1839)。
[300]“他”指布卢姆。加利利位于古代巴勒斯坦最北部地区(相当于今以色列北部)。“淡色的加利利”出自斯温伯恩的《普罗瑟派恩赋》(1866)。
[301]美臀,原文为希腊文。 美臀维纳斯是从罗马的尼禄金殿遗址发掘出来的一尊大理石雕像,收藏于那不勒斯国立美术馆。
[302]“天神……躲藏”,见斯温伯恩的长诗《阿塔兰忒在卡吕冬》(1866)。
[303]莎指莎士比亚。
[304]克丽雪达是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卜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中的一个逆来顺受的女子。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约1343-1400)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引用过她的故事。
[305]潘奈洛佩,见第七章注[255]。
[306]戈尔吉亚(纪元前约488-前约375),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见第七章注
[256]。
[307]在特洛伊战争中,尤利西斯等英雄藏在巨大的木马中潜入伊利昂城。后从里面跳出来,将该城攻陷。这里把引起这场战争的海伦比作母木马。
[308]他指莎士比亚。
[309]“封建主义艺术”,见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为诗集(十一月的枝桠)(1888)所写的前言《回顾曾经走过的道路》。
[310]沃尔特?雷利爵士(1554-1618),英国探险家。他曾两度被捕,关入伦敦塔。
[311)伊丽莎白(伊丽莎为昵称)一世是英国都锌王朝的最后一个君王。
[312]示巴女王(活动时期公元前l0世纪)以富有著称。传说示巴王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据《旧约?列王纪上》第10章记载,所罗门王在位期间,示巴女王曾亲自率领驼队,满载金钱财宝香料前往拜见。
[313]迪克是理查德的简称。见本章注[90]。
[314]原文为“without more ado About Nothing”。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译为《无事生非》)这里是反过来说的。
[315]阉鸡指妻子跟别人私通的丈夫。
[316]布兰代斯的《威廉?莎士比亚》(第19页)一书全文引用了约翰?曼宁汉姆在一六0一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对此所作的记载。曼宁汉姆听爱德华?柯尔说,有个市民的妻子看了迪克?伯比奇扮演的理查三世,便邀他当夜到自已家来。莎士比亚却抢先前往幽会,并按照那两人约好的那样,通报自己是“理查三世”。及至伯比奇来叫门,莎士比亚便派人这样向伯比奇回话。征服者威廉指英格兰第一位诺曼人国王威廉一世(约1028-1087)。他和莎士比亚同名。这里是莎士比亚自况,并把伯比奇比作同名的理查三世。
[317]菲顿,参看本章注[233]。
[318]这是波塞摩斯听信阿埃基摩的谎言(参看本章注[255]),对白己的妻子伊摩琴所作的猜疑。见《辛白林》第2幕第5场。
[319]以东拉德?梅西(1828-1907)为代表的几位英国十九世纪学者认为潘奈洛佩?里奇(见第七章注[259])乃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黑夫人”的原型。
[320]这是乔伊斯在巴黎王后大道(塞纳河右岸的闹市)所听到的娼妇拉客套话。原文为法语。苏是法国旧铜币,二十苏合一法郎。
[321]威廉?戴夫南特爵士(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和剧院经理。 其母在牛津经营皇冠客栈。莎士比亚在往返伦敦途中总在这里下塌。有人认为她是“黑夫人”的原型。戴夫南特是莎士比亚的教子,也可能是他的儿子。他曾于一六六七年与批评家、剧作家德莱顿(1631-1700)一道改编莎剧《暴风雨》。
[322]加那利(ary)是一种白葡萄酒,产于大西洋北部的加那利群岛。此字与“金丝雀”拼法相同。
[323]安尼科克的原文是Anycoy的意思是“任何”,cock原指公鸡,与其他动物名连用时则指雄性。所以此词就含有“只要是公的”之意。 法国有个圣女叫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穆利根把她的姓略加改动,就成了俏皮话。
[324]哈利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他曾结过六次婚。他死后,接连由他的三个子女(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这里指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325]“附近……女友”一语出自草地?丁尼生(见第三章注[2O4])的《公主,杂录》(1847)一诗的序。
[326]这里把莎士比亚的妻子比作潘奈洛佩。
[327]“干吧,干吧。”套用《麦克白》第1幕第3场中女巫甲的话。
[328]约翰?杰勒德(1545-1612),英国植物学家。他在离伦敦霍尔本的住所不近的费特小巷(毗邻舰队街)拥有一座花园。
[329]“像……风信子”,引自阿维拉古斯所说的话,见《辛白林》第4幕第2场。引用时将“你”改成了“她”。
[33O]“朱诺……紫罗兰”,引自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的女儿潘狄塔对波希米亚王子弗罗利泽所说的话,见《冬天的故事》第4幕第8场。
[331]语出自关于老夫少妻的一个笑话。牛津某学究对朋友说,他的年轻妻子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朋友说:“天哪,你猜疑谁呢?”参看第十三章注[545]。
[332]参看本章注[242]。
[333]“不敢说出口的爱”,指同性恋。
[334]查伦顿是距巴黎东南五英里的一座小镇。
[335]“未被……的胎”,参看《十四行诗》第3首,梁宗岱译为:“因为哪里会有女人那么淑贞――她那处女的胎不愿被你耕种?”
[336]“水性扬花的女子”指苏格拉底之妻。“撕毁床头盟”出自《十四行诗》第152首。
[337]指哈姆莱特王子的亡父的鬼魂。
[338]玛丽指莎士比亚的母亲玛丽?阿登(死于1608),约翰指莎士比亚的父亲(死于1601)。
[339]威伦是威廉的爱称,指莎士比亚(死于1616),其妻安死于一六二三年。
[340]琼(1558-1646)是莎士比亚的姐姐。除了莎士比亚,她还有三个弟弟:爱德蒙(1569-1607)、理查德(1584-1613)、吉尔伯特(1566-?)。吉尔伯特也和琼一样长寿,只比她死得略早一点。
[341]朱迪斯是莎士比亚的二女儿。
[342]苏姗是苏珊娜的爱称,莎士比亚的大女儿。她死于一六四九年,她丈夫约翰?霍尔死于一六三五年。
[343]莎士比亚的外孙女伊丽莎白于一六四七年居孀,后再嫁给鳏夫约翰?伯纳德。这里借用哈姆莱特王子指责他母亲的话:“简直就跟杀了一个国王再去嫁给他的兄弟一样坏。”见《哈姆菜特》第1幕第4场。
[344]自从安嫁给莎士比亚(1582),直到丈夫去世,关于安唯一的记载是她曾向过去替她父亲牧过羊的托马斯?惠廷顿借过四十先令。
[345]“天鹅之歌”见《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一1594)第1613行至1649行。作者把鲁克丽丝比作天鹅。她受辱后,嘱丈夫为自己报仇雪恨,并愤而举刀自刎。
[346]莎士比亚于一六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要求他的律师起草第二份遗嘱,其中写道:“我把我次好的床和全部家具留给我妻子。”
[347)“要点”,原文为德语。从这一行到“喔啊!”可以用德国作曲家、音乐戏剧家理查德?瓦格纳(18l3一1883)的《莱茵黄金》中少女合唱的曲调来唱。
[348]参看本章注[139]及有关正文。
[349]参看本章注[2O]、[23]。
[350]原文作Mr?Sedbest Best。贝斯特(Best)这个姓,与“最好的”拼法相同。
[351]原文是拉丁文,指分居。根据一八五七年修订的婚姻法,离婚之前必须经历分居的过程。
[352]这里,古人指迪奥杰尼斯?莱厄蒂尤斯(活动于公元前3世纪)。他在《哲学家传记》一书中写道,亚理斯多德在遗嘱中曾提出与自已的妻子合葬,让妾赫皮莉斯终生住在他的一幢房子里。亚理斯多德是斯塔基莱特人,顽童和异教贤人均指的是他。内尔?格温?赫尔派利斯(1650一1687),英国女演员,是英王查理二世(1630一1685)的情妇。他的遗言是:“不要让可怜的内尔饿肚子。”
[353]语出自流氓奥托里古斯所唱的歌,见《冬天的故事》第4幕第2场。
[354]爱德华?多顿(1843一1913),爱尔兰评论家、传记作者、诗人。他的《莎士比亚:关于他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研究》(伦敦,1875) 是第一部全面和系统地研究和介绍莎士比亚的英语专著。
[355]原文作Besteglinton。贝斯特和约翰?埃格林顿是两个人。这里把两个人的姓连在一起。也可译为贝斯特?埃格林顿。
[356]《尤利西斯》初版本系于一九二二年由西尔薇亚?毕奇(1887一1962)在巴黎所开的莎士比亚书店出版。
[357]多顿常说莎士比亚是人民的诗人,为人民而写作的诗人。他住在都柏林郡拉思加尔海菲尔德路的海菲尔德寓所。
[358]多顿在《莎士比亚》(1877)一文中写道:“十六世纪末叶,英国的生活中充满了欣喜欢乐。”
[359]博士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一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既吃了……手里”:英国谚语,指凡事不能两头都占着。
[360]美的棕榈枝,参看第七章注[255]、[258]及有关正文。这里把艺术家(我们)比作美丽的海伦,把道德家比作贞节的潘奈洛佩。
[361]长口袋指吝啬的富人。
[362]托德是英国重量单位。一托德合二十八磅。
[363]约翰?奥布里(1626一1697),英国文物研究者、作家,以替同时代人撰写传记小品而闻名。
[364]一五九四年二月,女王侍医、犹太人洛德利格?洛佩斯被控接受了西班牙间谍的贿赂,企图毒死女王和西班牙叛教者安东尼奥?佩雷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就当众被处以绞刑,因双脚着地,被肢解时尚未咽气。三年后,莎士比亚写成《威尼斯商人》。
[365]伪哲学家指詹姆士一世(1566一1625),他曾在苏格兰发表论文《恶魔研究》(1597),表述对精神世界感到恐惧的想法。 一六0三年伊丽莎白一世逝世后,他继承英国王位,在时间上与《哈姆莱特》(1601)和《麦克白》(1606)的写作日期接近。
[366]无敌舰队(见第三章注[63]),原文作Almada。《爱的徒劳》(1594)中有个名叫亚马多的西班牙怪人。西德尼?李在《威廉?莎士比亚传》一书中认为,作者写此剧时显然联想到了无敌舰队的溃败。剧名中的lost一词,亦作“溃败”解。
[367]马弗京是南非开普省北部城镇,英国要塞所在地。在布尔战争(英国为一方、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为另一方的战争)中,当被围困七个多月的英军于一九00年五月迫使布尔军队撤退后,英国曾举国欢腾。“马弗京的狂热”指对令人难以首肯的事所表示的过度狂热。
[368]耶稣会士指英格兰的耶稣会隐修院院长亨利?加尼特(1555一1606)。他因参加“火药阴谋”(企图在1605年国会开会时杀死信仰新教的英王詹姆斯一世,以报复当局对天主教徒施加酷刑),被捕处死。在法庭上, 他曾作一套暖昧含糊的理论替自己辩护。西德尼?李在《威廉?莎士比亚传》(第239页)中认为, 莎士比亚写《麦克白》一剧中门房的下述独白时,曾联想到加尼特:“一定是什么讲起话来暖昧含糊的家伙。……他那条暖昧含糊的舌头却不能把他送上天堂去。”(见第2幕第3场)
[369]西德尼?李(第252页)认为,《暴风雨》(1611)的写作受到了“海洋冒险”号船员们经历的启发。该船于一六0九年开往美国弗吉尼亚州。途中,在百慕大遇难。一六一0年,船员们历尽风险始得生还,在英国引起轰动。勒南,见本章注[208]。
[370)“我们的美国堂弟”,参看第七章注[179]。凯列班为《暴风雨》中野性而丑怪的奴隶。为了纪念十九世纪爱尔兰移民扮演这个角色, 人们在凯列班前加上帕齐(爱尔兰人常用的帕特里克一名的别称)这个教名。
[371]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梅尔斯(1565一1647)在所著文摘《帕拉迪斯?塔米亚》(1598;现代版本1938)一书中称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组诗为“馨美的十四行组诗”。
[372]仙女见于爱德蒙?斯宾塞的长诗《仙后》,影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是红头发,所以绰号叫“红毛贝斯”。“胖处女”指的也是她。英国评论家、剧作家约翰?丹尼斯(1657一1734)曾把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改写一遍,易名《滑稽的情郎》。他在题辞中重述了莎士比亚当年是根据女王授意而写《温》剧的说法。女王想要看到福斯塔夫在一出戏中堕入情网。在《温》剧第3幕第3场中,福斯塔夫藏进一只洗衣筐,被人连同脏衣服扔迸泰晤士河。
[373]原文为拉丁文“尿”字的四种变格,与英语“掺合”一词拼法相近。
[374]都柏林大学学院院长约瑟?达林顿(1850一1939)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主教信条》(见1897一1898年度《新爱尔兰评论》)一文中曾说莎士比亚是个天主教徒。
[375]原文为拉丁文。关于罗马雄辩家哈帖里乌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一公元14)曾说:“他应该受到抑制。”英国评论家本?琼森在其遗著、 评论文集《木材,又名关于人与物的发现》(1641)中,曾引用此语来评述莎士比亚。这里,把“他”改成了“我”。
[376]这是双关语:一方面暗喻十九世纪末叶德国产品开始泛滥于欧洲市场,同时又讽刺德国学者喜用“我们的莎士比亚”一词。
[377)法国磨光漆,参看本章注[176]。
[378]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一1834),英国湖畔诗人、思想家。 他把莎士比亚看成是完美无缺的作家。“拥有万众之心的人”是他在《文学传记》(1817)第15章中对莎士比亚的称誉。
[379]、[380]原文为拉丁文。
[381]原文为爱尔兰语。
[382]“从今天起,……毁灭啦!”出自辛格(见本章注[23])的独幕悲剧《骑马下海的人》(1904年上演),写老妇莫尔耶的丈夫和六个儿子全溺死在大海中。
[383]弗洛伊德(见本章注[359])和个体心理学理论的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一1937)均为奥地利人,所以这里称之为新维也纳学派。
[384)“用钢圈……上”,这里套用波洛涅斯对雷欧提斯所说的话。原话是:“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见《哈姆莱特》第l幕第3场。
[385]神老爹是布莱克在同名的诗中所塑造的凶恶的神明形象。
[386]“笑眯眯的邻居”出自里昂提斯的独白,见《冬天的故事》第l幕第2场。
[387)“不可贪……公驴”,套用《摩西十诫》,原话作:“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奴婢、牛驴,或其他东西。”见《出埃及记》第20章第17节。
[388]本?琼森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623)前面的序诗中,曾两次用“温和的莎士比亚”一词。这里把莎士比亚改为威尔(威廉的简称)。
[389]威尔(WiII)如作为人名,首字应大写。小写则可作愿望、意志及遗嘱解。
[390]原文为拉丁文。
[391]这是拉塞尔的《小路上唱的歌》(《诗集》,伦敦,1926)一诗的头两句。
[392]“那蒙面皇后”是剧中剧里伶甲的台词,皇后指伶后,见《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
[393]尿盆的原文作jordan(俚语),与《圣经》里经常提到的约旦河拼法相同,而water既指水,又暗指尿。有些清教徒把约旦河的水视为圣水,装瓶带走,用于施行洗礼时。
[394]《信徒长裤上的钩子和扣眼》(伦敦,约1650)是清教徒的一个论慈善事业的小册子;后者则是根据清教徒的另一个小册子《 使灵魂虔诚地打喷嚏的神圣的鼻烟盒》(伦敦,1653)的题目略作改动。
[395]原文为拉丁文。olologos(史学家)是把一个希腊字加以拉丁化了。
[396]这里套用《马太福音》第10章第36节中耶稣的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397]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2幕第2场中,朱丽叶的话:“ 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这里指约翰?埃格林顿放弃自己原来的姓(马吉),并背叛新教,参加神秘主义者的团体。参看本章注[l0]。
[398]原文为苏格兰方言,套用彭斯的《致自命清高的人》一诗的标题。
[399]在《亨利四世上篇》第3幕第3场中,福斯塔夫抱怨说,“那些坏朋友”(指亲王哈尔等人)害得他好久没进教堂了,并控告他们“偷酒杯”。
[400]安特里姆是北爱尔兰东北部一郡。
[401]埃格林顿在《关于硕果仔存者的两篇短论》(1896)中,对华兹华斯给予了很高评价。这里把来自农村的埃格林顿之父(一个新教牧师)比作华兹华斯。
[402]“人”,原文为爱尔兰语。这里把大马吉(即埃格林顿之父,参看本章注[397])比作华兹华斯早期诗歌里的人物马修,一个头发花白的乡村教师。
[403]蓬头乱发的庄稼汉,见《理查二世》第2幕第1场。
[404]短裤,见《亨利五世》第3幕第7场。
[405]布袜子,见《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
[406]“十座树林的泥污”,套用叶芝的戏剧《凯瑟琳伯爵夫人》(1895)第l场中谢姆斯的妻子的台词。
[407]“手执野生苹果木杖”,出自华兹华斯的《四月里的两个早晨》(1799、1800)的末段。这是以马修为主人公的诗中的一首。
[408]这里,斯蒂芬回忆起穆利根所说的话。见本章注[300]及有关正文。
[409]鲍勃?肯尼是北都柏林济贫法联合医院的一位外科大夫。斯蒂芬的母亲生前曾在这里接受施诊。
[410]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于一六0一年去世,《哈姆莱特》是在这之后数月内写成并上演的。
[411]莎士比亚是一五八二年结婚的。在一六0一年,他的两个女儿苏珊娜和珠迪丝分别为十八岁和十六岁。
[412]原文为意大利文。见《神曲?地狱》第1篇首句。当时认为人的平均寿命为七十岁。
[413]大学生指哈姆莱特王子。父王遇害时,他正在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
[414]在《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中,父王的幽灵对哈姆莱特王子说,他的“灵魂……被判在夜晚到处徘徊……”
[415]“一小时……烂下去”,见《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中杰奎斯对公爵所说的话。引用时,将“我们”改成了“它”。
[416]神秘的遗产指天才。
[417]卡拉特林是《十日谈》第九天第三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他的两个朋友串通大夫哄骗他说,他怀了孕,他竟信以为..真。
[418]原文为拉丁文。参看第二章注[38]。
[419]“母爱……东西”,是克兰利对斯蒂芬所说的话,参看《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5章。
[420]原文为拉下文。
[421]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统治者弥诺期触怒了海神波寒冬。作为报复,波寒冬使弥诺斯之妻帕西淮爱上一头白公牛,遂生下半人半牛怪物弥诺陶洛斯。
[422]原文为法语。本世纪初巴黎红灯区的一条街。
[423]撒伯里马,参看第一章注[116]。
[424]斗犬阿奎那指托马斯?阿奎那,参看第一章注[88]。
[425]拉特兰指第五代拉特兰伯爵罗杰?曼纳斯(1576一1612)。有人认为莎剧是他或培根所写(见本章注[214])。也有人认为是莎士比亚的保护人、南安普敦伯爵三世(1573一1624)所写。这里,原文把他们的名字连到一起。参看本章注[215]。
[426]莎士比亚的喜剧《错误的喜剧》中有两对同名的孪生兄弟,所以闹出一连串误会和笑话。
[427]“大自……的”一诗出自埃格林顿的《小河中的卵石》(都柏林,1901)一书。
[428]这是文字游戏。野蔷薇(egIantine)和埃格林顿(Eglintone)拼音相近。“盘绕……薇”一词,出自弥尔顿的短诗《快乐的人》(1632)。
[429]“他……父亲”,参看第一章注[116]。
[430]在希腊宗教里,雅典娜是城市的保护女神和明智女神。她没有母亲,是从宙斯的前额中跳出来的。品达罗斯还说,是赫菲斯托斯用斧头劈开宙斯的头,便她出生的。
[431]“关键……戏!”是哈姆莱特的一句独白,见《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
[432]莎士比亚的母亲名叫玛丽?亚登,而《皆大欢喜》一剧是以亚登森林为背景的。
[433]伏伦妮姬是《科利奥兰纳斯》(1607)的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
[434]埃及肉锅的典故,见第三章注[81]。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秀色可餐,所以这里把她比作肉锅。
[435]克瑞西达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女主人公,系向希腊投降的特洛亚祭司之女。
[436]作者这里是利用“公谊会”(音译为贵格会)作文章。“贵格”(quake)原意为“震动”。 此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于一六四八年在基督教内部闹过一次革命,反对一系列教条,自称“震动派”(Quaker,即造反之意), 因而备受迫害。此会反对一切战争,两次大战均拒服兵役。参看本章注[1]。
[437]参看本章注[340]。
[438]伍尔(WulI)是威廉的俗称。西德尼?李(参看本章注[223])在《威廉?莎士比亚传》(第42页)中转述了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一剧中扮演仆人亚当的故事。
[439]吃香肠说明吉尔伯特拿到的是池座里的站票。参看本章注[83]。
[440]“姓名有什么意义?”出自朱丽叶的独白,见《罗密欧与朱丽叶》第2幕第2场。
[441)()内的音乐术语均为意大利文,下同。
[442]这两句诗出自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参看第一章注[l])的未出版的黄色小诗《医学生迪克和医学生戴维》。作者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医时, 与乔伊斯同学。毕业后行医之余写了几本书。
[443]《李尔王》是一六0六年圣诞节期间在宫廷上演的;次年年底,爱德蒙?莎士比亚逝世,下葬于萨瑟克郡。
[444]“可是谁……名声”是旗官伊阿古在摩尔族贵胄奥瑟罗面前诽谤奥瑟罗的副将凯西奥而说的话。见《奥瑟罗》第3幕第3场。
[445]指《十四行诗》第135、136首。
[446]冈特?欧?约翰(1340一1399)是英格兰亲王,兰开斯特公爵。在《理查二世》第2幕第1场中,年老多病的他念念不忘自已的姓氏,说了不少俏皮话。
[447]盾面的纹章上自右上至左下的右斜线。
[448]原文为拉丁文,引自乡人考斯塔德对侍童毛子说的话。见《爱的徒劳》第5幕第l场。
[449]见本章注[440]。
[450]丹麦天文学家布拉赫?第谷(1546一1601)于一五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发现仙后座中出现了一颗比金星还亮的新星,起名第谷新星。按莎士比亚出生于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当时是八岁半。
[451]喷火龙见于北欧神。
[452]仙后座内的五颗亮星,如以线联接,形似拉丁字母W。那是“威廉”的第一个字母。
[453]肖特利是安?哈撒韦的娘家所在的沃利克州一村庄。
[454]一五七四年三月以后,第谷新星不再能用肉眼看到。当时莎士比亚是九岁十个月。
[455]“求爱”和“占有”,摘引自萨福克的旁白,原话是:“她既美如天仙,就该向她求爱;她既是个女人,就能将她占有。”见《亨利六世》第5幕第3场。 此处反过来,改成男人被女人求爱和占有。
[456]见《驯悍记》第2幕第l场中彼特鲁乔的台词。
[457]原文为希腊语。
[458]原文(BousStephanoumenos)为学生们所杜撰的希腊语。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4章中,当立志做艺术家的斯蒂芬向海滨走去时,同学们一遍遍地这么朝他喊叫。
[459]原文为意大利语。杰林多是男子名。文中最后的S?D,是双关语。既是斯蒂芬、迪达靳斯的首字,又是意大利语“suadonna”(“他的情妇”)的缩写。
[460]参看《出埃及记》第13章第22节。原典作“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
[461]原文作Stephanos,系希腊文,意思是王冠、花环。
[462]参看第一章注[9]。
[463]纽黑文是英格生东萨塞克斯郡的港口城镇。濒临英吉利海峡,与巴黎西北的海港迪耶普遥遥相望。
[464]原文作lapwing,又名田凫。在《哈姆莱特》第5幕第2场中,霍拉旭说:“这一只风头麦鸡顶着壳儿逃走了。”从语源上来看,这是由lap(跳跃的过去式)和wing(飞行)组成的复合词。wing又作“翼”解,故联系到下文中伊卡洛斯的蜡翼。
[465]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迪达勒斯之子。他借助于蜡翼飞上天空,随父逃离克瑞特。但因违背父嘱,飞得过高,蜡翼为太阳融化,遂坠海而死。
[466]原文为拉丁文。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五章末尾,斯蒂芬也曾以伊卡洛斯自况,呼吁道:“老父亲,古老的巧匠,现在请尽量给我一切帮助吧。”
[467]格林指德国民间文学研究者雅科布(1785一1863)和威廉(1786一1859)。他们合编的童话集里有以弟兄为题材的故事,但以睡美人为女主人公的《白雪公主》里,并没有这样的情节。
[468]贝斯特弟兄是本世纪初在都柏林开业的两个著名的爱尔兰律师。贝斯特和“最好”(best),拼法相同。
[469]帕特里克?S?迪宁神父(1860一1934),爱尔兰作家、翻译家、编辑及语言学家。
[470]这里套用约翰?弗莱彻(1579一1625)所写《两位高贵的亲族》一剧的题目。有些学者认为,莎士比亚也多少参与了该剧的写作。
[471]据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144页),乔伊斯的胞弟斯坦尼斯劳斯曾一度在药剂师的店里当店员。
[472]在《皆大欢喜》第1幕第2场中,西莉娅曾说:“傻瓜的愚蠢往往是聪明人的砺石。”这里,斯蒂芬把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克兰利和穆利根都当成是促使自己思考问题的人。
[473]据《创世记》第25至27章,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以扫生就浑身是毛,雅各用一碗红豆汤从以扫那里换来了长子的权利。他们的父亲以撒双目失明后,雅备冒充哥哥去接受祝福。以撤觉得那声音像是雅各的,但因雅各用山羊毛裹住双手和脖子,以撒摸了摸,以为站在自己面前的真是长子,就祝福了他,让他统治所有的弟兄。
[474]这里把理直三世的一句台词略加改动。原话是:“用我的王位换一匹马!”见《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
[475]“世界上的天使”,这里指国王。语出自《辛白林》第4幕第2场中贵族培拉律斯袒护王子的台词。
[476]莎士比亚在英国史学家拉雯尔?霍林希德(?一约1580)所著《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1857年,第二版)中找到了一个史前世纪的故事(写一个首领宠爱坏儿子,歧视好儿子),把它与菲利普?锡德尼的牧歌传奇《阿卡迪亚》(1590)第2卷第10章中的一个境遇凄凉的国王的末路糅合在一起,写成了《李尔王》(1606)。
[477]原文为法语。
[478]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1610)一剧直接取材于英国散文家罗伯特?格林(1558?一1592)的田园诗《潘多斯托》(1588),“把波希尼亚搬到海边” 这个错误即由此而来。
[479]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2)第2幕第2场中,赫克托(不是尤利西斯)曾说,“正像亚理斯多德所说的那种……”按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的年代迟于赫克托(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将近一千年。
[480]这里反用《马太福音》第26章第ll节的话。原话是:“常常会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意思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很少写穷人。
[481]普洛斯彼罗是《暴风雨》中的旧米兰公爵,精通魔术。他的兄弟篡了位,并把他和他的女儿米兰达一道放逐到海岛上。杖指魔杖,书指魔术书。
[482]这里把人生比作古希腊悲剧的四个阶段。
[483]西德尼?李在《威廉?莎士比亚传》(第266一267页)中写道,莎士比亚曾支持自己的女儿苏珊娜于一六一三年向宗教法庭控告莱恩以诽谤罪,因为莱恩首先控告已婚的苏珊娜与一个叫作拉尔夫?霍尔的人通奸。届时莱恩未出庭,因而被教会开除。
[484]梅努斯是爱尔兰基尔代尔郡一镇,位于都柏林东北十五英里。当地的圣帕特里克学院是不列颠诸岛中最大的天主教神学院。斯蒂芬这句话套自《梅努斯教义问答集》(都柏林,1882)。
[485]莎士比亚的墓志铭中写着:不得掘开这块碑石,移动遗骨。因而,死在他后面的妻子安就无法与他合葬了。
[486]关于克莉奥佩特拉,爱诺巴勃斯曾说:“年龄不能使她衰老,习惯也腐蚀不了她那变幻无穷的伎俩……”见《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2幕第3场。这里套用时把“她”改成“它”,用以指原罪。
[487]“他是圣灵”,参看第十五章注[409],“他什么都是”引自哈姆莱待对霍拉旭说的话。原指哈姆莱特的亡父。见《哈姆莱特》第l幕第2场。
[488]在《辛白林》中,阿埃基摩靠谎言促使伊摩琴的丈夫怀疑她与阿埃基摩私通。在《奥瑟罗》中,伊阿古欺骗奥瑟罗,说其妻子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私通。这里把他们比作凌辱妇女者。而伊阿古还毫无根据地猜疑自己的妻子与奥瑟罗和凯西奥私通。见《奥瑟罗》第l幕第3场和第2幕第l场。
[489]荷西是法国小说家普罗斯柏?梅里美(1803一1870)的中篇小说《嘉尔曼》(1845)中的一个纯真的青年。他为了爱吉卜赛女郎嘉尔曼而堕落成为强盗, 最后将嘉尔曼杀死,自己也被处绞刑。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1838一1875) 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一直脍炙人口。
[490]摩尔大指奥瑟罗。
[491]“咕咕!咕咕!啊,可怕的声音!”是《爱的徒劳》第5幕第2场末尾《春之歌》中的一行。下一行是“害得做丈夫的肉跳心惊”。咕咕在英文中既是布谷鸟,又指布谷鸟的啼声。Cuckold(奸妇的本夫)一词便是由cuckoo引伸而来,而cuckoo也含有“傻子”或“做了王八的丈夫”意。
[492]原文作“reverbed”。此词曾出现于《李尔王》第1幕第l场肯特的台词中:“那些声音低沉的人,发不出空洞的回响,然而并非无情无义。”
[493]小仲马(1824一1895)是大仲马(1802一1870)的私生子。父子均名亚历山大,并且都是法国作家。“小”和“大”,原文都是法语。
[494]“男人……喜悦”是哈姆莱特王子对朝臣所说的话。见《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两个“他”,原剧中均作“我”,是哈姆菜特自指。引用时改为“他”,以指莎士比亚。
[495]“从小到大”,见《哈姆莱特》第5幕第1场中掘墓者甲的台词。
[496]据莎士比亚在“新地”大宅的庭园里栽下一棵桑树,以便让后世知道他被埋葬在什么地方。
[497]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3幕第2场中,当朱丽叶误以为罗密欧在决斗中被提伯尔特杀死后,她巴望自己“赶快停止呼吸,……去和罗密欧同眠在一个墓穴里”。
[498]“大”、“小”,原文为法语。
[499]在英文中,富裕、兴旺的(prosperous)与普洛斯彼罗(Prospero)拼音相近。
[500]指莎士比亚的头一个外孙女伊丽莎白?霍尔。她是苏珊娜之女,生于一八0八年。
[5Ol]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1826一1864)所作歌曲《内德大叔》中有“好黑人注定去的地方”之句,这里把“好”改成了“坏”。
[502]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一1949)在《明智和命运》(巴黎,1899)中写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与我们的本性不相符的事是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倘若犹大今晚外出,他就会走向犹大,从而有了出卖的机会;然而倘若苏格拉底打开自己的门,他会发现苏格拉底睡在门口的台阶上, 从而就有了变得聪明起来的机会。”乔伊斯引用时做了改动。
[503]当晚斯蒂芬反用了“从自我内部穿行”一语,参看第十五章注[408]。下文中的“恋爱中的弟兄们”,原文作brothers一in一love,与brother一in一law(姻兄弟)拼法相近。这是文字游戏。
[504]据《创世记》第1章,天主在第一天创造了光,相隔两天又创造了太阳。
[505]原文为意大利语。
[506]参看本章注[487]。
[507]这一段套用哈姆莱特对奥菲利娅所说的话(“再不要结什么婚了”。见《哈姆莱特》第3幕第l场)和耶稣的一段训话(“他们要跟天上的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见,《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
[508]原文为希腊文。古希腊理论力学创始人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一约前212)奉命测定王冠含金的纯度,他洗澡时看到澡水溢出,从而发现了阿基米德浮力定理。这句是他当时所说的话。
[509]这里,他以与自己同名的先知玛拉基自况,参看第一章注[l0l]。《玛拉基书》第1章第1节有“上主交代玛拉基转告以色列人民的信息”语。
[5lO]“己经……再结婚”引自哈姆莱特对奥菲利娅所说的一段话。见《哈姆莱特》第3幕第l场。
[511]这里,把Eglinton改为Eclecti,以表示约翰?埃格林顿的观点是把当时流行的观点加以折衷(eclectic)汇集而成。
[512]爱德华?多顿(见本章注[345])在《莎士比亚:关于他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研究》一书(第126页)中写道:莎士比亚把哈姆莱特塑造得很神秘, “永远不可能完全解释清楚。”
[513]卡尔?勃莱布楚(1859一1928),德国诗人、评论家、戏剧家。他在《莎士比亚问题解答》(柏林,1907)中提出拉特兰(见本章注[425]) 是真正的莎剧写作者。比在他之前提出这一论点的马登(参看本章注[292])较有说服力。“先生”,原文为德语。
[514]“我信……我!”这原是求耶稣给自己的儿子治病的父亲所说的话。见《马可福音》第9章第24节。
[515]原文为希腊文。
[516]《达娜》第4期(1904年8月)上刊有乔伊斯的一首题名《歌》的诗,后收入《室内乐集》(伦敦,1907)。
[517]见本章注[179]。下文中的弗莱德琳是指弗雷德?瑞安咬字不清,把自己的姓名念成那个音调。
[518]这是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见本章注[442])所搜集的两篇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其中“新手内莉”还曾出现在戈加蒂的《诗集》(纽约,1954)里。
[519]《反异教大全》是圣托马斯?亚奎那的著作。
[520]安古斯?奥格神是爱尔兰神话中掌管青春、美和诗的神。他发现经常出现在梦境中的理想伴侣原来是一只白天鹅,自已便也变成白天鹅,与她比翼腾空而去。
[521]这里,斯蒂芬想起了当天早晨离开圆形炮塔之前穆利根对他说的那番话。参看第一章。
[522]、[523]原文为法语。
[524]原文作shakes,是双关语。既可作莎士比亚的简称,又作“摇晃不定”解。
[525]这里把《哈姆莱特》第5幕第l场中哈姆莱特对掘墓工甲所说的话略作了改动。原话是:“庄稼汉的脚趾头和朝廷贵人的脚后跟挨得那么近,足以磨破那上面的冻疮了。”原文作“gall his kibe”,转义为:触及他的痛处。
[526]原文作“aII amort”,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用语,见《驯悍记》第4幕第3场中彼特鲁乔对凯瑟丽娜所说的话:“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5Z7]这里,穆利根把谈兴正浓的利斯特比作《仲夏夜之梦》中那个戴着驴头和仙后提泰妮娅谈情说爱的织工波顿。
[528]“明契……如镜”引自弥尔顿曲《利西达斯》一诗。明契乌斯河在意大利,流经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家乡安第斯。
[529]迫克(Puck)是中世纪英格兰民间传说牛的顽皮小妖,系《仲夏夜之梦》的主角之一。勃克(Buck)也喜欢搞恶作剧,两个名字拼音又相近,所以这么称呼他。
[530]这里把罗伯特?彭斯的《约翰?安德森,我的乖》(1789一1790)一诗中的“安德森”改成了“埃格林顿”。安德森和埃格林顿都是秃头。
[531)“没……林唐”,套用《艺妓》(见第六章注[62])中的歌词,略作改动。
[532]管子工会会馆是机工协会会馆的俗称。一九0四年夏季, 该会馆被改建成阿贝剧院。该剧院可以说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摇篮,以叶芝为首的爱尔兰国民戏剧协会即设在这里。“我……臭味”一语暗指僧侣们曾竭力制止在该剧院上演新剧作。
[533]关于一五八六年左右莎士比亚离开家乡的原因,传说最多的是他偷了附近的乡绅托马斯?路希的鹿,挨了一顿鞭子,因而逃往伦敦。
[534]原文为法语。巴尔扎克有一部小说也题名为《三十岁的女人》(1831)。
[535]这句话与本章注[359]的“你不能既吃了点心又还拿在手里”相互呼应。
[536]见《十四行诗》第126首第9行:“可是你得怕她,你,她的小乖乘!”
[537]柏拉图在《菲多篇》中写道,苏格拉底抚摩着弟子菲多的头发说:“我想,菲多,当你明白过来,就会把这头秀发剪掉啦。”意思是说,菲多那套血气方刚的争辩也将随之而去。
[538]在第十五章中,醉汉非利普说:“他不姓阿特金森。”(见该章注[515])那儿指阿贝剧院。
[539)这首打油诗的文体模仿叶芝的《贝尔和艾琳》(19O3)一诗第1段。
[540]“继续嘲弄吧”,参看本章注[262]。“认识自己”是坐落于德尔斐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标出的警句,另一句是“适可而止”。
[541]这里,勃克?穆利根在挖苦为亡母戴孝的斯蒂芬。
[542]格雷戈里夫人(1852一1932),爱尔兰剧作家。原名伊萨贝拉?奥古斯塔?佩尔斯。她于一八九二年丧失后,开始文学生涯,一九0四年任阿贝剧院经理。 乔伊斯写过一篇批评其《诗人与梦想家》的文章,刊载在朗沃思主编的《每日快报》(1903年3月26日)上。叶芝曾称赞格雷戈里夫人的书为“当代爱尔兰首屈一指的”, 下文中的“令人想起荷马”,系穆利根添加的。
[543]“九个……舞”,见《仲夏夜之梦》第2幕第l场这是英国乡村的一种由九个男人组成的民间舞蹈,通常在五朔节时表演。此词源于“莫里斯科”(morisco),意力“摩尔人”的。
[544]《出埃及记》第34章第29节有“摩西带着十诫的法版从西奈山下来”之语,前文(见第一章注[lOl])中提到穆利根与先知同名,所以这里把他手中的纸片说成是法版。
[545)意译就是“睾丸的穆利根”。
[546]原文为意大利语。
[547]在英国大学里,托比和克雷布这两个名字均含有猥亵意。
[548]坎姆顿会堂原是卡姆登街的一座货栈,爱尔兰国民剧院协会迁入阿贝戏院之前曾设于此。
[549]爱琳是爱尔兰的古称,参看第七章注[46]。
[550]这里,斯蒂芬回忆起他曾站在门廊前的台阶上看鸟的飞翔,试试鸟占(古罗马时期开始的一种占卜办法。通过观察鸟的飞翔情况以判断神的旨意)的往事。参看《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5章。
[55l]参看第三章注[158]及有关正文。
[552]指刚刚从二人当中穿过去的布卢姆。
[553]“我怕你,老水手”,出自柯尔律治的《老水手》(1798)一诗。
[554]这是常见于中世纪城堡的一种结实的铁格子吊门。下端有一排倒刺。门卡在两边的承溜当中,可以上下移动。
[555]“让我们……鼻孔”,出自《辛白林》第5幕第5场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