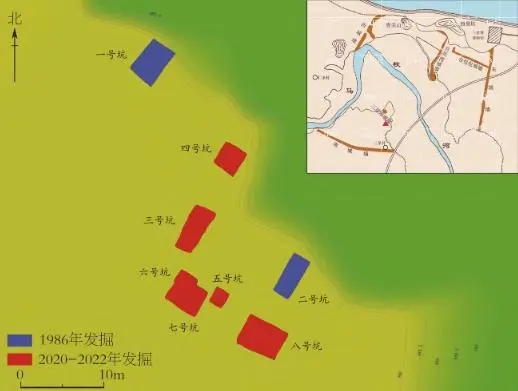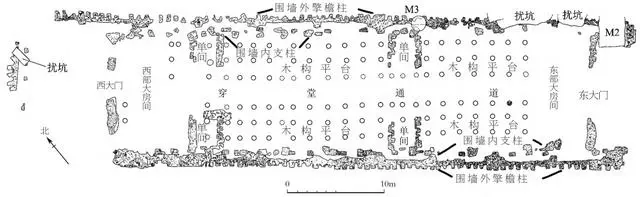一、引言
古代人类遗骸的疾病研究作为生物人类学的核心分支,兼具揭示人类健康演化历程与解码社会文化变迁的双重价值。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多局限于对骨骼病理特征的描述,未能充分阐释疾病如何作为隐形参与者,深度嵌入古代社会结构、人群迁徙与文明演进的进程之中。而体质特征分析、古分子生物学技术与多学科研究范式的递进与融合,正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局限,推动古代疾病研究重塑我们对人类历史与健康互动关系的理解。
学界将人类古代疾病研究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以动物遗骸研究为主,后三时期则是体现了人类对疾病与历史关联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具体来说:(1)起源时期(19世纪中叶至一战)对个体古病理的初步观察,虽尚未形成系统方法,却已开启从骨骼痕迹窥探古代健康的思路,为后续将疾病与人群生存状态关联奠定基础;(2)整合时期(一战至二战)放射学、统计学等生物医学方法的引入,使古病理学成为独立学科,此时的研究不再满足于识别疾病,而是开始通过病理特征的群体差异,试探性关联古代人群的生计模式与生存环境,例如通过骨骼感染率推测聚居地卫生条件,迈出了疾病链接社会的第一步;(3)新发展时期(二战结束至今)则迎来认知的两次关键突破,一是基于体质特征的科学诊断标准形成,使研究者能通过代谢性疾病的分布、创伤的类型差异,精准解读古代社会分工(如农牧人群的骨骼病变差异反映生业模式分化)与暴力程度(如颅骨创伤频率关联群体冲突);二是古分子方法的引入,彻底打破病原体演化与传播的时空壁垒,通过古DNA测序、蛋白质组学等技术,研究者得以追溯鼠疫耶尔森氏菌的遗传谱系与贸易网络的绑定关系,还原疟疾寄生虫随人群迁徙的扩散路径,首次从分子层面证实疾病是塑造人群迁徙与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
传统研究以骨骼、牙齿病理观察为核心,其价值远不止于初步诊断疾病。通过对体质特征的量化分析,研究者能将个体病变转化为群体认知,例如对比贾湖遗址与西坡墓地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发现农业转型可能导致人群营养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健康水平;结合稳定同位素分析与考古背景,更能揭示疾病易感性与饮食结构、生计模式的深层关联,如青铜时代单一农业人群的龋齿率高于农牧混合人群,印证了生业模式通过饮食塑造群体健康的认知,使疾病研究成为解析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依据。而分子生物学技术向考古学领域的渗透,则实现了从形态描述到机制阐释的认知跨越,填补了传统研究无法触及的疾病与历史互动空白。依托古分子技术,研究者不仅能重建古代病原体的基因组信息、精准还原鼠疫、疟疾等传染病的流行趋势,更能通过病原体分布与贸易路线、迁徙轨迹的叠加分析,重构疾病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例如新石器时代末期鼠疫耶尔森氏菌通过欧亚早期贸易网络扩散的分子证据,印证了疾病传播与人类物质交流同步发生的历史逻辑,使我们对古代人群互动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器物、技术的传播,更纳入了隐形病原体这一关键变量。此外,古分子研究还揭示了人类与病原体的基因共演化关系,如欧洲人群中与结核病易感性相关的TYK2 P1104基因变异的频率波动,反映了疾病对人类基因组的长期选择,为健康与演化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分子层面的实证。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将古代疾病发展历程的“新发展时期”细分为体质特征分析、古分子研究与多学科范式三个认知阶段(不涉及仅依据历史文献的古代疾病研究)。在体质特征分析阶段,聚焦代谢性疾病、骨骼感染、创伤等病症的病理规律,阐释如何通过骨骼痕迹还原古代人群的社会分工(如殷墟男性上肢骨关节炎高发反映体力劳动差异)、生存压力(如骨膜炎与上呼吸道感染关联揭示手工业污染影响);在古分子研究阶段,以鼠疫、疟疾、病毒性疾病为核心,解析病原体基因组如何解锁疾病、迁徙与贸易的关联(如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恶性疟原虫传播的分子证据);在多学科范式阶段,通过代谢性疾病、骨骼特异性感染与肿瘤的研究案例,展现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物学、稳定同位素分析的融合如何搭建疾病、社会与文化的完整认知链条(如软骨发育不全的基因检测与考古背景结合,推测古代社群对身体缺陷的接纳程度)。
通过对古代疾病类型、致病机制、古病原体传播与演化路径等核心议题的深度探讨,本文旨在清晰呈现疾病与职业分工、社会分化、人口流动的关联,为深入挖掘古代人类健康状况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提供生物学证据。同时,通过追溯病原体演化与文明互动的轨迹,探索疾病对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文化观念的塑造作用,还可为现代公共卫生策略的科学制定与医学研究的创新突破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充分彰显古代疾病研究在当下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当前国内研究仍以体质人类学的描述性分析为主,古分子等技术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导致对疾病、社会与文明互动机制的探讨仍显薄弱,而未来多学科交叉路径将成为古代疾病研究领域发展的关键方向。
二、体质特征视角下的古代疾病
通过对古代遗骸体质特征的观测与分析,可以初步判断疾病类型,了解古代人类健康状况。目前传统体质研究确定的疾病类型主要有代谢性疾病、骨骼感染、退行性疾病、神经血管疾病、口腔疾病等。此外,创伤也是传统古病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一)代谢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作为一类由机体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其中代谢性骨病(Metabolic bone disease)是古代人类遗骸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具体指导致正常骨形成、吸收或矿化发生系统性改变的疾病或疾病组合,多与营养不良和激素失调有关。根据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代谢性骨病早期发病特征不典型,中后期临床表现复杂,常见生长障碍、骨关节病、骨骼畸形。中后期代谢性骨病在骨骼上具有显著的体质特征表现,易于在考古材料中观察识别,因此,这类疾病在古代人类遗骸中观察到的比率较大,主要涉及骨质疏松症、氟骨症、佝偻病和坏血病等类型,目前针对代谢性骨病的多学科研究也在持续开展。
1. 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以骨矿盐密度减低、骨的微结构破坏,进而导致脆性骨折发生的疾病。早在距今9000至7800年前的贾湖遗址,OP病例就已发现,在距今5000至4000年前,OP已普遍出现于欧洲、美洲、亚洲地区,并在历史时期常见于各阶段各地区古代人类遗骸中。
骨质疏松症的致病因素较为复杂,通常认为与年龄、性别、饮食及营养状况有关,特定生活方式也可能诱发OP,可以此为线索探究古代人群社会分工和生活方式差异。例如,M. E. Zaki等学者对公元前2687年至前2191年古埃及人骨骼遗骸进行骨矿物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检测,这些骨骼来自两个不同社会阶层:高级官员和工人群体。结果显示BMD值与年龄、性别和社会身份存在关联,有关年龄和社会身份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老年群体的BMD值较年轻群体明显下降,且男性工人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率高于男性高级官员,而女性高级官员的发病率则高于女性工人。研究者认为不同群体的致病原因存在差异,推测男性工人骨质疏松症发病率较高可能与营养不足和过重的工作量有关,而女性高级官员的久坐生活方式则是潜在致病因素之一。此外,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平均发病时间早于男性且发病频率更高,这种现象可能与女性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有关。国内相关学者针对古代人类遗骸的骨质疏松症开展过诸多方面的研究,如郑晓瑛对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人骨进行了X-光病理鉴定,不仅确认了氟骨症的发病证据以及骨包虫病和骨肿瘤病的可能性,还发现样本骨质疏松症发病年龄呈现出低于现代人发病年龄的倾向,古代特殊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可能导致了发病年龄的差异。王明辉比较了贾湖遗址和西坡墓地出土人骨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指出西坡农业人群的高发病率除了可能存在的流失钙质的疾病外,应与人群间饮食和营养状况的差距有关,早期生业模式的转变可能提升了骨质疏松发病率。
2. 氟骨症。
氟骨症(Skeletal fluorosis)是氟中毒在骨骼上的表现,其骨骼的典型病理特征包括:骨组织的增长、骨小梁增粗增厚、骨密度增加,这些病理特征导致X光下出现“毛玻璃”样骨组织,全身所有骨骼都有累及。患者牙齿的微观病理表现为:牙齿表面有一层局限或弥散的云雾状不透明层,其下层为不同程度的矿化不全区,显示有多孔性。氟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而如寒食散中紫石英(CaF2)等过量的氟摄入可能导致氟中毒。现代病例多由工业污染和深井作业等因素导致,而古代氟骨症根据病因可分为饮水型氟中毒、燃煤污染型氟中毒、药物性氟中毒等。
骨骼证据表明氟骨症约公元元年就已经出现于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随后该病症零散发现于不同考古遗址的人类遗骸中。比如,Judith Littleton对巴林岛公元前250年至公元250年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开展了形态观察,根据牙齿染色、表面不透明度和孔洞的表现特征初步鉴定为氟骨症,进一步的氟元素检测结果确定了牙齿的氟含量偏高。氟中毒在牙齿上的病变特征较为明确,而除牙齿外其他骨骼的高度病变情况尚不足与氟骨病直接关联,推测巴林岛墓葬人骨应属于饮水型氟中毒。而山西榆次明清氟中毒人群除土壤与水体中氟含量较高这一地方性因素外,也存在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可能性,且氟骨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关节炎、骨质疏松、创伤等。
3. 佝偻病。
佝偻病(Rickets)是儿童青少年时期钙磷代谢障碍相关性骨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在古代人类骨骼遗骸上留下肋弓外翻、长骨弯曲等病理特征,严重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与健康。其中,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的发病机制与日照不足和日常饮食中维生素D的缺乏紧密相关,软骨细胞的正常排列被破坏。维生素D依赖性佝偻病和低血磷抗维生素D佝偻病则属于遗传病。
唐人《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记载“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但目前古代文献与医书中“偻”字含义的考证仍存在争议,早在唐朝时期古人可能就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佝偻病或与其病理表现相似疾病的存在。伴随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长期对人类群体健康产生影响。工业化进程初期,这类疾病更为常见,例如Rachel Ives在一组19世纪中叶的青少年骨骼样本中,观察到额隆上的不规则矿化沉积和尖刺状的新骨形成证据,且样本长骨皮质骨多孔,其生长板边缘出现垂直条纹和细缝等病变,确诊了138例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恶劣天气与工业迅猛发展带来的空气污染大幅减少了紫外线照射时长,致使儿童普遍缺乏维生素D。同时,这一时期社会不平等现象突出,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饮食存在较大差异,贫民儿童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这对骨骼发育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4. 坏血病。
坏血病(Scurvy)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C引发的疾病,主要病理表现是出血和骨量减少,古人骨骼遗骸上的典型病理特征为蝶骨大翼双侧异常多孔。受基因限制,不同于大多数哺乳动物,人无法生成维生素C合成中的关键酶,每日需要摄入一定量的维生素C,因此坏血病发与资源短缺和饮食结构单一等因素有关,是评估古代青少年健康状况和营养级的关键指标。研究表明不同时期坏血病的流行程度很可能与农耕方式、粮食生产及储存理念等社会文化行为密切相关。由于坏血病的病征在部分种类的骨骼上缺乏特异性,尤其在成年个体中,其古病理诊断相对困难,不易与佝偻病、骨软化症等病变区分,还需要结合对饮食结构、食物资源等生活状况进行分析与推测。
目前古代人类遗骸样本中坏血病证据跨越了数千年,几乎遍布全世界,较早的病例来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德国、希腊和约旦地区。早期报告的坏血病病例主要集中在成年人群体,随着诊断方法的完善,如今绝大多数病例都发现于青少年群体。通过对不同地区古代人群的研究,相关学者对古代坏血病的病理特征与致病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Haagen D. Klaus在南美洲出土的青少年骨骼表面发现颅外血管压痕,这表明古代青少年患者可能会出现积血症状,对古代坏血病的体质特征做出了补充。Anne Marie E. Snoddy等人观察到来自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距今约3400年的四具新生儿遗骸呈现出非特异性的骨骼畸变,其中一个新生儿与同一地区出土一位罹患坏血病的成年女性存在血缘关系,这显示出沙漠地区农业转型时期的资源短缺可能对产妇与胎儿的健康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受限于诊断技术,将目前的坏血病诊断标准应用于新生儿遗骸仍面临诸多挑战。Chryssi Bourbou通过研究11—12世纪希腊的青少年遗骸,成功发现青少年坏血病的证据,不仅丰富了该地区这一疾病的历史病例,还提出青少年坏血病的发生可能与断奶后摄入固体食物的种类与品质有关。综合多项研究可见,坏血病患病概率很可能与生活方式、资源获取及文化因素有关。
代谢性疾病长期与人类共存。通过骨骼遗骸的体质特征观察可以做出初步诊断,基本确定疾病类型,进而评估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同时结合具体考古学背景和其他体质特征证据,可进一步推测此类疾病与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的内在联系。因此,根据古代人类遗骸研究代谢性骨病,有助于探讨古代人类疾病、饮食、文化习俗、社会经济地位等问题,进而为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奠定基础。部分与遗传性相关的代谢性疾病可进一步通过古分子研究得到更为准确的鉴定,体现了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二)骨骼的非特异性感染及退行性疾病
非特异性感染是指由非特定病原体引发的骨骼炎症性病变,可由多种细菌、物理或化学因素引起。古代人类遗骸可见的骨骼非特异性感染包括上颌窦炎、骨髓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退行性疾病包括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等,而骨关节疾病和骨膜炎等疾病既属于非特异性感染也属于退行性疾病。
1. 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疾病,又称骨关节病(Osteoarthrosis)或退行性关节病(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DJD),对古代人类遗骸的诊断标准为:出现骨化灶或出现边缘骨赘、软骨下骨多孔、关节面新骨形成及关节轮廓改变中的至少两种病变。尽管“退行性”之名显示这种疾病是因年龄增长使组织和器官衰老而造成的,现代医学研究指出,骨关节病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除年龄和炎症因素外,运动方式、机械负荷、创伤、遗传、系统性疾病、体重和性别等因素均有可能作用于骨关节疾病的发病。在古代疾病研究领域,骨关节疾病可以反映关节的功能负荷。由于不同职业和社会劳动分工会对骨关节产生特定的影响,该疾病与古代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存在紧密联系,成为生物考古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此外,Ingemar等学者还提出了骨关节疾病和牙齿疾病之间存在潜在联系,提示研究者在分析骨骼病变时,可从关联性角度出发,综合考量多种疾病。
作为古代人群中最普遍的骨骼疾病之一,骨关节疾病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历史时期农业社会、近代城市社区居民等诸多人群中均有出现。在中国古代人类遗骸上诊断出骨关节疾病的相关研究报道也较多,如内蒙古兴隆沟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群中男性颈椎患DJD较多而女性腰椎患病较多,由此推测兴隆沟人群的行为方式应对其椎体造成了较显著的压力,男性与女性存在行为模式的差异。然而,由于样本数量和背景信息的局限性,目前研究尚且无法从骨关节疾病患病情况解析人群具体的行为模式,椎体患病情况也并不一定与生业模式存在直接关联。得益于殷墟的丰硕考古成果,张桦等对商晚期都城殷墟居民骨关节炎的疾病调查得以开展性别和职业角度的分析与讨论。通过评估来自孝民屯和新安庄两处遗址的167具骨骼遗存的骨关节炎状况,研究人员发现殷墟人群骨关节炎发病率较高,其中男性在上肢部位骨关节炎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这种性别差异在孝民屯样本中尤为明显。较高的上肢骨关节炎发病率可能源于重复性承重和搬运行为,使上肢长期承受更大压力。此类负重行为可能源于与职业关联的体力活动,而男性较高的患病率表明可能存在性别分工现象。此外,孝民屯男性与女性居民的骨关节炎发病率均显著高于新安庄样本,暗示了两地居民存在职业差异。不同于新安庄未表现出专业作坊特征,孝民屯为一处铸铜遗址,由该地女性较高发病率推测女性有一定概率也参与了铸铜生产,当地青铜铸造活动很可能以“家族产业”的形式开展。
2. 骨膜炎。
骨膜炎(Periostitis)作为另一类重要的骨骼非特异性感染,初期表现为细小的点蚀状凹陷,而后沿着骨的长轴形成条纹状瘢痕,晚期在原始骨皮质表面生成片状的新骨。胫骨是最常见的发病部位,或因胫骨距表皮较近,容易发生周期性的轻微感染。骨膜炎在人骨考古研究中具有关键意义,被视为衡量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尽管研究中存在骨学悖论和病变程度量化困难的问题,古病理学研究已经将其纳入生存压力评估体系,与牙釉质发育不全和缺铁性贫血等现象共同作为评估指标。以古代人群骨膜炎患病情况为线索,不仅可以揭示古代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更展现了环境、疾病、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骨膜炎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均有发现骨骼证据。前人对古代人群的骨膜炎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例如陕西大原村制陶遗址人骨开展的古病理学研究发现,该遗址西周时期居民罹患肋骨骨膜炎与上颌窦炎的比例较高。由于骨膜炎多与上呼吸道感染和牙齿根尖感染有关,研究者推测,手工业快速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可能诱发呼吸道疾病,进一步引发该遗址人群罹患骨膜炎等疾病。对高青县胥家村南遗址北朝至隋唐时期人群和山东广饶地区元代人群的生存压力研究,均选取了骨膜炎等多个病理现象作为健康状况及生存压力水平的观察项,结合稳定同位素分析,系统探讨古代人群的生活状况。
3. 上颌窦炎。
上颌窦炎(Maxillary sinusitis)就是一种与骨膜炎存在关联的呼吸道疾病,对古代样本的诊断主要根据其内壁骨形态的变化来确定,上颌窦内骨形态的变化可分为穗状骨片(spicules)、点状孔(pitting)、斑块(plaque)、囊肿(cyst)、小叶(lobules)和大孔(hole)。根据上颌窦炎的发病情况,可以推测古代人类生存环境,并为探讨生产方式与职业分工提供间接证据。
上颌窦较易受到感染产生炎症反应,因此上颌窦炎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炎症性疾病之一。然而,由于能够识别呼吸系统疾病的骨骼变化较少,其在考古样本中的报道与研究并不多见,目前发现的古代人类骨骼证据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都较为分散,最早的病例来自公元前5500年左右的欧洲地区,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上颌窦炎发病率明显升高。诱发上颌窦炎的因素较为复杂,比如,甘肃黑水国遗址汉代人群患上颌窦炎情况与性别和年龄均无关,推测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风沙天气、室内和室外的空气污染、病原微生物及牙齿根尖疾病等多种因素均可能导致黑水国古代居民患上严重的上颌窦炎。相关学者对欧洲、美洲、非洲的古代人类遗骸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中,上颌窦炎发病率存在差异,研究者认为空气质量欠佳是上颌窦炎的主要病因,如花粉、工业排放、雾霾等,与制陶、金属加工等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空气中的颗粒物具有较高的患病概率,而狩猎采集者、农业生产者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对上颌窦炎易感性较低。
4. 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症。
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症(Diffuse idiopathic skeletal hyperostosis,DISH)是一种以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及其附着部位的钙化和骨化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非炎症疾病,被纳入特殊表现的脊柱退行性疾病的范畴。在古代疾病研究中,应注意DISH与椎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椎间盘疾病及强直性脊柱炎等骨骼疾病的鉴别,早期研究中DISH的命名也并不统一。DISH的发病机制尚不明晰,目前研究发现其与地区、性别、饮食、遗传、脊柱创伤等因素存在关联,往往伴随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和心血管疾病等复杂的并发症,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组织学研究已经表明肥胖症与DISH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
目前报道的古代DISH病例时间跨度大,分布范围广,距今约5万年前的近东尼安德特人骨骼遗存上已经出现相关痕迹,公元前13世纪在位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可能也罹患该疾病,东亚地区最早的病例则相对较晚,发现于东周人群中。鉴于DISH与古代人群生活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相关性,学界对其致病机制有了一定的认识。DISH被认为与一些代谢性疾病如佩吉特骨病、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维生素A代谢紊乱和生长激素水平升高等存在关联,可能是由生活方式等因素引发的多系统激素紊乱,如Rogers等人发现欧洲中世纪主教等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由于高热量饮食更易患此病。部分研究者认为,DISH可能是特发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血管疾病或反复微创伤的结果。如东周东赵遗址人群的DISH被认为由脊柱长期机械负荷导致,支持DISH由反复微创伤引发的观点,该人群DISH发病率与行为模式和职业存在关联,而与饮食结构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骨骼非特异性感染与退行性疾病种类繁多、病因复杂、历史悠久,目前研究结果表明两类疾病与性别、职业分工、饮食结构、社会分化等重要话题紧密关联,是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产物,为研究古代社会文化提供了一定线索。然而,仅凭骨骼遗骸中非特异性病变的肉眼观察,无法准确判断其具体病因,以发病机制为基础的考古推理仍然存在较大空白。
(三)神经血管疾病
古病理学不仅可以诊断发生于骨骼的原发性疾病,亦可诊断起源于软组织并在骨骼上留下痕迹的疾病。凭借这一特性,在特定条件下,神经血管类疾病亦可通过骨骼呈现的体质特征进行诊断分析。然而,这类疾病在古代样本中较为罕见,古病理学领域的诊断标准尚未完全统一,病因溯源仍存在诸多争议,其与古代人类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及健康状况之间的潜在关联,仍有待多学科研究予以揭示与阐释。
古代神经血管疾病的报道主要为脑膜中动脉(Middle meningeal artery,MMA)动脉瘤。MMA动脉瘤极为罕见,可分为真动脉瘤和假动脉瘤两种类型,其中真动脉瘤的形成常与血流压力增加或病理状况相关,如硬脑膜动静脉畸形、佩吉特病、高血压和脑膜瘤等。神经血管疾病恶化、动脉瘤破裂带来的出血可能导致古代儿童死亡。早在公元前9世纪意大利地区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墓葬,研究人员在儿童骨骼上就发现了MMA动脉瘤痕迹。随后,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意大利地区相同文明墓葬中又发现一具8至9岁儿童骨骼遗骸,在其颅内可观察到大片凹陷的病变。经研究推测,该病变很可能由罕见且早发的脑膜中动脉囊状动脉瘤长期压迫引起,但此病变也存在由硬脑膜动静脉瘘(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DAVFs,即硬脑膜动脉与皮质静脉或静脉窦之间缺乏血管床的异常连接)引发的可能性,MMA动脉瘤与DAVFs可能有一定概率共存。由于研究材料的有限性,目前基于古代人类遗骸的神经血管疾病报道和研究均较少,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
(四)口腔疾病
在古病理学研究体系中,口腔疾病研究占据重要地位,这是由于牙齿样本保存状况较好,样本量较大,且该类疾病病理特征易于鉴别。作为口腔疾病的重要类型之一,龋齿(Caries)自智人分化以来就与人类相伴,早期研究在更古老的南方古猿、爪哇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化石上都发现了可能的龋齿病例,自从农业起源,伴随农业化程度的加深,龋齿率明显增高,与植物性食物的摄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牙齿生前脱落(Antemortem Tooth Loss,AMTL)、牙髓炎(Pulpitis)、根尖脓肿(Apical abscess)、釉质发育不全(Amelogenesis imperfecta)、牙结石(Dental calculus)和牙周病(Periodontal disease)等也均属于常见的口腔疾病类型,其中牙周病是指包括牙槽骨、牙周韧带、牙骨质、牙龈及黏膜在内的牙齿周围组织炎症,主要由牙结石的长期沉积引起,而牙齿生前脱落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如牙槽骨外伤、牙周病导致的严重骨质流失及人为拔牙等。这些口腔疾病或病症间存在复杂关联,常被综合运用于古代人群口腔健康状况的评估。古人口腔健康状况与其日常饮食紧密关联,据研究者总结,高蛋白饮食会增强口腔碱性,形成易于形成牙结石的口腔环境,高龋齿频率则指向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饮食结构。对牙齿病理状况的观察,为探究古代社会分化与复杂程度提供了新视角。
由于古代人群牙齿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国内外相关学者针对口腔疾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发现口腔健康与饮食结构、生业模式、性别分工以及社会阶层等相关。例如,通过比较青铜时代晚期中国北方不同生业模式人群的口腔健康差异,发现相较于农牧混合模式及游牧模式,以单一农业为生的人群口腔健康状况最差,这一结论与全球范围内诸多地区的研究结果相契合,进一步证实了高碳饮食对口腔健康的潜在损害。除饮食习惯外,牙齿病变也与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有关,具体表现为牙齿病变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增加,且女性的牙齿病变普遍比男性更严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的先秦至汉代古人类龋齿患病情况的研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印证了上述结论。国外学者Vu Tran将龋齿、牙齿生前脱落(AMTL)和牙结石作为口腔健康指标,通过口腔健康状况分析,Vu Tran研究了秘鲁库拉普遗址查查波亚人群的阶层分化程度与性别差异。该人群的龋齿与AMTL发病年龄较早,女性龋齿患病率更高而男性高牙结石的概率相对突出。咀嚼古柯叶的特殊文化习俗可能也对该人群的口腔健康产生了影响。除年龄与性别造成的口腔疾病差异外,该人群的口腔健康与丧葬规模整体较为一致,暗示尚未形成等级社会,同性个体饮食应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口腔健康的性别差异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农业社会中较为常见,但不同地区之间古代人群的性别差异可能遵循不同模式。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城市居民与北方边疆以农业为生的人群龋齿患病率的性别差异呈现不同模式。内蒙古土城子遗址中,女性的龋齿率远高于男性,与世界范围内多数考古遗存观察结果一致。而河南省新红遗址男性的龋齿率高于女性,这一特殊现象暗示着城市居民与新红遗址的边疆居民可能因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化程度的差异,在性别分工或食物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同机制,从而造成了口腔疾病的患病情况差异。
口腔疾病在数十万年前的化石材料上就已经发现,伴随着人类生业模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口腔疾病在患病率和病理表现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丰富的古代牙齿遗存为通过口腔疾病探究饮食话题奠定了基础,目前的口腔疾病研究能够探讨古代人群的资源分配、生活方式以及区域差异。由于涉及饮食话题,口腔疾病研究与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研究手段具有开展多学科研究的巨大前景。相关学者也在尝试构建口腔疾病指数来量化不同风险因素对古代人群口腔健康的影响,以进一步完善口腔疾病诊断及病因评估体系。
(五)创伤
创伤,即人骨上显示出的所有外部物理损伤或变化,可系统划分为四大类型:骨骼的部分至完全骨折、关节错位或脱位、神经断裂或血液供应中断、人为导致的骨骼形态或轮廓异常这四种类型。创伤与运动行为、生活方式及暴力冲突有较密切的关系,最早在古人类化石上出现,一直伴随着人类演化进程,在古代人群中的体质特征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深入了解古代社会文化进程拓宽了研究视野。
创伤在人类进化早期(如南方古猿)就已经出现,在后续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等中均有发现,如广东马坝人头骨化石表面发现一处面积约30mm2、深度约1.5mm的半圆形凹陷,该区域表面粗糙并伴有波纹状隆起,颅骨内侧凸起,周围有明显的愈合痕迹。通过CT扫描进一步证实,该区域存在颅骨外板和板障增厚等愈合证据。经过与世界各地中、晚更新世的人头骨外伤标本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者推断马坝人头骨上的痕迹是头骨局部受到钝器打击造成外伤的愈合痕迹,很可能是当时人类之间暴力行为的结果。此项研究不仅为东亚地区最早的人类之间暴力行为提供了确凿的骨骼证据,同时还展示了当时人类在受到严重暴力伤害后的自愈及长时间生存能力。
除了古人类化石研究,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常见人骨创伤痕迹,例如公元前5世纪内蒙古井沟子人群死亡年龄呈现年轻化的特征,骨骼上多见创伤,其中女性创伤率更高且颅骨创伤在女性群体中更常见。研究者分别在两个个体的右髂骨和第一腰椎上发现了嵌入的铜箭矢及其造成的损伤,通过扫描重建,获取了关于箭矢样式和损伤机制的详细信息。创口缺乏骨愈合的迹象表明个体在受伤后短时间内死亡,但箭矢对骨骼造成的创伤应均不足以致死,可能是伤及内脏器官导致了死亡,确切死因尚不明晰。根据箭矢样式并结合历史背景进行推断,伤者可能是游牧民族入侵者,在与当地居民作战中受伤。在青铜时代晚期的亚洲北部,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导致的移民可能引发了地区性的社会冲突,进而加速了中国北部农牧交错文化带的形成。这项研究丰富了研究者对中国北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融过程的认识,为欧亚大陆东部历史的重建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人群内部或人群之间的暴力冲突是导致古人骨骼创伤的重要因素,除群体间暴力冲突导致的创伤外,特殊情境下的创伤案例也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独特视角。明代晚期御龙湾建筑遗址出土的大部分具有死前创伤的人骨在出土位置、骨骼部位出现情况、伤痕位置与类型及灼烧痕迹等方面,都符合同类相食的基本标准,例如,部分人骨发现于容器中,在骨骼上存在肉眼可鉴别的暴力砍砸和肢解痕迹,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出低温加热痕迹。此遗址出土的具有死前创伤的一批人骨,是我国目前最有可能属于同类相食事件的人类骨骼标本,为深入了解古代人相食现象及社会生存压力等问题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学资料。
根据前述分类,骨骼变形也属于创伤的一种,常见的骨骼变形包括跪距面、缠足、人工颅骨变形和骑马人小平面等。跪距面(Kneeling facets),即足部跖趾关节由于频繁的超背屈姿势而在跖骨远端上侧留下的小平面,鉴于这种骨骼变形与个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如商代跪坐)密切相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山东北阡遗址人骨跪距面的研究中,跪距面作为职业应力标志,被用来指示个体生前所经常从事的活动。由于该人群中跪距面高比例出现,并结合稳定同位素等研究结果,研究者推测该贝丘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人骨的跪距面有可能与加工食物和打鱼相关。历史时期考古材料中跪踞现象更加多见,但与史前跪踞面的形成原因不尽相同。赵永生等人对商代人骨上跪踞面开展了观察与分析,认为跪踞面与性别、社会等级无关,随年龄增长跪踞面相对更为明显,且部分个体右侧略重于左侧,可能是个人习惯所致。跪踞面的研究为殷商甲骨文与文物中出现的人物跪坐形象提供了事实证据,证实了跪坐这一坐姿在商代社会中的普及。此外,缠足导致的足部形态异常、象征身份认同的人工颅骨变形(Artificial Cranial Deformation,ACD)和长期骑马形成的骑马人小平面(Horse-riding)等现象都展现了骨骼变形与文化习俗、日常生活习惯的紧密关联。
创伤作为持续性动作或暴力行为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迹,长期与人类共存,为探究古代人群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提供考古证据。各类创伤现象,如骨折、关节脱位、刺伤、箭矢射中、截肢和颅骨穿孔等,不仅直观反映出个体正常生活与生存所面临的挑战,更反映了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暴力程度(如凶杀、战争等)、医疗技术发展水平以及资源分配情况等重要信息。目前基于古代人类遗骸对创伤的研究在国内外均开展较多,成果较为丰富。
在具体研究的实践中,体质特征观察并不局限于传统肉眼观察,引入了医学中的影像学、定量超声测量等作为技术支持,使得病理观察和病情诊断更为细致和科学。然而,考虑到古代人类遗骸的特殊保存状况和古今人群健康状况及医疗水平差异,古代疾病的体质特征诊断标准并不能直接套用现代医学病理特征,需要系统整理并不断细化古代疾病的诊断标准。
三、古分子视角下的古代疾病
在古代疾病研究领域,传统方法是对古代骨骼遗存进行古病理学观察和描述。然而,由于大多数急性感染不会在骨骼上留下明显的病理痕迹,这种依托体质特征的方法存在局限性。因此,仅依赖传统的体质特征评估,难以准确、全面地了解古代人类疾病的病因和传播路径等真实情况。在此背景下,古分子研究作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古代疾病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古分子包括古DNA、古脂肪酸、古蛋白质以及非生命物质中的化学分子等。其中,古DNA研究是目前分子考古学研究的热门方向,是探讨人群迁徙、社会结构、疾病发展史等重要话题的科学手段。随着古DNA提取技术和测序方法(尤其是高通量测序)的发展,古DNA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动植物的遗骸上,还可以提取古代病原体基因组。通过古微生物DNA信息追溯古代疫病,能够为了解古代疾病的病因提供直接证据。目前通过古分子研究,确定了鼠疫、疟疾、流感、乙肝等多种传染病,构建了更加完整的古代人类疾病图谱,充分体现了古分子研究对于揭示古代病毒传播模式和适应性进化等信息的重要性。
(一)鼠疫
鼠疫(Pestis)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YP)引起的传染病,鼠疫耶尔森氏菌是伪结核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进化出的变种,主要差异在于获得了两个毒性质粒——pMT1质粒和高拷贝pPCP1质粒。鼠疫具有高度传染性,在人口密集、流动频繁、卫生条件落后的环境下易引发大规模疫情,造成人口大量伤亡,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引发社会恐慌甚至信仰危机,也可能影响战争结局,引发王朝更迭或加速国家衰亡,同时促使人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客观上加速医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
研究鼠疫的起源和扩散最关键的是要明确鼠疫耶尔森氏菌(YP)在古代人群中的存在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模式,而古分子研究在揭示鼠疫病史和理解其对人类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分子研究结果表明,鼠疫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于欧亚大陆,可能起源于亚洲并随贸易扩散,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分别是爆发于公元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和14世纪在欧洲迅速蔓延的“黑死病”。具体来说,Nicola’s Raskovic等学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农业人群遗骸中检测到已知最早的YP,重建并分析了瑞典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类遗骸中的YP基因组。存在于提取自人类牙齿的古DNA中的鼠疫杆菌显示个体血液中曾存在高滴度的病原体,且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人类遗骸频繁检测出鼠疫,表明YP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影响欧亚大陆人类健康,逐渐发展出多个谱系并扩散。新石器时代末期,YP于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很可能是依靠早期贸易网络而非通过大规模人类迁徙,这种传播方式使病原体得以快速、大规模、持续扩散,并且加速了欧洲人口衰减,有利于后来草原民族向欧洲的迁徙。此外,其他古DNA研究细化了YP的传播轨迹,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YP起源于亚洲地区,并随着古代贸易路线的拓展以及人类长距离迁移活动,逐步扩散至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些研究从分子层面揭示了YP的演化传播轨迹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YP曾多次引发历史上的大规模流行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6世纪爆发于地中海世界的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和14世纪爆发于欧洲的黑死病(Black Death)。查士丁尼瘟疫曾被质疑并非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Michaela Harbeck等学者通过古分子研究确认德国中世纪早期墓葬出土的人类遗骸样本感染鼠疫,并精准定位于全球范围的进化树主枝0的N03至N05节点间,确认了查士丁尼瘟疫为鼠疫。进化树显示,YP的基因组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可能与其应对多样化环境和宿主的适应能力有关,导致每次瘟疫的流行病学特征与致病性存在差异。引发黑死病的病原体就是一种现已灭绝的YP变体,具有极强的传播力。Marcel Keller等研究者聚焦于中世纪流行于欧洲不同国家的YP基因组的微多样性,通过系统的基因测序与分析,检测到在中世纪鼠疫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流行期间,YP基因组呈现出相似的退化,其中包括两种同样的毒性元素,暗示鼠疫杆菌在大规模流行期间可能经历了趋同的进化。其进化带来的数次大规模瘟疫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还对当时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乱葬坑可能指向传染病大流行导致的集中死亡,Michaela Harbeck等学者对这一传统观点做出了补充,2—3人等少数个体的集中埋葬现象也可能是鼠疫等传染病传播导致的。国内鼠疫研究资料相对较少,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内的埋人现象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其中“鼠疫说”曾是解释该现象的主流观点之一。但是房内所埋人骨遗骸的古病理学研究并未观察到明显的疾病导致的骨骼异常,无法从人骨上找到这一人群死亡原因的直接证据,且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未获得有效的古DNA数据,疾病研究结果尚不支持“鼠疫说”的论断。
鼠疫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古分子研究证实了鼠疫的多次大流行,将鼠疫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年,逐渐构建出病原体演化路径与可能的传播轨迹,同时补充了与鼠疫相关的考古学信息,提升了由考古背景初步推断鼠疫存在的可行性。目前,古代鼠疫的传播方式与路径仍存在争议,数次大流行的细节信息留有较多空白,有待未来更多古代样本的出土和研究。古代人类遗骸是否罹患鼠疫的科学诊断和对古代鼠疫的探究基本依赖于古分子研究,相较于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可直接通过体质特征观察的疾病而言,在诊断程序上更为复杂,对骨骼遗存保存条件的要求也更为严苛,因而开展古分子分析研究古代鼠疫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古分子学研究资料的匮乏,国内鼠疫的考古学报道数量相对较少,从考古背景初步推断鼠疫的标准也尚未形成。
(二)疟疾
疟疾(Malaria)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的寄生虫病,由疟原虫(Plasmodium species)引起,其中恶性疟原虫(P. falciparum)和间日疟原虫(P. vivax)是两种最致命的疟疾寄生虫。疟疾的传播与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和迁移模式等因素有关。
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现存所有恶性疟原虫均源自黑猩猩寄生虫瑞氏疟原虫,可能在距今300万年前至1万年前通过单宿主传播;间日疟原虫可能在约4.5万年前智人进入欧洲时已广泛存在,此后长期对各地区人群产生影响。在历史时期,疟疾的空间分布较广,不仅频发于欧洲和美洲,也存在于高海拔地区。例如,Stephanie Marciniak等人对意大利南部1至2世纪古代人类遗骸进行的研究表明,疟疾可能在罗马时期就已经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其他研究者还在位于尼泊尔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Chokhopani遗址发现了公元前800年的恶性疟原虫疟疾病例,提升了人类对于古代疟疾分布范围的认识。
除历史流行情况外,古DNA研究在揭示疟疾传播模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殖民者将间日疟原虫带至美洲,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可能将恶性疟原虫引入美洲。Megan Michel等人发现,现已灭绝的欧洲间日疟原虫与拉丁美洲古代及现代的寄生虫种群相似,很可能是在欧洲殖民美洲期间,欧洲殖民者将疟疾传播给美洲土著人民。此外,美国恶性疟原虫与现代非洲寄生虫基因表现出很强的相似性,由此推断,很可能是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导致了这种寄生虫在大西洋区域的传播。Pere Gelabert等人通过重建疟原虫线粒体基因组序列,对欧洲间日疟原虫线粒体DNA基因组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该欧洲分支与当今南美洲最常见的单倍型密切相关,支持疟疾可能在后哥伦布时代人群互动过程中由欧洲传入美洲这一假说。欧洲恶性疟原虫线粒体DNA还与当今的印度菌株存在关联,显示出疟疾在人类历史上复杂的分化发展与传播互动。重建古代疟原虫基因组的能力,也为今后研究人类历史上疟疾寄生虫的起源、传播、进化和文化影响奠定了基础。
古DNA研究还探讨了疟疾对人类遗传基因的影响。许多抗疟等位基因早在农业出现前就已存在,由于部分基因还与其他免疫应激反应相关,无法确定疟疾是否为致病因子。与镰状细胞性贫血相关的血红蛋白S变异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G6PD)缺乏症等变异被认为有助于人类对抗疟疾,在疟疾大流行地区,自然选择可能促进了这些遗传变异的频率增加。这些遗传适应性的研究不仅帮助现代人理解疟疾如何在历史上的长期互动中塑造了人类基因组,还为现代疟疾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信息。
古分子研究已经证实了通过人类骨骼遗骸可以重构疟原虫的线粒体与核基因组,获悉全基因组数据,为今后研究人类历史上疟疾寄生虫的起源、传播、进化和文化影响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讨论了疟疾的起源与流行、传播途径及疟原虫演化与人类基因突变的复杂关系等重要问题。然而,在研究材料上,地中海地区作为历史上疟疾最猖獗的区域,由于温暖的环境条件不利于DNA保存,其古代基因组数据较为匮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代疟疾研究的开展。目前,疟原虫自身的演化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关系等话题中仍有多种假说共存,各种类疟原虫之间的复杂关系尚不明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支持。
(三)病毒性疾病
古DNA技术在病毒性疾病研究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古代流感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的演化历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研究不仅为现代人提供了关于古代病毒流行病学的重要数据,还增进了现代人对历史进程中病毒与人类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1. 流感。
流感即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引起的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甲型流感的宿主范围广,包含猪、禽类等长期融入人类生活的动物,可在人与动物间传播,且具有高变异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较大。临床观察表明重症甲型流感患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且肺炎是流感患者最常见的继发症,发展至重症时致死率较高。流感病毒作为全球大流行病的病原体,其历史传播和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根据中医文献记载推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可能已经对流感有一定的认识,外国历史文献中最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412年的希腊。学界公认首次流感大流行发生于1580年,遵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传播路径,而自公元1590年以来可能发生了10至13次流感大流行。
通过应用古DNA技术,研究人员能够从保存下来的样本中重建流感病毒的遗传史。Taubenberger等人通过对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的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与系统发育分析,检测到了与现代高致病性禽流感毒株H5N1相似的聚合酶蛋白氨基酸变化。另一研究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当PB2、PA和NP蛋白来自人源病毒时,禽源PB1蛋白仍表现出最强的体外转录活性。由此,研究者提出1918年大流感并非像1957年和1968年大流行那样由重配毒株引起,而是禽流感病毒经过适应性进化感染人类,重配获得或是直接来自禽流感病毒的禽源PB1蛋白可能赋予了三次大流行的流感病毒复制优势,进一步提升了流感病毒的致病性。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流感病毒的历史传播和病毒对宿主的适应过程,还为现代流感病毒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尽管流感应该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发生多次大流行,目前流感仅能追溯至百年前,更早时期的资料较为模糊,主要依赖文献记载,缺乏科学实证。当下古分子研究关注的流感严格意义上发生于近代。
2. 乙型肝炎。
肝炎同样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中乙型肝炎是肝细胞癌的第二大致癌因素,由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引起,这也是导致人类肝炎的主要病原体,可由母婴传播或经血液和生殖器分泌液传播。
HBV的历史分布和演化一直是古代疾病研究的重点,其起源很可能与远古时期频繁的跨物种传播有关。通过对古代HBV患者的DNA进行测序,研究人员能够追溯该病毒的遗传变异和演化路径。关于HBV在人类中的起源这一话题,学界提出非洲和美洲两种起源假说。
几乎所有HBV基因型都有悠久历史,共同祖先可追溯至约12000年前,目前在俄罗斯和匈牙利发现了距今4300年的A基因型,D基因型古代样本均来自中亚,HBV的传播可能主要通过欧亚大陆人类大迁徙实现。具体来说,研究人员从亚欧大陆和美洲人类骨骼遗骸中提取到了长时段的HBV基因数据,将所有基因型最晚近的共同祖先追溯至距今约20000年至12000年前。Mühlemann等人分析了青铜时代至中世纪的HBV患者基因组,发现在非洲和亚洲常见的基因型以及一个印度亚基因型在欧亚大陆早已存在,从古代和现代HBV基因型中观察到的时空分布与这一时期人类大迁徙的历史记载吻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HBV在古代欧亚大陆的遗传多样性和演化历史以及欧亚大陆间人口的流动。此外,HBV的某些基因型可能与特定的地理区域或人群有关,构建完整传播网络还有待未来更多古DNA研究结果的支持。
经过数十年的古分子研究,HBV多种基因型的古老性已被考古发现与古分子研究证实,长期跟随人类大迁徙的传播网络初步构建。然而,HBV的起源与进化规律等诸多重要问题都存在矛盾的证据或不同的假说,亟需寻求更多确凿证据进行验证。
古分子研究突破了传统考古学研究和体质特征观察对少量个体的初步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人类,能够揭示疾病致病原理,揭示仅凭现代序列难以体现的病原体进化复杂性,追溯病原体的传播,探寻其与人类的复杂互动。
随着提取和分析技术的不断提升,10万年内的人类和病原体的遗传研究在未来将会越来越普遍。国内古分子研究在探究古代疾病进而解析古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演化进程方面仍有巨大潜力。
四、多学科研究范式下的古代疾病
古代疾病研究始终面临证据碎片化、疾病表现复杂性等诸多挑战,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难以全面且准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在此背景下,多学科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古代疾病研究的核心路径。该范式整合传统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不仅能够从骨骼病变等体质特征中获取直观信息,还能借助古 DNA 分析、蛋白质检测等前沿技术深入探究疾病在分子层面的发作机制、演化轨迹以及传播路径。无论解析代谢性疾病的致病原理,还是诊断骨骼特异性感染并构建疾病时空框架,多学科研究范式均展现出显著优势,有助于系统理解古代疾病的出现、发展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代谢性疾病
在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代谢性疾病始终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部分代谢性疾病会产生明显的骨骼病变,同时也和个体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如佩吉特骨病和软骨发育不全性侏儒症两大代谢性骨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传统体质特征和古分子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范式可以更准确地揭示该类代谢性疾病的致病原理。
1. 佩吉特骨病。
佩吉特骨病(Paget disease of bone,PDB)又称变形性骨炎,是一种慢性骨代谢疾病,其病理机制在细胞层面表现为破骨细胞增大、增多,同时伴随成骨细胞增加且矿化不良,致使骨形成加快6至7倍。这种代谢异常会导致新骨混乱,表现为骨骼外观增大、外表坚硬、但骨质量较差的病症,多累及盆骨、颅骨、长骨等骨骼,并且极易引发骨折、骨肉瘤或关节炎等并发症。PDB的病因尚不明晰,早期认为佩吉特骨病或与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有关,现代遗传学研究表明PDB有家族遗传倾向,患者的CSF1、OPTN和TNFRSF11A三种基因更易出现缺陷。
较早的PDB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的法国与意大利,欧洲地区不断有历史时期人骨证据出土,而亚洲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病例的发现与报道均较少。在欧洲地区,英国诺顿修道院遗址出土的多具中世纪成人骨骼与现代PDB具有相似的骨骼病理特征,且古DNA分析显示miR-16表达水平与现代病例一致,由此判断古代样本应罹患PDB。与现代PDB相比,中世纪PDB患者骨骼呈现的病理变化更多样,平均发病年龄更低,且发生病变的骨骼比例较高,可能由特殊生活环境或遗传因素所导致。蛋白质检测结果显示p62蛋白可能在C末端泛素结合结构域发生修饰,导致成骨细胞异常活跃,进而影响骨骼发育,这一发现为PDB这一疾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见解。
目前,有关古代PDB的多学科研究能够通过体质特征与核酸双重证据实现PDB的精确诊断,初步构建PDB的历史分布,比较PDB在古代特定时期与现代发展的差异,发现古代PDB在分子层面的发病机制。针对PDB等人畜共患或与动物存在一定关联的疾病,若能综合考量各类证据类型,对人类与动物骨骼遗存开展古病理学与古分子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复杂病症的认知。若能在目前病例较少的亚洲地区发现更多病例,也将丰富人类对PDB的认知。
2. 软骨发育不全。
侏儒症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一种代谢性疾病,软骨发育不全(Achondroplasia,ACH)是侏儒症的一种类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现代医学观察显示约80%患儿由新发变异引起,约20%是由家族遗传所致。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3(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3,FGFR3)基因(OMIM#134934)是其主要致病基因,c.1138G>A(p. Gly380Arg)和c.1138G>C(p. Gly380Arg)是最常见的2种致病性变异。软骨发育不全患者在外观上具有显著的体质特征,与人骨遗骸相关的典型临床表现为非匀称性身材矮小,身材明显缩短,且四肢较短,活体中也伴随有前额突出和面中部后缩,呈现特殊的面部形态,同时存在罹患多系统并发症的风险,患者平均寿命缩短10年。
软骨发育不全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根据历史记载和艺术作品的相关描绘,古代埃及应有不少相关病例,目前较早的骨骼证据来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法国。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对软骨发育不全的认识,Lucas L. Boer等学者在一例180年前软骨发育不全骨骼样本中检测到了FGFR3基因编码的杂合子G1138A变异,以历史证据有力证实了该病症是由基因FGFR3的致病性错义突变引起。对于体质特征不典型或不明确的古代人类骨骼遗存,通过古分子研究证实其携带FGFR3基因特定的致病性变异可以辅助诊断。
多学科方法在古代ACH研究中具有巨大运用潜力。体质人类学与古分子研究可以实现ACH的精确诊断,并进一步从分子层面探究致病原理。而ACH作为考古环境中最常见的发育不良类型之一,根据考古背景如墓葬位置体现出的患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研究者可以推测特定时期身体缺陷对社群融入的影响,从疾病探究社会文化因素。
传统体质鉴定、古分子检测与考古学的结合能够较为准确地鉴定古代人类的代谢性疾病类型及其患病情况,尤其是遗传类代谢性疾病,补充对疾病历史的认识,探究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同时也为致病机制的探索提供古分子学方面的证据,深化现代医学与生物学对于特定疾病的了解。
(二)骨骼的特异性感染
特异性感染是指由于已知确切致病菌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骨骼的特异性感染主要包括麻风、梅毒、雅司病和结核病等。当前,针对骨骼特异性感染的研究多采用体质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
1. 麻风。
麻风(Leprosy)是一种由麻风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leprae)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可能会导致鼻腭综合征、肢骨远端溶解等独特的骨变异。在古病理学研究中,发生骨质改变的瘤型麻风病最为常见,此类患者抵抗力低,通过与环境中的病原体的长期接触,人类自身的免疫力得以增强,发展为传染性更弱的结核样型麻风。历史证据表明,麻风患者由于面部和四肢形态异常,生理与心理健康都受较大影响,但这种在历史上引发空前大恐慌与偏见的疾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推动了人类免疫力的提高。
目前,较早的麻风病骨骼证据是来自埃及三角洲地区公元前250年(托勒密时期)的四具头骨,据学者推断此时麻风病已存在多年,可能起源于非洲。目前,麻风病最初如何感染人类及其传播过程都尚无定论,根据出土骨骼信息和历史文献,有说法认为麻风病是由亚历山大东征从印度恒河流域带入地中海地区,有研究者提出麻风病可能是在殖民时期传入新大陆,也有证据表明麻风病是从亚洲传入北美。
对古代麻风的研究开始较早,早在20世纪50年代,Møller-Christensen就运用来自丹麦中世纪麻风病医院墓地的骨骼材料,揭示了当时临床医学尚未察觉的麻风病典型骨病变特征,使人们首次识别麻风病患者的骨骼变化,古病理学研究直接对现代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过去古代麻风病的研究主要依赖出土人骨的形态学分析,国内外如西安幸福林带唐代遗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县汉代墓葬、意大利公元前4—前3世纪墓地等出土的人骨遗骸中均发现麻风病例。通过这些报道发现麻风病存在的时间跨度较大,分布范围较广。近年来,古分子研究为麻风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探讨麻风病的传播路径、影响麻风分枝杆菌毒力的基因变化与麻风病在中世纪衰落之间的关联,及其与结核病“此消彼长”的科学解释。
2. 密螺旋体疾病。
梅毒(Syphilis)和雅司病(Yaws)分别由梅毒螺旋体和雅司螺旋体引起,均属于密螺旋体疾病(Treponemiasis),会使骨骼发生特异性感染,但传播方式存在差异。晚期梅毒最显著的特征是骨膜反应和胫骨重塑,同时伴有骨质破坏,在古病理研究中具有易于辨认的人体骨骼改变。
密螺旋体疾病主要存在四种起源与传播理论,其中哥伦布假说认为该疾病由美洲传至欧洲,而前哥伦布假说持相反观点;一元论认为密螺旋体疾病由一种单一的有机体引起的,受气候、社会和人口因素影响产生不同表现;菌株进化论认为约公元前15000年时密螺旋体疾病从非洲向全球传播,约公元前10000年菌株第一次发生突变,将品他病转变为雅司病,约公元前7000年左右转变为地方性梅毒,适应温暖干旱气候,从非洲一直延伸到西亚至中亚地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西南亚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演变为性病梅毒。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密螺旋体病案例来自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青海地区的卡约文化,可能伴随游牧民族从地中海或中东地区与欧亚草原传播而来,正处菌株进化论支持的流行区最东北部。而性病梅毒在唐代就已存在于中国。
雅司病、性病梅毒和地方性梅毒三类疾病对骨骼造成的损伤范围和特点较为相似,在部分情况下仅针对病变的骨骼标本很难区分到底是由哪类疾病所造成,而多学科研究能够实现精细诊断。Kerttu Majander等学者从15世纪欧洲人类遗骸中提取到四个古代梅毒螺旋体基因组,其中两个属于梅毒螺旋体的变异范围内,另两个为近似雅司螺旋体的菌株,这显示古代欧洲梅毒螺旋体基因组中存在高度多样性,并证实了欧洲存在地方性梅毒。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普及还能够构建疾病发展的时空框架。根据分子钟推算,密螺旋体家族最晚近的共同祖先TMRCA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均发现了不同时期密螺旋体疾病古病理的实证案例,其传播可能与各地人群迁徙存在密切关系。根据测年结果,梅毒存在于接触新大陆前的欧洲,因此可能起源于旧大陆地区,近年来的古分子研究结果逐渐推翻了梅毒是由哥伦布从美洲带到欧洲的传播路径假设。
多种起源假说均支持密螺旋体疾病应非我国起源,国内对古代密螺旋体疾病的发现和报道较少,史前、汉晋、南北朝、唐宋均存在可能的个例,部分无法细分具体类型。研究方向主要为通过体质特征诊断密螺旋体疾病,并根据时代背景和地区特征的考古学或历史学讨论,认为其随外来移民和商业活动等传播,少量多学科研究依托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古环境学方法,未见融合古分子视角的相关研究。
在古籍中可见类似密螺旋体疾病的相关记载,且骨骼遗存表明密螺旋体疾病在青铜时代已经进入中国,因而我国作为重要的被传播地,研究国内古代密螺旋体疾病对了解该疾病的演化与传播具有一定意义。包含古分子研究的多学科研究范式可以确诊具体类型,讨论个体所属人种与来源,在全球视角下的密螺旋体疾病研究中对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分析结果作出重要补充,验证疾病起源假说。
3. 结核病。
结核病(Tuberculosis,TB),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引发的慢性传染病,是人属疾病中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至今仍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主要传染病。人体感染结核主要是由人型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和牛型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bovis)所致。受限于考古材料中软组织遗存的稀缺性,古代疾病研究在体质特征方面主要通过骨骼病变探究骨结核的患病情况。骨结核一般是继发病灶或是局部表现,较为罕见,仅约3%至5%的结核病病例会发生骨骼病变。脊柱病变占骨骼病变的半数左右,典型体质特征为椎体破坏,形成孔洞,导致受累椎体塌陷、相邻椎体粘连的骨骼形态变化。此外,关节干酪样变性、肋骨病变、胸膜钙化、颅内新骨形成等病变也可能与骨结核存在关联。
早期对结核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形态观察,结合放射学和组织学方法进行,总结出结核病的诊断标准,奠定了结核病古病理研究的基础。随着古分子研究的进步与古代病原体DNA的发现,对结核病的古病理研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结核分枝杆菌进化理论等得到突破,在揭示结核病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学科研究表明,与结核病相关的基因变异可追溯到30000年前,而最早的病例来自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以色列新石器遗址,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都有大量古代结核病的报道和研究,其在亚欧大陆的传播或与人群迁徙存在关联。具体而言,通过对1013个古代欧洲人群基因组的大型数据集进行分析,Gaspard Kerner等人发现了一个与TB易感性相关的基因变异——TYK2 P1104A。研究表明,TYK2 P1104A变异体可以追溯到约30,000年前的西欧亚人群的共同祖先。随着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农民和亚欧大陆牧民大规模迁入欧洲,变异体出现频率显著波动,其中在青铜时代P1104A变异体的频率显著增加,但在铁器时代之后,其频率急剧下降,这表明在过去2000年中,这一变异体受到了强烈的负向选择,导致纯合子的相对适应度降低了20%,证实了这一时期结核病给欧洲人群健康带来的巨大负担。这一研究不仅提供了TB在历史上流行的直接证据,还揭示了人类对TB的遗传易感性。
目前,结核病的古分子研究在国内开展较少,国内古代结核病的诊断仍主要依靠传统体质特征分析。例如,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出土了青铜至铁器时代的2例罕见脊椎病理性损伤个体,出现较为严重的溶解性病变。根据CT和X光影像学分析及临床医学资料参考,高国帅等人推测两例个体应患脊柱结核病,认为该病感染可能与动物的驯化和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城市化发展、人口过度拥挤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缺乏古分子学证据。
由于骨骼的特异性感染不仅可以通过体质特征和DNA检测两种方法进行精确诊断,还能对传染病具体病因、病菌的传播与自身演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多学科分析方法具有巨大运用前景。纵观人类文明史,人口流动始终是传染病扩散的主要途径,微生物与人类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同步传播、改变。对骨骼特异性感染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了解病菌演化的生物学意义,也是探究古代社会文化重要手段。
麻风、密螺旋体疾病、结核病等骨骼特异性感染的多学科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但疾病的起源、传播与演化以及人类与病原体的互动等话题仍然留有巨大的讨论空间,国内学者需进一步拓展多学科尤其是古分子方面的研究。
(三)肿瘤
肿瘤可分为良性和恶性两大类。良性肿瘤往往在原发病灶独自生长,仅在局部扩散;恶性肿瘤是指原发生长物向身体其他器官无限制地局部扩散,在肿瘤发生部位可能还伴有自发性骨折。国内外古代样本中可由体质特征判断的的良性肿瘤包括骨瘤、骨样骨瘤、骨血管瘤等。骨血管瘤(Hemangiomas)为原发于骨血管的良性肿瘤,是一种掺杂于骨小梁之间的呈瘤样增生的血管组织,好发于扁骨,如脊柱、颅骨、颌骨,长骨少见,分为海绵型和毛细血管型。在考古样本中可辨别血管瘤的皮质破坏属于疾病晚期特征,多发生于老年个体,因此考古样本中呈现的骨血管瘤患病率远低于现代临床样本,如Joseph E. Molto等研究者在一具埃及地区出土的罗马时期老年女性骨骼上诊断出晚期脊柱血管瘤(Vertebral hemangiomas,VHs)。恶性肿瘤包括骨肉瘤、多发性骨髓瘤、骨转移癌等。骨转移癌(Metastatic Carcinoma)是指原发于某些器官的恶性肿瘤通过血液循环、淋巴系统或脑脊液转移到骨骼的继发性恶性肿瘤,通过再转移或直接浸润到骨骼造成骨破坏。例如张群等对宁夏石砚子墓地出土的东汉时期颅骨缺损个体开展体质观察,血管压迹的增粗和加深显示出滋养肿瘤的异常血管形态,推测个体颅骨所见的大面积骨质破坏应由颅骨转移癌所导致。
根据文字记载,肿瘤在中国可追溯至公元前16至前11世纪的殷商时期,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有骨睢(疽)及其治疗方案的记载。错构瘤在距今约5300年的仰韶文化人群中已经出现,错构瘤是一种类瘤样畸形,不是一种真性肿瘤,可归入肿瘤性疾病,表现为古代人类颅骨上常见的圆形致密骨质凸起。在真性肿瘤中,中国甘肃地区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脑肿瘤病例。在世界范围内,北欧和北非地区的古代癌症病例最多,具有生物考古证据的人类癌症病例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研究人员还在南非斯瓦特颗兰斯洞穴距今160万至180万年前的人科骨骼化石上发现了癌症痕迹,显示出人类长期的癌症史。
目前,古代肿瘤主要基于骨骼上的缺陷或肿块进行诊断。人类遗体在腐烂分解过程中会对骨骼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能出现类似癌症破坏造成的结果,抑或掩盖原发肿瘤的踪迹。此外,股骨良性增生等病症也可能会被错误诊断为肿瘤。古代人群患癌率显著低于现代人群,除诊断误差外,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其死亡年龄普遍低于现代人群癌症高发年龄段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饮食和环境因素影响,与现代社会致癌物质的普遍性存在关联。
对肿瘤的初步诊断主要依赖骨骼遗存的体质特征观察,而组织学的应用则能够实现对木乃伊样本的肿瘤诊断,拓展了对古代肿瘤类型的了解。研究者已经成功诊断出了多种良性肿瘤,包括皮肤纤维瘤、脂肪瘤、寻常疣、尖锐湿疣等。其中,尖锐湿疣是由特定类型人乳头瘤病毒(HPV)引发的外生殖器及肛周区域皮肤乳头状瘤。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多美尼克教堂中的一具16世纪女性木乃伊是来自阿拉贡王国的贵族玛丽。其外阴区的宏观体质和组织学特征显示可能存在肛门生殖器疣,结合古DNA研究,确诊感染高危型HPV 18和基因为JC9813的低致癌性HPV。阿拉贡国王费兰特一世木乃伊的组织学分析显示其患结直肠癌,DNA研究检测到结直肠癌中K-ras基因最常见的突变,可能遵循K-ras突变驱动结直肠癌的典型病理机制。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费兰特一世摄入大量肉食,高肉食摄入可能导致体内烷基化物质的增加进而刺激K-ras基因突变。恶性肿瘤的显微诊断结果以上皮性癌为主,尚未发现现代人群中常见的肺癌、肝癌、胃癌等内脏器官癌症,有待进一步研究。对古代恶性肿瘤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恶性肿瘤所致的癌症的发病机制,以更好地应对这一全球性健康危机。
对古代肿瘤的研究综合了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物学、组织学、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学、医学、历史文献与艺术作品研究等多种学科,在少数较为全面的研究案例中能够进行精确诊断和病因推测。尽管近年来已开发出多种癌症生化检测方法,但由于假阳性结果的发生率较高,这些检测手段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也较为局限,不能作为干尸材料的诊断依据。组织学的运用对古代人类遗骸的保存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此类报道主要集中于埃及,智利和意大利可见少量。尽管适用样本较为有限,但组织学为研究古代人类疾病提供了全新思路,古代肿瘤的研究案例也是目前综合性最强的多学科研究范式。
当前,古代疾病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路径,可综合运用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物学、组织学、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学、医学及历史文献与艺术作品研究等多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文理结合的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应用潜力与学术价值已经在古代代谢性疾病、骨骼特异性感染和肿瘤的研究中得到了初步验证,是未来古代疾病研究的重要方向。
五、结语
古代疾病研究作为生物人类学、考古学与分子生物学深度交叉的前沿领域,其学科价值早已超越技术方法迭代的表层范畴,迈入以认知重塑为核心的新阶段。体质特征分析、古分子研究与多学科范式的递进融合,不仅为识别古代疾病类型、追溯病原体演化提供了更精准的工具,更从根本上打破了疾病史与人类文明史的割裂壁垒,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疾病作为隐形变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深层作用,彻底革新了对健康、疾病与文明互动关系的传统认知。
体质特征分析的价值重构,在于其从疾病诊断工具转变为解读古代社会的生物学密码。通过代谢性疾病(如骨质疏松症、氟骨症)的群体分布差异,我们得以关联农业转型对饮食结构的改变、社会阶层对营养资源的分配(如古埃及不同阶层人群的骨密度差异);通过骨骼感染(如骨关节病、骨膜炎)与创伤的类型分析,我们能还原古代人群的职业分工(如殷墟铸铜人群的上肢骨关节炎高发)、暴力冲突模式(如青铜时代农牧交错带的箭矢创伤),甚至生计模式的区域分化(如贝丘遗址人群的跪距面与渔猎活动的关联)。这种从骨骼痕迹到社会图景的认知跃迁,使古代健康史不再是孤立的病理记录,而是嵌入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可量化、可验证的生物学实证。
古分子研究的突破性贡献,则在于其打破了病原体演化与人类历史的时空壁垒,首次从分子层面证实疾病是塑造人群迁徙与文明格局的核心力量。对鼠疫耶尔森氏菌基因组的重建,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该病原体通过欧亚贸易网络扩散的轨迹,印证了物质交流与疾病传播同步发生的历史逻辑,填补了史前流行病如何影响人口结构与文化更替的认知空白;对疟疾、乙型肝炎病毒的古 DNA 分析,不仅追溯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欧亚人群迁徙中的病原体传播路径,更发现了人类与病原体的基因共演化证据(如抗疟基因的自然选择),使我们意识到健康适应本身就是人类演化的重要驱动力—这种认知突破,让疾病史从边缘学科话题跃升为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维度之一。而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成熟,则标志着古代疾病研究进入系统阐释文明互动的新阶段。通过整合体质人类学的病理观察、古分子生物学的基因证据、稳定同位素的饮食分析与考古学的文化背景等,我们得以搭建疾病、社会与文明的完整认知链条,例如对软骨发育不全的研究,不仅通过FGFR3基因变异确诊疾病,更结合墓葬位置、社群布局推测古代社会对身体缺陷的接纳程度;对肿瘤的多学科分析,通过组织学、古DNA与同位素结合,揭示了饮食结构(如高肉食摄入)与基因变异(如 K-ras 突变)的关联,为理解古代生活方式如何影响疾病发生提供了立体视角。这种跨学科融合,彻底超越了单一学科的局限,使疾病如何参与文明演进的深层探讨成为可能。
当前国内外研究的核心差距,并非技术应用的数量差异,而是认知层面的深度落差。国内研究仍以体质人类学的描述性分析为主,古分子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多停留在个案层面,尚未充分依托技术优势开展疾病、社会与文明互动的系统性研究。未来的研究需从三方面着力突破:其一,进一步细化体质特征分析标准,完善古代疾病的诊断体系,提升传统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其二,加强骨骼材料的古分子研究,以获得对古代疾病、病因和病史等更全面的了解,为研究古代人类健康状况和致病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其三,在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探索古代疾病的多学科研究范式,以体质特征为主、古分子为辅诊断疾病类型,依托古分子研究探索发病机制及疾病与人类在分子层面的互动关系,融合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科技考古手段和考古背景及文献材料等传统考古信息,探讨疾病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目前古代疾病研究起步较晚的亚洲地区也在逐步建立区域数据库,未来通过完善与整合不同时空框架下的古代疾病数据,结合多学科研究范式,不仅有望进一步识别疾病感染与传播的共性规律及区域差异,构建全球尺度的疾病发展史,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开辟新道路,同时深化对现代疾病的了解程度,为现代社会应对各类疾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历史经验与科学启示。
转自《学术月刊》2025年第11期